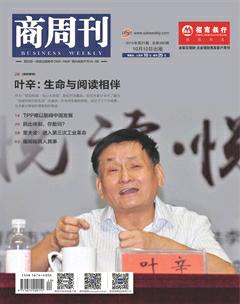琴界郎中
趙艷
有人說老胡無師自通是天才,短短五年就能做出音質—流的提琴來。但在老胡看來,這種一氣呵成全是因為有著前40年的經歷。50歲,正是制琴師黃金階段的開始,“急功近利的人當不了制琴師”,老胡說。
制琴師老胡有一雙很神奇的手。任何琴到他手里一掂量,就算是閉上眼,他也能把這把琴的質地和出處說個八九不離十。都說外行人看熱鬧,內行人看門道,尤其是制琴這么復雜的工藝,有些東西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像“用手識琴”的這招兒,在別人看來神奇,但對老胡來說,不過是制琴師的基本功。
為了揭開制琴師這個職業的神秘面紗,也想親眼看看一把提琴是如果煉成的,我們去了廣西路上的那棟紅房子,也就是老胡和另一個同行小韓開的“提琴門診”里一探究竟。
自封琴界郎中,修琴之前要先學做琴
提琴門診,是老胡和小韓給自己工作室起的諧號,而老胡就自封為“琴醫”,給來自天南地北的“病號們”治病。拉琴的人都知道,要修琴就必須先會做琴,否則琴病了后你怎么知道是該看外科還是內科?我們去的時候,老胡正系著厚厚的圍裙趴在工作臺上刮著提琴面板做調音,他一邊刮一邊解釋著:“這活得一口氣干完,要是歇會兒再做感覺就不對了”。
緊湊的工作室里堆放著各種型號的提琴,也有一些半成品在晾干。老胡對提琴的制作技藝已經到了癡迷的程度,除了吃飯睡覺,其他時間都在琢磨跟琴有關的事兒。
老胡做把琴需要差不多一個月,但前期構思的時間卻是做琴的好幾倍。當然,純手工打造的作品可比工廠里批量生產的機械琴品質高多了。當我跟他說有位意大利朋友很喜歡他的東西時,老胡哈哈大笑,他說:“全國現在有不少制琴師,但能把大中小三種提琴都做全聲音還配套的,大概只有我一個。我正在研究如何讓琴漆通透性更強,要是能成功,會給提琴的外觀工藝帶來巨大改變!”
確實,在做琴這個問題上,老胡的語氣里總有一股子壓不住的自信與狂放。
既然人家不讓我摸,那我就自己做一把
老胡的背有些彎了,做活的時候是一副地道的工匠模樣。100多道工序的制琴流程十分繁瑣,單就刮面板就需要三四天的時間。之所以迷上這么復雜的手藝,老胡說都是源自年輕時的一件憾事。
50年代人的經歷多帶有時代印記,像老胡這樣,小學沒上完就出來學木工,前后跟了四個師傅。20歲不到,老胡的手藝就在街坊鄰居中聞名,桌椅板凳無論啥樣,只要他看過、摸過后都能做得出來。但在17歲那年,他卻遇到了自己第一件不能做的東西。
當時的隔壁鄰居家住著三兄弟,老大、老三學琴,老二是木工。有一天,老大帶了只沒刷漆的小提琴去鄰居家串門,老胡也在。聽老大說這琴是二弟做的時候,老胡頓生好奇,原來小提琴還可以自己做啊?他立刻伸出手想去摸—下,卻被老大一把推開,怕他給弄壞。一直到后來搬家,老胡都沒機會摸到這把琴。這個遺憾,又或者說是不甘心,讓年輕的老胡埋下了做琴的念頭。
真正決定要做了,則是在青島首屆國際小提琴的一次名琴展上。同樣的,擺在展廳里的名琴更不能讓人隨便碰。老胡跑了好幾趟,跟工作人員都混熟了,帶上白手套后人家才破例讓他摸了—下。“握到琴的一刻時間都靜止了,”老胡形容他那天的感覺。同時,他也被手中琴的輕快閃了—下,因為世界名琴的質感跟他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樣。就在這一刻,深埋了幾十年的那個想法突然就爆發了——我要做琴!老胡對自己說道。從琴展回來,他立刻找到了曾經一起開琴行賣琴的小韓商量這事。于是,廣西路上的這棟紅房子就成了他倆的工作室,制琴師的生涯正式啟幕。
姜是老的辣,制琴師50歲正當青春年華
木工出身的人,照著圖紙作出一把像模像樣的琴不難,難的是怎么才能雕刻出大師級的聲音來。一些琴師做了幾十年的琴也賣不出高價來,都是因為他們的作品雖有形,卻缺乏魂。
老胡制琴的路子跟別人不同,他從未解剖過任何琴,卻像有一對“透視眼”似的對提琴內部看得一清二楚;他沒有學過一天琴,完全不懂音譜,卻能分辨出不同質地高低好壞的琴聲來。第一把琴,老胡構思了半年多才動手。第二把琴,也隔了好幾個月才出爐。魂,是老胡想賦予提琴的一種內在。他要讓拉琴的人一拿到他的作品,就驚嘆這是把好琴。
50歲才開始制琴,跟那些音樂學院畢業的年輕琴師相比有何優勢?老胡笑而不語。他從木工出身然后進單位,當領導,直到退休,50歲之前的生活看起來跟制琴毫無關系,卻又好像冥冥中自有安排。
1976年唐山大地震,青島市組織各單位派人學習抗災抗震,老胡記了一本子的地震原理回來;然后他又自學了醫學,對化學也略知一二,觀摩了很多工種的流程。上班那些年,他有課就聽,就講座就去,積攢了不少的零散知識。本以為就是些打發時間的愛好,卻像是上天提前做好的鋪墊,讓老胡后來的制琴生涯豁然開朗。
做琴的木工活就不必說了,老胡很嫻熟;醫學解剖中的透視原理,被他用來分析琴的內部構造;而琴弦拉動時的震動,則跟地震有著相同的原理,又被老胡拿來活學活用;決定提琴音質的木材和琴漆,又被含碳量這樣的化學問題所牽制……老胡從前積淀下來的各種知識,全都派上了用場。
有人說老胡無師自通是天才,短短5年就能做出音質一流的提琴來。但在老胡看來,這種一氣呵成全是因為有著前40年的經歷。制琴師的工作要用到很多學科的技術,沒有一定的年齡沉淀是無法擔當的。50歲,正是制琴師黃金階段的開始,老胡最崇拜的一位意大利巨匠級制琴大師就一直做到了80歲。“急功近利的人當不了制琴師”,老胡說道。因為這是在創造藝術品,琴存在的時間越久,越能顯出好音色,而這種聲音,可以子子孫孫一直傳承下去。
不迷信權威,就愛干別人不敢干的事兒
帶徒弟時,老胡一點也不吝嗇將自己的技術傳授給外人。只是哪一刀決定聲音的穿透力?哪一鑿決定音色的亮度?在削鑿之間如何依靠豐富的經驗來判斷木料的最佳厚度與弧度走勢?如何借助刮片砂紙的打磨把面板提煉得登峰造極?就只可意會而不可言傳了,并不是每個人都有資質成為一個好的制琴師
自學成才的老胡,往往不給行業的權威者們面子。一聽國內外的大師講制琴,或者看一些大師寫的書,他就會嘗試證明和推翻一些東西。“制琴這行沒有固定答案,一直都是后人研究前人,然后再推陳出新。”老胡的自信很有底氣,從第一把琴到現在,每做一把他都會用新路子去嘗試。前陣子,他跟小韓一起把三種類型的提琴都做了一遍,還拿給專業人士試了下,三部琴在音區上的完美銜接被高度肯定。而這種音色抱團的全系列提琴,正是演奏團所需要的。
老胡在做琴之前就知道,目前國內大多數的手工制琴師都只做一種型號,能做全系列提琴的鳳毛麟角,更別說還要將三種音區順暢銜接了,他就是愛干別人不敢想的事兒。
在制琴最初,老胡就篤信自己的琴將來會賣到—萬元以上。有一回,一個朋友買了把價值—萬七的意大利名琴,沒過多久,老胡就把自己剛做好的琴讓這位朋友試了試,朋友直接驚呼怎么比自己那把意大利琴還好?老胡的預言實現了,現在,從他手里出去的每把琴都價值不菲,而購買琴的客人,也從青島本土延伸到了日本、加拿大。
在粘好琴頭,壓上琴碼后,耗時近一個月的提琴制作就接近尾聲。這時的老胡最喜歡悠哉游哉地捧著一杯茶,蹺腿坐在門前的日光里曬太陽,構思他的下一個作品,或是對著那些慕名而來的尋琴者開出一個不算離譜的手工品價格。而那些人,要買的也正是這個差別,不是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