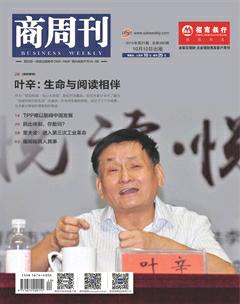分享經濟攪動未來
李菲
在這個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日益發達的時代,“分享經濟”正大行其道。它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還在改變人們的工作,更攪動著未來。
在擁擠的早晚高峰期,用手機輕點Uber,享受比出租車更優雅的出行;出門旅行時,通過Airbnb在目的地找到稱心如意的房子,體驗一段美妙的租房體驗;不管是求學謀職,還是創業創新,通過“在行”求助,都會有人為你出謀劃策,給予私人定制的選擇建議……在這個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日益發達的時代,“分享經濟”正大行其道。它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還在改變人們的工作,更攪動著未來。
在中國經濟發展探索新動力的時候,資源分享催生出巨大發展機遇。9月10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出席夏季達沃斯開幕式致辭中特別指出,雙創是發展分享經濟的重要理念,目前全球分享經濟呈快速發展態勢,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新路子,通過分享、協作方式搞創業創新,門檻更低,成本更小,速度更快,這有利于拓展我國分享經濟的新領域,讓更多人參與進來。作為一種新興經濟形態,分享經濟首次獲得政府層面的正面首肯,也對近年悄然興起的國內分享經濟模式的探索者、創業者和實踐者產生了莫大的鼓勵。種種跡象顯示,分享經濟“風口”已經來臨。
下一個風口
說起分享經濟,其實并不算是一個全新的概念。早在1978年,美國得克薩斯州立大學社會學教授費爾遜和伊利諾伊大學社會學教授斯潘思就提出一種閑時分享自己汽車的模式,“分享經濟”由此為人知曉。但起初并未吸引太大的關注,直到近幾年才流行起來。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等互聯網技術的發展,讓這種新形態下的分享模式煥發了蓬勃的生命力。
與以往傳統的商品購買方式和服務不同,人們開始在互聯網上尋找商品分享服務,投入分享型企業的懷抱,以更加方便、高效,而且價格低廉的新方式來滿足自己的需求。它給傳統行業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滲透速度和拓展寬度一次又一次刷新人們的認知。
同時,這種人人參與的模式也在讓傳統的企業和消費者之間的界限不斷弱化,實現了消費者的角色轉變。當下,消費者開始同時扮演著創造者、生產者、財務專家和旅店經營者等角色
如今的“分享經濟”早已遠遠超出其原本內涵。首都經貿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陳及認為,“互聯網+”的模式是通過互聯網與傳統行業結合,為行業發展注入新的動力。而分享經濟則改變了傳統產業的運行環境,通過社會存量資源調整實現了產品和服務的最大程度利用,改變了以往不斷通過新的投入刺激經濟增長的思路,既節約資源、保護環境,還創造新的價值。
毫無疑問,“分享經濟”有著推動各行業業務發展的巨大潛力。社會化媒體策略專家、CrowdCompanies的創始人耶利米·歐陽研究發現,目前分享經濟類的企業規模約為170億美元,它們擁有6萬名雇員。既有從舊有技術的昏暗迷霧中所誕生的古老eBay,也包括相對新興的網站Etsy、Chegg、WeWork、Airbnb和Uber等。令人驚訝的是,它們中的相當一部分誕生于2008年世界經濟低谷時期,最初依靠來自朋友和家人的投資,然后在獲得市場的青睞并開始尋找傳統投資者,并在幾年后終于出現了投資熱潮,迅速成長為成資產數十億美元級別的公司。
開源經濟新常態
事實上,分享經濟和社會經濟總量之間,呈現的是一種正比關系。只有在經濟發展越好時,有了更多過剩的產能,人們才愿意將自身閑置的資源、物品拿出來共享。而當分享經濟走向繁榮時,科學、高效的資源分配也會促使社會經濟朝著積極良性的方向發展。
空中食宿Airbnb公司首席執行官最初創立該公司時,只是因為沒有足夠的錢付房租,于是把空閑房間出租給了別人。這卻孕育了一個更大的創意,開拓了一種全新的賺錢方式。現在,Airbnb用戶只需通過網絡或手機應用程序就能完成發布、搜索度假房屋租賃信息并實現在線預定的程序。目前,Airbnb用戶遍布190個國家近34000個城市,已經有了100萬個被提供住所,2600萬房客,最高一晚的房客達到55萬。
作為打車應用的鼻祖,Uber同樣也是分享經濟的典型代表。它最大的吸引力就在于靈活性:幾乎任何人都可以隨時參與,并受益其中。很多的Uber司機都有一份穩定收入的長期工作。對他們來說,偶爾當一下陌生人的司機,除了可以獲取一筆額外的收益,也是一種放松休閑乃至社交的方式。
同為打車應用的Lyft的聯合創始人和首席執行官洛根·格林認為:“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越來越少。每個人都在更努力地工作,而科技到目前為止使個體之間變得更為孤立。社會上對真實可靠、個性化的產品需求很高。這些穿梭于城市之中的短途旅程,能在人與人之間建立起極為難得的聯系。”
當然,分享經濟絕不僅僅只能應用在出租車或房間出租領域里,它的觸角正在延伸到更多的行業和用戶群體,已經從最初的共享物實體物品(比如住所和車),逐漸發展到共享虛擬的東西。
在中國,分享經濟的發展也是方興未艾,從如火如荼的打車行業和旅游領域發起,先后崛起了滴滴打車、快的打車、木鳥短租、住百家等,后又進軍家政、二手市場、美容、家庭輔導、創意服務等領域。
果殼網的姬十三成立的“在行”,算得上是一個較為成功的案例。在“在行”,任何一個在某方面有所建樹或有所見解的人都可以注冊成為行家,這些行家是自由的、不依附于任何培訓機構的,利用業余時間展開培訓工作。約見效果被分為三個等級——答疑解惑、出謀劃策、解決問題,玩得就是謀略和想法。
爭辯中的前行
當人們滿懷欣喜去擁抱共享經濟時代來臨時,又必須用敬畏的眼光看到分享經濟的未來。
我們已經看到,全球范圍內的傳統行業對這類新興競爭對手發起了監管戰爭。以拼車行業為例,出租車公司試圖合力“封殺”拼車企業,提醒監管當局這類企業的業務模式可能違反了法規。像在中國,滴滴打車曾經被北京、上海、濟南、青島、淄博、沈陽、南京、重慶、天津、杭州等十個城市叫停,并把專車定位成“黑車”;在德國法蘭克福,Uber的運營模式甚至直接被判定為非法。
分享經濟要能夠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不可避免地要大規模的商業化并改造傳統經濟結構。
首先,足夠基數的用戶與豐富的資源,是分享經濟的基本條件。只有當用戶的可選擇性足夠多,閑置的資源極大豐富,才會產生差異化,更好地滿足用戶的個性化需求反之就會消耗多余的成本,得不償失。在日益豐富的資源和更加普及互聯網環境中,人們也要習慣新的觀念:某些東西其實可以不必“占有”,在需要時擁有“使用權”即可,在互聯網上既能尋找也可以分享閑置物品的信息,需求方據此發現供應方信息,再在第三方撮合下實現交易。
鑒于分享經濟是在陌生的個體之間通過第三方平臺進行物品租賃和交換,除了信息分享等網絡技術外,更加公平的競爭環境、成熟的社會信用體系和社會契約精神的建立也是關鍵因素。以往,將房子出租給一個陌生人是一種無法想象的事情。但是Airbnbhost的評價讓人們相互間產生信任,促成了正面、積極的大眾共享合作性消費。
正如美國著名社會學家杰里米·里夫金所言,在新興的協同共享中,創新和創造力的民主化正在孵化一種新的激勵機制,我們正在進入一個部分超越市場的世界,我們需要學習如何在一個相互依存性越來越強的全球協同共享中共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