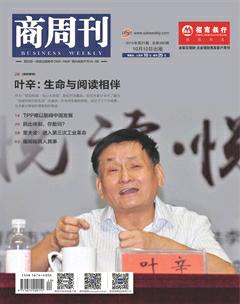跳出體制,你敢嗎?
王雅潔
跳出體制的實質,實際上與普通的擇業無異,不過是對自己未來規劃的一個選擇。而“跳”的意義,代表著“官本位”不再是束縛心靈的枷鎖,社會理念越來越趨于健康、開放、多元。
近幾年,“跳出體制”開始成為輿論熱詞。《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對2002人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體制內的吸引力,正在降低,有82%的受訪者認為體制內工作的優勢在削弱,有過半數的受訪者找工作時,已無所謂體制內外。對比起前幾年同類調查統計的結果,不難發現受訪者傾向于去體制外的比例越來越大。
最近發生的一些事情,似乎也在為數據提供例證:郎永淳、張泉靈、李小萌等著名主持人相繼離開央視。回歸家庭的“暖男”解釋、跳出魚缸的思維解放,一時間備受追捧。與此同時,濟寧市原市長梅永紅辭職加入深圳華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市浦東新區副區長丁磊掛冠而去加盟樂視。有媒體統計,十八大后,已經有數十位官員辭職,多數下海經商。官員的下海,則引來了更多解讀。這一次的跳出,仿佛不再是個體偶然的決定,而有著更多考量和意義,所以跳出體制,你真的敢嗎?
政治經濟背景的影響
歷史不是簡單的重復,但卻有著驚人的相似。上世紀80年代,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大量計劃體制內的官員紛紛下海經商,出現第一輪官員“下海”潮;上世紀90年代鄧小平視察南方加快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民營企業政治地位提高為新一輪官員下海創造條件。他們中的很多人成長為一代企業家,不僅在披荊斬棘中成就了自己的企業,也推動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被后人譽為“92派”;此外,2000年左右,中國政府機構改革與人員精簡力度空前,加入世貿組織推動經濟快速增長,再次誘發了第三輪官員下海現象的出現。回顧歷史不難發現,跳出體制與政治經濟背景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這一次對體制的反叛,又源自什么呢?青島市委黨校教授劉文儉認為:“一方面,確實有市場原因,在創新、創業的大潮下,資本正經歷一輪新的重新分配過程,市場上造富神話不斷出現,吸引了很多人下海搏擊。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體制內情況也在發生變化,因為之前這么多人考公務員,看到的不僅是工資,而是灰色收入,這是權力的作用。現在將權力關進制度籠子之后,因著人的趨利性,就會越發理性地考量一個職位的價值。所以,現在出現的公務員熱降溫,我覺得是正常的。”正如《人民日報》刊登的“人民時評”所言:“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重拳反腐、狠抓作風,黨內風氣為之一新,公款吃喝、濫發福利等現象變少了,官商勾結、左右逢源的空間大大縮小。如果期待體制內總有一些說不清道不明的福利,一些運作事情的空間,一些不為外人道的好處,那么這種變化無疑會導致吸引力下降。在某種程度上,近三年來政治風氣的變化,打破了這種對體制內的幻想。”
政府點贊
雖然跳出體制后的前景未卜,但可以看到的是,政府已經投了贊成票。著名中國問題專家鄭永年認為,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和增長進入了“新常態”。盡管經濟高增長階段已經過去,不可避免進入中速增長階段,但要實現和維持中速增長并不容易。政府要通過“眾創”運動來推動新的創業潮,培養新一代企業家。中國社會目前的企業家主體,是在1980年代改革開放之后,尤其是1990年代的下海潮之后成長起來的。這兩個企業家群體現在已經上了年紀,他們中的很多人已經不再有創業的沖動,而逐漸演變為消費群體。也有些則因為知識結構等原因,在產業升級和轉型方面遇到了巨大的困難。而在接班人選擇上,問題更大。二代繼承人的能力遭遇質疑,職業經理人制度還未完全被市場接納。在這樣的情況下,就非常有必要通過一些政策工具,來發現和培養新一代企業家。因此,政府開始鼓勵包括大學、研究院(所)和政府部門的人再次“下海”,加入大眾創業潮流,希望未來一代的很多企業家,會從這個創業運動中崛起。
劉文儉說:“經濟下行可能在一些傳統的方面,但是新的經濟增長點也在不斷孕育和產生,成功者也在不斷起到示范作用。這個時候才是時勢造英雄。所以現在愿意去創業的人都是有企業家精神的,政府和社會應該給予鼓勵。實際上從某種程度上講,目前我們國家正處在一個創新創業最好的階段,從國家政策到社會氛圍,提供了很多極其優惠和便利的條件。”
體制內外應互通
劉文儉認為:“人一生中不應該禁錮在一個領域。人們思想的創新意識增強了,要求變革,這樣社會才有活力。真正有創新性的人才應該在一線,在科研一線、在生產一線、在創造社會財富的一線,當然體制內也需要精英,但不應該像以前那種千軍萬馬擠獨木橋的樣式,那是一個不正常的狀態。并且,體制外的人也應該有能夠進入體制的渠道,應該為體制外的、富有公共服務意識、愿意實現自身社會價值的精英提供走進體制內的平臺。十八大提出要打破制約人才流動的壁壘。這樣的流動有利于人才找到最合適的工作領域。比如國外的企業家可以到大學當教授,而這些教授是真正能培養出實用性人才的教授。教授也可以去創業,這樣才可以將最新的學術成果應用于實踐。每一個人總是要經過兩三個崗位之后,才會覺得某一個工作相對而講比較適合自己,這樣對于整個社會人力資源的優化配置,也是一個好事。”
人才的跨界流動應該是雙向的,體制內不應總是扮演單向輸出的角色。培養一個干部代價高昂,比培養一個飛行員的難度還大。如果體制內精英缺乏,政府決策的科學性和正確性就難以保證,對于整個社會的發展有害無益。不論體制內還是體制外,事實上只是工作性質的區別,而不應有高低之分。應該鼓勵體制內外的準入和退出機制更加靈活,使每一個人在自己的崗位上都能實現個體價值,推動行業發展。
“跳”的實質
選擇跳槽,對于任何一個行業的從業者來說,都是一件需要深思熟慮的事。最重要的考量是,你到底有沒有能力跳?體制內有著傳統理解上的“旱澇保收”,敢于邁入市場,接受市場考驗的人畢竟是少數。梅永紅加入華大基因,因其曾有農業部與科技部二十多年的工作經歷,且曾任科技部政策法規與體制改革司司長多年;丁磊擔任樂視超級汽車聯合創始人,憑借的是“在汽車、高新園區和政府部門豐富的跨界經驗”;張泉靈剛剛進入“創投界”,就發現投資與記者身份“有很多相似之處”。翻閱這些告別體制者的履歷不難發現,體制并沒有局限他們的成長,反而正是因為有了體制內積攢的經驗和能力,才給予了他們跳出去的能力和勇氣。
張泉靈在辭職宣言中這樣說:“我要跳出去的魚缸,不是央視,不是體制,而是我已經在慢慢凝固的思維模式。”因此,改變固有思維,邁向創新大道并不是在向體制宣戰。在這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年代,體制絕不能成為阻攔創新的圍城,也不會成為限制個人能力發展的籠子。創新創業并不只是體制外、科技圈的事情,政府、事業單位、國企、私企都需要打破傳統理念的禁錮,解放思想,創新創業。這樣才是把創新理念放在一個核心位置上,成為引領整個社會發展的動力。跳槽后的梅永紅日前在河南參加華大基因研究院長垣分院掛牌活動時坦陳:“我國人才在體制內外流動仍面臨諸多障礙,希望三五年后,像我這樣從黨政機關轉崗到體制外機構,不再是新聞。”
“跳”的實質,實際上與普通的擇業無異,不過是對自己未來規劃的一個選擇。而“跳”的意義,代表著“官本位”不再是束縛心靈的枷鎖,社會理念越來越趨于健康、開放、多元。簡單說,這個社會需要的是創新,無論你在哪個位置。落后會被淘汰,無論體制內外。
尼采言:“世界圍繞新價值的創造者旋轉著”。翻開中國的改革史,體制內外的人才流動,曾經書寫了激動人心的創業故事。如果要對未來做一個期許的話,希望每一個勞動者的“跳出”或“跳入”,都不是落荒而逃,而是帶著勇氣與能力,在時代發展的浪尖快意逐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