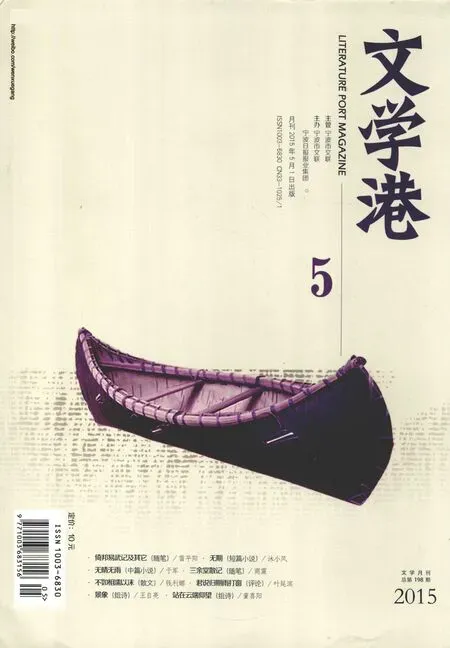小寒:茗粥芼茶泡米飯
王旭烽
小寒:茗粥芼茶泡米飯
王旭烽
一候雁聲春去舊
二候鵲巢始為筑
三候雉入數九鳴
寒意濃茶蘊陰陽重
——題記
小寒大寒,凍作一團。今日小寒,一家人沒能抱團聚暖,反倒是個離別之日。先生北上工作,女兒負笈重又求學萬里去也。好在女兒此趟歸家,甚為暖心,已知為家人沏茶敬客,尤其是為老人上茶。雖然她從前也事茶,但我知道她一直在文化上更認同咖啡,如今長大,漸漸地便開始知道咖啡與茶的不同之好來,尤知茶所可表達的敬意之處。那天女兒為外婆端上一杯茶,著實暖慰了我的心。
行前早餐,為她熱了茶粥,用的是杭州廣福寺僧人的臘八施粥罐頭。廣福寺就在杭州靈隱寺上面,寺內建了座茶禪一味的茶舍,還是一個有古琴傳統的教習之處。那主持是個美院畢業的畫僧,整座寺廟在我看來就染上了濃濃的文藝范兒。
記得以往我們杭人喝臘八粥,都是要早早排隊到寺廟門口去等的,如今僧廟也創新了,將粥制成了罐頭,分給眾信徒。我雖非信徒,也沾光被朋友送了一紙盒,正好與我女兒分享。
牛奶面包將就著吃多了,女兒覺得沒必要那么復雜,一大早起來煮粥多此一舉。我告訴她,中國人的傳統,小寒之日是要喝臘八粥啊。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一是祭祀八谷星神;二是禱祝來年風調雨順。臘八粥以八方食物合在一塊,和米共煮一鍋,是合聚萬物、調和千靈之意。
聽我那么說,女兒饞了,打開鍋蓋,見紅紅綠綠的一小鍋,黃米、白米、江米、小米、栗子、棗泥,加上桃仁、杏仁、瓜子、花生、葡萄、百合,還有蓮子……
“老媽,怎么還有茶葉呢?沒聽說臘八粥里放茶葉的呀?”她見我用熱水浸開了小半缸子的安吉白茶葉子,正往粥鍋里倒,很驚奇地問我。
女兒長期在外求學,不知道老媽我是一個特別喜歡在茶上做各種實驗的人,用茶包餃子,茶水洗澡,綠茶里浸新鮮紅玫瑰,綠茶加白糖,熱紅茶沖雞蛋,茶湯里放鹽擱生姜末,將茶葉末加肉末一起炒了煮湯喝,烏龍茶水加豆漿,茶與白酒加在一起龍虎斗,茶水里放蔥白,茶水里浸蜜餞等等。這回我又試了一個新的,我在臘八粥里加上了去年春上的安吉白茶。
倒也不是因為全年主題是此茶,所以非放那安吉白茶不可。恰是因為安吉白茶鮮嫩,氨基酸成分多,茶多酚成分少,吃起來苦味寡鮮味濃,況且葉片薄,色澤亮,嚼起來也方便,滑溜溜的,有種莼菜入口之感。我對女兒說:“茶禪一味,佛門干什么都離不開茶。你看綠茵茵茶點在紅紅白白的粥里,跟灑了蔥花似的,多漂亮啊!”
一片片的淺白綠的嫩茶葉,即便放了大半年,泡開了還是那么冰清玉潔,為圖她的顏色要好看,我幾乎一放下去攪一攪就撈上來了。臘八粥原本是甜的,加了茶葉汁,略作烹煮,嘗一嘗,微微的便有些甜中帶苦,味道便反而更豐富、更有層次了。女兒說:“有一點苦呢,老媽。”我說:“這算什么苦啊,這叫茶飯,是老祖宗的飲食文化傳統,中國人外國人都吃這個的。”
女兒笑而不答,不置可否,我知道,在那個肯德基與麥當勞的祖國,沒有茶飯這一說。但粥里加茶,或者飯里放茶,真不是我的新發明,三國時就有了,叫芼茶。
芼這個字,《詩經》開篇就出現了:“參差荇菜,左右芼之。”讀音好記,就念“毛”。它本來指的便是采摘可供食用的野菜或者水草,可這些野菜或水草身份特殊,被選來專門覆蓋獻祭時所奉的畜牲之體,故而便有了“覆蓋”之意。所以,在《禮記·昏義》中便記載了這樣一條:“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而清代知名學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則這樣說:“覒,擇也。玉篇引詩:左右覒之。按毛詩作芼,擇也。”芼后來便又有了提取、選拔之意。
當芼與茶結合成為芼茶時,出現了一個新概念,也就是混飲茶,在三國兩晉時,它也可被理解為茶粥。西晉時傅咸曾經為在洛陽南市的老嫗抱打不平,憤而舉報城管不公正,說的就是小攤販要賣茶粥而被強行欺壓趕走之事。
茶粥究竟是怎么回事,陸羽在《茶經》中轉述了三國時期魏人張揖在《廣雅》中的記載:“荊、巴間采葉作餅,葉老者,餅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飲,先炙令赤色,搗末,置瓷器中,以湯澆覆之,用蔥、姜、橘子芼(摻和之意)之。其飲醒酒,令人不眠。”這是中國關于制茶和飲茶方法的最早記載。它告訴我們:當時飲茶方法是“煮”,是將“采葉作餅”的餅茶,烤炙之后搗成粉末,摻和蔥、姜、橘子等調料,再放到鍋里烹煮。這樣煮出的茶成粥狀,飲時連佐料一起喝下。說到它的功能,則明確用來和酒對著干——醒酒。
今天的中國人,煮茶粥的可能真是不多了,但吃茶泡飯的還是不少。我小時便常吃茶泡飯,尤其是夏天。制作十分簡單,全是涼的,涼茶往涼干飯團里一倒,攪動幾下,散開了就吃。但這樣吃其實是錯誤的,茶泡飯是指用熱茶水來泡冷飯,講究一點的,還要放上鹽、梅干、海苔等配料,和著飯一起泡。我還記得讀《紅樓夢》時,那第四十九回“琉璃世界白雪紅梅,脂粉香娃割腥啖膻”這一章,專門有那么一句形容寶玉吃飯的——“寶玉卻等不得,只拿茶泡了一碗飯,就著野雞瓜齏忙忙的咽完了”。當時就想,什么是野雞瓜齏啊,用來泡茶飯,怎么吃啊。后來才知道,野雞瓜齏其實就是類似炒雞丁一類的下飯菜。清代《調鼎集》中有云:“野雞爪,去皮骨切丁配醬瓜、冬筍、瓜仁、生姜各丁、菜油、甜醬或加大椒炒。”原來野雞爪齏中加那么些咸菜,自然咸了,加茶湯,能不好吃嗎。
當然也有吃茶泡飯吃它本來面目的,比如明末清初時那個風流公子冒辟疆的妾董小宛,她自己精于烹飪,但性情卻淡泊,對于甘肥物質無一所好,每次吃飯,均以一小壺茶溫淘飯,還說這是古南京人的食俗,早在六朝時就已經有了。美人茶泡飯圖,想想都是意境極美的。
專門做了茶的學問之后,我就知道日本有部影片,很有名,就叫《茶泡飯之味》,是日本著名導演小津安二郎1952年的黑白片作品。說的是有個名叫妙子的少婦漸覺婚姻乏味,而丈夫茂吉在她眼里則是個大悶蛋。她喜歡生活享受,他卻偏愛粗茶淡飯。夫妻終于在侄女相親的問題上決裂,茂吉突然遠赴烏拉圭公干,行前妙子也不知所蹤。不曾想飛機延誤折返家中了,夫妻相見時恍若隔世。再度離別前,兩人共享了一頓茶泡飯,影片就那么結束了。小津電影的故事都稀松平常,寫食物也都是平平淡淡,什么米飯、腌菜、拉面、白飯配烤肉串、綠茶、清酒、秋刀魚……這些正是小津電影里的日本味,東方味。對我們東方人,單是這些食品的名字已經能喚起一種淡淡的共鳴。對于西方人來說,也許他們并不熟悉綠茶泡飯的滋味,然而那餐桌旁的柴米油鹽凡人瑣事,卻是不管是吃面包喝咖啡還是吃米飯喝綠茶都一樣要面對的,情感也是共通的。小津的電影看似漫不經心,可是隨了自然的節拍,有著內在的旋律。這部電影正如片名一樣,耐心的人會很喜歡,那茶泡飯中帶著的一絲清香,真是值得回味許久。不過,看慣美國大片的人,可能坐不了三分鐘就拍屁股走人了。

從日本學習茶道回來的老師們,也總是會跟我說起茶泡飯的。原來茶泡飯在日本還有著特殊的時代記憶,日本十八世紀著名俳句詩人小林一茶寫過:“誰家蓮花吹散,黃昏茶泡飯。”又有:“蓮花開矣,茶泡飯七文,蕎麥面二十八。”都是淡到骨子里的美。
日本人食茶泡飯的歷史很久,《枕草子》和《源氏物語》中就已經有了“開水泡飯”(湯漬)與“水飯”的記載。到江戶時代中期,煎茶與粗茶普及至庶民,茶泡飯也取代開水泡飯成為更流行的飲食,名曰“茶漬”。米飯上放鰹魚屑、海苔絲、梅干、納豆等物,玉色茶湯沖泡,煎茶泡白飯,頂上嵌一粒梅子,海苔切得很細,佐以腌菜,有平淡而甘香的風味。此時若人在鄉間,山影下一方一方水田傳來鼓噪的蛙鳴。竹簾外圓月當空,清輝教細竹篩碎,流水般灑了一地。卻不不可言說的茶泡飯的意境啊。
但日本也有一些不可吃茶泡飯的禁忌習俗。比如從前樵夫、馬夫、牛夫、獵人等在山中從事危苦工作的人,他們極其嫌惡吃“湯泡飯”,說吃了茶泡飯,會有不好的預兆。譬如炭坑內勞作的坑夫認為茶湯泡飯時米飯化開的樣子有如山崩,很不吉利。家人都會忌諱吃茶泡飯和湯泡飯。又如牛夫認為早上吃了茶泡飯,這一天的旅程即會中止,要多負擔一日停留的費用。而且據說京都人給人下逐客令時會說一句:“要吃茶泡飯么。”意思是:“家中只有茶泡飯這樣的食物招待您,您還是快走吧。”客人即領會其意,起身告退。這是京都人曖昧婉曲的禮節。也有外來的人不知其意,當真以為有茶泡飯可食,那就等著看笑話吧。
從另一個角度說,茶泡飯也算是一種日本武士的一種軍糧。原來日本武士在行軍作戰中用熱茶泡米飯,加上佐料,即飲即食,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充饑提神。如果選用沒有發酵和高溫處理過的茶葉,其中富含抗氧化劑,還可以預防敗血癥。所以,這種茶泡飯被稱之為“武士之食”。成型于日本戰國、也就是的室町幕府后期到安土桃山時代之間,這大約百年間政局紛亂、群雄割據的日本歷史,時間大致應該在十五世紀中葉到十七世紀初吧。
二戰結束后,日本食物供應短缺,許多人吃茶泡飯,喝醬湯。因此,茶泡飯本來是貧窮或困難時,沒有辦法的烹調方法。然而,茶泡飯不但沒有消失,反而成為日本料理中的“家常菜”。部分是因為日本的文學故事和電影里,常常出現當年的茶泡飯,令很多年長的人懷舊,想重溫當年吃茶泡飯的味道;部分是因為現代的快節奏和快餐文化,茶泡飯幾分鐘就可以準備好。況且如今的茶泡飯,其營養和做工都大大改進,有很好的解酒、消食、養胃的功效,日本男人下班后都有與同事結伴去喝酒的習慣,微醉后回到家里,最想吃的就是一碗清淡爽口而又暖胃的茶泡飯了。如此看來,小津的影片實在是有很深的民族情結在其中的呢。
其實要說到軍人吃茶,中國人早在兩晉時期就開始了。讀《茶經·七之事》,里面還專門記載了西晉時這樣一段茶掌故,說的是劉琨在《與兄子南兗州史演書》中寫道:“前得安州干姜一斤,桂一斤,黃岑一斤,皆所須也。吾體中潰悶,常仰真茶,汝可致之。”這個想要喝茶的英雄,就是中國歷史中那個大名鼎鼎“聞雞起舞”的主人。
劉琨(271—318)為西晉政治家、文學家、音樂家和軍事家。公元315年任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318年,與子侄四人被段匹磾殺害。后人陸游曾無限感慨地詩曰:“劉琨死后無奇士,獨聽荒雞淚滿衣。”
劉琨與祖逖一起擔任司州主簿時,感情深厚,不僅常常同床而臥,同被而眠,而且都有著建功立業,成為棟梁之才的遠大理想。一次半夜,祖逖聽到雞叫,叫醒劉琨道:此非惡聲,是老天在激勵我們上進,于是拉著劉琨就到屋外舞劍練武。劉琨還善吹胡笳。曾有數萬匈奴兵圍困晉陽。劉琨登上城樓,俯眺城外敵營,想起“四面楚歌”的故事,下令會吹卷葉胡笳的軍士全部到帳下報到,很快組成了一個胡笳樂隊,朝著敵營那邊吹起了《胡笳五弄》。他們吹得既哀傷又凄婉,匈奴兵聽了軍心騷動。半夜時分,再次吹起這支樂曲,匈奴兵懷念家鄉,皆泣淚而回。
劉琨無疑是《世說新語》中玉樹臨風式的人物。大司馬桓溫北伐歸來,帶回來一個劉琨家的老婢女,那老婢一見桓溫便潸然淚下道:“公甚似劉司空。”桓溫大喜,趕緊地問哪里像。老婢答道:“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須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原來哪兒哪兒都比不上劉琨,搞得桓溫大為掃興,抑郁了好些天。
愛喝茶的劉琨,被派往西北重鎮并州出任刺史時,生活環境不好,再加上憂國憂民夙興夜寐,身體出了毛病,就給他那在山東出任兗州刺史的侄子劉演寫了封信,說:……吾體中潰悶,常仰真茶,汝可置之。
并州環境惡劣,劉琨的身體狀況處在一種潰悶的狀態,尤其是缺少必要的維生素,局部地方潰爛就在所難免,在生理上茶葉對于劉琨是有益的,人若在心理上煩躁、悶亂,提不起精神來,茶葉中的咖啡堿能夠提神,多酚類能夠舒緩緊張情緒,已經得到現代科學證明,故用茶來除“悶”對劉琨來說,算是對癥下藥的了。可見茶在西晉時期,藥用價值還是排在第一位的。
時代演進到南北朝,《茶經》中又引用了一封有關茶的信件,梁朝劉孝綽的《謝晉安王餉米等啟》:“傳詔李孟孫宣教旨,垂賜米、酒、瓜、筍、菹、脯、酢、茗八種。……茗同食粲,酢類望柑。免千里宿春,省三月糧聚。小人懷惠,大懿難忘。”劉孝綽(481--539),名冉,他寫信的對象晉安王名肖綱,就是后來的簡文帝。這劉孝綽是個文學家,很被昭明太子賞識,出任過太子太仆兼廷尉卿。而這封信是感謝晉安王送來的禮物,說:李孟孫君帶來了您的告諭,賞賜我米、酒、瓜、筍、菹(酸菜)、脯(肉干)、酢(腌魚)、茗等八種食品……大米如玉粒晶瑩,茗荈又似大米精良,酸菜一看就令人開胃。(食品如此豐盛)即使我遠行千里,也用不著再籌措干糧。我記著您給我的恩惠,您的大德我永記不忘!
看這封信,會認為劉孝綽是個誠惶誠恐之人,其實他因為從小聰明,七歲便能寫文章,是個神童,文采過人,被學人所推崇。他每寫一篇文章,早晨寫完,晚上便傳遍各地,有些好事者都背誦傳抄他的文章,傳播到極遠的地方,文集幾十萬字,流傳在世。據說他還是中國春聯第一人,因做官數度被罷免,他干脆閉門不出,書寫了“閉門罷慶吊,高臥謝公卿”這樣一副對聯貼于自家門板上,春聯就這樣誕生了。
這樣一個人因為十分任性,盛氣凌人,凡有不合自己心意的人或事,便極力詆毀人家。看不上的人則尤其輕蔑他們,雖然同在朝中做官,卻從不與他們說話。公開稱他們為馬夫,只能詢問些道路上的事,同僚們因此對他也很畏懼。時間長了,被人告狀免職,發到京城之外去,此時收到佳物,卻大唱起贊歌來呢。在信中把茶與米相提并論,說茶似大米,大米似玉粒,因此推理而言,茶就是玉粒了。其實晉安王送劉孝綽的,都是日常可食之物,其中包括了茶。
那么劉孝綽究竟是吃的茶粥還是喝的茶湯呢?我感覺他可能還是與陸羽一路人,將茶做了精神品飲。陸羽在《茶經》中公開這樣說:“飲有粗茶、散茶、末茶、餅茶者。乃斫、乃熬、乃煬、乃舂,貯于瓶缶之中,以湯沃焉,謂之痷茶。或用蔥、姜、棗、桔皮、茱萸、薄荷之等,煮之百沸,或揚令滑,或煮去沫,斯溝渠間棄水耳,而習俗不已。”陸羽是把茶中置放它物視為應該倒到溝渠中的棄水。他自然是看不上這種習俗的,但習俗才不管茶圣看不看得上,照舊不已,也就是源源不斷該放什么就放什么。《保生集要》說:“茗粥,化痰消食,濃煎入粥。”能幫助治療急慢性痢疾、腸炎、急性腸胃炎、阿米巴痢疾、心臟病水腫、肺心病和過于疲勞等癥,無怪唐朝詩人儲光羲就寫了一首詩《吃茗粥作》:“淹留膳茶粥,共我飯蕨薇。”

女兒喝了母親為她烹熬的祖國的臘八茶粥,便遠渡重洋去了。從電視上得到的消息,小寒之日,紐約大雪,機場飛機停飛,人群滯留,不由想起了劉長卿的五言絕句: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
那風雪中的夜歸人推開柴門,還應該有一碗熱騰騰的茶粥端到眼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