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辛:我只寫我真切體驗思考過的生活
文/修曉林
葉辛:我只寫我真切體驗思考過的生活
文/修曉林

修曉林中國作協會員,上海文藝出版社編審。著有中短篇小說集《獨眼阿德》、散文集《瀾滄江邊》等

1991年6月的一天,葉辛來到上海文藝出版社《小說界》編輯部,向我們幾位文學編輯一一點頭問好,同時將他字跡遒勁、謄寫清楚的長篇小說《孽債》厚厚一疊文稿,交給文藝社的著名編輯、也是我和葉辛共同的恩師謝泉銘先生。陽光燦爛的房間里,葉辛靠在玻璃寬大的南窗邊,滿心是辛勞完成長篇創作之后的輕松快樂。好似回憶起自己在貴州山區知青歲月的艱難困苦,他以一種瀟然堅毅的身姿,手臂伸向那遙遠的前方,用地道的貴州方言說道:“那貴州的深山老林,一上路就是要不停地走大半天,那個遠啊,到啊——邊去了。”葉辛說這個“啊”字時,用了長長的、深遠的拖腔。我也曾在云南當過十年知青,這云貴高原的山民,往往是用這“啊”字的聲調,表示這路程的長短,如是干脆地說“啊邊”,那就是走不多時間就會到達目的地;而如果是“啊——”個不停,那就是路途遙遠得不敢想。那時,葉辛的文學創作之路也是分外艱辛,心里是焦急的盼望,但又何時能夠成功?這心中的夢想實現也是遙遠得連想都不敢想啊。在貴州修文縣久長鎮永興村砂鍋寨知青年代的日子何其艱難,白天是重體力活的挑糞、耙田、鏟田埂、鉆煤窯,晚上以床板或是椅子當桌,守著煤油燈,在鋼筆墨水幾乎無法順暢書寫的粗糙皺紙上寫作。夏天山蚊成群,實在受不住叮咬,就在門口燃一堆艾草驅趕蚊蟲;貴州山區的冬天特別寒冷,他就拖一把稻草圍住雙腳取暖。每晚,村民們看見那個寨子中心的土地廟里亮起微弱搖晃的燈光,那就是葉辛在苦苦夜讀和寫作……對于這段苦難歲月,葉辛稱其為“一生中最難忘的日子”,他當時就在日記中寫下堅毅文字:“必須腳踏實地地寫作,邁出我生活的腳步。”“人是不同的,有的人面對困難選擇退縮,有的人選擇的卻是前進。”葉辛認為,這是他性格中最倔強的部分。現在,從不曾放棄希望和奮斗、走過坎坷困苦之路、終于踏上人生坦途的葉辛,滿臉是幸福自在的笑容,這讓我們編輯部里的每一位新老編輯都受到感動和感染。
作家前來送稿,編輯就要盡快看稿。謝泉銘老師讓我與他一起擔任《孽債》的責任編輯。翻閱審讀此部長篇,我覺得這部反映那個特殊年代親情延續故事的作品情感真摯,文字樸實自有一種沉穩中的躍動,小說富含生活質感,故事性強,注重細節展示和描寫,矛盾沖突尖銳,人物性格鮮明,既關注知青們的下一代,又描繪了人性深度,挖掘出深厚的社會和歷史內涵。作品對社會上欲求與良知搏擊的生動刻畫,顯示出傳統文化中對美好道德回歸的呼喚。雖說小說“尚可更完美、更合理”,但這不影響我們對作品主題價值和預計社會反響的認可贊賞。《孽債》于1991年在《小說界》分兩期首發,后于1992年由江蘇文藝出版社出書,隨后同名電視連續劇于1995年播出,立即紅遍大江南北,創下收視率高達42.7﹪的記錄,電視劇主題歌《哪里有我的家》《曾經——》幾乎是人人會唱人人喜歡唱。夜晚,多少綠樹掩映的小區里,各家各戶的窗戶飄蕩出那憂傷激昂的旋律,在更大的空間形成了動人心扉的“環繞立體聲”。萬千觀眾坐在電視機前,他們的心弦已是被“千里尋母,孽債情緣”的故事吸引和撥動。當時已是九十四歲的巴金已長臥病榻,可每次播出《孽債》,巴老就會讓人將病床搖起來,自己靠在枕頭上看電視。家人不解,“你又不是知青,看這個干嘛?”巴金說,“我看的不是知青,是已經過去的一代人的生活”。
對于《孽債》,葉辛解讀說:一個男知青討兩個老婆,一個女知青嫁兩個丈夫,這在知青生活當中并沒有典型性,大多數知青不是這樣的。動筆創作《孽債》前,也猶豫了很久不敢下筆,但是這個故事后面折射出來的是一代人的命運。他感到這是生活恩賜給自己的素材和主題,應該把它寫出來,因為它帶著時代的烙印,其折射出來的是我們這代人的命運和情感經歷,讀者會從中獲得耐人尋味的思考。作品問世后,客觀上社會效果很好。自《孽債》后的這二十多年,葉辛的長篇新著一部接一部出版,且是本本引人注目,他同時還有大量散文隨筆發表,更有專題論文《中國大地上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論中國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落幕》在專業刊物發表,資料詳實,論述縝密,具有冷靜客觀的理性觀察和思考,引起國內外知青研究專家的高度重視,老知青們讀來也是津津有味、浮想聯翩、佩服有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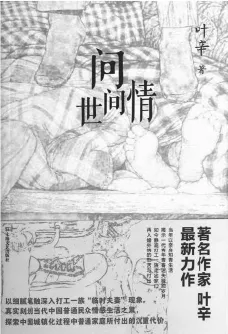
我有時會想,葉辛的成功之道是什么?與葉辛相識交往幾十年,我感覺他對事對人對生活對創作都有著既敏感又敏銳的深度思考。1991年底,《小說界》編輯部召開全國著名作家筆會,緩緩行駛的太湖游船上,出版社的編輯和各地作家們都在歡聲笑語地敘談,只見葉辛獨自坐在窗前,望著浩淼的湖面和粼粼水波,進入一種良久沉思的靜默狀態,真是“心思浩茫連廣宇”。直到游船靠岸,他這才激靈回神。在知青年月里,葉辛就養成了獨立思考的習慣,那個磋跎歲月,讓他思考了我們這一代年輕人的命運,他開始擺脫一個城市人的更多偏見,真正理解生活在山鄉里普通農民的心情,開始懂得中國是怎么回事。葉辛在遙遠的山區插隊,經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整個過程。他從小生活在上海,從未接觸過農村。知青生活讓他學會用兩副眼光來觀察生活:是一副眼光經常用都市人的目光來觀察偏遠、古樸、傳統的農村生活,看到那里很多與城市不一樣的東西;另一副眼光是常常用山里人的目光來看待都市里的一切,并總能發現都市里的人發現不了的東西。當兩種目光交織在一起的時候,對他的創作來講是非常重要、彌足珍貴的。葉辛起念創作長篇小說《客過亭》,緣起于他看到一本當年偏遠山區某縣上海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花名冊。這本花名冊雖然只有二十幾頁,但他看了四個多小時,當年的知青從十幾歲的年齡到現在,這些人的面貌全部在這本花名冊里體現出來了,從中可以看出上山下鄉知青的命運。葉辛邊看邊陷入深深的思索,看著看著突然覺得,可以寫這樣一部長篇小說:寫一幫老知青,約好了回歸當年插隊的山寨……還有近年出版的、反映城市務工人員“臨時夫妻”現象的長篇小說《問世間情》也受到廣泛關注。葉辛現在已經出版有九十多部文學作品,這著作等身的后面,可說是勤于思考、善于思考給他帶來的創作激情與靈感。
葉辛也是一位惜時如金、勤勉創作的作家。在早年插隊落戶的歲月中,他就養成了珍惜時間的習慣。只要一有時間,他就習慣于坐在書桌前沉思、書寫,把稍縱即逝的思緒記錄下來。一有整塊時間,他就立即進入寫作狀態。幾乎每一個夜晚,他都是臨近夜晚十二點才入睡。直到現在,幾乎每一個雙休日,他都是在寫作中度過。葉辛說,寫作當然需要各種條件,具備各種素質,但是勤奮創作、埋頭苦干是最基本的條件和素質。同時,他十分看重作品的故事性和可讀性,他崇尚的文學大師易卜生、契訶夫、屠格涅夫、大仲馬等,都是善于設置懸念和制造戲劇沖突的高手。葉辛在構思小說的時候,往往是根據生活中的一個故事,選準角度、謀篇布局,用不斷推進的故事情節和復雜的心理活動抓住讀者和觀眾的心,使文學作品成為人們認識人生的窗口和解釋生活難題的鑰匙。
葉辛為人寬厚,儒雅隨和,沒有讓人難以接近的架子,也毫無傲視他人、自滿凌人的淺薄言行。我的嘉定知青好友王世綏將所寫幾萬字知青生活的回憶文章寄給他看,大忙人葉辛很是理解他人的心情和愿望,仔細閱讀并提出自己的看法意見。葉辛曾對我說,知青運動結束后的十幾年,上海郊區一些當年云南知青的具體問題仍未得到妥善解決,作為市人大常委和教科文衛副主任的葉辛,以其重要身份和話語權,盡力全面反映這部分知青的訴求,終使問題得到合理解決。
葉辛十分看重不斷變化發展的生活給自己帶來的啟悟,他一直在向生活學習、深度感受生活,總是留意在生活中捕捉作品的新意。2014年10月,黨中央召開文藝座談會,葉辛發言說:“李白、杜甫、白居易,為那個時代留下了不朽的詩篇,每一個有追求的當代中國作家也應該為我們的祖國和我們今天所生活的時代書寫新篇章。李白、杜甫不可能寫社會主義,也不可能寫清朝明朝,他們只可能寫他們在唐朝的生活;而我,也只能寫我真切體驗過思考過的生活。”習近平總書記聽后說:“我和葉辛都是上山下鄉的一輩,你說的我非常理解,你是在南方的貴州,我是在陜北的黃土高原,寫這些是有意義的。”
作家要靠作品說話,寫出好作品是作家的天職。如今,每一位當代作家都會自問:我還能寫什么?我還能寫多少?當然,各人的具體情況有所不同,各人對自己的嚴格要求也是要建立在客觀因素是否許可的基礎之上,從來就沒有事事都心想事成、整齊劃一的事情,但仍可說這是一個令人肅然、驚醒甚而是內心糾結、略顯窘態的問題。但我想,這對于葉辛來說,這還算是問題嗎?2015年7月,葉辛又有長篇小說《圓圓魂》出版,并立即引起書界反響。有充滿熱望和激情的對于新生活的關注,有經年累月掌握的嫻熟寫作技巧,更有一雙看透生活本質、提煉素材新意的創作慧眼,只要有充沛精力和健康身體,完全可以預見,這小說創作的繼續寫作和出版,對于葉辛來說,只是時間的問題。因為,是涌動的生活,給葉辛以創作的火熱激情;是緊貼生活地氣的思考,給葉辛以旺盛的創作活力。

本文作者與葉辛合影
善哉,幸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