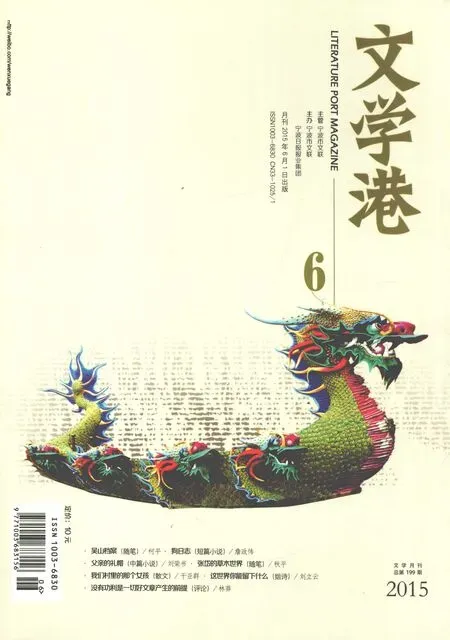吳山檔案
柯平
吳山檔案
柯平

上篇
在今杭州市區(qū)西湖東南,有一片迄邐起伏的帶形丘陵,名字雖以吳山冠之,實(shí)際上是由十幾座玲瓏的小山峰所組成的,所謂的吳山,不過是其中之一峰罷了,而且還不是最高的。但它在這座城市歷史上的分量,卻是怎么形容也不過分。市民們習(xí)慣將它看作自己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在地方史學(xué)者眼里,更視之為當(dāng)?shù)匚幕罟爬系脑搭^。因山上有一座著名的寺廟叫忠清廟,俗稱城隍廟,祀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春秋賢臣伍員。這個(gè)名字對(duì)于中國(guó)的歷史是個(gè)什么概念,這大家想必都知道,就不用多說了。地以人榮,山因名高,志士仁人千年不滅的精魂,自然連山上的一草一木也都跟著沾光。因?yàn)檫@個(gè)緣故,北宋時(shí)兩度出任地方行政長(zhǎng)官的蘇軾,還專門為它寫了首廣告詩(shī),叫做“朝見吳山橫,暮見吳山縱。吳山故多態(tài),轉(zhuǎn)側(cè)為君容”,從旅游角度作了很好的推介。而后來(lái)金主完顏亮為江南花花世界所迷,興師伐宋,行前以“提兵百萬(wàn)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作為自己的戰(zhàn)略目標(biāo),應(yīng)該說也是很有眼力的。
《儒林外史》第十四回講馬二先生在吳山頂上看杭州:“那日江上無(wú)風(fēng),水平如鏡,過江的船,船上有轎子,都看得明白。再走上些,右邊又看得見西湖,雷峰一帶、湖心亭都望見,那西湖里打魚船,一個(gè)一個(gè)如小鴨子浮在水面。……一邊是江,一邊是湖,又有那山色一轉(zhuǎn)圍著,又遙見隔江的山,高高低低,忽隱忽現(xiàn)。馬二先生嘆道:真乃載華岳而下重,振河海而不泄,萬(wàn)物載焉。”這段文字寫得實(shí)在漂亮,雖說地貌方面的摹本,來(lái)自歐陽(yáng)修的《有美堂記》:“邑屋華麗,蓋十余萬(wàn)家,環(huán)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fēng)帆浪舶,出入于江濤浩渺煙云杳靄之間,可謂盛矣。”但語(yǔ)言更見生動(dòng)傳神,難怪會(huì)被選入中學(xué)語(yǔ)文課本,可惜忘了把這位伍英雄給帶上一句,不然的話就更完美了。為了彌補(bǔ)這一缺憾,清代有個(gè)叫金志章的,甚至還專門修纂了一部《吳山伍公廟志》,來(lái)探討這一問題。
伍公即伍員,即伍子胥,這在今天固然已是常識(shí),但吳山原名青山,又名胥山,這就不是一般人所知道的了。杭州最早的地方志之一《淳祐臨安志》在交代它的來(lái)歷時(shí)語(yǔ)焉不詳,只引《史記》“吳人憐伍子胥以忠諫死,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了事。稍后《咸淳臨安志》似乎注意到了這一問題,略有改進(jìn),但也只是資料上的增加而已,改寫了《漢書》里的伍子胥傳,增補(bǔ)了唐宋間幾位太守留下的四篇碑記,及相關(guān)詩(shī)詞。至于這座廟是哪個(gè)年代開始建立的,吳越兩國(guó)當(dāng)初為敵國(guó),子胥的精神依戀之地何以不在彼而在此,姑蘇有廟,但基本只是個(gè)空殼,錢塘越地,卻虔誠(chéng)祭祀對(duì)方主帥,是否具有政治上文化上的合理性?尤其是廟的位置,《史記》里已明確說是在江邊,現(xiàn)在為什么卻矗立在山頂上。依然沒有作出有說服力的解釋。事實(shí)上從古代保留下來(lái)的文獻(xiàn)看,無(wú)論唐元和十年盧元輔《胥山銘記》“求忠者之尸,禱水星之舍”的描寫,還是南宋中期趙與懽《英衛(wèi)閣記》“冠山椒而特立,鎮(zhèn)江濤而不驚”的形容,地望方面所透露出的信息,跟《史記》里的紀(jì)錄基本是一致的。此外還有相關(guān)的那些詩(shī)詞,也讓人無(wú)法舍水而取山,如白居易的“濤聲夜入伍員祠,柳色春藏蘇小家”,李紳的“伍侯廟中多白浪,越王臺(tái)畔少晴煙”,蔡襄的“潮頭正對(duì)伍胥廟,燕子爭(zhēng)歸百姓家”。看了這些狀物如在目前的地理檔案,如果誰(shuí)還認(rèn)為這座廟應(yīng)該是在山上而不是水邊,只能說明自己的想象系統(tǒng)有點(diǎn)出問題了。
那么,為什么會(huì)有這樣的古怪,里頭是否藏有什么貓膩?在回答這個(gè)問題以前,有必要先來(lái)回顧一下歷史,尤其廟主伍某臨終前后的情況。據(jù)最早記錄此人生平的《越絕書》披露,身為吳國(guó)宰相的伍子胥跟吳王夫差的矛盾,始于周敬王二十六年(前494年,夫差三年,勾踐四年),因?qū)?zhàn)敗國(guó)越國(guó)的處置意見不合而起。伍主張堅(jiān)決不能予以寬恕,而必須從社稷宗祠上進(jìn)行徹底消滅,理由是兩國(guó)文化相近,國(guó)土相連,任何一方的強(qiáng)大,必以另一方的弱小為代價(jià),彼此間利害關(guān)系太深了,留著早晚是個(gè)禍根。而夫差顯然缺乏這樣的政治遠(yuǎn)見,虛榮好勝,對(duì)敵國(guó)君臣匍匐在自己腳邊、甘為奴仆車夫的場(chǎng)景有相當(dāng)興趣,加上另一大臣太宰嚭私底下收受了越方賄賂,也在一旁極力為之說情,最后還是同意以附庸國(guó)的形式,讓越國(guó)的國(guó)家政權(quán)得以繼續(xù)保存。這樣的結(jié)果,顯然為以前朝元老兼功臣自命的伍所無(wú)法容忍。另一東漢文獻(xiàn)《吳越春秋》所記的現(xiàn)場(chǎng)情景是:“伍胥在旁,目若熛火,聲如雷霆,乃進(jìn)曰:夫飛鳥在青云之上,尚欲繳微矢以射之,豈況近臥于華池,集于庭廡乎?今越王……入吾梐捆,此乃廚宰之成事食也,豈可失之乎?”而吳王為自己找的理由是:“吾聞?wù)D降殺服,禍及三世。吾非愛越而不殺也,畏皇天之咎教而赦之。”于是,“夫差遂不誅越王,令駕車養(yǎng)馬,秘于宮室之中”。
接下去的十年,為兩人的不斷交惡期,且彼此關(guān)系越來(lái)越壞。在子胥一方,看著君主被敵方利用,國(guó)家一天天走下坡路,而君主本人居然還蒙在鼓里,心里一著急,說話自然也就沒什么顧忌,有時(shí)甚至還會(huì)暴跳如雷,破口大罵。在夫差一方,一個(gè)所謂的老革命,居功自傲,整天在耳邊啰里八嗦,自己作出的任何國(guó)策都要反對(duì),而且說出來(lái)的話又是那么惡毒,開口閉口就是“你們不聽我的話,早晚全得死定”或“臣必見越之破吳,豸鹿游于姑胥之臺(tái),荊榛蔓于宮闕”。開始念著他是先王功臣,不免還讓著幾分,到后來(lái)可是越來(lái)越無(wú)法忍受了。夫差十三年伐齊歸來(lái)是兩人的最后攤牌時(shí)間。由于行前子胥極力反對(duì),并預(yù)言出師不利,夫差回來(lái)后得意洋洋,一見面就指責(zé)他“昏耄而不自安,生變起詐,怨惡而出,出則罪吾士眾,亂吾法度,欲以妖孽挫衄吾師”。沒想到這姓伍的絲毫不肯退縮,反口相釁,說這樣下去,國(guó)家的滅亡是遲早的事,并讓夫差趕緊把他殺了,“員誠(chéng)前死,掛吾目于門,以觀吳國(guó)之喪”。(詳見《吳越春秋夫差內(nèi)傳第五》)
春秋歷史上最著名的這一悲劇,因雙方個(gè)性的倔強(qiáng),就這么不可避免地釀成了。伍員死后頭懸國(guó)門的記載,聽起來(lái)像是段子,有著一定的傳奇色彩,但司馬遷的《史記》號(hào)稱是信史,書里非但也這么說,甚至還具體說明首級(jí)的懸掛地點(diǎn),是在都城的東門之上,那就不能不認(rèn)真對(duì)待了。都城即吳都,從前叫姑蘇,叫吳郡,現(xiàn)名江蘇省蘇州市是也,而東門一名蛇門,也有非今人所能想象的特別用意在。“曰蛇門者,為其于十二位在巳也;又云以越在巳地,為木蛇北向,示越屬吳也”。(見朱長(zhǎng)文《吳郡圖經(jīng)續(xù)記》)其地至今尚存,不過已改名叫盤門,好像是從范石湖的《吳郡志》開始的,也沒說清是什么理由。從地理方位看,大概算是正東偏南吧,可說基本符合死者自己生前的要求。當(dāng)然掛在那里的只是腦袋,而剩下的那個(gè)無(wú)頭尸身,則被盛進(jìn)一個(gè)叫鴟夷的物事,扔到了江里。這玩意據(jù)東漢寫《風(fēng)俗通義》的應(yīng)劭說,是用皮革做的,模樣像個(gè)大酒壺,浮在水面上不會(huì)沉下去,如同現(xiàn)代的橡皮艇一般。當(dāng)然,由于整體采用密封狀態(tài),你也不妨可以稱它是個(gè)大氣球或微型潛艇。

在兩千五百年后的今天,想象當(dāng)年發(fā)生在吳國(guó)首都這驚人的一幕,確實(shí)讓人唏噓不已。伍子胥這個(gè)人,毫無(wú)疑問是個(gè)個(gè)性有缺陷的人,他自負(fù)、狂傲、任性,典型的炮筒子脾氣,這從前面與吳王的幾次爭(zhēng)吵就看得出來(lái)。同時(shí)心里什么話也藏不住,想到什么說什么,當(dāng)年奔吳途中好心幫助過他,于他有恩的漁父和浣婦,即先后因此而死。行事更是憑一己之好惡,毫無(wú)原則和底線可言,比如闔閭九年(前506年)率吳師攻入楚國(guó)后,將仇人尸體從墳中挖出來(lái)鞭打出氣倒也罷了,最難讓人接受的是,竟然會(huì)“令闔閭妻昭王夫人,伍胥、孫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這里所謂的妻,是古人的玩法,跟現(xiàn)代漢語(yǔ)有別,指的當(dāng)然就是強(qiáng)奸了。這樣明目張膽的對(duì)待戰(zhàn)俘的犯罪行為,那是比后來(lái)的日本鬼子都要厲害了。對(duì)此他自己居然還有個(gè)解釋,叫做“吾日暮途窮,吾倒行而逆施之”。但這樣一位吳國(guó)歷史上拓土開疆、功勛蓋世的大英雄,由于不斷地進(jìn)諫,由于對(duì)國(guó)家的忠心耿耿,對(duì)民族前途命運(yùn)深懷關(guān)切和憂思,到頭來(lái)竟落得如此下場(chǎng),也實(shí)在是出人意表。后世的同情與緬懷,主要也是沖著這一點(diǎn)來(lái)的。因此,如果要評(píng)選春秋戰(zhàn)國(guó)版的感動(dòng)中國(guó)十大人物,此人不僅肯定可以入選,而且名次說不定還能進(jìn)入前三。
或許,對(duì)于本文要討論的主題,這些都還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史記伍子胥傳》“吳人憐之,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這段話后面,有唐人張守義《史記正義》的一段注解,而這段文字,亦非出自原創(chuàng),又是從比他還要早四百年的晉代學(xué)者顧夷的《吳地記》(原書已佚)里引來(lái)的:“越軍于蘇州東南三十里三江口,又向下三里,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dòng)酒盡,后因立廟于此江上。今其側(cè)有浦名上壇浦。”它告訴我們,歷史上真實(shí)的伍公廟,至少是最早的相關(guān)建筑物,地望確實(shí)是在江邊,而且還有兩座,一座是祠堂,在江心的一個(gè)洲島上,后來(lái)改作了廟,地名胥山;另一座是個(gè)祭壇,設(shè)在江的北岸,地名叫做上壇浦,顯然也是因壇而名。既不可能離江太遠(yuǎn),更不可能是在有著近百米高度的山上。除非你把司馬遷打倒,把《吳地記》和《史記正義》推翻,否則這歷史想要改變是相當(dāng)困難的。
前面說的有關(guān)伍公廟的兩個(gè)關(guān)鍵問題,現(xiàn)在有一個(gè)看來(lái)已經(jīng)基本解決,剩下的就是位置具體在哪里了。三江口的地望要落實(shí)不難,因上述顧夷《吳地記》里另有一條資料,稱“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也就是說,這地方以蘇州過來(lái)計(jì)是東南三十里,以吳江過來(lái)計(jì)是東北七十里,兩條直線交叉的那一點(diǎn),應(yīng)該就是當(dāng)年伍公祠或伍公廟的位置了。再向下三里的江北岸,即為祭臺(tái)所在,地名上壇浦。江是松江,祠在江心,這樣又可計(jì)算出當(dāng)時(shí)江面的寬度,大約為六里左右。北宋郟亶稱此江至唐初尚闊二十余里,這就不一定靠得住了。因古代松江是呈東西向的,在今上海市區(qū)吳淞口附近入海,稱壇在北岸,廟的原始地點(diǎn)就只能是在松江上,而不可能是在東江或婁江上。這個(gè)地方,實(shí)際上也就是《吳越春秋》里說的“三津”或“三道之翟水”。該書卷七勾踐入臣外傳述勾踐因主動(dòng)吃了夫差大便,提前獲釋后辭別吳王:“越王再拜跪伏,吳王乃引越王登車,范蠡執(zhí)御遂去。至三津之上,仰天嘆曰:嗟乎!孤之屯厄,誰(shuí)念復(fù)生渡此津也!”卷十勾踐伐吳外傳述越軍破槜李后一路上打過去,“大敗之于囿,又?jǐn)≈诮迹謹(jǐn)≈诮颍慈颍缡侨龖?zhàn)三北,徑至吳,圍吳于西城。”由于伍子胥冤魂作怪,只允許越人從東門進(jìn)入,因?yàn)樗念^顱懸掛在那里,要等著看好戲。“于是越軍明日更從江出,入海陽(yáng),于三道之翟水,乃穿東南隅以達(dá),越軍遂圍吳。”
伍子胥廟吳地的原始位置弄清楚了,另一頭越地的又是怎么回事呢?這里頭的秘密,應(yīng)該就在連結(jié)兩地的那條東江上了。此江一頭通松江,一頭在今嘉興海寧(古代槜李)通浙江,是春秋時(shí)連接吳越兩國(guó)的主要航道。包括當(dāng)年秦始皇上會(huì)稽祭大禹,巡視考察工作結(jié)束后,也是從這里走的。從現(xiàn)存文獻(xiàn)看,最早將伍子胥的神袛及相關(guān)傳說,通過這條江輸送到這邊的錢塘山陰來(lái)的,可能是東漢時(shí)的上虞人王充。在所著《論衡》中他是這樣說的:“傳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煮之于鑊,乃以鴟夷槖投之于江。子胥恚恨,驅(qū)水為濤,以溺殺人。今時(shí)會(huì)稽、丹徒大江、錢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濤也。”這一紀(jì)錄清楚表明,越地的伍相祠或稱伍公廟,至少在他生活的時(shí)代就已經(jīng)存在了。盡管作為一名唯物主義哲學(xué)家,他對(duì)當(dāng)時(shí)席卷整個(gè)江南的這場(chǎng)民間的信仰狂歡,基本持的是否定態(tài)度,認(rèn)為“夫言吳王殺子胥,投之于江,實(shí)也。言其恨恚,驅(qū)水為濤者,虛也”。但不管是懷疑還是反對(duì),東漢已降,其傳說實(shí)際上(包括寺廟)愈演愈烈,并從江南擴(kuò)散到江北,甚至包括遠(yuǎn)至江蘇淮安(見唐盧恕《楚州新修吳太宰伍相神廟記》)、湖南常德(見唐李善夷《重修伍員廟》)這樣的地方,已是無(wú)法抹殺的事實(shí)。而《越絕書》里“朝夕既有時(shí),動(dòng)作若驚駭,聲音若雷霆”、《錢塘記》里“朝暮再來(lái),其聲震怒,雷奔電走百余里。時(shí)有見子胥乘素車白馬在潮頭之中,因立廟以祀焉”的描寫,又成為有關(guān)后來(lái)名聞世界的浙江潮的最早記錄。
這里需要討論一下有關(guān)會(huì)稽的概念,這一地名來(lái)自偉大的夏禹,為他老人家當(dāng)初治水會(huì)江南諸侯之所。最初只是山名,秦王政二十五年,秦將王翦“定荊江南地,降越君,置會(huì)稽郡”。這才開始成為郡名,郡治所在地設(shè)在蘇州,西漢因之。雖說要到東漢永建四年(129年)政區(qū)調(diào)整,分拆為吳郡和會(huì)稽郡以后,這一冠名權(quán)才能完整地屬于現(xiàn)在的紹興,但越地余暨、山陰、上虞等縣原先也是歸它管的。也就是說,王充說的會(huì)稽也有伍子胥廟,基本指的就是今天紹興沿江一帶。而《吳越春秋》“越王葬種于國(guó)之西山。葬一年(明弘治刊本作七年,此據(jù)明吳琯古今逸史本),伍子胥從海上穿山脅而持種去,與之俱浮于海。故前潮水潘侯者,伍子胥也;后重水者,大夫種也”的記載,更是點(diǎn)明其具體地點(diǎn),很有可能就在現(xiàn)在的濱江區(qū)(原蕭山縣,漢時(shí)為余暨)。因權(quán)威的《漢書·地理志》描述余暨時(shí),文字雖然不多,只稱“蕭山,潘水所出。東入海。莽曰馀衍”。信息量還是相當(dāng)大的。其中最有價(jià)值的就是有關(guān)潘水的紀(jì)錄,連大名鼎鼎的酈道元當(dāng)年也被它難住了,一時(shí)吃不準(zhǔn)怎么回事,只好含含糊糊稱“疑是浦陽(yáng)江之別名也,自外無(wú)水以應(yīng)之”。他沒想到與班固同時(shí)或稍晚的趙曄在書里已經(jīng)補(bǔ)充了線索,只要將兩者聯(lián)系起來(lái),就不難得出結(jié)論。當(dāng)然,他說疑是浦陽(yáng)之別名也不能算錯(cuò),只是沒將出典交代清楚而已。當(dāng)年此江在這里入海,伍子胥的滿腔冤屈要向越地人民傾訴,往北可以借助臨平湖,往南就只有通過浦陽(yáng)江了。至于潘侯的出處何在?伍子胥為什么會(huì)被稱作潘侯?因史料匱乏,鉤稽無(wú)術(shù),只好姑存之以俟高明了。
行文至此,今天吳山上的伍公廟可基本確認(rèn)是個(gè)冒牌貨,《咸淳臨安志》的作者潛說友在書里盡管已做了點(diǎn)手腳,把《史記》里說的“吳人憐之,為立祠江上”。偷偷改成了“吳人憐之,為立祠山上”。(詳見該書卷七十一志五十六祠祀一)然后又以同樣手法,把王安石《伍子胥廟銘》里的“胥山之顏,殿屋渠渠;千載之祠,如祠之初”。也偷偷改成了“胥山之巔,殿屋渠渠;千載之祠,如祠之初”。(詳見《臨川文集卷三十八》)但估計(jì)也沒什么大的用處,因這里頭的戲法,只要稍微動(dòng)點(diǎn)腦筋想一想,要弄清楚并不困難。北宋張君房《靈夢(mèng)志》里述自己站在廟前看到的景象是:“西望阛阓樓臺(tái),出沒煙靄浮沉,若水若山,如繪如畫。”依稀是一派水域風(fēng)光。而程大昌《演繁露》里有條資料,是從已亡佚的北宋李宗諤《祥符杭州圖經(jīng)》里抄下來(lái)的,更能證明此廟的靠不住:“州《圖經(jīng)》云:塘(沙河塘)在縣南五里,此時(shí)河流去青山未甚遠(yuǎn),故李紳詩(shī)曰:猶瞻伍相青山廟。又曰:伍相廟前多白浪也。景龍沙漲之后,至于錢氏,隨沙移岸,漸至鐵幢。今新岸去青山已逾三里,皆為通衢,居民甚眾,此圖經(jīng)之言也。”(見《演繁露》續(xù)集卷四)就是說直到程大昌生活的公元十二世紀(jì)中葉,伍子胥廟的位置應(yīng)該還是在江邊,跟古時(shí)沒什么兩樣。而在稍后紹熙朝進(jìn)士周南的詩(shī)中,就有了很明顯的變化:“廢堞披榛舊,羈臣畢命心。江湖吞故壑,貌相匪斯今。激烈功名在,低徊歲月深。胥門沙衍淺,碑首未應(yīng)沉。”尤其這首詩(shī)的詩(shī)題,就叫做《又題伍相廟,時(shí)新作廟,塑像皆非其舊》(見周南《山房集·山房后稿》)。程卒于南宋慶元元年(1195年),周卒于南宋嘉定六年(1213年),它說明什么?說明就在這不到二十年中,發(fā)生了很讓人驚奇的事情,原來(lái)在西湖吳山上的伍子胥廟,這時(shí)已經(jīng)遷到了某個(gè)別的地方,連廟帶像,都是另起爐灶。潛氏咸淳志成書于宋末,距此不過五十年左右。作為一部號(hào)稱杭州歷史上最有名的方志,《四庫(kù)提要》譽(yù)為“區(qū)畫明晰,體例井然。縷析條分,可資考據(jù)”。地方上如此重大的文化事件,書里非但沒有絲毫交代,反而心有靈犀,遙相呼應(yīng),以對(duì)原始文獻(xiàn)進(jìn)行改動(dòng)的方式相配合,從而為一個(gè)山寨產(chǎn)品披上了合法的外衣。那么,這一切究竟是為了什么呢?
中篇
在杭州文化中,每年八月十八日達(dá)到高峰的錢江潮水,一向被視作是當(dāng)?shù)厝诵愿駝偭乙幻娴募姓故尽v史上,西湖的名氣雖然比它還要大,但因過于柔媚和女性化,尤其南宋林升那首《題臨安驛》產(chǎn)生的負(fù)面影響,持批評(píng)意見的人自然也不在少數(shù)。比如南宋的客寓者周密就曾說它像個(gè)“銷金鍋?zhàn)印保鞔脑欣梢舱f它里面蕩漾著的,是“一湖胭脂水”,像這樣直言不諱的話,杭州人聽了心里一定不以為然,又不好意思公開辯駁或跟人家打筆仗,實(shí)在是很糾結(jié)的事情。好在有一年一度的錢江潮,有那么多令人血脈僨脹的相關(guān)史實(shí),足以證明自己的城市實(shí)際上并不是那么窩囊的。錢镠甲兵三千持彎弓鐵矢射潮的故事;潘閬“萬(wàn)面鼓聲中。弄潮兒向濤頭立,手把紅旗旗不濕”的風(fēng)采;蘇東坡“八月錢江潮,壯觀天下無(wú)”的贊嘆,還有蘇曼殊在異國(guó)回憶杭州寫的那首詩(shī):“春雨樓頭尺八簫,何日重看浙江潮。芒鞋破缽無(wú)人識(shí),踏過櫻花第幾橋。”這詩(shī)的前面兩句,既有柳永紅牙檀拍的婉約,又有蘇軾鐵綽銅琵的豪放,較能代表浙江人的性情。何況在這一切的上面,還有著一個(gè)素車白馬,威風(fēng)凜凜,人見人愛的神,這個(gè)神的名字就叫伍員。
伍子胥是杭州的驕傲,是古時(shí)越地先人花了很大力氣,好不容易才從吳國(guó)人那里爭(zhēng)奪過來(lái)的精神財(cái)富,從春秋的勾踐、范蠡,到漢代的王充、枚乘(或許還有當(dāng)時(shí)的會(huì)稽郡西部都尉一份功勞),再到唐宋間的幾位賢守如李紳、白居易、蘇軾和王安石兄弟等,應(yīng)該說都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其中特別值得予以表?yè)P(yáng)的,還是要數(shù)東漢寫《論衡》的王充,這人畢竟是第一個(gè)從理論角度,為錢唐的伍子胥廟提供了強(qiáng)大的文獻(xiàn)依據(jù)。因勾踐、范蠡殺白馬、立祠祭之的那個(gè)原始地點(diǎn),我們已經(jīng)知道是在古代吳國(guó)地盤、現(xiàn)上海松江區(qū)境內(nèi)的古三江口,地名叫做胥山。而幾乎沒過多少時(shí)候,越國(guó)這邊的錢唐也已經(jīng)有了,地名最初叫做青山,后來(lái)又名吳山,青山廟或吳山廟,兩個(gè)名字基本可以通用。唐乾寧年間因被朝廷封為吳安王,且向有水仙之稱,因此又叫水仙王廟。南宋后期稱忠清廟,元明兩朝襲之,清代至今一直叫伍公廟。盧元輔《胥山廟銘》稱:“漢史遷曰胥山,今云青山者謬也。”強(qiáng)調(diào)廟之所在地古名胥山,叫青山是叫錯(cuò)了,言下之意自然是想露一手,表示自己比別人高明,實(shí)際上真正弄錯(cuò)了的恰恰是他。因胥山是蘇州那個(gè),這在歷史上已有定論,越地先人的高明,就在于一開始就有自己獨(dú)特的、別具一格的稱呼,不然的話,人家一眼就能瞧出你是個(gè)山寨產(chǎn)品,這多難為情啊。姓盧的是個(gè)政治人物,文史本不是他的專長(zhǎng),因此盡管好勝心強(qiáng)了一點(diǎn),應(yīng)該仍屬可恕之列。
現(xiàn)在情況已經(jīng)比較清楚,古代浙江有伍子胥廟,不僅有,而且可能還不止一座。因王充文章里說得很清楚:“今時(shí)會(huì)稽、丹徒、大江、錢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廟。……浙江、山陰江、上虞江皆有濤,三江有濤,豈分槖中之體,散置三江中乎?”盡管身為無(wú)神論者的他,不相信滿江怒濤與伍員的冤魂之間,會(huì)有什么內(nèi)在的精神關(guān)系,更不相信人死了以后其靈魂依然可以存在。客觀上卻也相當(dāng)于在告訴我們,當(dāng)年,只要是錢塘江潮一路經(jīng)過的地方,幾乎都有留下祠廟的可能,都能受到來(lái)自民間或官方的真情祭祀。也就是說,江對(duì)岸的錢塘縣有,江這邊的蕭山縣也有。這一點(diǎn),在前面說的連接原吳越兩國(guó)的東江沿途地區(qū),已得到了很好的印證。如海鹽有尚胥廟,見明張寧《方洲集》卷十八《尚胥廟復(fù)修碑》;平湖乍浦(古春秋武原鄉(xiāng))有水仙廟,又名子胥殿或碧水殿,見《道光乍浦備志》;海寧有鹽官潮神廟,祀子胥、文種等十八人,見《大清一統(tǒng)志》及《海塘志》。以上諸祠,位置無(wú)一不在濱海平地。嘉興城東的胥山廟雖去江已遠(yuǎn),且春秋時(shí)尚屬荒僻之地,顯系后來(lái)好事者附會(huì),故《至元嘉禾志》引邑人張堯同詩(shī):“馬革浮尸去,君王太忽人。此山空廟貌,何以勸忠臣。”實(shí)際上自己是有保留意見的。但此山高度二十余米,卻完全符合《史記》里的相關(guān)記載。只有杭州吳山的那個(gè),高踞于一百多米的山頂,既不合古制也不近情理。這樣明顯的破綻,當(dāng)?shù)貧v史上那么多的碩儒學(xué)者,相信一定也會(huì)有人瞧出有些不大對(duì)勁,或許只是出于某種顧忌,比如說,對(duì)地方文化完整性的維護(hù),以大局為重,因而不愿聲張、不愿捅破而已。
當(dāng)然,要證明吳山上矗著的那個(gè)是假的,是個(gè)典型的二手貨,必須拿出事實(shí)依據(jù)來(lái),說明真的在哪里才能讓人相信。這是一個(gè)相當(dāng)復(fù)雜和麻煩的問題,因古今山川的變遷太大了,所謂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就拿錢塘江兩岸來(lái)說,現(xiàn)在每平方房?jī)r(jià)達(dá)到十萬(wàn)元的西湖周邊地區(qū),一千三百年前的南朝時(shí)還泡在海里,而對(duì)岸紹興的王盤山和赭山,直到明代時(shí)尚屬海寧管轄。尤其是江的走向,據(jù)酈道元《水經(jīng)注》,東漢以前浙江的基本形態(tài)跟現(xiàn)在有較大區(qū)別,“北過余杭,東入于海。”也就是說,要先到安溪、良渚一帶去兜上一圈,合東苕溪而下,再經(jīng)錢唐至臨平入海。因此,王充《書虛篇》里被后世學(xué)者奉為至寶的那段有關(guān)吳越分界的論述,即所謂“越治山陰,吳都今吳,余暨以南屬越,錢塘以北屬吳,錢塘之江兩國(guó)界也。”如果倒轉(zhuǎn)九十度來(lái)看,或許有更能逼近真相的解讀。宋吳仁杰在《兩漢刊誤補(bǔ)遺》里稱“王仲任曰余暨以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吳,錢唐之江兩國(guó)界止。陳后山詩(shī)亦云吳越到江分,是皆承太史公之誤。”正是因?yàn)檫@個(gè)緣故。后漢及三國(guó)時(shí),錢塘、余杭一帶土地日見肥沃,一時(shí)有糧倉(cāng)之稱。為確保那里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國(guó)家最高層有一連串的動(dòng)作,前有陳渾筑西險(xiǎn)大塘之舉,后有吳帝孫皓設(shè)吳興郡,頒布《吳寶鼎置郡詔》,令“吳郡陽(yáng)羨、永安、余杭、臨水及丹陽(yáng)、故鄣、安吉、原鄉(xiāng)、于潛諸縣,地勢(shì)水流之便,悉注烏程。”其后水道大異,東苕溪泄太湖出松江入海,浙江由東西向改南北向,再加上劉道真《錢塘記》所稱之防海大塘的修筑,杭城東北原故道逐漸淤塞,古明圣湖因此形成。包括《水經(jīng)注》所載的其他那些湖泊,如詔息、寶鼎、臨平之類,其成因當(dāng)亦如此。
為什么要啰里八嗦說這些,因當(dāng)年伍子胥廟的位置,考之秦漢文獻(xiàn),應(yīng)該就在這一帶的某個(gè)湖邊或湖中之州島上。島的名字叫做青山,因子胥系吳人的關(guān)系,也有管它叫吳山的。同時(shí),由于周邊系平陸,孤零零突出在那里,時(shí)而又有孤山之名。唐《胥山廟銘》稱“千五百年,廟貌不改”。王安石廟記也感慨“嘆吳亡千有余年,事之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shù),獨(dú)子胥之祠不徙不絕,何其盛也”。但《咸淳臨安志》及《吳山伍公廟志》搜集資料盡管豐富,可惜都是唐宋以后的,于自漢及唐這一千多年間該廟的歷史,卻基本是個(gè)空白。除了署名梁簡(jiǎn)文帝蕭綱的那首五古,詩(shī)題即為《伍子胥廟》,中有句云:“濤洪猶鼓怒,靈廟尚凄清。”又云:“密樹臨寒水,疏扉望遠(yuǎn)城。窗寮野霧入,衣帳積苔生。”想來(lái)其時(shí)因國(guó)家戰(zhàn)事連年,尤其此前發(fā)生在這一帶的孫恩之亂及富陽(yáng)農(nóng)民唐寓之造反等的影響,廟中香火漸趨冷落,已無(wú)復(fù)漢時(shí)風(fēng)光。稍后隋唐時(shí)期錢塘子胥廟名的逐漸被淡化,代之以青山廟、水仙王廟,恐怕也是出于這個(gè)原因。
地方志史料的缺佚,對(duì)有志于研究該廟歷史的人肯定是件麻煩事。但廟志沒有收錄的,并不等于歷代文獻(xiàn)中原本就沒有。因此,打算為浙江的伍子胥廟提供一份相對(duì)完整的精神檔案,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設(shè)法補(bǔ)闕。《三國(guó)志》吳志卷十九孫綝傳敘綝扶持孫和為帝后居功自傲,“綝意彌溢,侮慢民神,遂燒大橋頭伍子胥廟,又壞浮圖祠,斬道人”。由于孫綝當(dāng)時(shí)的主要居住地是在首都建業(yè),因此這件事就被記在南京名下。但文后裴氏注記語(yǔ)焉不詳,只引了《史記正義》里“立祠江上”那段記載了事。《景定建康志》的撰者更是個(gè)老實(shí)人,該書伍相廟條下一會(huì)兒稱“按建康實(shí)錄,吳孫綝侮慢人神,燒大航及子胥廟,今不詳其所”;一會(huì)兒又稱“儀真觀西一水縈回,南入大江,號(hào)曰胥浦”。猜測(cè)那地方有可能就是《三國(guó)志》里所記的那個(gè),就是說,根本拿不出相應(yīng)的地望來(lái),證明當(dāng)?shù)貧v史確有伍子胥廟。實(shí)際上這件事的發(fā)生地,基本可斷定是在杭州。因?qū)O和登基前領(lǐng)瑯琊王銜,其封邑即為錢唐。孫綝在這事上出了力沒得相應(yīng)回報(bào),加上手下兵精將勇,勢(shì)力頗大,因此在皇帝故邑焚祠殺僧以泄憤,同時(shí)也不妨視作是一種有意識(shí)的示威和挑戰(zhàn)。這以后兩人關(guān)系迅速惡化,最終孫和設(shè)計(jì)以叛逆罪誅孫綝,可見這把火燒得實(shí)在有點(diǎn)大。另文中所說的大橋頭或大航,指的就是港口碼頭。三國(guó)時(shí)錢唐有臨平湖,為上通閩粵,下接江淮之重要交通樞紐,其地正當(dāng)杭城東北,跟伍子胥廟原始的位置相去不遠(yuǎn),也堪為一證。
接下來(lái)是南朝阮敘之(《太平寰宇記》作阮升之,此據(jù)《新唐書·藝文志》)《南兗州記》里的一條資料,“孤山有神祠,側(cè)悉生大竹,可以為涔田焉。伐之者必祀此神,言其所求之?dāng)?shù),無(wú)敢加焉。”雖說東晉僑置的南兗州的行政區(qū)域,先為揚(yáng)州,復(fù)為盱眙,后又移治于淮陰。但這些由后人輯錄的佚志,當(dāng)初寫作時(shí)規(guī)格應(yīng)該并不十分嚴(yán)密,比如同時(shí)山謙之的《南徐州記》,所記內(nèi)容就涵蓋了會(huì)稽山陰。加上又是神祠,又是大竹,又是涔田,從地望方面看,要同時(shí)符合這三個(gè)條件的,即使放在全國(guó)范圍內(nèi)來(lái)考察,也唯有杭州孤山之伍子胥廟才足以當(dāng)之。這條資料長(zhǎng)期為長(zhǎng)江對(duì)岸的靖江據(jù)有,應(yīng)該說是個(gè)歷史的誤會(huì)。因它那里那個(gè)孤山,要到唐初天臺(tái)伏虎禪師住錫后才有此名,在這以前一直叫馬汰沙或陰沙,何況沒過多久就墜入了江中。此后是長(zhǎng)達(dá)千年的沉寂,起碼要到明代晚期以后,才重又開始恢復(fù)使用,而且一下又變成了兩座,即太平天國(guó)戰(zhàn)事相關(guān)之大孤山、小孤山也。因此,阮氏筆下所記的孤山,在杭州的可能性,要遠(yuǎn)大于在蘇北靖江。把資料拿來(lái)這邊用了,盡管不無(wú)巧取豪奪之嫌,但靖江人民如果有意見,只要他們說得出那里的山上有何神祠?以及這神祠自古以來(lái)祀的是什么人?到時(shí)可以再還給他們不遲。
我們?cè)賮?lái)看一下同時(shí)代郭璞《神仙傳》所記之葛玄,此人是杭州文化一塊很大的牌子,只是民間常將他的名字跟葛洪混同,知名度受到一定影響罷了。實(shí)際上這個(gè)葛在道家歷史上,無(wú)論資格和地位,要遠(yuǎn)高于那一個(gè)葛,論起輩分來(lái)更是后者的爺爺一輩。當(dāng)?shù)厮^葛塢、葛嶺、葛仙翁葛公井之類景點(diǎn),其實(shí)都是他老人家當(dāng)年留下的行跡,可惜很多都讓他的孫子給分享了。此文后半所稱“又玄游會(huì)稽,有賈人從中國(guó)過神廟,廟神使主簿教語(yǔ)賈人曰:欲附一封書與葛公,可為致之。主簿因以函書擲賈人船頭,如釘著,不可取。及達(dá)會(huì)稽,即以報(bào)玄。玄自取之,即得。”文中賈人指行商者,中國(guó)是越人對(duì)江南吳地的習(xí)慣稱呼,《越絕書》里這方面的例子很多,恕不一一列舉。這個(gè)故事濃烈的神話色彩不去管它,而所謂的神廟,應(yīng)該就是阮升之《南兗州記》里說的那一座,即位于杭城東北,地名或稱青山,或稱吳山,或稱孤山,上面有一座自漢代起就已存在的廟,叫伍子胥廟。
現(xiàn)在大致可以確定,兩晉以降,錢塘伍子胥廟的馬甲,除了青山廟和吳山廟外,還有一個(gè)更帶世俗色彩的稱呼叫神祠或神廟。張君房《靈夢(mèng)志》開首便稱:“淳化癸巳仲冬之晦,張君房適自茂苑來(lái)客余杭,時(shí)抱瘡瘍之患。遽有告曰:凡經(jīng)游是郡者,當(dāng)謁吳山神祠,即伍君子胥也。”此人是北宋祥符年間的錢塘知縣,又是當(dāng)時(shí)的著名學(xué)者,相當(dāng)于已在地方史的意義上給出了明確的結(jié)論。此外南齊宋躬《孝子傳》里有個(gè)故事,或許也能對(duì)我們進(jìn)一步理解神祠這一名號(hào)的由來(lái)有所幫助:“繆斐,東海蘭陵人。父忽患病,醫(yī)藥不給。斐夜叩頭,不寢不食,氣息將盡。至三更中,忽有二神引鎖而至,求斐曰:尊府君昔經(jīng)見侵,故有怨報(bào)。君至孝所感,昨?yàn)樘觳軘z錄。斐驚起,視父已差,父云:吾昔過伍子胥廟,引二神像置地,當(dāng)是此耳。”大意是孝子繆斐因父親生病要死了,一連好幾天不吃飯不睡覺,只跪在地上磕頭,兩位前來(lái)索命的神仙告訴他原因是:你老爸從前在我們廟里,曾經(jīng)把我們的神像推倒在地,因此必須讓他受到懲罰。現(xiàn)在你的孝心感動(dòng)了我們,所以才決定放他一馬。這個(gè)故事或許有過多的傳奇成分,但中國(guó)的普通老百姓喜歡的就是這一套,因此其影響力是非常大的。同時(shí)它也告訴我們,南朝前后該廟確實(shí)有過一個(gè)相對(duì)荒涼的時(shí)期,可證梁簡(jiǎn)文詩(shī)中所詠不誣,是完全可以當(dāng)紀(jì)實(shí)作品來(lái)讀的。你想想,假如當(dāng)初廟相莊嚴(yán),香火旺盛,像現(xiàn)在杭州的靈隱寺或玉皇山的革命烈士陵園,繆斐的老爸膽子再大,性子再頑皮,想必也不敢隨便胡來(lái)。
唐宋兩朝是錢塘伍子胥廟知名度的巔峰時(shí)期,既緣那幫太守兼名士的重量級(jí)人物的抬愛和推波助瀾,也出于當(dāng)?shù)匮该桶l(fā)展的經(jīng)濟(jì)浪潮的現(xiàn)實(shí)需求,因口袋里漸漸有了幾個(gè)錢的杭州人民,變得比以往任何時(shí)候都更渴望獲得生命財(cái)產(chǎn)的安全和保障,錢塘江的掀天巨濤自古稱為天險(xiǎn),可不是隨便鬧著玩的,連秦始皇當(dāng)年到了這里,也被迫放下了皇帝架子,見“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見《史記·始皇本紀(jì)》)因此,一般士商百姓,渡江前到廟里燒炷香拜一拜,叩上幾個(gè)頭,心里畢竟能踏實(shí)不少。從這一意義上說,廟的位置也應(yīng)該是在江邊,而不可能是在距江岸有五六里遠(yuǎn)的高高的山上。謝承《后漢書》載“吳郡王閎渡錢塘江,遭風(fēng)船欲覆,閎拔劍斫水,罵伍子胥,水息得濟(jì)”。估計(jì)上船以前也是拜了磕頭了,因沒見有什么效果,反敬成惡,不過左右是個(gè)死嘛,這才豁出命來(lái)罵一場(chǎng)出出氣,沒想到這一票被他給押準(zhǔn)了呵呵。另一位唐朝的叫周匡物的舉子就沒這么好運(yùn)氣了,在《應(yīng)舉題錢塘公館》一詩(shī)里他感慨:“萬(wàn)里茫茫天塹遙,秦皇底事不安橋。錢塘江口無(wú)錢過,又阻西陵兩信潮。”此詩(shī)載《全唐詩(shī)》四九○卷,其四九四卷又稱系施肩吾作,詩(shī)題為《錢江渡口》。考《太平廣記》及《全唐詩(shī)話》均有周匡物條,稱這位周先生“字幾本,漳州人。元和十二年王播榜下進(jìn)士及第”。且詩(shī)后有“郡牧出見之,乃罪津吏,今天下津渡尚傳此詩(shī)諷誦”云云,當(dāng)以周作為是。
錢镠是五代吳越國(guó)的國(guó)王,同時(shí)也是杭州歷史文化最杰出的開創(chuàng)者。一般人只知道他在位時(shí)廣建佛寺,納土稱宋,筑鐵幢浦、強(qiáng)弩射潮什么的,實(shí)際他對(duì)地方最大的貢獻(xiàn)體現(xiàn)在城建方面,從公元890年到893年,通過兩次飛躍式的擴(kuò)建,讓原來(lái)只有“阛阓十里”的市區(qū),成為內(nèi)城周三十里,外城周七十里的現(xiàn)代化大都市。由于新筑面積大都為潮漲后淤積的沙灘,自然免不了要和伍子胥打交道,于是就有了《吳越備史》里“是歲終,郊封胥山伍子胥為惠應(yīng)侯”、“沙路之患未弭,乃祭江海而禱胥山祠”、“親筑胥山祠,仍為詩(shī)一章,函鑰置于海門”等等的這些頻繁的記錄,其殷勤恭謹(jǐn)之意可謂極矣。這也難怪,在沒有機(jī)械和電力的年代,哪怕其身貴為東南霸主,吃的也只能是望天飯,這姓伍的畢竟是古代浙江人精神世界里的最高主宰,誰(shuí)又敢得罪他啊。好在“為報(bào)龍神并水府,錢塘且借作錢城”的請(qǐng)求,倒也獲得了恩準(zhǔn)。“既而潮頭遂趨西陵,王乃命運(yùn)巨石,盛以竹籠,植巨材捍之,城基始定。其重濠累塹,通衢廣陌,亦由是而成焉”。(《吳越備史》卷二)比較可惡的是靈隱《武林截潮志》所載的那個(gè)版本,說什么“有寶達(dá)和尚,會(huì)浙江大溢,潮至湖山,達(dá)持咒止之。自是潮系西興,而錢塘沙漲成陸云”。(見《永樂大典》殘卷十一輯)把吳越國(guó)上下二十余萬(wàn)軍民的努力,居然變成是他一個(gè)人裝神弄鬼的功勞了,這也不去管它。本次造城運(yùn)動(dòng)帶來(lái)的另外一個(gè)好處是,本來(lái)在城外的伍子胥祠,從此以后變成是在城內(nèi),這對(duì)想要研究它,確定它真實(shí)位置的人來(lái)說,肯定是個(gè)好消息,至少搜索捕捉的范圍較前已大為縮小,從而使對(duì)真相的破譯,變得比以往任何時(shí)候都更有可能。如果再夸張一點(diǎn),差不多可以說已是甕中捉鱉、呼之欲出了。
下篇
公元九九三年深冬的一個(gè)下午,一位年輕的落魄士子從蘇州搭乘航船來(lái)杭州旅游,神情肅穆地佇立在吳山伍員廟前。因?yàn)楫?dāng)時(shí)他不僅久試未第,而且還身染惡疾,滿身都是大大小小的瘡皰,治了好久也沒治好。房東告訴他說:我們杭州有座吳山廟蠻靈的,有求必應(yīng),有難必解,不妨可以去試上一試。因此于到達(dá)次日就趕去那里,并在廟中道長(zhǎng)引導(dǎo)下抽了一簽,簽曰:時(shí)來(lái)自有期,此去不憂運(yùn)。行心但如此,非久銷疾病。“甫讀于口,意亦知其吉告矣。感激而別,既下山百步,忽聞梅香,回望其上,乃昨日所見之花,爛然在目。因驚悟曰:此吳山廟也。于是遂覺其清香芬馥,滿衾枕間,良久方歇。自是瘡瘍之苦,浹旬而愈,于戲靈神之告也若是乎?”(見《分門古今類事》卷八所引《該聞錄》)這個(gè)人,就是我們前文說起過的宋代道家杰出人物張君房。二十二年后當(dāng)他的身影重又出現(xiàn)在廟前,其身份已從昔日貧病交加的書生,搖身一變而為新上任的錢塘知縣大人了。在郡四年,政績(jī)不少。他寫于離任前的《靈夢(mèng)錄》,為歷史上有關(guān)杭州伍員廟的最早文獻(xiàn)之一,僅次于唐代盧元輔的《胥山銘序》,而早于王安石兄弟的《伍子胥廟記》和《胥山廟記》。根據(jù)原文“今考秩告滿,將遠(yuǎn)靈祠,茍不掲文志石,即不獨(dú)曠于宿心,亦負(fù)王之靈告也。因镵而壁之,冀人知王之靈應(yīng)事”所述,該記是以刻碑方式列于廟前的。時(shí)間為“天禧三年秋九月二十一日”。輯于清代中期的《吳山伍公廟志》素稱搜集資料贍富,但這篇重要的文獻(xiàn)還是給漏下了,不能不說是一個(gè)遺憾。這有可能限于編者的視野,也有可能是因文中所述與現(xiàn)吳山上那個(gè)有沖突,因此只好對(duì)不起它了。書中這方面例子很多,只要牽涉到該廟的原始地望,如詩(shī)文中有“江上”、“湖上”、“潮頭”之類字眼的,哪怕作者是如白居易、李紳、徐凝、蔡襄這樣的大名家,基本也都篩而不選,跟現(xiàn)在互聯(lián)網(wǎng)的關(guān)鍵詞預(yù)設(shè)功能差不多,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己去找來(lái)看一下。
然而,此人對(duì)杭州的貢獻(xiàn)并不僅于此,自漢迄唐,歷代文獻(xiàn)在解釋錢唐的出典時(shí),大都引用《漢書地理志》和《錢塘記》了事,前者稱:“錢唐,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后者稱:“防海大塘在縣東一里,郡議曹華信家議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有能致一斛土者,即與錢一千,旬月之間,來(lái)者云集,塘未成,而不復(fù)取,于是載土石者皆棄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錢塘。”這兩部書雖說是杭州地理的源頭性著作,但歷史久遠(yuǎn),加上句讀也存在爭(zhēng)議,因此根本解決不了實(shí)質(zhì)性的問題。而他作于任上的《辨錢塘》,引用了現(xiàn)已佚亡的《十三州記》里的資料,加上自己的實(shí)地踏勘,于這一研究領(lǐng)域有全新的突破:“杭州武林山高九十二丈,周回三十里,在錢塘縣南十二里,靈隱寺正坐其山。寺之東西瀵二水,東龍?jiān)矗瑱M過寺前,即龍溪也,冷泉亭在其上。西曰錢源,其流洪大,下山二里八十步過橫坑橋,入于錢湖,蓋錢源之聚滀也。錢湖一名金牛湖,一名明圣湖,湖有金牛,遇圣明即見,故有二名焉,錢湖即本名也。今萬(wàn)松嶺下西城第一門曰錢湖門,可驗(yàn)其實(shí)。行次北第二門曰涌金門,即金牛出見之所也。第三門曰錢塘門,乃縣廨在焉。蓋自前古以來(lái),居人筑塘以備錢湖之水,故曰錢塘。”(詳見趙彥衛(wèi)《云麓漫鈔》錢唐條)歷史上《十三州志》有二,作者一為東漢應(yīng)劭,一為南齊闞骃。后者有清人張澍輯本,只稱“武林山出錢水,東入海”。并無(wú)有關(guān)此山高度面積之詳細(xì)記載,因此引自應(yīng)劭原書的可能性很大,如果真是這樣,那就更有價(jià)值了。
張君房是北宋前期人,生卒年雖無(wú)法考證,但系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進(jìn)士這件事,卻于史可稽,所處時(shí)代去五代未遠(yuǎn),因此他筆下所記錄的杭城風(fēng)貌,應(yīng)該正是錢镠公元十世紀(jì)初重筑子城羅城(又名吳越西府和鳳凰城)后形成的規(guī)模。其中“西望阛阓樓臺(tái),出沒煙靄浮沉,若水若山,如繪如畫”的描寫,與周密《癸辛雜識(shí)》西湖好處條“江西有張秀才者,未始至杭,胡存齋攜之而來(lái)。一日泛湖,問之曰:西湖好否?曰:甚好。曰:何謂好?曰:青山四圍,中涵綠水,金碧樓臺(tái)相間,全似著色山水。獨(dú)東偏無(wú)山,乃有鱗鱗萬(wàn)瓦,屋宇充滿,此天生地設(shè)好處也”異曲同工,可見其格局至南宋尚基本保持不變。杭州最早的地方志《乾道臨安志》也稱“大內(nèi)在鳳皇山之東,以臨安府舊治子城增筑”。八十年后《淳佑臨安志》又進(jìn)一步予以了補(bǔ)充:“府治舊在鳳凰山之右,自唐為治所。據(jù)隋志,開皇中移州居錢塘城,復(fù)移州于柳浦西,依山筑城,即今郡是也,豈即鳳山之治乎?自唐以來(lái),實(shí)治鳳山,錢氏所居,特因之爾。”賴《南村輟耕錄》得以保存的南宋文獻(xiàn)陳隨應(yīng)的《南渡行宮記》,說得更是明白:“杭州治,舊錢王宮也。紹興因以為行宮,皇城九里。”
而我們要搜尋的伍子胥廟的原始地址,應(yīng)該就在這煙靄浮沉,青山四圍,中涵綠水,金碧樓臺(tái)相間的某處,確切點(diǎn)說,是在湖中的某個(gè)洲島上。不管這湖叫明圣湖、金牛湖、錢塘湖還是西湖,不管這山叫胥山、青山、孤山還是吳山,也不管這廟叫子胥廟、青山廟、伍員廟、孤山神祠、水仙王廟、忠清廟、伍龍王廟還是伍公廟,因?yàn)檫@些問題,自古以來(lái)好像就沒完全弄清楚過,或有人故意讓它弄不清楚。哪怕前有著名的南宋臨安三志、《萬(wàn)歷杭州府志》、《西湖游覽志》和《西湖游覽志余》,后有《西湖志》、《南宋古跡考》和總數(shù)為二十六集數(shù)千卷的洋洋灑灑的《武林掌故叢編》,大都也是你說你的,我說我的,或你抄我的,我抄你的,相信你如果下決心花上幾年時(shí)間通讀一遍的話,其結(jié)果可能也是越讀越糊涂。但有個(gè)基本事實(shí)恐無(wú)法改變,那就是說,它只是江中或湖中島上的一個(gè)建筑物,且具有濃厚的世俗色彩,而不可能是在遠(yuǎn)離水域的地方,更不可能是在海拔較高的地方。東漢以前湖水通江,它是在江上。兩晉浙江改道,劉道真筑防海大塘成,它是在湖上。陳隋兩朝海水、江水時(shí)分時(shí)合,它也只好跟著時(shí)江時(shí)湖。唐代景龍三年沙漲、尤其后來(lái)五代吳越錢镠增筑錢塘城,射潮捍堤,北宋張夏、陳堯佐等地方要員筑堤手段科技量提高,這才將它與江水海水基本分離了開來(lái)。蘇軾那個(gè)著名的論斷“潮水避錢塘,而東擊西陵,所從來(lái)遠(yuǎn)矣。沮洳斥鹵,化為桑麻之區(qū),而久乃為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陸,皆江之故地。”(《錢塘六井記》)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來(lái)的。盡管如此,也不能說從此就完全太平無(wú)虞了。在以后年代里,碰到江潮過猛或暴雨連旬,江水湖水還是免不了有會(huì)面的機(jī)會(huì),這樣的例子在《宋史》甚至《元史》里很容易找到。要說到徹底隔絕,估計(jì)要到明代中期海寧沿江四十多里的城邑集體塌陷,錢塘江放棄原來(lái)的南大門改走北大門以后。現(xiàn)在看潮的最佳位置是在鹽官,而不是原來(lái)的浙江閘和龍山閘,就是一個(gè)很好的證明。
說到蘇東坡,此人是西湖文化最積極的鼓吹者和推動(dòng)者,一生所寫的有關(guān)杭州的詩(shī)文,不下百首,且大多膾炙人口,影響彌遠(yuǎn)。盡管如此,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在某些地方志編撰者眼里,這位一千年前的杭州老市長(zhǎng),或許同時(shí)也會(huì)被視作是個(gè)麻煩制造者,讓他們一想起來(lái)就頭痛不已。為什么這么說因?yàn)樗?shī)中所包含的豐富的地理信息,與官方權(quán)威部門所告訴我們的頗多矛盾扦格之處,有的甚至是以唱對(duì)臺(tái)戲的方式呈現(xiàn)的。比如本文開頭提到的他的《法惠寺橫翠閣》詩(shī):“朝見吳山橫,暮見吳山縱。吳山故多態(tài),轉(zhuǎn)側(cè)為君容。”說明此山的外表特征應(yīng)為狹長(zhǎng)形。此公一生兩度出守杭州,上班喜歡在府治后鳳山上的十三間樓披閱公文,飲酒會(huì)客,傍晚時(shí)分才下來(lái)回市府大院賓館休憩,由于角度不同,時(shí)常能看到不同的形態(tài),因有此詠,跟現(xiàn)在杭州西湖大道盡頭那個(gè)根本對(duì)不上號(hào)。再比如他的《乞相度開石門河狀》,這是元祐六年再度宰杭時(shí)向朝廷打的報(bào)告,希望能獲得國(guó)家撥款,新筑一條從現(xiàn)在江干玉皇山南沿山腳至富陽(yáng)境內(nèi)石門的人工運(yùn)河,以避令當(dāng)時(shí)舟船聞之失色的定、浮二山江潮的兇險(xiǎn)。為節(jié)約成本,報(bào)告內(nèi)提到“并江為岸,度潮水所向則用石,所不向則用竹”。也就是說,靠江一面因需抵捍江潮沖擊,必須不惜工本以堅(jiān)固大石駁岸,靠山一面壓力相對(duì)小一些,因此用吳越時(shí)代的老辦法,即“以竹籠石植大木圉之”(見《吳越備史》)就可以了。而杭州的地志專家們——包括古代的和當(dāng)代的,卻幾乎異口同聲地認(rèn)為,《新唐書》里列于鹽官條下的“長(zhǎng)百二十四里,開元元年重筑”的捍海塘堤,還有后來(lái)錢镠時(shí)代的捍江大堤和鐵幢浦,早就已經(jīng)筑在那里了,運(yùn)河從唐代起就可以從玉皇山一直通到六和塔下,甚至還有不少人堅(jiān)稱那里就是北宋以前杭州市政府的所在地呵呵。
對(duì)本文而言,相比前面所引的,他任上留下的有關(guān)有美堂的那些詩(shī)或許更為關(guān)鍵,因這跟我們要找尋的伍子胥廟原址息息相關(guān),自然也就更值得引起重視。“游人腳底一聲雷,滿座頑云撥不開。天外黑風(fēng)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lái)。十分瀲滟金樽凸,千杖敲鏗羯鼓催。喚起謫仙泉灑面,倒傾蛟室瀉瓊瑰。”此詩(shī)是他同一題材中最有名的,題為《有美堂暴雨》,盡管意象詭奇繁復(fù),透露出的地理信息也有讓人不解之處,比如說以現(xiàn)在西湖的位置,說近江已經(jīng)很夸張了,更遑論近海,詩(shī)中卻不說“吹江立”而說“吹海立”。但等到讀了他另外的那些后,這小小疑問也就算不上什么了。《會(huì)客有美堂,周邠長(zhǎng)官與數(shù)僧同泛湖往北山,湖中聞堂上歌笑聲,以詩(shī)見寄,因和二首,時(shí)周有服》、《九日舟中望見有美堂上魯少卿飲處,以詩(shī)戲之》,這兩首詩(shī),相信光看看詩(shī)題就足以讓人吃驚,以至已不必再征引具體內(nèi)容了。我們知道,有美堂是杭州北宋的著名建筑,嘉佑二年龍圖閣直學(xué)士梅摯出守是邦,仁宗皇帝贈(zèng)行詩(shī)有“地有湖山美,東南第一州”之句,因此到任后就在原吳越西府江湖亭廢址上筑有美堂以示天寵,歐陽(yáng)修為之撰記,大書家蔡襄書碑,堪稱一時(shí)名流風(fēng)雅之最。《淳佑臨安志》該條名下介紹道:“在吳山最高處,左江右湖,故為登覽之勝。”
現(xiàn)在的問題是,盡管該堂的位置是在吳山絕頂,蘇東坡在湖上舟中不僅可以聽到堂中傳來(lái)的歡聲笑語(yǔ),甚至還能看到正在堂上喝酒的魯少卿的身影。可以想象,對(duì)于那些堅(jiān)稱吳山就是現(xiàn)在杭城西南高一百米、毗鄰鳳凰山的那個(gè)的人來(lái)說,這是何等的尷尬。當(dāng)然,比起后來(lái)撰咸淳志的潛說友來(lái),淳熙志作者施諤相對(duì)還是比較老實(shí)的,因他在自己大著里如實(shí)收入了蘇軾有關(guān)此堂的全部詩(shī)作,并坦承“東坡詩(shī)言自舟中望見堂上燕集,此必西湖舟中也。”這就相當(dāng)于承認(rèn)吳山是在西湖中了,不過是以一種比較含蓄的方式表達(dá)出來(lái)罷了。而姓潛的采取的卻是全然回避的態(tài)度,將相關(guān)詩(shī)文全部刪去,只稱“嘉佑二年梅龍學(xué)摯出守,仁宗皇帝賜詩(shī)。摯乃作堂,取賜詩(shī)首句名之曰有美。歐陽(yáng)公修為記,蔡端明襄書”了事。聯(lián)系到他前面篡改《史記》里的“立祠江上”為“立祠山上”,篡改王安石《伍子胥廟銘》里的“胥山之顔”為“胥山之巔”,就不能說是完全出自無(wú)心的了。如果只看潛志不看施志,這件事或許就很少會(huì)被人發(fā)現(xiàn),因又是蘇東坡粉絲又對(duì)杭州地理有特殊興趣的人,數(shù)量畢竟相當(dāng)?shù)挠邢蕖8螞r施諤的這部《淳佑志》問世未久即從人間蒸發(fā),連大名鼎鼎的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和馬端臨《文獻(xiàn)通考》都未著錄,可見在宋代晚期就已經(jīng)看不到了。該書現(xiàn)殘存的六卷,據(jù)知不足齋主人鮑廷博原跖,是混入一個(gè)殘本潛志內(nèi),因其中第四卷至第九卷稱宋理宗為今上,而《咸淳臨安志》的成書是在宋度宗時(shí)代,不應(yīng)出現(xiàn)這樣的低級(jí)錯(cuò)誤,這才引起懷疑。經(jīng)過嘉道年間孫學(xué)詩(shī)、黃丕烈、陳鳣、吳免床等一幫牛人考證,確認(rèn)“應(yīng)是施諤《淳佑志》羼入”,因而從中抄出,整理后單獨(dú)出版,這樣,絕跡八百年的這部南宋佚志的部分內(nèi)容,才有幸為世人所睹。
讓人不免產(chǎn)生聯(lián)想的是,杭州另一部南宋地方志《乾道臨安志》,其命運(yùn)好像也是這樣,甚至比《淳佑志》都不如。不僅后世人見不到,就連同時(shí)代人的著作里,也少見征引。無(wú)數(shù)年代的默默無(wú)聞,灰飛煙滅,好像歷史上從未有過這么一部書一樣,直到清代中期,才讓海寧藏書家孫晴厓先生于京師故舊人家售物中有幸見到,但僅存可憐的三卷,且內(nèi)容大都無(wú)關(guān)緊要。一般而論,書籍不像瓷器名畫那樣因是單件而保存不易,方志是工具書,發(fā)行量應(yīng)該更為可觀。縱觀本省南宋編撰的十余部志書,大多地方都保存得相當(dāng)完整的,唯獨(dú)杭州的三部,只留下一部完整的,就是潛說友自己那部,這種現(xiàn)象,能否可以說是完全正常?如果使用魯迅的方法,不憚以最大的惡意來(lái)揣測(cè),說這里頭或許有人為的痕跡,或者干脆挑明了,說這姓潛的可能從中做了什么手腳,也不算怎么冤枉他。何況此人在當(dāng)初也絕非善類,《宋史》無(wú)傳,但從散落書中那些零星記載看,沒說他一句好話,又是:“潛說友尹京,恃賈似道勢(shì),甚驕蹇,政事一切無(wú)所顧讓。”又是“潛說友以平江降,臺(tái)臣請(qǐng)籍其家。”又是“潛說友削三官,奪侍從恩數(shù)。”四庫(kù)提要《咸淳臨安志》條下稱:“說友字君高,處州人。宋淳佑甲辰進(jìn)士,咸淳庚午以中奉大夫權(quán)戶部尚書,知臨安軍府事,封縉云縣開國(guó)男。時(shí)賈似道勢(shì)方熾,說友曲意附和,故得進(jìn)。越四年,以誤捕似道私秫罷。明年起守平江,元兵至,棄城先遁。及宋亡,在福州降元,受其宣撫使之命。后以官軍支米不得,王積翁以言激眾,遂為李雄剖腹死。”算是為他的一生作了詳細(xì)介紹,或稱蓋棺定論。
更麻煩的事情應(yīng)該還在后面,《飲湖上初晴后雨二首》是蘇軾西湖系列詩(shī)作中最有名的,但一般人只知道他的“水光瀲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卻不知另一首“朝曦迎客艷重岡,晚雨留人入醉鄉(xiāng)。此意自佳君不會(huì),一杯當(dāng)屬水仙王”同樣也很重要,如果從地方文史角度而論,價(jià)值或許比前面一首還要重大。不僅因?yàn)樵?shī)里有個(gè)關(guān)鍵詞“水仙王”,更要命的是詩(shī)后還附有一個(gè)作者自注:“湖上有水仙王廟。”這就相當(dāng)于直接點(diǎn)明不僅吳山在西湖上,伍子胥廟也是在西湖上了。因杭州的水仙王廟就是伍子胥廟,這一點(diǎn)歷代方志文獻(xiàn)從沒有人懷疑過。沈德潛的《西湖志纂》因是受乾隆委托編的,自然不敢含糊,考證方面下的功夫不少,該書卷三稱:“臣謹(jǐn)按,水仙王廟,本伍胥祠。胥浮尸江上,吳人稱為水仙,見《越絕書》。唐乾寧間,封吳安王,因有水仙吳王之稱。”
或許有人還會(huì)有疑問,就算同意吳山是在西湖上的觀點(diǎn),又會(huì)是在西湖哪里呢?因這上面沒有別的山,只有一座孤山。準(zhǔn)確的答案是,吳山就是孤山,這兩座山實(shí)際上是一回事,包括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的巫山,漢代的胥山,唐代的青山,說的其實(shí)也就是它,不過一山多名罷了。這一結(jié)論實(shí)際上也來(lái)自蘇詩(shī),其《書林逋詩(shī)后》結(jié)尾“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盞寒泉薦秋菊。”詩(shī)后同樣也有作者自注:“湖上有水仙王廟。”跟前面的一字不多,一字不少,這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當(dāng)然,在潛說友的《咸淳臨安志》里,你可以找到這首詩(shī),但絕對(duì)找不到后面那個(gè)自注,這一點(diǎn)我可保證。宋代孤山最著名的人物是林逋,東坡守杭時(shí)其人過世已有近七十年,蘇認(rèn)為林的高風(fēng)亮節(jié)可追攀子胥,因此建議為他塑像,放進(jìn)水仙王廟里陪伴寂寞的伍員先生,彼此同享千古。他的好友黃庭堅(jiān)其時(shí)在湖北荊州,有詩(shī)紀(jì)其事云“錢塘昔聞水仙廟,荊州今見水仙花。暗香靜色撩詩(shī)句,宜在林逋處士家”。詩(shī)后也有自注:“錢塘水仙廟,林和靖祠堂近之。東坡先生以和靖清節(jié)映世,遂移神像,配食水仙王。”這就把吳山與孤山的關(guān)系挑得更明了。

一百三十年后南宋寶慶元年杭州市長(zhǎng)袁韶重筑伍廟,撰《水仙王廟記》,不過那時(shí)吳山早為南宋大內(nèi)所征用,成了皇家宮室禁苑,好在其過程在文中有較詳細(xì)的交代:“按錢唐水仙王事,始見于蘇文忠公詩(shī)。公詩(shī)石本今有,自書其左方曰:今西湖有水仙王廟。仙之廟于湖,公出守時(shí)蓋無(wú)恙,后莫知廟所在。六龍南渡,杭為帝所,絡(luò)孤山筑殊庭,得不廢者,惟和靖墓,他皆一掃刮絕去。荒基老屋,漫不見蹤跡,廟之廢未必不于此。”也就是說,林逋的舊居尚在,伍子胥卻早已被趕了出去,從此開始了它漫漫無(wú)期的流浪生涯。先是在西湖北山將就了一陣,跟錢塘廣潤(rùn)龍王併居,住在同一個(gè)廟里,多年后遇上新來(lái)的領(lǐng)導(dǎo)重視文化,這才在蘇堤六橋的第三橋北有了新居(即袁氏所筑),不過隔了那么些年,一般市民已很少有人知道水仙王廟就是原吳山的伍員廟,何況那時(shí)吳山的名字也早已習(xí)慣稱為孤山。等咸淳四年新市長(zhǎng)潛說友上臺(tái),當(dāng)年就動(dòng)手將廟改為崇真道院,留給伍子胥的大概只有某個(gè)角落里一個(gè)不起眼的位置。這話不是我說的,是他自己說的,有《咸淳臨安志》卷七十五寺觀一原文為證:“崇真道院在蘇公堤。咸淳四年,太傅平章賈魏公給錢創(chuàng)建,仍撥租田以贍云侶。其地舊有水仙王廟,并以香火之奉屬焉。”當(dāng)然,在此之前已被干掉的可能性,也不是沒有,如果那樣的話就更讓人痛心了。
再后來(lái),估計(jì)時(shí)機(jī)已經(jīng)成熟,加上宋末杭城那幾場(chǎng)毀滅性的大火,新的吳山和新的伍公廟于是橫空問世,時(shí)間大約為元代的至元年間,我們的子胥先生從此離開他賴以存身的水域,高高地永居在那里一百多米的峰頂了。這事杭州的地方志里自然不會(huì)有記錄,但碰巧被當(dāng)時(shí)隱居湖州的慈溪詩(shī)人黃玠看到了,非但看到,居然還用詩(shī)歌的形式秘密記錄了下來(lái)。這就是《弁山小隱吟錄》卷二里那首觀《浙省新址》了:“錢唐故都猶麗雄,民居百萬(wàn)如蟻封。一夕熛怒赤熁空,市舍歘忽隨歊風(fēng)。丞相夜下哀瘝恫,飛書走檄動(dòng)帝聰。大寬賦入振乏窮,乃恢黃堂基益隆。斯民子來(lái)爭(zhēng)赴功,豈弟君子汲黯同。吳山蜿蜒若火龍,渴欲急水鱗甲紅。胡不移置山南東,遠(yuǎn)挹江上青數(shù)峰。岡阜回合水朝宗,環(huán)拱北極當(dāng)天中。”至于離開了他賴于為生的水,搬到高高的山上去住的伍子胥,在那里能否習(xí)慣,是否適應(yīng),心里又會(huì)想些什么,這些就不是我們所能知道的了。為什么要這樣做,雖說存在著多方面的因素,但此人政治身份及寓意的復(fù)雜,應(yīng)該是其中最主要的,畢竟這是中國(guó)歷史上第一個(gè)無(wú)法無(wú)天的臣子,什么事情都有自己一套想法,要跟皇帝對(duì)著干,沒人吃得消他!這就注定他從此不會(huì)再有好日子過。
現(xiàn)在真相已經(jīng)基本清楚,但還有兩條事似值得一提,一是有個(gè)叫孫花翁的,系南宋中期著名詞人,長(zhǎng)期客寓杭州,詩(shī)酒風(fēng)流,在江湖上也很有些名頭,死后劉克莊等好友將他葬于吳山水仙王廟側(cè),在當(dāng)時(shí)也算是高檔墓地了,本想附此以托不朽,沒想到弄巧成拙,因水仙王廟一次次地搬遷,而他墓在廟側(cè)這件事是寫進(jìn)地方志的,如廟遷而墓存,這戲法就要穿幫,無(wú)奈之下只好跟著到處流浪。詳見俞曲園所撰《國(guó)朝重修孫花翁墓記》。二是《咸淳臨安志》里極力美譽(yù)的趙與(上睪下廾),此人系宋室宗親,生平先后四次出任臨安知府。姓潛的曾為他下屬,小有恩遇,因此涌字相報(bào),在書里提到他大名一百次都不止,把他的政績(jī)吹得比白居易蘇東坡還要出色,實(shí)際上此人是個(gè)奸猾之徒,跟潛氏自己可謂同路人物。《宋史》里記了他兩件事,慶元二年韓侘冑生日,“師(上睪下廾)最后至,出小盒曰:愿獻(xiàn)少果核侑觴。啟之,乃粟金蒲萄小架,上綴大珠百余,眾慚沮。侂胄有愛妾十四人,或獻(xiàn)北珠冠四枚于侂胄,侂胄以遺四妾,其十人亦欲之,侂胄未有以應(yīng)也。師(上睪下廾)聞之,亟出錢十萬(wàn)緡市北珠,制十冠以獻(xiàn)。妾為求遷官,得轉(zhuǎn)工部侍郎。”稍后由陸游撰記的韓的新居南園建成,“侂胄嘗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茅舍,謂師(上睪下廾):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犬嗥從薄間,視之乃師(上睪下廾)也,侂胄大笑久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更是記他借重修所謂五王廟之機(jī),“其中三像,一模韓侘胄像,一模陳自強(qiáng)像,一模師(上睪下廾)像”。實(shí)在無(wú)恥得有些過分了。因據(jù)沈德潛考證,“《越絕書》云子胥水仙也,唐時(shí)累封王爵,因號(hào)水仙王廟,在吳山。蘇軾有《開湖禱吳山水仙伍龍王廟文》,又有《謝吳山水仙伍龍王祝文》。后人訛伍為五,建祠柳洲,始建月日無(wú)考。咸淳志稱開禧中趙師(上睪下廾)并五龍王祠入柳洲寺,聞見錄又云重塑五王像,當(dāng)是師(上睪下廾)并舊祠而易以新祠,重為塑像,遂稱龍王堂。”也就是說,對(duì)原伍員廟進(jìn)行山寨化處理,實(shí)施調(diào)包計(jì),實(shí)際上最早是從此人手里開始的。因此在想象中,像岳廟處理秦檜等人一樣,讓趙、潛兩人的遺像跪于伍子胥廟門前,應(yīng)該是比較好玩的事情。當(dāng)然,這不過是想象,其定義就是現(xiàn)實(shí)中所無(wú)法完成的。就像我費(fèi)時(shí)三月寫作這篇文章,同樣也只能是紙上談兵,實(shí)際上什么問題也解決不了。今天,吳山上的伍公廟依然高高挺立在那里,接受科技時(shí)代的香火和膜拜,而我們當(dāng)年性如霹靂、聲如雷霆的憤王,經(jīng)過多年世俗煙火的熏陶,說不定也早已改變了原先剛烈的、視惡如仇的脾氣,成為一名人見人愛的好好先生了。歷史是個(gè)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這話是胡適說的,也有人稱系從西諺轉(zhuǎn)引。但不管是他說的,還是別人說的,總之這是一句相當(dāng)有道理的話。既然如此,我想我也就沒什么可抱怨的了。

續(xù)篇
公元一百四十四年初夏的一個(gè)上午,折合舊歷為東漢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時(shí)逢佳節(jié)端午,一場(chǎng)由民間組織的慶典活動(dòng)正在上虞城西江畔聲勢(shì)浩大舉行。其中有個(gè)主打節(jié)目,是由一名資深歌手扮演巫師,通過吟唱的方式與想象中的神進(jìn)行對(duì)話,向后者傳遞塵世蕓蕓眾生的訴求與期盼。此人姓曹名盱,是當(dāng)?shù)刈钪拿耖g音樂家,類似的活動(dòng)中每次都能見到他活躍的身影。但在這一年、這一天的這一刻,悲慘的事情意外發(fā)生了。當(dāng)祭祀進(jìn)行到一半時(shí),潮水突然兇猛上漲,正在船頭深情表演的曹先生猝不及防,連人帶船被瞬間卷入了江心。等才滿十四歲的愛女聞?dòng)嵑筇?hào)哭著趕來(lái),已經(jīng)連尸體都不知漂浮到了哪里,傷心欲絕的女兒在江邊哭了七天七夜后,毅然跳入江中追隨父親而去,這就是歷史上大大有名、我們今天在小學(xué)語(yǔ)言課本上還能讀到的孝女曹娥的故事。
此事最早由西晉作家虞預(yù)紀(jì)錄在所著《會(huì)稽典錄》里。或許,正因?yàn)檫@故事太動(dòng)人了,精神感染力太強(qiáng)大了,以致此文所包涵的其他重要信息,為后來(lái)研究者忽略。由于《會(huì)稽典錄》原文已佚,現(xiàn)存此條主要見于《后漢書》、《世說新語(yǔ)》、《太平御覽》、《藝文類聚》四書所引,其中又以《世說新語(yǔ)·捷悟》注引為最完整,開頭一段作者是這么說的:“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撫節(jié)按歌,婆娑樂神。漢安二年,迎伍君神,溯濤而上,為水所淹,不得其尸。”文中“伍君神”三字至為關(guān)鍵。自王充《論衡·書虛篇》首次指出伍子胥廟非蘇州一地所有,明言“今時(shí)會(huì)稽丹徒大江、錢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廟”。隨后又稱:“或言投于錢塘浙江,浙江、山陰江、上虞江皆有濤,三江有濤,豈分槖中之體,散置三江中乎?”文意所隱含的無(wú)神論思想因非本文重點(diǎn),可暫時(shí)不管,但越地有關(guān)伍氏身后最早的文獻(xiàn)始見于此,而《會(huì)稽典錄》所記,相當(dāng)于又為這一原始記錄作了很好的補(bǔ)充。如果這還不夠,《晉書·夏統(tǒng)傳》里另有一段對(duì)話,也相當(dāng)精彩。夏是會(huì)稽永興(蕭山古稱)人,當(dāng)初他向朝中諸公介紹家鄉(xiāng)的文化脈流,其中也談到了伍子胥,并稱當(dāng)?shù)赜袑iT為紀(jì)念此人創(chuàng)作的歌曲:“伍子胥諫吳王,言不納用,見戮投海,國(guó)人痛其忠烈,為作《小海唱》。”曹娥老爸遇難前在船上唱的,估計(jì)就是這首了。
這里又要牽涉到有關(guān)伍氏死后精神傳播路線那個(gè)老話題了,在沒有公路和高鐵的年代,水路運(yùn)輸在國(guó)家經(jīng)濟(jì)生活中占絕對(duì)主流地位,當(dāng)年遵循的基本也是這一原則。也就是說,它不可能流傳到泰山和大別山,哪怕連較近的黃山也不會(huì),而只能是江河川瀆暢通之地。吳越兩地相鄰,中間又有一條連接兩國(guó)的主航道吳通陵江(后名東江),因此成為最早的受益之地也是很自然的事。而且不僅僅是精神遺產(chǎn),按《越絕書》的說法:“王使人捐于大江口,勇士執(zhí)之,乃有遺響,發(fā)憤馳騰,氣若奔馬。威凌萬(wàn)物,歸神大海。仿佛之間,音兆常在。后世稱述,蓋子胥水仙也。”而稍后《錢塘記》更是聲稱“自是海門出潮頭洶高數(shù)百尺,越錢塘漁浦,方漸低小。朝暮再來(lái),其聲震怒,雷奔電走百余里。時(shí)有見子胥乘素車白馬在潮頭之中,因立廟以祀焉”。那是干脆連肉身也一起過來(lái)了。
至于廟的位置和數(shù)量,無(wú)論寫《論衡》的王充,還是寫《錢塘記》的劉道真,當(dāng)年都沒具體說明,但錢塘江那邊沿江一帶有,錢塘江這邊沿江一帶應(yīng)該也有,這一點(diǎn),在兩人筆下其實(shí)已說得很明白了。一個(gè)稱“錢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廟”;一個(gè)稱“越錢塘漁浦……因立廟以祀焉”;這就明顯不可能只是一座,至少也該兩邊都有才是,甚至更多。兩晉六朝,相關(guān)信息在詩(shī)文里雖留下不少,可惜大多概而言之,語(yǔ)焉不詳,就像寫信只書門牌號(hào)碼,不書城市街道,要真正落到實(shí)處難度很大。在這個(gè)問題上,杭州人民要感謝唐元和十年的刺史盧元輔,是他在所作《胥山銘》里,對(duì)當(dāng)?shù)氐奈樽玉銖R作了最早描繪。而越地人民要感謝的,則是唐太和七年的越州太守李紳了,此人同樣也是在自己的作品里,對(duì)當(dāng)?shù)氐奈樽玉銖R作了最早紀(jì)錄,這就是那首有名的七律《欲到西陵寄王行周》,其中最為人傳誦的那兩句是:“猶瞻伍相青山廟,未見雙童白鶴橋。”此前他另有《遙和元九送王行周游越》一詩(shī):“江湖隨月盈還縮,沙渚依潮斷更連。伍相廟中多白浪,越王臺(tái)畔少晴煙。低頭綠草羞枚乘,刺眼紅花笑杜鵑。莫倚西施舊苔石,由來(lái)破國(guó)是神仙。”通篇用越地典故,地望方面其義更為明確。
李紳是中唐著名詩(shī)人,生平與元稹、白居易、劉禹錫相友善。《全唐詩(shī)》里現(xiàn)存詩(shī)四卷,系從生前自訂詩(shī)集《追昔游詩(shī)》、《雜詩(shī)》轉(zhuǎn)錄。此君雖是江蘇無(wú)錫人氏,一生與越地卻似有著特殊因緣。其《龍宮寺》詩(shī)前長(zhǎng)序曰:“貞元十六年(800年),余為布衣,東游天臺(tái)。故人江西觀察使崔公,以殿中謫官,移疾剡溪。崔公坐中有僧人修真,自言居龍宮寺,起謂余言,異日必當(dāng)鎮(zhèn)此,為修此寺。”又曰:“至元和三年(808年),余以前進(jìn)士為故薛蘋常侍招至越中。此僧已臥疾,使門人相告:曩日所言,必當(dāng)鎮(zhèn)此,修寺之托,幸不見忘……及后符其言,而訊其存沒,則僧及門人悉已殂謝,寺更頹毀,惟荒基余像而已。因召僧人會(huì)真,余出俸錢為葺之,累月而畢,以成其往愿。”而《天上樹》詩(shī)前有序又稱:“新昌宅書堂前有藥樹一株,今已盈拱,則長(zhǎng)慶中于翰林院內(nèi)西軒藥樹下移得。才長(zhǎng)一寸,仆夫封一泥丸,以歸植。今則長(zhǎng)成,名之天上樹。”集中另有《渡西陵十六韻》一詩(shī),序言中詳細(xì)記載自己上任的那一天,為太和七年(833年)十月三日。“早渡浙江,寒雨方霖,軍吏悉在江次。越人年谷未成,霪雨不止,田畝浸溢,水不及穗者數(shù)寸。余至驛,命押衙裴行宗先赍祝詞,東望拜大禹廟,且以百姓請(qǐng)命。雨收云息,日朗者三旬有五日,刈獲皆畢,有以見神之不欺也”。中年以前似乎全在紹興度過。而從時(shí)間上看,這與前面所說的《欲到西陵寄王行周》,應(yīng)該寫于同一日期。因此,他筆下的西陵伍子胥廟,原址肯定是在蕭山,而不可能是在別的什么地方。
行文至此有必要回顧一下越地早期的水上交通歷史,這方面最權(quán)威的文獻(xiàn)是班固的《漢書·地理志》:“江水至?xí)疥帪檎憬|至余姚入海。”此言高屋建瓴,大處落墨,相當(dāng)于是為古代紹興畫了幅生動(dòng)的水路全景圖,同時(shí)對(duì)地方志里的某些遺留問題也有良好的釋疑作用。如《寶慶會(huì)稽續(xù)志》敘白馬湖,又說是在蕭山(現(xiàn)濱江區(qū)),又說是在上虞,又說是在余姚,以一名而為三地共有,已覺荒唐。其中以所謂《唐利濟(jì)廟記》為據(jù),稱上虞白馬湖得名于晉周鵬舉乘白馬沒水,否認(rèn)此前夏侯曾先《會(huì)稽地志》的東漢周舉說,更是有些近乎胡說八道了。夏侯曾先陳末隋初人,《利濟(jì)廟記》唐人所作,自當(dāng)以夏記為準(zhǔn)。參照班固所繪之路線圖,更能得出較為合理的推論。因從蕭山西陵到余姚東海,正是東漢以前浙江的入海主道,而上述三處剛好都分布在這一航線上。白馬為伍子胥形象代表,源出《史記》“殺白馬祭子胥”之紀(jì)錄,《錢塘記》又有“時(shí)有見子胥乘素車白馬在潮頭之中”的描繪,因此,在他老人家精魂馳騁之處均有相關(guān)傳說留下,應(yīng)該不難理解。包括本文開頭說的曹娥老爸的故事,也是一個(gè)很好的例子。而稍后《吳越春秋》釋浙江潮時(shí)又稱“前潮水潘侯者,伍子胥也;后重水者,大夫種也”。更是把重點(diǎn)放在了蕭山。此前《漢書》雖有“蕭山,潘水所出,東入海”之記載,但只說當(dāng)?shù)赜信怂瘁屍涿蓙?lái),因此從酈道元到李慈銘,一直說不清楚。一個(gè)稱“疑是浦陽(yáng)江之別名也,自外無(wú)水以應(yīng)之”。(《水經(jīng)注·漸江水》一個(gè)稱“當(dāng)系諸烏傷(原義烏)、諸暨下”。(《潘水考》)如果他們當(dāng)年注意到《吳越春秋》里的這段補(bǔ)充,想必就不會(huì)有這樣的誤會(huì)了,就會(huì)明白,潘水的本義,指的就是浙江在蕭山境內(nèi)的部分,是伍子胥所掀起的精神波瀾在該地的別名。
到了東漢晚期的時(shí)候,因城市發(fā)展需要,會(huì)稽太守馬臻在開鑿臨湖的同時(shí),順便把一條人工運(yùn)河筑到了蕭山江邊。加上此前已有的通往上虞余姚的浙江尾閭,通往諸暨方向的浦陽(yáng)江,通往富春方向的漁浦,這樣濱江一帶當(dāng)時(shí)實(shí)際上已擁有四條航道,成為名副其實(shí)的四通八達(dá)之地。而坐落在這中間的古老的白馬湖,盡管煙波浩渺,景色宜人,實(shí)際功能卻應(yīng)該是個(gè)避風(fēng)港,同時(shí)也起到為上述航道提供水量補(bǔ)給調(diào)配的作用。身后的越王城山如同一座豐碑,代表當(dāng)?shù)貧v史文化的絕對(duì)高度,而湖正面一南一北兩個(gè)渡口,南曰漁浦,北曰西陵,又為東晉以降最著名的錢塘江過江津渡。《越絕書》所記之越國(guó)大船軍,漢末孫策繞道柤瀆夜襲王朗之高遷戰(zhàn)役,《晉書》有關(guān)西陵牛埭、浦陽(yáng)南北津的記載及孫恩之亂,南朝謝靈運(yùn)謝惠連兄弟相別阻風(fēng),《水經(jīng)注》所敘之西陵湖、西城湖,《南齊書》富陽(yáng)新城唐宇之起義,都和這湖有著千絲萬(wàn)縷的關(guān)系。甚至可以懷疑當(dāng)年夏侯曾先筆下所記,也應(yīng)該就是這個(gè)地方,說此湖在上虞,或所謂余姚西北六十里,實(shí)際上出于《嘉泰會(huì)稽志》作者自己的解讀。這里不妨可以將原文找來(lái)看一下:“驛亭埭南有漁浦湖,深處可二丈。漢周舉乘白馬遊而不出,時(shí)人以為地仙。白馬湖之名由此。”驛亭埭其址不詳,現(xiàn)存文獻(xiàn)始見于五代,為錢镠部將朱全武逐淮將田頵處。“嘉禾平,全武等又乘勝逐田頵于驛亭埭,頵由吳興而遁”。(見《吳越備史》卷一,《新唐書》、《資治通鑒》所述同)其地必在杭蕭之間。漁浦為當(dāng)?shù)貧v史品牌,那就更不用說了。因此,斷夏侯先生筆下之白馬湖在蕭山,其他地方有可能出于附會(huì),理論上應(yīng)該是站得住腳的。
唐宋時(shí)期,隨著縣城擴(kuò)充和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發(fā)展,白馬湖的面積較前已大為縮小。據(jù)南宋紹興二十年(1150年)一次測(cè)量提供的數(shù)據(jù),當(dāng)時(shí)大約尚存三千余畝,為周圍百余項(xiàng)良田旱澇之年的唯一依賴。但期間發(fā)生過這樣一件荒唐的事,差點(diǎn)把它給徹底廢了。有個(gè)叫沈琮的當(dāng)?shù)厝耍揭运忝鼮闃I(yè),坑蒙拐騙的事大約也沒少干。為求立功自保,竟騙取鄉(xiāng)鄰六十一人聯(lián)名上書,提出要把該湖作為廢地獻(xiàn)給皇室寧壽觀充長(zhǎng)生田。考陸游文集中有《三茅寧壽觀記》:“紹興二十年十月,詔賜行在三茅堂名寧壽觀……乃命道士蔡君大象知觀事,蒙君守亮副之,許其徒世守。又命內(nèi)侍劉敖典領(lǐng)。”乞請(qǐng)獻(xiàn)湖之日,正當(dāng)立觀之年,而文中提到的內(nèi)侍劉敖,碰巧又是代上劄子的人,其中的蹊蹺與曖昧應(yīng)該不難看出。幸虧作為接受方的宋理宗趙昀還不是太傻,當(dāng)場(chǎng)下旨派員實(shí)地勘查,轉(zhuǎn)運(yùn)司干辦公事趙綱立下來(lái)一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回去后據(jù)實(shí)稟報(bào):“白馬湖古來(lái)系是蓄水湖地,難以作田。轉(zhuǎn)運(yùn)司點(diǎn)對(duì)指實(shí)申聞。十二月十七日,三省同奉圣旨,更不施行。”(詳見明富玹等撰《蕭山水利正續(xù)》)這才避免了一場(chǎng)意外災(zāi)難的發(fā)生。
再后來(lái),江潮成年累月的沖擊,導(dǎo)致沙涂面積不斷擴(kuò)大。隨著江岸的逐年外移,東晉時(shí)位于湖邊的西陵埭,至五代吳越時(shí)已遷至現(xiàn)在的西興,而原來(lái)在西陵的伍員廟,可能也在那時(shí),因津渡重設(shè),也跟著一起搬了過來(lái)。因前面文章里已經(jīng)說過,伍子胥的精神形象盡管高大威猛,堪稱古代政治人格中含義最豐富、象征色彩最濃的一個(gè)原型,但在一般老百姓的心目中,卻更多是從世俗功利上來(lái)理解的,包括當(dāng)初建廟的目的,塑其像于江邊,可能也只是為了讓人上船前能夠拜一拜,以求渡江時(shí)心里多一份踏實(shí)之感。渡口后來(lái)既然搬遷了,廟如果還在原來(lái)地方,那倒反而是不正常了。王十朋《會(huì)稽賦》稱“西觀驚濤,吊夫子胥。”其下有注云:“浙江在蕭山縣西十三里。”要表達(dá)的估計(jì)也是同樣的意思。
在這個(gè)背景下再來(lái)看唐代李公垂的那首詩(shī),于其本義或許會(huì)有更深的領(lǐng)會(huì)。這里不妨將原詩(shī)全錄:“西陵沙岸回流急,船底黏沙去岸遙。驛吏遞呼催下纜,棹郎閑立道齊橈。猶瞻伍相青山廟,未見雙童白鶴橋。欲責(zé)舟人無(wú)次第,自知貪酒過春潮。”此詩(shī)前半首寫船過江到西陵渡,因水淺舟澀,進(jìn)入縣河前很吃了一番苦頭。“催下纜”作背牽解,“齊橈”是合力劃槳的意思,有白居易《和春探》詩(shī)“齊橈爭(zhēng)渡處,一匹錦標(biāo)斜”可證。五、六兩句提到當(dāng)?shù)貎商幹包c(diǎn),蓋紀(jì)實(shí)也。結(jié)尾自稱因沒看到白鶴橋,本打算責(zé)怪水手,轉(zhuǎn)而又想可能是自己喝多了的緣故,于是就算了。全詩(shī)以自嘲結(jié)束,非常有意思,略可見詩(shī)人情懷。詩(shī)題作《欲到西陵寄王行周》,以《新唐書李紳傳》考之,必作于太和七年初任浙西觀察使之時(shí)。王行周名洲,行十一,與元稹相厚,《元白長(zhǎng)慶集》有《送王十一郎洲剡中》詩(shī),當(dāng)即此人。李紳當(dāng)年另有《遙和元九送王行周游越》相酬,已見前述。因此,不管這首詩(shī)里說的“猶瞻伍相青山廟”,還是前面那首詩(shī)里說的“伍相廟前多白浪”,廟的位置在蕭山濱江一帶可以無(wú)疑。何況同時(shí)代其他詩(shī)人好像也沒閑著,如比李紳小了沒幾歲的儲(chǔ)嗣宗和喻坦之,一個(gè)稱“水色西陵渡,松聲伍員祠”。(《鄭顧陶校書歸錢塘》)一個(gè)稱“西陵煙樹色,長(zhǎng)見伍員情”。(《題鄣亭驛樓》)都把西陵跟伍子胥廟緊緊綁在一起,可見這在當(dāng)時(shí)是蕭山相當(dāng)著名的一個(gè)地標(biāo)。
如果說唐代文人筆下的伍員廟還在西陵,到了宋代文人筆下,可能已經(jīng)遷移到了現(xiàn)在的西興鎮(zhèn)上。王明清是南宋學(xué)者兼歷史學(xué)家,他在多卷本巨著《揮麈錄》里,為我們記述了這樣一個(gè)故事:有個(gè)叫姚令聲的人,出生于紹興本地,據(jù)寫《直齋書錄解題》的陳振孫稱,現(xiàn)存《戰(zhàn)國(guó)策》漢高誘注本,當(dāng)初就是由他整理出版保存下來(lái)的。觀書前自序有“先秦古書見于世者無(wú)幾,而余居窮鄉(xiāng),無(wú)書可檢閱。訪春秋后語(yǔ),數(shù)年方得之,然不為無(wú)補(bǔ),尚覬博采老得定本,無(wú)劉公之遺恨。紹興丙寅中秋剡川姚宏伯聲父題”之語(yǔ),可知晚年定居在剡縣。此人北宋宣和年間初登仕途,“有僧妙應(yīng)者,能知人休咎,語(yǔ)令聲云:君不得以令終。候端午日伍子胥廟中見石榴花開,則奇禍至矣。”在杭州當(dāng)了三年稅官,足跡不敢登吳山一步。后來(lái)調(diào)任江山,“趨越來(lái)訪憲帥。既歸,出城數(shù)里,值大風(fēng)雨,亟愒路旁一小廟中,見庭下榴花盛開,妍甚可愛,詢祝史,云:此伍子胥廟。其日乃五月五日。令聲慘然登車,未幾遂罹其酷。”(詳見《揮麈后錄》卷十一)不僅同樣講到有兩座伍子胥廟,一座在杭地,一座在越地,而且明言越地的那座,他是在拜訪上司后回杭州的路上看到的。文中“出城數(shù)里”的“城”字,不清楚指的是紹興還是蕭山,而數(shù)里也有可能是實(shí)指,也有可能是虛指,但其地屬當(dāng)時(shí)交通要道、為旅途所必經(jīng)那是可以肯定的。
現(xiàn)在的問題是,杭地的伍子胥廟,我們已經(jīng)知道它是在吳山山頂,盡管原先只是西湖中一座洲島,后來(lái)搬到了現(xiàn)在的所謂吳山上。其間的演變錯(cuò)綜復(fù)雜,但至少直到目前為止尚有跡可尋,有廟可拜。而越地的伍子胥廟,北宋以前流傳尚大致有序,北宋以后,漸漸就有些銷聲匿跡,形象模糊,到現(xiàn)在更是已經(jīng)沒什么人知道了。
為什么會(huì)這樣,主要出于兩個(gè)方面的原因。一是《嘉泰會(huì)稽志》有寧濟(jì)廟條,稱:“寧濟(jì)廟在縣西一十三里西興鎮(zhèn)。政和三年賜今額。”也就是說,在西興鎮(zhèn)上原來(lái)有一座廟,自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朝廷恩賜新名后,開始叫寧濟(jì)廟了。至于這以前叫什么,嘉泰志沒有明說,但后來(lái)《嘉靖蕭山縣志》把它的身份給暴露了,因這廟在明代又改名叫潮神廟:“亦稱寧濟(jì)廟,位于西興沙岸鋪。”雖然同樣也沒交代廟主是誰(shuí),但撰者知縣林策應(yīng)該是有心人,因?yàn)樗诖藯l下附了一段文字,是致祭用的祝祠,并透露是個(gè)叫夏弦春的飽學(xué)儒生告訴他的,其中“勢(shì)傾山岳,聲震雷霆。素車白馬,出沒杳冥。實(shí)錢塘之壯觀。固海若之憑陵”云云,無(wú)意中泄漏天機(jī),明顯就是我們要找的伍子胥廟了。二是作為越地伍員廟最關(guān)鍵證據(jù)的李紳那兩首詩(shī),《嘉泰會(huì)稽志》里竟沒收錄,反為歷代杭志括入囊中,被說成是寫他們那里的。加上《武林舊事》《七修類稿》等地方筆記著述的推波助瀾,反復(fù)渲染,包括像程大昌《演繁露》這樣較為嚴(yán)謹(jǐn)?shù)闹鳎参茨苊馑住T摃硭姆Q:“(沙河)塘在縣南五里,此時(shí)河流去青山未甚遠(yuǎn),故李紳詩(shī)曰:猶瞻伍相青山廟。又曰:伍相廟前多白浪也。”這樣一來(lái),不該放棄的放棄,不該得到的得到,這筆張冠李戴的糊涂賬,從此也就再也沒有辦法算清。
歷史的發(fā)展就是這樣的波譎云詭,出人意表。從表面看,越地伍員廟的消失或相當(dāng)于消失,似乎由偶然因素所造成,即此地撰志者的漫不經(jīng)心和彼地撰志者的巧取豪奪,說得輕松一點(diǎn),也可說是某些人的不作為和某些人的過于作為。但事情其實(shí)并不如此簡(jiǎn)單,在這一文化事件背后,實(shí)際上閃動(dòng)著的是政治和權(quán)力的強(qiáng)大影子。因?yàn)樽阅纤纬跗谄穑蚺既坏囊蛩兀瓕?duì)岸的臨安在沒有任何準(zhǔn)備的前提下,突然成了皇城,國(guó)家政治經(jīng)濟(jì)的中心,自然需要各種高級(jí)別的文化資源來(lái)配套,這就是吳山上那座為什么炒得越來(lái)越熱,而蕭山這邊的卻漸趨清冷的更為深層的原因。李光祿的《西陵懷古》,或許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寫出來(lái)的:“西陵望處即吳關(guān),懷古情深復(fù)一攀。湖上笙簫何日始,渡頭車馬幾時(shí)閑。青山廟廢基空在,白鶴橋傾水自潺。卻問宋家蘭上里,白煙如雨隔江還。”(《甬上耆舊詩(shī)》卷二十七)其中“青山廟廢基空在,白鶴橋傾水自潺”這兩句,含不盡之意于言外,讓人讀后浮想聯(lián)翩,黯然神傷。蕭山本地的幾位文壇大佬自然也不甘落后,來(lái)集之《西江塘紀(jì)事》有“三折勢(shì)雄傳白馬,兩峰遙望下飛鳧”之詠,毛西河晚年撰《水仙五郎》詞,以游戲文字泄其憂思。詞前有自序稱:“上湘湖旁有白馬湖,是其跡也。”全詩(shī)共有九解,其第六解云:“榴火兮將燃。著單衣兮無(wú)綿。迎神不至兮潮欲干。神指水仙為期兮、今告予曰不閑。謇予將先期以要君兮、謂荷花為水仙。”第七解云:“水仙兮奈何。秋霜未降兮花開滿湖。神騎白馬兮張靈弧。解鞍歇馬兮在前山之岨。神之來(lái)兮待日下。”白馬、水仙為古代形容伍子胥的專用詞,白馬狀其神態(tài),水仙狀其精神,相當(dāng)于是一張個(gè)人名片,不是隨隨便便可以用的。“神騎白馬兮張靈弧。解鞍歇馬兮在前山之岨”。這是什么概念,用現(xiàn)在的話來(lái)說,就是早就在蕭山買了房子,入了戶口住下的,不過很少出來(lái)走動(dòng)而已。不像杭州今吳山上的那個(gè),每天香煙纏繞供在那里讓人看。但如果有心的話,在每年八月潮水來(lái)臨期間,相信你一定能如愿見到他。
在今天的濱江區(qū)西興鎮(zhèn)古塘路東近江一側(cè),一說在原西興初中校區(qū)內(nèi),傍晚時(shí)分華燈初上,路兩邊熙熙攘攘的商鋪與民居,加上每天肩扛鋪蓋涌向這里的外地打工者,使一切看上去顯得那么擁擠,仿佛連記憶和遐思,都已找不到落腳之地。時(shí)間畢竟已經(jīng)進(jìn)入二十一世紀(jì)了,因此當(dāng)?shù)氐拇蠖鄶?shù)居住者,包括轄區(qū)內(nèi)中學(xué)的學(xué)生甚至老師,不知道大名鼎鼎的蕭山伍員祠,原先居然就在他們的家門口,也不算是什么特別奇怪的事。或許,只有待更深人靜之時(shí),曾經(jīng)照過勾踐、范蠡、西施的那輪明月,依舊照在江畔的石堤和古橋上,濤聲中伍氏騎著白馬馳騁而來(lái),而掀動(dòng)的浪花,如同書頁(yè)嘩嘩打開。從最初西漢兩晉的伍神祠,到唐代西陵伍相祠,到兩宋的寧濟(jì)廟,到元明清三朝的潮神廟,到民國(guó)的西興鄉(xiāng)鄉(xiāng)立初等新民小學(xué),再到社會(huì)主義初級(jí)階段的西興中學(xué),一頁(yè)一頁(yè)翻開,一頁(yè)一頁(yè)都是輝煌的歷史。
這樣的時(shí)刻,時(shí)間是停止的。盡管世事滄桑、陵谷變遷,他的遺愛卻一直留存在這里,與敬他愛他的當(dāng)?shù)厝嗣癯榘椤0础睹駠?guó)蕭山志》的說法,廟南原有朱熹遺跡碑,正前有五代鐘樓一座,既供善男信女們寄托情思,又能為過江客旅鳴聲引渡,可謂精神文明物質(zhì)文明兩兼其美。蘇東坡《望海樓晚景五絕》之三“青山斷處塔層層,隔岸人家喚欲應(yīng)。江上秋風(fēng)晚來(lái)急,為傳鐘鼓到西興。”即專為此事而詠。而對(duì)于今天的我們來(lái)說,有關(guān)這位偉大的歷史人物的塵世寄所,無(wú)論是在浙西的杭州也罷,在浙東的蕭山(今濱江區(qū))也罷,考證和研究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對(duì)他人格力量的繼承,或者說,如何讓他老人家的精神融入身邊的現(xiàn)實(shí)生活,遠(yuǎn)比在原址重建或朝拜更為必要,也更有意義。過去的已經(jīng)遠(yuǎn)逝,未來(lái)的正在走來(lái),“英雄有恨余湖水,天地忘懷入酒杯。”這是元人張昱說的,是他當(dāng)年路過此地對(duì)山亭,重閱這段歷史所采取的一個(gè)基本態(tài)度,而本文想要表達(dá)的意思,應(yīng)該也就盡在于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