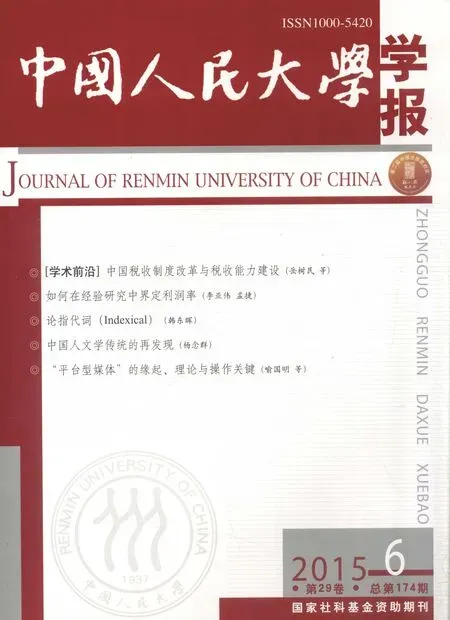論指代詞(Indexical)
韓東暉
?
論指代詞(Indexical)
韓東暉
指代詞是指稱隨語境的變化而變化的語言表達(dá)式。Indexical、deictic、和demonstrative均可充當(dāng)此類語言表達(dá)式,但其中文譯名和理解頗為混亂。比較而言,指代詞是Indexical的比較合適的譯名。指代詞研究呈現(xiàn)出兩條主要研究脈絡(luò),即語言學(xué)路徑和哲學(xué)路徑。其中哲學(xué)路徑中包含三個(gè)主要問題:指代詞使用的語言學(xué)—哲學(xué)預(yù)設(shè),指代詞的使用與個(gè)體對(duì)象的被給予方式,以及指代詞與語句的真值條件。對(duì)這些問題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準(zhǔn)確定位指代詞哲學(xué)研究的重要價(jià)值。
指代詞;語境化;指示詞
我們習(xí)慣于用名字稱呼某個(gè)人,也常常以指示的方式談及某人某物甚至自己。“我”、“他”、“這里”、“現(xiàn)在”、“這個(gè)”、“以上”,就是后一種方式,其意義隨語境而變,因?qū)ο蠖悺T谟⒄Z中,這種方式的特點(diǎn)主要被稱為indexicality、deixis或demonstration,相關(guān)的表達(dá)詞匯被稱為indexical、deictic或demonstrative。這三個(gè)術(shù)語的詞源意義都是“指示”(point to),因此均可譯為“指示詞”。但在中文譯名中,indexical大多被望文生義地誤譯為“索引詞”,仿佛跟“索引學(xué)”(index science)有關(guān)系一樣,在翻譯錯(cuò)誤中屬于“假朋友”一類(faux amis);demonstrative則被過于寬泛地譯為“指示詞”,有點(diǎn)辜負(fù)了“指示詞”這個(gè)好名字。當(dāng)然更重要的是,我們對(duì)相關(guān)問題的研究比較少,特別是哲學(xué)研究方面比較薄弱。本文擬從術(shù)語翻譯、研究脈絡(luò)和哲學(xué)問題三個(gè)方面,將indexical研究比較完整地勾勒出來。
一、正名
希臘語詞deixis本意為“指”(pointing)、“示”(indicating),自古希臘起論者已甚眾,例如斯多亞派嘗以此討論單稱可斷言對(duì)象。Deixis的形容詞形式deictic(deiktikos)意即“指示”,羅馬語法學(xué)家用拉丁語詞demonstrativus來翻譯斯多亞派及其他希臘語法學(xué)著作中的deiktikos。因此,源于拉丁語的demonstrative和出自希臘語的deictic是同義的;在后來的語言學(xué)習(xí)慣中,正如語言學(xué)家萊昂斯(John Lyons)所言,deixis的使用更廣泛,不僅涵蓋了指示代詞的功能,還包括了時(shí)態(tài)和人稱以及許多在句法上相關(guān)的言語—語境特征,甚至還將哲學(xué)上的實(shí)指(ostension)或?qū)嵵付x概念包括在內(nèi)。[1] (P636-637)
英文詞indexical源于美國哲學(xué)家、邏輯學(xué)家皮爾士指號(hào)三分法(圖像、標(biāo)志、象征)中的標(biāo)志——index,但index本身就源于印歐語言中的詞根deik-,意思是表明、表示或直接關(guān)注語詞或?qū)ο螅哂羞@個(gè)詞根的有動(dòng)詞teach、dictate、indicate,有名詞token、deixis,當(dāng)然還有index——用食指指指點(diǎn)點(diǎn)。[2] (P84)皮爾士說:“標(biāo)志(index)并不斷言什么,它只是說‘那兒!’它抓住我們的眼睛,仿佛要強(qiáng)迫眼睛朝向某個(gè)特殊對(duì)象,在那里停下來。指示詞(demonstrative)和關(guān)系代詞差不多是純粹的標(biāo)志,因?yàn)樗鼈冎阜Q事物而不描述事物。”[3] (P361)
就這三類指示語詞在英語中的特點(diǎn)而言,萊昂斯指出,deixis范圍比demonstrative更廣,且已成為語言學(xué)界的共識(shí),indexical主要用于哲學(xué)文獻(xiàn),意義類似于deixis。[4] (P637)語言學(xué)家列文森最近總結(jié)道,在現(xiàn)代語言學(xué)和哲學(xué)領(lǐng)域,deixis和indexicality這兩個(gè)術(shù)語是共存的,分屬于不同的傳統(tǒng),前者屬于語言學(xué)進(jìn)路,后者屬于哲學(xué)進(jìn)路*在1983年出版的《語用學(xué)》中,列文森稱之為描述進(jìn)路和哲學(xué)進(jìn)路。參見Stephen C.Levinson.Pragmat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55ff。;從范圍上講,后者可用于標(biāo)示更寬泛的語境依賴現(xiàn)象,而前者,則在較狹窄的語言學(xué)意義上屬于indexicality。[5] (P97)
列文森的兩條進(jìn)路說和寬窄范圍說大體上符合語言學(xué)界的一般看法,或者說大家也需要比較一致的方案來處理這些詞。因此,我們可以約定:indexicality的范圍最寬泛,我們用它來表達(dá)這一系列指示語詞和指示現(xiàn)象,但它與deixis的區(qū)分主要是哲學(xué)和語言學(xué)兩條進(jìn)路的差異*努恩伯格不同意將二者等量齊觀,他認(rèn)為引入與“我”、“那個(gè)”等語詞相聯(lián)系的特殊語義性質(zhì)的,是直指詞而非指代詞。參見Geoffrey Nunberg.“Indexicality and Deixis”,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1993 (1)。;demonstrative的指示范圍最狹窄。
基于以上的簡(jiǎn)要討論,我們嘗試為上述三個(gè)概念給出一套比較恰切的中譯名。實(shí)際上,對(duì)于這三個(gè)詞來說,“指示詞”都是比較合適的譯名。*例如,有學(xué)者將indexical和deictics均譯為“指示”(參見蔣嚴(yán)、潘海華:《形式語義學(xué)引論》,548頁,北京,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98);有學(xué)者將deictics和demonstratives均譯為“指示”(參見哈特曼:《語言與語言學(xué)詞典》,91-93頁,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1);不過,姜望琪明確反對(duì)用“指示”翻譯deixis和indexicality系列詞匯,在他看來,“指示”比較寬泛,范圍大于這兩個(gè)系列,例如指稱語詞的復(fù)指或照應(yīng)功能(anaphora),也可以看做指示。他沿用戚雨村和徐烈炯的譯名,將deixis譯為“指別”,而將indexicality譯為“直指”。(參見姜望琪:《當(dāng)代語用學(xué)》,17頁,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3)這個(gè)觀點(diǎn)和建議值得參考,但將indexicality譯為“直指”,似乎大大縮小了其應(yīng)用范圍。[6]不過,考慮到這三個(gè)詞雖然詞源相近,本義相似,但在西語中畢竟是不同的詞匯,分屬于不同的傳統(tǒng),在現(xiàn)代語言學(xué)和哲學(xué)研究中也在逐漸拉開距離,還是可以考慮賦予其不同的譯名。由于demonstrative約定俗成地占據(jù)了“指示詞”這個(gè)譯名,已難改變,我們只好將deictic譯為“直指詞”,這個(gè)譯名選自沈家煊譯克里斯特爾主編的《現(xiàn)代語言學(xué)詞典》。[7]
對(duì)于范圍最廣泛的indexical來說,“索引詞”是完全不合適的譯名,無論是古漢語中的索引還是現(xiàn)代意義上的索引,都不具有“指示語詞”的含義和用法。實(shí)際上,語言學(xué)家雖然很可能是“索引詞”譯名的始作俑者,但現(xiàn)在用這個(gè)譯名的語言學(xué)家并不多。在這里,我們把它改譯為“指代詞”,相應(yīng)地,indexicality譯為“指代”。之所以不循index(標(biāo)志)而譯為“標(biāo)志詞”,主要還是因?yàn)椤皹?biāo)志”在現(xiàn)代漢語中離indexicals的“指示”和語境依賴這兩個(gè)核心特征有較大距離,而“指代”則能夠體現(xiàn)這兩點(diǎn)。這個(gè)譯名的一個(gè)重要依據(jù)是:呂叔湘先生在20世紀(jì)40年代撰寫的《近代漢語指代詞》,用的就是“指代”而非其他;雖然他沒有明確說明用指代翻譯indexicals,但他討論的詞匯均是漢語的indexicals。[8] (P1-2)
唯一可能有問題的地方是“指代”一詞常被用來翻譯中世紀(jì)邏輯和語言學(xué)中的supposition(拉丁語suppositio)。不過,由于領(lǐng)域特殊,知之者寡,大概不會(huì)引起麻煩。
二、研究脈絡(luò)
指代詞研究雖然由來已久,但真正深入的研究還是于19世紀(jì)后期在語言學(xué)、哲學(xué)、邏輯學(xué)、心理學(xué)等領(lǐng)域逐步展開的,并且自20世紀(jì)80年代起在語言學(xué)界掀起了指代詞研究的熱潮。*國內(nèi)的研究集中在語言學(xué)特別是語用學(xué)領(lǐng)域,代表性的著作如姜望琪的《當(dāng)代語用學(xué)》,哲學(xué)領(lǐng)域可參見武慶榮、何向東:《索引詞研究的邏輯哲學(xué)意蘊(yùn)及其啟示》,載《自然辯證法研究》,2012(8)。[9](P190)本文將從語言學(xué)和哲學(xué)兩條主要進(jìn)路出發(fā)總結(jié)其脈絡(luò)。當(dāng)然,從指代詞研究的緣起和發(fā)展來看,它更多地由語言哲學(xué)家主導(dǎo),哲學(xué)家、邏輯學(xué)家和語言學(xué)家共同參與,因此,嚴(yán)格區(qū)分哲學(xué)進(jìn)路和語言學(xué)進(jìn)路實(shí)際上十分勉強(qiáng),我們只能根據(jù)研究者的主要領(lǐng)域來歸類。
(一)語言學(xué)進(jìn)路
在語言學(xué)進(jìn)路中,對(duì)指代詞的研究可分為歷史起源研究、心理語言學(xué)研究、語義學(xué)—語用學(xué)等方面。
在歷史研究方面,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德國語言學(xué)家卡爾·布拉格曼(Karl Bragmann),丹麥語言學(xué)巨擘奧托·葉斯柏森,語言學(xué)大家、俄國形式主義和布拉格學(xué)派的雅柯布森。葉斯柏森在《語言本性及其發(fā)展》(1923)一書中,將這種因其意義隨情境而變的語詞稱為移指詞(shifter),其中最重要的一類是人稱代詞。[10]雅柯布森在其著名論文《移指詞、語詞范疇與俄語動(dòng)詞》(1956)中深入討論了這個(gè)問題,給出了從皮爾士到布勒的概念流變史。[11] (P131-133)
雅柯布森首先給出了移指詞的基本特征:如果不指涉已知信息(message),則移指詞的一般意義無法確定。他進(jìn)而根據(jù)巴克斯的研究[12]指出,皮爾士的指號(hào)三分法已經(jīng)討論了符號(hào)學(xué)的本質(zhì):象征根據(jù)慣例規(guī)則與所表象的對(duì)象相聯(lián)系,標(biāo)志則與其所表象的對(duì)象處于實(shí)存關(guān)系之中。關(guān)鍵在于,雅柯布森認(rèn)為移指詞將這兩種功能結(jié)合在一起,因此,屬于指代象征(indexical symbols)一類。這恐怕是雅柯布森不用指代詞、直指詞這兩個(gè)名稱的原因。
在討論了胡塞爾、羅素、布勒(Karl Bü ̄hler)的觀點(diǎn)之后,雅柯布森認(rèn)為,移指詞不同于其他語言信碼(code)的地方在于它們對(duì)給定信息的強(qiáng)制指稱。這一點(diǎn)與雅柯布森的信碼—信息分析方法關(guān)系密切。他認(rèn)為這種指代象征詞,特別是關(guān)系代詞,在洪堡傳統(tǒng)中被視為最基本、最原始的語言底層,但實(shí)際上卻是信碼和信息交疊的復(fù)雜范疇。
雅柯布森堅(jiān)持使用葉斯柏森的移指詞這個(gè)名稱值得我們進(jìn)一步研究。例如,這一點(diǎn)與結(jié)構(gòu)主義語言學(xué)是否有明確關(guān)聯(lián),另一位結(jié)構(gòu)主義語言學(xué)家本維尼斯特關(guān)于人稱代詞的結(jié)論與他十分接近。[13] (P195-230)又如,移指詞這個(gè)名稱此后在文學(xué)批評(píng)領(lǐng)域特別是敘事研究中廣泛流行,拉康對(duì)這個(gè)詞也特別有興趣,用于分析主體或“我”[14] (P139),這也有必要結(jié)合起來思考。

概言之,正如費(fèi)爾默(Charles Fillmore)所言,直指現(xiàn)象向語法理論提出了大量重要問題,有經(jīng)驗(yàn)性的,也有概念性的和記號(hào)性質(zhì)的。[16] (P26)迪塞爾研究了85種語言中的直指詞,考察了直指詞的形態(tài)學(xué)、語義學(xué)、句法學(xué)、語用學(xué)和語法化等五個(gè)方面。[17] (P1)當(dāng)然,我們關(guān)注的主要還是語義學(xué)和語用學(xué)兩個(gè)方面,因?yàn)橹复袨槭锹?lián)結(jié)語義學(xué)和語用學(xué)的一條紐帶。
經(jīng)過萊昂斯、利奇(G.Leech)、列文森、費(fèi)爾默、努恩伯格等語言學(xué)家的努力,我們已經(jīng)能夠大致梳理出指代詞在語言學(xué)意義上的基本類型。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列文森在《語用學(xué)》一書中將指代詞分為五類:人稱的、時(shí)間的、位置的、語篇的(或文本的,discourse or text)和社交的(反映社會(huì)地位的,如敬語)。這五類基本上涵蓋了指代詞的主要類型。由于這些文獻(xiàn)在國內(nèi)語言學(xué)界已有介紹,這里從略。
(二)哲學(xué)進(jìn)路
針對(duì)指代詞的哲學(xué)研究,不需遠(yuǎn)溯,在黑格爾《精神現(xiàn)象學(xué)》第一章“感性確定性,或‘這一個(gè)’和意謂某物”中就有精彩的思辨。黑格爾用Aufzeigen表示我們所說的指示、指明行為。*英譯“pointing out”,中譯“指出”或“指明”。以下引文均出自該章。指明行為作為包含“我”、“這時(shí)”、“這里”的“這一個(gè)”(dieses,this),表明了感性確定性的辯證法無非就是這種確定性的一段單純的運(yùn)動(dòng)史或一段單純的經(jīng)驗(yàn)史,而感性確定性本身恰恰就是這段歷史:這一個(gè)東西是一個(gè)普遍者;不再是一個(gè)直接事物,而是一個(gè)折返回自身的事物*德文ein in sich Reflektiertes,英譯文something reflected into itself,中譯文或譯為“回復(fù)到自身的東西”。這個(gè)措辭可與賴辛巴赫的“token reflexive word”(自反標(biāo)記詞)相比較。,或一個(gè)在他者存在中保持不變的單純東西。這種辯證法的確可以回?fù)粼从诮?jīng)驗(yàn)主義的懷疑主義,亦可詮釋公孫龍《指物論》“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的謎題。
無獨(dú)有偶,胡塞爾在《邏輯研究》的第一研究開始,就從符號(hào)、指示(demonstration)和兩種指示方式(指明與證明,indication and proof)入手,并在第26節(jié)通過區(qū)分本質(zhì)上機(jī)遇性的(或偶然的)和客觀的表達(dá)式,著重討論了人稱代詞和指示代詞。當(dāng)然,這些討論與胡塞爾關(guān)于指明、知覺和命名的思考以及意義理論本身是結(jié)合在一起的。有研究者認(rèn)為,在《邏輯研究》中,胡塞爾關(guān)于指代詞的理論有兩個(gè)基本特征:其一,強(qiáng)調(diào)語言的指代用法至少包括兩種實(shí)質(zhì)上有區(qū)別的行為,即意謂行為和知覺行為;其二,說明了這兩種行為是如何關(guān)聯(lián)的,也就是說,二者的聯(lián)系包含一種行為(事件)對(duì)另一種行為的單方面的存在性依賴關(guān)系,這種依賴關(guān)系發(fā)生在一種特定類型的復(fù)雜整體的語境中。[18]
黑格爾和胡塞爾關(guān)于指代詞的論述并不是主流的指代詞理論。相對(duì)于布勒和費(fèi)爾默的理論對(duì)指代現(xiàn)象的心理學(xué)和功能性方面的關(guān)注,皮爾士、弗雷格、羅素、賴辛巴赫、維特根斯坦則更關(guān)注符號(hào)學(xué)—邏輯學(xué)方面,成為語言哲學(xué)關(guān)于指代詞研究的典范。弗雷格和羅素關(guān)于專名、意義、指稱的問題,這里不再贅言,我們主要關(guān)注與指稱關(guān)系(referential relation)相對(duì)的指代關(guān)系問題。
弗雷格討論指代詞的文獻(xiàn)集中在《思想》(1918)一文中,這篇文章的主旨是要說明思想到底是什么(外部事物、心理表象還是客觀領(lǐng)域)、思想與真的關(guān)系等問題,而包含指代詞的句子,特別是包含“我”的句子,對(duì)于思想的客觀性的表達(dá)造成了困難。用培里(John Perry)的表述就是:當(dāng)我們思考自己時(shí),我們把握的思想是其他人不可能把握的、不能交流的,但沒有比不可交流的、私人的思想更不符合弗雷格關(guān)于意義與思想的觀點(diǎn)了。[19]弗雷格的基本做法是用專名(以及給出專名對(duì)象的唯一方式)和摹狀詞來消除指代詞。但培里卻論證說,包含第一人稱信念的句子無法消除這種對(duì)語境敏感的指代詞。[20]第一人稱信念問題經(jīng)由埃文斯、麥克道爾、皮科克(Christopher Peacocke)、培里、大衛(wèi)·劉易斯、斯托內(nèi)克(Robert Staalnaker)以及更早的卡斯坦尼達(dá)(Hector-Neri Castaeda)等人的工作,已經(jīng)成為熱門的研究領(lǐng)域。不過,也有人不認(rèn)可這種流行觀點(diǎn),認(rèn)為弗雷格早在1897年撰寫但未發(fā)表的論文《邏輯》中就強(qiáng)調(diào),第一人稱、現(xiàn)在時(shí)等性質(zhì),只是語言的特征,而非思想的性質(zhì)。[21]埃文斯也認(rèn)為弗雷格對(duì)指示詞的處理方式本質(zhì)上是正確的。[22] (P71)
有一類指代詞的重要特性就是自指(或譯自反、自復(fù)),也恰恰是這些詞吸引了哲學(xué)家的關(guān)注。羅素曾專門討論了自我中心的特稱詞(egocentric particulars)。[23]這類詞的特點(diǎn)是意義隨著說話者和他在時(shí)間與空間中位置的不同而改變,其中“我”、“這個(gè)”、“這里”和“現(xiàn)在”是四個(gè)基本詞項(xiàng)。自我中心特稱詞的特點(diǎn)是靠知覺而產(chǎn)生的,因?yàn)樵谥挥形镔|(zhì)的世界里不會(huì)有什么“這里”和“現(xiàn)在”。知覺對(duì)于事物是從一個(gè)中心出發(fā)的;我們的知覺世界是對(duì)公共世界的一個(gè)透視。在時(shí)間和空間中近的事物引起的記憶和知覺,一般比遠(yuǎn)的事物更生動(dòng)、更清楚。在物理學(xué)的公共世界中卻沒有這種照明中心。這也恰恰說明為什么物理學(xué)通過消除感覺的個(gè)人性質(zhì)的努力變得越來越抽象。[24] (P112-113)
賴辛巴赫將指代表達(dá)式稱為自反標(biāo)記詞(token reflexive expressions),從而區(qū)別于使用專名、概念等詞項(xiàng)的指稱表達(dá)式。[25](P284-286)這個(gè)術(shù)語將自反性與標(biāo)記(實(shí)例)—類型(token-type)的區(qū)分結(jié)合在一起,既強(qiáng)調(diào)當(dāng)下指稱的特點(diǎn)是利用指稱對(duì)象在場(chǎng)的條件,也關(guān)注在非當(dāng)下指稱時(shí),利用的則是先前固定的(fixed)指稱,從而加強(qiáng)了言談?wù)Z境與固定指稱語境之間的區(qū)別。標(biāo)記(token)確定了自我指稱的實(shí)例特性,因此,“我”可以定義為“說出該標(biāo)記的人”,“現(xiàn)在”可根據(jù)“這一標(biāo)記被說出的時(shí)間”來定義,“這個(gè)桌子”也可以定義為“由伴隨這個(gè)標(biāo)記的姿勢(shì)所指示的桌子”,等等。對(duì)自反性的進(jìn)一步研究,可參見培里提出的“自反—指稱理論”(reflexive-referential theory)。在他看來,指代方式的重要性根本上在于它是自反性的最高形式,是通往自反性寶庫的大門。[26] (P590)
如果說培里發(fā)揮了指代詞的自反性,卡爾納普的學(xué)生、以色列邏輯學(xué)家巴爾-希勒爾則著重從type-token這個(gè)同樣源于皮爾士的二分法出發(fā),在1954年的論文中討論了指代表達(dá)式。[27]這篇論文大大促進(jìn)了對(duì)指代詞的研究。類型(type)是抽象語言單位,實(shí)例(token,此處不譯作標(biāo)記)是類型在具體場(chǎng)合的體現(xiàn),像“我餓了”這樣的句子,作為類型沒有指稱,只有作為實(shí)例才有。句子的指稱是命題,但后來他認(rèn)為指稱實(shí)際上不是實(shí)例與命題這兩個(gè)方面的關(guān)系,而是實(shí)例、語境和命題三者間的關(guān)系,也就是說,實(shí)例必須和語境結(jié)合才能指稱命題,實(shí)例本身也沒有指稱。[28](P18)巴爾-希勒爾利用其理論進(jìn)一步討論了一些哲學(xué)問題,特別是所謂語用學(xué)悖論的偽問題[29] (P376),如“我死了”這樣包含筆者稱之為踐言沖突(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的句子。[30]
當(dāng)然,對(duì)指代詞研究影響最為突出的非大衛(wèi)·卡普蘭的論文《論指示詞》莫屬。這篇論文系未竟之作,其中心思想在20世紀(jì)70年代即流傳,真正出版卻是在1989年(并附有長(zhǎng)篇補(bǔ)記)。[31]首先,這篇論文其實(shí)是一部大部頭著作的草圖,內(nèi)容非常豐富,幾乎涉及指示詞問題的各個(gè)重要方面;其次,論文中富有原創(chuàng)性的思想俯拾皆是,無論是對(duì)直接指稱問題的緊追不舍,還是關(guān)于內(nèi)容與特征(content and character)的區(qū)分,都令人欽佩;再次,卡普蘭展現(xiàn)出精細(xì)的分析能力和形式化技巧,在蒙塔古之后也給出了一套形式系統(tǒng)。
列文森認(rèn)為,在語義學(xué)的哲學(xué)進(jìn)路中,經(jīng)由蒙塔古、卡普蘭等人的工作,已經(jīng)形成了一種共識(shí):將指代詞處理為二階事態(tài),即從語境到命題內(nèi)容的映射(函數(shù)),從而也是一種從世界到真值的映射(函數(shù))。在蒙塔古的早期理論(“普遍語法”)中,直指表達(dá)式的內(nèi)容被捕獲的方式是從語境到內(nèi)涵。語境即一套標(biāo)志,涉及說話者、對(duì)話者、被指的對(duì)象、時(shí)間和地點(diǎn)等。在卡普蘭的指示詞理論中,一切表達(dá)式均有這種從語境到內(nèi)涵的映射(即與命題相關(guān)的內(nèi)容)。指代詞“我”的意義就是其特征,即一種函數(shù)或規(guī)則,在每一個(gè)語境中可變地指派給個(gè)體概念,即說話者。情境語義學(xué)也是一種有影響的二階理論。[32]話段(utterance)是從三種情境或事態(tài)方面被解釋的:話段情境,對(duì)應(yīng)于蒙塔古的標(biāo)志;來源情境,處理其他由語境決定的指稱,如復(fù)指;描述情境,對(duì)應(yīng)于命題內(nèi)容。這些二階理論的核心性質(zhì)是:指代詞并不直接對(duì)所表達(dá)的命題有所貢獻(xiàn),也不對(duì)所說的內(nèi)容和所描述的情境有所貢獻(xiàn)。相反,指代詞把我們帶到個(gè)體、所指物面前,它們?nèi)缓蟊恢萌胨磉_(dá)的命題或被描述的情境當(dāng)中,或如努恩伯格所言:指代詞的意義是復(fù)合函項(xiàng),把我們從語境要素帶到受語境限制的領(lǐng)域的要素,然后就溜走了。[33] (P104-105)
在《哲學(xué)研究》第43節(jié)中,維特根斯坦說了一段我們耳熟能詳?shù)脑挘骸皩?duì)于‘意義’這個(gè)詞的利用的諸情形中的一個(gè)大(large)類來說——雖然并非對(duì)于其利用的所有情形來說——人們可以以這樣的方式說明這個(gè)詞:一個(gè)語詞的意義就是它在語言中的使用……人們有時(shí)通過指向(point to)其承受者(its bearer)來說明一個(gè)名稱的意義。”[34] (P40)雖然我們可以說“語詞的意義在于其使用”是維特根斯坦的總體思想,但是維特根斯坦在這里卻非常謹(jǐn)慎,一方面特意強(qiáng)調(diào)意義即使用只是一大類情形而非全部,另一方面又明確強(qiáng)調(diào)了指向指稱對(duì)象來說明名稱意義的方式,這自然十分接近于指代詞的使用。所以在第44、45節(jié),維特根斯坦說:“因此,它們(名稱)總是可以由帶著指示手勢(shì)的指示代詞來代替。”“但是,這恰恰沒有使得這個(gè)詞(‘這個(gè)’)成為名稱。相反,因?yàn)槊Q并非總是同指示手勢(shì)一起運(yùn)用的,而只是經(jīng)由其得到說明的。”[35](P41-42)這種運(yùn)用其實(shí)是普通的、日常的,在語言休假的時(shí)候,哲學(xué)問題便出現(xiàn)了:將名稱—命名和指示詞—意指神秘化。
在維特根斯坦看來,指示的行為和指代詞的使用,是我們以不同方式學(xué)習(xí)到的,我們不能給出一個(gè)我們稱之為指向這個(gè)形狀(而非這個(gè)顏色)的身體的行為,因此就說,一個(gè)精神的活動(dòng)對(duì)應(yīng)于這些語詞。維特根斯坦不過是說,指示行為需要以大量的社會(huì)舞臺(tái)布景和語言訓(xùn)練為前提,指代詞的使用已經(jīng)隱含地與某種分類能力相聯(lián)系了,否則(比如說)我們無從分辨所指的是書還是書的封面或顏色。指代詞的使用是遵循了語言游戲的規(guī)范性的行為,而不是名稱與對(duì)象的、指示與對(duì)象的因果性關(guān)聯(lián)。[36] (P461)
三、指代詞的哲學(xué)問題
指代詞研究首先得益于哲學(xué)家在語言哲學(xué)、邏輯學(xué)領(lǐng)域的篳路藍(lán)縷之功,而后語言學(xué)家的持久努力也為哲學(xué)創(chuàng)造了進(jìn)一步思考的理論和材料。同時(shí),指代性質(zhì)也與非語言因素相關(guān),如說話者的態(tài)度、語法與文化的互動(dòng),這也為多種視角的研究提供了匯聚的場(chǎng)所,包括哲學(xué)、認(rèn)知心理學(xué)、心理語言學(xué)、社會(huì)語言學(xué)、人類學(xué)等等。我們現(xiàn)在的問題是,在指代詞研究取得了長(zhǎng)足進(jìn)展之際,哲學(xué)能夠進(jìn)一步做哪些工作。
(一)指代詞哲學(xué)研究的定位
如果我們延續(xù)對(duì)語言學(xué)的三分法,即語形學(xué)研究指號(hào)間的形式關(guān)系,語義學(xué)研究指號(hào)與所指物的關(guān)系,語用學(xué)研究指號(hào)的使用者與解釋者之間的關(guān)系,那么,在語言學(xué)中,指代詞研究大致屬于三者交叉領(lǐng)域的一部分,即一種意義—使用關(guān)系,一種對(duì)意義的語境化研究。這部分領(lǐng)域最獨(dú)特的區(qū)域是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系統(tǒng),在其中說話人選擇了自身的視角,將人稱、時(shí)間、空間信息整合在所傳遞的消息中:中心人物是說話者,中心時(shí)間是說話人對(duì)信息加以編碼的時(shí)間,中心位置是說話人編碼時(shí)的位置。
布蘭頓在《言行之際》中,力圖建立分析的實(shí)用主義(analytic pragmatism),以拓展分析事業(yè),其目標(biāo)是在傳統(tǒng)分析方案所關(guān)注的語匯(vocabulary)之間的經(jīng)典語義關(guān)系之外,也考慮以語用學(xué)為中介(pragmatically mediated)的語義關(guān)系。[37] (P11)這種語義關(guān)系被稱為“意用關(guān)系”,有兩種基本的意用關(guān)系:行—言充分性和言—行充分性(practice-vocabulary sufciency 和vocabulary-practice sufciency),前者表明何種行為和能力能讓我們駕馭某種語匯以表達(dá)意義,后者表明何種語匯足以明確某類行為或能力。*此外,還有“行—行”和“言—言”充分性(PP-and VV sufficiency),表示將一種行為闡釋為另一種行為的充分性,或?qū)⒂靡环N語匯刻畫另一種語匯的充分性。參見Robert Brandom.Between Saying and Doing.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39。以此為基礎(chǔ),布蘭頓給出了復(fù)雜的意用關(guān)系分析,其中最有特色的是針對(duì)不同類型的語匯展開的分析:邏輯語匯、指代詞語匯、模態(tài)語匯和規(guī)范性語匯。這里擇要討論之。
布蘭頓認(rèn)為對(duì)指代詞的理解有兩個(gè)重要階段:一是羅素、卡爾納普、賴辛巴赫等人將指代詞視為自反標(biāo)記詞(token-reflexive),指代詞的使用是標(biāo)記的實(shí)例化(tokening)的表現(xiàn)。如前所述,一個(gè)關(guān)于類型“現(xiàn)在”(now)的表達(dá)式就是該標(biāo)記詞的實(shí)例化,我們稱之為“n”,而“n”可定義為或在語義上分析為“說出‘n’的時(shí)間”。二是20世紀(jì)70年代,培里、大衛(wèi)·劉易斯、安斯康等人在模態(tài)和認(rèn)知語境中研究指代詞的用法,否定了前者,認(rèn)為用指代詞表達(dá)的東西不可能用非指代詞等值表達(dá)。基于這一區(qū)分,布蘭頓認(rèn)為,盡管在語義學(xué)上,指代詞和非指代詞不可還原,但完全以非指代詞項(xiàng)談?wù)撊缦禄顒?dòng)是可能的:為了正確使用指代詞,即為了說那些本質(zhì)上的、不可還原的指代的東西,我們必須做什么。[38](P25)也就是說,雖然指代語匯不可能完全還原為非指代語匯,但是非指代語匯可充當(dāng)指代語匯的充分的語用學(xué)元語匯(adequate pragmatic metavocabulary),即為了使用指代詞匯而必須做的一切,均可以完全用非指代詞匯來描述。[39](P56)
于是,布蘭頓認(rèn)為指代詞展現(xiàn)了兩種獨(dú)特的推論行為(discursive behavior):在語義學(xué)方面,指代詞是自反標(biāo)記詞的表達(dá)式類型,標(biāo)記詞的實(shí)例化所表達(dá)的內(nèi)容依賴于實(shí)例化的語境;在語用學(xué)方面,指代詞的使用能夠具有特殊的語用學(xué)意義,即清晰的闡釋能夠認(rèn)可實(shí)際行為所具有的承諾。布蘭頓將這兩種相互依賴的特征命名為卡普蘭—斯托內(nèi)克語義學(xué)和安斯康—培里語用學(xué)。[40](P56-57)布蘭頓由此通過語義學(xué)上的闡釋(explicating)和語用學(xué)上的詳釋(elaborated),表明指代詞與非指代詞之間的關(guān)鍵聯(lián)系。這就是說,知道如何使用非指代詞的人,原則上就已經(jīng)知道為了使用指代詞所需要做的一切。因此,我們能夠理解非指代詞,正是因?yàn)樗鼈儧]有被指代詞神秘化。
這里之所以要利用布蘭頓的理論,是因?yàn)楸M管該理論復(fù)雜而風(fēng)格獨(dú)特,但對(duì)問題的深入思考、對(duì)類型的恰當(dāng)劃分和對(duì)難題的精細(xì)闡釋,的確有非常值得深入研究之處。
(二)指代詞的哲學(xué)問題域
布蘭頓的意用分析是對(duì)塞拉斯推理主義語義學(xué)和維特根斯坦語言游戲觀的綜合和推進(jìn)。在這里,我們主要在語言哲學(xué)領(lǐng)域中勾勒指代詞的問題域,以下三個(gè)核心問題是最值得認(rèn)真考慮的。
1.指代詞使用的語言學(xué)—哲學(xué)預(yù)設(shè)
維特根斯坦在《哲學(xué)研究》第2節(jié)給出了一個(gè)原始的語言游戲,其中有語境、語言共同體、語詞(非指代詞)、理解標(biāo)準(zhǔn)、語詞使用標(biāo)準(zhǔn)。第8節(jié)則擴(kuò)展了這個(gè)語言游戲,增加了數(shù)字或字母詞列、指示詞、指示性手勢(shì)和顏色色樣四種新“工具”。維特根斯坦討論道:“‘到那里’和‘這個(gè)’也是實(shí)指地教給人的嗎?——請(qǐng)想象一下,人們可能會(huì)如何教人學(xué)習(xí)它們的用法!在此人們指向地點(diǎn)和東西,——但是,在這里,這種指向可能也發(fā)生在這些詞的使用中,而并非僅僅發(fā)生在這種使用的學(xué)習(xí)過程。”[41](P14)
隨后,維特根斯坦指出:“為了能夠追問名稱,人們必須已經(jīng)知道了某種東西(或者能夠做某種事情)。但是,人們必須知道什么?”[42](P29)
我們也可以套用這個(gè)問題:為了能夠追問指代詞,人們必須知道什么?必須能夠做什么事情?當(dāng)然,維特根斯坦已經(jīng)給了我們以提示,這就是說,以語言游戲、語言活動(dòng)、生活形式為出發(fā)點(diǎn),而不是將“x表示y”、“x意指y”作為一般模型去思考。
我們可以提出一組基本設(shè)想:(1)指代詞的使用是人類語言活動(dòng)中重要且必要的組成部分,同時(shí),指代詞的使用與非指代詞的使用是不可分割的,離開了非指代詞的使用,我們無法掌握指代詞的用法;(2)指代詞的使用尤其依賴于我們使用概念的能力,如區(qū)分形狀、顏色、狀態(tài)等描述語匯上的分類能力,對(duì)于區(qū)分(時(shí)空)距離、作用等相互關(guān)系的能力,甚至運(yùn)用概念進(jìn)行推理、要求理由和給出理由、做出承諾與承擔(dān)義務(wù)的能力;(3)指代詞的使用在語用學(xué)上也依賴于其他語用方式,如復(fù)指(anaphora,又譯照應(yīng))。
在這里,我們以復(fù)指為例討論指代與復(fù)指的關(guān)系。萊昂斯在《語義學(xué)》中認(rèn)為,直指比復(fù)指更基本,在文本直指(textual deixis)可以看到代詞的直指功能與復(fù)指功能的聯(lián)系。[43](P667)布蘭頓的觀點(diǎn)則截然相反。在《清晰闡釋》中,布蘭頓用整整一章討論了復(fù)指問題,從弗雷格在《算術(shù)基礎(chǔ)》中論述如何指認(rèn)(pick out)對(duì)象談起,著重研究了可重復(fù)標(biāo)記(token repeatables)的結(jié)構(gòu)。他的基本觀點(diǎn)是,復(fù)指絕不只是言內(nèi)設(shè)置(intralinguistic device),而是指稱對(duì)象的必不可少的要素。復(fù)指在概念上優(yōu)先于直指,因?yàn)橹复~被理解為復(fù)指式啟動(dòng)器。指代詞從復(fù)指的先行詞中指認(rèn)出指稱物的能力,是其他標(biāo)記詞具有其確定對(duì)象的能力的必要條件。直指預(yù)設(shè)復(fù)指,一個(gè)標(biāo)記實(shí)例要想具有指示詞的意義,其他標(biāo)記實(shí)例就必須具有復(fù)指依附語(anaphoric depen ̄dents)的意義;將一個(gè)表達(dá)式用作指示詞,就是將其用作一種特殊的復(fù)指啟動(dòng)器。[44](P462)就指認(rèn)個(gè)體對(duì)象、直接指稱對(duì)象而言,如果不能夠復(fù)指,則直指、指代就無法在語境中將對(duì)象意義固定下來,無法給出對(duì)象的坐標(biāo)位置,因此也就無從實(shí)現(xiàn)直指的這一功能。在這個(gè)意義上,布蘭頓是正確的。不過,指代詞仍然具有將一般信念與語境相聯(lián)系的功能,并不總是或必須用作復(fù)指啟動(dòng)器;相反,當(dāng)我們使用復(fù)指詞時(shí),就必須有復(fù)指啟動(dòng)器,其中會(huì)嵌入某種指代要素(不管是真正的指代詞還是專名)。[45] (P168)在這個(gè)意義上,萊昂斯的觀點(diǎn)自然也是有道理的。
在這里,指代或直指與復(fù)指的關(guān)系作為一個(gè)重要案例,提示我們應(yīng)當(dāng)深入思考指代與其他語用要素的關(guān)系,無論是哲學(xué)的還是語用學(xué)的關(guān)系。
2.指代詞的使用與個(gè)體對(duì)象的被給予方式
特定的個(gè)體對(duì)象如何在(認(rèn)知性的)語言游戲中被給予我們?我們?nèi)绾卧谡Z言游戲中指認(rèn)特定的個(gè)體對(duì)象?一般說來,大致有四種方式:(1)弗雷格通過區(qū)分專名的意義與指稱,以專名來描述并指稱對(duì)象;(2)描述主義(descriptivism)通過(羅素式的)摹狀詞或(塞爾式的)簇摹狀詞來描述對(duì)象,從而指稱對(duì)象,專名被理解為蛻化的或縮略的摹狀詞;(3)密爾—克里普克意義上的直接指稱論,即專名作為嚴(yán)格指示詞直接指稱對(duì)象;(4)通過指代詞直接指稱對(duì)象(無須弗雷格意義上的Sinn),如卡普蘭的“直接指稱語義學(xué)”(the semantics of direct reference)。
自從克里普克批判了描述主義之后,弗雷格和羅素的理論基本上被嚴(yán)格指示詞理論取代了。不過,嚴(yán)格指示詞要求某一專名N在一切可能世界中均指稱同一對(duì)象O,如果用模態(tài)詞匯,可以說嚴(yán)格指示詞要求N必然指稱O,這種必然性是一種形而上學(xué)的必然性。描述主義揭示了在認(rèn)識(shí)論上我們對(duì)專名與對(duì)象關(guān)系的把握,往往體現(xiàn)出我們對(duì)專名的實(shí)際使用。在特定語境中通過描述來指稱,恰恰是我們通常的指稱方式。
現(xiàn)在的問題是:(1)指代詞是否具有描述功能?(2)指代詞能否直接指稱?(3)如能直接指稱,指代詞指稱的是什么?(4)指代詞是否為嚴(yán)格指示詞?為了討論這些問題,我們有必要考慮指代詞的基本特征。事實(shí)上,倘若指代詞是嚴(yán)格指示詞,則“萬物一指也,天下一馬也”,指代詞的最大特點(diǎn)就是語境依賴性,因此,不可能成為克里普克意義上的嚴(yán)格指示詞。這種語境依賴性恰恰要求我們通過詳細(xì)闡明語境來確定指代詞的使用,對(duì)語境的闡明自然要借助指代詞所具有的語用學(xué)意義上的表達(dá)性引導(dǎo)作用(pragmatic expressive bootstraping),同時(shí)也要擺脫指代詞,在用非指代詞詳釋該語境,闡明為了使用指代詞,我們必須要做什么、遵循何種習(xí)慣、具備何種能力。
闡明語境就是闡明指代詞的用法。指代詞的用法與語境中的活動(dòng)交織在一起,它們都是語言游戲的組成部分。我們也許可以在語言學(xué)上對(duì)指代詞的描述功能、直接指稱功能進(jìn)行考察和分析,但在語言哲學(xué)層面上,必須在語用學(xué)層次上將指代詞的使用理解為標(biāo)記詞的實(shí)例化行為(tokening),從指代活動(dòng)而不僅僅是指代詞出發(fā)理解直接指稱的行為,否則甚至?xí)?dǎo)致“指代詞悖論”。例如:
“克里特說謊者”。他也可以寫下“這個(gè)命題是錯(cuò)的”取代“我在說謊”。回答可以是:“好啊,不過你意謂的(mean)是哪個(gè)命題?”——“唔,這個(gè)命題。”——“我明白,不過提到的(mentioned)是那里面的哪個(gè)命題?”——“這個(gè)。”——“好的,指的(refer to)是哪個(gè)命題呢?”如此等等。這樣一來,除非他轉(zhuǎn)到一個(gè)完整的命題,否則無法說明他意謂的是什么。——我們還可以說:根本錯(cuò)誤就在于,我們認(rèn)為像“這個(gè)命題”之類的短語,似乎能暗指(allude to)其對(duì)象(從遠(yuǎn)處指向它),卻用不著充當(dāng)其代理(go proxy for it)。[46] (P118-119)
指代詞,至少部分指代詞具有明確的語義內(nèi)容,如今天、明天、昨天,似乎具有某種指稱作用。但是,如果沒有一套相應(yīng)的語用學(xué)框架作為中介,指代詞無法直接指稱對(duì)象;即便說話人掌握了一套關(guān)于某指代詞的語用學(xué)知識(shí),如果此人不具備使用此類詞匯的能力和習(xí)慣,不經(jīng)過語言共同體內(nèi)的學(xué)習(xí)和練習(xí),也不能夠恰當(dāng)?shù)刂阜Q言外對(duì)象。因此,我們有必要區(qū)分包含指代詞的語言游戲的基本類型,從而為進(jìn)一步研究做準(zhǔn)備。
一般而言,在哲學(xué)上具有重要意義的包含指代詞的語言游戲可分為兩種主要類型。第一種類型是“距離定位系統(tǒng)”(distance-oriented systems):所有指代詞均指示指稱對(duì)象與直指中心的相對(duì)距離。[47](P39)這種類型又可細(xì)分為:(1)時(shí)間距離系統(tǒng),典型的時(shí)間距離指代詞是現(xiàn)在、過去和將來,其直指中心是“現(xiàn)在”(now)。(2) 空間距離系統(tǒng),典型的空間距離指代詞是這里、那里,其直指中心是“這里”(here)。(3)文內(nèi)距離系統(tǒng),典型的文內(nèi)距離指代詞是上述(above)、見下(the following)。第二種類型是“人稱定位系統(tǒng)”(person-oriented systems):說話人用指代詞指示鄰近聽話人的指稱對(duì)象。這種類型自然是以“我”、“你”、“他”為典型的,其中“我”是當(dāng)仁不讓的直指中心。
3.指代詞與語句的真值條件
直陳句的真值條件通常包含該句子的邏輯形式和諸詞項(xiàng)的語義內(nèi)容,但對(duì)于包含指代詞的語句來說,其真值條件必須強(qiáng)調(diào)語句及其詞項(xiàng)的語境敏感性和依賴性,而指代特性恰恰是語境依賴性的主要表現(xiàn)(此外還有含混和附帶特性)。因此,對(duì)于這一類句子的分析,真值條件語義學(xué)似乎應(yīng)該讓位于真值條件語用學(xué)。但是,在這里,出現(xiàn)了泛指代論(indexicalism)與真值條件語用學(xué)之間的分歧。
泛指代論認(rèn)為,指代表達(dá)式除了包含明顯的指代詞外(如“我”、“這里”),還包含隱含的指代詞。泛指代論者堅(jiān)持真值條件語義學(xué),主張即便單憑純粹的語義知識(shí)本身不足以確定直陳句的真值條件,只要附加以語用方式提供的具體的必要信息,就能讓純粹語義知識(shí)起到這樣的作用,因此,在不完全決定論證(under-determination argument)中,必要時(shí)用某些隱含的指代表達(dá)式就可以說明真值條件的語境敏感性。真值條件語用學(xué)論者則既反對(duì)純粹語義知識(shí)外加語用學(xué)必要信息的主張,也拒斥對(duì)隱含指代詞的使用。[48] (P438-439)
指代詞的語義泛化的確會(huì)造成麻煩,如果像“鄰居”、“敵人”、“朋友”、“附近”等等均可稱為隱含的指代詞,那么幾乎所有詞項(xiàng)原則上都容易被納入指代行為,因其詞項(xiàng)意義(特征)對(duì)其外延(內(nèi)容)的確定,僅僅相對(duì)于所發(fā)生的語境。[49](P115)這個(gè)問題類似于言語行為理論中關(guān)于踐言話段(performative utterance)的討論。[50]
包含指代詞的語句中最為獨(dú)特的一類是包含第一人稱指代詞的語句。雖然使用“我”這個(gè)指代詞并不等于使用“我”或“自我”這樣的概念,但這個(gè)指代詞的使用卻很可能是關(guān)于自我中心特性、自我知識(shí)、自我意識(shí)、唯我論、第一人稱信念等主題的起點(diǎn),每一個(gè)主題都值得在語言哲學(xué)層次上深究。同時(shí),我們也可以反過來提問:“我”是什么意思?“我”指的是什么?“我”是不是名稱?是不是描述詞項(xiàng)?當(dāng)然,也包括“我”是不是純粹指代詞。
在語言哲學(xué)對(duì)這些主題的討論中,涉及第一人稱信念問題較多,這在前面已有所涉及。這一問題之所以出現(xiàn),按照斯托內(nèi)克的概括,是因?yàn)殛P(guān)于信念的傳統(tǒng)理論認(rèn)為:(1)信念是有生命的主體與抽象對(duì)象(即命題)之間的關(guān)系;(2)命題具有真值,其真值不因時(shí)因地因人而變。[51] (P131)顯然,第一人稱信念語句因其信念狀態(tài)的主觀性而無法保證命題的客觀性、命題的“真”。在第一人稱信念的研究領(lǐng)域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有三個(gè)理論:佩里的涵義—思想理論、劉易斯的涉己態(tài)度理論和斯托內(nèi)克的命題概念理論。[52] (P1)這些理論深化了弗雷格提出的第一人稱信念問題的討論。
以上三個(gè)方面只是指代詞的哲學(xué)問題中基礎(chǔ)性的、最受關(guān)注的部分問題。此外,指代詞的概念性問題、指代詞語言游戲的類型分析、指代行為的整體性與規(guī)范性等問題,均有待深入討論。更重要的是,圍繞指代詞,特別是核心指代詞,我們期待著集語言哲學(xué)、心靈哲學(xué)、邏輯學(xué)、認(rèn)識(shí)論和形而上學(xué)于一體的綜合性哲學(xué)研究。
[1][4][43] John Lyons.Semant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2] Tony Jappy.IntroductiontoPeirceanVisualSemiotics.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2013.
[3] Charles Hartshorne,and Paul Weiss(eds.).CollectedPapersofCharlesSandersPeirce.vol.3.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3.
[5][33] Laurence Horn,and Gregory Ward(eds.).TheHandbookofPragmatics.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2006.
[6][28] 姜望琪:《當(dāng)代語用學(xué)》,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3。
[7] 克里斯特爾主編:《現(xiàn)代語言學(xué)詞典》(第四版),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0。
[8] 呂叔湘:《近代漢語指代詞》,上海,學(xué)林出版社,1985。
[9] Barbara Kryk.OnDeixisinEnglishandPolish.Frankfurt am Main: Verlag Peter Lang,1987.
[10] Otto Jespersen.Language,ItsNature,DevelopmentandOrigin.New York: Macmillan,1949.
[11] Roman Jakobson.SelectedWritings.vol.2,The Hague: Mouton,1971.
[12] Arthur Burks.“Icon,Index,and Symbol”.PhilosophyandPhenomenologicalResearch,1949 (4).
[13] Emile Benveniste.ProblemsinGeneralLinguistics.Coral Gables,Fla.: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1971.
[14] Jacques Lacan.TheFourFundamentalConceptsofPsycho-Analysis.Harmondsworth: Penguin,1979.
[15] Karl Bühler.TheoryofLanguage:TheRepresentationalFunctionofLanguage.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Co.,2011.
[16] Charles Fillmore.LecturesonDeixis.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1997.
[17][47] Holger Diessel.Demonstratives:Form,Function,andGrammaticalization.Amsterdam: J.Benjamins,1999.
[18] Kevin Mulligan and Barry Smith.“A Husserlian Theory of Indexicality”.GrazerPhilosophischeStudien,1986 (28).
[19] John Perry.“Frege on Demonstratives”.PhilosophicalReview,1977 (4).
[20] John Perry.“The Problem of the Essential Indexical”.Nos,1979 (1).
[21] Edward Harcourt.“Frege on ‘I’,‘Now’,‘Today’ and Some Other Linguistic Devices”.Synthese,1999 (3).
[22] Gareth Evans.“Understanding Demonstratives”.Palle Yourgrau(eds.).Demonstrative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23] Bertrand Russell.AnInquiryintoMeaningandTruth.London: G.Allan and Unwin ltd.,1940,Chapter seven.
[24] 羅素:《人類的知識(shí)》,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3。
[25] Hans Reichenbach.ElementsofSymbolicLogic.New York: Macmillan Co.,1947.
[26] John Perry.“Indexicals and Demonstratives” .Bob Hale,and Crispin Wright(eds.).ACompaniontothePhilosophyofLanguage.Oxford: Blackwell,1997.
[27][29] Yehoshua Bar-Hillel.“Indexical Expressions”.Mind,1954 (251).
[30][50] 韓東暉:《踐言沖突方法與哲學(xué)范式的重新奠基》,載《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2007(3)。
[31] Joseph Almog et al..ThemesfromKapla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32] Jon Barwise and,John Perry.SituationsandAttitudes.Cambridge,Mass.: MIT Press,1983.
[34][35][41][42] 維特根斯坦:《哲學(xué)研究》,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3。
[36][44] Robert Brandom.MakingItExplicit.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
[37][38][39][40] Robert Brandom.BetweenSayingandDoing.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45] Pirmin Stekeler-Weithofer.ThePragmaticsofMakingItExplicit.Amsterdam: John Benjamins,2008.
[46] Ludwig Wittgenstein.Zettel.Oxford: Blackwell,1981.
[48] Lenny Clapp.“Three Challenges for Indexicalism”.Mind&Language,2012 (4).
[49] Philippe de Brabanter,and Mikhail Kissine.UtteranceInterpretationandCognitiveModels.Bingley: Emerald Group Ltd.,2009.
[51] Robert Stalnaker.ContextandContent.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52] 周允程:《第一人稱信念的哲學(xué)研究》,清華大學(xué)博士學(xué)位論文,2008。
(責(zé)任編輯 李 理)
On Indexical
HAN Dong-hui
(School of Philosophy,Renmin University,Beijing 100872)
Indexical is linguistic expressions whose references shift from context to context.Indexicals,deictic,and demonstratives are among such kinds of expressions,yet the Chinese translated versions of these terms are rather confusing and therefore need to be rectified.There are two main approaches in the study of indexicals,namely,linguistic and philosophical ones.Three fundamental problems are included in the later approach and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the linguistic-philosophical presuppositions in the use of indexicals,the use of indexicals and the way of picking out individual objects,and the truth-condition of the sentence with indexicals.
indexical;contexualization;demonstratives
中國人民大學(xué)研究品牌計(jì)劃基礎(chǔ)研究項(xiàng)目“當(dāng)代西方哲學(xué)重大問題研究”(10XNI020)
韓東暉:哲學(xué)博士,中國人民大學(xué)哲學(xué)院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