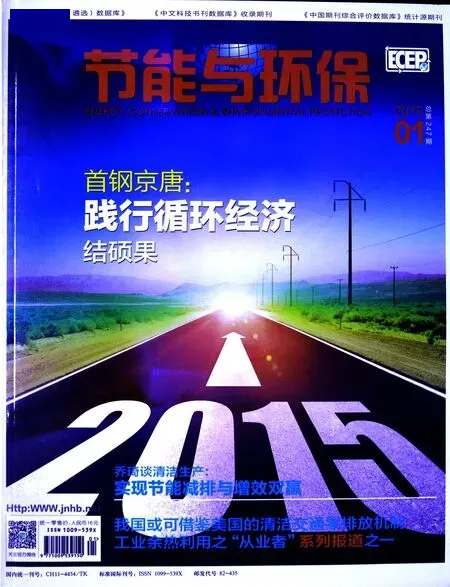建立健全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
建立健全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

一定要理清發展經濟與環境的關系,千萬不能把關系搞錯。其實,清潔生產最好的東西就是在節能降耗的前提下,幫助企業增效盈利。廣西貴港的經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國外的經驗也說明了這一點。
生產者是清潔生產與循環經濟無可替代的主體。為了使生產者這個主體能充分發揮正能量——能夠把環境污染防治與經濟發展結合起來,必須建立健全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簡稱EPR)。
建立健全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是全過程防控戰略的需要
記者:建立健全生產者責任制度意義何在?
喬琦:作為一項在歐美發達國家廣泛執行的、新的廢物管理制度,EPR是通過規定生產者對產品整個生命周期負責,特別是通過產品消費后階段的回收、再循環和最終的處理處置來減少產品對環境的影響。這一制度的實施,已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EPR在我國也日漸成為解決固廢污染防治、實現資源高效利用的必然選擇和重要途徑。另一方面,隨著我國環保和污染防控形勢的日益嚴峻,環境保護戰略由“末端治理”向“過程控制”和“源頭預防”的全過程防控戰略轉型,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正是實現上述戰略目標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國也必須通過立法體系完善和相關配套政策措施的完善,全面推行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從產品全生命周期污染防控角度實現環保管理模式的戰略轉型。
我國EPR與國外比有不小的差距
記者: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EPR不足之處體現在哪些方面?
喬琦: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EPR的實施相對較晚,且目前政策法律體系尚不完善,主要表現為:
一是立法體系不完整,決定了我國EPR推行力度和實施效果有限。我國針對EPR的立法,尚未遵循從基本法、部門法、部門規章等分類的形式進行系統立法,而是以原則、制度、規章、技術措施等紛雜的形式交叉散落在基本法、部門規章、技術規范等各種法律文件中,法律效率層次參差不齊,缺乏對EPR立法體系整體設計和立法推行。
二是責任主體界定不清晰,影響EPR的相關法律的公平性和科學性。我國針對“生產者”的界定各有側重、雜亂無序。我國EPR立法中對EPR責任主體“生產者”的定義更多側重在生產者、制造商或者銷售商,責任主體相對分散且責任范圍相對單一。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國污染防治管理政策的傾向和重心主要集中在生產制造環節,忽略了產品源頭設計、中間銷售、后端使用和報廢回收,最終導致責任主體和責任范圍不統一,部分責任主體搭便車,特別是末端廢物回收處理責任主體缺乏,最終導致政府買單。因此,對EPR中“生產者”的科學合理的界定是保障該制度合理以及可行的重要前提。
三是責任分擔模式的不合理影響了EPR制度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我國EPR責任分攤尚無統一規范的責任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幾類:生產者承擔回收和利用責任模式;銷售者、其它組織或廢物利用處置企業承擔回收利用責任模式;消費者承擔廢舊產品交回的責任模式。
上述幾種責任模式,仍舊處于產品鏈條分段責任模式,注重的是污染治理,而對于優化產品生命周期,從全產業鏈的角度降低污染負荷考慮較少,這也主要是責任分攤模式尚未從全生命周期角度出發展開責任分攤的原因造成的。
今后應重點解決的問題
記者:我國的EPR的確還處在成長期。今后應重點解決的問題是那些?
喬琦:針對我國推行EPR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結合國外該制度的推廣經驗和我國國情,今后我國在推行該制度方面應重點解決如下問題:
一是建立健全完善的EPR制度法律體系。針對EPR制度立法體系尚不健全的現狀,建議從污染防治和資源高效利用角度,從國家的基本法中確立EPR的法律地位。比如,在環保基本法和循環經濟法中明確EPR的法律地位,從各類污染防控法和資源回收利用的部門法中確立EPR原則和宗旨以及推行措施,篩選重點產品制定EPR的技術政策和部門規章。同時,還應考慮綠色消費和綠色供應鏈實施EPR,通過制定“綠色消費法”明確消費者應承擔的EPR責任類型和范圍,制定綠色供應鏈的規章等從產品的全生命周期強化EPR制度的推行和落實,界定供應鏈條上不同主體的EPR責任及分攤模式。
二是明確EPR“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主體。國外針對“生產者”的界定由產品、商品制造者到產品制造者和進口商,最終發展到產品鏈條上所有參與者的過程。因此,針對我國的EPR責任主體的界定,應遵循法律責任利益相關和產品全生命周期的原則,將產品生產者、制造商、銷售商、進口商、使用者以及后端廢物回收處理處置者作為EPR的法律責任主體群,共同但有區別的承擔EPR的法律責任。
三是科學制定“共享分擔”責任分攤模式。結合我國目前污染防治和資源高效利用的管理現狀,我國對EPR責任分攤模式的建立,應采取分階段、分類型的逐步推進模式,在EPR推行前期,重點采取生產者與政府之間進行共享分擔,重點通過政府政策引導和資金扶持,選擇重點行業領域如電子廢物、報廢汽車等領域開展EPR的推行;隨著EPR制度推行進入成熟階段,可適當以產品鏈條上全部的參與者共同分擔,但在責任分攤上應遵循“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
記者:“共同但有區別”的含義是什么?
喬琦:“共同”是指產品全生命周期污染負荷和資源消耗的降低的根本目標;“有區別”是指在EPR五種責任類型分攤時各有側重,比如,生產商負責產品的生態化設計,以保障產品生產、使用和消費乃至報廢后的可資源可循環利用率,制造商則更多地承擔產品生產過程中的污染防控和資源的高效利用責任,零售和進口商則承擔綠色產品采購的責任。與此同時,根據EPR實施產品類型差異,可適當選擇生產者與廢物回收企業或生產者責任組織共享。比如,汽車行業推行EPR,可通過市場合作方式實現汽車制造商與廢舊汽車回收組織的合作方式,實現該領域EPR的實施和推行。
企業必須擔當起來、行動起來
記者:盡管環保風暴越來越厲害,但仍然有地方打著清潔生產、循環經濟的旗號,干著破環環境的事。為什么會有這種現象?
喬琦: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想象,是把環境看成制約經濟發展的因素。人類對環境為所欲為已經習以為常。實際上,換個角度想,環境應該是幫助我國經濟發展的有力工具。國外一些國家已經實現了良好的環境與經濟發展共存。我們應該與環境交朋友,而不是對她為所欲為。清潔生產就是和環境交朋友的方式,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督促、監督生產者與環境交朋友。一定要理清發展經濟與環境的關系,千萬不能把關系搞錯。其實,清潔生產最好的東西就是在節能降耗的前提下,幫助企業增效盈利。廣西貴港的經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國外的經驗也說明了這一點。
記者:經常聽到埋怨環保標準太嚴的聲音。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喬琦:據我所知,現在的確有些部門、產業協會是抵觸環保的,埋怨環保標準太嚴的聲音的確有。這里面有兩個問題。一是企業不愿意參與標準制定。我們特別希望企業參與標準的制定。國外的企業都愿意參與標準的制定,尤其是環境方面的標準制定。為什么?因為他們覺得,做了環境標準,就可以成為自己的一種內在競爭力:參與制定標準的企業,通過防御性措施使自己具備一定水平的防御能力,而其他企業此時還未形成這樣的防御能力——這也就意味著這些企業的競爭力相對較弱。
記者:您覺得我國企業為什么不愿參與標準的制定?
喬琦:這可能跟我們環保一直采用堵的策略相關。其實在環保問題上,也要疏堵結合。清潔生產這種理念用好了,可以增強企業的環保意識。國外企業之所以比較守法,除跟執法嚴格、執法到位有關,同時也和這些企業感到參與定標的確對自己有好處相關。
記者:您要強調的第二個問題是什么?
喬琦:企業應該把真實的排放數據拿出來,否則遭罪的還是企業自己。這方面企業通常有兩種考慮,一是怕把真實數據拿出去對自己不利,二是報喜不報憂。可以想見,建立在失實數據基礎上的標準(一般是偏高),一定會對企業造成巨大的執行難度:但這與企業虛臺自己的排放控制能力相關:你自己都說可以零排放了,那國家為什么不要求你零排放呢?在此,我呼吁行業、產業組織、企業不要一味埋怨標準太嚴,而要積極主動行動起來,配合相關部門制定出適合行業、產業排放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