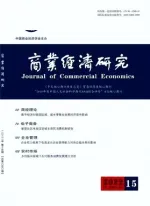東南沿海區際產業轉移模式研究
■ 柳天恩 博士 曹 洋 程振鋒 副教授(邢臺職業技術學院 河北邢臺 054035)
相關研究概述
當前中國正經歷一場大規模區際產業轉移浪潮,這波浪潮被學者們稱為“第四次全球產業轉移”。在這次產業轉移浪潮中,東南沿海無疑起著“領頭雁”的作用。
區際產業轉移是指由于資源供給或產品需求條件發生變化后,某些產業從某一地區轉移至另一地區的過程。國內外關于產業轉移相關問題的研究主要從兩個層面展開,一個是國際層面,另一個是區際層面。研究國際產業轉移具有代表性的理論包括赤松要(1962)提出的雁行理論、弗農(1966)提出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和小島清(1978)提出的邊際產業擴張理論,這些理論普遍認為由于不同國家之間存在產業發展差距和技術梯度勢差,產業遵循從高梯度國家向低梯度國家轉移的一般規律。20 世紀90 年代興起的新經濟地理學派則對區際產業轉移進行了較為系統深入的研究。以克魯格曼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將空間概念引入區域產業布局,解釋了一個存在報酬遞增、壟斷競爭和運輸成本的現實世界,產業為何會出現空間集聚和擴散現象。新經濟地理學派認為,由于歷史或偶然因素,某產業首先在一個地區集中,之后就會在“累積循環因果鏈”的作用下自我強化,形成路徑依賴。然而,產業集聚并非沒有限度,隨著中心地區市場擁擠效應和非流動要素(比如土地等)價格上升,部分傳統產業會從中心地區向外圍地區擴散,而中心地區的產業也會發生轉型升級。由于存在路徑依賴,產業擴散和轉型升級過程緩慢,需要借助外力作用打破均衡,使中心地區產業得到升級,外圍地區產業不斷發展。
國內關于區際產業轉移的研究主要始于21世紀初。主流觀點認為,隨著市場擁擠效應顯現和要素價格上漲,從東南沿海向內陸腹地的區際產業轉移已經開始。陳建軍(2002、2007)認為,自20 世紀80年代以來,長三角內部經濟發展過程實際上是一個以產業轉移為載體的“集聚-擴散”演化過程,體現為產業以上海為中心逐層向外梯度轉移。范劍勇(2004)、范劍勇和李方文(2011)認為制造業在長三角內部的空間調整是激烈的,但從東南沿海向內陸腹地大范圍產業轉移則出現于2004年以后。也有一些學者研究發現,沿海向內陸的產業轉移并非想象中的那樣順利,產業轉移存在滯緩現象。李婭和伏潤民(2010)、李占國和孫久文(2011)認為,目前產業轉移的內生臨界點尚未到來,加之產業布局存在路徑依賴和鎖定效應,要想實現沿海向內陸大規模產業轉移,還需要借助外生力量推動。
總而言之,當前中國區際產業轉移的浪潮已經形成,并開始從小地理范圍向大地理范圍擴展。這種產業的空間擴散轉移對于增強中國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調整優化區域產業結構、化解過剩產能、提高產業競爭力和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由于東南沿海是中國區際產業轉移的“領頭雁”,產業轉移已經積累一定的經驗,以其為研究對象,總結其成功做法,對下一步推動中國更大范圍的產業轉移,減少產業轉移的滯緩和鎖定效應,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東南沿海區際產業轉移的典型模式
東南沿海是我國對外開放較早的區域,也是我國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橋頭堡”和“中轉站”。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這一區域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和工業化水平最高的區域。近年來,這一區域經濟發展普遍面臨要素成本上升、環境承載能力下降、市場擁擠效應顯現的困境,亟需通過產業轉型升級來提升區域產業競爭力和促進區域產業可持續發展,而產業轉移正是推動區域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動力。盡管東南沿海整體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但區域內產業發展并不均衡,各種要素資源的空間分布也不平衡。區域間存在的產業梯度和資源稟賦差異為區際產業轉移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條件。而地方政府也有動力推動產業首先在省區內的轉移。因此,東南沿海的廣東省和江蘇省產業轉移主要表現為省內發達地區向欠發達地區的轉移。對于內部發展相對均衡的上海和浙江,產業轉移則呈現出向周邊省市逐步拓展的特征。
(一)廣東產業、勞動力雙轉移模式
廣東省的珠三角地區是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和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但目前其經濟發展正面臨著土地、勞動力、資源環境等制約,經濟增速出現下滑,產業結構調整壓力較大,省內區域發展極不平衡。為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縮小省內區域發展差距,廣東省早在2005年就制定了《廣東省人民政府關于我省山區及東西兩翼與珠江三角洲聯手推進產業轉移的意見》,支持珠江三角洲地區(包括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東莞、中山6個地級市)將傳統產業向山區及東西兩翼(包括廣東省除珠三角6個地級市以外的其他15 個地級市)轉移,并為此建立了由分管副省長為召集人,省發改委、經貿委、財政廳等相關部門領導參加的“省推進珠江三角洲產業向山區及東西兩翼轉移聯席會議”制度,負責處理產業轉移中出現的問題。2008 年,廣東省進一步制定了《中共廣東省委廣東省人民政府關于推進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的決定》,由此拉開了廣東省產業、勞動力雙轉移的序幕。具體做法為:第一,推進珠三角地區產業向東西兩翼和粵北山區轉移。截至2012 年底,廣東省在粵東西北已設立36 個產業轉移工業園,園區內建成項目1795個,其中規模以上企業1118個。珠三角地區向外轉移的產業包括服裝、五金、玩具、制鞋、包裝等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陶瓷、水泥、家具、再生金屬冶煉產品、有色金屬等資源型產業,IT、家電等資本密集型產業中的加工制造環節,農產品加工等帶動能力不足的產業,塑料制品、涂料、油漆等石化下游產業,工藝玩具、音像制品、食品生產等承接地相對成熟或具有較好承接條件的產業。東西兩翼和粵北山區則根據自身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選擇適合發展的產業進行承接,同時注意環境保護,嚴禁引進不符合產業政策和環保標準的產業,促進產業轉移園區的可持續發展(見表1)。第二,推進東西兩翼和粵北山區勞動力向珠三角地區轉移。為此,廣東省專門建立了農民工工作聯席會議制度,負責指導和協調全省勞動力轉移工作。對于珠三角地區企業招用本省勞動力給予表彰獎勵,對于農村勞動力給予職業技能培訓,對于勞動力轉移提供就業公共服務,對優秀農民工落戶城鎮采取優惠政策,向優秀農民工提供一定比例的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等。

表1 廣東省粵東西北地區重點承接和禁止承接的產業

表2 江蘇南北掛鉤共建開發區一覽表
(二)江蘇南北掛鉤共建開發區模式
江蘇省的蘇南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但面臨土地、資源、勞動力瓶頸,蘇北則恰恰相反。江蘇省為推進蘇南地區傳統產業向蘇北地區轉移,實現南北經濟協調發展和優勢互補,出臺了《關于支持南北掛鉤共建蘇北開發區政策措施》。具體做法為:蘇南地區和蘇北地區相互進行結對,由蘇北地區在本地設立的省級以上開發區中劃出一塊土地作為區中園,由蘇南地區的開發區負責規劃、建設、招商和經營管理,蘇北地區負責園區內的拆遷安置、基礎設施配套、社會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江蘇省政府對共建開發區采取扶持和激勵政策。對于區中園內新增增值稅、所得稅全部補貼給區中園,用于區中園滾動發展,省財政連續三年每年對每個試點開發區區中園以獎代補1000萬元,用于園內的基礎設施貸款貼息及獎勵。省政府采取措施對區中園內用地、用電、融資、員工培訓給予政策支持。園區獲得的收益由蘇南和蘇北合作方共享。江蘇省的做法取得了明顯成效,截至2012年底,江蘇省已經建成37個跨區域共建開發區(見表2)。這些共建開發區主要位于蘇北地區,通過政府自上而下推動建立。一般做法是由蘇南和蘇北按一定比例出資成立投資開發有限公司,作為共建開發區的投資主體,負責園區的開發、建設和運營。共建園區開發建設公司注冊資本總額達29 億元,其中蘇南方面投入23 億元,占注冊資本總額的近八成。為了促進產業轉移的有效性和根植性,37 個共建開發區都有明確的產業定位。
(三)上海異地工業園區模式
上海作為長三角地區的龍頭城市和中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城市,同樣面臨著生產成本上升和環境承載能力下降的壓力,也迫切需要通過產業轉移實現產業轉型升級。上海采取的做法主要是在市外建立異地工業園區,通過“總部經濟、異地生產”模式推進制造業生產環節向外轉移,在擴張企業規模、開拓市場范圍的同時,有效避免了產業“空心化”。目前,上海已經在市外建立了20 多個異地工業園區,主要分布在距離上海300公里以內的蘇北、浙西、皖江、閩北等地區,其中蘇北地區最多,僅在江蘇鹽城就建立了11 個異地工業園區。這些異地工業園區有三個典型特征:一是大型國有企業自下而上推動建立,如上海紡織(集團)有限公司在江蘇大豐建立的“上海紡織產業園”,寶鋼集團在江蘇海門建立的“海寶金屬工業園”,外高橋集團在江蘇啟東建立的“外高橋啟東產業園”等;二是合作雙方建立合資企業共同管理,如上海外高橋啟東產業園由外聯發(外高橋集團全資子公司)和啟東濱海工業園開發有限公司按6∶4 的比例出資成立合資公司外高橋集團(啟東)產業園有限公司,負責園區的開發,公司治理和招商引資以外聯發為主,稅收等收益按雙方出資比例進行分成;三是總部經濟,異地生產,如上海楊浦區在江蘇大豐和海安分別建立楊浦(大豐)工業園和楊浦(海安)工業園,采取企業總部及研發、銷售部門留在上海楊浦區,大中型企業生產環節轉移至大豐,小型企業生產環節轉移至海安的“兩頭在內、中間在外、一個園區、兩個基地”運作模式。這種模式既避免了上海產業空心化和稅收流失,又破解了企業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土地、勞動力等要素成本過高難題,同時也為大豐、海安提供了就業機會和稅收收入。
東南沿海區際產業轉移的經濟效應分析
(一)承接地經濟發展提速,促進了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由于廣東省和江蘇省都存在區際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因此通過區際產業轉移可以增強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動力,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廣東省主要通過產業和勞動力雙轉移,促進省內欠發達的粵東西北地區經濟發展。2012年,廣東省在粵東西北設立的36 個產業轉移工業園實現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766.9 億元,占粵東西北地區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為19.7%;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為27.4%,是廣東省平均增速的3.3倍。粵東西北15個產業承接市中,產業轉移工業園工業增加值增量占比平均達到22%,其中韶關、河源、陽江三市產業轉移工業園工業增加值增量占比超過50%,成為當地工業增長的重要載體。在產業轉移園的帶動下,粵東西北地區經濟發展速度連續多年超過珠三角和廣東省平均水平(見圖1)。江蘇省也呈現類似特征。2013年,蘇北地區新開工500萬元以上產業轉移項目2080 個;新開工項目總投資2920.6億元,同比增長14.6%;蘇北實際引資額1758.1 億元,同比增長19.5%。在南北共建開發區的帶動下,2013 年蘇北地區生產總值增長12%,高出江蘇省和全國平均水平2.4和4.3個百分點,主要經濟指標增速連續八年超出江蘇省和全國平均水平(見圖2)。
(二)轉出地產業結構優化,推動了區域產業轉型升級

圖1 廣東珠三角與粵東西北地區2006-2013 年經濟增速

圖2 江蘇蘇南與蘇北地區2006-2013 年經濟增速

圖3 江蘇省蘇南地區2005-2013 年產業結構變動

圖4 江蘇省蘇北地區2005-2013 年產業結構變動

圖5 上海市2005-2013 年產業結構變動

圖6 上海市2005-2013 年全員勞動生產率
廣東省的珠三角地區、江蘇省的蘇南地區和上海市作為東南沿海最發達的區域,是我國最先承接國際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的地區。近年來,隨著用工成本和土地成本的上升,勞動密集型產業在這一區域已不再具有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迫切需要通過產業轉移為戰略性新興產業騰出發展空間。但產業轉移又必然會對轉出地產生諸如就業和稅收減少等不利影響和產業空心化的風險。為此,在中國“行政區經濟”背景下,地方政府有動力首先推進傳統產業向省內或周邊地區轉移。以江蘇省為例,通過南北掛鉤共建開發區,推進了蘇南地區的傳統產業向蘇北地區的轉移。對產業轉出的蘇南地區來說,相當于在蘇北地區獲得了一塊“飛地”,突破了傳統產業在蘇南發展面臨的土地和勞動力瓶頸,為蘇南地區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拓展了發展空間。通過產業轉移,蘇南地區實現了“騰籠換鳥”和“退二進三”,三次產業結構得到了優化。從圖3可以看出,從2005 年到2013 年,蘇南地區的三次產業結構從3.0∶59.7∶37.4轉變為2.3∶50.3∶47.4。其中第二產業和第一產業呈現下降態勢,而第三產業則明顯上升,表明蘇南地區產業結構實現了高度化發展。與此同時,從圖4可以看出,蘇北地區在承接蘇南制造業轉移的同時,產業結構也得到了優化,第一產業占比明顯下降,第三產業占比則明顯上升,第二產業比重穩中有升。上海市通過在周邊省市建立“異地工業園區”,也有效的推動了上海市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圖5顯示,上海市的三次產業結構比例已經從2005年的1.0∶47.4∶51.6轉變為2013 年的0.6∶37.2∶62.2,現代服務業和高端制造業成為上海市經濟發展的新引擎。在產業轉移帶動下,上海市的全員勞動生產率從2005年的94967元/人大幅攀升至2013 年的191776 元/人,增長了101.9%(見圖6)。上海市全員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主要體現在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這表明產業轉移對產業轉出地技術和勞動效率提升效應非常明顯。
結論及啟示
(一)推進產業梯度有序轉移
產業梯度轉移與產業生命周期有關。任何一個產業部門,都會經歷創新、發展、成熟、衰老四個階段。對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來說,其創新能力較強,通常是新興產業部門的發源地,被稱為產業的高梯度地區。與之對應,欠發達地區則往往被稱為產業的低梯度地區。隨著時間推移,高梯度地區原來的新興部門逐漸走向成熟,生產的標準化和技術外溢使得低梯度地區也可能通過學習獲得相關生產技術。此時,對高梯度地區來說,其土地、勞動力等要素成本要比低梯度地區明顯偏高,如果不通過產業轉移和結構升級實現產業結構的高級化,其產業競爭力將會逐步喪失。而對于低梯度地區而言,由于在土地、勞動力、自然資源等方面具有成本優勢,成熟產業在當地還存在巨大市場需求,這些成熟的產業部門對本地尚屬于“朝陽產業”,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此時,高梯度地區與低梯度地區通過合作,推進成熟產業按梯度勢差從高向低轉移,可以實現互利雙贏。高梯度地區實現了產業結構高級化,為新興產業部門騰出了發展空間,低梯度地區提高了自身的工業化水平,解決了當地就業和稅收收入問題。產業梯度轉移從地理空間上可以通過兩種途徑實現,一種是按距離由近及遠從高梯度地區向經濟聯系較為緊密的周邊地區轉移,另一種是蛙跳式向外圍廣大地區擴散,后一種形式在形態上通常表現為“飛雁”模式。
(二)推進產業集群鏈式轉移
產業集群轉移又稱產業鏈式轉移,是指一個地區將具有上下游關聯的整個產業集群轉移至另一個地區。這種產業轉移模式至少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好處:一是通過產業集群網絡關系復制,可以形成中間產品市場,增強產業配套能力,降低轉移企業的交易成本。在集群內部,大家都比較熟悉,雙方存在穩定的信任關系和合作關系,無需花太多精力就可以搜尋到上游的原材料、中間品的供應商和下游的銷售渠道。二是通過產業集群轉移可以增強產業發展的內生動力。因為產業集群一旦形成,就會在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作用下不斷強化,形成路徑依賴,增強集群的吸引力和競爭力。三是通過企業抱團轉移,可以增強集群內企業與當地政府談判籌碼,降低因市場和政策的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產業集群內部通常有行業協會作為與當地政府交流的平臺,使當地政府不敢輕易對集群內部企業實現歧視性的政策。通過建立產業轉移園區,可以推進產業集聚發展,培育產業集群,形成上下游產業鏈相互配套,生產與服務相互配套,增強產業集群轉移的根植性,提升產業轉移園區的競爭力和吸引力。
(三)推進產業互補綠色轉移
優勢互補是區際產業轉移的根本動力。產業轉出地通常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土地資源緊缺,勞動力成本偏高,傳統產業發展面臨資源環境約束,而產業轉入地則恰恰相反。雙方在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上存在互補性,是區際產業轉移順利推進的基本前提。但即便雙方存在產業上的互補優勢,區際產業轉移也未必能夠順利推進。這是因為產業轉出地普遍擔心產業轉移會引起稅收流失、就業機會減少和產業“空心化”,通常會采取措施阻止企業遷移。因此,要想減少區際產業轉移的障礙,還必須建立產業轉移區域利益協調機制。例如,對產業轉移園區獲得的稅收收益留成部分,可以由合作雙方按比例分成;產業轉出地可以采取“總部經濟、異地生產”模式,鼓勵企業只轉移生產環節,將企業總部和研發部門等留在產業轉出地。此外,對于產業承接地來說,也不應不加選擇的承接發達地區產業轉移。承接產業轉移時應該按照主體功能區規劃的要求,根據生態環境承載能力,實行差異化的產業轉移與承接政策。對于生態環境脆弱的地區,要制定嚴格的環境準入標準,避免污染企業異地搬家。產業轉移應堅持綠色轉移,走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產業轉移道路,將產業轉移對生態環境的影響降至最低,實現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四)政府搭建產業轉移平臺
為消除產業轉移的粘性因素,政府應出面搭建產業轉移合作平臺,制定產業轉移專項規劃,出臺產業轉移優惠政策,推進產業有序轉移。當然,政府的主要作用只是為產業轉移搭建平臺,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既不能缺位,更不能越位。具體運作要以企業為主導,采取市場化方式,充分發揮企業在區際產業轉移中的主體作用和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東南沿海的普遍做法是由政府搭臺建立產業轉移園區,并出資成立園區投資開發公司,負責園區的開發建設和經營管理。這種通過“政府搭臺、企業唱戲、市場化運作”的產業轉移模式,有效的推動了區域間資源優化配置和要素合理流動,避免了政府主導的“拉郎配”,增強了產業轉移的有效性。
1.陳建軍.中國現階段的產業區域轉移及其動力機制[J].中國工業經濟,2002(8)
2.陳建軍.長江三角洲地區產業結構與空間結構的演變[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2)
3.范劍勇.長三角一體化、地區專業化與制造業空間轉移[J].管理世界,2004(11)
4.范劍勇,李方文.中國制造業空間集聚的影響:一個綜述[J].南方經濟,2011(6)
5.李婭,伏潤民.為什么東部產業不向西部轉移:基于空間經濟理論的解釋[J].世界經濟,2010(8)
6.李占國,孫久文.我國產業區域轉移滯緩的空間經濟學解釋及其加速途徑研究[J].經濟問題,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