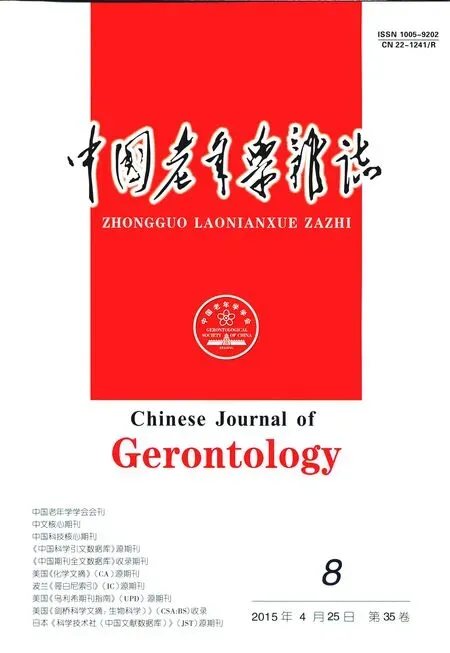城鄉社區老年人負性生活事件調查及對策
城鄉社區老年人負性生活事件調查及對策
付文寧柴云1劉巧艷2劉冰1
(遼寧醫學院研究生院,遼寧錦州121000)
摘要〔〕目的探討城鄉社區老年人社會支持與老年人負性生活事件的相關性差異。方法應用老年健康狀況(MDS)和相關因素調查量表對1 000例≥60歲以上的社區老人進行問卷調查,采用Logistic回歸分析社會支持與老年負性生活事件之間的聯系。結果城鄉社區老年人在健康惡化、經濟困難、難過事件的發生率間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在是否與子女同住、是否擔心子女、離最近親人的距離、健在兄弟姐妹居住距離、與親人和朋友聯系情況、是否獲得幫助方面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城市社區影響老年人負性生活發生的因素有:擔心子女、每月與朋友聯系1次、與親人居住距離、獲得幫助(均P<0.05);農村社區是:擔心子女、每天與鄰居聯系、不經常與親人聯系、獲得幫助(P<0.05)。結論農村社區與子女同住的老人多于城市;農村社區老人與親人、鄰居的聯系較城市老人頻繁;影響城鄉社區老人負性生活事件發生的共同因素是擔心子女和獲得幫助。結合研究結果,提出老年人負性生活事件的社區服務。
關鍵詞〔〕負性生活事件;社會支持
中圖分類號〔〕R2〔文獻標識碼〕A〔
基金項目:湖北省衛生廳專項研究項目(No.ZX2012-11)(英國BUPA
通訊作者:劉冰(1966-),男,博士,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衛生服務研究。
1湖北醫藥學院衛生管理與衛生事業發展研究中心
2湖北醫藥學院護理學院
第一作者:付文寧(1989-),女,在讀碩士,主要從事社區護理、護理教育研究。
隨著老齡化程度的加深,老年人的健康問題日益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而負性生活事件可作為應激原作用于個體并可能對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響〔1〕。近年來,國內外對負性生活事件進行了大量研究〔2〕,但對老年人負性生活事件與社會支持的研究較少。本研究主要探討城鄉社區社會支持對老年人負性生活事件影響的差異,以期為城鄉社區老年衛生服務保健工作提供更準確的決策依據。
1對象與方法
1.1對象采用入戶面對面詢問方式調查湖北省十堰市常住居民中≥60歲以上的老年人。農村社區按照多階段、整群抽樣方法,選擇3個行政村所有老年人進行調查,共531人,獲有效問卷500份,有效應答率為94.2%。城鎮社區采用多階段、隨機等距法抽取3個較大社區的501名老年人作為調查對象,獲有效問卷500份,有效應答率99.8%。
1.2調查工具與方法問卷采用英國利物浦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Copeland教授設計的《老年健康狀況和相關因素調查量表》,該量表在國內已有廣泛的應用〔3〕。與本論文有關的調查內容包括湖北省城鄉社區老年人的人口社會學特征、生活方式和行為、社會聯系和社會支持等。其中社會聯系和社會支持包括居住模式、與子女、親戚、朋友、鄰居的居住距離及聯系情況等。調查方案由安徽醫科大學相關專家進行論證并進行了預調查及后續修改,對調查人員統一集中培訓,成立專家技術組和領導小組負責調查工作的質量監督,并保證每天收回問卷有5%的復核率。
1.3統計學方法使用SPSS18.0進行描述性分析、χ2檢驗、非參數U檢驗、Logistic多因素回歸分析。
2結果
2.1城鄉社區老人社會人口學特征有效調查共1 000人。城市社區老年人平均年齡(68.8±6.9)歲,農村社區(70.6±7.9) 歲。城鄉社區老人的性別構成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城鄉社區老人的年齡、婚姻構成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均為 0.000);城市社區老人的文化程度以小學為主,農村社區以文盲為主,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00)。見表1。

表1 城鄉社區老人社會人口學特征比較〔 n(%)〕
2.2城鄉社區老年人負性生活事件發生情況城鄉社區老年人在健康惡化、經濟困難、難過事件的發生率間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城鄉社區老年人負性生活事件發生情況〔 n(%)〕
2.3城鄉社區老年人社會支持情況本研究從9個方面研究城鄉老年人的社會支持特征:擔心子女、子女同住、離最近親人的距離、離健在兄弟姐妹居住距離、與親人聯系情況、與子女或朋友聯系情況、與鄰居聯系情況、獲得幫助情況及對獲得幫助的滿意情況。城鄉老年人在獲得幫助滿意情況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農村社區老年人與子女同住的比例高于城市社區(P=0.000);城市社區老年人比農村社區老年人更擔心子女(P=0.043);城市社區老人每天聯系或每周聯系2~ 3次的比例為:18.8% (與親人)、87.4% (與朋友)、69.0% (與鄰居),農村社區此比例分別為41.6%、70.6%、79.4%,聯系頻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2.4城鄉社區老年人負性生活事件與社會支持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選擇單因素分析有統計學意義的變量建立logistic回歸模型,綜合分析這些因素對負性生活事件的影響,為排除混雜因素的影響,引入經濟收入滿意度、生活態度、是否患有抑郁和癡呆癥等9個變量進行校正后,影響城市社區老年人負性生活事件發生的因素有擔心子女、與朋友聯系1次/月、親戚居住在同縣/同市、獲得幫助(OR=2.435,7.686,0.361,0.406;95%CI:1.403~4.227,1.425~41.444,0.160~0.818,0.193~0.858,均P<0.05);農村社區為擔心子女、每天與鄰居聯系、不經常與子女或者親人聯系、獲得幫助(OR=2.002,0.301,1.857,0.386;95%CI:1.197~3.347,0.182~0.798,0.281~0.935,0.145~0.976;均P<0.05)。
3討論
老年人的生理特點決定了隨著年齡的增長,體質變弱,對疾病的抵抗力明顯下降,導致疾病增多,健康狀況惡化。本調查顯示,城市老年人健康惡化的發生率低于農村老年人。瑪麗琳.文克勒比認為,良好的教育能使人具有更加良好的生活方式,也能提高一個人解決健康問題的能力〔4〕,城市老年人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總體上更了解健康生活方式的好處和預防保健的重要性,當出現健康問題時,能夠更好地獲取醫療服務。農村老年人經濟困難發生率高于城市,這與錢薛飛〔5〕的研究結果一致。這種差異在一定程度上可由居民保障制度和受教育程度的差異來解釋。與城市老人相比,多數農村老人無退休保障,缺乏固定收入來源。同時,農村老人知識技能普遍較低,參與經濟活動的能力較差,很難獲得其他補充性收入。本調查結果也顯示,農村社區老年人意外事件發生率高于城市,與以往研究結果一致〔6〕。提示應在農村社區積極宣傳意外事件的危害和可預防性,提高老年人的防護意識,同時各級政府、醫療衛生、司法、公安等部門及工作人員應根據自身條件和當地農民的需求,建立健全意外傷害防護網絡。
城市社區,老人更多的是與朋友交流,而農村社區是與親人和鄰居交流。這與以往研究結果一致〔7〕。城市社區,每月與朋友交流1次的老人負性生活事件發生的危險是每天交流的7.686倍。農村社區,從不與親人交流的老人負性生活事件發生的危險是每天交流的1.857倍;每天與鄰居交流是農村老人負性生活事件發生的保護因素。在城市社區,首先,由于文化程度、工作經歷等因素,老人有同事、同學、戰友等人際關系,晚年有較為固定的朋友。其次,城市社區由于居民由不同社會經濟身份特征的人聚合構成,人口流動增大,鄰里間交往缺乏穩定性,導致聯系頻率下降明顯。瑞士一項社區老年人隨訪研究也發現,隨著老年人年齡的增加,朋友對其的支持影響將更為突出〔8〕。在農村社區,由于同村人中很多都出自一個大家族,且長期居住在一個固定地方,流動性較小,很容易獲得來自鄰居和親人提供的社會支持。無論是與親人、朋友還是鄰居交流的過程中,能使老年人克服孤獨感,保持積極樂觀的情緒,并增進健康的同時與同齡人交流是老年人情感宣泄和舒解的重要途徑,進而減少負性生活事件的發生。
由于農村老人的子女大都無固定工作,職業、崗位變動性比較大,因此反而沒有城市老人那么擔心。一項調查〔13〕也支持本研究的觀點,城市老人最擔心的是子女失業,而農村老人最害怕生病。無論是城市社區老人還是農村社區老人,都受到中國傳統家庭價值觀念的影響,許多老人心甘情愿地為子女提供各種支持,步入老年仍擔心他們的生活、工作和學習。年輕一代的許多觀念和生活方式,老人往往不能理解,更加重了他們的擔心,導致抑郁、焦慮等負性情緒,進而損害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增加治療身心疾病所需的醫藥費,加重家庭經濟負擔,最終影響老年人負性生活事件的發生。獲得幫助是城鄉老人負性生活事件發生的共同保護因素,說明獲得幫助可以減少老年人負性生活事件的發生。不過,由于城鄉老年人個性、文化程度、身心狀況等個體因素,以及外部的環境,如家庭、社區、社會條件等存在差異,可能每個老年人的需求有所不同,因此提示城鄉社區的工作人員應對老年人的各個方面加以細致調查,并根據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給予老年人最迫切的幫助和支持,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滿意度,減少負性生活事件的發生。
調查結果顯示,城鄉老年人所面臨的問題主要集中在健康問題和經濟問題上。對健康惡化發生率高的老年群體應加強護理,將這些老年人的資料存檔,并對其定期訪視和護理。社區護理工作人員應階段性地對所服務區域內的老年人定期進行體檢,建立疾病管理檔案,及時給予治療護理,有效控制疾病的發展,促進疾病的好轉。由于多數老年人在經濟方面比較困難,因此實施社區護理時應注意經濟的原則,盡量開設價格合理、低投入高產出的護理項目,使老年人健康和社區護理獲得雙贏局面。
研究結果表明,經常與親人、朋友、鄰居交流的城鄉老年人負性生活事件發生率低。在城市,老年人曾多為工人,文化程度相對較高,可以在社區設置一定的符合老人條件的職位,鼓勵其參與社區的管理,發揮“余熱”,還可以組織工友會等活動,購置相應活動設施,鼓勵居民參與,促進老人之間的相互交流。在農村,豐富新農村文化建設內涵,為他們提供一個和諧的交流環境,如在農村建立老年活動中心,老年俱樂部等。同時,社區可根據自身情況和老年人的需求,定期開展小講課等活動,采用深入淺出的方式教給老年人健康知識,降低負性生活事件的發生率。
4參考文獻
1涂陽軍,郭永玉.生活事件對負性情緒的影響:社會支持的調節效應與應對方式的中介效應〔J〕.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2011;19(5):652-5.
2劉壽,王兆芬,張發斌,等.民族地區醫學生負性生活事件及應對方式與健康關系〔J〕.中國公共衛生,2013;29(7):1034-38.
3陳蕾,李曼,李文霞,等.社區老年人慢性病與生活方式調查及分層護理模式構想〔J〕.中國全科醫學,2013;16(9):1012-5.
4Winkleby MA,Jatulis OE,Frank E,etal.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health:how education,income and occupation contribute to risk factor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J〕.Am J Public Health,1992;82(6):816-20.
5錢薛飛.城鄉老年人收入來源的差異及其經濟性影響〔J〕.華南農業大學學報,2011;10(1):104-13.
6那軍,張淑娟,楊曉麗,等.遼寧省城鄉老年人意外傷害流行病學調查〔J〕.中國慢性病預防與控制,2010;18(1):45-51.
7王春穎,劉新研,樊立華,等.城鄉社區老年人社會支持的現狀〔J〕.中國老年學雜志,2012;32(1):120-1.
8Moiler J,Bjorkenstam E,Ljung R,etal.Widowhood and the risk of psychiatric care,psychotropic medication and all-cause mortality:a cohort study of 658,022 elderly people in Sweden〔J〕.Aging Ment Health,2011;(15):259-66.
〔2014-02-17修回〕
(編輯袁左鳴/滕欣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