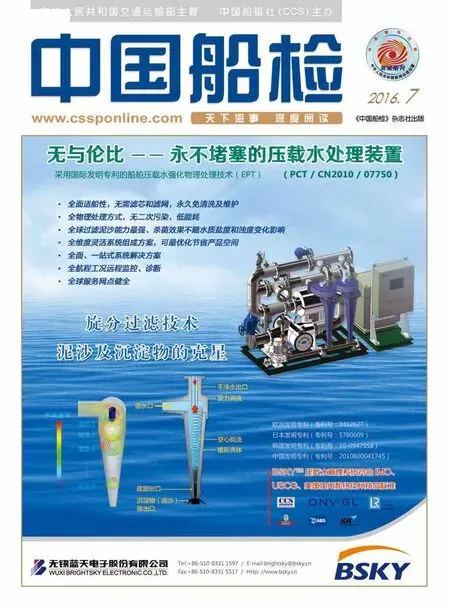船舶保險中的不適航除外責任
初北平 大連海事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
所謂保險除外責任通常是指保險單上載明的保險人不負賠償責任的災害事故及其損失范圍。保險人確定除外責任通常考慮的因素,包括法律角度和保險技術兩個方面。從法律角度看,鑒于保險合同的要素之一是事件發(fā)生的不確定性,因此不具備意外性和偶然性的事故自然不被保險人所承保,如固有缺陷、自然磨損、與船舶日常操作關聯(lián)的損失以及正常的維修保養(yǎng)或者更換的損失等;從保險技術的要求出發(fā),保險人一般都將特殊風險,即一些發(fā)生概率和損毀程度難以預測、危害范圍很廣、損失金額十分巨大的災害事故,如戰(zhàn)爭、軍事行動、暴力行動、核輻射等列為除外責任。
我國人保2009年船舶保險條款第二條明確列舉了四類除外責任:不適航;被保險人及其代表的疏忽或故意行為;被保險人恪盡職責應予發(fā)現(xiàn)的正常磨損、銹蝕、腐爛或保養(yǎng)不周,或材料缺陷包括不良狀態(tài)部件的更換或修理;以及戰(zhàn)爭和罷工險條款承保和除外的責任范圍。只要除外責任條款所列明的事項發(fā)生,不論是在“全損險”還是“一切險”下,保險人都不負賠償責任。本文將對船舶保險中的不適航除外責任予以具體的闡釋。
船舶保險條款對不適航除外責任的規(guī)定如下:“本保險不負責下列原因所致的損失、責任或費用:(一)不適航,包括人員配備不當、裝備或裝載不妥,但以被保險人在船舶開航時,知道或應該知道此種不適航為限;……”可見,無論是定期保險,還是航次保險,保險人根據(jù)本款規(guī)定免除賠償責任時,必須證明以下三點:一是客觀上,船舶存在不適航的事實;二是主觀上,在船舶開航時,被保險人實際知道或應該知道不適航;三是不適航與被保險人索賠的損失之間具有因果關系。
客觀事實:船舶不適航
根據(jù)本款規(guī)定,保險人免除賠償責任的前提是船舶存在不適航的客觀事實,此處的船舶適航是廣義的概念,包括配備船員、裝備船舶以及裝載貨物這三方面,任何一方面的不當或不妥,都將構成船舶的不適航。
船舶適航證書是船舶適航的表面證據(jù)。船舶適航與否是一個事實問題,船舶通過法定檢驗和船級社檢驗后,檢驗機構將給船舶頒發(fā)船舶法定檢驗證書和船舶適航證書,該證書是船舶適航的書面證明之一,構成海商法下船舶適航的形式要件。實踐中,海事法院會首先核定船舶的各類證書,如果船舶缺少法定證書、超越證書限定的航區(qū)航行,證書無合理原因過期又未及時提出延長,則會被認定為不適航。
船舶適航證書并非船舶適航的絕對證據(jù)。船舶證書體現(xiàn)的是船舶檢驗當時技術狀態(tài)滿足技術標準和管理標準的靜態(tài)情況,而船舶保險中的船舶適航是針對船舶抵御每一個具體航次的風險動態(tài)情況,因此船舶所載的法定證書符合要求只能說明船舶滿足了適航的最基本的形式要求,并不能作為司法實踐中判斷船舶是否適航的唯一依據(jù)。在船舶保險實務中,還應以保險合同雙方誰提供的證據(jù)更為充分可靠,來認定船舶是否適航。
1、船上人員配備不當
船上人員配備不當是指船員在數(shù)量上或質量上配備不當。數(shù)量上的配備不當是指船舶配備的船員數(shù)量不能滿足船舶正常航行值班或作業(yè)的需要,違反《船舶最低安全配員證書》的規(guī)定。
如在泰州市振陵運輸有限公司與安信農業(yè)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海上保險合同糾紛上訴案中,振陵公司為其所屬的“振陵機369”輪向安信保險投保了沿海內河船舶一切險,“振陵機369”輪在曹妃甸海域裝砂后船體傾覆下沉。保險船舶在出險時,船上僅有四名船員,不符合該輪最低配員7人的要求,影響了船舶排水和施救,構成了船舶不適航,且與船舶沉沒具有因果關系,因此法院最終以此認定該保險事故屬于保險人的除外責任。保險人不負保險賠償責任。
質量上的配備不當是指船長或船員不能勝任本職工作,表現(xiàn)為不滿足相應的職能和責任級別所要求的知識和技能,未持有相應的適任證書。如果船員持有相應的適任證書,但是在船期間經(jīng)常酗酒而影響履行職責,工作責任心不強或玩忽職守,亦構成船上人員配備不當。
在“浙普漁油31”一案中,保險船舶發(fā)生保險事故的所在地是渤海灣海域。“浙普漁油31”的二副持有200~1600總噸近岸航區(qū)船長證書(即C類船長證書),二審法院認為,該證書不是渤海灣沿岸各省港監(jiān)簽發(fā)的,其在渤海灣海域航行,違反了國家交通運輸部的有關規(guī)定,屬超區(qū)航行,船員的配備不合格導致船舶不適航,因而保險人不負保險賠償責任。
2、裝備不妥
裝備不妥主要指:①船舶技術性能不符合船級規(guī)范的要求和不具備其航程所需的技術性能要求;②助航設備、系泊設備裝備不妥;海圖、航路指南等航系資料以及相關法定證書等不齊全或存在效力問題;③開航前未能準備充足的燃料、物料、淡水和食品等物品,供船舶在下一停靠港添加之前使用。在配備燃料上,除應正確計算航程與船舶耗油量外,需考慮燃料的質量、航次中風浪、洋流等情況,確定安全系數(shù)。
3、裝載不妥
裝載不妥主要是指沒有按船舶的不同類型進行合理的裝載貨物或貨物裝船時配載不當。在中國太平洋保險公司杭州分公司訴應芝龍船舶保險合同糾紛案中,“浙紹海3”號輪裝載貨物時,由于積載不當,甲板上裝載貨物,使重心提高,導致穩(wěn)性不滿足法規(guī)要求,法院認定此時船舶處于不適航狀態(tài)。當擱淺后在受橫向水流作用下,該船的復原力矩已不足以抵抗水流傾覆力矩,致使該船向順流方向傾覆,即不適航與事故造成的損失具有因果關系,法院最終判決認為裝載不妥造成的不適航確系保單約定的免責事項之一。
4、不適航的時間
根據(jù)《海商法》第244條(一)款規(guī)定,不適航僅限于“船舶開航時”,即船舶開航前和船舶開航后的不適航不能作為保險人免于賠償?shù)囊罁?jù)。人保2009年保險條款中對“不適航”的時間未做任何限定,既未肯定海商法的規(guī)定,亦未明確地作出相反約定。筆者認為在理解該條款時,應當參照《海商法》的規(guī)定,對其做相同的解釋。此外,從上下文文義中也可推知該含義,人保條款要求保險人免于賠償責任應“以被保險人在開航時知道或應當知道此種不適航為限”,因此如不是開航時的不適航,被保險人不可能在開航時就已經(jīng)知道,而如果是開航前存在的卻在開航時已經(jīng)修復的不適航也不可能導致后來的損失。
需注意的是,在船舶航次保險的情況下,這樣的規(guī)定并不足以滿足實踐的需求,容易引起爭議。具體來說,人保2009年條款第五條對于載貨船舶的航次保險期限的規(guī)定為“自起運港裝貨時開始至目的港卸貨完畢時終止……”那么對于船舶已經(jīng)開始裝貨但尚未開航的在港期間,是否也要求保險船舶需具備抵抗港內一般風險的能力呢?《海商法》和人保2009年條款對此未作規(guī)定,這顯然不便于保險合同雙方確定開航前保險事故的責任承擔。1906年英國海上保險法( MIA1906)第39條第2款規(guī)定,“如果保險單生效時船舶停在港內,這亦含有默示保證,即保證船舶在所承保風險開始時就應具備合理的設備,足以能經(jīng)受港內的一般風險”,盡管我國海上保險立法尚未引入默示保證制度,但在船舶保險條款中,擴充被保險人自保險責任開始后至船舶開航前這一期間內的義務,有助于船舶保險糾紛的減少。船舶保險合同雙方有必要結合保險責任期限對不適港除外責任做進一步的約定。
主觀標準:被保險人知道或應當知道
在存在保險船舶不適航這一客觀事實的基礎上,保險合同又通過“主觀標準”將不適航限定在一定范圍內,即“以被保險人在船舶開航時,知道或應該知道此種不適航為限”。該限制條件可以從以下三方面解讀:
1、知道或應當知道的主體限于被保險人,當被保險人是一個公司法人時,知道或應當知道的主體為公司的股東、董事等。實踐中,船東往往把對船舶和船員的基礎管理委托給船舶管理人或者公司里董事以外的負責人。這些人知道船舶不適航相當于被保險人知道。但被保險人本人不包括船長和船員等被保險人的雇傭人員。因此,如果船長和船員在開航時知道船舶存在不適航的情形,但并未告訴被保險人時,屬于承保風險中的“船長、船員的疏忽行為”,而非“不適航”除外責任,保險人對因此造成的損失應承擔賠償責任。
2、知道是指被保險人對船舶不適航的狀態(tài)實然上的知曉和了解,但卻對此聽而不聞、視而不見或明知故犯。例如,被保險人明知船上的一些船員不合格,仍然錄用;明知被保險船舶技術性能達不到應去水域的要求,仍然派往。
3、“應當知道”以一般的謹慎被保險人的行為作為標準。在同樣的情形下,如果謹慎的被保險人會對船舶不適航狀態(tài)有所知曉,則認為實際被保險人也應當知道。該規(guī)定降低了保險人的證明難度。
上文提到的中國太平洋保險公司杭州分公司訴應芝龍船舶保險合同糾紛案中,很好的詮釋了“應當知道”在上述情形的適用情況。法院認為被保險人對“浙紹海3”號輪在開航時不適航狀態(tài)是應當知道的,理由在于:①保險船舶裝有23件甲板貨,而裝載甲板貨會影響船舶的穩(wěn)性進而可能導致船舶不適航是一個普通常識,因此作為該輪二副且就在船上的被保險人應當是明知的。②事發(fā)后船員對裝載甲板貨數(shù)量所作的虛假陳述,該行為也證明了船長和船員對裝載甲板貨足以影響船舶穩(wěn)性是明知的,因此,很難說被保險人對船舶不適航完全不知情。
人保2009年條款的規(guī)定與我國《海商法》的規(guī)定存在不同,根據(jù)《海商法》第244條第(一)款規(guī)定,不適航構成除外責任的限制條件是:“船舶定期保險中被保險人不知道的除外”。可見,《海商法》對船舶定期保險與航次保險做了不同的處理。船舶定期保險中,被保險人在開航時對船舶的不適航不知道的,不喪失從保險人處獲得賠償?shù)臋嗬欢诖昂酱伪kU中,被保險人無論在開航時是否知道船舶不適航,保險人均可依據(jù)不適航免于承擔保險賠償責任。《海商法》第244條允許合同另做約定,且人保2009年條款的規(guī)定是有利于被保險人的,因此應當承認人保2009年條款的效力。
不適航與被保險人索賠的損失之間具有因果關系
無論是《海商法》第244條還是人保2009年保險條款,都使用了“下列原因所致的”這一措辭,這意味著保險人免于賠償?shù)膿p失、責任或費用必須是由除外風險“所致的”,即除外事項的存在或發(fā)生本身尚不足以構成保險人免于賠償?shù)睦碛桑€要求損失與除外事項之間存在保險法上的因果關系。例如,船上消防設備的故障可能使船舶處于不適航狀態(tài),但是保險人若因此主張免于賠償責任,還需證明:如果該消防設備正常,使用該設備本可以成功滅火,控制火情。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理的“林文杰訴寧波人保公司船舶保險合同賠償責任案”中,保險船舶發(fā)生事故時船上有八名船員,低于十人的最低配員要求,但法院認為,事發(fā)當時值班的均為職務船員,所缺少的兩名船員非船上職務船員,故不能據(jù)此認定本案船舶在開航前或當時不適航。同時,缺少船員須與保險事故存在因果關系,該案船舶觸礁并非因船員配備不當,所以認為此次事故并不構成保險合同所約定的除外責任。
與英國法的比較
英國MIA1906第39條對船舶航次保險和船舶定期保險下的不適航處理機制不同:在航次保險中,適航被規(guī)定為被保險人的一項默示的保證義務;而在定期保險中,被保險人沒有此項默示保證,而是將不適航列為了除外責任的事項,但以被保險人的明知為限。
1、船舶定期保險適航制度的比較
根據(jù)MIA1906第39(5)條的規(guī)定,不適航在船舶定期保險中是一種除外責任,這與“不適航”在我國《海商法》和保險條款中的性質相同。并且都要求不適航與損失之間具有因果關系。
中英兩國關于船舶定期保險下不適航除外責任的區(qū)別,主要表現(xiàn)在對被保險人主觀方面的要求。英國MIA1906第39條要求被保險人對船舶不適航的狀態(tài)是“明知的(privity of the assured)”。“明知(Privity)”有兩層含義,一是被保險人事實上知道并同意;二是被保險人“蓄意不查明(blind-eye Knowledge)”,即被保險人懷疑存在不適航的情形,但是因害怕自己的懷疑變?yōu)槭聦嵍室獠蝗ゴ_認查明。需注意的是,如果被保險人不去查明的原因是其態(tài)度的消極懶惰或存在疏忽過失,尚不構成“蓄意不查”,不滿足“被保險人明知”這一主觀要件的要求。
在“Manifest Shipping & Co Ltd v. Uni-Polaris Shipping Co Ltd (The Star Sea)”一案中,“The star sea”在由科林托港駛往澤布呂赫港口時,輪機室突發(fā)大火造成船舶推定全損。損失發(fā)生的原因包括三方面,一是緊急消防泵在船舶滿載時存在故障;二是輪機艙密封性不良;三是在火情通過其他方式無法控制的情況下,船長并未立即意識到需使用二氧化碳滅火裝置,亦未意識到需要將所有的二氧化碳釋放出來才能起到效果。保險人據(jù)此認為被保險人在明知船舶處于不適航的狀態(tài)而使之航行,其依據(jù)MIA1906第39條第5款的規(guī)定,無需承擔賠償責任。一審法院支持了保險人的主張,但上議院推翻了上述判決,認為這并不能證明被保險人對船長的任職能力以及船舶的缺陷存有任何懷疑。Lord Hobhouse同時指出,因疏忽而不知道船舶不適航并不等于知情,被保險人因疏忽而未能查實證際情況也不等同于“蓄意未查”。
與英國法不同,我國人保2009年船舶保險條款要求被保險人知道或應當知道,“應當知道”不僅包括英國法下“蓄意不查”的情況,還包括被保險人因疏忽大意的過失而未能發(fā)現(xiàn)船舶不適航的情形,在范圍上相比英國保險條款更加寬泛,對“主觀要件”的要求相對較低。
2、船舶航次保險不適航制度的比較
英國法下,船舶不適航在航次保險中被規(guī)定為一種默示保證義務,MIA1906第39條1款即明確規(guī)定:“航次保險單中含有默示保證,即船舶在開航時必須具有經(jīng)受承擔特定航程的適航能力”。而中國法將船舶不適航作為航次保險的除外責任,兩者的區(qū)別具體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1)被保險人的主觀標準不同。根據(jù)MIA1906,在航次保險中,被保險人對船舶開航時不適航是否明知在所不問,只要存在不適航的客觀事實,保險人即不負賠償責任。但人保船舶保險保條款中不適航除外責任適用的前提是被保險人對船舶不適航是明知的。
(2)英國法并不要求適航義務的違反與損失之間具有因果關系,即無需考慮違反適航義務是否實際促成了損失的發(fā)生,只要其與特定種類、特定時間或特定地點的損失有關,保險人對損失的發(fā)生即不負賠償責任,相比因果關系標準,保險人擁有更加廣泛的救濟權利。但是在中國法下,作為除外責任的船舶不適航與發(fā)生的損失必須具有因果關系,才能成為保險人免責的依據(jù)。
(3)違反適航義務的法律后果不同。根據(jù)英國2015年新保險法的規(guī)定,被保險人如違反適航保證,保險合同的效力“中止”(Suspension), 直到該違反行為被改正(或情況已發(fā)生變化而不需要改正),保險人對合同中止期間發(fā)生的事故或責任沒有保險賠償責任。在中國法下,不適航作為保險除外責任,在滿足上述各條件的情況下,其效果是免除保險人的賠償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