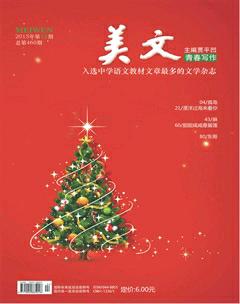漂洋過海來看你
潘云貴
2015年2月下旬,我坐上飛往臺灣的航班。
飛機沖上云霄的那一刻,整個人向后傾斜,我突然想起了自己在西南大學的生活,如何派去東吳大學交換學習的種種過程。好多事情都不斷往后翻滾,最后只剩下我爸和我媽的臉在眼前浮現。
在去長樂機場的路上,我爸坐在的士里囑咐我,到了之后別忘了給家里打電話,錢不夠就跟家里說。我媽沒說什么,臉上一直掛著不舍的神色。我靠在座位上,點點頭。
抵達桃園機場的時候已經是深夜。天空下著小雨,飛機還未停穩(wěn),雨珠在窗戶上打滾,一顆顆,拖著細細的尾巴,像蝌蚪。我感覺自己也是其中一顆,嘀嗒一聲,落到了這座從小在書上反復出現,實際上卻很陌生的島嶼。
臺北用冬日末梢的雨水歡迎我。我終于漂洋過海來看它了。
來之前,除了我爸,我媽更是在家囑咐多次,到了之后一定要給他們報聲平安。夫妻倆真像兩個日漸衰老的鬧鐘,雖然也在叮叮當當響著,我卻聽到了他們身體發(fā)出的帶著銹跡的聲音。我總是點頭說好。
到達臺北后,也想第一時間就打電話回去,卻發(fā)現忘了給手機辦理國際業(yè)務,卡已失效。兩天后,我辦了中華電信交換生專用的手機卡,打電話回去,我爸接的,著急問我為什么到現在才給家里消息。我跟他說了電話卡的事。之后,他就跟我去重慶念書時一樣,說了好多要照顧好自己的話。我在電話這頭聽著,也不打斷他,等他把憋了好幾天的話說完。我應了聲好,沒說再見,就掛斷了電話。
原以為自己會有一種解脫的心情,可心里一下子卻變得空落落的。深夜,窗外的雨仍舊下著,密密麻麻,像豆子撒在屋頂上,大珠小珠落玉盤。
臺北人習慣了冬天的雨水。積雨云籠罩著城市,遮蔽陽光,使他們的皮膚要比長期被太陽毒曬的高雄人白嫩很多,也使這座城市有了一絲英倫氣息。
臺灣島被北回歸線穿過,冬天不冷,經常在街頭看見衣著混搭的學生、青年們,上半身穿著衛(wèi)衣,下半身則是夏天的短褲,或者往里再穿一條緊身長褲。如果我在長樂家里這樣穿,肯定會被當成精神病患者,或被我媽嚴厲批評。
從小,我媽都只讓我和我哥留短發(fā),不準燙發(fā)、染發(fā)。穿衣打扮上則是怎么土怎么來。所以在我離開家到市里念高中的時候,才從前桌女生嘴里第一次聽到自己有點兒帥。
內地的話費是按分鐘算,島上的則是按秒計費,加上是國際長途,我就重拾自小養(yǎng)成的“勤儉節(jié)約”的好習慣,不再跟人褒電話粥。偶爾上網聊天,朋友們問的情況也都一樣,我一直都不是一個喜歡重復說話的人,后來加上有一些人讓我?guī)兔Υ徃鞣N護膚品和蘋果系列產品,我就連微信、QQ都不登了。
開始喜歡一個人在異鄉(xiāng)生活的時光,因為陌生,無人打攪,時間便驟然停下。
一個人起來跑步,去麥當勞吃50臺幣的早餐;上課或者到圖書館看書,翻的都是豎排繁體字,讀得很慢;快到黃昏時,坐捷運到淡水,買上一杯新鮮的“檸檬愛玉”和一串炭燒豆腐,趁著暮色吃起來,等天黑回去,再一次熟悉臺北天亮的過程。
在十八歲之前,因為發(fā)育期的緣故,淚腺特別發(fā)達,只要情緒一上來,眼淚無需用力,就跟鬧著玩兒似的嘩然下落。跟父母鬧脾氣,不小心和同學吵架,成績沒提高,到班主任那里喝茶,苦苦喜歡一個人未果,種種事端都在誘惑眼淚決堤。我也知道流淚的男生在別人看來很嗲氣。我迫切希望身體里的雨季快點結束。
后來有一天,突然發(fā)現自己不怎么流淚了,或者說是因為流不出來了,我才覺察到自己的十七歲已經過去。我開始向往理性、客觀,不想動情。
但自己所處的這座島卻仍舊像少年一樣感性,容易哭泣。
以前都不怎么看臺灣偶像劇,覺得情節(jié)都很雷同,演員們演技浮夸。每一兩集里總有人哭,年輕的女生哭起來還挺漂亮,但那些上了歲數卻仍舊努力表演出少女心的中年媽媽們,一哭起來特恐怖,妝化得讓人沒有再看下去的勇氣。在島上生活了一段時間后,才知道這里的人們真的都像電視劇里演的一樣,感性十足。
在學校聽當地同學做課程報告,常常聽得迷糊起來。他們講得有些零亂,更像是自我學習的心得與感悟,不如內地學生思路清晰,條理分明。我堅持聽了好幾場,有東吳大學的,也有臺灣大學的,大體上都如此。
有一次和一起來臺交換的L去中正紀念堂旁邊的音樂廳聽一場交響樂演出,在門口拿到宣傳手冊時,看到上面介紹這個樂團在內地曾演出過的地方,寫著“東北、廣東、深圳、鼓浪嶼、廈門”等地。
我跟L說:“鼓浪嶼不就在廈門嗎?”
L答道:“可能他們專指鼓浪嶼這座島。”
“可是,那廣東跟深圳又怎么解釋?”
L笑了。
跟L去逛書店的時候,他說了一件事,讓我覺得很逗。L在臺灣師大做交換生,附近有一家書店,平日若只有男老板或者他的兒子在,女生去買書,統統打五折,男生則是原價。若老板娘在,則男女平等,一律原價。我問:“是真的嗎?”L笑著點了一下頭:“我們班上女生買過,真的是五折。”
有一次看電視上的新聞,關于“反課綱運動”的學生夜里私闖教育部門大樓的事。主持人問一個教授嘉賓,為什么現在的臺灣學生會這樣?教授說:“都是因為教育出了問題,學生不讀哲學、邏輯學,思維感性。”
來到臺灣兩個月,跟家里只通過一次電話,就是剛來那會兒,之后沒有再聯系。自己一點都不想家,這讓我很開心。因為不想家,就覺得自己好像長大了。
身邊有很多人就是在經歷離開家、不想家、少回家這些過程后,徹底變成了大人,過著自己或理想或不如意的生活,走著走著,離父母越來越遠,與過去分道揚鑣,最后回不去了。
我想,自己如果能一直待在島上也挺好的。
沒來之前,看過很多臺灣電影。每周一上完課,就開始計劃旅行。去過侯孝賢《悲情城市》中的九份,到過楊德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發(fā)生地牯嶺街,也來過鈕承澤電影中的艋舺。有些地方較遠,便上網訂車票,然后再到學校里面的“全家”便利店取票。坐著臺鐵自強號或莒光號南下,去《海角七號》里的恒春半島、墾丁沙灘,到《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中的彰化精誠中學。最愛的,還是《練習曲》中的花蓮。
一個人騎單車前往七星潭,白晝漸熄,細小礫石組成的沙灘在夜色之下顯出淺白。眼前的海因為夜的到來變得更加廣闊,踏浪撿石的人在海灣靠近村落的一端,多是成雙成對的情侶,點點船影在遠處。不遠處的地方,則有人抱著吉他,唱著一首《島歌》,女孩聲音清澈,很多人都停下來,圍在她身邊。
我想起有次從臺大聽完課出來,去誠品書店,過地下通道時,遇到一個抱吉他的女生。她閉著眼睛,大聲唱著自己的歌,好像忘了全世界。臺灣的街頭藝人都需要有專門證件以及排隊取號才能出來表演。他們分散在島上不同的角落,卻都一樣純粹熱愛著藝術,并勇敢展示著自己。海風吹著,我又多坐了一會兒,心里空空的,什么也不愿去想,前塵往事都變得越來越遠,仿佛跟自己沒有關系。單車成了此刻我唯一的伴侶,在我背后默默看著我和這片深藍色的海。
在蘭嶼,一個人也在夜里騎著單車出去。海邊刮起風浪,沿海礁石被狠狠拍打著,發(fā)出恐怖的聲音。我沒害怕,因為頭上星星特別多,像成千上萬的燈盞,為我驅趕內心的鬼。
我把車騎到了達悟族民宿老板說的看星星的最佳地點。四周無一點燈光,我把車燈關掉的瞬間,黑暗覆蓋了我。頭頂的星星更亮了,一顆顆集結在天幕上,數也數不清。眼前的世界就跟電影《星空》中小美、小杰看到的那片星空一樣,又燦爛又寂寞。我望著望著,仿佛回到了久違的童年,一片在內地再也無法看到的天空。
突然想起自己的手機里還存著五月天的那首《星空》,就找出來播放。
摸不到的顏色是否叫彩虹/看不到的擁抱是否叫做微風/一個人想著一個人/是否就叫寂寞/命運偷走如果只留下結果/時間偷走初衷只留下了苦衷/你來過/然后你走后/只留下星空/那一年我們望著星空/有那么多的燦爛的夢/以為快樂會永久/像不變星空陪著我……
歌聲好像順著浪潮一會兒遠去,到海的那頭,一會兒又折回,向我心上沖過來。天上的星星那么多,那么亮。我舍不得夜晚過去,舍不得離開。
在臺北學校時,夜晚去過西門町紅樓那里吃飯,有幾次是跟當地的兩個博士學長去吃的。我們點了三份鯖魚定食,小菜有花生、豆干、辣白菜。臺灣青年都習慣AA制,一頓飯下來,人均花費400塊臺幣,也就是80塊人民幣。我們 聊旅行、明星、學校的論文、符號學、性別意識、兩岸的學費等話題,談很久, 每個人臉上都很放松,吃倒是變成了次要的事情。后來,我跟L也去了紅樓,想找之前去的那家店吃飯。
L卻拖住我,說:“我們換個地方吧?”
我問:“為什么?”
L說:“你沒看見這里氣氛很不一樣嗎?”
我愣住了。
L告訴我,這一帶都是同志經常來的地方,飯店酒吧里都是同志,店與店之間還有區(qū)別:桌子上放燈的是一般同志吃飯的地方,門口放著大熊公仔的,則是熊圈的。
我說:“不會吧,上次我們學校的兩個博士學長還帶我來這里呢!”
隨后,我看看四周,在門口招呼客人的服務生都是男的,而坐下來用餐的也都是男的。他們的打扮都很時尚,我的鼻子里充斥著一股香水味。
我很奇怪,L為什么會懂這么多。
在寶島,也有難以習慣的時候,雖然感到難受,但自己沒掉眼淚。
當地居民都很友善,但千萬不要跟他們聊兩岸關系,特別是對那些年輕人。印象很深的一次,是在學校楓雅樓一層跟一個叫“龍三”的學生宿管聊自己對臺灣的印象。起初,我們談話都很和氣,但一提及兩岸關系,“龍三”的臉色就變了,說話不像之前那么客氣。他說,如果蔣介石沒來,臺灣人會過得更好。之后,他就開始聊起國民黨的罪狀,特別提到了臺灣“二·二八”事件。而在提到日本對臺灣的殖民時,他一直用“日治”兩個字,而不是“日據殖民”。當我知道“龍三”的政治立場后,便沒有再跟他聊下去。
我們班里也有一個男生,是學校彩虹社的負責人,平日知道他說話很尖酸,但我沒想到他那么激進。有一次,給我們上“文學與性別意識”的連老師在課上問我有關大陸論文期刊發(fā)表的問題,并勸當地學生要擴大視野,寫好論文,給大陸投稿。那個男生突然大聲地對老師說:“他們中國學生天天在寫論文,但都寫得超爛!”我突然感到有一股抑制不住的難受勁兒向我撲來,于是激動地對他說:“不要用‘他們中國‘你們中國這樣的詞,好嗎?我聽著很不舒服!” 他沒理睬我,繼續(xù)在全班同學面前數落起內地民眾的素質,列舉了很多。我聽得比較清楚的是“中國人來故宮博物院,在那兒吵吵嚷嚷,有一回我聽到他們說:‘這么多寶貝都是他們的,遲早要收回去……”連老師看到我難過的表情,便打斷了那個男生,讓他轉回正題,不要在課堂上聊無關的話題。
那節(jié)課后,我沒有再跟那個男生說過一句話。
深夜,一個人用手機聽廣播,說話超嗲的女主播在一番心靈絮語后,放出一首歌:來自孟庭葦新版的《冬季到臺北來看雨》。歌的開頭是一聲雷響,雨水淅淅瀝瀝地落下,輕柔的旋律開始在空蕩蕩的夜里響起:
冬季到臺北來看雨/別在異鄉(xiāng)哭泣/冬季到臺北來看雨/夢是唯一行李/輕輕回來不吵醒往事/就當我從來不曾遠離/如果相逢把話藏心底/沒有人比我更懂你/天還是天喔雨還是雨/我的傘下不再有你/我還是我喔你還是你/只是多了一個冬季……
想起自己漂洋過海來寶島的那天,飛機從長樂飛往桃園,途中云層很厚,我在云中穿行。氣流有時不穩(wěn)定,整個機艙都晃動起來,我想起之前電視上報道的臺機空難事件,我媽跟我說“一定要照顧好自己”時的場景反復在腦中浮現。那時,我正一個人挎著單肩背包,興沖沖地向海關那里快步走去。身后是我爸我媽,像兩匹年老的駱駝那樣站著,目送我離開。
天還是天喔雨還是雨/這城市我不再熟悉/我還是我喔你還是你/只是多了一個冬季……
十八歲之后,我們都喜歡把眼淚流進心里,在每一個想念潮涌的夜晚,嘩嘩作響,熱浪騰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