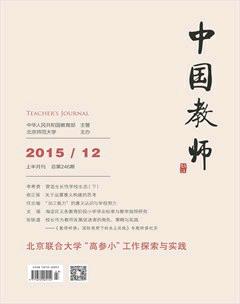“加工能力”的意義認識與學校努力
任志瑜
一提“加工”這個詞,人們或多或少地會和工業工廠相聯系,教育領域似乎在有意回避。其實,深入思考,發現“加工能力”哲學意義上的普適道理,對推進教育均衡、公平這一改革背景下的中小學校如何真正辦成“人民滿意的學校”,很有啟示意義。教育者要本真地關注學校或教師的“加工能力”。“根雕”與“玉佩”,從原材料到作品的“創造加工”,皆令人嘆服,這一道理和意義也適用于教育。這大概是北京教育結構布局新調整時,中小學校學區制集團化(北京教育新地圖)過程對全市中小學校長以“北京市熱點學校‘加工能力到底怎樣”進行主題追問的意義所在吧。
教育領域談“加工能力”,有其特殊含義。第一,直觀性。借用人們熟悉和容易理解的工業、工藝技術水平指標,對學校和教師的教育教學能力水平進行直觀感覺評價。第二,科學性。現在,社會、家長及行政部門,總是用統一標準衡量,或站在終點裁判,我們都知道這并不科學。“加工能力”給人的第一感覺,是針對“原材料”,我們會有怎樣的“產品”的能力。這符合教育的客觀規律,即針對學生個體一個歷史時間段,觀察他們的變化和發展,自己和自己比。也就是說,對學生的教育成長評價,應多一些個體縱向看發展,少一些群體橫向比高低。第三,時代性。在追求教育均衡和公平的當前,提“加工能力”符合大眾認知時代觀,會讓薄弱學校和教師看到希望,有盼頭。上級管理部門和學校領導“以起點看終點”的思維模式評價班級和學科成績,會使“教育均衡、公平”有了實在的“著陸地”。
評價一所學校的“加工能力”,要看孩子在這所學校數年后會有怎樣的變化?這個變化不僅隨著時間身體會自然長高,更主要的是,孩子身上會體現出學校和教師的“加工痕跡”:更懂禮貌,更知感恩,更有獨立見解,習慣更好,學習更優……即在學校的幾年,德智體美實現怎樣的“自我超越”。我們總在經歷這樣的感受:不同學校的學生,在同一場合總會給人不同的感覺,甚至舉手投足、開口說話,也能清晰地辨認他們來自哪所學校。學生身上帶著就讀學校的“logo”或“胎記”,這告誡學校和教師:因我們的“加工”,為學生“烙印”最優秀的“學校文化”!例如,在北京理工大學附屬中學的“人文奠基、理工見長”這一辦學特色下培養出來的學生,應該展現出不一樣的內在氣質與外在形象:男生英俊,女生淑雅。結合學校校訓,以“大氣、沉毅、擔當”作為“英俊男生”的刻畫,以“內秀、和善、文雅”展現“女生淑雅”的形象。
“加工能力”樸實而普通的哲學道理,告訴每一位教育工作者要為提升學校和自己的“教育加工能力”而努力。首先,有“科學加工”的指導思想—先進的教育理念。從校長到教師,要堅守:學生“在此一段受用一生”的“學校加工”理念。中小學階段不僅是學生良好習慣形成的決定性階段,也是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養成的關鍵性階段,更是學生學業水平和特長發展的奠基階段,是學生結交成長伙伴的積淀階段。即“中學階段是學生素質修養的快速提升期,是人生蛻變的關鍵期,是親子關系轉型的微妙期,是人脈積累的基礎期”。所以,學校領導應本著“為學生一生著想”的負責與擔當,建設學校與管理學校。
其次,遵循教育規律—教育加工者的職業操守。教育“加工能力”是針對活生生的人,是對不同的個體及其不同年齡階段而開展教育的。尊重主體,遵循規律,特別重要。有的家長讓孩子在三四歲就開始算數,部分孩子雖能很快說出答案,但并非他們真正掌握了數學知識。一般來說,3歲前的幼兒對數已有籠統的感知,能區分明顯的多和少;3~5歲的孩子,在點數實物后能說出總數,能按成人說出的數取出相應數量的物體;5歲以后的孩子,才能認識到數不因實物的變化而改變,形成數的“抽象概念”。心理學實驗證明,只有到5歲之后,孩子才能脫離實物的支持,進行小數目的加減運算,學會100以內的數數。一旦孩子發展到這個階段,他們對數的理解與運算就會變得簡單,能達到真正意義上的理解。一些家長通過死記硬背的方式,讓孩子記字、識數,認知過早符號化,會影響孩子想象力的發展和學習興趣的激發。
美國社會學教授唐納德·埃爾南德斯帶領團隊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無法進行流利閱讀的小學三年級學生到高中輟學者,是當年能夠流利閱讀學生的4倍。這是因為小學三年級是學生從“學習如何閱讀”過渡到“通過閱讀去學習”的一個關鍵階段,即“小學三年級的閱讀水平成為學生學習狀況的一個里程碑”。在后續的學習中,“通過閱讀去學習”的模式占主導地位。閱讀能力差的學生,在小學四年級時開始進入“學習低迷期”。當流利閱讀者如饑似渴地從書本、網絡等多種媒介信息中吸收新知時,閱讀能力差的學生因閱讀障礙而感到學習困難,逐步掉隊。于是,惡性循環出現。
再次,為學生全面發展的學校“整體加工”功能的發揮—學校加工能力的特殊性。對學生的培養,絕不可能像工廠對零件的加工那樣,這道程序完成之后再進入下道工序。也就是說,學生不可能先練習長手臂,再訓練長腿。人的身高和各個器官一定是同步生長,對學生的能力培養,一定是全面展開,而不是片面的應試教育,只是不同年齡(年級)階段有能力水平的層級之分。這就是學校“加工能力”的一大特點—同步集體創作。美國洛杉磯愛樂樂團指揮卡洛·瑪利亞·朱利尼說:“創作偉大音樂作品的奧妙在于要求一同演奏的人們有真正的友誼,每個成員都從內心深處時刻提醒自己‘我在與他(她)共事”,揭示出學校“加工能力”的特殊意義。學校不等同于工廠的特殊之處在于:學校絕不可以出次品,甚至廢品。根本方法是根據學生成長過程中的情況及時采取措施,絕不允許教育有偏離方向甚至行走在錯誤道路上的機會。
最后,給學生裝上一生成長的“發動機”—學生因此而善學。學生從就讀學校、班主任和科任教師那里帶走的絕不是當時有限的死知識,而是終身受用的善于學習的習慣、方法與思維方式等。楊瀾“自我求進”的例子,能夠說明一些道理:她在做主持人時,請求導演,“我是不是可以自己寫臺詞?”寫了臺詞取得好的主持效果后,再問導演,“我可不可以自己做一次編輯?”做完編輯獲得極佳評價后,又問主任,“我可不可以做一次制片人?”做了制片人,還想,“我能不能同時負責幾個節目?”負責幾個節目后,“更想能不能辦個頻道?”……就這樣,楊瀾在人生道路上不斷地自我奮進,從“陽光衛視”追求到中國申奧形象大使。
學校“加工能力”是最直白表達老百姓孩子優秀成長的民生話語,是最直接考察學校辦學水平的客觀指標,更是家長、社會評價教師教育教學能力水平的現實標尺。在多元發展和多主體評價中,學校加工能力確實需要“出口看入口,成長看綜合”的思想,對學生“多縱向看自我超越,多橫向看特長優勢”。在北京教育“學前玩、小學慢、初中寬、高中活”的新定位下,學校“加工能力”一定是體現在“學校為每一個學生裝上終身受用‘發動機的能力”。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學附屬中學校長,特級教師)
(責任編輯:孫建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