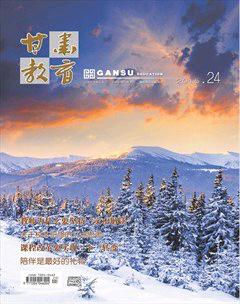教師為什么要堅持“文本解讀”
霍軍
文本解讀,在語文學科的意義上,是指教師個人對課文的理解。在課文都是“文本”的意義上,各學科其實都存在自己的“文本解讀”。
文本解讀概念的提出本身意味著,授課不是簡單傳遞,不是照本宣科、灌輸或者轉述。授課,如果除卻用媒體資源展示的向所有人開放的“資源”供給,那就應該是在特定場域下,由特定教師面對特定學生而展開的一種知識、思維、能力、情感甚至美感培育過程。在此過程中,教師面對的始終是具體而個性迥異的學生個體。簡單灌輸在功利化的機械訓練中也許可獲一時提高分數之效,但絕不會形成可以喚醒學生生命和學習潛能的力量。一個只會復述教材的教師,也許能夠成為一個合格的“經師”——口述圣賢經典讓學生埋頭筆錄的人,但絕不會成為一個能夠上出有質量的好課的“人師”——將所有教授內容轉化為自己的精神營養然后跟學生分享的人。因此,文本解讀就不能僅僅是在教學參考資料上尋找現成答案的照搬活動,而是教師個人首先面對文本,用自己的全部學科能力去靜心“閱讀”、通曉教材學理、把握教材邏輯、領會教材精神實質、發現教材意義的歷程。把教材變成“我”必須閱讀、也讀有心得的“作品”,把自己通曉的過程變成教學設計的資源,把自己遇到的問題困惑當成接近學生初學狀態的鑰匙。
教師的文本解讀,使教材的全部潛能被激活。蘊含在教材中的人類智慧重新閃現它們被發現、創造的那一刻曾經激起的生命活力。這些知識不僅是一些章節條款、公式定理、數據要點和修辭技巧,也還是人的生活歷程的見證。它們內在的邏輯得以揭示,這種邏輯體現著人的偉大和人性的光輝。這些知識被再次發現,展現知識的內在力量,煥發生命的美學光彩。
教師的文本解讀,讓教師與教材文本相遇、融合,再次成為一個學習者。海德格爾因此說,教師之所以能夠教,是因為他自己首先可教。一個面對每一個文本都展開最深入的個人解讀的教師,必定是一個積極主動的學習者。這種學習體驗會變成對學生的真正理解——從我的學習境遇理解學生的學習境遇,我的求知歷程和體驗方式也一定會在同樣的求知者身上發生。教師不應對學生的學習困境著急上火、譏諷嘲弄,而是足夠包容、耐心等待、循循善誘的理由是,教師本人深知文本解讀過程的個中奧秘和酸甜苦辣。文本解讀不僅讓他獲得新知,重溫已知,而且讓他更深切體驗了學習的心路歷程。因為通曉,教師找到了文本與閱讀者、理解者的對接口。因為自己嘗過這個梨子并細加品味,所以能夠帶著飽滿的感情、充分的底氣,用被激發出來的鮮活準確的語言,講出這個梨子的真正甘甜。這時的教學語言不再是傳聲筒里發出的空洞聲音,不是別人反復述說過的現成便宜、不費力氣的套話,而是自己的實話,是一個沉浸在活生生知識流脈里酣泳的健兒的現場說法,是飽含情感準確生動的藝術化教學語言,這樣的語言才能激活學生。很多講授的低效率和失敗,不是來自教師能力不足,而是來自把一切知識都當成轉述貨物的冷漠態度。而一個真正熱愛教材并從中受到智慧引領、精神鼓勵、靈感啟迪和生活熱情的教師,他自會錘煉出自己的教學語言。
因此,教師這個職業,也許可以有一種新的定義——用自己的眼光重新發現教材的人。文本解讀,就是這樣的發現。而不斷寫下批注、感想、聯想,特別是不斷寫下自己對文本的整個解讀內涵,必定促進我們成為有激情、喚醒力量和教學藝術的老師。
因此,文本解讀,要求我們不簡單依賴教參,首先能夠“素讀”——不借助任何評價和解說資料,自己去欣賞教材文本這份“作品”。要求我們用自己的理解力去靜心克服難點,貫通整體,理出脈絡,要求我們精讀細研,揣摩品味,涵詠玩味,要求我們手執筆墨,圈點批注,廣泛聯想,比較印證,要求我們尋根索源,旁征博引,博學審問。特別是,文本解讀應該是我們的作品——寫下來,寫出我們自己的解讀文本,并因為這樣的寫作而融入那些教材作品,讓教材融入我們的見識情感,讓教材首先成為我們自己的精神營養,從而讓自己變成一個能夠引領學生的明師。
編輯:謝穎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