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因素、制度變遷與現代商業精神
歷史因素、制度變遷與現代商業精神
邵傳林1,張存剛2
(1.蘭州商學院 金融學院,蘭州 730020; 2.蘭州商學院 經濟學院,蘭州 730020)
摘要:文章基于中國省級層面的面板數據資料定量測度了歷史因素對現代商業精神的影響。實證研究表明:歷史上曾擁有頻繁商人活動的地區,越有利于現代商業精神的涵育;歷史因素可解釋不可觀測地區固定效應的32.8%~40%;各種穩健性檢驗均表明,與市場化制度變遷進程較緩慢的地區相比,歷史因素在市場化制度變遷進程較快的地區對現代商業精神的促進作用更強。為了減弱內生性問題對估計結果的影響,本文基于工具變量法進行了實證檢驗,從而使本文結論具有較強的說服力。
關鍵詞:歷史因素;體制改革;市場化制度變遷;現代商業精神
收稿日期:2015-01-07
作者簡介:邵傳林,男,蘭州商學院金融學院副教授,博士,主要從事制度經濟學研究;張存剛,男,蘭州商學院經濟學院教授,博士,主要從事制度經濟學研究。
中圖分類號:F069文獻標志碼:A
Historical Factors, Institutional Changes and Modern Commercial Spirit
SHAO Chuan-lin1, ZHANG Cun-gang2
(1.SchoolofFinance,LanzhouCommercialCollege,Lanzhou730020,China;
2.SchoolofEconomics,LanzhouCommercialCollege,Lanzhou730020,China)
Abstract:The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historical factors on modern commercial spiri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provincial level in China. Empirical research shows that, in areas with richer initial endowment of commercial activities, it is more conducive to cultivate and propagate the modern commercial spirit, and the unobserved fixed effects can be explained about 32.8%—40% by the initial endowment of commercial activities. Various robustness tes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regions with slower market-oriented institutional change process, the initial endowment of commercial activities can promote modern commercial spirit stronger in regions with faster market-oriented institutional change process. In order to weaken the endogenous problem that may affect the estimation results, this paper uses instrumental variables of the initial endowment of commercial activities, but estimation results once again confirms the above conclusion.
Key words: historical factors; reform; market-oriented institutional change; modern commercial spirit
一、引言
根據余英時(2004)與杜維明(2013)的前期研究,漢語中的“現代商業精神”類似于英語中的“The spirit of capitalism”,正是這種類似于資本主義精神的東西曾經為西方世界的興起提供了強大的原初動力。中國在明清時期曾產生過“資本主義經濟”,但卻沒能形成現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更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商業精神[1-2]。有學者指出,自宋至明清時期中國商人精神之所以沒能轉向現代商業精神,主要原因在于封建專制制度的束縛[1]。厲以寧(2010)[3]也指出,中國自宋以降的彈性封建體制是中國商人精神無法轉向現代商業精神的重要原因。Weber(1951)[4]在《中國宗教》中進一步指出,中國傳統文化(如儒家文化)不利于資本主義精神的產生,甚至還可能是資本主義沒有在中國崛起的重要原因。盡管如此,由于中國各地區在地理環境、歷史、人文等方面差異較大,經過幾個世紀的發展和實踐,各地區還是逐漸孕育了不同的歷史因素。正如韋森(2004)教授所言,華北地區的農耕文化不利于現代商業精神的培育和發展,東南沿海地區的“吳越文化”和華南地區的“嶺南文化”卻有利于現代商業精神的培育和發展[5]。毋庸諱言,本文無意于厘清現代商業精神究竟緣何沒能在中國傳統社會生成,而是想指出,自1978年經濟體制改革伊始,中國各地區經過30多年的市場經濟實踐與探索終于涵育出了不同發展程度的現代商業精神。但令人困惑的是,即使剔除地理因素、自然條件、開放程度、市場規模、經濟發展水平、城市化等因素對現代商業精神的影響,還是難以理解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地區之間現代商業精神成長程度的差異如此之大?譬如,東南沿海的浙東地區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就擁有豐富的企業家資源和創業經驗,但地處西北內陸的甘肅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就非常缺乏企業家資源和創業經驗,兩地區早期歷史因素的差異為改革開放后現代商業精神的成長提供了不同的初始稟賦條件。
不同于既有的研究多采取整體化視角分析現代商業精神的起源及其當代意義,本文重點從初始稟賦條件的視角探討歷史因素對現代商業精神發展和培育的影響。那么,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是歷史因素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釋地區之間現代商業精神的差異性,本文擬基于中國省級層面的面板數據資料對此進行定量測度。具體來說,本文的工作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本文從學理上分析歷史因素影響現代商業精神的內在機制,闡釋市場化制度變遷在歷史因素影響現代商業精神過程中的調節作用,從而為更進一步的研究奠定理論基礎。其二,本文不僅在理論上探討歷史因素對現代商業精神的影響,還基于中國省級層面的非平衡面板數據資料定量測度了歷史因素對現代商業精神的影響程度,定量測度歷史因素與市場化制度變遷的交互效應對現代商業精神的影響。其三,本文使用1949年地區商業貸款占比和地區識字率變量作為歷史因素的工具變量,并基于兩階段最小二乘法回歸控制內生性問題;鑒于市場化制度變遷與現代商業精神在理論上具有逆向因果關系,本文還使用建國初期地區自然災害嚴重程度作為市場化制度變遷進程的工具變量,并基于預測的外生性制度變遷變量進行了穩健性測試。
二、理論闡釋與假說提出
(一)歷史因素的差異性
既有的研究表明,經濟體制改革之前中國各地區經過幾個世紀的實踐與發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商業亞文化[5]。比如,長江三角洲地區早在南宋以后形成了以“經世致用、務實求真、勇于創新”為特征的“吳越文化”,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在清朝中葉以后逐漸形成了以“務實世俗、重商遠儒、兼容求新”為核心的“嶺南文化”。顯然,上述地方亞文化在思想內涵上比較接近韋伯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精神”,或者說上述地方亞文化與現代市場經濟中的“資本主義精神”或現代商業精神具有一致性,它們不僅不排除商業活動,反而具有“親”商業的價值觀念,倡導商品的流通和個人的創業精神、冒險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還具有無止境追求利潤和個人英雄主義精神的色彩。上述地方亞文化與山東、河北、河南等地區儒家“農耕文化”在對待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上具有迥然的價值觀念,儒家中原文化“重農抑商”,在本質上是一種“農耕文化”,而吳越文化和嶺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以“重商輕農”為核心的現代商業精神。譬如,作為中國市場經濟典范的溫州,早在宋末明初時期就是中國重要的對外貿易口岸,此后不論在哪個朝代該地區的商業活動均很發達,經過幾百年的商業實踐該地區逐漸形成了“重商輕農”的商業文化精神。溫州人特別強調學以致用,倡導對社會實際問題的研究,注重實踐精神,反對虛言空行,尤為反對儒家學說中的只重義而不講利的觀念,主張“以利和義”與“義利并舉”,而不是“以義抑利”[6]。上述分析表明,中國各地區并不具有統一的歷史文化因素,東南沿海地區在歷史上曾經產生過類似于“資本主義精神”的東西,但在“農耕文化”繁榮的地區卻不曾產生過類似于“資本主義精神”的東西。毋庸諱言,經過幾個世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實踐,中國各地區早在建國之前就形成了迥異的因素,這為本文探討歷史因素的橫向差異影響現代商業精神的傳播和培育提供了現實基礎。
(二)歷史因素如何涵育了現代商業精神?
問題的關鍵是,改革開放之后歷史因素開始在現代商業精神的培育和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那么,為什么在歷史上曾經擁有頻繁商人活動的地區更能夠促進現代商業精神的培育與成長?本文認為,首先,歷史因素是改革開放后商人活動和企業商業活動的豐富知識源泉。有學者指出,在1978年改革開放伊始,中國社會并不具有關于企業如何運作的知識和大范圍遠程交易的契約知識[7]。無疑,并非所有地區的經濟行為主體都具有如何進行創業、生產、經營管理、產品銷售等方面的知識,但那些在歷史上原本就擁有豐富、頻繁的商業活動的地區似乎并不缺乏如何開辦商業企業的知識。其實,這些地區早就擁有關于市場制度的完整知識,只是這些知識在計劃經濟時期被“束之高閣”了。一旦經濟體制發生根本性變革,便為這些知識的運用和傳播提供了新的機會。事實上,民營及個體經濟之所以能夠在溫州、泉州等東南沿海地區率先興起,這與當地的重商主義文化傳統密不可分,這種商業文化傳統為當地群眾快速融入市場經濟提供了一種共同知識或共同信息,而這種知識或信息是從事商品生產和市場運作的先決條件。因此,當全國其他地區還在對市場存疑或者沉浸在社會主義國家到底要不要發展市場經濟的爭論中時,這些地區的企業家們早已將其商品打入了全國市場,并在市場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此外,歷史因素在商人活動和企業商業活動中發揮著“社會資本”的作用。歷史上傳承下來的歷史因素在某種程度上還具有社會資本的功能,而社會資本是一種重要的經濟資源,它與土地、勞動力、技術、物質資本等生產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相類似。進言之,根據經濟社會學的理論可知,社會資本對經濟發展而言,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它為經濟行為主體之間的合作提供社會信任,這不僅有助于降低經濟主體之間的交易費用,還有助于將信任范圍從熟人圈擴展到陌生人世界。不僅如此,還有證據表明,現代商業精神在好的社會信用環境下能夠得到更好地傳播和培育[5]。事實上,歷史因素折射出一種合作意識或合作信念,使陌生人之間的合作成為可能,而合作會使商人間的商業行為變得成本更低,于是,現代資本主義精神能夠得到更好的發揮,這進而又促進了合作信念的普遍化,它們互為因果、相互促進。總之,作為社會資本的歷史商業文化因素能夠為現代商業精神的培育和傳播提供途徑。另外,歷史因素還會通過家庭組織進行代際傳承,從而具有路徑依賴特征;盡管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快速實施了計劃經濟體制,絕大部分家庭被納入到該體制內,但歷史商業文化因素仍會由家庭進行“潛移默化”的傳承。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說:
假說1:在歷史上曾擁有頻繁商人活動的地區,就越有利于現代商業精神的涵育。
(三)市場化制度變遷的調節作用:收斂抑或發散?
從1978年末開始,中國經濟從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這被經濟學者稱為市場化制度變遷過程。在此過程中,外部制度環境在不斷變遷,其中,最核心的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在不斷增強。現代商業精神隨著市場化改革進程的不斷推進得以廣泛傳播、推廣,尤其是現代商業精神的跨地區傳播必然會給傳統農業區帶來新的外部沖擊,于是,傳統的“農耕文化”逐漸喪失現實基礎。更為關鍵的是,現代商業精神的跨地區傳播使“如何做生意”這類商業知識的傳播成本大幅下降,變革原來不利于市場經濟的傳統農耕文化的成本也變得越來越低。與此同時,由于其他地區的商業行為與物質收益差距變得越來越明顯,那些在文化上“落后”的地區便產生了模仿或學習的動力。這表明,外來商業文化在向落后地區傳播的過程中所遭受的阻力在下降。在上述背景下,歷史因素之于現代商業精神傳播和培育的重要性也在不斷下降或已經變得不再如此重要,或者說歷史因素對現代商業精神的影響會隨著中國市場化制度變遷的不斷深入而產生收斂效應。
另一方面,中國市場化制度變遷進程在地區之間并不具有同步性,這可能會使歷史因素對現代商業精神的影響具有不同的效果。有些地區市場化進程較為緩慢,政府對市場的不當干預依然較嚴重,生產要素的扭曲性配置也比較嚴重,而且國有經濟占比偏高,商人活動的外部營商環境也較差,如西部內陸地區就具有上述特征;在這些地區,即使歷史因素更有利于現代商業精神的傳播與發展,但由于外部制度環境較惡劣,或者說外部制度環境的不利影響已大大抵消歷史因素在傳播與培育現代商業精神上的優勢。反之,在市場化制度變遷程度較高的地區,政府對市場的不當干預已被限制,生產要素配置更具市場化特征,國有經濟的占比較低,商人活動的營商環境較好,如東南沿海地區;若這些地區擁有較為豐富的歷史因素,再加上這些地區還擁有較好的外部制度環境,于是,歷史因素對現代商業精神的影響會隨著市場化制度變遷的不斷深入而產生發散效應(即拉大效應)。另外,就中國的實際情況而言,歷史因素較為豐富的地區往往也是政府質量較高的地區,這些地區的制度環境更有利于現代商業精神的傳播,地方政府也比較開明、對市場的干預和控制均較弱;并且,歷史因素也會影響政府對待商業活動的態度,這些地區的地方政府會努力創建開放型、包容型的政府服務,進而會對現代商業精神的培育和發展產生更強的促進作用。基于上述分析,中國市場化制度變遷的發散效應似乎大于其收斂效應,故本文提出如下假說:
假說2:與市場化制度變遷進程較緩慢的地區相比,歷史因素在市場化制度變遷進程較快的地區對現代商業精神的促進作用更強。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模型
為檢驗假說1,本文構建如下計量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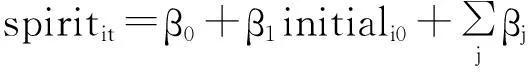
(1)
上式中,因變量spiritit表示第i地區第t期的現代商業精神。但令人遺憾的是,時至今日經濟學界并未能找到一個現成可用的衡量指標來刻畫現代商業精神,本文不得不使用其他指標間接性地進行衡量。鑒于本文中的現代商業精神主要指企業家從事商業活動的意愿、規范和價值觀念,主要以企業家的創業精神和創新精神為核心,故在理論上本文可使用地區私人企業家和民營企業家創業的人均數量作為現代商業精神的替代性衡量指標。顯然,使用該指標衡量現代商業精神在理論上與本文對現代商業精神的定義相接近,即在現代商業精神越流行的地區,企業家創業的積極性往往也較高,從而保證本指標的選取具有一定的理論基礎。核心解釋變量initiali0表示第i地區的歷史因素變量。基于上述分析可知,采用1949年中國各地區民營企業家創業的人均數量衡量歷史因素,則就理論層面而言非常符合本文的研究思路,但限于本文無法搜集到這方面的官方歷史數據,并且所能搜集到的最早有關地區民營企業家創業的人均數量的資料也只有1992年的數據。事實上,中國官方統計機構從1992年才開始統計民營企業和個體企業戶數、從業人數等數據資料,故本文也只能使用1992年各地區人均創業戶數作為歷史因素的替代性衡量指標。另外,為了避免采用1992年各地區人均創業戶數作為歷史因素會產生衡量偏誤問題,在本文穩健性檢驗部分,還將采用民國時期各地區著名企業家的人數(ming)作為歷史因素的替代性衡量指標,因為只有在傳統商業精神比較發達的地區,才有可能產生更多的著名企業家,因此地區著名企業家人數越多則表示該地區歷史商業文化資源越豐富。
另外,本文借鑒李后建(2013)[8]、江春和張秀麗(2010)[9]、邵傳林(2014)[10]等學者的前期研究,選取實際人均產出(GDP)、市場分割(MFI)、總人口(pop_n)、基礎設施(lnroad)、產業結構(struc)、城市化水平(urban)、金融發展(f_p)、地區開放程度(trade)、教育水平(edu)等變量構成控制變量集Xit。最后,由于現代商業精神的傳播與發展還受宏觀經濟走勢、國家政策等隨時間發生變化的因素的影響,在估計模型(1)時,本文還考慮了時間效應ut。εit為殘差項。相關變量的詳細界定見表1。
為檢驗假說2,構建如下計量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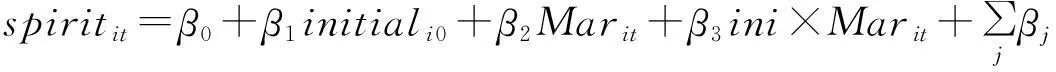
(2)
(2)式在(1)式的基礎上加入了制度變遷變量(Marit)以及制度變遷與歷史因素的交乘項ini×Marit,其他變量的定義同式(1)。在(2)式中,若β3>0且顯著,則表示制度變遷與歷史因素的交互作用對現代商業精神具有正影響,即假說2得到驗證。

表1 變量定義及統計特征
(二)樣本與數據
本文基于中國1992—2011年省級層面的非平衡面板數據進行實證檢驗。其中,衡量地區制度變遷程度的指標(Mar)來源于樊綱等(2011)[11]編著的《中國市場化指數(2011)》一書,時間范圍均為1997—2009年。應當強調的是,由于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制度變遷指標(Mar)來自《中國市場化指數(2011)》,但該書最新版數據僅更新到2009年,最早的數據起始于1997年,到目前尚未發現有更新的數據,限于此,本文無法將數據更新到2013年,但這已經是本文可以獲取的最長時間段了。本文根據維基百科“中華民國企業家”條目中列示的名人企業家統計資料,手工查詢名人企業家的祖籍,然后分省(市)統計各地區民國時期著名企業家的總人數,即民國時期各地區著名企業家的人數(ming)。另外,其他變量的原始數據取自《新中國五十五年統計資料匯編》《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匯編》、各年《中國統計年鑒》、各省統計年鑒。自然災害嚴重程度(nature_d)變量用1952年自然災害救濟費支出除以民政事業費支出來衡量,自然災害救濟費支出和民政事業費支出來自于《全國民政事業費統計資料匯編(1950—1977)》;需要特別強調的是,西藏自然災害嚴重程度使用1954年的數據,寧夏自然災害嚴重程度使用1958年的數據,新疆自然災害嚴重程度使用1953年的數據,上海自然災害嚴重程度使用1956年的數據,其他各省均為1952的數據,但本文無法獲得海南省自然災害嚴重程度的數據資料。另外,金融發展(f_p)的計算參考了張軍和金煜(2005)[12]的計算思路。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對假說1的初步檢驗
表2列出了基于方程(1)進行回歸的估計結果。列(1)僅控制了年度固定效應,發現調整的決定系數(R2_adj)為0.2107,這表明,地區現代商業精神隨著市場化改革進程的推進有一種自發生長的趨勢。列(2)又進一步控制了不可觀測的個體固定效應*不可觀測的個體固定效應通過加入30個省份虛擬變量來實現。,結果發現調整的決定系數(R2_adj)為0.618,這表明,不可觀測的個體固定效應已經解釋了因變量變化的40.73%。列(3)在列(1)的基礎上控制了歷史因素變量(initial),結果發現,歷史因素變量的估計系數為0.9682,且在1%的水平上高度顯著,這表明,歷史因素與現代商業精神正相關;在列(3)中調整的決定系數為0.3736,這表明,不可觀測的個體固定效應已經解釋了因變量變化的16.29%;通過計算還發現,歷史因素的解釋能力在不可觀測的個體固定效應中的占比為40%(即0.1629/0.4073),這表明,不可觀測的個體固定效應中有很大的一部分可以由歷史因素解釋;進言之,地區現代商業精神確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歷史因素進行解釋,初步表明假說1是成立的。列(4)、列(5)和列(6)分別在前3列的基礎上進一步控制了實際人均產出(GDP)、市場分割(MFI)、總人口(pop_n)、基礎設施(lnroad)、產業結構(struc)、城市化水平(urban)、金融發展(f_p)、地區開放程度(trade)、教育水平(edu)等變量,結果發現,歷史因素的解釋能力在不可觀測的個體固定效應中的占比為32.8%,也即(0.6162-0.5425)/(0.7669-0.5425),歷史因素變量的估計系數為0.7347,且在1%的水平上高度顯著,再次表明假說1是成立的*本文還使用現代商業精神的其他衡量指標(如spirit1和spirit2)進行穩健性測試,結果得出了類似的研究結論;當本文使用歷史因素的其他衡量指標(如initial1和initial2)進行穩健性測試時,也得出了類似的研究結論;并且,當使用1993年或1994年各地區人均創業戶數作為歷史因素的替代性衡量指標時,全文的結論亦成立。限于篇幅,并未呈現這些估計結果。。
(二)對假說2的初步檢驗
表3列出了基于式(2)進行回歸的估計結果。列(1)未控制歷史因素與制度變遷變量的交乘項(ini×Mar),結果發現,歷史因素變量的估計系數為0.5674,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制度變遷變量(Mar)估計系數為0.0019,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歷史因素對現代商業精神的影響并沒有因加入制度變遷變量而喪失顯著性,或者說歷史因素與制度變遷變量獨立地對現代商業精神產生正向影響。列(2)表明,交乘項(ini×Mar)的估計系數為0.1648,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制度變遷與歷史因素的交互作用對現代商業精神具有正影響,假說2初步得到驗證。為了避免制度變遷與現代商業精神有可能在同期互為因果性,在列(3)中分別取制度變遷變量(Mar)及交乘項(ini×Mar)的滯后1期作為解釋變量,結果發現,交乘項(L.ini×Mar)的估計系數為0.1375,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仍與上述結論相一致。

表2 對假說1的初步檢驗
注:(1)***、**和*分別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顯著,括號內為P值;(2)所有模型均使用穩健性標準誤進行統計推斷;(3)所有模型均使用混合OLS進行估計。
除了依據回歸方程(2)進行實證檢驗外,本文還依據樣本地區制度變遷程度將全樣本進行分組,然后采用回歸方程(1)進行檢驗。表3中的列(4)和列(5)依據樣本地區制度變遷程度是否大于等于該年度上的平均值,將所有地區分為制度變遷程度較高的地區和制度變遷程度較低的地區,即:若某地區某年的制度變遷變量大于該年度所有地區制度變遷程度的平均值,則將該地區劃分到制度變遷程度較高的地區,否則劃分到制度變遷程度較低的地區,因此依據上述分組方法,某地區上一年若進入高制度變遷程度地區,其下一年則不一定能持續進入高制度變遷程度地區,即在時序上不一定具有連續性。其中,列(4)為高制度變遷程度組,列(5)為低制度變遷程度組。從列(4)和列(5)的估計結果可發現,歷史因素(initial)在制度變遷程度較高的地區的估計系數為1.0748,歷史因素(initial)在制度變遷程度較低的地區的估計系數為0.6904,當運用自助法(Bootstrap)對這兩組系數的差異性進行跨組檢驗時發現,兩組系數的估計值在1%的水平上顯著不同,這表明,制度變遷程度確實在歷史因素對現代商業精神的影響中起到了正向調節作用,再次表明假說2是成立的。

表3 對假說2的初步檢驗
注:(1)***、**和*分別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顯著,括號內為P值;(2)所有模型均使用穩健性標準誤進行統計推斷;(3)所有模型均使用混合OLS進行估計;(4)控制變量包括GDP、MFI、pop_n、lnroad、struc、urban、f_p、trade、edu等變量。下表類同。
(三)穩健性檢驗
1.基于制度變遷變量分指標的穩健性檢驗。為了確保上文結論的穩健性,在表4中,本文進一步使用市場化制度變遷變量(Mar)的5項分指數(即非國有經濟發展(mar1)、產品市場發育(mar2)、要素市場發育(mar3)、中介組織發育與法律(mar4)、政府與企業的關系(mar5))衡量市場化制度變遷。表4的估計結果表明,中介組織發育與法律(mar4)變量與歷史因素變量的交乘項(ini×mar4)的估計系數得出了符合理論預期的估計符號但并不顯著,其他4個分指標與歷史因素變量的交乘項均得出了大于零的估計系數且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進一步表明,假說2的結論是比較穩健的,不因衡量指標的選擇而發生改變。上述分析再次表明,與市場化制度變遷程度較低的地區相比,現代商業精神在市場化制度變遷程度高的地區能得到更充分地發展。

表4 穩健性檢驗Ⅰ

(續表)
2.基于制度變遷變量分指標的分組檢驗。表5參照表3中列(4)和列(5)并使用制度變遷變量的5個分指標作為分組依據,檢驗歷史因素是否在高制度變遷程度的地區與低制度變遷程度的地區具有同樣的估計系數。行(1)和行(2)依據非國有經濟發展(mar1)進行分組;行(1)的估計結果表明,歷史因素對現代商業精神的影響在高制度變遷程度的地區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行(2)的估計結果表明,歷史因素對現代商業精神的影響在低制度變遷程度的地區并不顯著。這再次表明假設2具有較強的穩健性。在行(3)~行(10)中逐次依據產品市場發育(mar2)、要素市場發育(mar3)、中介組織發育與法律(mar4)、政府與企業的關系(mar5)等制度變遷分指標進行分組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再次表明本文假說具有較強的穩定性。

表5 穩健性檢驗Ⅱ
3.基于工具變量法的穩健性檢驗。歷史因素會影響現代商業精神,那么,現代商業精神會不會逆向影響歷史因素?這一點似乎很難想象,今天的現代商業精神會對歷史因素產生影響,故逆向因果關系所導致的內生性問題似乎不會成為本文的計量難題。但鑒于國家統計局從1992年開始統計民營企業和個體企業的數據資料,且由于民營企業和個體企業具有較強的靈活性、隱蔽性,很難客觀地統計出各地區民企的數量,故歷史因素變量可能存在衡量偏誤問題,進而會影響到估計系數的大小及其顯著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接下來擬用工具變量法處理衡量偏誤問題*當然,遺漏變量也會導致內生性問題,但本文中的工具變量法同時也有助于克服該問題。。在研究思路上,筆者首先找到歷史因素的兩個工具變量,即1949年的地區商業經濟發展指標和地區識字率變量;前者采用新中國成立初期地區商業貸款在農業貸款、工業貸款及商業貸款中的占比衡量,該比值越大則表示地區商業經濟越發達,進而地區商業文化傳統稟賦就越豐富。但1949年地區商業貸款占比指標對改革開放后現代商業精神的發展似乎沒有直接的影響,并且,本文在對現代商業精神進行回歸時已經控制住產業結構變量(struc),故該指標的設計符合工具變量的特征;而地區識字率反映了1949年中國各地區人力資本水平,商業經濟的發展離不開一定水平的人力資本,事實上,商人的受教育程度在“士、農、工、商”中僅次于“士”的受教育水平,故地區識字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歷史因素的豐富程度,同時1949年的地區識字率除了通過歷史因素對現代商業精神產生影響之外,很難產生直接的影響,并且,在對現代商業精神進行回歸時已經控制了教育水平變量(edu),故該指標也符合工具變量的要求。
基于上述分析,在表6中的列(1)首先使用商業貸款占比與識字率充當歷史因素的工具變量進行IV估計,結果發現,與表2列(6)中的估計結果相比(0.7347),在列(1)中歷史因素變量(initial)的估計系數已經下降到了0.4857,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盡管歷史因素的影響程度已小幅下降,但假說1仍成立,或者說若不考慮衡量偏誤問題,則會高估歷史因素的影響程度。列(2)在列(1)的基礎上控制了市場化制度變遷變量(Mar)同時繼續運用IV進行估計,結果發現,與列(1)相比,歷史因素變量(initial)的估計系數已經下降到0.1452,且在統計上已不顯著,這可能是由于市場化制度變遷變量(Mar)自身也是內生變量導致的。由于現代商業精神自身也會影響市場化制度變遷進程,在現代商業精神越繁榮的地區,市場化體制改革的阻力往往較小進而促進了制度變遷的推進,故有必要使用制度變遷變量的工具變量解決此問題。本文采用建國初期地區自然災害的發生率或嚴重性作為制度變遷變量的工具變量。顯然,在自然災害的發生越頻繁和嚴重程度越大的地區,這種自然地理環境所要求的制度應該越具有權威性和等級制,需要依賴政府的動員能力和組織能力解決自然災害的不利沖擊,經過長時期的演化,在這些地區居民對政府的依賴性會比較強,同時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能力和控制能力也比較強;相反,在自然災害不怎么發生的地區,對政府的依賴程度較低和群眾的自主能力往往較強,更需要依賴市場來配置資源,同時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能力及控制能力均比較弱,因此采用地區自然災害嚴重程度作為地區市場化制度變遷進程的工具變量具有理論上一致性。接下來,筆者首先使用建國初期自然災害嚴重程度和年度虛擬變量將地區制度變遷變量預測出來,并將該預測值(Marp)作為外生變量替代內生性制度變遷變量(Mar)放入回歸方程(1)。列(3)的估計結果表明,在考慮了制度變遷變量的內生性問題后,歷史因素變量(initial)的估計系數為0.7684,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再次表明假說1是成立的。列(4)繼續使用工具變量法并基于公式(2)進行回歸,結果發現,歷史因素變量與用自然災害嚴重程度預測出來的制度變遷變量的交乘項(ini_Marp)的估計系數為1.6003,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再次表明假說2也是成立的。最后,為了避免制度變遷變量(Mar)的內生性問題對分組檢驗的不利影響,接下來,本文基于使用自然災害嚴重程度變量預測的制度變遷變量將所有的樣本地區分為高制度變遷程度的地區和低制度變遷程度的地區,然后基于方程(1)進行分地區回歸,列(5)和列(6)的估計結果表明,歷史因素在高制度變遷程度的地區對現代商業精神具有更強的影響,但是在低制度變遷程度的地區對現代商業精神并不具有顯著的影響,再次印證了假說2*列(1)~列(6)均通過了識別不足檢驗、弱工具變量檢驗及過度識別檢驗,在此不再贅述。。

表6 穩健性檢驗Ⅲ
注:(1)***、**和*分別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顯著,括號內為P值;(2)本表所有模型均使用工具變量法(IV)進行估計;(3)控制變量包括GDP、MFI、pop_n、lnroad、struc、urban、f_p、trade、edu等變量;(4)F統計量用于檢驗是否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估計結果均表明無法拒絕不存在弱工具變量的原假設;chi2(1)P-val.表示過度識別檢驗的P值,本表估計結果表明,工具變量均為有效工具變量,其中,歷史因素(initial)的工具變量為商業貸款占比(shangye_iv)與識字率(literacy)。
4.關于歷史因素變量的衡量問題。為了確保本文研究假說的成立不是由于核心解釋變量的衡量問題所造成的,接下來,我們將采用民國時期各地區著名企業家的人數(ming)作為歷史因素的替代性衡量指標。毋庸諱言,地區著名企業家人數與地區歷史文化因素具有一定的相關性,只有在地方商業文化傳統較濃厚的地區才會產生更多的著名企業家。表7列出了基于地區著名企業家人數(ming)的回歸結果。在列(1)中,民國時期企業家人數(ming)的估計系數是0.0005,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民國時期地區企業家人數與現代商業精神呈正相關關系,從而印證了假說1。列(2)在列(1)的基礎上進一步控制了民國時期企業家人數(ming)與制度變遷變量(Mar)的交乘項(ming_mar),結果表明,交乘項的估計系數顯著大于零,這與表3中的結論非常一致,再次印證了假說2。列(3)和列(4)基于地區制度變遷程度進行了分組檢驗,結果表明,民國時期企業家人數(ming)變量在制度變遷程度高的地區具有較大的估計系數,但民國時期企業家人數(ming)變量在制度變遷程度低的地區具有較小的估計系數,這進一步印證了表3和表5中的結論。另外,我們還參照表7中工具變量法的估計思路重新使用民國時期企業家人數(ming)變量作為歷史因素的衡量指標對方程(1)進行了回歸分析,但這仍未影響上文結論,這表明,本文假說并不因核心解釋變量的衡量問題而發生變化*限于篇幅,并未呈現工具變量法的估計結果。事實上,本文使用民國時期企業家人數(ming)變量替代表2~表6中的變量initial,結果發現,本文的研究結論仍成立。并且,我們還使用1949年地區人口規模對民國時期企業家人數(ming)進行標準化處理,即使用地區人均企業家人數衡量歷史因素,但計量結果表明,本文的研究假說仍成立。。

表7 穩健性檢驗Ⅳ
五、研究結論
文章基于中國省級層面的面板數據資料定量測度了歷史因素對現代商業精神的影響。實證研究表明:在歷史因素資源越豐富的地區,越有利于現代商業精神的培育和傳播;簡單的測算表明,歷史因素可以解釋不可觀測的地區固定效應的32.8%~40%,即在不可觀測的地區固定效應中有較大的一部分可由歷史因素來解釋;不論是基于交乘項進行回歸分析,還是依據市場化制度變遷進程進行分組檢驗,均表明,與市場化制度變遷進程較緩慢的地區相比,歷史因素在市場化制度變遷進程較快的地區對現代商業精神的促進作用更強;并且,進一步使用市場化進程指標的5項分指數來衡量市場化制度變遷過程再次印證了上述假說。此外,本文使用工具變量法處理了衡量偏誤問題,進行工具變量法回歸后發現,本文的研究假說仍然成立;并且,即使采用民國時期各地區著名企業家的人數作為歷史因素的替代性衡量指標進行穩健性檢驗,本文結論仍成立。
參考文獻:
[1]余英時.儒家倫理與商人精神[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1-20.
[2]杜維明.新加坡的挑戰:新儒家倫理與企業精神[M].高專誠,譯.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1-16.
[3]厲以寧.資本主義的起源——比較經濟史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1-30.
[4]WEBER M. The Religion of China[M]. New York: Free Press,1951.
[5]韋森.從傳統齊魯農耕文化到現代商業精神的創造性轉化[J].東岳論叢,2004(6):5-12.
[6]胡必亮.村莊信任與標會[J].經濟研究,2004(10):115-125.
[7]朱錫慶.中國經濟發展的知識來源[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6):115-122.
[8]李后建.市場化、腐敗與企業家精神[J].經濟科學,2013(1):99-111.
[9]江春,張秀麗.金融發展與企業家精神:基于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檢驗[J].廣東金融學院學報,2010(2):62-70.
[10]邵傳林.法律制度效率、地區腐敗與企業家精神[J].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14(5):48-57.
[11]樊綱,王小魯,朱恒鵬.中國市場化指數[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1:350-400.
[12]張軍,金煜.中國的金融深化和生產率關系的再檢測:1987-2001[J].經濟研究,2005(11):34-45.
(責任編輯何志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