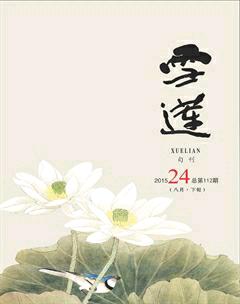雨果《巴黎圣母院》中所體現(xiàn)人性的悲哀
李少華
【摘要】“丑就在美的旁邊”“美與惡并存”是對十九世紀法國作家雨果浪漫主義美學(xué)原則的集中概括,其“唯美”精神傾向在其代表作品《巴黎圣母院》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xiàn)。無論是加西莫多和愛斯梅哈爾達、法比和愛斯梅哈爾達還是克羅德和愛斯梅哈爾達都是對人性本質(zhì)的闡述,在立項對比間滲透人性的悲哀,在不可抗拒的關(guān)感中,《巴黎圣母院》的唯美品質(zhì)也得到了完整體現(xiàn)。本文針對雨果《巴黎圣母院》中所體現(xiàn)的人性悲哀展開了重點分析。
【關(guān)鍵詞】雨果;巴黎圣母院;人性悲哀;唯美主義
通過對三組二象對立項關(guān)系的描述,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對美的不可抗拒及至高無上精神內(nèi)涵進行了闡述。源于本能對于外在美的一種愛慕,愛斯梅哈爾達與法比之間的悲劇愛情顯得荒誕而低級,美與丑的抗斥是加西莫多和愛斯梅哈爾達之間愛情的描述,在生命和死亡面前加西莫多的唯美主義情懷展露無遺,而愛斯梅哈爾達和克羅德之間的愛情則是人性缺陷與占有之間的較量,以此期望達到真善美的和諧狀態(tài),這其中盡管克羅德獲得了人性重塑的契機,然而卻最終逃脫不了毀滅的宿命。不難看出,人性的悲哀貫穿于《巴黎圣母院》始終,這與雨果的唯美精神傾向顯然有著直接聯(lián)系。
一、《巴黎圣母院》中的人性悲哀
作為一種臆想,自然狀態(tài)與人類本性狀態(tài)的結(jié)合是十八世紀浪漫主義時期興起的對唯美精神傾向的暢想,這其中將人類活動的原始狀態(tài)與淳樸的尼德蘭圖畫相等同。在人們的迫切心理導(dǎo)向下,一些處于自然狀態(tài)中的人物比如愛斯梅哈爾達就出現(xiàn)在了浪漫主義文學(xué)作品當中。
在對愛斯梅哈爾達進行形象塑造時,雨果傾注了個人對于完美人性的全部思考,這也與當時人們的自然狀態(tài)相吻合。無論是外貌還是靈魂,愛斯梅哈爾達都顯得格外美好,不存在一絲被世俗污染的痕跡,是自然人的集中呈現(xiàn)。完美的容貌、清純的靈魂,對于各種邪惡和欺騙她渾然無知,見到挾持過她的加西莫多受到烈日的曝曬,她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對待愛情時她忠貞不渝,以堅貞的心將人性感化,面對克羅德的利誘不為之所動,這足以證明愛斯梅哈爾達的善良和純潔。作為完美的化身,愛斯梅哈爾達是以女人的姿態(tài)出現(xiàn)的天然人性之花,實則她更像是雨果臆想出來的優(yōu)美幻覺,同時這也注定了結(jié)尾人性的悲哀。之所以得到人們的喜愛,是由于愛斯梅哈爾達是我們失去童年的一種代表,同時也是對臆想中純潔天真自然狀態(tài)的一種刻畫,她寄托人們理想狀態(tài)的同時也通過審美教育和文化教養(yǎng)突出了這層喜愛中的另外一層含義,則是人物的崇高情緒。
作為一個自然人,愛斯梅哈爾達與自然之間有著出于本性的和諧,然而這也使得她在認識事物時帶有不可避免的膚淺和愚昧一面。男女之間的關(guān)系是人與人之間的自然和直接的一種關(guān)系,在感性的形式表現(xiàn)中成為一種必然現(xiàn)實,這一過程中的人的本質(zhì)更加趨向于自然界中所特有的人類本質(zhì),從這一關(guān)系中我們不難看出自然人的文化修養(yǎng)及其受教養(yǎng)程度。在《巴黎圣母院》當中,雨果通過對愛斯梅哈爾達自然純美愛情追求的刻畫表現(xiàn)出她本身作為自然人的一種淺薄與無奈,在愛情選擇面前人性變得極為微小。
在愛情選擇面前愛斯梅哈爾達身為一個自然人僅僅出于自身的本性選擇自身的保護本能。由于并不具備與克羅德相等的心智,因此愛斯梅哈爾達難以對其博學(xué)與睿智進行欣賞,這就無法在愛情選擇面前產(chǎn)生共鳴。雨果將愛斯梅哈爾達視為其內(nèi)心深處的一方凈土,這一自然理想回歸的化身是對文化人自然天性的一種彌補,然而這一自然回歸過程卻顯然高于雨果的理想狀態(tài)。在和諧純美的自然狀態(tài)下文明發(fā)展的前進步伐是緩慢的,然而這一過程中人們體會到更多的是內(nèi)心痛苦,在道德文明驅(qū)使下人們迫切回歸自然,然而這并非是簡單的到原始狀態(tài)的過渡,而是在道德文明指導(dǎo)下真正達到人性和諧狀態(tài)。
二、人性與信仰間的痛苦掙扎
與愛斯梅哈爾達的純潔天真不同的是,克羅德更加像是一個陰森可怕的魔鬼,他陰郁、沉著、嚴峻而狡黠,是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性格刻畫最為復(fù)雜的一個人物。他是圣母院的副主教,同時他也是象征宗教勢力的典型人物,是對教會兇殘和虛偽本質(zhì)的一種暴露。與此同時,在追求愛斯梅哈爾達的過程中克羅德作為禁欲主義代表是對禁欲主義破產(chǎn)的有力宣告,從其人性的悲哀和悲劇命運分析這同時也是對禁欲主義虛偽本質(zhì)和宗教制度殘酷不仁的一種揭露。此外,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還塑造了不容忽視的幾個人物,比如遇到問題就出賣愛斯梅哈爾達的格蘭古瓦以及內(nèi)心與外表形成鮮明對比的弗比斯等等。然而在人物安排方面卻始終徘徊在人與自然及人與社會當中,在美丑對襯中揭示其中的美學(xué)原理,明確美丑善惡之間的本質(zhì)關(guān)聯(lián)。在相對狀態(tài)下,美丑與善惡之間的聯(lián)系互為一體,若是不存在美就無法對應(yīng)丑,若是沒有了惡也就無法突出善,在循環(huán)發(fā)展間是對人性本質(zhì)的有效揭示。面對現(xiàn)實生活中的美與丑,從審美角度分析實則也是對藝術(shù)內(nèi)容的轉(zhuǎn)化過程,作家通過對作品藝術(shù)性與悲劇元素的結(jié)合賦予了《巴黎圣母院》更多的人性魅力,使得它對人性的刻畫更加具體和細致,從中我們也不難看出人物在人性和信仰之間的痛苦與掙扎。
從審美規(guī)律出發(fā),對于事物的客觀認知需要從事物存在的感性化形式入手,通過由表及里的方式實現(xiàn)從外觀直覺到倫理道德之間的逐層滲透。無論是加西莫多的悲劇人生還是愛斯梅哈爾達的人性悲哀,都是唯美精神傾向在作品中的集中體現(xiàn)。在生理機制與人性本質(zhì)的趨向下,人類審美的悲劇化傾向更加明顯。
綜上所述,作為浪漫主義作品的代表,《巴黎圣母院》的道德追求賦予其永恒的生命力,在美與道德的層面實現(xiàn)了對人性的刻畫,其現(xiàn)實意義在今天仍得到彰顯。美好理想是雨果畢生追求的內(nèi)容,而在《巴黎圣母院》中,他將道德與美的追求轉(zhuǎn)變?yōu)槿宋锏乃廾⑷诵缘谋ㄟ^理想而闡述,這是對現(xiàn)實生活痛苦的一種哀嘆。從加西莫多的不幸等不難看出人性悲哀的造成與文化扭曲有著必然聯(lián)系。當前社會文明高速發(fā)展,當前對于道德和美的追求仍舊是時代發(fā)展的主題,然而人性深處卻也不免隱藏著諸多浮躁與不安,這不得不說是現(xiàn)代人人性悲哀的展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