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覽眾山小
阿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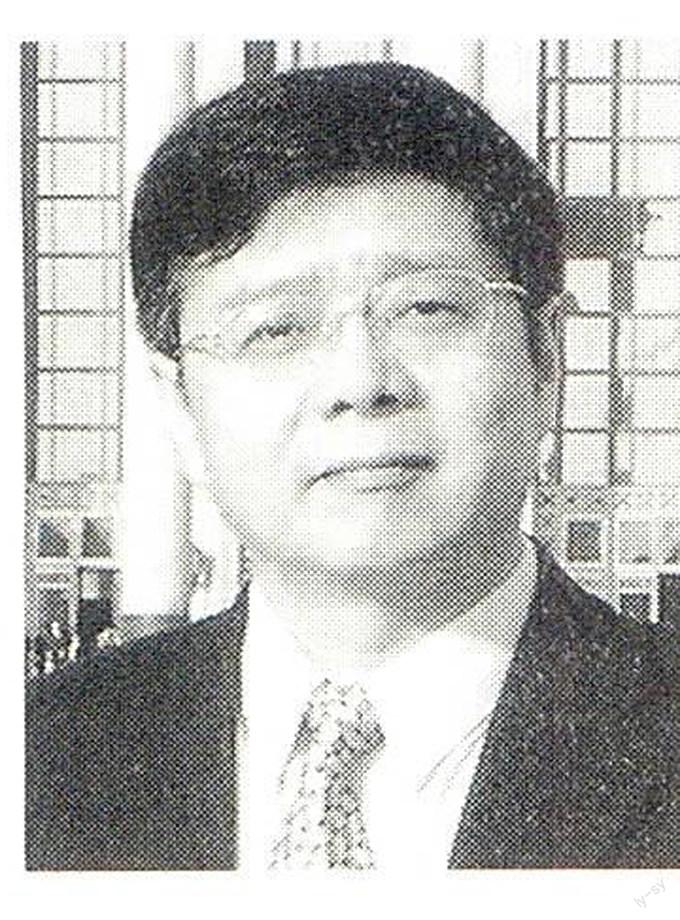
我知曉長安畫派已經(jīng)是上世紀(jì)的八十年代了,那時候由于社會氛圍和資訊的落后,人們對這個藝術(shù)流派的形成充滿了好奇和期待,可是隨著市場經(jīng)濟(jì)鋪天蓋地的沖刷,各種“畫派”脫穎而出,幾乎讓人目不暇接,也就漸漸減弱了我對長安畫派的熱情。然而,最近我聽到習(xí)近平總書記在接見陜西領(lǐng)導(dǎo)時提到長安畫派對中國美術(shù)事業(yè)的影響,便不由得萌生了研究這一藝術(shù)現(xiàn)象的念頭,進(jìn)而閱讀了長安畫派領(lǐng)軍人物趙望云、石魯?shù)热说臋n案,瞅著那一個個蠅頭般大小的鋼筆字,眼前便浮現(xiàn)出畫家們孤傲而坦蕩的身影,便想到他們坎坷而又執(zhí)著的一生,不由得被這些卓越藝術(shù)家對美術(shù)事業(yè)的不懈追求所激勵。盡管他們已經(jīng)相繼辭世三四十年了,但他們的筆墨精神依然活躍在當(dāng)今畫壇,他們所鑄煉的人格力量,已不是一句“高山仰止”就能概括。
隨后我又仔細(xì)閱讀了近年面世的趙望云、石魯?shù)热说漠嬚摦嫾峙c依然熱衷美術(shù)創(chuàng)作的畫家后人們進(jìn)行探討,我忽然發(fā)現(xiàn),由于種種浮躁的因由,人們對長安畫派的研究始終處于一種簡單疏淺的狀態(tài),這不能不讓人為這個在新中國建立以后成長起來的這一珍貴的藝術(shù)現(xiàn)象感到遺憾,尤其感到長安畫派的藝術(shù)實(shí)踐符合習(xí)總書記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于是我開始梳理有關(guān)長安畫派的形成與成就,似乎對我國今天美術(shù)事業(yè)的發(fā)展不無裨益。
上 篇
世界上任何一個藝術(shù)流派都有一個循序漸進(jìn)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今天,我們討論長安畫派的藝術(shù)成就,首先要把握這個流派核心成員的創(chuàng)作實(shí)踐,準(zhǔn)確把握他們所取得的藝術(shù)風(fēng)貌。我們知道長安畫派是上世紀(jì)六十年代初提出的學(xué)術(shù)概念,今天回顧和審視這個藝術(shù)現(xiàn)象,首先應(yīng)該對這個藝術(shù)流派的畫家狀態(tài)有一個清醒的認(rèn)識,以便從容把握和理解長安畫派在中國美術(shù)史上的位置。令人欣慰的是沒有人質(zhì)疑長安畫派是以趙望云、石魯為核心的,而品讀有關(guān)長安畫派的作品和評論,我們會清楚地意識到,這些杰出的畫家在匯聚西安以前藝術(shù)主張和學(xué)術(shù)抱負(fù)是基本一致的。
趙望云從23歲步入畫壇的那天起,就立志要創(chuàng)立中國畫的“民族形式”和“中國氣派”。他之后進(jìn)行了一系列瞄準(zhǔn)現(xiàn)實(shí)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舉辦了三十多次的個人畫展,在報紙刊物上發(fā)表了一系列表現(xiàn)勞苦大眾疾苦的作品,申明要拋掉清代“四王”的范式,將筆墨和目光投向現(xiàn)實(shí)生活,在中國畫壇刮起一股趙氏畫風(fēng),引起了中國藝術(shù)界的廣泛關(guān)注,從此這一風(fēng)格再也沒有發(fā)生過動搖和偏離。而石魯是從20歲就走進(jìn)紅色延安的,他致力于創(chuàng)立浪漫主義與現(xiàn)實(shí)主義相結(jié)合的新畫風(fēng),開始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索。為此他還將自己的姓名也由馮亞珩改為石魯,取國畫大師石濤和文學(xué)巨匠魯迅的姓氏組和而成。那清代的石濤以強(qiáng)調(diào)筆墨的時代性而著名,那現(xiàn)代的魯迅始終將文學(xué)作為投槍匕首,所以這個名字本身就是傳統(tǒng)與現(xiàn)實(shí)的結(jié)合,極其鮮明地概括了他的思想和藝術(shù)追求,數(shù)年之后這個名字果真響徹中國畫壇。也許,這就是命運(yùn)的絕妙安排,那時候他們兩人一個在國統(tǒng)區(qū),一個在革命圣地,卻殊途同歸西安,為長安畫派后來的崛起奠定了基礎(chǔ)。
這里,我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在長安畫派的形成過程,發(fā)生過三次極其重要的“事件”,從而匯聚了一批國內(nèi)頂級的美術(shù)人才,構(gòu)成了這個藝術(shù)流派的智慧核心。
一是1949年7月,來自國統(tǒng)區(qū)的左派畫家趙望云與來自紅色延安的石魯在北京召開的第一屆文代會上相見。這應(yīng)該是長安畫派形成過程最具歷史意義的“事件”,兩人的檔案記載得很清楚,盡管現(xiàn)在我們已經(jīng)無法知曉當(dāng)時兩位極具才華和抱負(fù)的美術(shù)家在京見面時的情形,但可以推斷兩位美術(shù)家的藝術(shù)追求不謀而合。當(dāng)時趙望云四十三歲,大大小小的畫作上報刊進(jìn)畫展,與愛國將領(lǐng)馮玉祥的合作更引起了社會強(qiáng)烈反響,吸引了國內(nèi)眾多文藝大家的關(guān)注,郭沫若就曾為此寫過頌詩,周恩來也曾慕名買過畫作,葉淺予、黃苗子等一批享譽(yù)中國畫壇的藝術(shù)家對趙望云的創(chuàng)作實(shí)踐給予了毫不吝嗇的贊揚(yáng)。而此時的石魯剛剛進(jìn)入而立之年,年輕的石魯在延安系統(tǒng)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和唯物主義辯證法的熏陶,其藝術(shù)才華已在根據(jù)地展露風(fēng)采,盡管如今保留下來的資料很少,但我們依然可以從那有限的版畫和速寫稿中看到他卓然超群的天賦。我注意到延安時期的所有鑒定材料,都對石魯?shù)乃囆g(shù)水平給予了積極的評價。所以,我說在新中國成立前的北京靜悄悄地發(fā)生了一個對后來的中國畫壇產(chǎn)生深刻影響的會晤,無意中為長安畫派的最終形成做了一個“未經(jīng)批準(zhǔn)”的準(zhǔn)備,在長安畫派的發(fā)展史上應(yīng)該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二是1950年9月,陜西以趙望云、石魯為主成立新的國畫研究會,吸收了何海霞、方濟(jì)眾、康師堯、李梓盛等一批頗有藝術(shù)底蘊(yùn)的優(yōu)秀畫家,在西安形成了一個高揚(yáng)革命現(xiàn)實(shí)主義旗幟的藝術(shù)群體。從此這些畫家便在兩位大師的帶領(lǐng)下,一次次地上陜南下陜北寫生素描,一次次地匯聚在美協(xié)小院的某個小屋討論畫稿,幾乎每位畫家都有代表自己最高水平的代表作當(dāng)期問世。按說作為趙望云入室弟子的黃胄和徐庶之也屬于這個范疇,只是他們剛剛聚合不久就奔赴自己傾慕的地方,但他倆的創(chuàng)作始終沒有沖出長安畫派的窠臼。的確在中國美術(shù)史上還沒有哪一個畫派能集聚這么多頂級的藝術(shù)家,為日后創(chuàng)立長安畫派奠定了組織和藝術(shù)的基礎(chǔ)。
三是1961年10月,西安美協(xié)在中國美術(shù)館舉辦“西安分會國畫研究室班習(xí)作展”,整個藝術(shù)團(tuán)隊(duì)在京整體亮相。這些作品以精湛的筆墨描繪了西北風(fēng)貌和新社會的新生活。其中趙望云、何海霞、方濟(jì)眾、康師堯各有二十余幅,石魯有五十幅,李梓盛有近十幅。這一百五十余幅畫作,猶如猛烈刮來的一股西北風(fēng),新的構(gòu)圖,新的色彩,讓中國畫壇為之一振,標(biāo)志著中國畫在現(xiàn)代意義上取得一個可喜收獲。雖然當(dāng)時他們謙卑地把展出的作品統(tǒng)稱為“習(xí)作”,但還是讓沉寂已久的中國畫壇轟動起來,評論家們毫不猶豫地將這一群畫家創(chuàng)作的這一種風(fēng)格的作品,概括為“長安畫派”,從此這些畫家這個畫派再沒有離開過評論家們的視線,至今還讓人感到振奮和驕傲!
這里,我們厘清了長安畫派的發(fā)展過程,有必要對這一藝術(shù)流派核心成員的人生狀態(tài)有個清醒認(rèn)識,以便準(zhǔn)確把握長安畫派的藝術(shù)特性。無論當(dāng)時還是現(xiàn)在,大家都認(rèn)為趙望云和石魯是長安畫派的核心,沒有他們便沒有長安畫派。是的,自從兩人在西安匯合,命運(yùn)便把他倆緊緊扭結(jié)到一起,也把他們的藝術(shù)實(shí)踐和友誼帶到生命的終點(diǎn),使得兩個耀眼的名字深深嵌進(jìn)長安畫派再也無法分開。如今,由于各種原因時常在坊間會有長安畫派的流言溢出,其實(shí)這些杰出藝術(shù)家的胸懷之博大,是我們這些凡夫俗子難以理解的。由于趙望云與石魯?shù)娜烁窳α颗c長安畫派的形成息息相關(guān),我試圖對兩位杰出藝術(shù)家的藝術(shù)與感情狀態(tài)做些分析:
一方面,我們應(yīng)該看到石魯對趙望云始終充滿期待和敬重。這個判斷首先是基于檔案里記錄了一個今天看來頗為有趣的史實(shí),當(dāng)年他們從北京回到西安后,上級便任命趙望云為西北文聯(lián)美術(shù)工作委員會的副主任,石魯居然在會上對任命決定提出質(zhì)疑,直言這是藝術(shù)團(tuán)體應(yīng)該由趙望云擔(dān)任一把手。石魯這個十分莽撞的表態(tài)引起了有關(guān)方面的“擔(dān)憂”,并把這件事記進(jìn)了當(dāng)年的鑒定。我要指出的是,這次任命距離他們在北京的會面剛剛過去不到半年,我們可以透過這件事看到石魯?shù)穆收婧蛨?zhí)拗,也可以看到石魯對趙望云的認(rèn)同和敬佩。遺憾的是后來在1956年,趙望云受到政治打擊被“劃為右派但不以右派分子論處”。這右派和右派分子的差別究竟有多大,今天的人們似乎已經(jīng)難以理解了,但兩人的情誼依然,自傳顯示石魯并沒有因?yàn)橼w望云被錯劃右派而與之疏遠(yuǎn),反而愈加積極地與趙望云切磋畫藝,年年同行采風(fēng)寫生,這在當(dāng)時那個政治敏感的時代該有多大的勇氣啊!
然而“文革”期間,兩位藝術(shù)家又相繼成為批斗對象,每周安排兩人拉架子車參加勞動,盡管那時的石魯已經(jīng)患病,但每次拉車他都主動駕轅,執(zhí)意讓趙望云在旁邊拉纖,感動得趙望云回家就說:“今天又是石魯駕的轅。”特別讓我感動的是,當(dāng)有人時常拿來趙望云繪制的冊頁,病中的石魯睹畫生情欣然提筆:“落落大方,骨高氣淳,藝貴獨(dú)創(chuàng),猶貴人品,此之一代畫師也。”“蒙蒙雨露下甘霖,山川無處不生春,操管如生稱大作,清壇無不敬先生。”想想以石魯那樣的直率和孤傲能夠作此評價,絕不是心血來潮隨性而為的。那年冬天石魯?shù)弥粟w望云辭世的消息,一個人在畫案前佇立許久,親自鋪紙?zhí)峁P寫下了八個大字:“尊美重讀,藝為人民。”然后執(zhí)意拖著病衰的身子,搖搖晃晃地走到四里路遠(yuǎn)的趙望云家里,送上挽聯(lián),鞠躬悼念,為同道者做最后的告別,惺惺相惜,百感交集,任何話語都已多余,這一幕使在場人至今憶起仍然淚流不止。
另一方面,趙望云對石魯也十分敬佩和欣賞。從我們閱到的資料看,趙望云對石魯?shù)拿佬g(shù)抱負(fù)高度評價,自傳中兩人同行到陜南、陜北、關(guān)中去采風(fēng)的次數(shù)多得令人感動,而且趙望云每次都把石魯寫在同行者的第一位。兩人出訪印度、埃及回來后,第二年就出版了兩人的寫生合集,幀幀小品,域外風(fēng)情,且把彼此的友情和追求表達(dá)得淋漓盡致。特別能說明趙望云對石魯?shù)乃囆g(shù)實(shí)踐甚為欣賞的是,1962年他見愛子趙振川有意承續(xù)趙家文脈,便鄭重地請石魯收兒為徒,力促趙振川走上學(xué)畫的正途,這其中所包含的贊許和欣賞顯而易見。國人歷來重視藝術(shù)源流,強(qiáng)調(diào)名師出高徒,至今人們對趙振川有過這樣的學(xué)習(xí)經(jīng)歷羨慕得唏噓不已。
后來殘酷的政治斗爭使得石魯病了,趙望云的身體也每況愈下,當(dāng)時美協(xié)的干部都下放農(nóng)村了,家屬院里只剩下趙家與石家,人們時常看見兩位病入膏肓的老人坐在夕陽里聊著并不久遠(yuǎn)的往事,其情也悲,其景也慘矣。有一天病中的石魯被一伙紅衛(wèi)兵激怒了,半夜起來把美協(xié)唯一的電話拔掉,扔進(jìn)了后院防空洞,又把美協(xié)大門反鎖上,自己手持一柄鐵棒,像衛(wèi)士一樣守衛(wèi)在門口阻擋紅衛(wèi)兵進(jìn)院,任誰勸說都置之不理。后來是趙望云擔(dān)心僵持下去會給石魯帶來災(zāi)難,便主動下樓勸他“停止抵抗”,石魯聞聲這才放下鐵棒打開大門。后來美協(xié)發(fā)現(xiàn)了一條“反動標(biāo)語”,這在當(dāng)時可是要抓人判刑的。由于石魯當(dāng)時已經(jīng)被內(nèi)定為“現(xiàn)行反革命”,公安人員便拿著“反標(biāo)照片”直接去問趙望云:“看這是不是石魯寫的?”趙望云掃過一眼直截了當(dāng)說:“這絕對不是石魯?shù)淖帧!毕胂朐谀呛谠茐撼堑姆諊拢軌蜻@樣不留余地的坦言相護(hù)該有多大的膽識啊!
趙望云、石魯可謂大師攜手,雙峰并峙,捧讀著檔案里那些細(xì)碎難辨的蠅頭小字,仿佛看到一個個艱難的腳印在跋涉前行,也感受到了兩位卓越藝術(shù)家的人格魅力,令人不禁感嘆萬端!我注意到,在趙望云的畫冊里常常會發(fā)現(xiàn)石魯慣常的筆意,在石魯?shù)漠嫾幸矔吹节w望云繪畫的語境,相教相長,相互砥礪,兩位極具個性的藝術(shù)家若沒有相互欣賞的基礎(chǔ),筆下絕不可能出現(xiàn)這般現(xiàn)象,以致長安畫派各個畫家那個時期的作品也都有著驚人的相似。所以,是趙望云、石魯高摯長安畫派的大旗,實(shí)現(xiàn)了中國現(xiàn)代美術(shù)史上一次激動人心的跨越。
當(dāng)然,進(jìn)入上世紀(jì)七十年代以后,這些杰出的美術(shù)家好像意識到個性的重要,一個個都在竭力發(fā)展著自己的筆墨語言,紛紛開始回歸各自的創(chuàng)作習(xí)慣,應(yīng)該說石魯、何海霞邁的步子最大,取得的成就讓畫壇矚目,但他們的筆墨與構(gòu)圖最終還是可見長安畫派的思維模式。當(dāng)然,趙望云和石魯在長達(dá)三十年的合作中,經(jīng)歷了一連串驚心動魄的政治運(yùn)動,兩人在生活和藝術(shù)追求上可能會有這樣或那樣的差異,但彼此的藝術(shù)實(shí)踐是相互欣賞的,尤其是彼此的心是相通的,隨著他們創(chuàng)作生涯的終結(jié),彼此也完成了各自的人格塑造,這種強(qiáng)大的人格力量值得我們深入地挖掘和敬仰。
下 篇
從長安畫派橫空出世震驚了中國畫壇以后,國內(nèi)的文化氛圍一度處于沉悶而又焦慮的狀態(tài),似乎那句“一手伸向傳統(tǒng),一手伸向生活”的藝術(shù)主張成了長安畫派唯一的標(biāo)簽。其實(shí),若把長安畫派的創(chuàng)新成果放到中國美術(shù)史的全景下去觀照,會對長安畫派的藝術(shù)實(shí)踐有更深刻的認(rèn)識,這是上世紀(jì)中葉以來一批有志于創(chuàng)新的美術(shù)家把中國畫的理論和實(shí)踐提高到一個新水平的標(biāo)志,正是他們的卓越努力給徘徊在故紙堆里的藝術(shù)注入了活力,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形式”和“中國氣派”,稱得上是一項(xiàng)彪炳史冊的藝術(shù)創(chuàng)新。
那么,長安畫派在哪些方面有創(chuàng)新呢?
第一,創(chuàng)新了中國畫的描寫內(nèi)容。歷史上中國畫在形成獨(dú)立的門類以后,描寫的內(nèi)容大都是佛道仙鬼和達(dá)官仕女,即使后來山水和花鳥分離出來形成獨(dú)立的畫種,依然是在表現(xiàn)貴族的情趣;即使所謂的文人畫窮途末路遁入竹林,依然不變的是表現(xiàn)士大夫的感受;即使在畫中偶見樵夫村姑,也是作為閑情逸致的景致點(diǎn)綴。尤其是明末清初的“八大”和“八怪”更將筆墨搬進(jìn)山野自成一統(tǒng),喜歡用那陰郁的目光來審視琳瑯滿目的現(xiàn)實(shí)生活。盡管后來石濤、黃賓虹們也想在繪畫形式上、在筆法結(jié)構(gòu)上、在色彩運(yùn)用上尋求突破。但是“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以后,中國的有識之士依然不斷發(fā)出國畫藝術(shù)窮途末路的哀嘆。而長安畫派的藝術(shù)實(shí)踐所以能讓藝術(shù)界耳目一新,最為突出的是藝術(shù)家們在這方面實(shí)現(xiàn)了突破。
一方面,長安畫派注重反映百姓的現(xiàn)實(shí)生活。我注意到長安畫派上世紀(jì)五十年代的作品都秉承著一個共同的宗旨,就是描寫火熱的現(xiàn)實(shí)生活,而沒有把筆墨浪費(fèi)在反映古人詩意和閑情逸致上。趙望云應(yīng)該是那個時期最清醒的國畫家了,而用中國筆墨來系統(tǒng)反映農(nóng)民的生活他應(yīng)該是第一人。這位眼力獨(dú)到的大師創(chuàng)新了中國畫的表現(xiàn)方式,他始終強(qiáng)調(diào):“國畫如果要有前途,就必須從芥子園的框框里跳出來與現(xiàn)實(shí)結(jié)合,應(yīng)該對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加倍關(guān)心。”大師對百姓的摯愛是深入骨髓的,他始終將筆墨瞄準(zhǔn)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百姓,解放前畫家不避風(fēng)險游歷大江南北,穿越國統(tǒng)區(qū)和淪陷區(qū),用畫筆將人民的吶喊和苦難表現(xiàn)得動人魂魄。解放后畫家筆下依然充滿對底層百姓的關(guān)注和熱情,一大批精品力作應(yīng)運(yùn)而生。那一套《桑蠶組畫》就是新農(nóng)村史詩般的寫照,有的畫面是郁郁蔥蔥的桑樹,姑娘們在樹林間若隱若現(xiàn),桑葉的清香便微微飄出來;有的畫面姑娘們在清洗蠶具,圓圓的簸箕舞蹈般在溪水里起起伏伏;有的畫面是養(yǎng)蠶小屋,密密麻麻的蠶寶寶帶給人豐收的暢想,幸福也都全印到蠶農(nóng)們的臉上了。選擇這個角度來概括新社會,顯示了杰出藝術(shù)家的智慧和表現(xiàn)力。值得一提的是“文革”后有外貿(mào)部門專請趙望云繪制一批仕女騷客的畫作,畫家依舊固執(zhí)己見上交了一批農(nóng)村題材的作品,執(zhí)著的藝術(shù)追求令人聞之動容。
另一方面,長安畫派注重提煉創(chuàng)作對象內(nèi)在精神。石魯也注重反映現(xiàn)實(shí)生活,但要求更深入,他有段談?wù)撊A山的論述極為精辟:“大家都在畫華山,可那古人眼里的華山是修行煉道的地方,而我們看到的華山則是祖國壯麗河山,蘊(yùn)含著民族的精神。”所以這位激情澎湃的大師努力使創(chuàng)作更集中更純粹,以使作品更具有藝術(shù)感染力。因此石魯筆下的華山巍峨挺拔,透出一股凜然正氣,蘊(yùn)含著中華民族的偉岸。筆者特別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石魯堅持藝術(shù)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尤其是用筆墨表現(xiàn)重大歷史題材方面做出了杰出貢獻(xiàn),最著名的就是那幅《轉(zhuǎn)戰(zhàn)陜北》了,今天我們平靜地欣賞這幅部曠世之作,依然會被作品所傳達(dá)出的豪邁所感染。蒼蒼茫茫的山巒之間,一位背著斗笠的小戰(zhàn)士將戰(zhàn)馬拴住歇息,毛澤東偉岸的身軀屹立在浩瀚深邃的群山之上,顯示出運(yùn)籌帷幄的自信和淡定,使人想起偉大領(lǐng)袖氣勢磅礴的詩句,“數(shù)風(fēng)流人物還看今朝”!這幅作品之所以令人震撼,之所以能成為長安畫派的扛鼎之作,就是畫家將偉大領(lǐng)袖置于壯闊的山河懷抱之間,領(lǐng)袖與人民與時代與祖國山河的關(guān)系把握得生動而又準(zhǔn)確。后來畫家談到這幅作品的創(chuàng)作,正是他經(jīng)歷了轉(zhuǎn)戰(zhàn)陜北的過程,從而精妙地駕馭和藝術(shù)再現(xiàn)了這一重大革命題材,任何時候去品讀都會感覺到作品昂揚(yáng)的張力,而這恰恰在中國傳統(tǒng)繪畫里難見其蹤,被視為中國國家博物館的鎮(zhèn)館之寶毫不為過。
第二,創(chuàng)新了中國畫的表現(xiàn)形式。從中國畫的發(fā)展看,傳統(tǒng)繪畫基本是以人物為中心的,山水、花鳥只是為了襯托人物氛圍而存在著,后來三類分野以后,愈發(fā)強(qiáng)化了各自門類的獨(dú)立性,從此似乎互不搭界了。而長安畫派卻是將山水、花鳥與人物融為一體互為背景來表現(xiàn)創(chuàng)作者的主題,從而把中國畫的表現(xiàn)形式向現(xiàn)代思維推進(jìn)了一大步。
首先,是將人物置于山水之間,人物是作品的點(diǎn)睛之筆。傳統(tǒng)的山水畫也有飲茶撫琴的隱士和山坳里的樵夫,也有市井的賣家和游歷的商客,這應(yīng)該是這種表現(xiàn)形式的濫觴,但那些人物只是山水風(fēng)貌的點(diǎn)綴,僅僅是畫面的陪襯而已,起到的是渲染山水主題的作用。而長安畫派是將人物納入作品的核心,使風(fēng)景與人物融為一體,取舍哪一部分都難成佳作。比如趙望云那幅《集場歸來》,我們看到一群農(nóng)家男女簇?fù)碇H馬車,提著背著集市購買的貨物走在回家的路上,路邊一棵棵參天的老樹似張開的翅膀,撫慰著經(jīng)過的農(nóng)家兒女,其中的景色和人物互為補(bǔ)充,生動地描寫了那個激情燃燒歲月的典型場面。而且畫家沒有直接描寫集市,僅僅抓住了返家歸途的瞬間,巧妙地展示了勞動者生活富足的風(fēng)貌。這種構(gòu)圖延續(xù)了畫家始終不渝的藝術(shù)主張,畫面人物與風(fēng)景互補(bǔ),洋溢著輕松與自然,新中國的新面貌也由此可見矣。
這種創(chuàng)作風(fēng)格與石魯?shù)乃囆g(shù)實(shí)踐也大體一致。在上世紀(jì)五十年代,石魯?shù)膭?chuàng)作風(fēng)格明顯在向這方面靠攏,同時他又大膽進(jìn)行創(chuàng)新發(fā)揮,達(dá)到了一種更加集中更加強(qiáng)烈的震撼效果。比如那幅代表作《東渡》,洶涌的黃河浪花四濺,一群赤露上身的戰(zhàn)士奮力駕馭著小船向著勝利的彼岸,而毛澤東站在小船中央氣定神閑成竹在胸,把指揮千軍萬馬的大將風(fēng)度生動展現(xiàn)在讀者面前,那河水的洶涌和危巖的猙獰,都是為襯托船上人物的氣場,誰見到那幅飽蘸著創(chuàng)作者才情的作品,都會感到運(yùn)籌帷幄的豪邁席卷而來。
其次,是將山水融于人物情懷,山水盡顯意境之美。人們欣賞山水畫所能傳達(dá)的意境閑逸,所以古時的山水畫總能看到茅屋、亭閣、板橋、山徑,里面也常有小小人物半遮半隱,讓看慣了神道仙姑的達(dá)官閑士找到了進(jìn)入逸情的通道,成了居室附庸風(fēng)雅的象征。而長安畫派的作品,山水是他們描寫的主要背景,但這個背景是為畫面中的人物服務(wù)的,閱讀這些作品一方面會為壯美的山河所感染,另一方面會為山河里的人物所牽掛,似乎在石濤、黃賓虹們等山水大師的畫作里較少這樣的范例。趙望云早年畫的那幅《牧馬圖》把奔騰的馬兒趕到山崖,牧馬人揚(yáng)鞭勒馬英姿颯爽,把山的壯闊與人的瀟灑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這里最為經(jīng)典的就是趙望云那幅《深入祁連門》了,層巒疊嶂的山峰與深深淺淺的溝壑?jǐn)D壓著,讓人可見山的壯闊和溝的深邃,而行進(jìn)在山下的騎馬人盤旋于群山之巔,且不知何時才能到達(dá)終點(diǎn),不由得為跋涉者不避艱險的壯舉而肅然起敬,也為畫家選取這樣一個角度表現(xiàn)山與人的壯美而贊嘆不已。
而石魯在這方面也進(jìn)行著積極探索,他創(chuàng)作的山水畫同樣引入了人物形象,但他更深一步提出:“要把山水當(dāng)作人來畫,有的是高大的,有的是堅強(qiáng)的,有的是優(yōu)美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山水畫就是人物畫。”這種“形而上”的畫論,至今讀來依然振聾發(fā)聵令人沉思。為此他進(jìn)行了卓越的實(shí)踐,那幅《逆流過禹門》,氣勢磅礴,驚濤拍岸,群山似被激流劈開,江水順勢而下,只見一位船夫奮力駕馭著小船,洶涌的波浪更將小船掀得快要側(cè)立起來,其浪也高,其勢也險,強(qiáng)大的藝術(shù)感染力讓讀者幾乎會感到身體都禁不住劇烈搖晃。那幅《延河飲馬》卻把山的壯闊與晚霞的恬靜拉到面前,巍巍寶塔迎面而立,一群馬兒歡快地?fù)湎蜓雍影哆叄榴R人緊隨其后瀟灑自如,整個山河都沐浴在紅燦燦的霞光里,延安人的幸福也就躍然紙上了。所以,這幅杰作如果沒有牧馬人的點(diǎn)睛,就難以由純粹的山水來實(shí)現(xiàn)意境的升華,如果沒有山水創(chuàng)造的意境,那牧馬人就會顯得單薄無力,二則缺一不可矣。
第三,創(chuàng)新了中國畫的筆墨語言。有人曾經(jīng)追問長安畫派的特點(diǎn),老畫家概括了四個字:“不斷探索。”的確,“不斷探索”應(yīng)該是長安畫派的精神所在,而畫家們所竭力推崇的“民族形式”和“中國氣派”就是長安畫派的不懈追求。我們注意到趙望云和石魯都有大量的作品沒有題款,那可不是他們的疏忽,而是他們對自己的創(chuàng)作不甚滿意的表現(xiàn)。一生注重詩、書、畫、印和諧的石魯,甚至到晚年磨平了印章,喜歡在作品上畫印讓人感覺怪異,其實(shí)大師直言是他感覺那些傳統(tǒng)鈐印已不符合創(chuàng)新的筆墨意境了。
一是將寫生帶入筆墨。我們知道中國畫的筆墨講究寫意,甫一面世就將寫意作為這個藝術(shù)品類的風(fēng)格頑強(qiáng)地延續(xù)下來,所以中國古代畫家講究看山讀水,喜歡游歷江河湖泊,尋覓能感動自己的神韻。但這種閱歷更多地是一種尋找美感的過程,而很少會將閱讀對象真實(shí)地收入尺幅,所以中國畫不論是山水、人物、花鳥,寫意的成分始終占據(jù)著統(tǒng)治地位,幾乎可以說基本拒絕寫生。但趙望云認(rèn)為中國畫創(chuàng)新的突破口在于寫生,在于內(nèi)容與現(xiàn)實(shí)生活緊密結(jié)合。所以畫家身體力行走南闖北,即使是在戰(zhàn)火紛飛的抗戰(zhàn)年月,依然將看到的山水人物凝聚到筆端,通過寫生去采擷創(chuàng)作靈感,此法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獲,獲得了藝術(shù)界的滿堂彩。那幅《耕田圖》畫的是一位老農(nóng)駕著毛驢在田間犁地,神態(tài)之生動,田壟之精細(xì),令人不由得為之感慨。而且趙望云在上世紀(jì)五六十年代的創(chuàng)作,大都具有寫生筆墨的鮮明特征。那《初探三門峽》就是這一創(chuàng)作方法的代表之作,站在這幅巨作前,盡管山勢狂野危石林立,盡管江水湍流濤聲拍岸,但你感覺不到大自然的壓迫,反而會被熱氣騰騰的勞動場面所感染,在這些激情萬丈的勞動者面前必然高山低頭江河讓路,這就是優(yōu)秀藝術(shù)作品給人的感受。而且趙望云不但身體力行,還要求入室弟子黃胄、方濟(jì)眾、徐庶之白天到街上去寫生,晚上將寫生稿改繪成水墨畫,這些畫家后來也都能夠成為美術(shù)大家,與當(dāng)時苦練的創(chuàng)作方式不無關(guān)系。后來趙望云擔(dān)任西北美協(xié)領(lǐng)導(dǎo)后更把這種心得無保留地與同道們分享,一次次帶領(lǐng)大家看山望水寫生采風(fēng),一次次讀畫閱書體驗(yàn)傳統(tǒng),使得國畫藝術(shù)從象牙塔里走到了十字街頭,這在今天看來依然需要宏揚(yáng)。
同時,畫家們還竭力給寫生注入真摯情感。我們知道寫生強(qiáng)調(diào)的是真實(shí)描繪目視物狀,而石魯直將寫生提到創(chuàng)作的高度。他有一篇專論寫生的文章,對寫什么、如何寫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寫生能發(fā)現(xiàn)真正活潑的東西,這是創(chuàng)作代替不了的,好的寫生就是創(chuàng)作,但不能將寫生直接搬進(jìn)畫幅。”石魯?shù)慕?jīng)典之作,似與趙望云有異曲同工之妙。那幅《案頭精品》應(yīng)是畫家不多的幾幅心情平伏的恬靜之作,凝視良久會嗅見蘭花散發(fā)的芬芳,令人不由得感嘆神韻精妙。而那幅《春播圖》更把春天里農(nóng)民喜播糧種的歡悅直接揮灑到臉上,那趕牛的老農(nóng)、扶犁的青年、等待收獲幸福的女人們多姿多彩,使翻身農(nóng)民的興奮一覽無遺。而且這幅作品只在上角畫了一牛四人,大面積的留白裸露著土色,你會發(fā)現(xiàn)這是一群土改后的農(nóng)民在給自己的地里播種,杰出的藝術(shù)品實(shí)在是太有概括力了,不能不伸出大拇指。
這里筆者特別要指出的是,這種創(chuàng)作思維畫家已經(jīng)滲入骨髓了,石魯不但努力寫生現(xiàn)實(shí)世界,還瞄向自己的精神世界。我們閱讀畫家在精神發(fā)病時創(chuàng)作的十余幅似乎充滿囈語的怪誕作品常常會感到震撼,也會感到莫名深奧,似乎誰也道不清那些畫作的意蘊(yùn),其實(shí)這是一位杰出藝術(shù)家完成藝術(shù)實(shí)踐和人格塑造的巔峰之作。那些作品大多是在他十年前訪印作品上的二度創(chuàng)作。當(dāng)時石魯人雖病了,但思想絕對沒有病,藝術(shù)狀態(tài)依然完整,所以沒有一幅是涂鴉,也沒有一筆是多余,你看那些印度老人和少女衣皺上繪滿了似乎誰也無法解讀的字符,那可不是精神錯亂的涂抹,而是藝術(shù)家精神苦惱在藝術(shù)上尋求解脫,是試圖用這種神秘的線條與筆墨表達(dá)對迫害的反抗和不滿,當(dāng)是畫家精神世界的寫生素描,是畫家強(qiáng)大的精神力量和卓越的藝術(shù)品質(zhì)在作品上的升華。而且,令人敬佩的是畫家即使在病中依然在追求美,那幅迷人的《美典神》,雙眸微閉,圓潤恬靜,安詳?shù)匦币性跐鉂獾募t色里,中間露出的點(diǎn)點(diǎn)留白,還繪有篆刻般的提示字符,襯托著女神的熱情和美麗。這幅杰作哪里是病人所為?翻遍石魯所有的畫作再沒見過如此迷人的形象,所以這幅作品實(shí)質(zhì)上是畫家對美的真情告白,也是畫家心靈的寫生,是畫家對美的追求登峰造極的表達(dá)。可能大師明白美的最高境界是殘缺,而這幅作品太完美了,所以大師完成創(chuàng)作后竟將畫作一撕為二,鄭重地交給兒女一人一半,也許就是寓意世界上從來沒有絕對的完美!
二是將赭黃融進(jìn)筆墨。如果我們有興趣翻開厚厚的中國美術(shù)史稿,就會發(fā)現(xiàn)中國的山水人物畫追求的是雅逸和恬淡,偶爾會有畫家把筆墨濃重地?fù)]灑到宣紙上,依然是在表現(xiàn)逸情呈現(xiàn)悠遠(yuǎn)。而長安畫派卻旗幟鮮明地將赭黃的風(fēng)格大片涂到畫面上,在中國畫創(chuàng)作領(lǐng)域可謂獨(dú)樹一幟。趙望云提出:“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基本色彩,不論歷史怎樣變化,文化形態(tài)怎樣演進(jìn),而民族間的個性色彩是始終存在的。”
為此,長安畫派的經(jīng)典作家經(jīng)過對西北風(fēng)貌的長期觀察和揣摩,提煉出了“瀝瀝搓搓的筆墨”,一種蒼茫渾厚的色澤基調(diào),與國內(nèi)各地畫家的風(fēng)貌都拉開了距離。具體到作品上,就是彩與墨混同,多種皴法并用,其色澤渾厚,一展大西北韻味,又內(nèi)隱筋骨,藏匿大西北的倔強(qiáng),形成了一種接近黃土高原的美術(shù)色彩,把西北高原的蒼涼與厚重透過色彩呈現(xiàn)出來。這種方法在趙望云解放前的作品中多有表現(xiàn),解放后又加以精進(jìn),更加符合大西北的風(fēng)情物貌,后經(jīng)長安畫派的進(jìn)一步錘煉而更加生動自然。可以說長安畫派經(jīng)典畫家創(chuàng)作的多數(shù)作品都喜用這種色調(diào),其實(shí)這也就是美術(shù)作品時代精神的體現(xiàn)。趙望云特別喜歡描寫祁連山和陜北風(fēng)情,總能把這方水土的神韻描繪得生動貼切,與他把握了這種色調(diào)不無關(guān)系。那幅《陜北秋收寫景》,山脊被一道道的梯田托起來,一孔孔窯洞高低錯落在山峁間,喜獲豐收的農(nóng)民與毛驢拖著轆軸在麥場上脫粒,還隱約可見從窯洞出來的老鄉(xiāng)和孩子,整個畫面幾被赭黃所籠罩,隱隱透出沉甸甸的喜悅。那幅《鄉(xiāng)村小學(xué)》,一條曲曲彎彎的山路上,散布著上學(xué)去的農(nóng)家孩子,幾間茅屋校舍隱隱若若,赭黃的山坡蜿蜒而來,場景幽靜而又甜美,好一幅春光無限的幸福寫照。
而且,石魯也實(shí)踐了這種西北風(fēng)貌的色調(diào),創(chuàng)作了一批這種風(fēng)貌的繪畫作品,但是他對色彩的運(yùn)用更濃重更熱烈,似乎也沒有任何顧忌,直將人的感官都逼得氣喘,這當(dāng)然是優(yōu)秀藝術(shù)作品的魅力使然。那幅《山腰修梯田》,在層層疊疊的山腰上,密密麻麻的農(nóng)民兄弟揮鋤大干,一塊梯田依次而上,且把勞動者汗水澆過的梯田染得一片赭黃,與那黑黝黝的山崖形成對照,凸顯了今日農(nóng)民的創(chuàng)造力。還有那幅《高原鐵路到我家》,更把熱火朝天的建設(shè)工地用筆墨精致地刻畫出來,盡管山頂白雪皚皚,山下卻是熱浪撲面,鱗次櫛比的帳篷依山而列,運(yùn)料的馬隊(duì)絡(luò)繹不絕,直把山腳下的山坳鬧得熱熱烘烘,橫貫畫面的赭黃沖擊著人的視覺,相信很快就有天路鋪到藏胞帳前。作品所以能有這樣的藝術(shù)感染力,就是畫家把握住了大西北的風(fēng)土基調(diào),使得畫面充滿朝氣而又真切。
綜上所述,趙望云四十年代以創(chuàng)新中國畫表現(xiàn)方式名載畫壇,五十年代以反映百姓幸福為己任,六十年代則以提煉筆墨韻律為追求。而石魯五十年代以歌頌新生活為目標(biāo),六十年代以重大題材突破而著名,七十年代以創(chuàng)新筆墨入史冊。長安畫派的確為中國畫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開拓了一條新路,在中國畫壇上高高揚(yáng)起了長安的旗幟,隨著歷史的演進(jìn),隨著各種復(fù)雜因素的蕩滌,我們將會更加清楚地看到他們的創(chuàng)作實(shí)踐給中國畫壇帶來的持久影響力。
偉哉,長安畫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