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鄉(xiāng)
熊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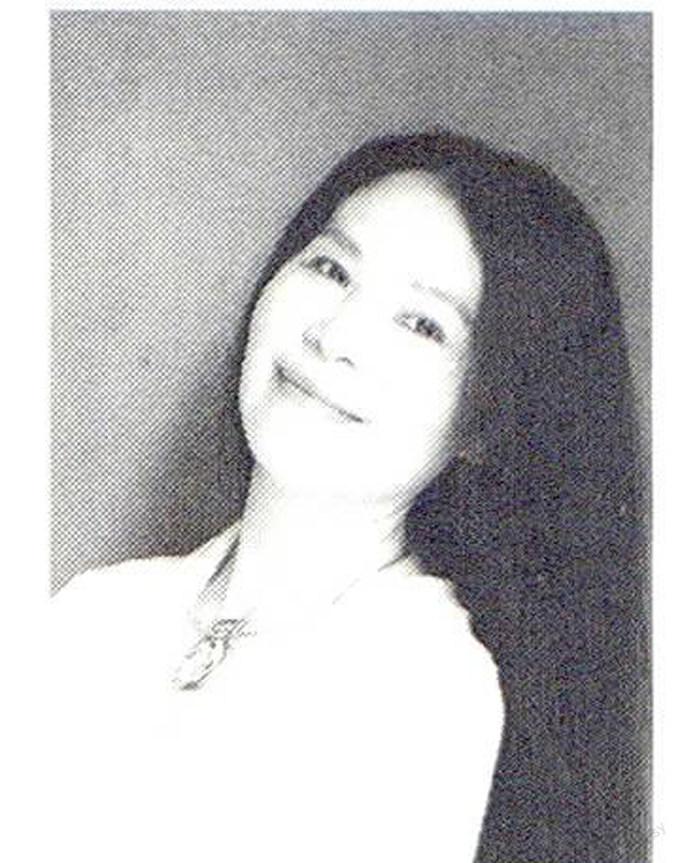
一
“前世,我是做了什么壞事嗎?”老人蔣淳英看著我。她立在門側(cè),身后以及周遭的泥墻,將屋內(nèi)的光線吮吸殆盡。“不然,我的命咋會這么苦?”她問。
華發(fā)滿頭,她將發(fā)絲熨熨帖帖梳在腦后。發(fā)梢處,束成兩團(tuán)元宵般的小鬏。
因?yàn)槭菪。腥婚g,你總以為,是一位小女生在暗處絮絮呢噥。
我將滿眼淚花的老人淳英攬過來,“我們?nèi)ノ萃庾聛砺f,好嗎?”
于是,金秋,在秦巴山南麓的群巒之中,四川廣元蒼溪縣月山鄉(xiāng)的這座小山村,在一排“尺子拐”土坯泥屋半圍的曬壩里,我傾聽——
1950年出生的淳英只念到小學(xué)二年級,因?yàn)榧依锾嫔a(chǎn)隊(duì)養(yǎng)牛,母親需要幫手,一對弟弟妹妹需要照顧,她輟學(xué)了。
從河壩那邊的小山村嫁到這山中來,那年,淳英十八歲。
夫家人口薄少,丈夫是獨(dú)子,也是這戶樸素人家的養(yǎng)子。土屋,老灶,門前有樹,有狗,不遠(yuǎn)處有糧田,有菜地。她與她的公公、婆婆、丈夫,還有之后來到人世的她的三個(gè)孝順女兒,一家人就這樣平平靜靜在這里度著時(shí)光。
她很滿足于這樣的平淡日子。一只狗莫名地一聲叫,感應(yīng)似地,整個(gè)山坳里的狗,都次第叫開來。大歡大愉地叫。日子很慢,天亮披衣下床,照料家禽,照料人,然后出坡,打理田地。
那些田里地里水庫里的家禽,白天孩子似地跑出去,天色漸晚,又一只只牽著線似地往家回。
這個(gè)小家庭的平靜,是從六年前被打破的。
深秋地里點(diǎn)麥子時(shí),淳英發(fā)現(xiàn)丈夫新奎老捂著肚。汗珠綴滿額頭。他陪丈夫去鄉(xiāng)上檢查,醫(yī)生回,慢性胃炎。
每天一服中藥,如山里不疾不徐的日子,人就這樣將息著。
新奎的疼痛在加劇。后來,山塆里,誰家都能聽見新奎在床榻上的呻吟聲。三個(gè)女兒分別在上海和四川的廣元、巴中打工,淳英給遠(yuǎn)在上海做工的大女兒玉瓊打去電話。
后來,新奎被送往縣城醫(yī)院復(fù)查,診斷結(jié)果,肝硬化。
經(jīng)過長長一年多的治療,新奎最終還是走了。走在第三個(gè)年頭的初春。
這個(gè)小家如果沒有那些個(gè)病魔作祟,土屋里的日子當(dāng)是如意吉祥的。但是淳英的家遇上了,他年邁的公公和婆婆,彼時(shí),都因病抱憾而去。
給新奎燒“三七”那日,那個(gè)黃昏,淳英獨(dú)自一人上山。是不是心事重重,新奎葬在高高的山腰上,燒完紙下山的路上,一截樹枝攔路,她被拌了一下,竟一頭栽在了地上。
人如中魔咒,她就那樣倚靠著濕漉漉山石樹叢而坐,動彈不得。
她八十三歲的娘家母親第二天叫來了醫(yī)生上門,她被告之,肋骨多處骨折。
一年后,淳英在上海做工的大女兒玉瓊又被查出肝病。
所有的劫難對于這個(gè)只剩下女人的家庭而言,仿佛來得太急太快。
玉瓊做手術(shù)那日,從廣元和巴中趕去上海的玉瓊的兩個(gè)妹妹,撲通一下,徑直跪在了那位手術(shù)醫(yī)生面前。但醫(yī)生打開玉瓊的腹腔后,未敢去觸碰那個(gè)“瘤”,最終縫合上了。
在四川,在秦巴山脈深處的這一處農(nóng)舍里,那些日子里,淳英淚如雨下。她的娘家母親那日再度從河壩那邊上山來,老母嘆,“我都八十多歲人了,老天爺要帶就把我?guī)ё甙桑盐业膶O女,留下!”
回家后的頭一天,淳英記得,母親下田割了谷子。那個(gè)上午,母親曬好谷子,做好午飯,手起手落端碗吃飯的剎那,她倒在了地上。
突發(fā)腦溢血。老母從發(fā)病到離世,僅十五天。
但老天爺并未順?biāo)爝@位八旬老婦的心意,她的孫女依舊病著,孫女與病魔拉鋸抗?fàn)幦缃褚讶哪辍I虾4蚬な陻€下錢在廣元置下的房,賣了。前后八次手術(shù)引流腹水,如今,她的孫女玉瓊的腹部,傷痕滿布。
避世而居,不諳人間事,晚年的淳英如今仿佛大夢方醒,淳英沒有購買“農(nóng)保”。而一戶一個(gè)名額的“低保”資格,她又讓位給了急需用錢、病中的玉瓊。也就是說,每個(gè)月,走過一個(gè)多甲子的淳英不似其他山村里的老人,她沒有分文現(xiàn)金收入。
老伴走了,兩個(gè)小女遠(yuǎn)嫁戶口被遷走,淳英、玉瓊,以及玉瓊丈夫和女兒,一家四口人的幾畝田地,是老人淳英晚年每日每時(shí)生活意義的全部。
此外老人所養(yǎng)的一頭豬,五只老鴨,還有十五只小鴨,這些,成了這位山里母親經(jīng)濟(jì)來源的全部依托。
淳英不愿跟孩子們?nèi)コ抢锒热眨故菐讉€(gè)孩子 在城里吃的米和油,差不多都源自淳英之手,源自那幾畝良田。淳英悉心侍弄著那些土地,那是一位山里母親的另一種“盼頭”。我去的頭一天,據(jù)說淳英正好托鎮(zhèn)上的長途車司機(jī),給她在廣元治病的女兒玉瓊捎去了二十斤米、一壺油,還有一百個(gè)鴨蛋和一只老鴨。
山里人過日子,地里有嘴里就有,錢,孩子們可以自己去想辦法,這位個(gè)子不足一米五高的母親所愁的是:可還有回天之藥,可救她的玉瓊的命?
“我這一世,連螞蟻都不踩的人……”
曬壩里,穿得整整潔潔的淳英,用生滿老繭的一只手去拭淚,而另一只眼里的淚滴,又盈出眼簾。
二
每人六元錢,村里幾十個(gè)人包下了一輛解放牌敞篷汽車。早春曉風(fēng)刺骨,但擠在人叢中的少年勇益,他并不覺得冷。
從白驛鎮(zhèn),過蒼溪,到廣元,少年乘了大半日的車。車到廣元后他與兄長方知,開往河北的列車,所有車次的票早已售罄。三個(gè)少年——勇益、勇益的哥哥,還有勇益的一位同學(xué),所帶干糧悉數(shù)吃完,他們索性睡覺,展開行李,躺在露天的站臺上睡。
被困三天,第四天他們終于上了車。購得站票的他們,選擇了廁所旁的過道而坐。他們需要衛(wèi)生間里的那一股涓涓細(xì)水,維持生命。
餓了整整六日,到達(dá)河北那晚,磚廠的伙計(jì)做了一大鍋面片,須臾之間他們給吃了個(gè)精光。三個(gè)少年一直睡到次日日落時(shí)分才醒來。
那時(shí)的勇益想到的是他于十二歲時(shí)寫下的一篇作文,“我的媽媽”。老師念給全班同學(xué)聽——媽媽在他七歲時(shí)過世了,九歲的他,那年終于有了人生的第一雙鞋。那是他的奶奶找本隊(duì)的人要來的一雙鞋……記事起,媽媽總是病懨懨……
是什么因緣讓勇益邁出了打工這一步?繼母?擔(dān)心父親兩頭為難?還是家窮,只想跟著哥哥走出去?
那一年,1990年,白驛鎮(zhèn)岫云村輟學(xué)的少年陳勇益,十六歲。
“童工”陳勇益,在這家民營磚廠所做的工作是運(yùn)磚。用手推車運(yùn)送磚。四五百米不等的一段路,他來回運(yùn)送。每趟5分錢。
這工作,少年最沒有把握的事,是初春那半尺深的雪,車輪碾在上面,夢幻般纏綿,使不上勁。
少年年末回到家,他帶回了現(xiàn)金200多元。
此后的歲月少年一路打工,從少年打到了中年。前后二十余載。文化不高,漂泊異鄉(xiāng)的勇益最難忘的是那一回。
“人進(jìn)磚廠,牛進(jìn)磨房”。那年出門前,他的哥哥與他商量,聽說煤礦掙錢多,一起去山西挖煤吧。他們買下了去山西的車票。
煤礦在山里,山上沒有生活用水,得由毛驢運(yùn)水上去。初來乍到,那晚兄弟倆站在煤窯洞口,沒走幾步路,再也不敢前行了。“尺八煤”,即最高處約八十厘米高的煤窯,從里出來的人,除了眼與牙雪一樣白,渾身漆黑。
夜半,兄弟倆起身逃跑。跑出約兩里地時(shí),后面有人追來了。他們翻山越嶺,往人跡罕至的地方跑,往深山溝里藏,顛沛了三天三夜,方才脫險(xiǎn)。
最后一次打工,是2014年在新疆。勇益獨(dú)自乘火車去。一下火車,四下戒嚴(yán)。后來知道,他們的車次與新疆烏魯木齊火車站“暴恐案”,從時(shí)間來看,擦身而過。
被囿于工地,不能出入,四十一歲的勇益那時(shí)躺在工棚里反復(fù)自問:為什么要出來?如今在外,活難找,薪難討,背井離鄉(xiāng),流離……流離……不出來,真的,不行嗎?
為什么要出來?!
三
八零后大學(xué)生李君,從2008年開始,就思考著他的小舅舅陳勇益六年后才開始問天的問題。
蒼溪距地震極重災(zāi)區(qū)廣元青川縣不遠(yuǎn),2008年“5·12”地震那天,李君從那一刻開始到晚上,一直給家里撥電話。無法接通。夜里,終于聯(lián)系上母親,母親的第一句話是,“要死,我們一家人,一定要死在一起!”
以志愿者的身份,李君從成都星夜兼程往家鄉(xiāng)往大山里趕。這一趟回家,他至今未“返”。
大山里出一名大學(xué)生不易。
上世紀(jì)的90年代初,山里的孩子,仍舊在為著每學(xué)年并不多的幾元學(xué)雜費(fèi)煩惱。交不上學(xué)費(fèi),老師會讓那些學(xué)生站著聽課。小李君就那樣,常常孤零零站在自己的課桌前。
上學(xué)放學(xué)路上,大眼睛圓臉的男孩李君總一邊走一邊哭。那時(shí)節(jié),他聽見媽媽講得最多的一句話是,“等賣了豬,媽給你交學(xué)費(fèi)。”
男孩的媽媽后來去集市上擺地?cái)偂7陥觯膵寢尠褟目h里進(jìn)來的針頭線腦日用百貨,列在街頭。那日,李君看中了別家地?cái)偵系囊患A克,八塊錢。他去找媽媽。媽媽自是不舍得錢。李君從場頭哭到場尾,那天他的媽媽也來了氣,追打他,從場頭打到場尾。
更小時(shí),家里修房子,請來人燒窯,兩斤肉要待兩天的客。是不是知道無望,小李君站在院子里抽噎跌足,“老子要吃肉,老子要吃肉……”
憤怒的“老子”沒能如愿。
去成都電子科技大學(xué)報(bào)到那天,他的母親也是第一次上成都。大學(xué)在成都建設(shè)路附近,母子倆站在建設(shè)路邊問道“建設(shè)路”,一位三輪車夫走過來,拉著他母子跑了一會又回到了原地不遠(yuǎn)處。李君的母親下車后哭了。不僅僅是為了那三元錢的人力車費(fèi)。
那時(shí)的李君只有一個(gè)想法,留在城里,成為這座大城市的主人。
與李君當(dāng)年一起打拼的大學(xué)同學(xué)舒義,如今已是一家即將上市的公司的老板。2008年,李君辭別好友舒義,回到了家鄉(xiāng)岫云村。那天他徑直去找到村主任侯俊益。他問侯叔,我怎樣才能留下來,同時(shí),能夠?yàn)榧亦l(xiāng)做點(diǎn)事。
他侯叔使出一計(jì),先做村主任助理,然后參加一年后的村支書選舉。
全國最小的“官”,而且是這個(gè)小“官”的助理,拿
著這張“令牌”,年輕人李君自費(fèi)出發(fā)了。
他去名噪一時(shí)的彭州市寶山村取經(jīng),村支書賈正方慷慨捐資10萬元,以資助岫云村的道路建設(shè)。蒼溪縣慈善家地產(chǎn)商馮文忠后又捐助了20萬元。至此,遙遠(yuǎn)的小山村岫云村,有了那條如錦似帛繚繞叢山中的水泥路。
再之后,村民小組的“組”級公路,也先后貫通。
岫云村村黨支部換屆那日,25歲奶氣未脫的李君站在臺上,全村27名黨員,他得24票。
2010年后,靜心下來的村支書李君開始和“班子”成員思考另一個(gè)大問題。農(nóng)村如今最嚴(yán)峻的問題是鄉(xiāng)里沒有人,勞動力大量外出,家里留下老人、孩子和婦女,他們怎么辦?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怎樣突圍?
那日一位看著他長大的老人取笑他,“你們干部讓我們?nèi)プ龅模覀兤粫プ觥保斜臼拢盐壹茵B(yǎng)的雞呀鴨呀豬肉呀,給我變成錢!
“鄉(xiāng)村經(jīng)濟(jì)”的個(gè)體性、它的“小”,小到費(fèi)孝通時(shí)代,費(fèi)母當(dāng)年出嫁時(shí),他母親的母親陪嫁給女兒的是一臺織布機(jī)。以個(gè)體以家庭為單位,小農(nóng)經(jīng)濟(jì)小規(guī)模經(jīng)營,點(diǎn)點(diǎn)滴滴的家庭細(xì)小經(jīng)濟(jì)補(bǔ)給,構(gòu)成了上世紀(jì)一輩又一輩人,鄉(xiāng)村自然經(jīng)濟(jì)的基礎(chǔ)。
岫云村與中國大多數(shù)的鄉(xiāng)村一樣,“規(guī)模化”種植過各種果樹,經(jīng)濟(jì)作物,但最終這些規(guī)模化效應(yīng)給鄉(xiāng)村釀成苦果。曾經(jīng)有村民把一種叫 “脆香甜”的柑子,一背一背給村主任侯俊益家門前壘了一地。
李君悄悄回到了成都,他念大學(xué)的地方。他從成都請回來了攝影師,給村里的每一個(gè)老幼拍照。他要給城里人在鄉(xiāng)下找個(gè)“親戚”——讓城里人吃到最放心,最天然的綠色食品。同時(shí),給他家鄉(xiāng)的父老鄉(xiāng)親——那些老人和婦女,給暮氣沉沉的山村覓一條出路。
幾十個(gè)笑靨如花的老人、婦女,還有留守于家的孩子們的彩色照片,印刷在了一張鮮艷瑰麗的宣傳單上。李君記得拍照那天,山里的人們奔走相告,許多老人一世沒出過大山,過世時(shí),在子女們返家合影的照片上“挖”出一個(gè)頭像,了事。攝影師進(jìn)山了,有講究的老人蘸清水梳頭,梳了又梳。衣角整了又整。
李君拿著這些宣傳單開始去成都為他們尋“親”。
機(jī)關(guān)單位是進(jìn)不去的,他去民營公司。公司一般設(shè)四道崗,第一道崗是大門,第二道是辦公樓門,第三道是部門經(jīng)理門,最后一道,才是他要找的“尋親”對象,總經(jīng)理的門。但是每一道門,都不是為他而開的,無論機(jī)關(guān)還是民營公司,所有的大門外都貼著紙條,“推銷人員禁止入內(nèi)”。
李君站在門口佯裝等人,員工刷卡進(jìn)門的剎那,他瞄準(zhǔn)機(jī)會,尾隨而入。一道一道“防線”,他就這樣突破。
好幾次,總經(jīng)理靠在老板椅上,斜睨他。李君跟對方說,“我不是乞丐,我的父老鄉(xiāng)親們也不是,我是村支書。”
許多時(shí)候,話說不下去了,他垂目端詳宣傳單上面的那一張張他熟悉的臉。
蒼溪,國家級貧困縣,境內(nèi)的岫云村,耕地659畝,荒地占240畝。全村944人,400多強(qiáng)勞動力外出,村里如今剩下,老人300多人,兒童70多人,婦女幾十人……這是這個(gè)村莊的現(xiàn)狀,也是大多數(shù)中國農(nóng)村的一個(gè)縮影。
他抬起頭來繼續(xù)迎戰(zhàn)另一道“防線”,現(xiàn)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彼此信任。
2013年4月,“合村并校”關(guān)張多年,雜草叢生的岫云村小學(xué)的大門再度被打開。全村老少都來了。他們來到這里歡迎來自成都、重慶、綿陽還有樂山的兩大車“親人”。這一天,遠(yuǎn)方親人們一下子在這里簽訂了約53萬元、由村里的老人和婦女們 “生產(chǎn)”的訂單。
農(nóng)婦鄭慧家用糧食和青菜青草飼養(yǎng)的生態(tài)豬,那時(shí)當(dāng)?shù)厥袌鰞r(jià)行情1000多元一頭,遠(yuǎn)方親人“以購代捐”,給出了每頭3000元的愛心價(jià)。村民一組小組長李雪云老人家的生態(tài)豬,也以同樣價(jià)格成交。
村主任侯俊益算過一筆賬,53萬元的訂單,按岫云村留守在家、尚有“生產(chǎn)”能力的186個(gè)老人和幾十個(gè)婦女計(jì),可實(shí)現(xiàn)年人均增收2000多元。
“省親”現(xiàn)場,28歲的李君,記得自己只對他的父老鄉(xiāng)親說了一句話,“貧窮不是別人‘施舍我們的理由,我們有手有腳,我們要有尊嚴(yán)地,活著!”
四
大山里,每一位耄耋老人,每一位背著重?fù)?dān)蹣跚行走的婦女,都是“遠(yuǎn)山結(jié)親”計(jì)劃里的生產(chǎn)主體,一個(gè)獨(dú)立“生產(chǎn)作坊”的有價(jià)值的工人。
“作坊”大了,對接每一個(gè)“作坊”的端口,變成了岫云村“農(nóng)村合作社”。如今,有了民間資本的進(jìn)入,“合作社”升級成了 “電商”,由公司化運(yùn)作。
電商的末梢,一端在鄉(xiāng)村,一端接都市。城市客戶如今直逼5000家,簽約生產(chǎn)合同的鄉(xiāng)村“作坊”,目前已上千戶。
今年30歲的李君未曾想過,自己有一天會辦起如此規(guī)模龐大的“養(yǎng)殖場”,在沒有半寸工廠廠房的前提下。
李君愛發(fā)微信,他的“朋友圈”里,轉(zhuǎn)發(fā)有這樣的內(nèi)容:《農(nóng)業(yè)資本化威脅中國》。
文章講述香港理工大學(xué)學(xué)者嚴(yán)海蓉和四名青年學(xué)者在三農(nóng)問題上,發(fā)出的與“主流”不同的聲音。中國農(nóng)業(yè)正在經(jīng)歷前所未有的變遷,學(xué)者們認(rèn)為,城市工業(yè)資本大舉進(jìn)入農(nóng)村,是與廣大農(nóng)民爭奪利益,而不是形成互補(bǔ),這是當(dāng)前三農(nóng)問題面臨的新挑戰(zhàn)。
在這群年輕的學(xué)者們看來,小農(nóng)經(jīng)濟(jì),小規(guī)模經(jīng)營,仍舊是我國當(dāng)前農(nóng)村的經(jīng)濟(jì)主體。
他愛在“朋友圈”里發(fā)感慨:
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曬家鄉(xiāng)風(fēng)光)。
九十歲的老人(一老人田間勞作背影)
老了就回農(nóng)村吧!(點(diǎn)評轉(zhuǎn)發(fā)文章《揭示4600 萬老年農(nóng)民工生存現(xiàn)狀,夾縫中的苦與累》)
……
李君的語速不算快,但在交談中,信息量大亮點(diǎn)多。那晚在他家鄉(xiāng)小鎮(zhèn)的一家客棧里聊天,我不得不收起筆帽開啟錄音:
“跟Uber經(jīng)濟(jì)一樣,利用互聯(lián)網(wǎng)來解決市場剛需。Uber是將民間閑余的私家車輛,分享于社會。我們現(xiàn)在做的,正是在利用這種‘分享經(jīng)濟(jì)模式,來解決生態(tài)農(nóng)產(chǎn)品的賣出難問題,繼而解決生態(tài)農(nóng)業(yè)的剛需問題。”
“互聯(lián)網(wǎng)的出現(xiàn),不是‘消滅農(nóng)民,而是保障最末端農(nóng)民利益,讓農(nóng)民利益更大化……”
“互聯(lián)網(wǎng)只是工具……”
落在實(shí)處,我可不可以這樣來理解淳英老人,公司數(shù)月前簽約的這位鄉(xiāng)村“工人”的利益。
公司目前給老人簽訂的“合同”,事關(guān)今年和明年。今年淳英家愿意出售的只有3只老鴨,每只按80元計(jì),如果立即出售,老人足不出戶,能收成240元。
明年,老人在喂養(yǎng)自家“年豬”的同時(shí),完成“合同”里一頭生態(tài)豬的生產(chǎn)任務(wù)。合同價(jià),這筆收入2000元。除去現(xiàn)金成本購買豬仔420元,十個(gè)月需要喂養(yǎng)玉米500斤、黃豆50斤、糠500斤,以及田間地頭的草料等,因這些糧食都是自產(chǎn),如不納入現(xiàn)金成本核算,按村主任侯俊益的計(jì)算“公式”,淳英的純收入,可在1580元。
侯主任的算盤也敲過另一筆賬,如喂養(yǎng)飼料豬,生長周期雖短,一年理論上可出欄兩槽,但除去飼料費(fèi)用以及市場銷售價(jià)格因素,兩槽豬收益相加,與一頭生態(tài)豬的價(jià),相差無幾。
年收入1580元,平均每月約130元,這差不多是一個(gè)農(nóng)村老人一個(gè)月的“農(nóng)保”,加上一個(gè)月“低保”的津貼。也是一位平凡老農(nóng)人的“底氣”,家底。
五
白云深處的岫云村,于梁上俯瞰,童話般旖旎。山影依稀,魚塘恬靜。農(nóng)舍,灰瓦白墻,如玉似佩般點(diǎn)染。李君說,“可別看表面,其實(shí),他們比任何一個(gè)地方的農(nóng)民更貧困。災(zāi)后重建,國家補(bǔ)助建房款,這是好事,可相互攀比家家蓋起了小樓房,幾輩人的錢都用進(jìn)去了,因此,他們負(fù)債更多。”
農(nóng)村勞動力“回流”,岫云村,任重道遠(yuǎn)!
“遠(yuǎn)山結(jié)親”“讓留守的人們有尊嚴(yán)地生活”,幻若一盞“燈”。
這“燈”的意義,我理解——
老有所為。
倦鳥知返。年逾不惑的李君的小舅舅陳勇益,去年已返鄉(xiāng)就業(yè)。如今他是“遠(yuǎn)山結(jié)親”計(jì)劃團(tuán)隊(duì)的一員,月薪2000元。每天,他穿戴如都市“白領(lǐng)”,走村串戶,與他熟悉的土地上的人們用鄉(xiāng)音交談,簽訂“生產(chǎn)”合同。“遠(yuǎn)山結(jié)親”創(chuàng)意在鄉(xiāng)間生根,如今這一模式已在岫云村以外的幾個(gè)村莊拓展。
三位應(yīng)屆畢業(yè)大學(xué)生來鄉(xiāng)下“打工”:
李軍之:畢業(yè)于四川理工學(xué)院,人力資源管理專業(yè);
向文科:畢業(yè)于西南科技大學(xué),工程力學(xué)專業(yè);
李釘生:畢業(yè)于四川理工學(xué)院,生物技術(shù)與應(yīng)用專業(yè)。
農(nóng)業(yè)問題,中國的現(xiàn)實(shí)問題,誰能說學(xué)子們又不是在困厄之中擊石取火,推進(jìn)鄉(xiāng)村文明進(jìn)程的薪火傳遞者?
那日,勇益去回訪他的簽約農(nóng)戶、月山村的淳英,他帶上了我。淳英是勇益及同事上門去簽訂的第475單生產(chǎn)合同,如今公司簽約農(nóng)戶已1100多戶。
水塘邊,我、李君、勇益,我們站在那里。淳英早上給鴨子用半熟的米飯拌的糠食還在那里。我目睹,淳英家?guī)字灰岩粴q半的老鴨在水面,破冰似倏地游出了幾縷,銀絲。
山光日影,天地,靜得入冥。
六
去白驛鎮(zhèn)趕集,那日,白驛鎮(zhèn)郵政局支局長胡澤勇,帶我去看位于小鎮(zhèn)老街深處的老郵政局舊址。他講,八九十年代,這個(gè)鎮(zhèn),在外打工的人郵回來的錢,全年二三十萬元。那時(shí)候5000元,就算大額存款。而去年(2014年),鎮(zhèn)郵政局收到的款額,已達(dá)一個(gè)多億。
數(shù)字改變著鄉(xiāng)村,改變著鄉(xiāng)土中國,而這些驚人的數(shù)字,又消融在了鄉(xiāng)村的哪里?建房、還貸、婚喪嫁娶、醫(yī)療救急、孩子教育、人情支應(yīng)、創(chuàng)業(yè)投資,還是別的什么地方?
中國鄉(xiāng)村目前最大的問題是什么?
以城市資本為主導(dǎo)的農(nóng)業(yè)規(guī)模化,可是鄉(xiāng)村的最佳出路?資本化農(nóng)業(yè),誰是利益主體?
如何摒棄化工農(nóng)業(yè)?
勞動力外流,當(dāng)前農(nóng)村“結(jié)構(gòu)性”力量,在哪里?
打工者“回流”,他們能做什么?
留守老人,留守兒童問題,老無所養(yǎng),少無所教(家庭教育),他們的權(quán)益誰來維護(hù)?
“換工互助”時(shí)代的鄉(xiāng)村良風(fēng)美德,可有溯回的那一天?
無數(shù)空村,誰是它們未來的主人?
……
差不多在近一年的時(shí)間里,我在我熱愛的土地上進(jìn)行著精神行走,我總?cè)栁宜姷降睦先恕D女、孩子、村主任,老支書,以及路邊、田間地里的百靈,哪怕乞丐。今天,我也問眼前、不時(shí)站在扶貧勵(lì)志領(lǐng)獎(jiǎng)臺上,趑趑趄趄跌跌撞撞探出一條“小生產(chǎn)+大合作”路子的李君。
因?yàn)橐粫r(shí)無答,我如棄嬰,合目蜷縮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