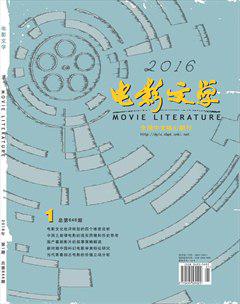《為奴十二年》從文字到影像的呈現
程惠敏
[摘要]史蒂夫·麥奎因執導的《為奴十二年》,根據所羅門·諾瑟普的同名自傳體小說改編。影片不僅獲得學院派的青睞,同時也以其靈性獲得觀眾的好評,絕非僅僅是因為其題材上的“政治正確”以及大牌配角的保駕護航。麥奎因將電影拍攝成了一部美麗凄楚的圖像傳記,為公民的自由和權利發出了自己的吶喊。文章從影片的敘事方式、歌謠對情感的烘托、特寫與虛焦鏡頭三個方面,分析《為奴十二年》從文字到影像的呈現方式。
[關鍵詞]《為奴十二年》;電影;史蒂夫·麥奎因;小說;所羅門·諾瑟普
《為奴十二年》(Twelve years a slave)原是所羅門·諾瑟普(1808—1864)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所撰寫的一部小說。諾瑟普本是一個擁有自由身份的非裔美國人,有著幸福的家庭,然而不幸的是,1841年他在紐約被人綁架并販賣到還存在奴隸制的南方,成為一名悲慘的奴隸。在經歷了12年的磨難之后,他成功逃脫并成為一個堅定的廢奴主義者。隨后他出版了自傳體小說《為奴十二年》,小說一經面世便在美國社會引起了轟動。2013年,同為黑人的英國導演,曾經以《饑餓》《羞恥》而成名的史蒂夫·麥奎因(Steve McQueen,1969—)將這個故事搬上了銀幕。影片堪稱一曲獻給逆境者的挽歌,該片不但吸引了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邁克爾·法斯賓德、布拉德·皮特等一眾影星加盟,還獲得了第86屆奧斯卡最佳影片獎。[1]麥奎因被譽為是繼史派克·李之后最有希望的黑人導演,他本身也有著對黑奴的深切同情。導演完成了《為奴十二年》從文字到影像的成功轉換,是傳記片拍攝及相關理論研究的一個較好的范例。
一、敘事方式
《為奴十二年》并不是完全按照線性時間順序展開的,它采取的是一種半倒敘半插敘的方式,這一點與小說有著微妙的區別。影片的一開頭便給了奴隸們勞作的田地一個特寫,并且展現了白人對奴隸們的呵斥以及黑奴們毫無生氣的麻木傾聽。并且,類似這樣的鏡頭隨著影片的進行反復地出現,進一步強調所羅門承受苦難的重復性。這里實際上是兩條故事線的第一個交會點。故事的一條時間線是男主人公所羅門的回憶,而另一條線索則是影片的主干,那便是所羅門在美國南部成為奴隸的12年光陰。這種敘述方式的好處,就在于能夠對觀眾起到一種情節提示的作用,使得劇情在兩個多小時的電影中處處形成呼應,不顯得松散。兩條線索之間以蒙太奇的手法進行剪輯,它們的切換并不是隨意的,往往在切換的對比之中,能表現出影片的時代背景、奴隸生活氛圍的壓抑以及奴隸的商品屬性。如,在影片開頭,所羅門與其他黑奴一起擠在狹小的房間中休息,身邊的女奴懇求所羅門幫助她自慰,此時影片又切換到所羅門的回憶,在景深控制等方面有著一種畫面上的相似。在他的回憶之中,他與妻子一同躺在床上親密低語。對于所羅門來說,與女奴互相安慰原本并不是他道德范圍內的事情,然而此刻的他已經失去了尊嚴和自由,甚至失去了自己真正的名字。他身處這種人剝削人、罪惡的黑暗制度下,曾經的道德約束也只能被湮滅。場景雖然似曾相識,但是情境意境迥然不同,這個切換就明確地展現出所羅門對于自由的渴望以及對家庭溫暖的追憶。
此外,平心而論,從《饑餓》《羞恥》再到《為奴十二年》,麥奎因在電影創作上的個人特色正在逐漸減少,而對主流審美的迎合則越來越多,以至于《為奴十二年》整體上是一部導演個人風格并不明顯的電影。但是麥奎因仍然在這部電影中保留了他的“個人標簽”,那就是長鏡頭的運用。[2]并且,這種長鏡頭有著特殊的意義。如,當所羅門因為毆打了提比斯而被吊起來,只有腳尖能接觸地上的一點兒爛泥時,麥奎因采用了一個三分鐘的長鏡頭。在這三分鐘內,所羅門身后的黑人奴隸們置若罔聞,專心地做著自己的工作。為了自己的生存,他們不敢過來解下所羅門,而更為殘忍的是,甚至還有幾個小孩子在一旁愉快地玩耍,這無疑是一種諷刺。只有一個心存不忍的女奴拿了一點兒水給所羅門喝。麥奎因用這個長鏡頭暗示了,電影并不僅僅對白人奴隸主進行批判,任何奴隸制度的根源都離不開民眾自身根深蒂固的奴性。美國奴隸制的最終被推翻并非全是白人的恩賜,也源于黑人的反抗。相對的,南方蓄奴傳統的長久存在,也與黑人自身的不敢反抗或反抗不夠徹底有著不可回避的關系。在所羅門·諾瑟普的原著之中,他曾經寫過自己的真實想法:“南方的奴隸,吃主人的,穿主人的,挨主人的鞭子,凡此種種,但只要能受到主人的庇護,就比北方自由的黑人更幸福些。”出身于北方,有文化且有著自由身份的所羅門尚且如此想,那么那些始終沒有品嘗過自由滋味的南方奴隸的內心也就可想而知了。電影中并沒有將小說中的這段話直接表現出來,但這并不意味著麥奎因放棄了對奴性的批判。在影片結束前,麥奎因又使用了一次長鏡頭對好不容易回到家中的所羅門進行面部特寫,此時的所羅門眼含熱淚,眼前的家早已物是人非。麥奎因希望能表現出所羅門在12年的苦難之中,他的希望以及對他人的信任已經一次次地被粉碎,即使重獲自由,他也有著一種因為命運不確定的彷徨。在這個長鏡頭里,所羅門基本上沉浸在自我意識之中,與小說不同的是,他的心理活動成為留給觀眾想象的留白,但是觀眾依然能夠捕捉到所羅門復雜和難以名狀的心情。
二、歌謠對情感的烘托
《為奴十二年》本身就是一個極難改編的故事。首先,它缺乏一定的懸念。即使是沒有接觸過原著的觀眾,也多半能夠猜到故事的結尾,主人公一定會得救而脫離這種暗無天日的奴隸生活。導演如果嚴格地照搬原著,一不小心就會使電影成為乏味的流水賬。其次,它缺乏高潮。與昆汀·塔倫蒂諾的《被解救的姜戈》不同,《為奴十二年》由于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真實感是麥奎因首要考慮的問題,這也就導致了其戲劇沖突感難免比前者要稍弱一籌。為此,麥奎因選擇采用另一種方式來烘托影片中的氣氛和情感,以彌補情節略顯平淡的不足,那就是穿插在劇情之中的歌謠。在很多場景之中,歌謠甚至被麥奎因當成了電影配樂來使用。
首先,白人歌謠的運用有效地烘托出影片的情感氛圍。在影片開場不久,監工、木匠約翰·提比斯與黑奴們第一次見面,他在訓誡了黑奴一通之后,就以得意的口吻唱起了一首歌。歌詞中全部是對黑奴的戲謔和諷刺,提比斯用這種方式侮辱黑人,如譴責他們又蠢又喜歡偷東西等,無疑是為了在首次見面就給對方一個下馬威。這個人物本身也不過是一個手藝粗糙的木匠,雖然沒有威嚴感(如在后面他就曾被所羅門痛打),但又想在黑奴面前樹立一種高高在上的形象,讓黑奴們稱呼他為主人,因此就選擇了唱歌,并且強迫黑奴們為他鼓掌、打節拍這種蹩腳的侮辱方式。這首歌謠在影片之中持續時間很長,提比斯的口吻也越來越囂張。此時的鏡頭則在埋頭砍樹的黑奴與越唱越開心的提比斯之間來回切換,原本的拍手聲為伐木聲所取代。原本是小提琴家的所羅門感到忍無可忍,然而與其他黑奴的區別只是在于他不滿地抬了一下頭,就不得不繼續勞作。甚至在福特先生念圣經的場景中,提比斯歌謠的畫外音也沒有停止。福特先生在電影中是一個善良的奴隸主形象,他對黑奴有著一定程度的同情。他因為所羅門會拉小提琴而對他高看一眼,但是當所羅門與提比斯的矛盾爆發之后,福特先生并沒有秉公判斷,而是抱著一種息事寧人的態度,將所羅門賣給了有“奴隸終結者”之稱的更為殘酷的奴隸主。因此,在他宣道時所念的“我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等《圣經》上的語言,配上提比斯侮辱性的歌謠時,無疑是對福特先生這個“圣人”虛偽形象的一種揭露。在提比斯的演唱之中,電影之前一直壓抑著的情緒以及對奴隸制赤裸裸的揭露態度就體現了出來。
其次,黑人歌謠的運用是黑奴情緒的宣泄。影片中,一個老黑奴因過度勞累而死在田地之中,黑人們給他舉行了簡單的葬禮。在一排歪歪扭扭的十字架前,一群黑人在女奴的引領下為其唱歌送葬。原本所羅門并沒有跟唱,然而隨著被歌聲感染,他開始難以克制自己的情緒而跟著高聲歌唱。對于所羅門來說,這是一種被壓抑了太久之后的發泄。在從自由人一夜之間變為奴隸時,他還有著憤怒與反抗之心。只是在奴隸販子的痛打與折磨之下,為了求生,他不得不屈辱地承認自己生而為奴。在整個美國南方的大環境之下,他確實也無路可逃。盡管他每日都生不如死,但為了有朝一日能夠恢復自由身,重新回到家人身邊,他不得不忍辱負重。在同伴死時,所羅門感到物傷其類,對自己是否還能活著回去,自己的忍耐是否值得感到了困惑,這樣悲苦的情緒只能在歌聲之中得到釋放。一言以蔽之,歌謠成為強化戲劇元素,對觀眾產生明確情緒影響的重要媒介。
三、特寫與虛焦鏡頭
電影與小說的區別就在于表現形式。在《為奴十二年》之中,麥奎因采取了豐富的造型畫面表現方式。其中對于黑人女奴帕茜這一重要的角色,就采用了特寫與虛焦鏡頭來豐富這一人物形象。特寫鏡頭的使用能夠表現出人物細微的、瞬間的細部特征,對于觀眾來說是視距最近的畫面,隱含了導演一種強烈的主觀感情和價值判斷。[3]在帕茜被鞭打的一場戲中,因為帕茜表示肖太太給了她肥皂,讓她終于可以洗澡而轉投肖太太門下(女主人故意不讓帕茜洗澡,以免她“勾引”男主人),遭到了主人艾普斯的毒打。這是一段讓觀眾的絕望心理層層遞進的鏡頭。艾普斯先是逼迫所羅門抽打帕茜,所羅門一開始不愿意出全力而遭到了艾普斯的威脅,所羅門不得不猛烈鞭打帕茜,甚至希望能夠幫助她實現她曾經懇求的“殺了她”的愿望。而已經喪心病狂的艾普斯索性奪過鞭子親自鞭笞帕茜,帕茜的后背甚至隨著每一下鞭打而濺起血霧。麥奎因先是在這里給了帕茜已經皮開肉綻的后背一個特寫鏡頭,伴隨著帕茜深深的悲鳴,這已經使觀眾備感不忍。在帕茜癱倒被拖走之后,麥奎因再次給了落在地上的已經被觀眾所遺忘的小小的肥皂一個特寫。如果說前一個特寫制造的是一種視覺震驚效果,那么這個鏡頭則具有強烈的暗示與強調作用。帕茜遭受了一場如此慘絕人寰的鞭刑,起因僅僅是這塊并不起眼的肥皂,它看似無足輕重,卻是帕茜維護自身貞潔與艾普斯病態的控制欲矛盾的縮影。從這塊肥皂中體現出來的是一種讓人感到恐懼的荒謬。
而在影片的最后,所羅門獲救之后,他因為聽到了帕茜的呼喊而停下了登上馬車的腳步,與帕茜進行了一個最后的沉默的擁抱,才決絕地踏上了歸程。此時麥奎因對帕茜采用了一個一閃而過的虛焦的鏡頭。帕茜在與所羅門告別之后重重地昏倒在地上。僅這一個鏡頭,就表現出了帕茜內心的復雜情緒。她既為唯一的朋友重獲自由而感到高興,又有一種絕望的羨慕。因為她作為一個家生奴隸,是不可能有所羅門這樣的逃離機會的。在她今后的人生中,依然要每天面對著無窮無盡的恐懼與折磨,既要繼續做男主人的性奴,又要忍受女主人刻薄的挑釁和攻擊。這種虛焦鏡頭讓帕茜以一種模糊的方式離開了這部電影,而所羅門慢慢離去的馬車卻是清晰的,兩人的分道揚鑣一虛一實、涇渭分明。這也暗示了類似帕茜這種命運幾乎難以被改變的可悲女奴是黑奴中的大多數,而后人卻往往將目光留在所羅門這樣的幸運兒身上,沒有多少人能夠真正想得起帕茜這樣的最后有可能名字也不能留下來的卑微生命的苦難。
可以說,《為奴十二年》能夠在當年各大電影節頒獎季成為熱門,不僅獲得學院派的青睞,同時也以其靈性獲得觀眾的好評,絕非僅僅是因為其題材上的“政治正確”以及大牌配角的保駕護航。麥奎因在這部電影中充分展現了個人的才華,運用精妙復雜的視覺語言,歌謠的穿插以及演員精湛的、富有層次的表演,將電影拍攝成了一部美麗凄楚的圖像傳記,為公民的自由和權利發出了自己的吶喊。
[參考文獻]
[1]趙柔柔.《為奴十二載》:歷史魅影與現實危機[J].藝術評論,2014(05).
[2]李松睿.刻印在身體上的暴行——以史蒂夫·麥克奎因的電影《為奴十二載》為中心[J].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14(03).
[3]車濟民.特寫鏡頭的表現魅力[J].電視研究,20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