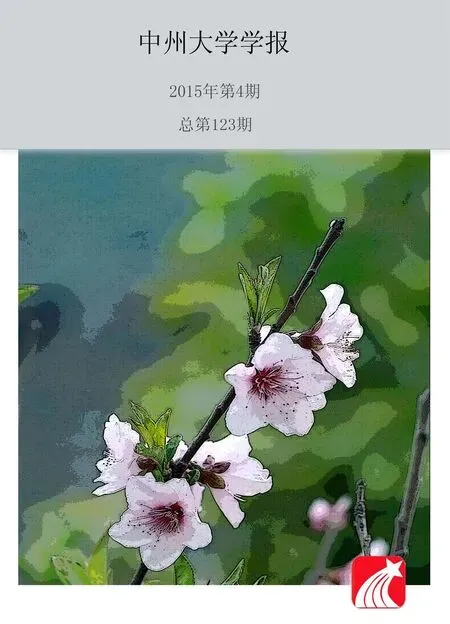“重寫文學史”和《今天》的相遇與重疊
“重寫文學史”和《今天》的相遇與重疊
劉忠
(上海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上海 200234)

摘要:提及“重寫文學史”,人們首先想到的是《上海文論》1988年第4期至1989年第6期開設的“重寫文學史”專欄,以及圍繞“要不要”重寫、“如何”重寫、“價值”何在等問題展開的論爭。其實,從1991至2001年間,遠在海外的《今天》接過這個旗號,把“重寫文學史”專欄薪火相傳了十年。如果把《上海文論》時期的“重寫”專欄稱為“重寫文學史”的上半場的話,那么《今天》時期的“重寫”專欄則是它的下半場。毫無疑問,無論是精彩度還是影響力,下半場都不及上半場。這之中,除了《今天》的“民刊”性質為“重寫”專欄罩上了一層非意識形態的神秘色彩之外,20世紀90年代以后文學史研究漸趨冷靜、理性,現代性反思之聲漸起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再就是《今天》與重寫文學史定位的抵牾和錯位。
關鍵詞:重寫文學史;《今天》;相遇;重疊
收稿日期:2015-07-10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1BZW101);上海市曙光計劃項目(10SG43);上海高校一流學科(B)建設計劃項目(12sg12)
作者簡介:劉忠(1971—),男,河南固始人,文學博士,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5.04.001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3715(2015)04-0001-08
Abstract:Referring to “Rewriting Literary History”, people firstly think of the “Rewriting Literary History” column of Shanghai literary theory from No.4 1988 to No.6 1989, and the debates on such issues as “whether or not” rewriting, “how” to rewrite and its “value”. Actually, from 1991 to 2001, Today far away from overseas took the banner and had the “Rewriting Literary History” column for ten years. If the rewriting column during the period of Shanghai literary theory is called the first half of “Rewriting Literary History”, the rewriting column of Today is its second half. Undoubtedly, the wonderful degree or influential power of the second half can not be compared with the first half. In addition to the privately-possessed nature of Today which covers a layer of ideology of mystery to rewriting column, researches on literary history have gradually become calmer and more rational since 1990s, and the gradually rising of modern reflection is also an important reason. Moreover, the contradictions and dislocation between Today and “Rewriting Literary History” column is another important reason.
提及“重寫文學史”,人們首先想到的是《上海文論》1988年第4期至1989年第6期開設的“重寫文學史”專欄,以及圍繞“要不要”重寫、“如何”重寫、“價值”何在等問題展開的論爭。其實,從1991至2001年間,遠在海外的《今天》接過這個旗號,把“重寫文學史”專欄薪火相傳了十年。
一、精彩不夠——重寫文學史的“下半場”
如果把《上海文論》時期的“重寫”專欄稱為重寫文學史的上半場的話,那么《今天》時期的“重寫”專欄則是它的下半場。毫無疑問,無論是精彩度還是影響力,下半場都不及上半場。何以如此?遠在海外,讀者和研究者很難及時知曉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今天》刊物的民間、同仁性質為“重寫”專欄罩上了一層非意識形態的神秘色彩;還有一個原因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文學史研究漸趨沉靜、理性,思潮、跟進式的“重寫熱”開始降溫,影響力大大減弱。事實上,《今天》“重寫文學史”專欄的尷尬從開設之初就顯現了出來。
首先,相左的意識形態取向不可回避。創辦于1978年12月的民刊《今天》,因為“告別過去、迎接未來”宣言的引領作用,在新時期思想史、文學史、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至今人們仍能如數家珍地列舉那些與《今天》有關的作家與作品,食指、北島、芒克、多多、舒婷、顧城、江河、楊煉、方含、嚴力……趙振開的小說《在廢墟上》《歸來的陌生人》,詩歌《回答》《一切》《宣告》《結局或開始》,食指的《相信未來》《命運》《瘋狗》《四點零八分的北京》,芒克的《天空》《十月的獻詩》,江河的《祖國啊,祖國》《星星變奏曲》,舒婷的《致橡樹》《中秋夜》……一份油印同人的文學刊物,從最初的張貼式發布到后來的郵寄發行,從1980年9月因“刊物未經注冊,不得出版”勒令停刊到1990年8月在挪威奧斯陸復刊,幾經沉浮和變遷,不變的是對文學的熱愛。
與主流意識形態相左是《今天》不容回避的取向,它帶給《今天》的不僅有“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批評,還有延續至今的言說禁忌。這一點,從重寫文學史口號提出者王曉明在其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的“前言”“后記”中絕口不提《今天》“重寫文學史”專欄的隱秘做法中,似乎可以找到草蛇灰線。他說:“有心的讀者可能還會注意到,本書較多地選收了一些在港臺、海外的學者的論文,這不僅因為他們的研究成果展示了他們極富特色的研究視角和方法,而且還因為他們的著述不容易被一般的讀者見到,他們的論文從選題到思想方法上都有其獨到之處,應該得到重視。”[1]388巧妙地回避了《今天》與《上海文論》“重寫文學史”專欄的續接關系,以及它在文學史研究領域的創新價值。
其次,傳播不暢、受眾面狹小是客觀事實。《今天》創刊之時,正值新時期改革開放之初,經歷“文革”的一代知識分子迫切需要一個表達自我的話語場,《今天》見證和言說了一代人的成長,他們在迷茫中尋找出路,在下沉中獲得力量,在集體失語中呼喊。自由、平等、真理、正義、理想、未來,這些閃光的詞匯曾經照亮了一代人的黑眼睛,影響波及文學、美術、電影、戲劇等多個領域,成為新時期先鋒文藝的開端。其后,經歷了停刊、自由化批判、同仁星散、遠走去國等風波,進入90年代,《今天》的影像越來越模糊,國內同時期讀者群的思索熱情漸趨冷卻,代表著叛逆、反抗的《今天》更多地留存在于人們的記憶中;文學熱點也由之前的傷痕、朦朧、反思、改革、尋根、先鋒、新寫實、新歷史、女性主義等“純文學”話題轉移至后現代主義、大眾文化、現代性、網絡文學等“泛文學”話題上,新成長起來的讀者更是“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了。不要說“重寫文學史”專欄,甚至《今天》復刊的消息也是知之甚少。何況從1990年夏季復刊至今,《今天》僅編輯部就幾經移址,挪威的奧斯陸、瑞典的斯德哥爾摩、美國紐約、洛杉磯、中國的香港,每到一處常常面臨嚴重的資金緊張和發行困境,國內市場因為種種原因未能得到開發,客觀上造成刊物傳播不暢、受眾面狹小,很多的研究者、專業人士都不知道《今天》有一個堅持十年之久的“重寫文學史”專欄,自然也不會把《今天》和《上海文論》的“重寫文學史”進行比較研究,尋繹它們的相同與相異。這既是對《今天》的不公,也給“重寫文學史”的全面研究造成了盲視。
最后,時過境遷,《今天》的反抗、先鋒姿態與國內文學史寫作的學科化走向明顯背離。經歷了90年代初“重寫文學史”的論爭與實踐,學者們發現僅僅在審美藝術和純文學視閾中對抗革命文學和政治話語,藉此實現文學與生活、文學史與文學的分離無異于緣木求魚,不僅不能很好地認識文學自身,而且容易滑向“審美—純文學”的單一、偏執泥沼,成為一種架空思想、政治、道德、倫理的“單向度”文學,限制了“重寫”的高度與深度,與既有文學史并無二致。于此,以“反思現代性”為突破口的文化研究恰逢其時地為文學史寫作擺脫“啟蒙與救亡”“政治與審美”“大眾化與化大眾”“官方與民間”的二元對立思維定勢提供了契機。90年代中后期開始,重寫文學史研究不再堅持異質化,而是在歷史語境和全球化秩序中尋找同質的可能性,整合文學史的社會、政治、思想、文化、審美、心理等質素,打通橫亙在文學史寫作中“審美主義”與“生活實踐”(包括政治革命、社會運動)之間人為的界墻,進而實現從“對抗”走向“和解”。很顯然,這種研究趨勢與《今天》的“重寫文學史”專欄貌合神離。“《今天》抗議和反抗的對象不僅是文學和藝術的體制,還包含著這些體制后面的制度安排和歷史含義”,“《今天》代表的寫作和學術性寫作之間,天然有一種不和諧,或者說敵對”等的價值取向從一開始就為國內學者的研究制造了觀念接受上的障礙。關于這一點,《今天》“重寫文學史”專欄主持人李陀本人有著清醒的認識,他說:“如果把八十年代至今的‘重寫’歷史拿來做一番比照,我想文學史寫作如何受制于體制,可以看得更為清楚。十多年前,為《今天》‘重寫文學史’專欄撰稿的作者們今天還都很活躍,很多人都已經是自己學術領域中的權威人物。如果《今天》再一次開設‘重寫’專欄,再一次熱情邀請大家寫文章,還會有人寄來文章嗎?專欄還能再繼續十年嗎?我可以肯定,不會的。這不是因為這些人不再愿意為《今天》寫作,我相信,只要有機會,大家都愿意以自己的寫作支持《今天》。問題不在這兒,在別的地方。《今天》和‘重寫’相逢,無論對《今天》,還是對文學史寫作,都是一段插曲,這個插曲如今之所以不能再重復,更深刻的原因還在它們和體制的不同關系。”[2]8這里,李陀所說的“體制”是指經過十多年時間的和“國際接軌”,文學史寫作愈加規范化、學術化,與主流意識非但沒有遠離,相反還在跨文化交流中,與體制更加密切了。
二、必然與偶然——重寫文學史與《今天》的“重疊”
人們常說,世事難料,許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成為了現實。1991年夏,在挪威奧斯陸復刊剛滿一年的《今天》在第3、4期合刊上接過來“重寫文學史”專欄的接力棒,開啟了重寫文學史在海外的十年之旅。一個飄洋過海的民間刊物,一個爭議不斷的熱門話題,兩者的相逢偶然之中又有著必然。反抗、顛覆既有文學史寫作體制,確認自己的存在價值,讓兩者相互倚重,走過一段“是盟友,是支持,是合作,但絕不是一個戰壕里的戰友”的艱難歷程。
在專欄“編者按”中,主持人李陀說:“1988年,《上海文論》開辟了一個欄目——‘重寫文學史’,由此引起了一場風波。在反對者看來,文學史是不準重寫的,可恰恰是歷史告訴我們:一切叫做歷史的東西都在歷史中不斷地被重寫。……‘重寫文學史’的欄目早就被停掉了,十分可惜。本刊早就有意接過這個話題,使之繼續。前不久正好收到王曉明先生的一篇來稿,與‘重寫’有關,而王又恰是‘重寫文學史’一事的始作俑者之一,這自然是個很好的機會。我們在本期鄭重辟出‘重寫文學史’專欄,希望這個欄目會得到讀者的關心,也希望對這個題目有興趣的各方人士踴躍來稿,使‘重寫’的事再度熱鬧起來。”[2]2“編者按”表達了三層意思:其一、肯定文學史是可以而且能夠重寫的,為《上海文論》和《今天》架設重寫觀念的“相通”橋梁;其二、亮明重寫主旨與重點,彰顯與《上海文論》重寫目標之不同;其三、敘述“重寫”專欄開設的觸發點,在《上海文論》和《今天》之間接通血緣紐帶。
正是在“目標之不同”上,《今天》的刊物定位與“重寫”專欄的初衷產生了罅隙和抵牾,這為之后很長一段時間里兩者的“游離”和“不協調”留下了遺患。為“重寫文學史”的兩種不同敘述方式播下種子:放在“文學史”的學術傳統和學術機制里進行分析和討論;放在《今天》的歷史和命運里予以審視和評判。很顯然,前者是大陸學界的敘述,后者是《今天》的敘述。
《上海文論》時期,重寫文學史的對象是官方的新民主主義話語,并未觸及文學史寫作背后的體制因素,也沒有把評判的矛頭對準“文學史寫作”本身,只是把“啟蒙”“審美—純文學”作為標桿,期待文學史寫作的多樣化,而非徹底的去“官方”、去“政治”、架空“道德”,這在之后的重寫文學史實踐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無論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新文學整體觀”,還是新中國文學、兩岸三地文學,抑或是現代性文學、女性主義文學,打破的僅僅是文學史寫作的種種束縛,以回到常識、回歸文學本身的策略淡化政治與文學史寫作的規訓,尋找文學史寫作的多種可能性,“外部研究”和“內部研究”始終處在此消彼長的狀態。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依然是主基調,對待革命文學、左翼文學、解放區文學、十七年文學是“重讀”“新解”;對待為藝術而藝術的文學、人性文學是“肯定”“張揚”;對待通俗文學、大眾文學是“認識”“默許”。總之,文學史寫作走在一條多元化的整合道路上,兼容并蓄、互動共存是它最顯著的特點。而在《今天》看來,這種寫作尚處在修修補補的學科化、學術化初級階段,實在是太落伍、太保守了。與《上海文論》的“重寫”相比,《今天》的“重寫”更加徹底、堅決,有它自己的知識譜系,有它特殊的烙印。反抗、先鋒、解構、顛覆、異質、拒絕等標簽可以輕而易舉地貼到它的身上。“《今天》的挑戰和質疑的矛頭,并不是只指向文學寫作,而且也直接指向文學史寫作”;“《今天》生來就是一切體制,也包括文學體制的敵人——在‘我不相信’這面旗幟下,《今天》所追求的寫作永遠是拒絕和反抗的象征,是對現存世界的種種壓迫關系,對現今一切統治秩序進行批評和反抗的不屈不撓的表達”。如此的《今天》,如此的“重寫”專欄,與《上海文論》的差異何至道里?
《今天》視野中的“重寫文學史”敘述存在兩個悖論。
其一、“重寫”使命與《今天》的視野難以匹配。作為一個專欄,放在《今天》的歷史和命運中審視自有其道理,“可以扔掉一些包袱,澄清一些遮蔽,給文學史的重寫一個新的方向,提出一些新的可能”。但是重寫文學史畢竟是一個學科建設的系統工程,涉及到歷史語境、意識形態、社會風氣、心理積淀、思想導向、閱讀習慣、傳播方式、文學史家的知識結構、價值標準等方方面面的因素。任何單向度的寫作都會破壞文學史的豐富性、多樣性,甚至造成“翻烙餅”式的內耗,無休止的顛覆和對抗,而沒有建構和生成,滋生文學史寫作的相對主義,陷入不可能論。共性的消失換來的是個性的膨脹。
其二、《今天》“重寫”專欄的初衷與文本實踐相左。從“專欄”開設初衷來看,是要把《今天》的反抗性、解構性進行到底,避免同質化,進而實現對文學史寫作的“重寫”。挑戰體制、警惕體制、疏離體制、突破體制、解構體制等詞語,屢屢為《今天》“重寫文學史”專欄主持人李陀提及,而且每次提及似乎都充溢著自豪與興奮,認為這才是《今天》與“重寫文學史”相逢的深遠意義。但是,事與愿違,實際的情形是,《今天》“重寫”專欄發表的29篇論文中,沒有一篇對《今天》與“重寫文學史”之間相互“重疊”的意義與價值進行關注。很明顯,論文的寫作者并沒有意識到他們的論文在《今天》上發表與在國內其他刊物上發表有什么不同。“《今天》的特殊歷史和它的特殊意義,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也許,激勵文章撰寫者們的唯一念頭,是被無情腰斬的‘重寫’竟然死里逃生,大家終于又有一個空間可以思考和寫作”。[2]4不僅思想觀念上,“重寫”專欄上的論文與《今天》的先鋒品格不相協調,而且體例、寫法上也迥然有別。“就拿在《今天》發表論文的這些作者來說,明顯的,大家都想以自己的‘重寫’,來對舊的文學史做出質疑和批判,但是,這樣做的同時,每一位作者又都同時在努力保持寫作的‘學術性’,使其符合學術體制所要求的規范。如果放在一本正常、普通的學術論文集里,這種做法是當然的,沒有什么特別,只能如此。但是這些文字,還有這些文字所負載的學術性和學術規范出現在《今天》這本刊物里,就顯得十分不協調,甚至怪異。”[2]5這種怪異甚至傳染到主持人李陀本人,他說:“每當一輯‘重寫’文章刊出時,不論這些文章寫得多么出色,心里總有點別扭,覺得它們不過是混跡在《今天》里,這兒其實不是它們待著的地方。”姑且不論《今天》把“對抗”“解構”“顛覆”“先鋒”作為唯一尺度的做法對錯與否,單就它要求論文寫作不拘泥于學術性的做法還是有可取之處的,至少在90年代中后期“學術與世界接軌”的大潮中葆有了論文寫作的“文學性”和“主體性”。正是在這一點上,李陀說,“重寫”專欄的文本實踐與《今天》是“盟友”的關系,“合作、支持”的關系,而非“一個戰壕里的戰友”。因為“《今天》生來就是一切體制,也包括文學體制的敵人”。
在糾結和悖論的反向弱化作用下,2001年《今天》夏季號上“重寫”專欄宣告終結,至此,“重寫”與《今天》的“重疊”正好走過十個年頭。如果把《上海文論》時期也算上的話,“重寫”專欄前后持續了十二三年。在這個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的時間里,文學創作、文學研究經歷太多的變化,個性化、多元化、主體性、審美性已經成為常態,表達不同意見和看法的渠道更趨開放。作為“雙百”方針之一部分,思想爭鳴、觀點論辯不再與立場身份掛鉤,成為人身攻擊和思想批判的工具。知識分子的精英角色在淡化,學術報刊的號召力在減弱,經濟、網絡、大眾、移動互聯在文學生產、研究、接受、流通環節中的地位大幅提升,不要說“重寫文學史”,即便是“人文精神討論”,抑或是新左翼、新自由主義、底層文學都很難在人們心目中激起群體性共鳴,人人爭說“重寫”的景象很難復現。如此,《今天》和“重寫”分道揚鑣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兩者之間不僅“神離”太久,而且當初的“形似”也面目可憎,失去了相互倚重、“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如果我們把《今天》時期的“重寫”稱之為“后重寫”的話,它的終結似乎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結束,文學史寫作再無“重寫”一詞,或者說很難再現“政治”與“審美”絕然對立、“社會”與“個體”互相敵視的敘述方式,當下乃至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的文學史寫作都將在多元并存的軌道上行進。
三、美麗的誤會——《今天》“重寫文學史”專欄文本解讀
自1991年設立“重寫文學史”專欄至2001年停辦,《今天》共發表“重寫”論文33篇,記錄了《今天》與“重寫文學史”的十年重合歷史。
《今天》“重寫”專欄的“編者按”中有一段看似不經意的話,“‘重寫文學史’的欄目早就停掉了,十分可惜。本刊早就有意接過這個話題,使之繼續。前不久正好收到王曉明先生的一篇來稿,與‘重寫’有關,而王又恰是‘重寫文學史’一事的始作俑者之一,這自然是個很好的機會”。兩個“早就”說明是有意為之,蓄謀已久,與“重寫文學史”相逢乃歷史的必然;“正好”“恰是”把接續“重寫”專欄解釋為偶然、意外之舉。綜合起來,就是“偶然中的必然”。以此觀之,專欄第一篇文章《一份雜志和一個“社團”》當是有意組稿所得,而非自然來稿。
《一份雜志和一個“社團”》正是《今天》需要的文章,見解獨到、另辟蹊徑、質疑、批判,有“我注六經”式的生機和風采;不僅與雜志風格一致,而且可以起到樣板、示范作用。當年的《新青年》何嘗不是現在的《今天》,它們在做著同一件事——顛覆、打破、反抗,擁有相同的底色和主張——經由刊物促進思想、文化的活躍,進而達成社會政治的變革。《新青年》不是一個純文學刊物,在它的周圍,有同仁的意見分歧,有讀者來信的不同反響,有發行收入的經濟制約。《今天》雖然是一個文學刊物,但從它的生長軌跡來看,政治的、思想的、文學的“先鋒”一以貫之,“《今天》有著豐富的先鋒性內涵,無論這一運動和‘文革’的復雜淵源,還是這一運動與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聯系,以及它在全球化中獲得的機遇和位置,都使得《今天》和它推動的先鋒運動有著西方先鋒派無法比擬的深刻的政治文化內涵”。顯然,在這一點上,《今天》希望“重寫”專欄上的文章能夠遠離學術,走出體制的規范和羈絆,把“重寫”的種子播散到文本之外,一如既往地“反抗”與“顛覆”。與雜志風格如此之吻合,與專欄初衷如此之一致,這樣的文章只能是有意約稿,而非自然來稿。
在《一份雜志和一個“社團”》一文中,王曉明認為,陳獨秀之所以創辦《新青年》,是因為他相信思想文化是繼政治、軍事之后的“第三種武器”,“批評時政,非其旨也”僅是表面之舉,離開是為了更好地返回,不談變幻莫測的時政,而是預謀民主、科學這樣的宏大政治。胡適回憶,“在民國六年,大家辦《新青年》的時候,本有一個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談政治,二十年離開政治,而在教育思想文化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設基礎政治”。胡適把《新青年》那份深藏的政治動機表達得更加清楚。盡管在編輯理念上,陳獨秀、胡適、周作人、魯迅等人之間有分歧,陳獨秀難耐介入政治的沖動,“本志主旨,固不再批評時政,青年修養,亦不在討論政治,然有關國家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胡適強調思想學術對政治的間接作用,希望雜志與政治保持一定距離,但是在“實效至上的功利主義”面前,在“國家民族存亡”面前,他們表現出前所未有的一致。綜合《新青年》產生的語境、編輯理念、文學主張等因素,王曉明認為《新青年》有四大個性特點:“實效至上的功利主義”“措辭激烈,不惜在論述上走極端的習氣”“絕對主義的思路”“以救世自居的姿態”。
由于《新青年》是當時唯一倡導新思想的刊物,“它的個性逐漸擴散為整個新文化運動的個性,它所登載的文字,也就構成了一套獨特的話語體系”;“《新青年》就像是一把鑰匙,可以幫助你打開新文化大廈的許多暗門”[3]。 它的個性滲透到五四新思潮、新文化、新文學的方方面面,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人都不是致力于文學創作和研究的人,他們鼓吹“文學革命”的目的何在?無論是陳獨秀的“今欲革新政治,勢必革新盤踞于運動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4],還是胡適的“我們提倡的文學革命,是要替中國創造一個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才可以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才可算得真正國語”[5],目的似乎只有一個:把文學革命作為傳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渠道。在《新青年》同仁眼里,文學革命與思想啟蒙其實是同一涵義,他們談論文學、從事創作,無不出自宣傳主張之虞,而非思索文學的意義與價值。如此,就可以解釋當時的人們為什么熱衷“規劃”“建設”新文學路徑了。王曉明說:“五四新文學的這種獨特的誕生方式派生出三個觀念:一、文學的進程是可以設計、倡導和指引的;二、文學史應該而且可以有一個主導傾向的;三、文學理論是非常重要的,它完全可以對創作發揮強大的指導和規范作用。”正是在這樣三個觀念的作用下,文學研究會才擔負著組織文學、發展文學之責任,如同今日之“中國作協”;新文學才會在一個個或這樣、或那樣的主義影響下前行,文學革命、革命文學、左翼文學、抗戰文學、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這種輕視、無視文學創作的個性差異,追求群體立場的做法在《新青年》和文學研究會中均可找到源頭。
既有文學史讓我們耳熟能詳了反帝反封建文學、革命文學、左翼文學、解放區文學、工農兵文學、《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等范疇,王曉明的《一份雜志和一個“社團”》一文讓我們透過《新青年》和文學研究會的身影,看到了一段迥然不同的文學史圖志。
1993年《今天》第4期“重寫”專欄刊發李歐梵的文章《漫談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頹廢”》,以“漫談”方式考察“頹廢”在現代文學中的“出場”和“演出”,為文學史寫作提供了一個新坐標。李歐梵指出:“自文藝復興以來,隨著科學、理性和人道主義信念的確立,人們逐漸發展出了一套關于歷史是無限發展的樂觀主義信念,但在這種樂觀主義背后同樣伴生出一種新的‘頹廢’觀念。高度技術的發展同一種深刻的頹廢感顯得極為融洽。進步的事實沒有被否認,但越來越多的人懷著一種痛苦的失落和異化感覺來經驗進步的后果。這種‘頹廢’感從19世紀中后期法國象征派詩歌中逐步發展起來,并最終形成了一種‘現代性’自身的對立面——‘美學現代性’。”“五四”啟蒙對人們最大的沖擊是時間觀念的改變,即“從古代的循環變成近代西方式的時間直接前進——從過去經由現在而走向未來,所以,著眼點不在過去而在未來,從而對未來產生烏托邦式的憧憬”。這種線性前進的時間想象“經過五四改頭換面之后,變成了一種統治性的價值觀,文藝必須服膺這種價值觀”[6]。由于“頹廢”從未作為“現代性”的另一面進入中國文學研究專家、學者的視野,因此,在一切求新的“五四”時代,“頹廢”成為一個類同于墮落、衰敗的“不道德的名詞”。事實上,“頹廢”具有重要的意義與價值,不僅是反抗資產階級庸俗現代性的美學立場,而且“它注重藝術本身的現實距離,并進一步探究藝術世界的內在真諦”,為“重寫文學史”提供了新路徑。不過,洞見與盲區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那樣,新的視域可能產生新的遮蔽,在救亡壓力遠勝于啟蒙批判的時代,在一個工業化尚處在起步階段的國家,頹廢現代性的負面作用也就明顯了。
1993年《今天》第4期“重寫”專欄還發表了陳思和的文章《民間的浮沉——從抗戰到“文革”——文學史的一個解釋》,題目明確亮出“重寫文學史”的新思路,一種既迥異于“官方”又有別于“精英”的文學史闡釋方式——民間。陳思和說,“民間”是一個極其復雜的概念,它和西方的民間社會、公眾空間并非同一概念,吸收了其中自由、自為、自在之意。在官方與精英之外,在中心與邊緣地帶,“民間”以一種特有的隱形結構潛滋暗長,豐富著文學創作和文學史形態。文章從民間在文學史的地位、民間形態與官方形態的關系、民間隱形結構對文學創作的影響三個方面探討了民間的文學價值,認為文學史上的“民間”一直被意識形態的“官方”遮蔽,被處在官方與民間之間按照意識形態的要求創造新文化,獻媚于官,愚弄于民,服從現實功利的“精英”漠視;“民間”以反改造、反滲透的姿態潛藏在主流文學之中,構成文本的復雜性、多義性悖論。陳思和認為,從辛亥革命到抗日戰爭,中國文化的三大領域基本處于割裂狀態,文化沖突主要發生在官方和精英之間,知識分子雖然提倡白話文,主張大眾化,但這只是他們對抗官方文化的語言策略,并不是接納民間文化,而是把民間視為充滿了封建毒素而需要改造的對象。抗戰的全面爆發使得官方、精英、民間的互動、融合成為可能,“民間文化形態”得以確立的標志是發生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關于“民族形式”的論爭,期間伴隨著官方與民間的改造、反改造等一系列矛盾沖突。20世紀50、60年代的文學作品中經常存在兩個文本——“顯形文本”和“隱形文本”,前者通過外在故事內容表現主流意識形態的干預;后者受民間文化形態制約,內蘊為文本的娛樂情緒,展現自身的存在價值和魅力[7]。
面對既有文學史“主流與非主流”“左冀文化與非左冀文化”“反帝反封建傳統與非五四傳統”“進步文學與反動文學”之類的二元對立敘述模式,我們看到,《民間的浮沉》及其關鍵詞“民間文化形態”“民間隱形結構”實現了對過去文學史理論框架的突破,把被遮蔽已久的文學史歸還給了文學。相對于王瑤先生開創的“相信文學歷史的不斷進步,強調社會政治因素對于文學的決定性的影響”的研究范式和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開創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整體研究范式,陳思和的民間文化形態、民間隱形結構等范疇延續了《上海文論》的“重寫文學史”觀念:從新的理論視角提出對新文學史的個人創見,文學史研究應當多元化,突出文學史寫作的主體性,強調文學史寫作的當代性,從而“沖擊那些似乎已成定論的文學史結論,激起人們重新思考昨天的興趣和熱情”[8]。
鐘愛“不確定”“多元的”文學史闡釋是《今天》“重寫”專欄的一個重要特點,《一份雜志和一個“社團”》《民間的浮沉》都是這樣,一個開拓文學史研究空間,一個重建文學史寫作范型,與《今天》的風格十分貼近。
《丁玲不簡單——毛體制下知識分子在話語生產中的復雜角色》,是李陀親自撰寫的一篇“重寫”文章,發表在《今天》1993年第3期上。李陀將丁玲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樣本進行拆解,以回答千千萬萬知識分子“為毛文體感召,并且以毛文體參與話語實踐”的深層次原因。對于習慣于“壓迫/反抗”“啟蒙/救亡”二元對立思維的人們來說,理解1940—1942年間在延安創作《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新的信念》《我們需要雜文》《“三八節”有感》等作品的丁玲輕而易舉地放棄批判立場、心甘情愿地歸順到毛文體之中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流行的“救亡壓倒啟蒙說”“苦難說”只能解釋局部,不僅不能令人信服,甚至有點勉強,“僅僅靠政治壓力就能使千千萬萬個知識分子改變自己的語言而接受另一種語言?蔣介石當年施加給知識分子的政治壓力并不小,其特務統治形成的恐怖一直延續到臺灣,可三民主義話語為什么沒有取得絕對霸權,反而大量的知識分子更加傾向革命,傾向馬克思主義?問題顯然不那么簡單。一種話語在激烈的話語斗爭中,為什么能排斥其他的話語而最終取得霸權地位,這是由許多具體的歷史條件所決定的,是多種社會實踐和話語實踐在互相沖突又互相制約中最終形成的結果。毛文體或毛話語形成支配性的、具有絕對權威的歷史也只能是如此”。
“五四”以來的知識分子深受西方現代性話語影響,毛文體何嘗不是一種現代性話語,而且是“一種和西方現代話語有著密切關系,卻被深刻地中國化了的中國現代性話語”。但是,在許多研究者看來,毛文體與現代性話語是對立、不相容的,而忽視了毛文體與現代性話語的同一性,“考慮到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歷史環境給中國知識分子帶來的種種復雜的壓力,考慮到他們不得不在反帝、反列強的前提下追求‘現代化’,則在中國生產出這樣一種具有雙重性的、適應中國情況的現代性話語,并且用它來推動改造中國的社會實踐,這實在是合情合理的。反過來,一旦這樣的話語被生產出來,知識分子們為它所吸引,并且積極地參與這種話語的生產,也是毫不奇怪的。在這個意義上,‘啟蒙’和‘救亡’的合奏正是中國式現代性話語的魅力所在”。李陀的毛文體的“現代性”觀點跳出李澤厚“啟蒙與救亡”二分法和人們習見的“壓迫說”局限,為文學史寫作拓展了解釋空間。但他沒有看到“革命”“救亡”“集體”對文化造成的巨大破壞,對作為新中國成立后權力話語象征的“毛文本”缺少整體認識和反思,以偏概全,很容易走向“現代性”的反面。
在作家作品解讀上,《今天》與《上海文論》“重寫”專欄沒有什么兩樣,或為曾經的邊緣作家的作品“叫好”,發掘其筆下人性深邃、審美的特異;或為熟悉的作家作品進行一番“重寫”,批評“革命”“階級”“工農兵”“集體”“思想改造”如何阻礙了作家主體精神的實現、審美藝術的表現。一定程度上,以作家作品論為主要形式是重寫文學史的基礎工作,既可以避免整體性“顛覆”“解構”造成的強烈震動,又能夠收到積少成多的效果。黃子平的《文學住院記——重讀丁玲短篇小說〈在醫院中〉》采用隱喻的方式,把《在醫院中》置于20世紀的“話語—權力”網格中進行解讀,考察小說與歷史語境的互文關系,呈現以丁玲為代表的一代知識分子如何在權力話語支配下放棄自我言說的過程。黃子平認為,主人公陸萍走的是一條與魯迅“棄醫從文”相反的“棄文從醫”的道路,不是自我追求的啟蒙國民的文學道路,而是受黨指派到新建的醫院做“產婆”的醫生道路。在醫院中,陸萍積極向上、認真負責、友好善良的工作態度與醫院上下愚昧無知、偏狹保守、自私茍安的整體環境格格不入,她提意見、抱怨、抗爭,相信“還是雜文時代”,但根據地的嚴酷現實是:不僅醫院人浮于事、官僚主義作風一時難以改變,就是自由表達的“文學也要住院”,知識分子改造、整風運動的結果是——雜文時代夭折,秧歌劇時代來臨,“懲前毖后”“治病救人”“脫胎換骨”等醫學術語取代“科學民主”“個性解放”“批判現實”等文學術語,成為知識分子日常必修的科目。為此,黃子平說:“如果文學家能被‘治愈’,文學真的能被治愈嗎?如果文學已被治愈,‘國民性的病根’又于今如何了呢?更重要的是:社會群體真的可以視作與人的身體一樣的有機整體嗎?文學真的是醫治這個有機體的一種藥物嗎?文學家的道德承諾與他們實際承受的社會角色之間真的毫無扦格嗎?”[9]黃子平的詰問是沉重的,意味悠長。
統計學告訴我們,如果選取的樣板有足夠的代表性,通過對一定數量樣本的分析,得出的結論當是有說服力。在考察和梳理了一些“重寫”專欄文章之后,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專欄文章多局限于文學史范疇,為典型的作家作品論,很少溢出文學場閾,更不要說對抗意識形態,與《今天》本身的“反抗”“解構”風格不相協調、不相融洽。這種不協調、不融洽堪稱與生俱來,很難突破,特別是對于王曉明、陳思和等一批高校的中青年學者來說,論文寫作已經與教學、科研工作不可分割地融在了一起。從文本實踐來看,敘事學、語言學、接受美學、形式主義等批評方法不同程度地讓“文學回到它自身”,韋勒克、沃倫所言的“內部結構”的不及物性更加不能把反抗、顛覆尤其是體制的批判落到實處。盡管黃子平、蔡翔、孟悅們最大可能地將丁玲、張愛玲、錢鐘書等人的作品與外部的意識形態牽連起來,發上一通“迫害說”“從眾說”指責,但似乎收效甚微,與《今天》的期望甚遠。這也從一個側面注解了主持人李陀的遺憾——“重寫”專欄的許多作者沒有考慮到在《今天》上發表文章有何特殊性。這是“重寫”論者的尷尬,亦是《今天》的尷尬——在海外,失去了意識形態束縛,“重寫文學史”不再是一個富有沖擊性的話題,很難獲得一種變相的話語權力。
除“論文體”文本與《今天》的先鋒風格不協調、不默契之外,《今天》更大的尷尬來自“重寫”論者星散,組織不起隊伍,形成不了規模,這種個體化的自言自語式寫作無法滿足《今天》“反抗”體制的心理期待。與之前《上海文論》時期的“重寫文學史”動議引發的群體熱議、規模效應構成了極大反差,礙于國內1989年學運風波影響,“重寫”論者僅僅把《今天》作為他們在海外的臨時棲居地、《上海文論》的備胎。在學術范圍內討論文學史寫作,“審美原則”“多樣性”“學科建設”是陳思和、王曉明在“主持人的話”中反復提到的詞匯,而非體制層面的對抗,更不是意識形態方面的干預,這種意圖、宗旨上的分歧注定兩者的“重逢”有點陰差陽錯,有始無終。難怪十多年后,專欄主持人李陀深有感觸地說:“現在回頭看看,當初開辟這樣一個專欄,就《今天》的性質和特色來說,并不合適。”[2]2專欄還是那個專欄,加盟成員陳思和、王曉明們的熱情依舊,但刊物風格不同了,當年以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上海作協的青年教師、學生為主體的“圈子”不在了,來自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中國作協的資深文學史家王瑤、嚴家炎、錢理群等人的聲援沒有了,時過境遷,留給《今天》“重寫文學史”專欄的是大環境的文學邊緣化、學術專業化,小環境的文學史寫作已經進入到一個實踐操作時期,而不再是理論層面的爭鳴時期。2001年夏,《今天》“重寫文學史”專欄黯然收場,終結了它與重寫的十年之緣。
當然,這樣說并非否定《今天》“重寫”專欄十年的存在價值,更不是否認重寫文學史行為的意義。如果把重寫文學史的歷史拉長來看,《今天》十年不僅意味著新的研究空間的開拓,也收獲了文學史研究的新視角、新方法、新成果,比如能否從文學期刊的經緯、讀者接受的理路編寫一部期刊文學史?能否以跨語體交際的修辭變遷寫作一部話語文學史?能否突破文學史寫作的學術規范寫作一部抒情文學史?能否以知識分子的結社交游活動寫作一部編年文學史?……應當說,在這些方面,王曉明的文章《一份雜志和一個“社團”》、陳思和的《民間的浮沉》等文章給了我們不少啟示,刺激了中國現代文學社團、報刊、出版中介研究,豐富了文學史研究方法和實踐,理當是重寫文學史之一部分,與《上海文論》時期的重寫文學史構成了時間上的前后序列,空間上的互文參照。
參考文獻:
[1]王曉明,主編.批評空間的開創[C].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
[2]李陀,編選.昨天的故事:關于重寫文學史[C].北京:三聯書店,2011.
[3]王曉明.一份雜志和一個“社團”[J].今天,1991(3,4).
[4]陳獨秀.文學革命論[J].新青年,1917,2(6).
[5]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J].新青年,1918,4(4).
[6]李歐梵.漫談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頹廢”[J].今天,1993(4).
[7]陳思和.民間的浮沉:從抗戰到“文革”[J].今天,1993(4).
[8]陳思和,王曉明.主持人的話[J].上海文論,1988(4).
[9]黃子平.文學住院記:重讀丁玲短篇小說《在醫院中》[J].今天,1992(4).
(責任編輯劉海燕)
Meeting and Overlapping between
“Rewriting Literary History” andToday
LIU Zho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Key words:Rewriting Literary History;Today; meeting; overlapp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