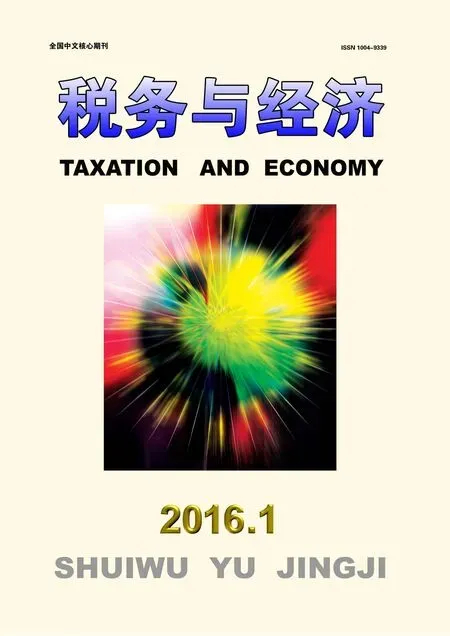基于稅收視角的商業(yè)銀行存差擴(kuò)大成因分析
魏 彧,馮 月,趙 敏
(貴州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 經(jīng)濟(jì)學(xué)院,貴州 貴陽 550025)
一、引 言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適應(yīng)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體制的銀行體制已初步形成,銀行業(yè)整體實(shí)力不斷增強(qiáng),商業(yè)銀行在參與宏觀調(diào)控方面發(fā)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中,一方面銀行存差*銀行存差是上世紀(jì)80年代作為我國信貸資金管理制度中控制銀行信貸的指標(biāo)提出的,如果銀行存款大于貸款為存差,銀行貸款大于存款為貸差。影響存貸利差,而存貸利差一直是我國商業(yè)銀行主要的利潤來源;另一方面銀行存差直接影響著投資和儲(chǔ)蓄規(guī)模的變化,進(jìn)而影響微觀經(jīng)濟(jì)主體的決策與宏觀經(jīng)濟(jì)運(yùn)行。特別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jī)之后,銀行“惜貸”行為對(duì)國民經(jīng)濟(jì)的復(fù)蘇雪上加霜。因此,對(duì)銀行存差問題的研究業(yè)已成為我國政府和學(xué)術(shù)界重點(diǎn)關(guān)注的問題之一。
一般情況下,商業(yè)銀行等金融中介機(jī)構(gòu)在經(jīng)營存貸款業(yè)務(wù)時(shí)應(yīng)保持適當(dāng)?shù)拇娌睿^高的存貸差說明銀行系統(tǒng)內(nèi)部資金運(yùn)行效率低下。對(duì)于銀行存差不斷擴(kuò)大的解釋比較多,但大多數(shù)解釋停留在理論假說層面上,實(shí)證研究較少。財(cái)政借款假說認(rèn)為,銀行將一部分資產(chǎn)從信貸形式轉(zhuǎn)化為持有政府債券形式,導(dǎo)致信貸規(guī)模下降,存差擴(kuò)大;銀行監(jiān)管機(jī)構(gòu)對(duì)銀行資產(chǎn)負(fù)債進(jìn)行管理,也對(duì)銀行存貸款比例進(jìn)行硬性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yè)銀行法》第三十九條有關(guān)商業(yè)銀行貸款資產(chǎn)負(fù)債比例管理的規(guī)定:貸款余額與存款余額的比例不得超過75%。外部沖擊假說認(rèn)為金融危機(jī),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jī)的爆發(fā)也導(dǎo)致信貸約束強(qiáng)化,存差擴(kuò)大。金融抑制理論認(rèn)為,信貸市場(chǎng)信用體系的不完善是導(dǎo)致存差擴(kuò)大的一個(gè)原因。
伍志文等(2004)[1]對(duì)上述部分理論假說進(jìn)行了實(shí)證研究檢驗(yàn),發(fā)現(xiàn)金融深化對(duì)存差擴(kuò)大產(chǎn)生了一定影響,但其他假說對(duì)存差擴(kuò)大的解釋能力不強(qiáng);作者進(jìn)一步提出銀行存差擴(kuò)大在于我國特殊的金融制度安排,即存款在一定程度上作為銀行資本金的替代品,扮演著風(fēng)險(xiǎn)緩沖器的角色。楊萬東(2006)[2]對(duì)存貸差產(chǎn)生的原因以及存貸差擴(kuò)大的影響的文獻(xiàn)進(jìn)行綜述,認(rèn)為銀行存差擴(kuò)大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包括經(jīng)濟(jì)基本面、宏觀經(jīng)濟(jì)政策變化以及銀行監(jiān)管等方面;但是其中沒有提到商業(yè)銀行稅收因素對(duì)銀行存貸差的影響。鄭慧(2010)[3]構(gòu)建誤差修正模型,實(shí)證分析影響存貸差擴(kuò)大的原因,發(fā)現(xiàn)固定資產(chǎn)投資、外匯占款存貸利率的變化以及城鄉(xiāng)居民儲(chǔ)蓄均為影響存貸差擴(kuò)大的原因。由于商業(yè)銀行稅收對(duì)信貸的扭曲效應(yīng),降低了銀行最優(yōu)信貸水平,銀行存在“惜貸”行為。薛薇(2011)[4]分析了流轉(zhuǎn)稅與銀行存貸差規(guī)模增長之間的關(guān)系,從宏觀層面得出了兩者存在正相關(guān)的結(jié)論。目前較少文獻(xiàn)探討稅收與銀行存差的關(guān)系,而且還沒有學(xué)者基于微觀層面從稅收角度給出我國商業(yè)銀行存貸差擴(kuò)大的原因。此外,由于學(xué)者們沒有考慮我國特殊的信貸市場(chǎng)體系,即大型國有商業(yè)銀行與非國有商業(yè)銀行并存的寡頭壟斷市場(chǎng),因而可能導(dǎo)致分析結(jié)論的可靠性大打折扣。
我們認(rèn)為商業(yè)銀行稅收也會(huì)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我國銀行存差擴(kuò)大,即:商業(yè)銀行征收流轉(zhuǎn)稅與所得稅扭曲銀行最優(yōu)信貸行為,銀行傾向于減少信貸水平,而考慮銀行稅負(fù)轉(zhuǎn)嫁的情況,商業(yè)銀行稅收也會(huì)影響銀行最優(yōu)存款規(guī)模,這兩方面共同作用下可能導(dǎo)致銀行存差進(jìn)一步擴(kuò)大。基于此,本文結(jié)合我國上市商業(yè)銀行微觀數(shù)據(jù)從實(shí)證分析角度重點(diǎn)研究我國銀行稅收制度是否顯著影響銀行存差擴(kuò)大,稅收對(duì)不同所有制屬性商業(yè)銀行存差影響是否存在顯著差異性。
二、數(shù)據(jù)來源與樣本統(tǒng)計(jì)性質(zhì)描述
1.數(shù)據(jù)來源與樣本選擇
本部分主要研究商業(yè)銀行稅收對(duì)上市銀行存差的影響,屬于探討商業(yè)銀行微觀經(jīng)濟(jì)效應(yīng)范疇,我們采用的樣本為全體16家在A股上市的商業(yè)銀行,時(shí)間跨度為2004年至2013年末,樣本數(shù)據(jù)來源于國泰安數(shù)據(jù)服務(wù)中心CSMAR系列研究數(shù)據(jù)庫、RESSET(銳思)金融數(shù)據(jù)庫以及中經(jīng)網(wǎng)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
2.變量的選取與統(tǒng)計(jì)性質(zhì)的描述
薛薇(2011)[4]采用多元統(tǒng)計(jì)中相關(guān)性分析得出銀行存差增長率與營業(yè)稅稅率存在顯著正負(fù)相關(guān)的結(jié)論,但文章采用的是宏觀數(shù)據(jù)且營業(yè)稅稅率為法定稅率,并沒有控制其他變量的影響,因而采用描述性統(tǒng)計(jì)方法并不能嚴(yán)格證明營業(yè)稅與存差擴(kuò)大之間的相關(guān)性。本文在借鑒前人研究的基礎(chǔ)上,從微觀視角,分析商業(yè)銀行稅收對(duì)上市銀行存差的影響。
按照銀行存差的定義,我們選取商業(yè)銀行存差作為被解釋變量,即扣除法定存款準(zhǔn)備金的銀行存款高于貸款的部分。設(shè)定相應(yīng)的流轉(zhuǎn)稅指標(biāo)與所得稅指標(biāo)作為影響上市銀行存差的稅收因素指標(biāo),該指標(biāo)也是我們實(shí)證部分重點(diǎn)關(guān)注的解釋變量。同時(shí)我們也將影響商業(yè)銀行存差的一系列因素,如信貸規(guī)模、銀行固定資產(chǎn)、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以及貨幣發(fā)行量,作為控制變量納入實(shí)證模型中。變量的選取與基本設(shè)定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說明
由表1可知,對(duì)于被解釋變量銀行存差而言,我們通過計(jì)算銀行存貸款額之間的差額的對(duì)數(shù)值來確定,其中銀行存款指標(biāo)由“銀行發(fā)放的貸款和貼現(xiàn)資產(chǎn)扣減貸款損失準(zhǔn)備期末余額后的金額”確定,銀行貸款指標(biāo)由“銀行吸收的客戶存款或者其他金融機(jī)構(gòu)存放于本行的款項(xiàng)”。
對(duì)于解釋變量而言,依據(jù)我國現(xiàn)行銀行業(yè)稅制,我們選取上市銀行年報(bào)利潤表中披露的“營業(yè)稅金及附加”科目余額的對(duì)數(shù)值作為衡量商業(yè)銀行流轉(zhuǎn)稅的指標(biāo);選取上市銀行當(dāng)期實(shí)際繳納的企業(yè)所得稅金額的對(duì)數(shù)值作為衡量商業(yè)銀行直接稅的指標(biāo)。根據(jù)前文理論分析,考慮到商業(yè)銀行稅收的扭曲效應(yīng),因此我們預(yù)測(cè)商業(yè)銀行稅收存在傾向于擴(kuò)大銀行存差的效應(yīng),兩者呈現(xiàn)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
對(duì)于控制變量而言,銀行固定資產(chǎn)反映了銀行資產(chǎn)質(zhì)量水平,資產(chǎn)質(zhì)量越高的銀行抵御金融風(fēng)險(xiǎn)的能力越強(qiáng),因而儲(chǔ)蓄者也愿意將資金存入風(fēng)險(xiǎn)系數(shù)小的銀行,然而,該指標(biāo)值越高,銀行的信貸規(guī)模通常也越大,因而固定資產(chǎn)規(guī)模對(duì)銀行存差的影響效應(yīng)不定。通過銀行存差的計(jì)算公式可知,銀行信貸規(guī)模也是影響存差的因素之一*這里不引入銀行存款指標(biāo)是為了防止銀行存差、貸款與存款之間存在多重共線性。,因而我們將銀行信貸指標(biāo)作為控制變量引入。我們把GDP指標(biāo)作為影響銀行存差的經(jīng)濟(jì)基本面因素引入實(shí)證模型中,現(xiàn)實(shí)經(jīng)濟(jì)中,經(jīng)濟(jì)繁榮,商業(yè)銀行信貸投放量通常增加,通常會(huì)縮小銀行存差,因而我們預(yù)計(jì)GDP與銀行存差之間呈現(xiàn)出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我們將廣義貨幣供應(yīng)量M2作為貨幣政策控制變量引入模型中,考察貨幣政策對(duì)銀行存差的影響。相關(guān)變量的統(tǒng)計(jì)性質(zhì)描述如表2所示。

表2 變量統(tǒng)計(jì)性質(zhì)描述
從表2樣本統(tǒng)計(jì)性質(zhì)描述可知,在取對(duì)數(shù)后各變量波動(dòng)幅度較小,樣本數(shù)據(jù)較為集中。同時(shí),我們也對(duì)16家上市銀行存貸差變量的時(shí)間趨勢(shì)進(jìn)行考察,如圖1所示。

圖1 16家上市銀行存貸差變動(dòng)趨勢(shì)
根據(jù)圖1可知,除少數(shù)商業(yè)銀行由于上市的時(shí)間較晚,時(shí)間趨勢(shì)還不明顯外,大部分商業(yè)銀行的存差呈現(xiàn)出隨著時(shí)間而逐步擴(kuò)大的趨勢(shì),該現(xiàn)象是否與商業(yè)銀行稅制相關(guān),需要我們進(jìn)一步實(shí)證檢驗(yàn)。
三、實(shí)證模型的構(gòu)建
本部分采用面板數(shù)據(jù)模型考察商業(yè)銀行信貸對(duì)銀行存差的影響。鑒于數(shù)據(jù)結(jié)構(gòu)中個(gè)體變量N大于時(shí)間趨勢(shì)變量T,樣本符合短面板數(shù)據(jù)特點(diǎn)。我們構(gòu)建如下基本模型:
GAPit=β0+β1turnovertaxit+β2incometaxit+ΓXit+μit
(1)
基準(zhǔn)模型(1)式中,i代表樣本中16家上市銀行,t代表時(shí)間趨勢(shì);被解釋變量GAPit表示第i個(gè)上市銀行在t年的存差;解釋變量turnovertaxit與incometaxit分別表示第i個(gè)上市銀行在t年的流轉(zhuǎn)稅總額對(duì)數(shù)值與所得稅總額對(duì)數(shù)值;Xit表示影響上市銀行存差規(guī)模的一系列控制變量,具體包括:銀行固定資產(chǎn)(lnfixit)、銀行信貸規(guī)模(lnloanit)、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增長率(GDPt)以及廣義貨幣供應(yīng)量(M2)。
在基準(zhǔn)模型(1)式的基礎(chǔ)上,我們擴(kuò)展模型,引入所有制差異視角,即:當(dāng)dummy=1時(shí),表明其屬于非國有大型商業(yè)銀行;而當(dāng)dummy=0時(shí),表明其屬于國有大型商業(yè)銀行。基于此,我們進(jìn)而考察不同所有制條件下,商業(yè)銀行稅收對(duì)銀行存差規(guī)模的影響,構(gòu)建如下面板數(shù)據(jù)計(jì)量模型:
GAPit=β0+β1turnovertaxit×dummy+β2incometaxit×dummy+ΓΞit+μit
(2)
基準(zhǔn)模型(1)與擴(kuò)展模型(2)的區(qū)別在于加入所有制差異因素,即我們所重點(diǎn)關(guān)注的解釋變量為虛擬變量與流轉(zhuǎn)稅稅收總額和所得稅稅收總額相乘的交叉項(xiàng),體現(xiàn)不同所有制屬性商業(yè)銀行稅收的差異性。控制變量Ξ不僅包含基準(zhǔn)模型中一系列控制變量(銀行固定資產(chǎn)、銀行信貸規(guī)模、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增長率以及廣義貨幣供應(yīng)量),還包含所有制差異虛擬變量(dummy={0,1})。
四、實(shí)證結(jié)果分析及經(jīng)濟(jì)學(xué)解釋
應(yīng)用計(jì)量分析軟件STATA 12.0,采用個(gè)體固定效應(yīng)模型估測(cè)上述基準(zhǔn)模型與擴(kuò)展模型。
1.基本模型回歸結(jié)果分析及經(jīng)濟(jì)學(xué)解釋

表3 基本模型回歸結(jié)果分析
注:*、**、***分別表示變量在10%、5%、1%的水平上顯著。
表3為控制各商業(yè)銀行個(gè)體異質(zhì)性后的面板數(shù)據(jù)回歸結(jié)果,與上述參數(shù)估計(jì)方法一致,均采用LSDV估計(jì)面板數(shù)據(jù)模型,輸出的方差為聚類穩(wěn)健標(biāo)準(zhǔn)差。
從表3的回歸結(jié)果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整體上看回歸結(jié)果的R統(tǒng)計(jì)量為0.9871,表明所構(gòu)建的面板數(shù)據(jù)實(shí)證模型能夠解釋樣本數(shù)據(jù)98.71%的變化,對(duì)樣本數(shù)據(jù)的解釋能力較強(qiáng)。變量id_2至id_16為體現(xiàn)不同上市銀行個(gè)體差異的截距項(xiàng),可知部分上市銀行截距項(xiàng)十分顯著(P值接近于0),存在個(gè)體差異現(xiàn)象,這也印證了本文采用個(gè)體固定效應(yīng)回歸的正確性。
與上節(jié)面板數(shù)據(jù)模型設(shè)定檢驗(yàn)相一致,我們?cè)谀P偷脑O(shè)定方面也考慮所構(gòu)建的模型是否為隨機(jī)效應(yīng)模型,通過相應(yīng)Hausman Test可知,輸出的卡方統(tǒng)計(jì)量為χ2(7)=17.61,P值為0.013,在5%的水平上強(qiáng)烈拒絕所構(gòu)建的模型為隨機(jī)效應(yīng)模型假設(shè),因此本文所采用個(gè)體固定效應(yīng)(Fixed effect)模型進(jìn)行回歸的結(jié)果是穩(wěn)健而準(zhǔn)確的。
表3中還報(bào)告了各解釋變量與控制變量對(duì)銀行存差的影響。對(duì)于解釋變量而言,銀行流轉(zhuǎn)稅稅收總額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能夠促進(jìn)商業(yè)銀行存差擴(kuò)大,即流轉(zhuǎn)稅增加一個(gè)百分點(diǎn)會(huì)導(dǎo)致銀行存差增加0.195%。驗(yàn)證我們上述假說,稅收確實(shí)是導(dǎo)致銀行存差擴(kuò)大的因素之一。該結(jié)論的經(jīng)濟(jì)學(xué)含義為:商業(yè)銀行稅收扭曲了銀行最優(yōu)信貸行為,降低了銀行稅后貸款收益率,銀行最優(yōu)信貸水平下降;同時(shí)考慮到銀行營業(yè)稅負(fù)擔(dān)很難向后轉(zhuǎn)嫁給儲(chǔ)蓄者的情況,即銀行最優(yōu)存款數(shù)量對(duì)營業(yè)稅的變動(dòng)不敏感,銀行最優(yōu)儲(chǔ)蓄量幾乎不變,通過這兩個(gè)方面的作用,商業(yè)銀行存差會(huì)進(jìn)一步擴(kuò)大。該結(jié)論從稅收角度揭示了商業(yè)銀行經(jīng)營中“信貸保守”現(xiàn)象產(chǎn)生的原因。*解釋商業(yè)銀行信貸保守或者銀行存差擴(kuò)大的文獻(xiàn)較多,大多數(shù)從銀行風(fēng)險(xiǎn)監(jiān)管角度以及外部沖擊角度予以解釋,這里我們主要從銀行稅收角度解釋銀行信貸保守現(xiàn)象。
同樣,銀行所得稅稅收總額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也對(duì)銀行存差產(chǎn)生正向影響,即銀行所得稅提高一個(gè)百分點(diǎn)導(dǎo)致銀行存差擴(kuò)大0.328%,該結(jié)論的經(jīng)濟(jì)學(xué)含義為:如果不考慮銀行自有資本,那么我們就會(huì)得出所得稅是“中性稅收”,一般不會(huì)扭曲銀行最優(yōu)信貸行為的結(jié)論,然而,考慮到銀行存貸款之間的相互影響,所得稅最終也是構(gòu)成銀行貸款資本成本的一部分。如果銀行貸款利率低于銀行信貸資本成本,那么稅收負(fù)擔(dān)部分或者全部由銀行自身承擔(dān),這會(huì)導(dǎo)致銀行貸款收益下降,最優(yōu)貸款數(shù)量減少,扭曲銀行最優(yōu)信貸行為,同時(shí)也會(huì)導(dǎo)致銀行存差擴(kuò)大。因此,所得稅確實(shí)影響商業(yè)銀行信貸行為進(jìn)而導(dǎo)致銀行存差擴(kuò)大。
對(duì)于控制變量而言,商業(yè)銀行固定資產(chǎn)總額與銀行存差的擴(kuò)大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呈現(xiàn)出負(fù)相關(guān)關(guān)系,即銀行固定資產(chǎn)總額上升一個(gè)百分點(diǎn)將導(dǎo)致銀行存差擴(kuò)大下降0.218%,銀行資產(chǎn)作為衡量銀行資產(chǎn)質(zhì)量的指標(biāo),資產(chǎn)質(zhì)量越高的銀行信貸風(fēng)險(xiǎn)越低,越有能力進(jìn)行大規(guī)模的放貸,因此兩者呈現(xiàn)出負(fù)相關(guān)關(guān)系。傳統(tǒng)的貨幣信貸理論認(rèn)為,存差=存款-貸款,貸款的增加必然導(dǎo)致存差的下降,然而我們的實(shí)證結(jié)論卻得出兩者呈現(xiàn)出顯著的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一個(gè)可能的原因是,存款規(guī)模的擴(kuò)大要遠(yuǎn)遠(yuǎn)高于信貸規(guī)模的擴(kuò)大,因而表現(xiàn)出隨著銀行信貸規(guī)模的擴(kuò)大,銀行存差規(guī)模也會(huì)擴(kuò)大的現(xiàn)象,這也與我國銀行存款增長率高于貸款增長率的典型事實(shí)相符。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增長率與銀行存差之間在接近5%的顯著性水平下呈現(xiàn)出反向相關(guān)關(guān)系,經(jīng)濟(jì)學(xué)含義為:我國GDP的增長很大程度上是由投資拉動(dòng),而我國企業(yè)投資資金絕大部分通過銀行信貸市場(chǎng)獲得,這樣,信貸規(guī)模的增長伴隨著投資水平的增加,最終促進(jìn)GDP的增長,因而存差擴(kuò)大與GDP之間反向相關(guān)。廣義貨幣余額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反向影響銀行存差規(guī)模的擴(kuò)大,我國目前基礎(chǔ)貨幣的投放主要通過中央銀行再貸款的形式,廣義貨幣余額增加表明銀行信貸投放的增加,因而存差規(guī)模下降。
2.擴(kuò)展模型回歸結(jié)果分析及經(jīng)濟(jì)學(xué)解釋
在基準(zhǔn)模型回歸分析的基礎(chǔ)上,我們進(jìn)一步考察在所有制差異條件下,商業(yè)銀行稅收對(duì)銀行存差擴(kuò)大影響的差異性。同樣我們也通過Hausman Test驗(yàn)證模型是否屬于隨機(jī)效應(yīng)模型,檢驗(yàn)輸出結(jié)果為:χ2(7)=27.54,P值接近于零,故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擴(kuò)展模型為隨機(jī)效應(yīng)模型,因而采用個(gè)體固定效應(yīng)模型回歸是恰當(dāng)?shù)摹?/p>
擴(kuò)展模型回歸結(jié)果如表4所示。

表4 擴(kuò)展模型回歸結(jié)果分析
注:*、**、***分別表示變量在10%、5%、1%的水平上顯著。
從表4的回歸結(jié)果中我們可知,整體上看回歸結(jié)果的R統(tǒng)計(jì)量為0.9909,表明所構(gòu)建的面板數(shù)據(jù)實(shí)證模型能夠解釋樣本數(shù)據(jù)99.05%的變化,對(duì)樣本數(shù)據(jù)的解釋能力較強(qiáng)。通過與表3的回歸結(jié)果對(duì)比可知,R統(tǒng)計(jì)量增加,表明控制所有制因素后,模型的解釋能力進(jìn)一步增強(qiáng)。從體現(xiàn)商業(yè)銀行個(gè)體差異的截距項(xiàng)可知,部分截距項(xiàng)十分顯著(P值接近于0),存在個(gè)體差異現(xiàn)象,表明本文所采用個(gè)體固定效應(yīng)回歸是正確的。
對(duì)于解釋變量而言,流轉(zhuǎn)稅增加一個(gè)百分點(diǎn),非國有大型商業(yè)銀行(股份制商業(yè)銀行與城市商業(yè)銀行)存差規(guī)模比國有大型商業(yè)銀行存差規(guī)模顯著增加0.409%;同樣,所得稅增加一個(gè)百分點(diǎn),非國有大型商業(yè)銀行存差規(guī)模比國有大型商業(yè)銀行存差規(guī)模增加0.234%,表明非國有大型商業(yè)銀行的存差對(duì)商業(yè)銀行稅收變動(dòng)更為敏感。張杰(2003)[5]、伍志文等(2004)[1]提出“貸款與資本金共謀的特殊資本結(jié)構(gòu)”來解釋銀行存差規(guī)模擴(kuò)大的原因。我們?cè)诖嘶A(chǔ)上認(rèn)為,由于長期以來國家信用的存在,國有銀行的風(fēng)險(xiǎn)水平要低于非國有銀行,而從銀行風(fēng)險(xiǎn)管理的角度看,存差與銀行資本金的作用效果類似,兩者存在一定的替代性,因此在面臨相同銀行風(fēng)險(xiǎn)狀況下,國有銀行中國家信用就可以替代部分存差在降低風(fēng)險(xiǎn)方面的作用,與股份制商業(yè)銀行相比,國有銀行不需要保有更多的存差。
對(duì)于控制變量而言,所有制差異因素在1%的顯著水平下正向影響非國有商業(yè)銀行存差規(guī)模的擴(kuò)大,該實(shí)證結(jié)論也支持上述分析結(jié)論,非國有銀行確實(shí)比國有銀行傾向于擴(kuò)大存差規(guī)模。其余控制變量,除廣義貨幣供應(yīng)量對(duì)銀行存差的影響不顯著,作用方向相反外,其余控制變量的顯著性水平以及與被解釋變量的作用方向均與基本模型一致。
綜上所述,從表3與表4模型的回歸結(jié)果表明,流轉(zhuǎn)稅顯著地促進(jìn)商業(yè)銀行存差規(guī)模擴(kuò)大,同樣所得稅也會(huì)導(dǎo)致銀行存差擴(kuò)大;商業(yè)銀行固定資產(chǎn)總額與銀行存差的擴(kuò)大呈現(xiàn)顯著的負(fù)相關(guān)關(guān)系;銀行存差擴(kuò)大與GDP之間反向相關(guān);廣義貨幣余額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反向影響銀行存差規(guī)模的擴(kuò)大。此外,擴(kuò)展模型實(shí)證結(jié)果還顯示,相對(duì)于大型國有商業(yè)銀行而言,流轉(zhuǎn)稅與所得稅顯著促進(jìn)非國有大型商業(yè)銀行存差規(guī)模擴(kuò)大。
五、結(jié)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構(gòu)建面板數(shù)據(jù)模型實(shí)證檢驗(yàn)了稅收對(duì)銀行存差擴(kuò)大的影響,實(shí)證結(jié)論表明,無論是流轉(zhuǎn)稅還是所得稅均對(duì)銀行存差產(chǎn)生顯著正向影響。此外,擴(kuò)展模型實(shí)證結(jié)果顯示,不同所有制屬性商業(yè)銀行存差對(duì)稅收變動(dòng)的敏感性不同,具體而言,與國有商業(yè)銀行相比,稅收導(dǎo)致非國有商業(yè)銀行存差增長幅度更高。結(jié)合前文的實(shí)證結(jié)論我們從稅收角度給出了銀行存差擴(kuò)大的一個(gè)解釋,進(jìn)一步提出三個(gè)方面的政策建議,解決一方面銀行存差擴(kuò)大另一方面中小企業(yè)貸款難的資金供求矛盾問題。
第一,盡快推進(jìn)金融業(yè)“營改增”,降低銀行稅收負(fù)擔(dān)。前文實(shí)證結(jié)果均表明,銀行稅收與存差規(guī)模呈現(xiàn)顯著正相關(guān)。因此金融業(yè)“營改增”有助于降低銀行稅收負(fù)擔(dān)進(jìn)而降低銀行存差規(guī)模,引導(dǎo)資金流向?qū)嶓w經(jīng)濟(jì),特別是中小企業(yè)。
第二,加快國有銀行改革,逐漸形成銀行業(yè)的競(jìng)爭格局。我們發(fā)現(xiàn),由于國有銀行與非國有銀行在信貸市場(chǎng)中的地位不同,導(dǎo)致稅收對(duì)其存差的影響不同。因此,調(diào)整信貸市場(chǎng)結(jié)構(gòu),提升非國有銀行市場(chǎng)競(jìng)爭力,而削弱國有銀行對(duì)市場(chǎng)的控制力,會(huì)進(jìn)一步抑制銀行存差擴(kuò)大。
第三,加強(qiáng)利率市場(chǎng)化改革,使得資金價(jià)格能夠真實(shí)反映信貸市場(chǎng)需求。通過推進(jìn)利率市場(chǎng)化的途徑,逐步降低銀行存差水平。
[1]伍志文,鞠方,趙細(xì)英.我國銀行存差擴(kuò)大成因的實(shí)證分析[J].財(cái)經(jīng)研究,2004,(4):27-38 .
[2]楊萬東.商業(yè)銀行存貸差問題討論綜述[J].經(jīng)濟(jì)理論與經(jīng)濟(jì)管理,2006,(2).
[3]鄭慧.我國商業(yè)銀行存貸差擴(kuò)大原因的實(shí)證分析[J].山西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0,(6):728-731.
[4]薛薇.銀行稅收理論與制度研究[M].北京:經(jīng)濟(jì)管理出版社,2011.
[5]張杰.國有銀行的存差:邏輯與性質(zhì)[J].金融研究,2003,(6):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