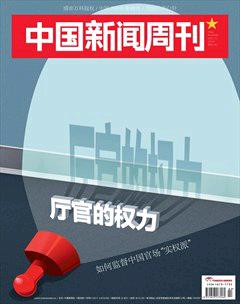當IT男任性地闖進動畫世界
周鳳婷

《小門神》劇照。圖/CFP
北京北五環外的一號地藝術園區,遠離市區且尚未形成如798藝術區那樣知名度,偏僻而清靜,在霧霾刺鼻的時候,在這里抬頭竟還能看到一小片藍天。“追光動畫”的大本營就位于園區一角的兩棟建筑內。
“追光”的員工給兩棟建筑起了名字,各有內涵,紅磚建筑被命名被“夸父樓”,相隔百米外的灰色建筑則是“后羿樓”。夸父追日,后羿射日,都是用生命在追“光”。
夸父樓是“追光動畫”制作的主場地,4層樓全是開放式辦公區域,有餐廳、咖啡廳、健身房、還有一個可曬太陽辦派對的露天陽臺,散發著創業公司的范兒。工作人員都對著電腦埋頭工作,看上去像召集了一整屋子程序員的互聯網科技公司。只有走近了,才發現他們做的完全是另一回事。
他們是在計算機上折騰的藝術家。

王微。圖/CFP
2013年3月,土豆網(后與優酷合并為優酷土豆集團)前CEO王微宣布成立“追光動畫”,二次創業,并跨界擔任編劇和導演。
一個有技術的理工男帶著自己的美麗設想,帶著一群做動畫的年輕人就這么闖進了動畫電影里,并專注于原創“中國故事”。在將近三年的時間里,這個有IT基因的公司用高效的執行力為追光動畫團隊帶來了資本、技術、人才、管理模式和可持續的創作力。
然而,他的第一部動畫長片《小門神》上映后,市場反應卻并沒有預期熱烈。
王微瘦高,1米86,大長腿,和《小門神》中門神郁壘的造型頗像,嚴肅時氣場強大,說起得意的事情,忍不住笑。牛仔褲和衛衣,簡單隨意,他陷在沙發里,開始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三年的“追光”歷程。
要做中國版皮克斯
2012年8月24日七夕夜,王微在微博上宣布,離開他一手創辦并運營了七年的土豆網。他把這稱為“退休”。
“退休”之后,突然有了大把的時間和更充裕的精力,王微到處游走、寫專欄,曾考慮過開一家酒莊,釀葡萄酒,或者開一家漆器工作室,做一個傳統工藝藝人,但不久后都作罷。
那段時間,王微給《時尚先生》寫專欄,在一篇發表于2013年3月題為《為什么要旅行》的文章中,王微寫道,“有些時候,你想找一個東西,那東西非常珍貴,無比重要,但是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你就想,也許換一個地方,你就想起來你要找的究竟是什么了。”年輕時王微不安分,19歲到美國念書,23歲自駕環游美國,也曾輾轉在紐約、華盛頓、巴黎讀書工作,他一直沒有放棄尋找那個“無比珍貴的東西”。
在文章的末尾,他寫道,“但我早就知道,所有這些旅行,也許可以讓我踏上更多的土地,但我要找的東西,無論在哪里都找不到。它藏在我的意識里的某個地方。”
兜兜轉轉7個月之后,2013年3月13日上午7點,王微又發了一條微博,短短三個字,“回來了。”同一天下午3點,華爾街日報中文網發布了一篇有關王微的報道:“中國最大在線視頻網站土豆網創始人王微現在開始著手打造下一個項目:中國版皮克斯。”
準確地說,不是一個項目,是一家公司。王微不但是這家名為追光動畫的動畫電影制作公司的創始人,他還負責劇本創作,同時擔任導演。“每個人都是生活的導演”,土豆網那句著名的口號,被王微扎扎實實地用在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
二次創業,從互聯網公司的CEO大跨步跨界成為電影編劇和導演,還是當時并不被看好的國產動畫領域,王微受到過一些質疑,“那時候很多人聽了會覺得,一個以前從沒做過動畫的人,三年做出一個片子,扯吧?” 他回憶道。
王微給“追光”的目標清晰,“做出世界一流品質的作品”。這不是王微第一次提出這樣的目標。2011年11月,土豆網曾成立北京提線數字科技有限公司,致力動漫原創。時任土豆網CEO的王微在當時接受采訪時便表示,土豆網會將科技與項目管理的經驗引入動漫制作,力爭3年內制作能力達到國際一流動畫電影大片的水準。這正是兩年后王微在“追光”想做的事情。
這一次,王微的行動來得很堅決。寫劇本、融資、招人組建團隊,他逐一親力親為。
此前,對于動畫電影制作,王微是門外漢。他喜歡皮克斯的作品,至于那些作品怎么從無到有,需要哪些管理流程,他并不太懂。在決定做追光動畫之后,他專門飛到好萊塢學習經驗,也拜訪了二三百位行業內大佬們,因為土豆創始人的身份,大家都愿意和他聊,并給他建議。
王微接受了他們大多數的建議,但有兩點,他沒有采納,或者說不愿意妥協。“當時大多數的人都認為要在美國建一個工作室,在美國招聘成熟的人才。第二,沒有必要維持那么大的人員團體,前期進來做完可以走,再來一批人做中期,中期結束后期再進來,偏項目制的,風險比較小。”而這兩點,也是制作國產動畫最通行且經濟有效的方式。
王微不這么認為,“動畫公司最重要的是建一個團隊,有了團隊才能做一部一部的片子出來。每年都有片子出來,這樣公司才能立得長久。”2014年6月,追光動畫完成B輪2000萬美元的融資,而王微給“追光”處女作《小門神》的制作預算用去了其中的一半多,7000萬人民幣。
王微沒有指望片子一炮而紅。他覺得《大圣歸來》是可遇不可求的案例,追光動畫希望做到的是產量穩定、質量穩定。他相信,保證持續的生產力,多做幾部片子,做出口碑和票房雙贏的片子的概率就提高了。
而最終把公司建在北京,招聘國內動畫人才,則是出于他做原創“中國故事”的考慮。“美國動畫師做出來,一看就知道是美國人說話的方式,因為創作都是從生活經歷來。”王微說。
王微請過美國好萊塢的顧問,他感覺到對方在掌握中國故事中國文化時的遲疑,“動畫是細微的,表情、情緒、交流的方式,(中美)都會有一些系列的差別。他只能做一些技術性的東西,至于故事、人物的情感、情緒方面,為什么這么動、這樣笑、這么說話,他很茫然。”王微說。
技術、藝術與管理的融合
皮克斯最近的一部動畫長片《頭腦特工隊》,由45位動畫師制作5年而成,成本1.7億美元。《小門神》用了7000萬人民幣和3年制作時間,對于一個初創期團隊而言,按時按質地制作出一部高水準的作品,并不容易。
動畫新人王微承認,他借鑒了小黃人的制作團隊照明娛樂公司的經驗,在管理上非常注重“紀律”。他稱這個是管理上的哲學理念。
小黃人系列中,《神偷奶爸2》以7000萬美元的成本完成制作,最終全球票房接近10個億。他們的制片人曾告訴王微,我們的成本是7000萬美元,是皮克斯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為什么能做下來?最主要就是紀律。因為時間和成本有限,不可能有機會反復修改完成的內容。有問題隨時解決,但需要不斷往前推進。”
在“追光”負責故事板的蘇昊丹一開始不能理解“有限的時間內做到最好”的概念。“我們做藝術的都還是偏執的,我創作的內容有問題我受不了。但公司流程時間控制非常嚴格,過了截止時間就一定要傳給下一個環節。” 她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為此,她曾經和制片不止一次爭論,但現在她已經學會了讓步。如果力求完美,就利用自己的時間加班加點完成。
于洲是王微在土豆時期的老搭檔,此次也是第一次擔任動畫制片人,在他看來,管理的理念都是相通的,“動畫片制作需要團隊在藝術、技術、管理的結合”。他很清楚自己的職責,“作為制片人,我們需要保證項目按時完成并達到預期的目標。2015年7月10日要完成《小門神》的全部1940個鏡頭,同時每個團隊每周要完成哪一個場景或者鏡頭,這些非常透明,所有人都可以看到,而且必須要知道。”
2014年夏天,《小門神》制作全面鋪開,剛開始時,各個環節都出了問題,沒有按進度推進,團隊為此制定了“追進計劃”,七個星期、六個周末,全公司周六上一天班,最終追回進度。2015年7月10日,《小門神》按原計劃殺青。
除了紀律,“追光”還注重流程。王微學計算機出身,作為一個理工男,他甚至是個技術控,并堅信“技術是動畫電影的精神”。早在成立提線動畫之前,即使在土豆網上市前最緊張的那段日子,他的北京辦公室會議桌上還堆著好幾本磚頭一樣厚的動畫制作書、Pixar的書,“我一般做什么事情之前會先買一些教科書,動畫到底怎么回事,歷史過程,動畫基本的原理之類的,就先看看。”王微說。
但閱讀和實踐之間,隔著幾重山。進入到真正的制作環節,王微才意識到制作的復雜性。“所有開發,它等于要搭建一個工程,你覺得一些簡單的程序,其實非常復雜,就跟建工廠差不多。”
到了于洲這里,工廠就是由每一個環節構成的流水線,“建工廠的首要環節是建立一個生產流水線,不同的軟件就像同一生產線的不同加工設備。”有了流程,才能能討論用什么軟件、工具更適合大規模、高品質動畫電影制作。
而生產線的搭建和運維都需要有技術人員,這是追光動畫最開始招聘的員工。技術人員為藝術家更好地實現創意提供了后勤保障。“但技術人員(TD)非常難找,國內的動畫電影公司TD的比例,差不多是1:50,即50個藝術家或者藝術人才,差不多一個TD技術人員。我們現在是1:7——160個制作團隊有20個是TD,130個藝術人才,剩下的將近10人是管理人員。”
工位的設置按照制作流程順序往下。模型制作師負責把紙上的平面形象轉化為三維立體形象,他時常是對著一個石膏雕塑凝神發呆。而隔壁的綁定組的計算機屏幕上,已經創建完成的人物模型身上多了很多線條——一個三維模型在制作完成后,是不能直接被動畫師操控的,需要綁定師為模型添加骨骼和關節,以及能精確操作的控制器。動畫電影制作中,人、動物、機械、道具等所有需要動的模型都需要綁定,而綁定越精細準確,后期人物的動作才能更生動真實。
下一個環節的動畫師正對著鏡子旁若無人地做各種表情包,為了更好地表現角色的面部特征,每個動畫師的桌子上都有一面鏡子,工作狀態下,動畫師每天照800遍鏡子也不足為奇。
三維分鏡、角色特效,材質組、燈光組,十幾個部門依次鋪開,除了幾間會議室,“夸父樓”沒有單獨分隔的辦公室。CEO王微的辦公桌也在這個開放空間里,位于西南角落,他對面是制片人于洲的辦公桌,兩者沒有任何區別。
《小門神》的項目管理表上有一個甘特圖(Gantt chart),就像日歷,在上面標注每天團隊的所有任務。于洲反問記者,你知道每天在系統上運行的任務有多少個?頓了一頓他揭曉謎底:三千個。
“我們平均每天都有三千個任務在系統上,正在進行中的任務。《小門神》中有140個角色,每個角色可能有上百個任務。一個角色需要設計、模型、毛發、衣服,身上的道具,而一件衣服又細分出來,需要設計、模型等等,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他解釋說。
比如一個不足4秒的鏡頭,在劇本里僅僅20字,“門神年畫下,祖孫三代埋頭默默地吃著熱的餛飩”,但從故事板、模型、三維分鏡、角色特效到最后的數字繪景,整個流程歷經13個環節,用時349天。
而這只是全片1940個鏡頭中相對簡單的一個。于洲在《小門神》發布會上公布過一組數據,29個月,160個人,8000萬小時的全片渲染時長和102000個版本的修改。他笑稱“1個動畫師,用人間28800秒換來神界1秒”。
從IT男成為文藝男青年
從科技一步邁入文藝圈,外人覺得步子有點大,但熟悉王微的人并不感覺意外。王微有個博客,從2005年開始至今,陸續發布文章,文字利落而理性,那些認真的表達像是他人生履歷的一個備注。此外,這些年,他還做過很多文藝范兒的事情。
王微寫過一部小說,《等待夏天》,12萬字,講述幾個中國年輕人在美國冒險和掙扎,發表在2006年第五期《收獲》雜志上,一年后出版發行。他創作的話劇劇本《大院》被搬上舞臺,2011年7月在北京公演,央視主持人和晶任導演,著名話劇導演田沁鑫任藝術顧問。和晶評價劇本是“一個商業精英對社會做的觀察和思考”。從土豆網“退休”后,王微為《時尚先生》寫過專欄,內容都是他對生活的種種思考,無關商業。
在一次和家人去泰國旅游的途中,王微在泰皇宮門口看到了有兩個中國青石神像,“放在那兒特別突兀,國內很少看到這樣的青石。”王微回憶道。
他覺得“有意思”,任由好奇心勾著著思緒往前游走。“(如果)神仙、民俗這些東西都沒有,沒有人相信也沒有人需要它們,他們就失業了嗎?”王微寫下了《小門神》的故事雛形。“新舊更替沒有對或者不對,但這兩個門神一直在做同一份工作,正好卡到轉折點上,他們要怎么辦?做什么樣的選擇?”
王微是福建人,小時候每年都有四五個與風俗有關的節日,拜土地公、拜祖先或者各類神仙,“在奶奶家,每年八月中秋的時候,附近幾個村莊都會把本村供奉的神仙搬出來游街、比賽,也會有唱戲班子,特別熱鬧。”而時間過去,那些村莊被逐一推倒,漸次消失,高樓原地拔起,老家“現在是市區,內環以內,有一點北京三環以內的感覺”。
這也是他想做原創中國故事的初衷。對于中國來說,社會正在經歷巨大變化,然后該怎么辦?經濟轉型期,我們的根在哪里、傳統在哪?這些是王微關心的。此后故事一再修改,但總體框架和王微想傳達的這些核心,一直被他堅守。
王微喜歡思考哲學。他給員工推薦的也都是莫泊桑的小說、尼采的論著、榮格自傳這樣的書籍。
《小門神》最初創作的2012年、2013年,逃離北上廣的話題正興起。“失業”的王微正好回了一趟福州老家。20歲離家的王微是個游子,旅行的足跡遍布世界,但對故鄉的記憶依然停留在小時候的街頭巷尾,重回故鄉時,那些記憶都早已經變成了旅游區。
“一方面,覺得小時候的回憶還挺溫馨;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真的讓我回福州在小時候的環境住下來,估計夠嗆。回憶只是回憶,我不可能天天走在街上,天天覺得很溫馨,可能兩天我就煩了。這也是一個矛盾。”王微說,這些感覺觸動了他,在故事里他又加入了小英母女的故事,兩人因受挫折從大城市搬回故鄉,接手了祖輩傳下來的一家餛飩店。這個故事,承載了一些王微對根、故鄉和現代生活的思考。
2014年初,《小門神》出了第一版剪輯,剪輯師也是第一次做長片,大家都很興奮,最終剪完三個半小時,遠超過一部動畫片能被接受的時長。也許因為首部作品的關系,精剪的版本刪掉了許多最初設定的笑點和幾個段落,但王微堅持保留故事情節框架。
《小門神》的故事分為神界和人間兩條敘事線,各自獨立,但又互有交集。門神兄弟倆下崗后先后來到人間,遇到了小鎮上的單親母女小英和雨兒。
之后《小門神》辦了幾次試映會,觀眾也提出意見,認為故事太復雜了。為了讓觀眾把焦點更關注在兩個門神的身上,王微試圖對小英母女的故事做了一些刪減。但還是舍不得這條故事線。
《小門神》公映之后,動畫特效的制作水準受到普遍肯定,觀眾對于《小門神》的意見集中在劇情上。豆瓣上的短評寫道:“制作有亮點,劇情卻太過混亂,影片缺乏一些基本的邏輯性和條理。餛飩店與門神的故事結合得太松散了。”
想講的道理超過了一個故事能承載的容量,為了壓縮時間只能犧牲細節,壓縮情節,第一次接觸到這個故事的觀眾看得有點蒙。《小門神》像一塊壓縮餅干,入口干澀,需要時間消化。對于定位在合家歡的動畫電影來說,它想表達的有點多了。
《小門神》只是一個開始
成立“追光”之初,整個團隊僅20多人,初入動畫行業的王微甚至不確定,自己劇本上的很多情節到底能不能被制作出來。
比如,在王微早先創作完成的劇本里,完全沒有意識到給角色換一套衣服是如此費力的一個過程。他設置了四季變化,季節一變化,角色就要換衣服,“每一季等于又做一個新的角色。”王微說。
他還寫了一場夜總會的戲,里面角色眾多,并安排有兩三百盞顏色不一的燈。光是布燈一項就已經讓動畫師崩潰。“追光動畫”的視效總監韓雷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解釋說,“燈是動畫電影最難操作的東西,因為光源所造成的環境氛圍和明暗差距并不是僅僅靠消耗人力和時間所能解決的,它更多是由非常復雜的計算機算法和渲染技術處理。”
最終,4分鐘的段落做了5個月的時間,是整部戲里成本耗費最高的場景。這場戲最終被“逼著”制作出來了,王微有些小欣喜,但也吸取經驗教訓,他說之后的作品,不會再急于“炫技”。
對于《小門神》最終的制作水準,王微是驕傲的。當初27人在雙子湖畔討論定下的的信條,“融合科技與藝術,不斷創造出前所未有的卓越作品”,被認真嚴格地執行了,并沿用至今。
但他也明白和真正世界一流的差距。“渲染的時候他們分七八層,每一層都有燈光的景深和控制,我們現在只能控制到3層,再多就崩了。”崩了,就是系統就跑不動了。皮克斯的片子每一個屏幕截圖下來,基本上都能當畫一樣去欣賞,但“追光”的畫面還是有小部分做不到。

《小門神》劇照。圖/CFP
現在“追光”已經擁有200人,平均年齡28歲。
蘇昊丹是“追光”的第18名員工,她負責故事板的創作。在進入追光之前,她在兩家動畫公司工作,有一個項目做了一年,還是黃了。她形容自己“那會兒就像一艘小船在波濤洶涌的海浪上,一個勁兒想往前沖,但是浪太大了”。但在“追光”她感覺到了踏實,讓她能安心沉浸于專業。
雖然已經看過千百遍,蘇昊丹還是專門買了票到電影院看,“沒有第一次看的驚喜感,但音樂一響起就想哭”。對于蘇昊丹來說,《小門神》已經是很久之前的工作了,過去一年,她和團隊,已經完成了“追光”第二部動畫作品的故事板創作,目前已經馬不停蹄進入第三部作品的故事板繪制。
《小門神》存在很多遺憾,有瑕疵,不完美,但足夠誠意。蘇昊丹相信,“追光”的第二部長片還會有進步。經過《小門神》,團隊得到磨合,流程進一步優化。從第二部電影開始,她和故事板的團隊也從早期就介入了劇本的討論。她透露,第二部的笑點會比《小門神》多很多。
一名“追光”的員工曾寫道,“贊美《大圣歸來》是能體會到它的艱辛,但不代表贊同它路線成功。8年磨一劍,磨出了主創,也磨死了很多從業者的夢想。片子的計劃肯定不是八年才做完。而參與的大多數人也不知道做完了《大圣》下一個腳印該踩在哪里。”他感謝“互聯網那頭殺過來的Boss給CG行業吹來一陣健康的風,吹掉了這個華麗麗外表上那層硬邦邦的行業淤泥”。
王微說,之前做的所有事情,都是科技類的事情,現在回想起來,卻沒什么印象,“這是科技類產品的悲哀吧。從面市的第一天起,科技產品就過時了”。他說“追光”的目標,是創作一些能被記住和流傳的東西。
《小門神》只是“追光”的一個開始。動畫電影這座殿堂,王微才剛把門打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