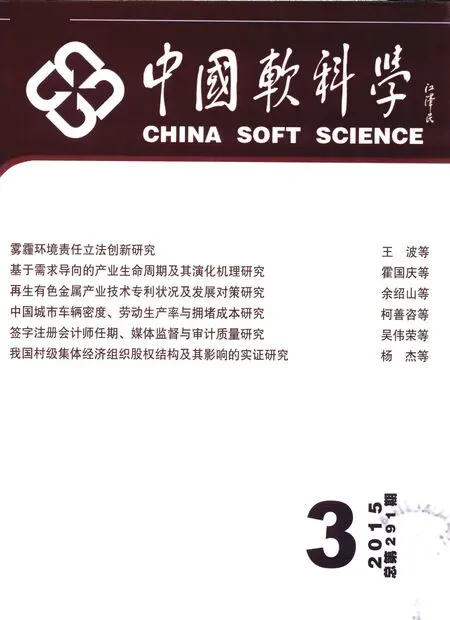新型產業分工、功能專業化與區域治理 ——基于京津冀地區的實證研究
新型產業分工、功能專業化與區域治理
——基于京津冀地區的實證研究
李靖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北京100142)

摘要:本文對當前出現的新型產業分工現象進行研究。首先,研究新型產業分工的形成機制、類型和特征,研究發現新型產業分工的發展可以形成地區功能專業化,這與傳統分工的效應不同。接著,對新型產業分工進行實證檢驗,選取具有典型意義的京津冀都市圈地區,研究新型產業分工在我國特定區域的發展程度。實證結果基本符合預期,即各類區域的功能專業化水平表現出不同的發展趨勢,而且在都市圈內部,區域功能專業化表現出較為明顯的層次。最后,將研究結論落實到我國區域治理,提出了新型產業分工形勢下,基于功能專業化的都市圈治理理念和相應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新型產業分工;功能專業化;都市圈治理
收稿日期:2014-10-15修回日期:2015-01-03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中國企業遷移的決定因素與區位政策研究》(70473098)及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61188)資助項目。
作者簡介:李靖(1978-),女,山東臨沂人,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產業經濟、區域發展與財稅政策。
中圖分類號:F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9753(2015)03-0080-13
Abstract:This article researched the new industrial division of labor appearing at present.First,the formation mechanism,classific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ew industrial division of labor had been researched,and the author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industrial division of labor could form regional functional specialization,which was different from the effect in the traditional division of labor.Then,the author selected the typ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tan region and studied the new industrial division of labor in a particular region in China.Through the empirical test,the author found empirical results were basically in line with expectations,that is,functional specialization level in various regions showed different trends of development,and in the metropolitan region,the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of function showed obvious hierarchy.Finally,th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was used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gional governance in China,and the metropolitan governance idea based on functional specialization and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had been put forward.

New Industrial Division of Labor,Functional Specialization and Regional Governance:
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tan Region
LI Jing
(TheResearchInstituteforFiscalScienceMinistryofFinance,Beijing100142,China)
Key words:new industrial division of labor; functional specialization; governance of metropolitan region
一、引言
在人類發展的過程中,分工在促進經濟和社會進步方面表現出巨大的作用,而分工本身也在不斷向前發展。從最初的部門分工到產品分工,分工取得了巨大的進步;而隨著分工的不斷演進,以產業鏈分工為代表的一種新的分工形式開始出現,它不再將一項產品或服務的所有過程局限在一個企業或某個區域進行,而是根據不同生產環節的要求,分布到具備生產條件的多個區域進行,然后通過產業鏈各環節的有序協作,完成最終產品或服務的供給。新型產業分工是在產業層面上進行的,在區域層面則產生了功能專業化效應。在新型產業分工體系下,區域可以根據自身比較優勢,承接產業鏈不同環節的生產和經營,區域之間通過產業鏈上下游的緊密協作,完成跨區域資源配置,并形成各自區域的核心競爭力。
新型產業分工不但可以發揮地區比較優勢,而且加大了區域之間的溝通與協作。在產業鏈運轉的整個過程中,不同區域提供的是真正的差異化產品,因此,區域之間就不需要僅從競爭中尋求利益,可以更多地通過合作實現自我發展。因此,這種充分發揮區域比較優勢、建立在區域協作基礎上的新型產業分工模式,可以解決當前區際合作不暢通、產業惡性競爭、區域發展不平衡和環境矛盾日益突出等問題,引導區域形成良性發展的格局。
近年來,新型產業分工這一現象逐漸受到重視,與之相關的研究成果在最近十年陸續出現,主要集中在國際分工、產業經濟和區域發展等學科領域。國內外學界對新型產業分工的研究總結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研究新型產業分工的現象,對它的特征及與以往分工的不同進行探討。隨著海外組裝、外包生產方式的出現,國外學者開始對生產環節的多國家配置進行了研究。Dixit and Grossman(1982)曾考察多區段生產系統如何在不同國家進行分配,并建立了理論模型進行分析[1]。Jones and Kierzkowski(1990)研究了“生產過程分離并散布到不同空間區位”的分工狀態,并將其稱為“零散化生產”[2]。 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國學者從國際分工角度提出新型產業分工和中國(或某些區域)面臨的機遇問題,魏后凱(2001)認為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型產業分工,特別要重視全球性產業鏈和地區性產業鏈對傳統分工理論的挑戰[3]。二是對分工的影響因素進行研究,比較優勢、規模經濟、技術和貿易壁壘等因素受到重視,但究竟什么是推動新型產業分工的源泉尚未形成共識。Jones(2001)等人提出了“技術說”,認為技術進步是推動產品內分工發展的重要原因。認為對于勞動力豐富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可以通過參與勞動密集工序的生產而獲利[4]。Deardorff(1998)提出“壁壘說”,認為產品內分工本來在技術上是可行的,但某些壁壘的存在會阻礙它的進一步發展[5]。李小建等(2004)認為規模經濟、分工經濟和網絡聯系被認為是產業集群所共有的競爭優勢的三個重要來源,所以集群的收益遞增速度必然大于其周圍非集群區域的收益遞增速度[6]。三是對新型產業分工的度量提出了一些方法,尤其國外有些學者試圖在傳統分工框架下,通過一些條件的改變,對分工的新現象重新詮釋,但尚未形成統一的研究體系。Arndt(1997)利用國際貿易常規分析技術,對全球外包和轉包等現象進行了研究[7]。Durantou and Puga(2002)以城市為地域研究單元,將產業研究與區域研究緊密結合起來,用就業數據比較了美國都市在1977-1997年間部門專業化和功能專業化的變化趨勢[8]。Feenstra(2003)將外包分為垂直一體化和垂直分離化兩種形式,分別置于激勵理論和產權理論下進行研究,并采用中國1997-1999年出口加工業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9]。張紀(2006)以筆記本電腦行業為例,對產品內國際分工的收益分配進行了研究[10]。四是雖然新型產業分工的研究逐漸增多,但目前對這種分工還沒有給出明確的界定。Ardnt 于1997年首次提出產品內分工的概念,并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對這一現象進行了開拓性的研究[7]。盧峰(2004)最早指出產品內分工是一種更為細致深入的國際分工形態,并認為產品內分工與產業內分工有著本質區別[11]。田文(2005)則認為產業內貿易與產品內貿易是有交集的[12]。魏后凱(2007)認為,由于這種發生在產業鏈內部的新型分工形式具有顯著的區域特征,在區域競爭與合作的過程中,推進形成一體化的新型產業分工體系,是消除和緩解大都市區產業發展惡性沖突的有效途徑,因此,將其稱為“新型區域產業分工”[13]。筆者(2007)沿用了魏后凱做出的“新型區域產業分工”概念,并對這種新型分工現象的區域和產業兩種特性做了進一步研究[14]。筆者(2009)在繼續研究中發現,雖然這種新型分工形式具有雙重屬性,但產業屬性更為本質[15],區域屬性則是其具體的空間表現形式,因此,提出“新型產業分工”這一概念,并在專著(2012)中給出了定義[16],指出它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區域和產業分工呈現出的新特點和發展趨勢,新型產業分工的形成在區域層面又必然帶來功能專業化。
為探討新型產業分工對區域發展和區域關系的作用,本文首先從理論上研究新型產業分工的來源、類型和特征,并探討了其形成的動力機制。然后選取特定地區進行實證研究。研究認為,目前我國有些區域已經表現出新型產業分工的趨勢,這些區域不但形成了較強的產業競爭力,而且區域內部產業關聯度高,區域整體呈現持續發展態勢,這從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明新型產業分工對于重塑區域發展格局的推動力。作為分工發展歷程的一個新階段,新型產業分工對于區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因此,本文提出我國應加快推動從傳統分工向新型產業分工的戰略轉變。鑒于當前我國正處于傳統分工和新型產業分工等形式并存的局面,國家政策應該做出相應的調整。首先,要從戰略上對區域發展的指導思想做出調整,在市場發揮決定作用的前提下,政府要加強跨區域產業分工的引導與協調,規范我國區域發展秩序,加快推動新型產業分工格局的形成。其次,新型產業分工形成區域功能專業化,地區比較優勢的充分發揮會強化地區間經濟的不平衡程度,因此,國家要出臺相應的財稅政策,對資源輸出區和生態涵養區給予合理的援助和補償,以達到基本公共服務的空間均衡。
二、新型產業分工的形成與類型特征
產業分工發展的歷程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部門分工,不同區域重點發展不同類型的產業部門,它是經濟發展早期的產業分工形式。第二階段為產品分工,不同區域可能選擇發展同一個產業,但其產品種類不同。近年來,產業分工出現了一種新的形式,同一產品的生產分布到不同地區來進行,從產業或產品角度來看,這些地區存在結構雷同。但透過產業鏈可以發現,這些區域按照產業鏈的不同環節、工序甚至模塊進行專業化生產,各地生產環節不但沒有雷同,而且形成了跨區域協作分工。這種新的分工形式與以往分工不同,承擔不同生產環節的地區一般不直接向市場供給完整的消費品或服務,而要通過跨區域的協作,最終完成產品或服務向市場的提供,這是分工發展的第三個階段,我們將其稱為新型產業分工。
1.新型產業分工的形成機制
新型產業分工是分工向更深入、更細化領域發展的結果,它的形成機制有兩個:交易成本和市場需求。其中,交易成本是新型產業分工形成的必要條件,市場需求則是根本動力。
(1)交易成本的降低。交易成本降低或交易效率的提升是分工得以深化發展的必要條件。交易成本降低源于三個方面:
一是交通通訊技術的發展。技術進步與信息革命有力地推動了分工向縱深領域拓展。從18世紀60年代到19世紀中葉的工業革命,帶來了交通運輸工具和通訊工具的變革,運輸速度大幅提升并降低了各項費用;19世紀下半葉第二次工業革命發生后,電力、電報、電話及海底電纜等現代通訊工具陸續出現,使信息傳播日益廣泛和迅速。20世紀中葉發生的信息技術革命,使人們之間的溝通、交易變得更加方便、高效和低廉,極大地突破了時間、地域的限制。現今,互聯網交易不但降低了信息溝通的空間距離和流通時間,而且讓整個過程趨于更加透明、規范。技術的發展也為廣大發展中國家以及大量的中小企業參與國際分工提供了條件,進一步擴大了產業分工的地域范圍。
二是生產技術的進步。由于技術的進步,生產方式得到改進,更深的專業化生產才可以實現。技術進步是產業鏈環節可分性增加的必要條件,例如,傳統農業由于生產受地域限制而無法像工業那樣進行細密的分工,但無土栽培技術使耕地的不可移動性減弱;制造業的標準化生產使很多環節可以從垂直一體化的工廠中分包出去。20世紀90年代以來,模塊化生產方式幾乎讓生產環節可以完全分離。生產技術提升是分工不斷深化和空間分離的基礎。
三是地區開放制度和產權制度的建立。經濟全球化加快了國家和地區開放制度的實施,有利推動了市場環境的改善。通過降低貿易壁壘,取消貿易歧視等政策來擴大國內市場的開放程度,加快了商品和服務更大程度的自由流動。經濟全球化下的國家開放戰略,不但創造了新的分工與交易機會,也降低了勞動生產過程空間分離的成本。制度可以降低交易的不確定性,從而提高交易效率,而其中以產權制度尤為突出。產權實際上是交易的前提,隨著產權的明確化、受保護程度的提高,交易效率也逐漸提高,分工演進的速度因此加快。
(2)市場需求的規模化與多樣化
一市場規模的擴大。市場容量的擴大,使更深程度的分工和專業化變為可能。出于交換的需要,斯密指出分工要受市場的限制。斯蒂格勒(Stigler,1951)在比較1919年和1937年美國工廠數據后發現,當一個產業發展到成熟期時,由于市場擴大使產業內分工越來越細,廠商功能越來越單一而活動范圍越來越小,這一證據表明了市場容量對分工的決定作用。究其原理,即市場規模的擴大可以使專業化生產達到規模經濟的要求,從而形成個人和企業之間的進一步分工(如圖1)[17]。

圖1 市場規模擴大與分工深化的可能性
假設廠商的生產分為三個階段,其平均成本分別為ATC1,ATC2和ATC3,其中,工序1為收益遞減,工序2收益遞增,工序3先遞增后遞減。廠商的總平均成本為ATCc。如果產出為q1,則總的平均成本為C1。如果市場足夠大,工序2可能由某個專業化的廠商從事,由于工序2為收益遞增,所以專業化廠商能以更低的價格,如p2來出售其生產或服務。這時,原廠商的總成本曲線就會從ATCc移動到ATCc’,總成本相應地從C1降到C2。即隨著市場范圍的擴大,專業化生產會使總平均成本降低,從而使分工的深化成為可能。
二消費需求的多樣化。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消費者從購買大規模生產的商品逐漸轉向多樣化消費,個性化商品的需求開始出現。標準化的大規模生產領域得到限制甚至某些領域出現收縮,與之替代的則是 “柔性專業化”(Piore and Sabel,1984)生產方式[18]。伴隨著大規模生產向柔性化定制的轉變,大型一體化企業開始解體,分包、轉包等企業組織形式出現。為了滿足不同地區人群的需求,跨國企業尋求在全球范圍內組織生產,因此,生產環節在空間布局上逐漸分散。各類分包企業不但可以選擇在要素等條件優越的地區進行生產,解決原有企業資源緊缺的狀態,而且可以根據當地需求做出一定的設計改進和戰略調整,提高產品的本地化水平,解決產品的市場銷售問題。與大規模生產相比,柔性化生產模式滿足了個性需求、提高了生產效率,使分工程度更加深化。
2.新型產業分工的界定和類型特征
部門分工、產品分工是分工發展的前兩個階段,當前它們雖然仍大量存在,但其發展已經過了較長的歷史,在此,稱之為傳統產業分工。而上述第三階段的分工是當前出現的一種新的分工形式,將其稱為新型產業分工,并予以界定:新型產業分工以產業鏈為主要形式,表現為特定產品從生產到銷售服務等一系列過程中,不同工序或區段在空間上產生分離,在地域上表現為產業鏈環節的縱向分離與同類集中,從而形成一種跨區域的產業鏈分工協作狀態[16]。新型產業分工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產業分工的發展趨勢。從產業角度來看,新型產業分工從研發、加工制造、到營銷服務等一系列過程,表現出跨產業的協作性;從空間角度來看,新型產業分工的整個運作過程分布到不同區域進行,體現了這種分工形式在空間上的分離性。
新型產業分工的出現是分工發展史上的又一次變革,它表現出與以往分工形式較多不同。第一階段的部門分工是在農業、工業和商業等不同產業之間的分工,并形成了部門專業化,即馬克思所說的一般分工,這一次分工的產業界限明確,比較優勢理論和要素稟賦理論對這種分工做出了較多的解釋;分工繼而過渡到產品分工,即在同一產業內部由于產品的差別產生了分工和貿易往來,由此形成了產品專業化,雖然產業界限已經模糊,但產品之間的分工界限較為清晰,新國際貿易理論主要通過規模經濟等要素的引入對其進行了解釋。當前出現的新型產業分工,主要以產業鏈分工的形式表現出來。產業鏈由不同特性的環節構成,各個環節按照不同的要求,可以將其生產活動分布到不同的區域進行。這些環節雖然同屬于一種最終產品,但它們作為中間產品又具有各自的主要功能和優勢特征,于是形成了區域的功能專業化(Duranton & Puga,2003)[19]。模塊化分工可以作為產業鏈分工的一種特例,因為模塊首先是產業鏈的一個環節,它是產業鏈縱向分解的產物,其次它的獨立性更強,能適應分工進一步深化的要求。模塊這種半自律系統,本身可以獨立運作,它不但可以達到更高的標準化要求,而且在信息的保密性能方面比產業鏈的一般環節要優越,可以說模塊是產業鏈分工在某些產業領域的典型體現。

表1 新型產業分工的類型及特征比較
資料來源:據魏后凱(2007)整理[14]。
產業鏈可以跨越一國之內的不同區域,也可能跨越國界,在全球范圍內安排生產運行。因此,根據區域范圍的不同,新型產業分工可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產業鏈在國內區域間的分工;另一類是產業鏈的國際分工。雖然區域概念沒有范圍大小的具體要求,但在產業分工研究中,國內區域和跨國界區域有所不同,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1)要素流動性不同。國內各區域之間雖然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地方保護主義,但相比國家之間,各國出于國家利益、安全等問題的考慮,要素的流動遠比國內要困難得多;(2)國家政策的影響程度或政府的協調力度不同。對于一國內部的跨區域產業分工,國家可以從宏觀上進行調控,及時協調各地區的利益平衡,但是跨國界的分工則更多地要遵循國際制度或市場規則,各國政府的調控力度較低。因此,從國家政策層面來看,對于國內區域間產業分工的研究更有現實意義。(3)利益追求或目標不同。區域雖然是相對獨立的利益主體,但國內區域利益主體與不同國家之間的區域利益主體存在一定的差別。一定程度上,區域可能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標,但國家內部區域間分工格局的最終形成,卻要取決于區域局部利益與國家整體利益的平衡,有時甚至更多考慮整體利益的最大化。本文將區域限定在國家內部,即研究國內區域之間的新型產業分工,并探討其對我國區域發展的影響及政策意義等。
三、新型產業分工下的地區功能專業化
分工與專業化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有什么水平的分工,則對應什么程度的專業化。地區專業化是生產專業化的空間表現形式,是勞動地域分工不斷深化的結果。地區專業化(Regional Specialization)即“各區域專門生產某種產品,有時是某一類產品甚至是產品的一部分”(列寧,1960)[20]。地區專業化生產,一方面使各地區按照自身的資源稟賦和市場需求進行專業化生產,帶來明顯的經濟效益;另一方面,地區專業化有利于發揮機械化的效力,便于加強經濟管理,提高勞動技能和勞動素質,廣泛開展資源綜合利用,充分利用規模經濟和集聚經濟,從而為最大程度地提高勞動生產效率提供可能(魏后凱,1995)[21]。
新型產業分工形成的是地區功能專業化,它主要有兩個特點:第一,功能專業化體現了產業鏈的跨區域分離。功能專業化對應的不再是一個完整的部門甚至產品,它只是形成最終產品的某個環節或階段的專業化,由于不同的環節對發展條件有特定的要求,因此表現在承接不同環節的區域專業功能的深化。例如,廣東省的專業鎮,從大的范圍來看,許多鎮都在生產同一種最終產品,而實際上這些鎮之間各有分工,一個鎮只生產某種產品的一個部分甚至一道工序,它們各自完成不同的工藝環節,并形成了一定規模的集聚,使專業鎮的特定生產功能得以實現。第二,功能專業化加深了區域之間的協作。產業鏈分工的深入,集中體現在地區專業化程度的提高。由于地區有各自的資源、市場等優勢,而產業鏈的各環節又對生產經營條件的要求不同,這兩方面的結合將加深地區功能的專業化,提高區域生產率和產業競爭力。從理論上來說,產業鏈從研發、產品設計、原材料采購、零部件生產、裝配、成品儲運、市場營銷到售后服務,每個環節都要在具有優勢條件的區域進行。只有通過跨區域協作,才能完成最終產品或服務,從而實現整條產業鏈的利益最大化。因此,新型產業分工的實現就是跨區域分工協作的過程。
新型產業分工的出現是與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的。對于這種新型分工形式的研究也較早出現在美國等先行工業化國家。杜蘭頓和蒲伽研究了美國不同類型城市的功能專業化,并于2002年將其成果公開發表。他們將美國城市按人口規模分成6個等級進行研究,結果表明,美國城市的部門專業化在不斷弱化,而功能專業化在逐步提高,即城市的專業功能在提升。具體表現為,大城市的經營管理職能在不斷加強,中小城市的生產制造功能在逐步強化,即說明,城市間的分工程度在不斷深化。
雖然我國工業化開始較晚,但新型產業分工在我國也已出現。尤其在東南沿海和大都市集聚區,新型產業分工和地區功能專業化特征已經顯現。新型產業分工具體體現在企業行為中,例如,企業選擇在不同地區安排生產時,從各地資源稟賦出發,并通過跨區域資源要素的整合,最終獲得成本較低且能更好滿足市場需求的產品,同時,這一過程也讓區域比較優勢得以發揮,從而促進了專業化功能區的形成。從產業層面,產業鏈環節在不同區域發生縱向分離,通過區域協作形成最終產品或服務;從區域層面,各地區按照產業鏈的不同環節、工序甚至模塊進行分工,形成各具特色的專業化城市或鄉鎮。在新型產業分工體系下,通過比較優勢的發揮,城市的核心功能進一步強化。各類城市或鄉鎮在市場資源配置中考慮自身定位,一些經濟發達的大城市,選擇在中心區著重發展公司總部、研發、設計、培訓以及營銷、批發零售、商標廣告管理、售后服務等產業環節;大城市郊區或中等城市側重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先進制造業;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則發展一般制造業和配套的零部件生產。由此,在一定范圍內,出現了特色產業環節與城市功能密切結合的格局,如圖2所示。

圖2 基于新型產業分工的功能專業化區域
目前,新型產業分工體系下的地區功能專業化在我國一些經濟發達的都市圈已有體現,例如,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地區。在都市圈內部,憑借近距離的優勢,跨區域新型產業分工可以更緊密地結合,共同形成以產業鏈分工協作為主導的都市圈產業體系。
四、功能專業化的檢驗:以京津冀都市圈為例
由于分工與專業化緊密相關,衡量分工發展的程度一般通過測度分工對應的專業化水平。新型產業分工對應的是地區功能專業化,因此,本文通過對地區功能專業化的檢驗來說明當前新型產業分工在我國的發展程度。
在分工發展的歷程中,新型產業分工出現的時間較晚,而且從我國目前產業分工的態勢看,部門分工、產品分工和新型產業分工多種形式并存,新型產業分工是否已成為一種主導形式還難以確定。因此,為檢驗新型產業分工在我國的發展程度,筆者選擇最有可能的區域進行研究,即經濟發展水平高、各地區之間存在較為緊密的經濟往來、各類城鎮具有一定層次關系的都市圈區域,以期取得較為典型的研究結果。
1.測量方法的建立
衡量地區部門專業化的指標和方法較多,例如,全域專業化指數、地區區位熵指數等,但地區功能專業化的測度卻面臨較大難題。第一,由于功能專業化不是發生在產業或產品之間,而是發生在產品內部的一種現象,因此,如果使用行業數據進行測度,至少要達到四位數分類,如此精細的行業分類數據難以從統計部門直接獲取。第二,如果利用企業數據,建立指標體系、分類匯總,因涉及產業鏈不同環節的確定,需要研究者具有分解整條產業鏈的能力,包括技術研發、生產管理、市場營銷以及投融資等知識,才能把企業恰當歸類,顯然這項工程非常龐大而復雜。而且,即使得出各個分行業的測度結果,也無法直接比較地區功能專業化,只能分行業比較地區功能專業化程度。由于這兩個難題,筆者以此選題做博士論文時,僅選擇汽車行業來衡量地區功能專業化水平,主要因為汽車產業鏈相對清晰,關鍵環節在業內已有共識,可以較容易地把汽車企業歸類整理。這項研究得出的結果只是汽車行業的在不同地間的新型產業分工水平。
新型產業分工不但表現出企業生產類型的差別,也體現在勞動者從事職業的不同。因此,筆者轉換了選取行業統計數據的一貫方式,考慮用勞動者的職業分工代替產業鏈分工來檢驗新型產業分工水平。在文獻閱讀中發現,由于諸多國家采用國際職業分類統計體系,學者們使用職業數據進行行業測度的研究在國外文獻中并不少見,從中可以找到一些可供參照的方法。本文根據專業化指數和區位熵指數的計算原理,參考杜蘭頓和蒲伽計算功能專業化的方法,構建地區功能專業化計算公式:
(1)
式中,s表示地區,S表示全國,下標i表示管理人員數,j表示生產人員數,si表示地區管理人員數,sj表示地區生產人員數,Si表示全國管理人員數,Sj表示全國生產人員數。本公式沒有絕對值符號,計算結果可能為正值或負值,當結果為正時,說明計算地區的功能專業化水平高于全國平均值,數值越大,專業化水平越高;當結果為負時,說明計算地區的功能專業化水平低于全國平均值,絕對值越大,專業化水平越低。
2.研究區域的選取
從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狀態來看,都市圈是發展較快的區域,而且對于周邊地區的帶動作用也較為明顯,因此,都市圈成為較明顯的區域經濟增長極,對于我國整體經濟的發展意義重大。我國目前有三個較為典型的都市圈,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都市圈。選擇京津冀都市圈作為實證研究的對象,主要考慮兩點原因:
第一,京津冀都市圈發展層次較明顯。京津冀都市圈分為較明顯的三個層次,北京為一級核心,天津相對于北京為次級中心,而河北省的廣大地區則為第三層次。在這三個層次中,城市發展的條件不同、定位不同,因此,從理論分析,該都市圈可以形成較明顯的產業分工協作體系。北京定位為國家首都、世界城市、歷史名城、宜居城市,應發揮政治、文化、交流與創新優勢,發展總部經濟;天津作為我國北方重要的工業城市,經濟力量雄厚、制造業發達,借助其港口優勢應該規劃建成“國際港口大都市和北方經濟中心”,重點發展現代制造業、信息技術業、海洋高新技術產業、國際航運和國際物流產業等(肖金成等,2006)[22];河北省作為京津兩市的主要腹地,自然資源豐富、勞動力價格較低,并具有一定的工業基礎,可以建成重化工業和制造業基地,同時發展京津農副產品供應基地、勞務輸出基地、能源和水資源基地及綠色生態基地。因此,三地存在跨區域分工協作的現實需要和可能性。
第二,鑒于首都的特殊性,對此都市圈產業分工研究具有較強的政策意義。京津冀都市圈是我國發展基礎較好、最具發展潛力的經濟區域之一。目前,該都市圈內部地區間的分工合作已經具有一定的基礎。京津冀都市圈是我國的政治文化中心所在地,也是目前我國北方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發展潛力最大的經濟核心區域。依據區域的資源稟賦和發展基礎,京津冀都市圈以發展知識型產業為龍頭,現代制造業為重點,加工型工業為支撐,逐步發展成為經濟、社會、環境協調,而具有國際、國內競爭力并帶動中國北方經濟發展的經濟中心區域為基礎,繼而則有可能發展成為全球經濟系統的重要節點和對全球經濟有強大影響及控制力的世界都市區。在推動區域協同發展的新形勢下,研究京津冀都市圈的新型產業分工體系,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
學者們對于京津冀都市圈范圍的確定有多種意見,從一些研究文獻來看,“1+1+8”模式被多次提及,它指以特大城市北京、區域中心城市天津為核心,包括河北省的石家莊、唐山、保定、秦皇島、廊坊、滄州、承德、張家口8個城市的圈層地區。可以看出,這種“1+1+8”模式的確定主要以城市規模及發展水平為主要依據,選擇了河北省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8個城市。但是,都市圈內部城市間聯系的強弱并非以經濟發展水平為唯一依據,還要考慮地理位置、歷史淵源等多個方面。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的發展,京津冀地區內部的聯系范圍在不斷擴大,因此,本文將京津冀都市圈的范圍加以拓展,即北京、天津二市及河北省的全部范圍。京津冀都市圈土地面積為21.64萬平方公里,2012年總人口10770萬人,地區生產總值57348.29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1.05%。
3.數據來源及說明
本文的功能專業化計算公式,是參考杜蘭頓和蒲伽在國際職業分類標準基礎上建立的,因此,將其應用到我國地區功能專業化檢測時,需要處理統計分類不統一的問題。美國等采用的國際標準職業分類是國際勞工組織(簡稱ILO)制定的,以最新的2008年國際職業分類標準(簡稱ISCO- 08)為例,它的分類依據是各類工作的“技能水平”和技能的“專業程度”,主要反映生產部門和勞動者的要求和利益,而我國的職業分類是按照社會工作性質同一性的基本原則進行的,主要服務于計劃管理部門(張迎春,2009)[23]。從“大類”看,國際職業分類與我國職業分類相差不大,而“中類”具有較大懸殊,因此,為了在公式使用時便于指標處理,本文在采用“大類”數據。將國際職業分類與我國職業分類的“大類”對比,如表2所示。

表2 ISO- 08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
資料來源:張迎春(2009)。
從表2可以看出,我國職業分類與國際標準的“大類”名稱有一定的差距,但從各項分類所包含的內容解釋來看則差別不大,結合“中類”(由于中類系列較多,在此不列出)所列的詳細內容,做如下處理:將我國職業分類中的第1大類“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業、事業單位負責人”近似于國際職業分類的第1大類“管理者”,即管理人員指標;將第6大類“生產、運輸設備操作人員及有關人員”近似于國際分類的第7大類“工藝與相關行業工”和第8大類“工廠、機械操作與裝配工”,即生產人員指標。
我國分地區的職業分類數據只有人口普查數據,沒在每年的勞動統計年鑒和就業統計年鑒中公布,因此,本研究只能依據建國以來六次人口普查資料。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尤其工業化進程,檢驗新型產業分工僅在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較高階段才有實際意義,因此,本研究選取了改革開放以后的四次人口普查,即第三次(1982年)、第四次(1990年)、第五次(2000年)和第六次(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并結合相關年度的《中國人口就業統計年鑒》中抽樣調查數據,進行對照。需要說明的是,由于我國第三次和第四次人口普查數據中,將各類機關單位的“工勤人員”也統計在內等原因,導致“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業、事業單位負責人”一項數量過大,近乎是第五次和第六次數據的十倍,筆者曾試圖按“中類”統計數據,考慮將黨群、機關、企業和事業單位管理人員等分開計算,但我國以上四次人口普查職業“中類”分類變化較大:第三次人口普查職業分類沒有“中類”統計;四次人口普查職業“中類”為4類,企業和事業兩項沒有分開;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職業“中類”為現在通用的5類。如果采用中類指標,各年度數據難以統一,因此,本文所做測算一概采用“大類”分類數據。
4.計算結果與分析
首先按照計算公式得出京津冀三地的功能專業化數值,由于地區功能專業化是與全國水平進行比較的結果,它顯示的是地區功能專業化水平的絕對值,如表3絕對值一欄所示。為了進一步分析京津冀三地比較的結果,本文又在功能專業化數值的基礎上,計算了離差,離差值可以突出顯示功能專業化在三地內部比較的結果。

表3 京津冀都市圈的功能專業化
第一,從功能專業化絕對值來看:
從檢測結果可以看出:本高速公路通車運營一年后路面產生了一定數量的微裂縫,隨著通車年限的增加,裂縫數量沒有持續增加,這是因為連續配筋混凝土路面產生的微裂縫分散面板開裂,同時路面板內鋼筋也承受了一定的收縮應力;裂縫平均寬度在通車兩年內沒有出現變化,之后便開始減小,這是因為早期裂縫出現后,隨著時間延長,路面板內的水泥繼續水化并析出水化物積聚填充微裂縫,從而使裂縫平均寬度減小。綜上所述,連續配筋混凝土路面具有良好耐久性能、穩定性能,通車運營3年后仍保持較好的路用性能,推薦其作為高速公路路面結構推廣使用。
(1)總體上,北京和天津兩地功能專業化水平較高,而且基本呈現上升趨勢,河北省功能專業化水平較低而且有下降趨勢。這種趨勢符合京津冀三地產業發展的實際狀況,也符合新型產業分工的演進規律,即在產業緊密關聯的都市圈內部,大城市功能專業化水平逐漸提升,中小城市則發展緩慢或呈現相對下降趨勢。
從圖3可以看出,2000年數值較為特殊,京津冀三地在2000年的數值都大幅高于其它時期,這說明從全國范圍來看,在這段時期,京津冀都市圈總體功能專業化水平有了較大提升。在這一時間點上,從京津冀三地比較來看,仍表現出北京最高、天津其次、河北最低的格局,符合都市圈內部產業分工的總體趨勢。

圖3 京津冀功能專業化發展趨勢示意
(2)北京的功能專業化水平普遍高于天津,說明京津兩地在產業分工領域有一定的層次性和互補性;但北京功能專業化水平在2000年達到最高值,2010年則出現下降趨勢,說明北京在此階段之后產業發展做出了戰略調整,可能與北京大力推進首都非核心功能疏解,將工業向外搬遷而著重發展科技創新和現代服務經濟有關。
天津市的功能專業化一直處于上升狀態,體現了天津在產業發展進程中的連貫性。以2000年為分界點,此前本市的功能專業化水平成加速增長趨勢,2000年之后增長速度則有所放緩,這與天津市工業化發展進程的趨勢相符合,即由快速推進逐漸轉向穩步發展和產業調整升級階段。
河北省的功能專業化水平在最初時期較高,但隨著時間推移,先是落后于北京,接著落后于天津,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河北省產業發展逐漸融入京津冀都市圈,并與京津兩地產業形成一定的互補。
第二,從功能專業化相對值來看:
為了更清晰地看出京津冀都市圈內部功能專業化的相對水平,消除某些時間數據普遍偏高(2000年數值)或偏低的情況,本文對功能專業化數值進行了離差計算并繪制趨勢圖。
從表3可以看出,北京的功能專業化離差一直為正值,即功能專業化水平一直高于京津冀三地的平均值;天津的功能專業化離差值起初低于平均值,但由于一直呈現上升趨勢,最后高于平均值;河北則一直表現出下降趨勢,并于第二個時間點1990年開始轉為負值,即低于三地平均水平。如圖4,通過離差的比較,我們可以看出,在京津冀都市圈內部,三地的功能專業化水平呈現明顯的層次性,并與城市功能定位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表現出較高的一致性,即在都市圈內部,新型產業分工的模式較為清晰。

圖4 京津冀功能專業化離差示意
5.小結
選取都市圈為案例,通過以上計算和分析表明:第一,總體上,新型產業分工在京津冀都市圈得到了較好的驗證。新型產業分工帶來的地區功能專業化不但表現出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緊密相關的特性,即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功能專業化水平也相對較高,而且在地域臨近、經濟聯系緊密的區域,隨著經濟的發展,新型產業分工趨勢日益明顯。第二,國家經濟發展戰略和階段性政策對地區功能專業化的變化趨勢產生明顯的影響。在國家鼓勵產業發展規模化、集聚化時期,地區功能專業化提升加快,而在政府政策倡導城市非核心功能疏解和轉型升級的戰略下,地區功能專業化則出現放緩或減速趨勢。這一結論為從國家層面實施跨區域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據。
五、基于功能專業化的跨區域治理:推進都市圈協同發展
新型產業分工是建立在產業鏈運作基礎上的分工形式,一方面,可以充分發揮地區比較優勢、提高地區功能專業化水平;另一方面,有助于加強區域之間的溝通與協作。因此,它為我國推動區域經濟發展和跨區域治理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但是,完全由市場機制決定的新型產業分工會在發揮地區比較優勢的基礎上,不斷強化地區功能專業化水平,從而加劇區域發展的不平衡,因此,需要政府進行適當的引導和調控,在發揮效率的同時兼顧公平,推動區域步入良性發展的軌道。
1.消除區域市場分割,促進要素流動,在更大范圍內推動新型產業分工的形成
生產要素的充分、自由流動,既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區域發揮比較優勢、形成合理分工的前提條件。根據俄林的要素稟賦理論,要使各區域按照其要素稟賦組織經濟活動,實現區域分工,區域間要素流動是自由的。只有在要素充分流動的前提下,企業才能根據區內要素供給,選擇最能體現區域優勢的要素組合來安排生產活動。因此,促進要素自由流動,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體系是推進新型產業分工的必要前提。然而,我國區域關系卻存在著較大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地方政府發展經濟權限的不斷擴大,地區之間在原料和市場等方面惡性競爭、相互封鎖等現象屢見不鮮。尤其隨著我國工業化進程的推進,重化工業的發展導致地方政府大肆爭奪資源要素,形成重復建設、原料大戰、市場封鎖和價格大戰等規模大、范圍廣、破壞性強的“區域大戰”(張可云,2001)[24]。要推進新型產業分工,必須結束地區分割與行政壟斷下的區域惡性競爭局面,建立合理的區域發展秩序。
當前形勢下,充分發揮地區比較優勢,推動全國更大范圍內新型產業分工格局的形成是跨區域治理的一項綜合戰略。為發揮市場資源配置的決定作用,首先要加強區域關系范疇的制度建設,為規范地方政府行為提供依據。制度基礎是區域經濟關系協調的“核心”,沒有基本的制度框架,再好的政策和規劃也很難操作,而制度的完善有兩個標志,即區域管理機構設置合理和區域劃分框架明確(張可云,2001)。然后確立行政干預機制,及時解決區域間的利益爭端。中央政府作為國家經濟利益的最高代表,以國家整體利益最大化為其實現的目標;地方政府作為相對獨立的利益主體,難免為了自身的利益在經濟活動中產生沖突。這時,中央政府有權力也有責任對區域關系與區域利益做出協調。例如,嚴禁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打破地區分割局面;實行區際經濟銜接和協調政策,避免貿易封鎖以及隨之而來的重復建設等。
2.對重點區域加強政策引導,在新型產業分工基礎上推進都市圈協同發展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和地區投資環境的改善,跨區域產業轉移在逐漸推進。在沿海城市加快產業轉型升級的同時,必須優化當前產業跨區域分工的格局,不能簡單地將東部地區資源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中西部,而是要在產業鏈分工協作的基礎上推動跨區域轉移,從而構建新型產業分工格局。只有建立在地區產業鏈關聯基礎上的產業轉移,才能更好地發揮地區比較優勢并有持續發展的動力。
都市圈是中心城市拓展與周邊城市聚集融合而形成的空間體,它作為區域經濟高度關聯的城市聚集體,已成為國家或地區拓展發展空間和獲得區域競爭力的戰略重點。從我國都市圈的產業發展來看,大概有兩方面特征:一基于相似的自然歷史條件,形成了具有一定地區特色的產業集中區;二以中心大城市為主導,各級城市間具有一定的產業分工與配套關聯(張兆安,2006)[25]。當前我國以都市圈為重點,加快推動新型產業分工的形成是較為現實的選擇,而且國家應該建立健全區域利益協調機制,采取適當的政策措施,為都市圈內產業分工發展提供保障。以京津冀都市圈為例,鑒于目前首都功能重新定位和非核心功能向外疏解的需求,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勢在必行。
(1)加強行政協調力度,探討區域性合作組織的建立
區域性合作組織建立可以對都市圈經濟協調發展提供有力保障。根據國外區域合作的經驗,推動一定區域范圍內的合作,區域合作同盟機構的建立非常必要。區域合作同盟機構可以協調區域合作同盟成員之間的關系,制定區域合作的章程及有關規則,制定區域發展規劃,并處理合作同盟成員之間發生的各種矛盾等。雖然京津冀有過經濟技術合作組織的建立,但其協調力度遠遠不夠。當前,應從區域協同角度,積極構建三地多政府合作管理模式,在財政領域推行改革,逐步形成財力分擔、過程合作、成果共享的長效機制。通過財政領域的切實合作,才可以將跨區域協作機構的工作落到實處。
(2)盡快在資源交通等基礎設施、產業配套體系等領域開展實質性合作
在城市聚集程度較高的都市圈率先推動新型產業分工,就是考慮到都市圈內已有或可能較快建立統一完善的基礎設施體系,為產業分工協作提供基礎。以大都市為中心,強化交通運輸網絡特別是城際快速通道建設,加快建立一體化的1小時或2小時產業協作配套圈,才能有效提高都市圈內產業協作配套能力。這種產業配套不僅包括基礎設施的配套,更包括生產、生活配套和創業環境配套(魏后凱,2007)。
對于都市圈內部基礎設施的建設與完善,需要統一規劃,各級城市聯手共建,逐漸形成區內、城市各層次配套的綜合網絡體系。中央政府的協調作用和地方政府間的密切合作都必不可少。在樹立一體化發展理念的基礎上,統一協調京津冀大型基礎設施規劃建設是最具先行性和必要性的。深度聯合發展大流通,構建京津冀區域一體化交通信息網絡體系,一是地方財政共同出資,設立專項支持資金;二是國家可從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和支持新型產業分工示范區的角度,給予一定的轉移支付等財力支持,激發各級政府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為都市圈新型產業分工體系的形成提供基礎。
3.建立補償和援助機制,促進基本公共服務空間均衡
新型產業分工可以充分發揮地區比較優勢并提高發展效率,但由此帶來的功能專業化也將加劇區域發展的不平衡。在新型產業分工體系下,處于產業鏈不同環節的區域獲得的價值回報不同,多數區域提供的只是中間產品,有的地區甚至提供的只是資源要素,得到的價值補償極低。因此,考慮到輸出區域在資源和環境的損失,以及依靠市場機制難以得到合理補償的情況,國家應該充分發揮跨區域協調作用,給予一定的資源或生態補償和發展援助。
在區域差異擴大和彌合的過程中,并非任由市場機制任意擴大其作用范圍,政府政策時刻都試圖進行反向調節并發揮著重要作用(賈康、馬衍偉,2008)[26],建立生態補償長效機制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措施。按照誰開發誰保護、誰受益誰補償的原則,通過轉移支付等財政政策,建立自然保護區、重要生態功能區以及流域水環境保護等重點領域的生態補償標準體系,明確生態補償的資金來源、補償方式以及相應的保障體系。
政策性援助通常是政府在國家建設和經濟發展中對欠發達區域或問題區域實施的一種措施。在我國,政策性援助在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之間較為普遍。政策援助機制的建立,首先通過縱向轉移支付等手段對問題區域做好環境的綜合治理和欠發達地區的開發整治;其次針對問題區域的衰退產業進行援助,在有條件的區域,培育新興產業,保障資源型產業平穩退出和資源型城市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張國寶,2008)[27];然后要考慮對問題區域或欠發達地區的人口援助以及通過適當的政策措施引導人口向適宜地區轉移或回流等。
總之,為實現新型產業分工體系下的跨區域治理,國家要按照符合市場經濟規律導向實施更細致、更有針對性的差異化調控政策,從而增強區域調控的有效性和科學性,逐步達到資源要素合理流動、經濟效率提升、促進環境保護以及使居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綜合目標。
參考文獻:
[1]Dixit Avinash K,Gene M.Grossman.Trade and protection with multistage production[J].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82,49(4):583-594.
[2]Jones Ronald W,Kierzkowski Henryk.The role of services in prod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J].in R.W.Jones and A.O.Krueger (ed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Oxford: Blackwell,1990:31- 48.
[3]魏后凱.走向可持續協調發展[M].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2001.
[4]Jones Ronald W,Kierzkowski Henryk.A framework for fragmentation[C].Tinbergen Institute Discussion Paper,2001.
[5]Deardorff Alan V.Fragmentation Across Cones[C].RISE Discussion Paper,1998,No.427.
[6]李小建,李二玲.中國中部農區企業集群的競爭優勢研究——以河南省虞城縣南莊村鋼卷尺企業集群為例[J].地理科學,2004(4):136-143.
[7]Arndt Sven W.Globalization and the open economy[J].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1997,8(1): 71-79.
[8]Duranton G,Puga D.From sector to functional urban specialization[C].Cambridge,MA.National Bureau of Econ ̄omic Research,2002.
[9]Feenstra Robert C.Ownership and control in outsourcing to China[C].NBER Working Paper,2003,No.10198.
[10]張紀.產品內國際分工中的收益分配——基于筆記本電腦商品鏈的分析[J].中國工業經濟,2006(7):36- 44.
[7]Arndt Sven W.Globalization and the open economy[J].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1997,8(1): 71-79.
[11]盧鋒.產品內分工[J].經濟學(季刊),2004(10):55-82.
[12]田文.產品內貿易的定義、計量及比較分析[J].財貿經濟,2005(5):77-79.
[13]魏后凱.大都市區新型產業分工與沖突管理——基于產業鏈分工的視角[J].中國工業經濟,2007(2):28-34.
[14]李靖.論新型區域產業分工[D].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論文,2007:6.
[15]李靖.新型區域產業分工研究綜述[J].經濟經緯,2009(5):56-59.
[16]李靖.新型產業分工:重塑區域發展格局[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8.
[17]Stigler G.The division of labor is limited by the extend of the market[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1(59):185-193.
[18]Piore M,Sabel C.The second industry divide:possibilities for prosperity[M].New York:Basic Books,1984.
[16]李靖.新型產業分工:重塑區域發展格局[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8.
[19]Duranton G,Puga D.Micro-foundations of urban agglome ̄ration economies[R].CEPR Discussion Paper,2003:4060.
[14]李靖.論新型區域產業分工[D].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論文,2007:6.
[20]列寧.俄國資本主義發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1]魏后凱.區域經濟發展的新格局[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22]肖金成,史育龍,李忠.第三增長極的崛起——天津濱海新區發展戰略研究[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
[23]張迎春.國際標準職業分類的更新及其對中國的啟示[J].中國行政管理,2009(1):105-107.
[24]張可云.區域大戰與區域經濟關系[M].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01.
[25]張兆安.大都市圈語區域經濟一體化——兼論長江三角洲區域經濟一體化[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6.
[26]賈康,馬衍偉.推動我國主體功能區協調發展的財稅政策研究[J].經濟研究參考,2008(3):2-18.
[27]張國寶.東北地區振興規劃研究.專項規劃研究卷[M].北京:中國標準出版社,2008.
(本文責編:王延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