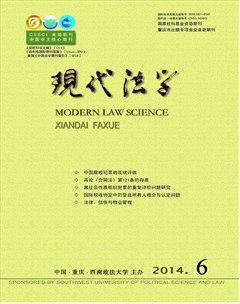論被追訴人沉默的證據能力
摘要: 被追訴人面對訊問時可能會保持沉默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我國理論界普遍存在著過于簡單化地理解不被強迫自證其罪的基本理論而一概否定被追訴人沉默證據能力的觀點。被追訴人沉默與案件事實存在關聯性,認為存在排除被追訴人沉默證據能力的正當理由之觀點值得商榷。西方法治國家對被追訴人沉默的證據能力并非一概持否定態度,而是在一定的程度上認可其證據能力。對被追訴人沉默的證據能力之規定,各國雖然存在著差異,但也有相通之處。在《刑事訴訟法》已經確立不被強迫自證其罪的背景下,我國有必要建立被追訴人沉默的證據能力規則,明確被追訴人沉默可以有條件地作為定罪的間接證據和證明其主觀態度的量刑證據使用。
關鍵詞: 被追訴人;沉默;證據能力
中圖分類號:DF73文獻標識碼:A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4.06.10
不被強迫自證其罪,如同無罪推定,已經成為現代法治國家刑事訴訟中的公理性原則。我國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第50條增加規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并在第54條規定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獲取的口供應當排除,標志著我國已經確立不被強迫自證其罪原則。雖然理論界對能否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不被強迫自證其罪推斷出被追訴人享有沉默權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被追訴人在面對追訴和審判機關的訊問時可能會保持沉默顯然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對于能否以被追訴人的沉默作為對其不利的證據使用之問題,我國理論界由于對不被強迫自證其罪的理論和西方國家有關實踐做法的理解過于簡單,目前普遍存在著一概否定被追訴人沉默證據能力的觀點。為此,本文擬對被追訴人沉默的證據能力進行探討,以求教于方家。
一、否定被追訴人沉默的證據能力之理論檢討否定被追訴人沉默的證據能力,意味著不能以被追訴人沉默作為對其不利的證據使用。根據證據能力的基本屬性,判斷被追訴人沉默是否具有證據能力需要考慮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是被追訴人沉默與案件事實是否有關聯性,二是是否存在排除具有關聯性的證據之正當理由。綜觀國內外理論界否定被追訴人沉默的證據能力之理由,大致是從以下兩個方面展開。
(一)被追訴人沉默與案件事實是否存在關聯性
與案件事實存在關聯性是具有證據能力之前提。對被追訴人沉默與案件事實是否有關聯性,理論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種觀點認為,被追訴人沉默與案件事實不存在關聯性,允許以沉默做出對其不利的推論,實非理性之結果。這是因為:被追訴人沉默并不完全是因為自己實施了犯罪行為,可能是出于保護朋友、同事、家人等考慮;也可能是不愿意配合在他看來是專制、暴虐的政府;或是不愿意做不精確的陳述;或者因恐懼、尷尬、焦慮、憤怒而保持沉默;有時沉默是被追訴人自己的意思,但亦可能是出于辯護律師的建議等[1]。總之,在此觀點看來,證據的關聯性是一種邏輯上的必然聯系,而被追訴人沉默與其是否實施了犯罪行為不存在必然聯系,因而沉默與案件事實不存在關聯性,不應賦予其證據能力。另一種觀點可以追溯至19世紀早期英國法哲學家邊沁(Bentham)之主張,“無辜者主張陳述之權,有罪者行使沉默之權。”[2]被追訴人選擇沉默,往往是因為其實施了犯罪行為,因而沉默與案件事實存在關聯性。這是因為,無辜者會抓住機會為自己辯解,故以沉默作為對其不利之推論,實為理性分析之結果;反之,若禁止以沉默作為證據使用,反而有違一般人之經驗法則[3]。此觀點從經驗主義的角度進行分析,反推被追訴人沉默與其實施犯罪有關,因而主張其有證據能力。
現代法學陳學權:論被追訴人沉默的證據能力誠然,上述兩種觀點不無道理。不過,在筆者看來,全面、科學地認識被追訴人沉默是否具有關聯性,需要緊扣證據的關聯性之核心要義。我國理論界一般認為,“證據的關聯性,又稱證據的相關性,是指證據事實與案件事實存在著客觀上的內在聯系,從而能起到證明作用。”[4] 這種“客觀上的內在聯系”是一種必然性聯系,是“能夠”證明案件事實的,因而我國學者對證據關聯性的理解側重于證明力,而非證據能力。比較而言,英美學者側重于從證據能力的角度理解關聯性。在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401條對“相關證據”的解釋是,“‘相關證據是指使任何事實的存在具有任何趨向性的證據,即對于訴訟裁判的結果來說,若有此證據將比缺乏此證據時更有可能或更無可能。”[5]在此,證據的關聯性強調的是證據是否具有證明案件事實的可能性。某一證據只要具有影響裁判者對案件事實真實與否的判斷之可能性,該證據就具有關聯性;反之,就沒有關聯性。對此,我國臺灣地區學者陳樸生先生曾就這兩種關聯性的區別做出如下精辟論述,“惟證據評價之關聯性,乃證據經現實調查后之作業,系檢索其與現實之可能的關系,為具體的關聯,屬于現實的可能;而證據能力之關聯性,系調查與假定之要證事實間具有可能的關系之證據,為調查證據前之作業,仍是抽象的關系,亦即單純的可能,可能的可能。故證據之關聯性,得分為證據能力關聯性與證明價值關聯性兩種。前者,屬于調查范圍,亦即調查前之關聯性;后者,屬于判斷范圍,亦即調查后之關聯性。”[6]因此,當我們從證據能力的角度來理解關聯性時,關注的重點應該是證明案件事實的可能性,而非必然性。
而且,證據的關聯性,永遠是相對于特定的案件事實而言。因此,判斷被追訴人沉默是否具有關聯性,還需要結合案件事實具體分析。首先,被追訴人沉默與其是否實施犯罪行為具有關聯性。誠然,被追訴人沉默與其是否實施犯罪并不存在必然的聯系,實踐中確實可能會存在一些沒有實施犯罪行為的人不為自己辯解而選擇沉默。但是,如上所述,衡量某一證據是否具有關聯性,并非根據是否存在必然的聯系,而是以其是否存在證明犯罪事實之可能性為判斷標準。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講,一個無辜的人在遭受不實指控時,積極為自己辯解以洗刷冤屈可以說是人之本能。因此,對于被追訴人沉默的真實原因,盡管在概率上不排除其客觀無罪而保持沉默的可能,但是蓋然性更高的則是:被追訴人選擇沉默是因為其確實實施了犯罪行為。簡言之,在面對訊問而保持沉默的被追訴人中,有罪之可能性遠高于無罪之可能。既然被追訴人實施了犯罪是導致其沉默的重要原因,因而可以認為沉默本身有助于證明被追訴人實施了犯罪,相對于犯罪事實而言具有關聯性。事實上,將被追訴人針對指控之生理反應作為證據使用,自古以來就是允許的。我國古代刑事案件調查中的“五聽”制度,就是要求裁判者通過察言觀色來判斷當事人陳述真偽的重要方法,此種方法至今依然被認為是科學的方法。時至今日,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裁判者根據被告人在法庭上陳述時低頭、臉紅等面部表情以及陳述前后不一等做出對其不利的推論——推斷其說謊,在任何國家都無禁止性規定。既然如此,惟獨否定被追訴人沉默的證據能力,禁止裁判者根據被追訴人沉默做出對其不利的推論,在邏輯上難以成立。
其次,被追訴人沉默與量刑事實存在關聯性。對于被認定有罪的被告人來說,認罪態度是量刑事實的重要組成部分。面對國家的刑事追訴,對于案件事實之陳述,被追訴人的態度大體可以分為三個層次:一是積極交代,客觀陳述;二是保持沉默,拒絕陳述;三是放棄沉默,但謊話連篇。被追訴人積極如實陳述,既節省國家追訴犯罪的司法資源,又在一定的程度上體現出悔罪心理,因而世界各國的刑事司法無不將其作為可以從寬處罰的量刑情節的證據。對于故意做虛假陳述的被告人,英美法系國家會以偽證罪追究刑事責任;大陸法系國家對能否以此加重處罰在理論上雖然存有爭議,但是德國在判例上認為,“如被告頑固說謊以致足以使法官認定其不知悔改,并有礙真相之調查時,會加重其刑罰”[7],這說明被追訴人故意作虛假陳述之本身在被作為證據使用。相應地,對于保持沉默、拒絕陳述的被告人,則按照刑法規定的基準刑處罰,此時被追訴人沉默之本身也是在被作為證據使用。例如,在日本,“在量刑時,行使沉默權這個事實本身不能構成對被告人不利的因素,但是可以作為被告人未反省的資料之一予以參考。”[8]因此,無論是被追訴人如實陳述、故意作虛假陳述,還是保持沉默,對于案件之量刑事實而言都具有關聯性,都是認定被告人的犯罪態度及悔罪表現的證據。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被追訴人沉默對于定罪和量刑兩方面的事實都具有關聯性,但是其關聯性之程度有所差別。對于量刑情節中被追訴人認罪態度之事實而言,被追訴人沉默直接證明了被追訴人既沒有積極配合國家追訴,又沒有故意作虛假陳述以誤導甚至妨礙國家追訴,而是處于一種消極狀態,屬于認定被追訴人主觀態度及悔罪表現的直接證據。對于定罪事實而言,被追訴人沉默只是從日常生活經驗的角度反映出被追訴人可能與已經發生的犯罪事實有關,但并不能單獨證明其有罪,屬于間接證據,因而不能僅僅根據被追訴人沉默推斷其有罪。對此,我國臺灣地區“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4款就規定,“被告未經自白,又無證據,不得僅因其拒絕陳述或保持沉默,而推斷其罪行。”[9]總之,被追訴人沉默無論是對于定罪事實還是量刑事實而言,均具有關聯性,因而以其沒有關聯性為由否定被追訴人沉默的證據能力是不足以令人信服的。
(二)是否存在排除被追訴人沉默作為證據的正當理由
關聯性是享有證據能力的必要但非充分條件。即便某一證據材料具有關聯性,但如果存在排除的正當理由,依然可以否定其證據能力。綜觀國內外相關文獻資料,主張否定被追訴人沉默證據能力的主要理由是:禁止對被追訴人沉默進行評價是沉默權的應有之意,否定被追訴人沉默的證據能力是保障被追訴人沉默權的必然結果。例如,國內有教科書認為,被追訴者不會因為沉默、拒絕提供陳述和其他證據而遭受懲罰或者法律上的不利推測是反對強迫自證其罪原則包含的基本內容之一[10]。日本學者認為,“被告人有沉默權,當然不允許對不交代這一態度本身作出不利的評價。”[11]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持此觀點的學者擔心:一方面承認被追訴人有權保持沉默,另一方面又允許裁判者對被追訴人沉默做出不利的評價,將會使被追訴人擔心不利的后果而不敢行使沉默權,等于強迫其做出不利于己的陳述。
筆者認為,此觀點值得商榷。首先,禁止將被追訴人沉默作為不利的證據使用并非不被強迫自證其罪或沉默權的內涵。從字面上來看,不被強迫自證其罪或沉默權強調的只是被追訴人有權拒絕承認自己有罪或者交出對其不利的證據,并不能解釋出包含有否定被追訴人沉默的證據能力之義。事實上,在有關刑事司法的國際人權公約中,如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保護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監禁的人的原則》、《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均僅規定被追訴人有權“不被強迫做出不利于自己的證言或承認犯罪”或是“保持沉默”,并無明確禁止將被追訴人沉默作為證據使用的規定。誠如歐洲人權法院所言,“這個領域既存的國際標準雖然規定了沉默權與不被強迫自我歸罪的標準,但是在此具體問題(即被追訴人沉默的證據能力問題,筆者加)上卻保持了沉默。”[12]唯一明確規定不得以沉默作為證據使用的是《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第67條第1款第7項,該條文規定,“不被強迫作證或認罪,保持沉默,而且這種沉默不得作為判定有罪或無罪的考慮因素”。值得強調的是,該規定在表達方式上將不被強迫自證其罪、沉默權和否定沉默的證據能力三者并列,這進一步說明不被強迫自證其罪并不包含否定沉默的證據能力之內涵。因此,承認被追訴人沉默的證據能力與不被強迫自證其罪及沉默權在表面形式上并未發生直接的沖突。
其次,承認被追訴人沉默的證據能力不構成對不被強迫自證其罪及沉默權的侵犯。一方面,認可沉默的證據能力所引起的間接強制并未達到不被強迫自證其罪之強迫的程度。有學者認為:告訴嫌疑人可以用沉默作為證據起訴他們,就等于在向他們施壓,使其承認有罪,因而違反不被強迫自證其罪[13]。筆者認為,此觀點不當地理解了不被強迫自證其罪中之“強迫”的含義。不被強迫自證其罪保護被追訴人自由陳述,但此種自由并非是絕對的。綜觀法治國家的刑事訴訟立法和實踐,在保護被追訴人自由陳述方面,不被強迫自證其罪之“強迫”,并非指所有的強迫。例如,在德國,“所謂的恐嚇、脅迫需為違反刑訴法之行為,故依聯邦最高法院之見解,如脅以合法的暫時逮捕,此應屬合法之行為。但如果脅以刑法第56f條未加規定的不予緩刑之情形時,則屬違法。”[7]在法國,“實踐中犯罪嫌疑人很難實現這項權利(沉默權),因為警察通常會對其施加巨大的心理壓力而迫使其開口。”[14]在美國,“一些艱難的決定并沒有被視為憲法意義上的‘強制,……上述強制性選擇,盡管‘并非輕松的、令人愉悅的選擇,但是,其強制性并沒有達到第五修正案規定的程度。”[15]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在解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的不被強迫自證其罪時特別強調,“在考慮這項保障時應記住第7條(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和第10條第1款(所有被剝奪自由的人應受到人道及尊重其固有的人格尊嚴的待遇)的規定。強迫被告供認或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證言的常用方法往往違反這些規定。”[16]因此,從聯合國刑事司法準則的角度來看,不被強迫自證其罪中的強迫,主要是指通過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方法,而非指所有的強迫。也許正是因為如此,無論是在漢語還是英語中,追訴機關在向被追訴人和證人問話時,采用的是兩種表達方式,即作為對被追訴人問話的訊問(interrogation)與對證人問話的詢問(questioning)。與后者相比,前者在語氣上體現出一定的命令性,這表明訊問時給被追訴人施加一定的心理壓力是正當的。
承認沉默的證據能力,雖然會給被追訴人帶來一些心理壓力,但是此種壓力尚未達到與酷刑等類似的強迫程度,這是因為:即便承認沉默的證據能力,也不必然導致法官將沉默當作被追訴人承認對其不利的犯罪事實,而只是意味著沉默有可能被法官作為推論對其不利事實的根據。至于在具體的個案中是否足以支持這樣的推論,還取決于案件中證據的整體情況以及相關的經驗和倫理法則。需要強調的是,根據證據的整體情況及經驗和倫理法則形成心證,并非職業法官之專利,包括被追訴人在內的普通人也有此能力。因此,被追訴人在決定是否行使沉默權時,完全有能力判斷拒絕陳述在多大的程度上足以支持法官作出不利的推論。一般來說,在其他對被追訴人不利的證據越少時,如果法官越難根據沉默做出對被追訴人不利的推論,被追訴人就更可能選擇沉默;反之,如果法官越容易根據沉默做出對被追訴人不利的推論,被追訴人則更可能選擇放棄沉默。由此可見,立法是否承認沉默的證據能力,只是被追訴人在決定是否行使沉默權時考慮的因素之一,被追訴人陳述的意志自由并未被完全剝奪。總之,承認沉默的證據能力,雖然對于被追訴人陳述具有一定的強制性,但此種強制性與不被強迫自證其罪禁止的強迫程度顯然不可同日而語。
另一方面,認可沉默的證據能力不構成對行使合法權利之懲罰。美國有學者認為,雖然承認沉默的證據能力并不等于強迫被追訴人陳述,但被追訴人在決定是否保持沉默時,顯然會考慮沉默可能被作為對其不利證據使用的后果,因而形成壓力而不敢行使沉默權,此壓力為憲法所不容許,也等于在處罰人民行使憲法權利[17]。誠然,對合法行使權利之行為,法律不應該予以處罰;否則,就失去了權利存在的意義。不過,在賦予沉默證據能力的情況下,即便法院將沉默作為對被追訴人不利的證據使用,最終法院對被追訴人做出定罪量刑的判決,懲罰的并不是沉默本身,而是被追訴人實施的犯罪行為,因而不構成對行使合法權利之懲罰。事實上,如果認為將沉默作為對其不利的證據使用就構成對行使合法權利之懲罰,那么在被追訴人放棄沉默權時又該作何種解釋呢?放棄沉默而開口陳述也是被追訴人的權利,但一旦被追訴人開口陳述,其有罪的陳述一般都會被作為定罪的證據使用;其無罪的不合情理的辯解或者前后相互矛盾的陳述,也有可能成為法院認定犯罪事實存在的心證之來源。顯然,被追訴人放棄沉默而行使開口陳述之權利,與行使沉默權拒絕陳述一樣,其陳述或沉默本身都有可能被作為對其不利的證據使用。但是,我們并沒有認為將被追訴人陳述作為對其不利的證據使用構成對行使合法權利之懲罰。因此,片面地認為肯定沉默的證據能力是對被追訴人行使合法權利之懲罰在邏輯上是站不住的。
二、肯定被追訴人沉默的證據能力之比較法分析根據筆者掌握的有關資料,在立法上明確否定被追訴人沉默證據能力的是俄羅斯《刑事訴訟法》。該法第340條第3款第6項規定,“在致辭中,審判長應該提請陪審團注意:受審人拒絕做陳述或在法庭上保持沉默沒有法律意義,不得解釋成受審人有罪的證明。”[18]此外,日本《刑事訴訟法》雖對被追訴人沉默有無證據能力沒有明確規定,不過判例在認可被追訴人沉默可以作為量刑材料參考的同時,明確否定了被追訴人沉默作為定罪證據使用的資格,即,“不允許以被告人在偵查、審理過程中一直沉默的態度作為認定殺人意圖的證據”,“不能根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沉默權這一事實,推定不利于他們的事實。不能將行使沉默權作為有罪證據提出,也不能作為評價證據的資料。”[8]除此之外,其他西方主要國家在被追訴人沉默證據能力問題上,并非如國內主流觀點所認為的一概持否定態度,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認可其證據能力。
(一)西方主要國家肯定被追訴人沉默證據能力之考察
歸納西方主要國家有關被追訴人沉默證據能力的立法及判例,大致有以下四種類型。
1.認可被追訴人沉默作為彈劾證據使用
美國有關被追訴人沉默能否作為證據使用的問題,聯邦憲法及成文法并無規定,早期的判例法也未涉及。美國有的州憲法如加利福尼亞州憲法曾經規定,被告在審判時對其不利的事實既不解釋又不否認的,法官或檢察官可以對此進行評論,陪審團亦可將此沉默作為證據使用。然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1965年在格里訴加利福尼亞州案(Griffin v. California)中解釋憲法修正案第五條時,鮮明地表達了如下態度,“對于審判中被告保持沉默一事,檢察官或法官不得評論,也不得據此作任何不利于被告的推論。”Griffin v. California, 380 U.S. 609(1965).對于被追訴人在偵查階段的沉默,美國聯邦最高法院1966年在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案(Miranda v.Arizona)中認為,被告在偵查階段面對訊問時保持沉默或者主張沉默權,檢察官不得以此作為證明被告有罪的證據使用,否則等于懲罰被告行使憲法權利。Miranda v.Arizona,384 U.S.436(1966).自此,有關州允許將被追訴人沉默作為定罪證據使用的規定自動無效。聯邦最高法院至今認為,將被追訴人沉默作為證明有罪的實體證據使用違反憲法第五修正案規定。
將證據分為實體證據與彈劾證據是美國證據法的傳統。前者是證明犯罪是否成立的證據;后者是與證明犯罪是否成立無直接關系,但能夠發揮質疑證人信用作用的證據。聯邦最高法院認為:雖然將被追訴人沉默作為定罪證據使用違反不被強迫自證其罪,但是被追訴人沉默在以下三種情形下可以作為彈劾證據使用:首先,被告人在先前審判中的沉默在嗣后的審判中可以作為彈劾證據使用。在拉弗爾訴美國案(Raffel v. United States)中,在第一次審判時被告行使沉默權拒絕陳述,但因陪審團對本案未能達成決議而出現第二次審判時,被告在法庭上作證陳述,為自己辯解。隨后,檢察官向法官提出,若被告陳述屬實,那為何第一次審判時被告拒絕陳述。對此,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檢察官以被告第一次審判時的沉默質疑第二次審判時的陳述,不違反憲法第五修正案規定。其次,犯罪嫌疑人在逮捕之前的沉默可以在審判中作為彈劾證據使用。在詹金斯訴安迪生案(Jenkins v. Anderson)中,被告在審判中辯解其是正當防衛,檢察官則反問被告:在兇殺案后的兩周內,為何未主動向警察報案并交代正當防衛之事,對此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在嫌疑人沉默之前,警方既未明示也未暗示沉默不得為證據。而且,允許該沉默為彈劾證據,不會對憲法第五修正案權利的行使造成不受容許的負擔。Jenkins v. Anderson,447 U.S.231 (1980).最后,犯罪嫌疑人在被逮捕后收到米蘭達警告之前的沉默可以在審判中作為彈劾證據使用。在弗萊徹訴韋爾案(Fletcher v. Weir)中,嫌疑人在逮捕后保持沉默,但在審判中陳述其殺人出于正當防衛,公訴方提出被告為何在偵查階段未主動告知警方的質疑,聯邦最高法院認為,以偵查階段的沉默質疑庭審陳述的可信度不違反憲法修正案規定,因為警方從未告知被告享有沉默權,也未保證沉默不會作為證據被使用。Fletcher v. Weir,455 U. S.603 (1975).值得注意的是,對于警方逮捕嫌疑人并為米蘭達權利警告之后,嫌疑人保持沉默的事實,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數起案件中均認為,既不能作為實體證據使用,也不能作為彈劾證據使用。究其原因,是因為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在警方明確告知嫌疑人有權沉默后,嫌疑人基于信賴而行使沉默權,如果容許此沉默為證據使用,則警察就有違反禁止反言之嫌。有關此方面的案例參見:United States v. Hale, 422 U.S.171 (1975); Doyle v. Ohio, 426 U.S.610 (1976) .
2. 明確規定幾種法定情形下被追訴人沉默具有證據能力
明確肯定被追訴人沉默具有證據能力的國家有英國、新加坡和愛爾蘭等。英國法在傳統上禁止將被追訴人沉默作為證據使用。不過,英國刑事法修改委員會(The Criminal Law Revision Committee)于1972年發布了關于修改證據規則的研究報告,建議賦予被追訴人沉默證據能力。經過20余年的爭論,英國于1994年通過了《刑事審判與公共秩序法》,該法第34至37條規定以下四種情形下被追訴人沉默具有證據能力:(1)被追訴人在警察訊問時依當時的情況被合理期待對某項事實做出回答,然其保持沉默,但在審判時又據此事實進行辯護,則可根據先前的沉默做出對其不利的推論;(2)在審判中當控方對指控舉證完畢后,被告依然保持沉默,審判者可以據此做出適當的推論;(3)如果警察在犯罪嫌疑人的身體、衣服或被逮捕的處所發現可疑的物品、材料或痕跡,當警察就此訊問時,犯罪嫌疑人保持沉默,則可以據此對其做出不利的推論;(4)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針對警察提出的其為何會出現在犯罪現場等特定的場所之問題拒絕回答,審判者可以據此做出對其不利的推論[19]。需要說明的是,我國刑訴法學理論界在上世紀90年代后期已經注意到英國的這一立法動態,不過一般將其視為英國對沉默權的限制,而沒有從被追訴人沉默證據能力的角度進行解釋。
事實上,上述英國刑事法修改委員會發布的關于修改證據規則的研究報告的相關建議最早被新加坡和愛爾蘭采納。新加坡于1976年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和愛爾蘭于1984年通過的《刑事審判法》均對沉默的證據能力做出了與上述英國《刑事審判與公共秩序法》類似的規定[20]。值得注意的是,對于英國法賦予沉默證據能力之做法,歐洲人權法院于1996年在約翰·默里訴英國(John Murray v. the United Kingdom)、2001年在埃弗里爾訴英國(Averill v. the United Kingdom)等案件中認為,“警告被告人其在警察訊問階段保持沉默可以作為不利的推斷,不構成不當的強制”。“鑒于沒有直接的強制,國內法院又沒有僅僅依靠或者主要依靠被告人的沉默來證明有罪,因此不牽涉到《公約》第6條的問題。”[12]由此可見,歐洲人權法院認為承認沉默的證據能力沒有違反不被強迫自證其罪。
3.僅認可被追訴人的選擇性沉默具有證據能力
根據沉默對象的不同,可以將被追訴人沉默分為完全沉默和選擇性沉默。前者指被追訴人對整個案件事實行使沉默權,后者指被追訴人陳述部分案件事實、但對個別案件事實拒絕回答。對于完全沉默,無論是被追訴人在整個訴訟過程中自始至終,還是在某一訴訟階段,德國和意大利均認為,不能將此種沉默作為對被追訴人不利的證據使用。
但是,對于選擇性沉默,德國法院認為,“沉默權不損害被告人利益的規則并不平等適用于以下情況,即當被告人做出供述,但對案件的某些方面沒有交代(這一點被告人很清楚)。這種情況常會發生,因此法院并不僅僅對被告人的供述進行評價,而是從被告人可能對法院隱瞞部分案情的實際情況去判斷其可信度。”[21]在意大利,被追訴人如果在陳述的同時只是對所提的某些具體問題選擇不予回答,那么這種消極態度——沉默可以作為不利于他的證據使用[22]。對于此種做法之緣由,我國臺灣地區學者曾分析指出,“法律賦予被告緘默權,便是賦予被告開啟或關閉以被告陳述之證據方法的主動權利,被告固然得以保持緘默而關閉此種證據方法;但是,倘若被告依其自由意思選擇陳述,則是開啟此種證據方法,同時也開啟法院自由評價其證明力的路徑。”[23]筆者深以為然,事實上,允許裁判者將選擇性沉默作為證據使用,猶如允許裁判者根據被追訴人反復矛盾的陳述來推斷其口供是否可信一樣。
4.僅認可審判階段被追訴人沉默的證據能力
根據沉默所處訴訟階段的不同,可以將被追訴人沉默分為全部沉默和階段性沉默。前者指被追訴人在偵查至審判的整個訴訟過程中都保持沉默,后者指被追訴人僅在偵查或審判階段沉默。對于被追訴人在偵查階段沉默的證據能力,除上述美國和英國附條件地認可其證據能力外,其他西方主要國家均持否定態度。
不過,對于被追訴人在審判階段的沉默,有的國家承認其證據能力。例如,在法國,“(雖然)初審法庭不得就被告人在庭審中保持沉默或者拒絕回答某一問題做出不利于他的推論,但根據法國刑事證據法,一切證據包括被告人的舉止和態度,都由法官和陪審員本著自由心證原則自由判斷,法官和檢察官可以對被告人的沉默態度進行評論,因而事實上被告人在庭審中保持沉默或者對有關提問拒絕回答通常會加強控方案件的說服力。”[20]加拿大的判例法認為,在審判過程中如果被告人不作證,法律并不禁止陪審員運用其智慧把沒有否認或解釋考慮進去;而且,在控方的舉證已達到“表面上成立”時,如果被告人依然拒絕陳述,則法官和陪審團有權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做出不利于被告人的推論[20]。法國、加拿大之所以認可審判階段被追訴人沉默的證據能力,可能與自由心證證據制度相關。因為根據自由心證原則,被告人在法庭上的一切言行和舉止,都在裁判者自由評價范圍之內。
(二)對西方主要國家肯定被追訴人沉默證據能力的比較分析
綜觀上述考察,可以得出的基本結論是:在被追訴人沉默證據能力問題上,西方法治國家并非如國內主流觀點所想象的一概持否定態度,而是在一定的程度上認可。之所以如此,除本文前面提到的被追訴人沉默與案件事實存在關聯性外,還可能是因為:無論立法對被追訴人沉默的證據能力做出何種規定,客觀上均無法阻止裁判者對被追訴人沉默進行推測。在現代刑事訴訟中,無論采取何種審判方式,均無法將被追訴人沉默的事實阻擋在負責認定案件事實的裁判者之視線外。而且,裁判者自由評價證據證明力又是現代法治國家普遍確認的證據法原則。因此,對于裁判者內心會如何評價被追訴人面對指控而保持沉默,在現代法治國家公認的訴訟原則面前,立法幾乎無能為力。正是因為如此,在匈牙利,“據一些警察、檢察官和法官講,他們不會因為被告人沉默而施以不利后果,因為這與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不符;而辯護律師卻講到,實踐經驗告訴他們,沉默行為確實影響到某些判決,尤其是對于那些未決羈押的被告人。一位律師指出,在司法實踐中,被告人的如實供述是決定其是否可以得到從輕判決的重要條件,那么實際上被告人是供認不諱還是保持沉默就會直接影響到量刑的輕重。”[14]英國刑事法律委員會也曾經指出,“假定被告人面對指控時保持沉默絕不等于承認自己有罪,然而事實上,普通法對此相當困惑。陪審團無論從法官那里得到什么指示,總可以從被告人不回答提問做出最壞的推論。”[5]而且,在禁止以被追訴人在法庭上的沉默作為定罪證據使用的美國,為了把陪審員根據沉默進行不利推測的可能降到最低限度,聯邦最高法院賦予了法官向陪審團發出“不能根據被追訴人的沉默作出對其不利的推論”的指示之權力。然而,有的辯護律師卻申請法官不向陪審團發出此類指示,因為他們認為在被追訴人沉默的情況下,允許法官向陪審團發出此類指示,無異于“像在陪審團面前揮舞紅旗”,反而更容易引發陪審團對被告人沉默的不利推測[6]。這進一步說明通過立法很難阻止裁判者對被追訴人沉默進行推測。法諺云:法律不強人所難。因此,在立法無法阻止裁判者內心不自覺地評價被追訴人沉默的情況下,一概否定被追訴人沉默的證據能力顯然是癡人說夢。
綜觀上述考察,還可以發現:在被追訴人沉默證據能力問題上,西方主要法治國家都試圖極力在保障人權與懲治犯罪、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之間妥善尋求平衡。例如,德國舊的判例學說曾毫無疑問地認為可將被告人沉默作為對其不利的證據使用[7]。但是,隨著正當程序和人權保障理論的發展,德國法對被追訴人沉默的證據能力進行了限制,目前僅承認選擇性沉默的證據能力。與之相反,英國原本是一概反對賦予被追訴人沉默證據能力,但是隨著國內打擊犯罪呼聲的高漲和對正當程序理論的反思,終于在20世紀90年代通過立法承認了特定情形下被追訴人沉默的證據能力。因此,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說,現代西方法治國家有關被追訴人沉默證據能力的規定,是注重程序正義、人權保障的英美法系和注重實體正義、懲治犯罪的大陸法系相互作用的結果,是理性追求多元訴訟價值均衡實現的產物。
西方主要國家關于被追訴人沉默證據能力的規定,顯然也存在一些差別。不過,這種差別很難用傳統的兩大法系的刑事訴訟構造及價值理念的不同來解釋,因為在此問題上,作為英美法系的主要代表國家——英國和美國的做法并不一致;作為大陸法系的主要代表國家——法國和德國的做法同樣有別。甚至出現了屬于大陸法系的法國和英美法系的加拿大、澳大利亞卻基本相同的情況。這些差別的出現,一方面說明被追訴人沉默證據能力問題的復雜性,同時反映出現代法治國家在面對不被強迫自證其罪時如何平衡保障人權與懲治犯罪上的糾結心態。如前所述,美國、英國、德國對被追訴人沉默的證據能力之態度都曾發生過變化。另一方面可能與該國獨特的法律文化和法制傳統有關,例如在美國,僅僅允許被追訴人沉默作為彈劾證據使用,而法國對審判階段被追訴人沉默證據能力的無條件認可,可能與其作為現代自由心證的發源地有關。
在認可被追訴人沉默證據能力問題上,上述西方主要國家的做法存在以下兩個共同點:一是被追訴人沉默享有證據能力需要滿足一定的條件,并非所有的被追訴人沉默都能作為證據使用。在美國,被追訴人沉默只能作為彈劾證據使用,實際上是僅僅承認階段性沉默的證據能力;英國、新加坡等國只是規定了在幾種法定情形下被追訴人沉默有證據能力;德國和意大利則承認選擇性沉默的證據能力;法國和加拿大等僅認可審判階段被追訴人沉默的證據能力。二是被追訴人沉默至多只能作為定罪的間接證據和量刑證據;不能僅以被追訴人沉默推定被追訴人有罪,而且不能將被追訴人沉默作為認定其有罪的主要證據。對此,有的國家甚至在立法上作了明確規定,如根據英國1994年《刑事審判與公共秩序法》第38條規定,被告人不會僅僅因為從他沒有回答或拒絕回答問題中做出的推論,而使案件移送到刑事法院接受審判、應訴或被裁定有罪[19]。歐洲人權法院也認為,“一方面,僅僅或者主要以被追訴人保持沉默、拒絕回答問題或者自己提出證據就定罪,明顯與公約的豁免是不相容的。另外一方面,本院認為,同樣明顯的是,這些豁免不能夠也不應該阻止將被告人的沉默(在明顯有必要要求其進行解釋的情況下)用作評估控方舉出證據之證明力大小。”[12]之所以不能以被追訴人沉默推定有罪或作為定罪的主要證據,除了其與犯罪事實在關聯性程度上不存在必然聯系外,還因為如果允許以被追訴人沉默推定有罪或作為定罪的主要證據,那么就等于在以定罪制裁為要挾直接強制被追訴人開口陳述,從而違反不被強迫自證其罪。
三、被追訴人沉默的證據能力規則在我國之確立目前,我國理論界普遍認為不被強迫自證其罪包含有否定被追訴人沉默的證據能力之觀點,立法及司法解釋對被追訴人沉默的證據能力沒有任何規定。在我國《刑事訴訟法》沒有確立不被強迫自證其罪的情況下,將沉默作為對其不利的證據使用,在正當程序方面不存在任何障礙。然而,隨著不被強迫自證其罪在我國的確立,在證據制度上如何構建我國被追訴人沉默的證據能力規則,便成為亟需探討的問題。
(一)確立我國被追訴人沉默證據能力規則的必要性
充分考慮當前我國懲治犯罪和保障人權的實踐要求,筆者認為,我國應當盡快確立被追訴人沉默的證據能力規則。
首先,如何評價被追訴人沉默是我國司法現實無法回避的問題。我國《刑事訴訟法》第50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第54條還規定,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應當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這意味著在被追訴人拒絕陳述、保持沉默的情況下,公安司法機關無權強迫被追訴人陳述。隨著被追訴人主體意識和人權觀念的增強,被追訴人、尤其是了解我國《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的被追訴人拒絕回答公安司法機關訊問的可能性顯然存在,甚至會逐步變大。因此,只要公安司法機關依法辦案,不采用刑訊逼供等方法強迫被追訴人供述,被追訴人沉默的可能性就存在。在被追訴人沉默的情況下,司法機關如何評價被追訴人的沉默,顯然是必須面對的問題。
其次,確立科學的沉默證據能力規則有助于降低沉默權對我國刑事司法之沖擊。賦予被追訴人沉默權,會在一定的程度上阻礙案件事實真相的發現,給公安司法機關的工作帶來壓力,這是我國有關機關在《刑事訴訟法》修改時強烈反對確立沉默權、在修法完畢后又極力反對將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解釋成我國已經確立沉默權的重要原因。為了降低沉默權對查明案件事實真相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一些西方國家在一定的程度上賦予被追訴人沉默證據能力,通過沉默推定給被追訴人施加心理壓力,促使其開口講話并回答提問。對此,有學者在比較分析境外被追訴人沉默不利推定制度后認為,總體而言,與英美法系國家相比,大陸法系國家的被追訴人較少行使沉默權;與美國相比,英國刑事訴訟中被追訴人較少行使沉默權。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不利評論和推論的規則不同,反過來直接影響被告人沉默權的行使情況[20]。目前,我國理論界與實務部門對能否及是否應該將《刑事訴訟法》確立的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解釋成包含沉默權尚存爭議。筆者認為,在不違背不被強迫自證其罪精神的前提下,附條件地賦予被追訴人沉默證據能力,有助于降低被追訴人沉默的概率,從而消解沉默權對案件事實真相查明的負作用。如此一來,還可以打消有關機關對將我國《刑事訴訟法》確立的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解釋為包含沉默權的疑慮。
再次,確立被追訴人沉默的證據能力規則有助于防止裁判者以不科學的方式評價沉默。在立法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裁判者在刑事司法中對被追訴人沉默的評價,容易走向極端。一方面,有的法官,特別是陪審員容易過分看重被追訴人沉默的證據價值,將沉默作為推定被告人有罪的主要證據。例如,鑒于陪審員常常會不自覺地對被告的沉默進行推斷,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第五修正案要求法官依職權主動提示陪審團不能從被告人的沉默中做出推斷。然而,一些律師認為,至少在某些情形下給出這樣的指示更多的是加大而非減小了陪審團考慮被告沉默而做出不利推論的可能性,因此現在越來越多的司法轄區要求審判法官在被告人反對時不作這種指示[23]。顯然,無論法官是否對陪審團給出指示,陪審員基于日常生活之經驗,均容易根據被告人的沉默做出對其不利的推論。另一方面,有的法官可能會完全忽視沉默的證據價值。罪從供定、無供不定案,曾是大陸法系國家在法定證據時期以及我國在封建社會時期刑事司法的傳統。時至今日,即便我國《刑事訴訟法》早就規定“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確實、充分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但司法實踐中依然存在著無口供不敢定案的心理。此種心理之盛行,是誘發刑訊逼供的重要原因。在間接證據達到一定證明要求的情況下,僅僅因為被告人沉默,而不敢對其做出有罪判決,顯然是無視被告人沉默的證據價值。因此,在立法上確立科學的被追訴人沉默證據能力規則,有助于避免裁判者在如何對待被追訴人沉默的問題上陷入上述兩種極端境地。
最后,認可被追訴人沉默的證據能力,是保證我國《刑法》與《刑事訴訟法》相互協調的必然要求。我國《刑法》第282條第2款規定,“非法持有屬于國家絕密、機密的文件、資料或者其他物品,拒不說明來源與用途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第395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或者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差額巨大的,可以責令該國家工作人員說明來源,不能說明來源的,差額部分以非法所得論,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差額特別巨大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財產的差額部分予以追繳”。這兩條規定要求被追訴人陳述、交代相關文件、資料、金錢或其他物品的來源;如果被追訴人拒絕交代或者保持沉默,則可以追究刑事責任。目前,我國理論界一般從推定的角度解釋此法條。然而,此推定之完成,必須依賴于被追訴人沉默的基礎事實。也就是說,在此類案件中,法院最終對被追訴人定罪,在事實認定上依據之一便是被追訴人沉默,這意味著法院已經將被追訴人沉默作為證據使用。在我國《刑法》已經規定被追訴人沉默是犯罪成立條件之一的情況下,我國《刑事訴訟法》無論是否定被追訴人沉默的證據能力還是對此不予回應,都不利于同《刑法》保持協調。
(二)被追訴人沉默在我國刑事訴訟中的證據種類定位
承認被追訴人沉默的證據能力,在我國刑事訴訟理論上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回答被追訴人沉默的證據種類定位。我國《刑事訴訟法》自1979年頒布以來,均對證據種類做出了明確規定。而且,理論上一般認為,“訴訟中作為起訴依據和定案根據的證據,必須符合法律規定的證據形式和要求,也就是說,應當屬于法定的證據種類中的一種。”[10]鑒于立法對證據種類規定的封閉性和滯后性,實踐中常常會出現一些具有證明價值但又難以確切歸入現行法定證據種類的材料。近些年來,我國對此類問題之解決,大體采用以下兩種方法:一是由辦案人員想方設法地將其歸入與《刑事訴訟法》規定相近的某一法定證據種類之中,例如在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電子數據為證據種類之前,實踐中辦案人員一般將電子數據視為視聽資料或書證使用;二是由立法機關修改《刑事訴訟法》,增加規定新的證據種類,如全國人大在2012年修改《刑事訴訟法》時,就增加規定了電子數據和辨認、偵查實驗筆錄等新的證據種類。
我國《刑事訴訟法》對于證據種類的法定化,對于指導辦案人員科學認識各種證據的特征、準確認定案件事實,無疑具有積極作用。但是,一方面,《刑事訴訟法》第48條將證據規定為八種,即“證據包括:(一)物證;(二)書證;(三)證人證言;(四)被害人陳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六)鑒定意見;(七)勘驗、檢查、辨認、偵查實驗等筆錄;(八)視聽資料、電子數據”,此劃分并無明確、統一的標準,致使實踐中有時難以判斷某一證據材料究竟屬于何種證據種類。例如電子郵件,既符合書證的特征,可以視為書證;也符合電子數據的特征,可視為電子數據。另一方面,此種劃分難以窮盡所有證據的表現形式,由此導致的后果是:如果嚴格執行此規定,可能會使一些新的能夠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被阻擋在訴訟證明的大門之外,不利于案件事實真相的發現;如果不嚴格執行此規定,隨意地將一些新的證據材料視為某種證據種類,又會使得立法規定證據種類的意義蕩然無存,破壞法律的權威性。
顯然,在我國現行立法和主流理論背景下,明確被追訴人沉默的證據種類定位是認可其證據能力時必須解決的問題。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接受訊問時,其開口供述或辯解在證據種類上屬于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然而,從字面含義來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既不屬于供述,也不屬于辯解,因而在證據種類上難以將其視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在司法實踐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訊問時保持沉默,其載體是追訴機關的訊問筆錄或法庭的審判筆錄。鑒于我國《刑事訴訟法》已經規定“勘驗、檢查、辨認、偵查實驗等筆錄”是法定的證據種類,目前可以考慮將此處的“等”字解釋為“等外等”,即所有有助于證明案件事實真相的偵查、審判筆錄都可以作為證據使用。如此一來,以訊問筆錄形式呈現出來的被追訴人沉默,在證據種類上就可以找到其歸屬,即與勘驗、檢查、辨認、偵查實驗筆錄等同屬于訴訟筆錄類證據。
不過,從長遠的角度看,最徹底的做法可能是將來我國《刑事訴訟法》對證據法定種類的規定采取開放性的立法表述,即在列舉具體證據種類的同時,明確所有可能證明案件情況的材料都可以作為證據。事實上,境外有的國家就明確規定包括偵查、審判筆錄在內的所有材料均可以作為證據使用,如俄羅斯《刑事訴訟法典》第74條第1款規定,“刑事案件的證據是法院、檢察長、偵查員、調查人員依照本法典規定的程序據以確定在案件辦理過程中存在還是不存在應該證明的情況的任何信息材料以及對于刑事案件有意義的其他情況”。第2款規定,“允許作為證據的有:(1)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陳述……(5)偵查行為的筆錄和審判行為的筆錄;(6)其他文件。”[18]顯然,如果將來我國《刑事訴訟法》采取類似于現在俄羅斯《刑事訴訟法典》關于證據種類的開放式立法表述,則被追訴人沉默的證據種類問題將迎刃而解。
(三)我國被追訴人沉默的證據能力規則之內容
考慮到被追訴人沉默對于定罪及量刑事實的關聯程度存在差異,我國被追訴人沉默的證據能力規則可以考慮從定罪與量刑兩個層次確立。
1.被追訴人沉默可以有條件地作為定罪的間接證據使用
綜觀境外認可被追訴人沉默證據能力的相關立法及判例規則,均是有條件地認可。我國對被追訴人沉默證據能力條件的設定,既需要考慮不被強迫自證其罪在我國的發展水平,還需要考慮我國庭審訊問被告的相關規定。一方面,不被強迫自證其罪在我國尚處于剛剛確立的階段,如何解釋與適用有待在實踐的基礎上逐漸完善。西方學者曾言:“不被強迫自證其罪原則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不同的環境會有不同的含義。”[23]基于當前中國刑事司法的發展水平,考慮控制犯罪與保障人權的平衡關系,當前我國對不被強迫自證其罪的解釋不宜過嚴。承認被追訴人沉默證據能力與不被強迫自證其罪之間存在著內在的緊張關系,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承認被追訴人沉默的證據能力,取決于一國對不被強迫自證其罪的具體解釋。我國2012年修改《刑事訴訟法》時增加規定不被強迫自證其罪的立法目的是“為從制度上進一步遏制刑訊逼供和其他非法收集證據的行為,維護司法公正和刑事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利”[24]。因此,對于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不被強迫自證其罪,在堅持不逾越刑訊逼供之底線的前提下,可以做出適當寬松的解釋。
另一方面,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86條已經明確規定公訴人、審判人員在法庭上有權訊問被告。雖然不被強迫自證其罪已成為公理性原則,但是兩大法系在被告人是否有權決定出庭接受訊問的問題上立場迥異。在審判中英美法系的被告享有的是“不被訊問的權利”,而大陸法系的被告享有的是“面對訊問時不回答問題的權利”。對此,西方學者曾指出,“與普通法系的特權概念形成對照,大陸法系的被告人不能自由決定是否出庭作證和接受訊問。可以隨時對他進行發問,他的權利只是拒絕回答任何問題或者不回應特定的問題。”[25]在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公訴人、審判人員在法庭上有權訊問被告的背景下,被告人拒絕回答全部或部分問題,審判人員從內心很容易產生對被告人不利的猜測。而且,在允許根據被告人沉默進行不利推定的情況下,與選擇拒絕作證相比,出庭接受訊問但拒絕回答的被告人往往面臨更大的心理壓力,從而更傾向于放棄沉默。
基于上述分析,我國對被追訴人沉默證據能力之條件的設定不宜過高。借鑒國外有關被追訴人沉默證據能力的規定,除了我國《刑法》已經明確規定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和非法持有國家絕密、機密文件、資料和其他物品罪的相關構成要件事實可以根據被追訴人沉默推定外,我國立法還可以考慮規定在特定情形下,賦予被追訴人沉默證據能力,允許裁判者以沉默作為對其不利的證據使用。這些特定的情形包括:第一,如果偵查機關在犯罪嫌疑人的身體、衣服、住所、汽車等處發現與犯罪相關的物品或者材料,但犯罪嫌疑人針對此方面的訊問拒絕回答的;第二,如果偵查機關已有證據證明犯罪嫌疑人到達過特定的犯罪現場,而犯罪嫌疑人拒絕解釋其為何會出現在該犯罪現場;第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部分案件事實陳述,但對個別案件事實拒絕回答的;第四,被告人在法庭上對公訴人和審判人員的訊問拒絕回答的。筆者之所以主張上述四種情形下的被追訴人沉默具有證據能力,還考慮到:在前三種情形下,被追訴人先前做出的特定行為或相關狀態,已使得追訴機關有合理根據地相信其可能實施了犯罪;而且在此種情況下,與公安司法機關的進一步調查相比,被追訴人的口頭陳述更有助于澄清事實真相。此外,在上述四種情形下,裁判者基于日常生活經驗,內心也會不可避免地思量被追訴人沉默的原因。在無法阻止裁判者內心評價沉默的情況下,合理地疏導顯然才是明智的選擇。總之,在一定的條件下,賦予被追訴人沉默的證據能力,是利益權衡原則在刑事訴訟中的又一體現。
考慮到被追訴人法律知識的欠缺以及我國刑事訴訟追求案件客觀事實真相的傳統,在有條件地賦予被追訴人沉默證據能力的同時,我國法律還應當明確以下兩點:第一,在根據被追訴人沉默進行不利推定之前公安司法人員負有釋明義務。即在被追訴人應當回答訊問的情形下,公安司法人員必須明確告知此種情況下被追訴人的沉默可能會被作為對其不利的證據使用之法律規定。只有在公安司法人員履行釋明義務的情況下,審判人員才能將被追訴人的沉默作為對其不利的證據使用。第二,被追訴人沉默只能作為定罪的間接證據。如前所述,被追訴人沉默與其是否實施犯罪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只能在一定的程度上證明被追訴人可能實施了犯罪。因此,被追訴人沉默只能作為定罪的間接證據使用,不能僅以被追訴人沉默作為認定有罪的主要證據。就心證的程度而言,裁判者根據被追訴人沉默做出有罪裁決,必須是在除被追訴人沉默外,其余所有證據之總和已經非常接近讓裁判者做出有罪判決之臨界點。簡言之,在證明有罪的價值上,被追訴人沉默只是促使裁判者形成被告人有罪之心證的證據之一,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2.被追訴人沉默可以作為證明其主觀態度的量刑證據使用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是我國刑事司法長期堅持的重要政策。上世紀90年代后期,隨著正當程序理念在我國的傳播,理論界對此傳統的刑事司法政策提出了質疑,有學者甚至認為,“坦白從寬是誘供,抗拒從嚴是逼供”,“沉默權與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水火不相容”,“在我們不斷加強法制建設的今天,作為有罪推定原則的必然產物,坦白叢寬、抗拒從嚴應當永別了。”[26]筆者認為,此觀點有失偏頗。事實上,坦白從寬是世界各國刑事訴訟普遍認可的司法政策。例如,在美國,只要被告承認犯罪,就可以以辯訴交易的方式結案從而獲得輕判;意大利《刑事訴訟法典》第442條第2款甚至明確規定被告人認罪的案件,“在判罰的情況下,法官在考慮一切情節后所確定的刑罰應當減少三分之一。無期徒刑由30年有期徒刑替代。”[27]我國2012年修正《刑事訴訟法》時在第118條第2款增加規定,“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的時候,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如實供述自己罪行可以從寬處理的法律規定”。在認可坦白從寬之刑事司法政策的前提下,被追訴人之坦白,從證據角度來講,屬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在證據價值上,既是證明其有罪的證據,又可以證明其有悔罪表現、作為量刑證據使用。
對于被追訴人拒絕回答公安司法人員的訊問或者故意作虛假回答之行為,我國傳統理論和做法均將其視為“抗拒”,對其從嚴處罰。隨著不被強迫自證其罪理念在我國的普及,理論界對“抗拒從嚴”的正當性提出質疑,認為“抗拒從嚴”與不被強迫自證其罪相沖突,侵犯了被追訴人的沉默權。顯然,對傳統的“抗拒從嚴”提出質疑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一概否定“抗拒從嚴”又似有矯枉過正之嫌。這是因為:抗拒有積極與消極之分。被追訴人沉默,是對國家追訴犯罪的消極抗拒;被追訴人故意作虛假陳述,是對國家追訴犯罪的積極抗拒。對于故意做虛假陳述的被追訴人,如前所述,英美法系國家會以偽證罪追究刑事責任,大陸法系國家對于被追訴人頑固說謊的,會對其酌情從重處罰。我國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第118條保留了該法原第93條中的“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之規定。對此規定,立法部門有關負責人在解釋此條時認為,“犯罪嫌疑人要回答問題的話,就應當如實回答;如實回答,就會得到從寬處理。”[28]基于此,考慮到《刑事訴訟法》第50條已經規定不被強迫自證其罪,筆者認為,我國已經確立了沉默權。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有選擇是否回答的權利,但如果他選擇了回答,就負有實話實說的義務。既然被追訴人對其陳述負有真實義務,那么其故意虛假陳述就意味著違反了該義務,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因此,從不被強迫自證其罪的基本原理和被追訴人真實陳述義務之要求出發,對待被追訴人“抗拒”的科學做法應當是:尊重沉默,懲罰說謊。無論是對坦白的被追訴人從寬還是對說謊的被告人從嚴處罰,事實上都應該存在一個參照,也就是說在什么樣的基礎上從寬或者從嚴。顯然,此參照就是在被追訴人既不坦白、又不說謊而保持沉默時應當判處的刑罰狀態。當法院對被追訴人既不從嚴、又不從寬處罰時,根據便是被追訴人沉默的事實,此時被追訴人沉默就作為量刑證據在使用了。需要說明的是,被追訴人對公安司法機關的訊問,一概以“不知道”或者“記不清”之類的模糊表達作回答或者對指控的犯罪事實直接予以否認的,均應等同于其在行使沉默權,既不能從寬處罰,也不能認為其認罪態度不好而從重處罰;只有那些積極地編造謊言,以致可能誤導公安司法機關的,才屬于應當懲罰的“說謊”。總之,只要我們承認坦白從寬或者認可懲罰說謊,就意味著我們在邏輯上必然承認被追訴人沉默的證據能力,因為無論是對坦白者從寬還是對故意說謊者從嚴,都是相對于被追訴人沉默時的基準刑而言的。ML
參考文獻:
[1]王兆鵬. 美國刑事訴訟法[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26.
[2] Christopher Allen. The Law of Evidence in Victorian England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164.
[3] Ayer. The Fifth Amendment and the Inference of Guilt FROM Silence: Griffin v. California after Fifteen Years [J]. Michigan Law Review, 1980,(78):855.
[4] 陳光中. 刑事訴訟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161.
[5]羅納德·J·艾倫,等. 證據法文本、問題和案例[M]. 張保生,等,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49.
[6] 陳樸生. 刑事證據法[M]. 臺北:臺灣三民書局,1979:276.
[7]克勞思·羅科信. 刑事訴訟法[M].吳麗琪,譯.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29,122.
[8]田口守一.刑事訴訟法[M].張凌,于秀峰,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106,107.
[9] 李永然. 臺灣“刑事訴訟法”及相關法規[Z]. 臺北:臺灣永然文化出版公司,2003:62.
[10]陳光中.證據法學[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131,157.
[11]松尾浩也.日本刑事訴訟法[M].張凌,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142.
[12]薩拉·J·薩默斯.公正審判——歐洲刑事訴訟傳統與歐洲人權法院[M].朱奎彬,譯.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198.
[13]詹妮·麥克埃文.現代證據法與對抗式程序[M].蔡巍,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224.
[14]伊德·凱普.歐洲四國有效刑事辯護研究[M].丁鵬,等,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150,298.
[15]約書亞·德雷斯勒.美國刑事訴訟法精解:第1卷[M].吳宏耀,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462.
[16]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人事事務中心.國際人權文書:各人權條約機構通過的一般性意見和一般性建議匯編[Z].聯合國出版,2004:137.
[17] Anne Bowen Poulin. Evidentiary Use of Silence and the Constitution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J]. The 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 1984,(52):210.
[18]俄羅斯聯邦刑事訴訟法典[Z].黃道秀,譯.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6:281,75.
[19]中國政法大學刑事法律研究中心.英國刑事訴訟法(選編)[Z].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556,561.
[20]孫長永.沉默權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57,87,57,97.
[21] 托馬斯·魏根特.德國刑事訴訟[M].岳禮玲,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81.
[22] Christine Van Den Wyngaert. Criminal Procedure Systems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M].Butterworths & Co.Ltd,1993:250.
[23]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129.
[24]詹妮·麥克埃文.現代證據法與對抗式程序[M].蔡巍,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225.
[25]偉恩·R·拉費弗,等.刑事訴訟法[M].卞建林,等,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1235.
[26]約翰·W·斯特龍.麥考密克論證據[M].湯維建,等,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252.
[27] David M. Paciocco, Lee Stuesser. Essential of Canadian Law: The Law of Evidence[M].Irwin Law,1996:154.
[28] 王兆國.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的說明[G]//吳宏耀,種松志.中國刑事訴訟法典百年(中冊).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873.
[29]米爾吉安·R·達馬斯卡.比較法視野中的證據制度[M].吳宏耀,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6:114.
[30]江曉陽.坦白從寬是誘供,抗拒從嚴是逼供[N].中國青年報,1999-06-24.
[31]意大利刑事訴訟法典[Z].黃風,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158.
[32] 陳菲,等.推進民主法制進步的重大舉措——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負責人就刑訴法修改回答中外記者提問[N].人民日報,2012-03-09.
On Admissibility of the Criminal Defendants Silence
CHEN Xuequan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It is an objective fact that when being interrogated, the accused may choose to keep silent. There is a universal phenomenon among the theorists in China that the admissibility of the criminal defendants silence is totally denied because of the simplis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ory of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Since the criminal defendants silence is associated with the facts of the case, the point that there is justified reason to exclude the admissibility of the criminal defendants silence is worth rethinking. Far from the domestic mainstream view, western countries recognize the admissibility of the criminal defendants silence to a larger extent instead of totally denying it. Although there exist big differences of the regulations about it among them, there are still obvious similar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has been recognized by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in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rules of admissibility of the criminal defendants silence, under which the criminal defendants silence can be used as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to convict the accused and prove his subjective attitude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Key Words:? the accused; silence; admissi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