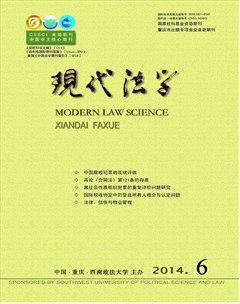再論WTO執行法律本質:遵守抑或再平衡
摘要:長期以來,學界對WTO執行的法律本質一直存在爭論。遵守說倡導者主張WTO執行的目的是促使遵守爭端解決機構專家組或上訴機構的裁決,并阻止未來對該協定的違反;再平衡說陣營則發現了WTO執行中固有的“補償或履行”邏輯。分別考察論戰雙方的主張、理論基礎和理論盲點后可以發現,爭論源于其未對WTO兩種不履行及相應后果加以區分。但是,過于強調WTO法某個特定方面,會造成對WTO一種誤導、歪曲的看法。
關鍵詞:WTO執行;“遵守—再平衡”爭論;外契約行為;內契約行為
中圖分類號:DF961文獻標識碼:A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4.06.13
由于對WTO執行的法律本質持有不同觀點,學術界出現“遵守—再平衡”的爭論,該爭論源自Judith H. Bello的編者評論[1]。她認為,WTO與GATT的規則一樣,并沒有傳統意義上的拘束力。GATT唯一神圣和不可違反之處,在于其對整體權利和義務的平衡。WTO并沒有改變主權國家之間討價還價談判的根本性質,WTO唯一有約束力的義務是維持為獲得成員對該協定政治支持的平衡[1] 417。
與此相反,大多數國際法文獻對國家在國際合作中的“退出”或“不遵守”行為感到痛惜,因為這相當于揭開了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的面具,削弱了以條約為基礎創造國際義務的整個框架。John Jackson和Jide Nzelibe等學者認為,WTO法是具有強制性的法律,即便國家接受中止減讓的后果,也不允許違反[2-4]。Krzysztof J.Pelc反對有效違反國際貿易協定的觀點,認為補償和貿易報復將產生很大的成本[5]。David Collins認為,由于缺乏回溯性補償和不精確的損失計算,會導致損失計算方面的雙重無效率[6]。
這兩個對立的陣營也被稱為“財產規則vs.責任規則”、“合法性觀點vs.有效性觀點”、“規則導向vs.效率導向”或“契約觀點vs.條約觀點”。前者認為WTO協定要求成員使其貿易政策符合WTO紀律(根據“財產規則”實際履行),后者認為WTO協定允許甚至提倡成員通過支付補償或接受同等貿易報復以“買斷”(buy off)它們的WTO義務。前者依據“約定必須信守原則”和國際強行法,后者基于經濟邏輯和理性選擇理論。本文通過梳理論戰雙方的理論根據和理論盲點,認為該爭論源于美國和歐洲在法律傳統上對國際法態度的不同,并指出這兩種觀點都具有片面性。
一、“遵守”說(一)理論基礎
根據“遵守”說,WTO執行旨在促進專家組或上訴機構裁決的遵守,以及為全球貿易法律體制的可預見性和穩定性而阻止未來的違約行為。自從1995年WTO建立時起,世界貿易體制的游戲規則就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GATT1947更多地被描述為權力政治和外交的談判場所,當今WTO代表著以規則為導向、遵循強大的基礎規則和整套共享價值的國際經濟法律體制。烏拉圭回合的貿易自由化談判產生了大量的額外規則和義務,這股完善WTO契約的推動力被理解為偏離互惠性和再平衡的范式,并朝向完全法律化的“貿易憲法”發展。整個體制的重心向規則轉變表明,再平衡在WTO語境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小。
現代法學韓逸疇:再論WTO執行法律本質:遵守抑或再平衡“遵守”說的支持者認為,WTO的根本價值和目的不是狹隘的國家利益,而是整個貿易體制的穩定性和可預見性(《馬拉喀什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第16條和DSU第3.2條)。WTO旨在保護所有經濟代理人,包括貿易者和商業實體、消費者、市民社會和不參與的第三方政府之期待和競爭關系[7]。
同“安全性和可預見性”緊密相關的目標經常出現在任何旨在可靠、客觀和無偏見的爭端解決體制里,換句話說,其目的在于矯正權力的不對稱。該目標源于這樣的愿望:為小的或相對無力的實體(例如小國家、非工業化國家和個人)提供機會和獲得以某種方式保護他們可信賴利益的體制。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就是“正義”的概念,對于任何爭端解決體制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而言,這也很重要。如果允許有利于富國的“買斷”機會,就會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上述目標。因此,減讓的“再平衡”和“有效違約”不應當在爭端解決程序中成為中心甚至起作用[3]117-118,否則,其可能會損害多邊貿易體制的安全性和可預見性之長遠目標。
“遵守”說的支持者還認為,WTO法并非孤立的“自足體系”,而是在國際公法的大背景之中創制。爭端解決機構的裁決是每個成員對全體成員承擔的國際法律義務,而非只是與爭端當事方有關。因此,如果否定專家組或上訴機構的裁決,無異于否定WTO規則本身。如果成員可以不遵循共同商定的規則和程序,整個法律體系將是無效的。DSU通過提供額外時間的措施,在此期間補償和中止可以避開完全遵守的部分壓力,這種“安全閥”的作用使得敗訴的政府有能力改善其在國內法律和政府語境下棘手的處境。但終極的理念是,對于一個理念是客觀的、可信賴的以及為該組織所有成員和非政府受惠者提供安全性和可預見性基礎的、以規則為導向的體制而言,完全遵守仍然是一項很重要的國際法義務[3]122。
對于GATT締約方或WTO成員遵守多邊貿易體制的原因有多種解釋。首先,聲譽成本是成員遵守WTO契約的原因之一。對于某些成員而言,WTO契約與它們正義的理念密切相符,因而即便沒有法律強制,它們無論如何也會對其予以遵守。或者,對其他成員而言,WTO契約只不過是更廣泛的合作博弈的一部分:國家在很多戰線上互動,而貿易關系只是其中之一。如果WTO契約不被尊重,其他戰線的既得利益也會最終受到損害。這些解釋有利于增進人們對遵守國際義務的理解,但它們都涉及一項契約被遵守的個人原因,因此,遵守的原因決定于主觀的理由。然而,法律安全性(交易成本)旨在維護所有情形下契約得到遵守的情勢,其獨立于遵守契約的個人原因。換句話說,為服務于法律安全性,制度上而非個人的原因,必須在契約中取得一致并嵌入其中,以保證其始終得到遵守。救濟所起到的作用正是WTO協定將一直得到遵守的制度保證[8]。其次,WTO體制是國際法之一部分,即便不存在有效的救濟或懲罰機制,成員也會如同遵守一般國際法那樣習慣性地遵守WTO規則或裁決。早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社會心理學家Stanley Milgram就通過研究發現,人們之所以遵守法律規則,部分是由于他們受到這樣做的教育。人們通過學校、家庭和市民組織等學習尊重法律,尊重法律和遵守習慣因此被內在化。在這個內在化的過程中,違反法律將受到制裁的認識很重要。該認識已經足夠,無須事實上受到制裁[9]。因此,國家根據其利益需要理性地遵守國際法,只能是國家行為與國際法規則相一致的部分解釋,而無意識地接受和理所當然地遵守已建立的國際法制度,也構成國家遵守國際法的部分原因[10]。
綜上所述,“遵守說”認為WTO法是具有強制性的法律,補償或貿易報復只是暫時方法,并不決定權利的最后改變。WTO法律框架為其成員在法律安全性和靈活性之間提供一種平衡,在既有爭端解決機制的設計中,經濟效率應當只被視為附隨因素。現今WTO所珍視的基本價值和目的是多邊貿易體制的安全性和可預見性,因此,“再平衡”或“有效違約”理論在正常的爭端解決程序中并不占主導地位甚至不起作用。
(二)法理支持
“遵守”說的支持者求助于以文本為導向的法律解釋方法[3]111。據此,除無條件實際履行的一般規則外,他們并沒有看到任何文本和國際法律容許存在不遵守的回旋余地。如果在WTO協定實施的過程中出現契約漏洞,或當事方既對承諾的減讓又對條約文本的相關段落很不滿意,各個成員有義務進行正式和建設性的再談判。例如,GATT第28.3條規定再談判的義務,是基于貿易伙伴是否最初參與減讓的談判、具有特別的需要或者其他方面的需要。 GATT第28.3條規定,談判時應適當考慮:(甲)某些締約國和某些工業的需要;(乙)發展中國家為了有助于經濟的發展靈活運用關稅保護的需要,以及為了財政收入維持關稅的特別需要;以及(丙)其他有關情況,包括有關締約各國在財政上、發展上、戰略上和其他方面的需要。為了證明WTO執行目的是促進嚴格遵守規則,“遵守”說支持者指向DSU無數的段落、《馬拉喀什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的序言和文本、籌備記錄、各個專家組和上訴機構報告[7]13。
正如上訴機構在美國汽油標準案中所提到的那樣,條約解釋的一般方法已經獲得習慣國際法或一般國際法的地位。根據DSU第3.2條規定,WTO體制可以依照解釋國際公法的習慣規則澄清其現有的規定。 Appellate Body Report on United States - Standards for Reformulated,WT/DS2/AB/R,adopted on 20 May 1996,p.17.這對于很多WTO談判者而言是一個有益的啟示,而對于認為WTO規則不是國際法規則的人來說就如同致命一擊。因為如果WTO規則必須與國際公法規則相一致地解釋,其肯定只能是國際公法的規則[11]。此時,如果不遵守WTO裁決,這同否認其規則本身無異。如果條約當事方可以不遵守規則,整個法律體系就會失去作用。專家組的建議是公共物品,而不只是與爭端當事方有關,這不但由于其創立的先例,更因為其確定法律規則的穩定性[3]120。根據DSU中11個單獨的段落,可以得出一項遵守爭端解決裁決義務的存在這一結論。例如,第3.7條規定:“如不能達成雙方同意的解決辦法,則爭端解決機制的首要目標通常是保證撤銷被認為與任何適用協定的規定不一致的有關措施。”
二、“再平衡”說 “再平衡”說的支持者認為,WTO法并不要求不惜一切代價地遵守。貿易協定是內生不完全契約,WTO協定是世界貿易體制中最為核心的貿易協定[12]。正因為WTO協定是不能明確考慮到成員之間關系復雜性以及不能預測所有未來緊急情況的不完全契約,如果情況發生改變,根據條約文字嚴格履行并不是一直都能共同獲益[7]248-249。WTO的本質正如其前身GATT,是WTO成員相互給予和交換彼此市場準入機會的機制。
再平衡方法根植于這樣的信念,即世界貿易體制從根本上說是由產生“平衡減讓”的貿易自由化互惠承諾所驅動的。根據該學說,DSU執行機制通過平衡相互的減讓,確保受害者得到賠償和為加害者提供有效的退出可能性。WTO成員可以選擇不遵守其所承擔的WTO義務,只要其愿意提供賠償或承受報復。這就把WTO爭端解決機制視為違約并補償的體制,或認為WTO應當允許成員“買斷”違約。這種以單一“責任規則”(liability rules )保護權利的理念,后來發展成為更寬泛意義上的“有效違反國際協定”(efficient breach of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理論。
根據“再平衡”說,WTO包含市場準入的互惠允諾產生總體上的權利義務平衡。相應地,WTO最好被概念化為雙邊平衡之網(web of bilateral equilibria),而執行WTO義務如同在該平衡被擾亂時恢復到承諾水平的平衡[7]17。GATT談判使用的基本概念是“互惠性”,即視對方行動采取相應行動的行為。互惠性貿易自由化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比在19世紀更為盛行。GATT成員曾使用一系列標準來評價關稅減讓的交換是否平衡。有關具體減讓的GATT談判開始過程基本上是雙邊的,即兩個締約方互相提出要價和出價的清單,談判集中于雙邊平衡減讓的交換[13]。該學說支持者傾向于從法律經濟學中汲取營養,并從美國私人商業契約的經濟學理論里提取有用的類比。
在契約理論用語中,“再平衡”說反映了事后免除契約義務的“責任規則”觀點。即如果某成員的行為違背WTO原則,或使其他成員在WTO規則下享有的利益喪失或受到損害,該被訴方應向申訴方提供包括金錢補償或提供新的關稅減讓承諾或市場準入條件作為補償,以保護彼此貿易利益在總體上之平衡。這不僅意味著被訴方有權選擇補償的形式,而且有權選擇是否遵守WTO義務。
從根本上說,“再平衡”說基本上將爭端解決的目的看作為受害者在不平穩世界(non-stationary world)中提供安全閥。DSU執行機制通過確保平衡相互的減讓,實現了對受害者進行賠償和為加害者提供有效退出可能性的雙重目標[14]。
(一)理論基礎
“再平衡”說主要是基于經濟學理論。據此,WTO和其前身GATT具有相似的本質,即為成員之間相互交換市場準入提供機會。很多文獻的基本直覺導向(basic intuition guiding)是國家在貿易事項上進行合作以限制單邊的以鄰為壑(beggar-thy-neighbor)的政策[7]6。無論是在GATT或WTO體制下,貿易爭端意味著最初的市場準入平衡出現不協調,而WTO爭端解決機制的執行措施則確保出現適當的平衡。
根據“再平衡”說,如果遵守法律規則沒有效率,就不存在必須遵守的法律義務,是否有效率將決定著法律具有拘束力與否。在GATT體制下,主觀的群體利益決定法律規則的拘束力,現在卻根據“效率”這一客觀標準進行判斷[15]。即如果一方當事人的履行沒有效率,或履行成本超過其收益,就不應該有義務履行契約。“再平衡”說將WTO成員根據自身利益得失作為遵守或違反規則的重要根據,這是應用法律經濟學中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的具體表現,據此,執行涉及遵守的成本—效益分析[16]。
值得一提的是,關稅補償并不會壓低先前商定的市場準入平衡,而是使其保持與當初相同的水平,這符合“再平衡”的說法。金錢補償對于關稅賠償而言具有可替代性,但從自利的決策者角度來看,這種選擇缺乏吸引力。由于WTO從某種程度上講是一個政治契約,各成員需要顧及國內選民的支持。故而,這里所謂“效率”,就不一定是世界市場貿易的經濟效率以及消費者的福利,而是適用于政治行動者的效率概念,即通常是以符合政治家的利益為標準。可見,如果WTO協定被視為相互交換利益的契約,并聲稱法律是而且應當設計來保護政治精英的福利,就將與WTO尋求促進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的宗旨背道而馳。
(二)法理支持
根據“再平衡”說,WTO協定的用語特別是DSU規則和程序可以有效地以與霍姆斯式的賠償或履行體系(Holmesian pay-or-perform system)相一致的方式解釋:因為受害者可以從有問題的措施中獲得相應水平的賠償,潛在加害者有權從任何條約義務中單邊退出或免責。根據DSU第3.7條、第19.1條、第22.1條和第22.4條規定,WTO協定提供通常意義上法律可依靠的責任規則[17]。Alexander Roitinger認為,DSU明確承認違反WTO協定是貿易政策靈活性機制設計之一部分。因此,DSU的主要功能是決定一項違反是否已發生并確立違規者必須支付的代價(再平衡)[18]。換句話說,WTO協定中規定的任何偶發事項都能夠被違反,鑒于受害者的期待值會得到維護,加害者可以利用任何契約的漏洞[7]10。
“再平衡”說也因為GATT第19條例外條款和第28條再談判條款的可用性而得到證明。在一般公約用語中,外契約行為(extra-contractual behavior)被稱為“契約背棄”(contractual defection)、“背離”(deviation)或“行為不當”(misdemeanor)[14]7。但是,在以責任規則保護權利的假設之下,所有退出行為都為協定措辭所覆蓋和允許,這將意味著不存在外契約行為。換句話說,DSU規則和程序的措辭成為“不履行”的合法工具,可以內部化(internalizes)所有類型的違約行為[14]250。以非違反之訴為例,其力圖在協定沒有約定的情況下發生糾紛時為成員尋求一種禮儀的平衡。因為與所有成文法的局限性一樣,WTO規則不可能涵蓋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但某種WTO協定字面上沒有規定的情形卻可能阻礙該協定宗旨的實現,此時就需要一套獨特的法律規則來調整成員之間的利益平衡。
根據DSU第3.7條,如果“爭端各方均可接受且與適用協定相一致的解決辦法”的“首選辦法”無法實現,可由被訴方“撤銷被認為與任何適用協定的規定不一致的有關措施”,或起訴方在經DSB授權后采取“最后手段”,即“在歧視性的基礎上針對另一成員中止實施適用協定項下的減讓或其他義務”。雖然“中止減讓或其他義務”可能在促進規則的遵守或爭端的解決方面并沒有很有效的作用,但其作為自助的工具使得申訴方可矯正其所遭受的貿易不公正。換言之,提起訴訟的國家通過撤銷其先前對有不當行為的政府之貿易減讓或承諾,從而恢復到違約之前的平衡。
烏拉圭回合是朝著增強紀律性和推行名副其實的威懾方向發展,但其整體模式仍然是民事而非刑事司法。違規國家的首要選擇是停止有異議的實踐,第二種選擇是違規國家支付補償或承受先前獲得利益的撤銷。對違法行為的懲罰并不在預期或被允許的范圍之列[19]。就WTO中止(suspension)而言,如果成員想以該制度設計促進遵守,它們會允許超過而不只是對等性的報復。將對等性作為上限意味著WTO成員只希望“再平衡”和避免懲罰性報復(這也是小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所懼怕的),并希望保持一些偏離規則的靈活性[20]。
根據1969年《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60.2條規定,特別受違約影響之當事國有權援引違約為理由,在其本國與違約國之關系上將條約全部或局部停止施行。DSU的救濟條款反映出《維也納條約法公約》關于違約影響之當事國可以在條約下中止其義務的原則,如DSU第3.8條“違反”規則的用語。此外,“中止減讓和其他義務”也出現在《保障措施協定》中。該協定第8.2條允許政府在某種情形下對進口施加保護主義的保障措施,然后讓出口成員以中止實施1994年關貿總協定項下實質相等的減讓和其他義務相回應。保障措施下的“中止減讓和其他義務”明顯是基于“再平衡”而非執行規則。關于“再平衡”的含義,最簡單的答案指DSU第22.4條的規定,即DSB授權的中止減讓或其他義務的程度應等于利益喪失或減損的程度。因此,在法律用語上,“再平衡”在WTO爭端解決中指兩個水平上的同等:中止和損害,即起訴方成員將被允許實施與違反造成的不利影響同等水平的報復。(參見:Holger Spamann.The Myth of Rebalancing Retaliation in WTO Dispute Settlement Practic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2006,9(1):37-38.)退一步講,由于實際履行一直被視為對個人自由的威脅,而賠償比起改變法律而言侵略性更小一些[21]。因此,在嚴格遵守WTO義務可能干涉違法國家的主權而在政治上行不通時,給予賠償無疑是更具有合理性的替代方法。
三、論戰雙方之理論盲點(一)“遵守”說
由于WTO協定主要是國際貿易方面的多邊規則,其在促進規則得到遵守的同時也要保證經濟效率的最大化。如果在任何情形下都要求成員完全遵守或實際履行,將不符合私人經濟運營商對于可預測性的利益要求。從系統的觀點看,賠償或其他形式的雙邊解決,與堅持在所有情形下的完全和即時遵守截然不同,這可能實際上使該體制免于崩潰,而不是損害WTO法律制度的完整性。
正如Joseph Nye所指出的那樣,賠償或中止減讓的程序作為遵守的支持,就像是一所房子的電力系統的保險絲,保險絲燒斷總比房子被燒毀好[22]。即便John H. Jackson支持在WTO中強有力的“規則導向”,他也承認成員在簽訂協定時并不想要完美地遵守WTO主要義務的事實[23]。既然爭端解決機制的首要目標“通常”是保證撤銷被認為與任何適用協定的規定不一致的有關措施,這就意味著遵守并不會一直是其追求的目標。如果說DSU創造出一項從長遠來說需要實際履行的義務,就不一定表明其排除暫時偏離這種義務的選擇。促使遵守專家組或上訴機構的建議可被理解為禁止拖延的策略,而不是排除補償或報復的選擇。因此,條約文本對于違反者超時維持一項違反并提供補償或接受報復的選擇之合法性并沒有完全的確定性。
WTO協定和DSU有大量的段落為存在遵守的義務提供支持,但這種支持也并非十分確定,其他段落表明了更加寬松的標準。更重要的是,即便從正式的、法律的角度看,John H. Jackson的觀點是對的,但這不能否定在實際情況中違反者可簡單地選擇不遵守裁決的事實。此外,DSU關于反措施的條約文本和仲裁員對于《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的解釋將反措施的大小與違約所造成的損害連接起來。仲裁員很清楚該等水平的反措施不足以促使遵守,但他們并沒有權力授予更加嚴格的措施。實際的結果就是,只要成員愿意付出相應的“代價”,就有違反義務的選擇權。這種行為就國際法而言可能被認為是“非法”的,但WTO體制仍顯而易見地允許其發生[24]。
(二)“再平衡”說
第一,“再平衡”說很難說是解釋WTO義務和執行的法律效力理論,更像是與市場準入靈活性有關的理論。當該理論的支持者認為WTO規則并不具備傳統意義上的拘束力時,事實上是想表明通過談判達成的市場準入并無嚴格約束力。該學說的主要缺陷在于,其主張WTO義務沒有約束力的結論,是建立在明確達成一致意見的有關市場準入承諾上的,即所有WTO權利的法律效力均基于“內契約”(intra-contractual)的靈活性之上。一個最理想的契約將能夠規定所需的靈活性,它將在“內契約”的行為和外契約的行為之間有所區分。前者如由外部沖擊(不曾預料到的意外事件)所引起的在契約上允許的行為,后者如可歸因于機會主義行為的不被允許的行為。(參見:Anne Van Aaken.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between Commitment and Flexibility: A Contract Theory Analysi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2009,12(2):518.)例如,GATT第28條和GATS第21條所規定的靈活性受到WTO兩種權利的明確措辭所限制:WTO成員可單邊修改GATT“減讓”和GATS“承諾”。上訴機構認為,上述措辭的通常意義表明“成員可以放棄權利和給予利益,但其不能減少自己的義務”。參見:ECBananas III (AB),para. 154; ECPoultry (AB),para.98; USRestrictions on Imports of Sugar (GATT panel),para. 5.2.因此,成員不能根據GATT第28條和GATS第21條單邊修改其承諾而減少其他WTO義務。
第二,雖然存在單邊修改承諾的可能性,但WTO義務的拘束性并未受到影響。換句話說,WTO義務具有互惠性和整體性之分,前者如市場準入承諾,后者如非歧視義務。影響或改變一項雙邊關系,通常不會侵犯到其他雙邊關系,其違反只可能被互惠關系的另一方援用。由于整體性義務的約束力在本質上反映了成員的共同意愿,改變一項整體性規則,必然要對所有為該規則約束的成員造成沖擊。誠然,在法律經濟學者看來,WTO的主要任務是市場準入的相互交換,但如果僅僅以互惠的權利與義務為中心,就會不恰當地縮小其適用范圍。很顯然,WTO還包含貿易權利之外的其他權利和義務。只要一項不是基于雙邊市場準入承諾的條約義務被違反,“再平衡”說就不能從邏輯上找到可求助的救濟手段。WTO法所促進的相互作用不僅僅是雙邊關系的集合,還是在定性和定量方面與個體經濟關系明顯不同的結果。
第三,“再平衡”說基于經濟學的契約模型,通常用以解決具有雙方當事人的簡單貿易關系,但WTO協定比起任何正式契約理論所處理的契約關系都要復雜得多。根據該理論,執行的主要目的是“促使當事人在遵守對承諾人產生的利益超過要約人成本時遵守其義務,而認可要約人在自身遵守成本超過承諾人所獲得利益時選擇違反其義務”[25]。WTO再談判和爭端解決關于違反義務的條款,其設計旨在面對不可預期情況時促進有效率的調整,市場準入權利最終由“責任規則”所保護。成員可單邊修改其承諾,但必須對此負責,其責任被限定為受影響當事方“實質上相同”的報復。既然WTO成員已明確同意單邊修改承諾,檢驗違約是否有效率的價值就很有限。“從實在法的角度看,在DSU措辭中并不存在‘賠償或履行(pay-or-perform)的責任類型。”[14]261
在既有體制下,補償和中止減讓只是在“合理期限”業已屆滿而某成員仍然不遵守時提供某種相互貿易減讓的再平衡。兩者都只是遵守爭端解決最終目標(DSU第22.1條)的暫時性措施[26]。因此,WTO并不是鼓勵成員以接受補償或中止減讓來代替完全的執行,DSU現有的設計明顯標志著“違約并補償”至少都只是“暫時性措施”。此外,DSU第21.1條強調,“為所有成員的利益而有效解決爭端,迅速符合DSB的建議或裁決是必要的”。如果違反WTO規則對于國內利益團體和選民而言是一項現實的政策選擇,這也將違反國家締結國際貿易協定的初衷。再者,根據DSU規則,政府使用“中止減讓和其他義務”時缺乏任何減輕私人經濟行為者的經濟或社會后果的義務。根據第DSU第22.8條,如果旨在使一措施符合有關適用協定的建議未得到執行,DSB將會繼續監督其執行。可見,GATT和GATS為某些權利提供靈活性并不能改變WTO承諾或義務的拘束力,成員以同意賠償或接受中止減讓來代替履行也不能改變其違反義務的事實。
毋庸置疑,國際貿易依賴于比較成本和收益,但國際貿易法的根基是“條約必須信守”的絕對命令。根據國際法,成員應當受到WTO協定的法律約束,從GATT到WTO的轉變是旨在增強既有的GATT原則而不是改變這些原則自身。這種增強有望提高成員對WTO法的遵守,并減少對單邊貿易措施的使用[27]。還應當看到,在GATT和WTO體系下,已存在單獨的“再平衡”機制,包括第19條的保障措施和第28條有關修改減讓表再談判等規定。由于減讓承諾表是GATT和GATS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應當視為代表“所有當事方的共同意志”(the common intentions of the parties)。這些“共同意志”不能在某條約當事方主觀和單邊的基礎上得以確定。Appellate Body Report,European Communities-Customs Classification of Certain Computer Equipment,WT/DS62/AB/R,WT/DS67/AB/R,WT/DS68/AB/R,adopted on 5 June 1998,Para.84.因此,在既有規則不能滿足其需要時,成員只可根據“再平衡”進行再談判,或利用WTO法允許的其他靈活性機制。一般而言,承諾與直接來自協定的義務具有同等意義上的約束力,即使承諾可能因為任何成員的意愿而修改,但在此之前,承諾的法律效力并不會有所減損,成員也不因共同議定允許單邊修改的條款而放棄其質疑修改計劃的權利。
第四,如何量化互惠或再平衡減讓的“價值”,這也是“再平衡”說存在的根本問題。換言之,是否存在一個可計算“再平衡”的“比較基準”(comparator)仍有疑問[28]。當GATT體制的首要主旨由關稅約束組成時,雖然制定可量化關稅減讓的措施可能在方法上涉及相當大的差異并導致不同的量化水平,但多少還是比較容易的。然而,在1960年之后,整個GATT體制將其注意力從關稅轉向非關稅壁壘和所謂的規則。在通常情況下,這在事實上不可能量化違反一項規則對未來潛在貿易的影響,即便是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義務,可能有時也難以量化。對于環境保護和食品安全的管理手段,通常不可能對其影響設定任何正當的、量化的措施。整個體制向規則轉變表明“再平衡”在WTO語境下能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小。在條約規則大部分是程序性的時候,如DSU中的措施和WTO憲章中的某些條款,這種傾向就更加突出[3]121。其次,要確知“相稱”和“水平”意欲何指也會相當困難,對此不存在簡單的解決方案。由于貿易流動的非對稱性,即便是一項相同的特定措施,受制于其適用的貿易流動規模和構成,也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因此,WTO實踐中必須使用某些抽象的“比較基準”估量中止和損害的水平,以及決定其等效性。核心問題是,是否要以貿易額、經濟損失和收益(福利效果)或關稅作為貌似合理的“比較儀”。DSU第22.4條文本及其語境都不能解決什么是法律上正確的“比較儀”的問題,在DSU或其他地方也沒有這種界定[28]38。
即便DSU第3.3條提及權利與義務的平衡,其有時被認為是WTO協定應當保證來自遵守的實體利益合理的平衡,在GATT中,這種觀點經常導致批評,認為其以實用主義方法解決締約當事人之間的爭端。該實用主義方法要求對于協定實體目標達成根本上的共識,但是,在WTO這樣有如此不同成員資格的組織中,并不存在這樣的共識,外交和實用主義不大可能會導致相互接受的解決方案[15]34-35。事實上,WTO爭端解決體制主要是從多邊貿易體制提供可靠性和可預測性的角度來保護各成員在適用協定項下的權利和義務。WTO中止減讓可能具有以下目標:以受害者為中心的補償,包括相互撤銷減讓(再平衡)和補償受害方的損失;以違約方為中心的制裁,包括促使遵守和懲罰[20]37-38。因此,“再平衡”說基本上將爭端解決的目的看成受害者在不穩定世界中的“安全閥”,這不足以概括WTO體制的全貌。
WTO成員選擇和實施反措施的實踐也表明,申訴方的主要目的是促使遵守而不是為了獲得減讓之再平衡。首先,當被申訴方不遵守一項WTO裁決時,申訴方并沒有經常地適用授權的反措施。在60個可以報復的爭端中,WTO成員只在17個爭端中正式請求授權報復,只有10個案件完成訴訟并獲得授權實施反措施,其中只有5個實施反措施。如果再平衡是申訴方的主要目標,其將會更加積極地尋求和實施報復權利,以在被申訴方違反WTO規則和不遵守WTO裁決時恢復其貿易利益和減讓的平衡。即便是WTO最有實力的兩個成員也不經常適用報復,例如,美國只在兩個爭端中謀求和實施報復,歐盟正式謀求報復權利7次但只實施2次。在實踐中,即便獲得授權,申訴方也經常訴諸旨在向外國出口商施加遵守壓力的機制而不是報復。如果成員尋求貿易減讓的再平衡,其必定在被申訴方未能遵守裁決時更少猶豫地利用報復性的裁決。其次,針對被申訴方國內少量在政治上很重要的生產商的戰略,再次表明申訴方的主要目的是遵守而不是再平衡。申訴方發現,比起全面地以較低比率提高關稅和針對與WTO不一致措施中獲利的行業,將報復措施集中于政治上有影響力的出口團體是促使遵守的更有效方式。第三,小型發展中國家申訴方的實踐同樣表明其目標是促使遵守。當大型WTO成員(就其行使市場權力而言)以提高關稅施以報復時,小型發展中國家以中止知識產權保護的形式謀求和獲得報復權利,因為這有利于向各個申訴方(美國和歐盟)有影響力的選民施加游說遵守的壓力[29]。
四、結語“再平衡”陣營的論據是借鑒私人契約中的經濟學理論,“遵守”陣營的依據則深植于傳統的國際法理論。前者將WTO協定簡化為成員交換互惠的市場準入減讓或關稅自由化承諾的單一權利契約,這些相互的自由化承諾事實上由純粹的“責任規則”所保護,后者嚴格根據“條約必須信守”原則,要求國家在任何情況下都要信守其先前作出的承諾。“遵守—再平衡”爭論的主要分歧在于應當采用何種方式和力度保護WTO法所規定的法定權利(entitlements)。在卡拉布雷西和梅拉米德的理論框架中,“權利”一詞是用“entitlements”而不是“rights”來表示,因為他們分析的目的,正是要基于權利享有的法律保護程度來區分不同種類的法律權利。他們提醒防備對法律用語“rights”不加區別地使用,并認為所有的法律可被視為是權利的所有權和交換(強制的或自愿的)的規則。由于“rights”一詞的習慣用法通常只對應一種類型的權利(即那些由所謂“財產規則”保護的權利),需要有更寬泛的詞語“entitlements”來避免混亂,并概括不僅一種而是所有類型的權利。(參見:Joost Pauwelyn.Optimal Protec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Navigating between European Absolutism and American Voluntarism[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5-6.)
但是,上述兩個陣營都未能區分WTO體制下“不履行”的兩種情況。在WTO的語境下,成員的不履行可分為“外契約”和“內契約”兩種情況。具體而言,事后不履行或違反先前商定的契約義務可能有兩種方式:第一種“不履行”構成“外契約”、非法的行為,與其相應的救濟方式被稱為懲罰或制裁。任何當事方在契約上不得不根據其先前所作出的貿易自由化承諾執行,任何與該嚴格實際履行義務相抵觸的“外契約”行為都將受到嚴厲的懲罰。“外契約”違反行為和相應的懲罰一并被稱為執行。WTO主要是在GATT/GATS第23條和DSU第21條和第22條涉及執行問題。另一種不履行是契約整體規定的一部分,并不違反契約的措辭,因而是被允許的、合法的行為,與其相聯系的救濟方式是補償。當事人就允許撤回先前商定的減讓達成之共識,可稱為免責、不履行或免除義務。免責規則一般可系統化為退出機制或再談判條款。例如,再談判就明顯缺乏“違約”的特征:在違反協定之前,成員的義務業已為相互之間的共識所修改,因此,這并未違反契約條款。“內契約”的不履行及其救濟程序一并構成WTO貿易政策靈活性機制。Simon A. B. Schropp將貿易政策靈活性稱為“結構性背離”(structured defection)、“選擇性脫離”(selective disengagement)或“安全閥”[14]8-9。
綜上所述,“遵守說”可有效地解釋“外契約”行為和相應的懲罰,而“再平衡”說描述的是“內契約”行為及其救濟。“遵守—再平衡”爭論是圍繞著WTO執行的本質進行的,它們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分析WTO協定,兩種觀點是相互補充而不是相互排斥的關系。因此,強調WTO法某個特定方面往往會造成對WTO一種誤導、歪曲的看法。WTO議題的復雜性導致上述爭論的持續,這也意味著WTO協定應進一步改革,以更靈活的方式保護不同性質的權利。當然,隨著國際法的更加發達和制度化,包括WTO在內的國際貿易協定很可能出現類似于國內法更為多樣化和具有滑動尺度的權利保護和執行方法,這樣才能確保國際權利得到最佳水平的法律保護。 ML
參考文獻:
[1]Judith Hippler Bello.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Understanding: Less Is More[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6, 90(3):416-418.
[2]Joel P. Trachtman. Building the WTO Cathedral[J].Stanfor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7, 43(1):14.
[3]John H. Jackson. International Law Status of WTO Dispute Settlement Reports: Obligation to Comply or Option to “Buy Out”?[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4, 98(1):109-125.
[4]Jide Nzelibe. The Credibility Imperative: 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Retaliation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s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J].Theoretical Inquiries in Law, 2005, 6(1):215-254.
[5]Krzysztof J. Pelc. Seeking Escape: The Use of Escape Claus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greements[J].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09, 53(2):349-368.
[6]David Collins. Efficient Breach, Reliance and Contract Remedies at the WTO[J].Journal of World Trade, 2009, 43(2):225-244.
[7]Simon A.B. Scropp. Revisiting the “Compliance vs. Rebalancing” Debate in WTO Scholarship: Towards a Unified Research Agenda[R].HEI Working Paper No. 29,2007:11.
[8]PC Mavroidis. Remedies in the WTO Legal System: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J].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0, 11(4):810-811.
[9]Stanley Milgram. 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M].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1974.
[10]Onuma Yasuaki. International Law in and with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Func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J].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3, 14(1):122.
[11]Joost Pauwelyn. The Role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WTO: How Far Can We Go?[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1, 95(3):543.
[12]Henrik Horn, Giovanni Maggi, Robert W. Staiger. Trade Agreements as Endogenously Incomplete Contract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0, 100(1):394-419.
[13]Bernard M. Hoekman, Michael M. Kosteck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From GATT to WTO[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66-69.
[14]Simon A.B. Schropp. Trade Policy Flexibility and Enforcement in the WTO–Reform Agenda towards an Efficient “Breach” Contract[D].University of St. Gallen,2008:246.
[15]Isabel Feichtner. The Law and Politics of WTO Waivers: Stability and Flexibility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35.
[16]Robert E.Scott, Paul B.Stephan. The Limits of Leviathan: Contract Theory and the Enforcement[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55.
[17]Alan O. Sykes. The Remedy for Breach of Obligations under the WTO Dispute: Damages or Specific Performance[G]//M. Bronckers and R. Quick. New Direction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Essays in Honour of John H. Jackson. 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0:349.
[18]Alexander Roitinger.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of Trade Policy Flexibility in the World Trading Order: Analysis and New Direction for Reform[D]. University of? St. Gallen, 2004:144.
[19]Andreas F. Lowenfeld. Remedies along with Rights: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the New GATT[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4, 88(3):487.
[20]Joost Pauwelyn. The Calculation and Design of Trade Sanctions in Context: What Is the Goal of Suspending WTO Concessions?[G]//Joost Pauwelyn, Chad P. Bown. The Law,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Retaliation in WTO Dispute Settle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41-42.
[21]Alan Schwartz. The Case for Specific Performance[J].Yale Law Journal, 1979, 89(2):296-297.
[22]Joseph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G]//M. Mike Moore. A World without Walls, Freedom, Development, Free Trade and Global Govern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109.
[23]Carlos Manuel Vazquez, John H. Jackson. Some Reflections of Compliance with WTO Dispute Settlement Decisions[J].Law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2002, 33(4):565.
[24]Amrita Narlikar, Martin Daunton, Robert M. Stern.The Oxford Handbook o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564-568.
[25]Warren F. Schwartz, Alan O. Sykes.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Renegotiation and Dispute Resolution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J].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002, 31(1):181.
[26]Claus D. Zimmermann. Strengthening the WTO by Replacing Trade Retaliation with Stronger Informal Remedi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 Policy, 2012, 11(1): 83-84.
[27]Sebastiaan Princen.EC Compliance with WTO Law: The Interplay of Law and Politics[J].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4, 15(3):556.
[28]Holger Spamann. The Myth of Rebalancing Retaliation in WTO Dispute Settlement Practic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006, 9(1):31-79.
[29]Gregory Shaffer, Daniel Ganin. Extrapolating Purpose from Practice: Rebalancing or Inducing Compliance[G]// Chad Brown, Joost Pauwelyn .The Law,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Retaliation in WTO Dispute Settle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73-86.
The Legal Nature of WTO Enforcement Revisited: Compliance or Rebalancing
HAN Yichou
(Law Schoo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The legal nature of WTO enforcement has been debated in academic circles for a long time. Compliance advocates maintain that the objective of WTO enforcement is to induce compliance with DSB panel/AB rulings, and to deter future violations of the Agreement, while rebalancing camp detects an inherent “payorperform” logic in WTO enforcemen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ntentions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s well as theoretical blind spots on both sides separately.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debate has not made a distinction between two kinds of nonperformance and relevant consequences in the WTO. However, overemphasizing one particular aspect of the WTO law tends to create a misguided and distorted image of the WTO.
Key Words:? WTO enforcement; “compliance vs. rebalancing” debate; extracontractual behavior; intracontractual behavi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