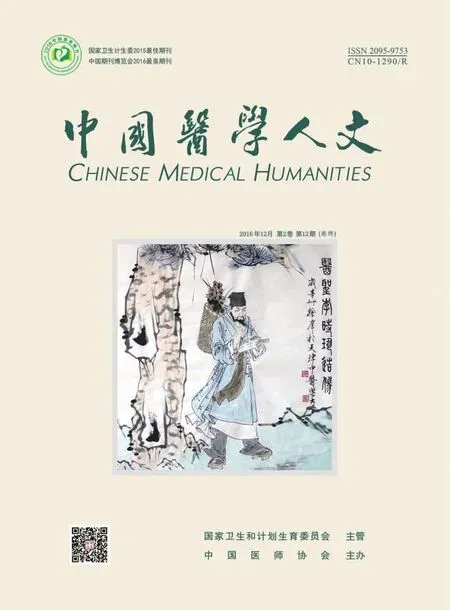批判性醫學人文接受復雜與挑戰
文/威廉·瓦伊尼 費利西蒂·卡拉爾 安吉拉·伍茲 譯/李怡然
批判性醫學人文接受復雜與挑戰
文/威廉·瓦伊尼 費利西蒂·卡拉爾 安吉拉·伍茲 譯/李怡然
批判性醫學人文的目的是什么?
面對這個問題,醫學人文領域的臨床醫生、研究者、醫療工作者、藝術家可能會感到很絕望,因為他們認為這又是一次對醫學人文進行定義的嘗試,將批判性醫學人文視作一門學科、某一詢問范圍或是一整套干預手段、共同價值觀或跨學科的合作關系。這一特殊議題包含了“critical(批判性)”這個單詞的很多方面——緊急的、懷疑的、可評估的以及運用批判的哲學和政治學傳統去探索批判性醫學人文能夠做什么,而不是去發現批判性醫學人文意味著什么或是決定它能提供的精確的學科和跨學科知識。如果過去是醫學人文的學科多樣性鼓勵了其創造性和認識論創新,那么現在涌現出的文章則試圖幫助醫學人文接受新理念、新挑戰以及醫學與健康學科已經相銜接的這一事實。醫學人文也進一步對其涉及的知識、實際操作以及與政治領域的銜接進行探索。
這些并不意味著我們將否認醫學人文所取得的成果,如它對實證主義的生物醫學“簡化論”的抵制;它對敘述為主的醫療干預以及其局限性的敏感性;它對醫患關系的重新審視與關注;它對疾病的定義及診斷實踐的興趣;藝術在健康中的動態角色;比較歷史學的治療作用。以上領域的特點是專注于生物醫學知識的局限性及人文學科如何為醫生的臨床操作帶來同理心。對這一特殊議題的解答主要來自相關領域,包括大陸哲學、科技研究、激進政治、酷兒理論(指文化中所有非常態的表達方式)和殘障研究。這些領域雖然很接近通常的醫學人文領域,但是醫學人文有時會對這些領域視而不見。它們都遭遇著全球分配不平衡的健康資源、醫療護理和政策以及科學研究。這一特殊議題也將醫學人文視作一個強大的工具,借助這個工具不僅強調了健康和疾病的意義及歷史文化環境,也強調了健康與疾病的產物、疾病的愈合以及疾病在這個岌岌可危的、不平等的、環境惡化的社會中的傳播。
在本文中,我們首先討論一些我們希望涉及的理論爭論:醫學人文在當今社會的位置,醫學人文與占主導位置的生物醫學對于健康和幸福的理解的關系。我們希望有更多的學者深入關注醫學人文中的健康、疾病和治療以及相關的人類和非人類的生物社會有機體、政治經濟體、對話及情緒反應。醫學人文是否可以更加顯性地參與到本體問題的討論中,特別是病因學、發病機理、醫療干預和護理,而不是像往常一樣,將這些問題歸入生命科學和生物醫學領域。
“批判”什么?
20世紀到21世紀之間,在歐洲和美國的很多大學,“批判主義”對那些致力于政治研究的學者來說充滿了號召力。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法蘭克福學院的哲學懷疑論和政治激進主義。該學院將批判理論作為形成知識團體的途徑并帶來了社會的改變。Theodor Adorno, Max Horkheimer以及Hannah Arendt的作品使歐洲人撰寫“評論”的歷史更加悠久。他們作品的特點是持續地有系統地對某一既定的事物或過程進行批判。社會學、地理學、法律、公共衛生和文學研究都有“批判的轉折”,通常通過豐富政治承諾的表達方式,來顯性地思考那些能夠捍衛其相關知識的假設。因此,我們意識到有必要思考醫學人文研究中已經存在的標準和價值。這些包括但不僅限于“人種”和種族劃分、性別、殘疾(包括精神疾病)、科技與傳媒、國家的經濟狀況以及社會和環境的不平等,都對醫學知識的發展和健康以及人們對于疾病的體驗至關重要。我們主張以全新的視角看待“批判的”。我們也對如何闡明多種多樣的醫學人文實踐方式更感興趣,不僅限于對權力失衡的敏感,也包括以創新和懷疑的方式重新理解醫學(包括與醫學密切相關的領域),然后將其造福于個人和社會的健康。在這里,我們很感激Judith Butler 的理論,她將批判的特征描述為不僅僅是簡單的“破壞的行為、說不的行為或是肆意的懷疑”。她認為,批判也許可以在步驟階段幫助改革,否則我們將無法保證人們擁有不同意見的權利以及立法進程。我們希望醫學人文,通過在步驟層面發起改革來扮演其批判的角色。
本文將“批判性醫學人文”描述為一系列趨勢,這些趨勢是醫學人文以舊途徑就能輕易獲得的。這個短語承認和定義我們希望推進的責任,但是我們并不希望成為批判的把關者。實際上,我們真的希望有更加尖銳的批判精神來作為把關者。我們相信批判性醫學人文將使人文學科、社會科學的步驟、規范和慣例更加完善,并且使生物科學更加公開地、平等地、有創意地接受人們的審問和改造。這意味著承認其中的偏見,并且挑戰那些局限了我們對健康和疾病的理解的權威言論。因此,一個以人文“觀點”與科學或社會科學的“觀點”競爭為特點的框架,將會讓路于一個更加豐富的和更加復雜的調查研究。這一調查研究能夠探究提高任何有機體的生命和死亡質量的生物-心理-社會-身體事件。
反對角色扮演
我們呼吁醫學人文能夠更加批判性地參與到規范和慣例的制定中去,這樣的批判性已經在醫學和隨后的應用中有了一席之地。我們想要摒棄兩種附加給醫學人文的,并且挑戰其身份和所組成部分的常見敘述。首先,存在著一種服務或實用主義模型可以包容但不會主動挑戰已經存在的權力結構。這一模型宣稱可以通過成為生物醫學科學的“額外的伙伴或支持的朋友”來改善醫患之間的關系。其次,由于醫學人文賦予了生物醫學的客觀性以人性化,因此醫學人文給了大眾一種“被要求在教育和實踐中扮演角色”的感覺。從積極的角度來看,這兩種互補的文化通力合作,共同打造平穩的、最佳的醫學和健康模式。
從消極的角度來看,醫學人文破壞了生物醫學推崇的關于人類經驗的唯物論和科學定義。醫學人文忽略了身體的物質性,因此,正如Bethan Evans 所說:有一些身體相較于其它身體更平等。醫學人文通過主觀證據和頻繁地重新評估那些包含非醫學從業者的分析判斷的臨床場景,探索和拓寬了人類健康、幸福以及疾病的觀點。醫學人文以前的自我描述將自身描述為敵對的、聒噪的、自以為是的存在。對生物醫學來說,它更像是一個“搞破壞的青少年”而不是一名“支持的朋友”。
以上觀點鼓勵醫學人文的傳統性和責任感——為患者服務和反對“生物醫學文化”。我們小心謹慎地遵守這一規矩:醫學人文和生物醫學各自都有強大的盟友和對手,并且逐漸積極地投入到以學科和專門知識為基礎的競爭中。許多醫學人文學者都是能同時處理多個任務的專家:他們尋求跨學科間的合作,臨床內與臨床外的以及類似臨床的領域間的合作,頻繁地進行角色的轉換(從患者到醫生到研究者再到未來的患者)。在這樣的角色轉換中,關于不同方法、認識論、實驗場所的新的實踐方式和新的聯盟應運而生。在我們看來,我們不應該寄希望于“批判”來創造新的正統,而是應該用“批判”來慶祝和發展創新的非正統精神和實踐,它們一直被認為是醫學人文的核心。
這里我們需要提醒自己的是,Stephen Pattison 十年前就提出醫學人文正在被“常規化、排外主義、局限性、專業化以及職業化”所威脅。其中一個醫學人文面臨的嚴峻挑戰是醫學人文似乎把自己封閉在一個看似具有創造性的空間里,它并沒有試圖使其概念合法化(雖然某些團體說它已經合法了)。在此,我們再次強調批判的開放性,多元性和合作性。首先,醫學和健康相關的知識、護理、醫療干預、教育與研究正在通過相關機構、媒體以及政府模式大范圍地影響著這個社會。醫學人文并不是獨立于生命科學的存在。醫學人文的實踐正深刻地與注重物質性和生理性的生物醫學研究交織在一起。以前醫學人文或多或少地被定義為獨立的“演員”,調節著患者、臨床工作者、教育者和學生的關系,卻忽略了醫學、疾病與健康如何不均衡地產生,如何通過臨床和臨床以外的領域滲透到當今社會。其次,作為非主流的和跨學科的實踐(臨床、治療、藝術、教育等),醫學人文堅持從靈活多變與包容性中獲得更多。這樣的包容性來自于沒有必須的或預設的軌跡——特別是當提出創新的研究問題時,做好準備重新審視其規范和操作步驟,并扮演好平衡占優勢的正統角色。
批判性合作與風險
批判性醫學人文贊美實驗、反思實踐、合作以及關于生物醫學的不固執于特定角色的懷疑性風險思維,這些都使對于批判性醫學人文的期盼面臨著挑戰。這些挑戰來自于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它們在“知識經濟”中被多次長期地認為是危機和突發事件。在此,我們想將合作作為醫學人文接近其他領域的重要途徑,尤其是那些受到生物醫學和社會科學的抽象描述的領域。例如,人文科學被要求“能夠提出有代表性的無所畏懼的質疑”,那么我們會思考,醫學人文如何利用這些質疑來使自己改變?換句話說,醫學人文(當它逐漸靠近歷史、哲學、神學、文學研究等領域時)可能被產生于生物醫學和社會科學的生活方式、病理學和健康理念改變嗎?
形式多樣的合作賦予了這一特殊議題以特點。例如,Jan Slaby討論了批判性神經學和批判性醫學人文的關系。作為一名從事跨學科研究的哲學家,他與生命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進行了多年的合作。這一特殊議題吸引了關注點不同的學者。例如,大陸哲學、文化理論、殘障研究、酷兒理論以及科技研究是否是虛無縹緲的或是古怪的存在?(即使他們已經解答了大量關于醫學人文核心的問題)試圖占據醫學人文中心位置的學科分支(這里指醫學教學、醫學的歷史和哲學、文學與醫學、藝術療法)如何揭示醫學人文領域的關注與興趣。
批判中的實驗
每一個對這一特殊議題的貢獻都關注“批判性的”不同方面。Andrew Goffey 調查了知識產生的不同形式、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相對孤立性以及這些對已經滲透到社會、政治和文化領域的免疫學語言的影響。免疫學在生命科學內外的理論化已經滲透進戰爭語言、刑事和移民系統。Jan Slaby 從哲學的角度討論了批判與合作在神經科學中的角色。他的作品的重要性在于他向我們展示了現如今人文學科流行的觀點不一定“反對”或組成物質世界的“外部”, 物質世界是自然科學的傳統興趣。Slaby并不認為人文學科和自然科學的工作在本質上阻礙了不同認識論的發展,他解釋了為什么反對的批判必須存在于合作實驗中。他還認為醫學人文能夠從“批判性神經科學”中學到很多,醫學人文試圖理解正在出現的科技科學規范性——商業的、法律的、科技的、概念的以及認識論的趨勢。
最近醫學人文領域的研究強調了經驗的體驗性。我們小心地處理科學方法中的問詢,并延伸體驗的概念去適應人們的身體可以被分割成商業部分并且在全世界走私的這一現狀。組織、器官、細胞、DNA,這些都可以被提取,被改造,被分級、從體內取出、重新放入體內。Bronwyn Parry關于器官捐助者和代孕的討論反映了肉體的分離和商業化。她的文章強烈抨擊了新自由經濟,因為新自由經濟認為協調商業炒作的新類型可以冒著忽視地方文化、物質實際以及打擊臨床從業者積極性的風險。為了展示臨床勞動力的不同分類,Parry比較了加利福利亞的精子捐獻者和孟買的卵子捐獻者的生活條件。他們在安全水平、經濟狀況以及動機方面都存在著很大差異,但是這些差異被很多研究忽視了。
Parry的觀點為醫學人文上了重要的一課。批判或反對新興的臨床實踐,特別是當這種臨床實踐在全球范圍內的分布并不均衡,并不具有說服力時。她強調當地的體驗和體制風格以及現代經濟如何孕育與舊的社會實踐、不均衡發展以及社會不平等相一致的新興醫學實踐。她重視醫學實踐和資本主義企業(例如臨床捐獻者和代孕者相關的企業)如何在當地得到發展。
總結
醫學人文事業一直以細致入微的思考方式,通過形式各異的創新合作方式、以及多樣的問詢方式分析健康、疾病與醫療護理。這些健康、疾病與醫療護理處于不同地區、規模、歷史時期和文化背景之下。面對批判性合作者的多重角色,我們建議豐富和發展醫學人文領域的核心競爭力,即創新的非正統精神和實踐,開展跨學科間的合作,以促進批判性醫學人文在社會中的發展。
/李怡然:北京中醫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