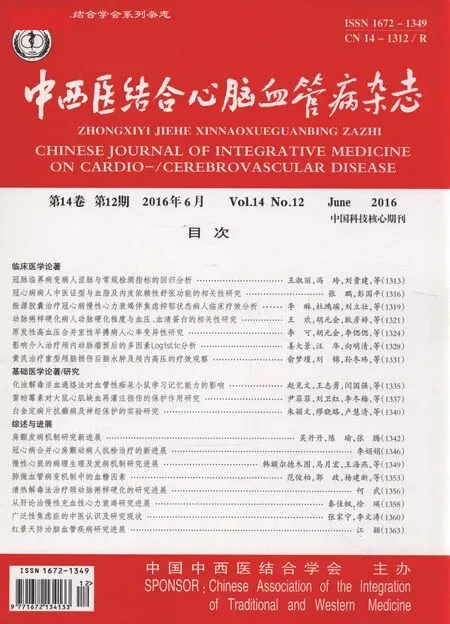慢性心衰的病理生理及發病機制研究進展
韓額爾德木圖 ,馬月宏,王海燕,孟永梅
?
慢性心衰的病理生理及發病機制研究進展
韓額爾德木圖1,馬月宏2,王海燕2,孟永梅2
1.內蒙古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呼和浩特 010050);2.內蒙古醫科大學
摘要:心力衰竭(心衰),是各種心臟結構或功能性疾病導致心室充盈及(或)射血能力受損而引起的一組綜合征。心衰是各種心臟病的嚴重階段,其發病率高,正成為21世紀最為重要的心血管病癥。針對上述問題,本研究就心衰的病理生理及發病機制的研究進展綜述如下。
關鍵詞:心衰;病理生理;發病機制
心衰是各種心臟病的嚴重階段,其發病率高,5年存活率與惡性腫瘤相仿,近年來心衰的發病率仍持續增長,正成為21世紀最為重要的心血管病癥。慢性心力衰竭(chronic hear failure,CHF)有一個緩慢的發展過程,一般均有代償性心臟擴大或肥厚,是大多數心臟病的最終歸宿,也是最主要的死亡原因。根據我國2003年的抽樣統計,成人心衰患病率為0.9%,根據美國心臟病學會(AHA)2005年的統計報告顯示,全美約有500萬心衰病人,心衰的年增長數為55萬[1]。CHF常由器質性心血管疾病引起,如冠心病、瓣膜性心臟病、高血壓病、肺心病和內分泌疾患等。正確認識CHF,合理的治療CHF,提高病人生活質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近年來,隨著基礎醫學研究的不斷深入研究,循證醫學對心衰的診治提供了充足的實證,心衰的發病發展機制和概念都有了較大的改變和更新。
醫學對心衰的認識經歷了從器官到細胞再到基因的發展過程,其病理生理改變也十分復雜,對其認識也將不斷的深入,20 世紀40 年代主要是體液潴留機制,20 世紀60年代則是泵功能障礙機制,20 世紀80 年代開始重視神經內分泌細胞因子系統的過度激活,直至現在為止認識到心肌重構是心衰發生發展的重要機制。目前認為血流動力學異常是心衰癥狀的病理生理基礎,或者說是心衰的結果;而神經內分泌細胞因子系統的過度激活等導致的心室重塑則是心衰發生發展的病理生理學基礎。心室重塑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涉及到一系列的分子和細胞機制,比如心肌細胞的凋亡、心肌細胞的肥厚、心肌細胞外基質的沉積、基因表達異常及多種基因之間的相互作用等等,從而導致心肌結構、表型、功能的變化,表現為心肌質量、心室容量及心室形狀的改變。其次,心肌梗死、炎癥、過高的壓力或容量負荷增加了心室壁的機械負荷,激活了一系列神經內分泌信號,加重心衰的進程。神經內分泌細胞因子系統的長期、慢性激活促進心室重塑,加重心肌損傷和心功能惡化,后者又激活神經內分泌因子系統,形成一種惡性循環[2]。本研究從心衰的病理生理及發病機制的研究進展簡要綜述如下。
1代償機制
1.1Frank-Starling機制增加心臟的前負荷,使回心血量增多,提高心臟血流量。同時心室舒張末期容積增加,相應地心房壓、靜脈壓也升高;待后者達到一定程度時出現肺或腔靜脈系統的充血。
1.2心肌肥厚心肌纖維增多,細胞數并不增多。
1.3神經體液的代償機制交感神經系統(SNS)興奮性增強,心衰時低心排血量興奮壓力感受器,反射性激活交感神經。此類早期交感神經系統激活,使心率增快,心肌收縮力增強,心排血量增多,使衰竭的心肌得到血流動力學的代償。但SNS 長期、過度的激活,可導致心肌肥厚、細胞凋亡及間質纖維化;腎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系統(RAAS)激活,RAAS激活較SNS 慢。其主要活性物質為血管緊張素Ⅱ(AngⅡ),AngⅡ可引起心室后負荷增加,致使心肌細胞肥厚、細胞凋亡以及間質纖維化和血管、心室的重構;而且RAAS 與SNS也密切相關,交感神經激活可增加腎素的釋放,而AngⅡ作用于交感神經,正反饋促進去甲腎上腺素(NE)的分泌,同時還可以促進腎上腺素、醛固酮及血管加壓素的釋放。高醛固酮血癥可致自主神經功能失調,交感激活、副交感活性降低,特別是在心肌細胞外基質重構中起重要作用。AngⅡ 促使心肌交感神經末梢釋放NE,并促進心室肥厚及血管平滑肌生長,最終
導致進行性的心室功能障礙[3]。
2體液因子(激素、神經遞質和神經肽、細胞因子、局部化學介質)的改變
2.1利鈉肽利鈉肽包括心鈉素(ANP)、腦鈉素(BNP)、C 利鈉肽(CNP)。ANP 擴張血管,增加排鈉,對抗腎上腺素和腎素-血管緊張素等的水鈉潴留;BNP 可以用來判別心源性呼吸困難與肺源性呼吸困難。另研究顯示血漿BNP 濃度與心衰病人心源性死亡密切相關,對心源性死亡的預測有非常重要的臨床價值[4]。血漿ANP 及BNP 水平升高,其增高的程度與心衰的程度呈正相關,因此血漿ANP 及BNP 水平可作為評定心衰的進程和判斷預后的指標。
2.2精氨酸加壓素(arginine vasopressin,AVP)精氨酸加壓素合成于下丘腦,儲存于垂體,具有抗利尿和縮血管功能,因此又稱抗利尿激素(ADH)和血管升壓素。AVP 的釋放過量可引起全身血管的收縮、水液潴留、稀釋性低血鈉而加重心衰。研究發現,AVP 拮抗劑能減輕心衰病人的臨床癥狀,但是結果顯示不能影響病人的壽命[5];急慢性心衰病人的血漿AVP 濃度升高與病人預后不利有一定的相關性[6]。因此,AVP 拮抗劑是否可作為心衰靶治療的手段尚無定論,有待于進一步研究。
2.3內皮源性激素內皮素(endothelin,ET)是1988 年由豬主動脈內皮細胞上清液中分離出來的,它是由一族血管內皮細胞、心肌、平滑肌等合成及分泌的含21 個氨基酸的多肽,是迄今為止所知人體內最強的血管收縮肽。該家族有ET-1、ET-2 及ET-3 三種同源異構體,它們分別位于第6、1 和20 號染色體上,其中ET-1 既有強烈而持久的收縮血管作用,又有促進細胞生長和有絲分裂特性,是引起多種疾病的炎癥因子[7],還包括血管活性腸收縮肽。內皮素可導致細胞肥大增生,參與心臟的重塑過程。內皮素不僅能使冠狀動脈強烈收縮痙攣,冠狀動脈血流減少,而且還能增加心肌耗氧量,因此產生急性心臟損傷的作用。心衰病人由于心室充盈壓升高和肺動脈壓升高,促使ET 分泌及釋放,研究已證實,心衰病人ET 濃度顯著增高[8-9]。直至目前為止,ET 可以加重心臟負荷、降低心輸出量,誘發心肌缺血或心律失常,對心肌有直接的毒性作用;促使心肌細胞肥厚、心室重構。此外,兒茶酚胺(CA)、前列環素(PGs)、神經肽(YNPY)、血管內皮舒張因子(NO)、激肽(BK)、降鈣素基因相關肽(CGRP)、腎上腺髓質素(ADM)等多種內分泌激素也參與了心衰的病理進程。
2.4細胞因子(cytokine,CK)細胞因子的激活與心衰發生發展也有著密切關系,即心衰很可能與炎癥的發生發展相關,如細胞炎性因子的產生及增多、刺激造血系統功能、細胞與組織的代謝失調有關。炎性細胞因子通過各種途徑,參與心衰的病理過程。目前通常把細胞因子分為六大類:腫瘤壞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白細胞介素(interleukin,IL)、干擾素(interferon,IFN)、集落刺激因子(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CSF)、生長因子、趨化因子家族(chemokinefamily)。目前研究比較多的是TNF-α,有學者認為,心衰時心臟有大量TNF-α的信使核糖核酸(mRNA)表達和蛋白合成;心衰病人血漿中TNF-α水平增高的幅度與心衰的程度具有明顯正相關且與NYHA 心功能分級相一致,由此說明TNF-α是反映心衰嚴重程度的一個很重要的指標;血漿中TNF-α水平增高是心衰病人死亡的獨立預測因子。研究還發現,IL-1β具有單獨調節心肌功能的作用,顯示其負性變力效應;實驗研究提示,IL-1β也是促進心肌重構的重要因素;心衰病人IL-6 水平與心功能分級呈正相關,與LVEF 呈負相關,IL-6 與心衰的預后相關,是一個獨立的預測預后指標;在心衰早期,TNF-α尚屬正常,但IL-6 水平已有升高,說明IL-6 可能更早反映心衰的一個敏感性指標[10]。脂肪組織是不僅儲存能量的場所,而且是一個很大的內分泌器官,能分泌多種脂肪因子,其中瘦素(Leptin,LP)、脂聯素(APN)研究為數最多。血漿Leptin 濃度與心肌肥厚程度呈明顯正相關[11];動物實驗表明Leptin 有增加交感神經活性和升高血壓,增加心率的作用[12-13],這些研究結果提示Leptin 可能是心肌肥厚新的致病因素。另有研究認為生理水平的瘦素可引起血管舒張,對心臟功能無明顯影響,而病理情況下可促進大量氧化自由基的產生,進而產生明顯的負性肌力作用。APN 在CHF 的作用還不清楚,劉素云等[14]研究發現APN 與心衰嚴重程度相關。另有研究提示血清APN 的水平與NYHA 心功能分級呈正相關,并且對數轉換的APN 水平與BNP 的水平呈正相關,表明APN 與CHF 嚴重程度有關,可以作為預測心衰變化趨勢的指標,推測這是CHF 的病理生理過程中神經內分泌因子被激活,APN 是被激活的激素之一[15]。但也有學者總結到APN 作為所有脂肪因子中的唯一負性調節激素在心臟疾病的形成等生理及病理過程中發揮重要的調節作用[16]。
3舒張功能不全
最近有報告指出,40%~50%的心衰是由舒張功能不全引起,與收縮功能不全相比,舒張功能不全以女性居多,平均年齡較大。導致舒張功能不全的基礎心臟病以高血壓最多,且多以合并房顫、貧血為特征[17]。另外,老齡化所帶來的心血管生理性的變化也是一個重要的危險因素。另有一組對射血分數正常的心衰(HF-nlEF)病人進行對照研究后指出[18],HF-nlEF 存在著無法單獨用年齡與高血壓等因素來解釋的收縮性心室和動脈僵硬,動脈和心室僵硬的不良耦聯促使左心室舒張末壓增高,壓力-容量曲線偏向右移,加重了收縮壓對舒張功能的影響,從而使血壓更不穩定,應激時心臟耗氧量增加而加重舒張功能障礙。除此之外,影響舒張功能的因素有,心肌細胞骨架蛋白(微管、中間肌絲、微肌絲和胞漿內蛋白)異常、細胞外基質(膠原纖維、基底膜蛋白、蛋白多糖)變化、心肌外因素(血流動力學負荷、舒張早期前后負荷、心包結構的改變)等因素影響心臟的舒張、心室的充盈及血液的排出,導致舒張終末期左心室內壓升高,引起心衰等[19]。總之心臟舒張功能不全的作用機制,大體上可分為兩大類:一種是主動舒張功能障礙,另一種是心室肌的順應性減退及充盈障礙,以下一一簡單敘述。
3.1主動舒張功能障礙主動舒張功能障礙多因Ca2+不能及時地被肌漿網攝取及泵出胞外,而這兩種過程均為耗能的主動過程,故凡是能影響到心肌能量生成的因素,必將影響到心肌主動舒張過程。除心肌能量缺乏會影響到Ca2+內儲、外運以外,肥厚心肌中肌質網鈣泵mRNA 表達和蛋白水平降低,鈣泵調節蛋白受磷蛋白mRNA 表達和蛋白水平降低,都是影響肥厚心肌主動舒張的因素。氧自由基和某些炎癥因子造成心肌細胞膜損傷,導致鈣超負荷,會加重Ca2+轉運量,成為影響此時心肌舒張功能的另一因素[20]。
3.2心室肌的順應性減退及充盈障礙心室的順應性是指心室在單位壓力變化下所引起的容積改變,心室肌的順應性是心室肌的順隨應力,長度改變的特性。心肌舒張后期,隨著回心血量的增加心肌被動拉長,為心肌被動充盈期,相當于心動周期中的緩慢充盈期和心房收縮充盈期。影響心肌被動充盈的因素,主要是心肌順應性。心肌肥厚中心肌間質增生的速度遠超過于心肌細胞肥大的程度,隨病情的加重,肥厚心肌發生進行性的纖維化或心肌炎等心肌細胞壞死導致心肌間質成分增多,以及含鐵血黃素沉積和心肌淀粉樣病變引起心肌不同程度纖維化等均影響心室肌順應性。除此之外,縮窄性心包炎、心包填塞時,心臟舒張受限,同樣可導致心室順應性降低,故而妨礙了心室的充盈。
4心肌損害與心室重塑
心室重塑是心衰發生發展的基本機制,長期血流動力學的改變如壓力和容量負荷過重,通過增加心肌室壁張力、促進細胞因子、信號肽釋放,神經內分泌信號機制或氧化應激反應導致心室重塑。臨床上表現為心室腔擴大、室壁肥厚和心室腔幾何形態的改變,心肌肥厚在初期可起到一定的代償作用。但是由于肥厚心肌處于能量饑餓狀態,心肌缺血,心肌細胞凋亡,左室進行性擴大伴功能減退,最后發展至不可逆性心肌損害的終末階段。許多過程均參與了心室重塑,它包括病理性心肌細胞肥大伴胚胎基因再表達、心肌細胞肥大凋亡與壞死,成纖維細胞的增生,心肌細胞外基質過度沉積或降解增加等,均能引起、加強或中止心室重塑的過程。在心衰過程中,尤其神經內分泌的過度激活,心臟功能與心肌細胞的生物學改變,可致心肌細胞的肥厚及心肌細胞的凋亡,從而加重心室重塑。
4.1心肌細胞肥厚心肌細胞肥厚與超負荷的心臟異常相關。心臟肥大的本質是心肌細胞的肥大,即心肌細胞表型變化,體積變大,同時也有心肌間質細胞的增殖。心臟肥大常發生于心臟負荷上升時,包括后負荷上升(如高血壓、血管狹窄)和前負荷上升(如瓣膜關閉不全)。前負荷上升引起心臟肥大以心腔擴大為主,心室壁肥厚有限(離心性肥厚);后負荷上升所引起的以心室壁肥厚為主,心腔不擴大(向心性肥大),早期,心室肥大屬于生理反應,晚期則成為心臟猝死和其他心血管事件的獨立危險因子[21]。由于心肌細胞不能再生,因此心肌肥厚和擴張并不是心肌細胞數量的增加,而是心肌細胞肌節增多及重組的結果,心肌細胞延長則與新生肌節相互連接有關[22]。另外,心肌細胞肥厚,也有部分由于神經內分泌的過度激活相關。
4.2心肌細胞死亡心肌細胞死亡包括心肌細胞壞死和凋亡兩個方面。心肌細胞凋亡與心衰發生、發展有著尤為重要的聯系。有學者認為,心衰與凋亡導致心肌細胞不可逆的丟失有關聯,心肌細胞凋亡的特點是維持在非常低水平并持續數周至數年,即使是低水平的丟失,也能引起心臟的功能失調[23]。終末期心衰病人心肌細胞的凋亡增加,擴張型心肌病中心肌細胞凋亡是終末期心衰的持續特征,且與疾病的嚴重性相關。因此,細胞凋亡和左心室重構程度有密切關系[24]。
4.3心肌細胞外基質(ECM)心衰時,ECM 的變化主要是膠原沉積和纖維化。有一項研究報告提示[25],心肌膠原纖維含量增加2~3倍時,可改變心室的充盈性,從而舒張期的室壁僵硬度增加,則促發舒張性心衰;若心肌膠原纖維含量增加4倍或以上,則促發收縮性心衰。心肌間質纖維化使心肌電傳導的各向導性增加,使沖動傳導不均,不連續,誘發心律失常和猝死。
此外,氧化應激在心室重塑過程中也起很重要的作用,主要是反應性活性氧的增加,如心肌細胞牽拉、炎性細胞因子的作用、兒茶酚胺自身氧化、反復發作的心肌缺血及再灌注等使心肌細胞損傷;其次抗氧化系統的缺陷,氧自由基亦可通過損傷心肌,促進心肌鈣轉運異常,誘導心肌細胞凋亡等途徑導致心肌舒縮功能降低,加速了心衰進展。
5結語
心衰是大多數心血管疾病的最終歸宿,也是最主要的死亡原因。心肌炎癥、心肌梗死、血流動力學負荷過重是心衰的始動因素。心功能下降導致血流動力學障礙,誘發神經內分泌激活、細胞因子釋放為其續動因素。打破這種神經內分泌激活和心室重塑的惡性循環,則是治療CHF 的關鍵。現代醫學為改善心衰病人癥狀和降低病死率等起到了積極作用,但還有一些問題制約著其發展,如心衰病人再次住院率高,病人生活質量差,醫療費用高,因此尋求臨床療效確切、改善復發、安全毒副反應小的治療方法和藥物一直為各國研究者所廣泛關注。今后可否借助蛋白質組學等新技術進行新型高效藥物分析和篩選,同時在臨床實踐中嚴格遵循循證醫學的原則進行合理的應用藥物。相信隨著新型藥物的不斷開發與大規模臨床研究,心衰的治療必將迎來嶄新的歷程。
參考文獻:
[1]陸再英,鐘南山.內科學 [M].第7版.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8:170.
[2]陳良華,劉同寶.心力衰竭的病理生理機制及治療模式[J].山東醫藥,2005,45(13):67-68.
[3]宮玉霞.慢性心力衰竭機制的研究進展[J].吉林醫學,2007,28(5):717-719.
[4]Berger R,Huelsm an M,Strecker K,et al.B-type natriuretic peptide predicts sudden death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J].Circulation,2002,105(20):2392-2397.
[5]Konstam MA,Gheorghiade M,Burnett JC,et al.Effects of oral tolvaptan in patients hospitalized for worsening heart failure the EVEREST Outcome Trial [J].JAMA,2007,297:1319-1331.
[6]Schrier RW.Water and sodium retention in edematous disorders role of vaso- pressin and aldosterone[J].Am J Med,2006,119(suppl):S47-S53.
[7]倪國華.內皮素系統與心力衰竭[J].心血管病學進展,2007,28(2):280-282.
[8]Hunt SA,Abraham WT,ChinMH,et al.ACC/AHA 2005 guideline update for the di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chronic heart in the adult-summary article[J].Circulation,2005,112(9):1825-1852.
[9]Moe GW.B-type natriuretic peptide in heart failure[J].Curr Opin Cardiol,2006,21(3):208-214.
[10]閆晉康,張志平,王蘇芳.心力衰竭與腫瘤壞死因子、白細胞介素相關性的研究進展[J].中西醫結合心腦血管病雜志,2009,8(7):946-947.
[11]Singhal A,Farooqi IS,Cole TJ,et al.Influence of leptin on arterial distensibility:a novel link between obesity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J].Circulation,2002,106:1919-1924.
[12]Bouloumie A,Marumo T,Lafontan M,et al.Leptin induces oxidative stress in human endothelial cells[J].FASEB J,1999,13:1231-1238.
[13]Yamagishi SI,Edelstein D,Du XL,et al.Leptin induces mitochondrial superoxide production and monocyte chemoatractant protein-1 expression in aortic endothelialcells by increasing fatty acid oxidation via protein kinase A[J].J Biol Chem,2001,276:25096-25100.
[14]劉素云,張麗楓,張瑞寧,等.脂聯素在充血性心力衰竭中的變化及意義[J].河北醫藥,2010,32(12):1590-1591.
[15]姜紅峰,彭少蓉,繆希莉,等.老年慢性心力衰竭病人血清脂聯素與嚴重程度的關系[J].中國老年學雜志,2008,3(28):494-497.
[16]鄒云龍,田國忠,李艷君,等.脂聯素研究進展[J].黑龍江醫藥科學,2008,31(5):64-65.
[17]磯部光章,等.心力衰竭[J].日本醫學介紹,2007,28(8):342-345.
[18] Kawaguchi M,Hay I,Fetics B,et al.Combined ventricular systolic and arterial stiffening in patients with heart failure andpreserved ejection fraction:implications for systolic and diastolic reserve limitations[J].Circulation,2003,107(5):715-719.
[19]王志軍,孫寧玲,柯元南.舒張性心力衰竭的研究進展[J].中日友好醫院學報,2006,20(5):302-304.
[20]孫衛東,尹魯驊,王伯松.心力衰竭診療進展及循證醫學[M].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2007:38-41.
[21]祝善俊,徐成斌.心力衰竭基礎與臨床[M].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2001:24.
[22]Baig MK,Makon N,Makenna WJ,et al.The pathophysiology of advanced heart failure[J].Am Heart J,1998,135:216.
[23]馮慧遠.心力衰竭的機制及臨床診治研究進展[J].中國醫學裝備,2010,7(9):47-49.
[24]鄧元江,梁偉雄,劉衛英,等.生脈膠囊對慢性心力衰竭大鼠心肌細胞凋亡的影響[J].中國中醫藥信息雜志,2009,16(4):27-29.
[25]Weber KJ,Sun Y,Campbell SE.Structural reccodeling of the heart by fibcous tissuet role of elrculating honmones and locally produced peptides[J].Eur Heart J,1995,16(supp1):12.
(本文編輯王雅潔)
基金資助:國家自然基金項目(No.81260596);內蒙古自治區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項目(No.201301053)
通訊作者:孟永梅,E-mail:mym930@126.com
中圖分類號:R541.6R256.2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1349.2016.12.013
文章編號:1672-1349(2016)12-1349-04
(收稿日期:2015-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