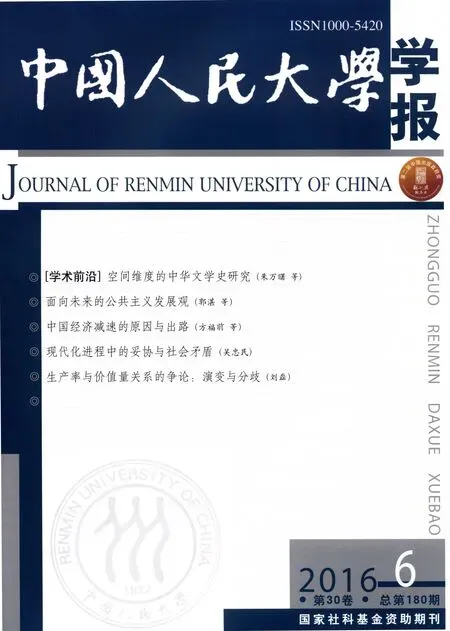小玲瓏山館:一個“有意味”的文學(xué)空間
朱萬曙
?
小玲瓏山館:一個“有意味”的文學(xué)空間
朱萬曙
清代揚州馬曰琯、馬曰璐兄弟的小玲瓏山館是一個典型的文學(xué)空間,其空間包括了看山樓、叢書樓等在內(nèi)的私家園林。作為公共的文學(xué)空間,這里經(jīng)常舉行雅集活動,這些活動具有集群性、高雅性、平民性等特點。作為私人空間,主人馬曰琯的“獨坐”其間,將其生命體驗轉(zhuǎn)換為文學(xué)書寫。這個空間的文學(xué)集群之間有著深厚的情感交流,體現(xiàn)出生命的體溫。通過對這一文學(xué)空間的挖掘,可以發(fā)現(xiàn)蘊含其中的各種文學(xué)史的“意味”。
小玲瓏山館;文學(xué)空間;“意味”
本文所使用的“文學(xué)空間”概念,不是指作品虛構(gòu)的空間,而是指文學(xué)史上曾經(jīng)存在的空間。如果我們還原文學(xué)史的原貌,它其實是由無數(shù)個大大小小的“空間”構(gòu)成的。大而一個自然地域或一個行政區(qū)域,如塞北、如草原、如高原、如“江南”和“江南省”;小而一個斗室書齋、一個園林、一方山水勝境,如李攀龍之“白雪樓”、如蔣士銓之“紅雪樓”、如影園、如蘭亭、如西湖。這些空間與文學(xué)家的生存和活動密切關(guān)聯(lián),物理空間與他們的生命、情感融為一體,躍動著文學(xué)家的心跳,可以觸摸到他們的體溫。注重從空間的視角研究文學(xué)史,無疑可以讓文學(xué)史變得極其豐富而具有生命的質(zhì)感。
清代雍正、乾隆間揚州馬曰琯、馬曰璐兄弟的小玲瓏山館算得上是一個典型的文學(xué)空間。它的主人雖然是鹽商,卻“賈而好儒”,不僅有詩詞創(chuàng)作,而且是清代屈指可數(shù)的幾位大藏書家之一。特別是他們營建的私家園林“小玲瓏山館”,是諸多文人經(jīng)常雅集乃至長期館住的所在。這里不僅是馬氏兄弟文思醞釀的空間,更是一批和他們交好的文友們流連駐足、研讀典籍、詩賦翰墨的空間。復(fù)原和探究這一文學(xué)空間曾經(jīng)發(fā)生的各種場景,既可以獲得文學(xué)史的生命趣味,也可以看出文學(xué)空間研究的多重“意味”。
一、小玲瓏山館之空間布局
小玲瓏山館是清代揚州鹽商馬曰琯、馬曰璐兄弟營建的私家園林。兄,馬曰琯,字秋玉,號嶰谷、沙河逸老。弟,馬曰璐,字佩兮,號半查、半槎、南齋。他們互為師友,研習(xí)經(jīng)史文集,旁逮金石字畫,俱以詩名。他們又富于藏書,禮遇寒士,慷慨于公益事業(yè),多善舉義行。因此,頗得時名,被稱做“揚州二馬”*李斗《揚州畫舫錄》卷4曰:“馬主政曰琯字秋玉,號嶰谷……弟曰璐,字佩兮,號半查……與兄齊名,稱‘揚州二馬’”。 參見李斗:《揚州畫舫錄》卷4,88頁,北京,中華書局,1969。。
作為私家園林,小玲瓏山館大約建于雍正年間*關(guān)于小玲瓏山館營建時間可參考方盛良的考證,參見方盛良:《清代揚州徽商與東南地區(qū)文學(xué)藝術(shù)研究》,38頁,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8。。李斗的《揚州畫舫錄》卷四記載道:馬氏居住在揚州“新城東關(guān)街”,他們“于所居對門筑別墅曰街南書屋,又曰小玲瓏山館,有看山樓、紅藥階、透風(fēng)透月兩明軒、七峰草堂、清響閣、藤花書屋、叢書樓、覓句廊、澆藥井、梅寮諸勝”[1](P88)。這個園林的面貌今天已不可知,但清代畫家張庚所繪寫的《小玲瓏山館圖》卻流傳至今,據(jù)丘良任《“揚州二馬”及〈小玲瓏山館圖記〉》一文介紹,他從老友姚藹士先生處得見此圖,“畫心長約九十公分,高二十余公分。圖中一太湖巨石矗立,玲瓏剔透,山館命名以此。遠(yuǎn)處有樓二,修篁千干,掩映左右。高木蘢嵸,桐檜之屬。閣一,庵一,亭一,雜花生樹,垂柳迎風(fēng)。繞以長廊,蕉葉正肥”。圖后還有署名馬曰璐書寫的《小玲瓏山館圖記》,復(fù)有包世臣、汪鋆的題跋。馬曰璐的“圖記”不見于他書,茲將丘良任文所錄轉(zhuǎn)引如下:
中有樓二:一為看山遠(yuǎn)矚之資,登之則對江諸山,約略可數(shù);一為藏書涉獵之所,登之則歷代叢書,勘校自娛。有軒二:一曰透風(fēng)披襟,納涼處也;一曰透月把酒,顧影處也。一為紅藥階,種芍藥一畦,附之以澆藥井,資灌溉也。一為梅寮,具朱綠數(shù)種,媵之以石屋,表潔清也。閣一,曰清響,周栽修竹以承清露。庵一,曰藤花,中有老藤如怪虬。有草亭一,旁列峰石七,各擅其奇,故名之曰七峰草亭。其四隅相通處,繞之以長廊,暇時小步其間,搜索詩腸,從事吟詠者也,因顏之曰覓句廊。將落成時,余方擬榜其門為街南書屋,適得太湖巨石,其秀美與真州之美人石相埒,其奇奧偕海陵之皺云石爭雄。雖非媧皇煉補之遺,當(dāng)亦宣和花綱之品。米老見之,當(dāng)拜其下;巢民得之,必匿其廬。余不惜資財,不憚工力,運之而至。甫謀位置其中,藉他山之助,遂定其名小玲瓏山館。適彌伽居士張君過此,挽留繪圖。只以石身較岑樓尤高,比鄰惑風(fēng)水之說,頗欲尼之。余兄弟卜鄰于此,殊不欲以游目之奇峰,致德鄰之缺望。故館既因石得名,圖已繪石之矗立,而石猶堰臥,以待將來。[2]
如果說李斗的《揚州畫舫錄》只是記載了小玲瓏山館中十個建筑景點的名稱,那么這篇“圖記”則很詳細(xì)地介紹了小玲瓏山館各個建筑景點的布局、功用以及景色。例如:看山樓是為了“遠(yuǎn)矚之資”,登樓可見對面諸山;李斗所記“透風(fēng)透月兩明軒”實為兩軒,一為“透風(fēng)軒”,其功用是“納涼”,一為“透月軒”,其功用則為“顧影”賞月。“七峰草堂”乃是因為在草亭周圍放置了七尊峰石,且它們的行狀“各擅其奇”,故而得名。不僅如此,“圖記”還交代了“小玲瓏山館”之名的由來:就在園林即將落成、準(zhǔn)備擬名為“街南書屋”之際,馬氏兄弟得到了一塊太湖巨石,其秀美、奇奧都足以和當(dāng)時的名石“美人石”、“皺云石”相比。他們本想將石矗立于園內(nèi),但有礙于鄰居惑于風(fēng)水之說,沒有這樣做,不過還是將園林命名為“小玲瓏山館”。
園林建成之后,馬氏兄弟對其中的建筑景點賦詩吟詠。馬曰璐《街南書屋十二詠》:
小玲瓏山館:愛此一拳石,置之在庭角。如見天地初,游心到廬霍。
看山樓:隱隱江南山,遙隔幾重樹。山云知我閑,時來入窗戶。
紅藥階:孤花開春余,韶光亦暫勒。寧藉青油幕,徒夸好顏色。
覓句廊:詩情渺何許,有句在空際。寂寂無人聲,林蔭正搖曳。
石屋:嵌空藏陰崖,不知有三伏。蒼松吟天風(fēng),靜聽疑飛瀑。
透風(fēng)透月兩明軒:好風(fēng)來無時,明月亦東上。延玩夜將闌,披襟坐閑敞。
藤花庵:何來紫絲障,侵曉煙濛濛。忘言獨立久,人在吹香中。
澆藥井:井華清且甘,靈苗待灑沃。連筒及春葩,亦溉不材木。
梅寮:瘦梅具高格,況與竹掩映。孤興入寒香,人間總清境。
七峰草亭:七峰七丈人,離立在竹外。有時入我夢,一一曳仙佩。
叢書樓:卷帙不厭多,所重先皇墳。惜哉飽白蟫,撫弄長欣欣。
清響閣:林間鳥不鳴,何處發(fā)清響。攜琴石上彈,悠然動遐想。[3]
應(yīng)該說,這些詩作,書寫了園中各個景點的景致和怡人的感受。例如《看山樓》一詩所寫“隱隱江南山,遙隔幾重樹”,與馬曰璐“圖記”中“登之則對江諸山,約略可數(shù)”所見之景,互相印證。而“山云知我閑,時來入窗戶”兩句,又借景寫心中閑情,可謂景為心生。除馬氏兄弟之外,他們的文友也賦詩吟詠園中景點。經(jīng)常來往于園中的詞人厲鶚,賦有《題秋玉佩兮街南書屋十二首》[4](P419-428);陳章有《街南書屋十二詠為馬獬谷半槎昆季賦》[5];同居揚州的程夢星亦有《街南書屋雜題十二首》[6]。
園中諸景中,文人喜愛的當(dāng)是叢書樓。全祖望、厲鶚等人經(jīng)常讀書其中,厲鶚還在此完成了《宋詩紀(jì)事》。全祖望撰寫了《叢書樓記》,稱道:“揚州自古以來所稱聲色歌吹之區(qū),其人不肯親書卷,而近日尤甚。吾友馬氏獬谷、半查兄弟橫厲其間,其居之南,有小玲瓏山館,園亭明瑟,而巍然高出者,叢書樓也,迸疊十萬余卷。”[7](P1065)從全祖望“巍然高出”的記敘看,叢書樓的高度超過其他建筑。全祖望還寫到馬曰琯對藏書的癡迷:“而獬谷相見,寒暄之外,必問近來得未見之書幾何,其有聞而未得者幾何,隨余所答,輒記其目,或借鈔,或轉(zhuǎn)購,窮年兀兀,不以為疲。”叢書樓不僅在小玲瓏山館中“巍然高出”,更因為馬曰琯“不以為疲”的搜集,藏書極為豐富。與馬氏兄弟交好的文人杭世駿應(yīng)馬曰琯之請,寫了一篇《七峰草亭記》,文章一開始實寫其景:“街南別墅中,修竹盈畝,有石若筍者七,高秀聳擢,掀土而刺天。”然后寫具體的觀感:“今試據(jù)斯亭而望,俯者如笏,植者如竿,削者如珪,聯(lián)者如璧。開戶而揖,若毅夫介士,肅手而卻立;啟窗而窺,若高人羽士,拔俗而寡偕。有刻勵之行,有勁正之節(jié),有廉傑儁岸、孤高介特之風(fēng)范。”[8]把七尊石頭充分?jǐn)M人化,暗示馬氏兄弟之“庸以比德”之心。
二、雅集:作為公共空間的小玲瓏山館
全祖望在《叢書樓記》中,還記載了這樣一個場面:“其得異書,則必出以示余。席上滿斟碧山朱氏銀槎,侑以佳果,得余論定一語,即浮白相向。”在小玲瓏山館中,馬曰琯與朋友全祖望品鑒“異書”,用元代朱碧山所制的銀槎杯斟滿酒,得到滿意的結(jié)論,兩人就喝上一杯酒。山館中這樣的場面既散發(fā)著書香氣,也顯示出文人的風(fēng)雅味。山館也由個人的私家園林,變成了文友們討論學(xué)問乃至舉行文學(xué)活動的公共空間。
小玲瓏山館建成之后,立即就成為馬氏兄弟和文友們經(jīng)常聚會的所在。《揚州畫舫錄》記載道:“揚州詩文之會,以馬氏小玲瓏山館、程氏蓧園及鄭氏休園為最盛。至?xí)冢趫@中各設(shè)一案,上置筆二,墨一,端硯一,水注一,箋紙四,詩韻一,茶壺一,碗一,果盒、茶食盒各一,詩成即發(fā)刻,三日內(nèi)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9](P180)李斗說了三個詩文之會“最盛”的揚州園林,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馬氏小玲瓏山館”。這樣的聚會,不同于尋常人家或者是富豪之家以吃喝為主的聚會,而是“詩文之會”,是自古以來文人們所喜愛的“雅集”。
可以列舉一些山館中舉行的“雅集”活動。乾隆八年(1743年)十月,從金陵移古梅植于館內(nèi)。梅花是高潔的象征,向來為文人所喜愛,厲鶚、全祖望等10多位文人都有詩吟詠唱和,厲鶚《金陵移梅歌為獬谷半查賦》吟道:“預(yù)想他時雪滿眼,仿佛此際香橫苔。不須健步煩杜老,芳心更用狂吟催。”[10](P1225)全祖望則賦《七峰草堂移梅歌》,其中有句:“寂寥小雪霜葉凋,崢嶸幾點春芽勁。新寒未消九九期,微風(fēng)已動番番勝。”[11](P2092)乾隆十二年(1747年)五月十五日,馬氏兄弟邀集文友們?yōu)椤爸匚逯畷保瑓桖樧挠涊d道:“歲丁卯五月十五日,馬君半槎招同人展重五之會于小玲瓏山館。維時梅候未除,綠陰滿庭,偏懸舊人鐘馗畫于壁……遂人占一畫,各就畫中物色,賦七言古詩一篇。”[12](P1724)在這次活動中,馬氏作《展重五集小玲瓏山館分賦鐘馗畫得踏雪圖》:“黑云垂華天漠漠,滕六翻空七蕭索。巖壑慘澹森寒光,九首山人鬚戟張……我張此圖五月中,但愛幽澗鳴迥風(fēng)。畫師有意與無意,道眼看來等游戲。一庭冰雪凈吾胸,子虛烏有亡是公。”[13]
馬氏將他們和當(dāng)時文人們文會唱和的作品結(jié)集刊刻為《韓江雅集》,今存乾隆間刊本《韓江雅集》共十二卷,收錄了馬氏兄弟和揚州文人們雅集唱和達(dá)80次之多,唱和的地點有時候在馬氏的居所行庵,有時在馬氏另外一處別業(yè)南莊,有時在其他人的園林,如程夢星的篠園,其中多次都在小玲瓏山館中舉行。包括《微雪初晴集小玲瓏山館》、《消寒初集晚清軒分韻》、《十一月三十日集小玲瓏山館分詠》、《五月二日集小玲瓏山館題五毒圖》、《過玲瓏山館看玉蘭花》、《山館坐雨以雨檻臥花叢風(fēng)床展書卷分韻》、《七峰草亭遲雪以張伯雨山留待伴雪春禁隔年花分韻》、《小玲瓏山館對雪聯(lián)句》、《看山樓雪月聯(lián)句》等,可見山館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公共文學(xué)活動空間。
這些活動始終保持著高雅的品格,文人們聚集在園林之中,如李斗所描述的那樣,每人面前擺放著寫詩的文具和茶果,或者以韻為詩,或者以題為詩。從以題為詩中,我們可以見出他們的“高雅”情致。以《十一月三十日集小玲瓏山館分詠》為例,這次分詠,因為已經(jīng)是冬季,所以均以“寒”為題,“胡期恒得寒燈,唐建中得寒溪,程夢星得寒月,高翔得寒松,馬曰琯得寒山,汪玉樞得寒云,厲鶚得寒林,方士庶得寒更,王藻得寒旅,方士捷得寒煙,馬曰璐得寒江,陳章得寒原,閔華得寒砧,陸鐘輝得寒鐘,全祖望得寒竹,張四科得寒泉”[14]。以“寒”為題,又分出“寒燈”、“寒月”等諸多詩題。又如《書唐人詩集后》,“胡期恒分得白香山,唐建中分得杜樊川,程夢星分得李玉溪,馬曰琯分得杜少陵,王藻分得柳柳州,方士捷分得韓昌黎,馬曰璐分得王右丞,陳章分得李昌谷,閔華分得元微之,陸鐘輝分得孟襄陽,張四科分得李青蓮”[15]。再如《冬日小集行庵分詠》:“胡期恒得詩狂,唐建中得詩律,程夢星得詩囊,馬曰琯得詩壇,汪玉樞得詩城,厲鶚得詩債,方士庶得詩壁,王藻得詩材,方士捷得詩筒,馬曰璐得詩國,陳章得詩將,閔華得詩仙,陸鐘輝得詩瓢,張四科得詩禪”[16]。這些詩題,不僅富有情趣,更需要深厚的文學(xué)功底和知識,對于每個參加集會的人都是高難度的命題創(chuàng)作。就詩歌創(chuàng)作而言,它們也擴(kuò)展了某一類題材內(nèi)容的書寫。
聯(lián)句,也是“雅集”活動的方式之一。阮元說道:“聯(lián)句之盛,莫過于馬氏小玲瓏山館、程氏今有堂、張氏著老書堂。馬氏有食鰣魚聯(lián)句,有禹鴻臚尚基五瑞圖聯(lián)句,有看山樓雪月聯(lián)句,有五日席間詠嘉靖雕漆盤聯(lián)句,有寒夜石壁庵聯(lián)句,有壬申山館上元聯(lián)句,有乙亥上元聯(lián)句。”[17]如《看山樓雪月聯(lián)句》:
雪初晴月復(fù)清(厲鶚),氣赑屃光晶瑩(陳章),登層樓暢幽情(姚世鈺),炙冰硯溫酒鐺(馬曰琯),澄萬象增雙明(馬曰璐),廣寒府白玉京(鶚),竹聲瀉松影橫(章),籟既寂思已盈(世鈺),剪殘燭戀更深(曰琯),歲韻晏志合并(曰璐)。[18]
這次聯(lián)句的參加者,除了馬氏兄弟外,還有厲鶚、陳章、姚世鈺。聯(lián)句地點在山館內(nèi)的看山樓。聯(lián)句所詠之景是雪后之月,所用的詩體則是六言。這首聯(lián)句將雪、月、寒、夜、樓諸景以及文友們的共同情趣都表達(dá)了出來。
沈德潛在為《韓江雅集》所作的序言說道:
韓江雅集,韓江諸詩人分題倡和作也。故里諸公暨遠(yuǎn)方寓公咸在,略出處,忘年歲,凡稱同志、長風(fēng)雅者與焉。既久成帙,并繪雅集圖,共一十六人,詩筒郵寄,屬予序。惟古人倡和者,如王裴倡和,賈岑杜王倡和,荊潭裴楊倡和,元之與白、白之于劉,皮之于陸并以倡和稱。宋初西昆體有楊劉之徒十余人,元季玉山宴集有顧仲英、楊鐵崖諸人。明代如沈石田、文徴仲、唐子畏諸人次韻詩亦復(fù)斐然。而吾謂韓江雅集有不同于古人者。蓋賈岑杜王楊劉十余人倡和于朝省館閣者也,荊潭諸公倡和于政府官舍者也,王裴之于輞川,皮陸之于松陵,同屬山林之詩。然此贈彼答,只屬兩人。仲英草堂宴集只極聲伎宴游之盛。沈文數(shù)子會合素交,量才呈藝,別于賈岑以后詩家矣。然專詠落花,而此外又無聞焉。今韓江詩人不于朝而于野,不私兩人而公乎同人,匪矜聲譽,匪競豪華,而林園往復(fù),迭為賓主,寄興詠吟,聯(lián)接常課,并異乎興高而集、興盡而止者。則今人倡和,不必同于古人,亦不得謂古今人不相及也。昔王新城尚書官揚州司李,時招林茂之、杜于皇、孫豹人諸名士修褉紅橋,各賦冶春絕句,客俱屬和,迄今追憶,比于杜牧風(fēng)流,付之夢寐矣!乃八十余年后,有好事者追前塵而從之。新城余韻,不仍在綠楊城郭間也?予嘗經(jīng)蜀崗、登平山堂,吊歐陽公遺跡,遠(yuǎn)山長江,溶溶(獻(xiàn)齒),如眉如練,嘗夢魂飛躍于此,倘得側(cè)名賢之末,相與搜奇抉勝,較工拙于鏗鏘幽眇之間,亦江湖之至樂。而留滯春明,有懷莫能遂也。書復(fù)諸公,以志我愧,且為他日息壤之券云。[19]
沈德潛在追溯了歷代的文人雅集之后,指出馬氏兄弟與文友們園林雅集與往昔的不同:其一,他們不同于前朝的“朝省館閣”或“政府官舍”唱和,在身份上他們是“不于朝而于野”。其二,不同于前朝兩人之間(如元稹、白居易)的唱和,他們“不私兩人而公乎同人”,“韓江雅集”唱和者達(dá)十六人之多。其三,他們的唱和沒有什么功利性,“匪矜聲譽,匪競豪華”。其四,他們有一定的唱和空間,就是“林園往復(fù)”。其五,他們的唱和不是偶一為之,而是持續(xù)不斷的行為,所謂“迭為賓主,寄興詠吟,聯(lián)接常課,并異乎興高而集、興盡而止者”。最后他感嘆,當(dāng)年王士禎修褉紅橋,可與杜牧風(fēng)流相比;八十年后,竟然又有韓江雅集之步追前塵,讓自己向往不已。作為公共的文學(xué)空間,小玲瓏山館不僅活動頻繁、集群性突出、品味高雅、持續(xù)不斷,更重要的是體現(xiàn)了明清兩代文化下移的趨勢,的確具有不同于前朝以往的獨特性。
三、“獨坐”:作為私人空間的小玲瓏山館
根據(jù)杭世駿《朝議大夫候補主事加二級馬君墓志銘》的記載,馬曰琯雖然是商人,卻“以濟(jì)人利物為本,以設(shè)誠致行為實務(wù)。為粥食江都之餓人,出粟以振鎮(zhèn)江之昏執(zhí)。開揚城之溝渠,而重膇不病;筑漁亭之孔道,而擔(dān)負(fù)稱便。葺祠宇以收族,建書院以育才,設(shè)義渡以通往來,造救生船以拯覆溺。冬綿夏帳,櫝死醫(yī)羸,仁義所施,各當(dāng)其阸”[20]。看起來,馬曰琯的善行頗多,稱得上是一位有社會擔(dān)當(dāng)?shù)纳倘恕?/p>
杭世駿還記載,馬曰琯“及長,德器端凝,不茍訾笑。授經(jīng)后,據(jù)案堅坐,矻然如老儒;說經(jīng)岳岳,不可撼難”。在另外一個版本的“墓志銘”中,杭世駿還有對馬曰琯的這樣一段描述:“天骨英異,弱不勝衣,而遇事飚發(fā),動中機會,雖毅夫介士不能及。退居一室,如枯僧靜衲,夷猶澹遠(yuǎn),以奇文秘冊為師資,以法書古鼎為食飲,以長松怪石為游處,擺脫愛染,陶冶性靈,非多生有凈業(yè)者,不能到也”[21]。馬曰琯的形象與他的商人身份很不一樣,他“德器端凝,不茍訾笑”,很有自己的原則和操守;他“說經(jīng)岳岳,不可撼難”,不僅喜愛讀書,而且善于讀書;他又“弱不勝衣”,看上去是一介文弱書生。當(dāng)然,他處事的風(fēng)格并不文弱,所謂“遇事飚發(fā),動中機會,雖毅夫介士不能及”。將杭世駿這兩處描述聯(lián)系在一起,我們能夠感受到,馬曰琯的性格中有著濃厚的書生氣質(zhì),這種氣質(zhì)甚至連一般的書生都遠(yuǎn)不能及。
其實,杭世駿的描述在馬曰琯的詩作里能夠得到印證。小玲瓏山館并不僅僅是馬氏兄弟自我享受的物質(zhì)空間,也不僅僅是他們作為商人為了商業(yè)利益酬酢之所。在這個屬于他們的私人空間里,與文友們歡聚雅集只是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他們喜歡和文朋詩友們唱和,這是精神的需要。但是他的時間并不完全被這些內(nèi)容所占領(lǐng),他們還有日常生活,得應(yīng)付商業(yè)上的事,他們還要面對家庭,這些世俗的生活同樣不能避免。同時,他們也有靜下來的時候,有“獨坐”的時候,有寂寞的時光,他們也還有不便、不能或者沒有機會對朋友言說的內(nèi)心。在這些情形下,他們的精神活動并沒有停止,而是轉(zhuǎn)換為文學(xué)的書寫。且看馬曰琯的幾首詩詞:
《秋夜獨坐》:雨余檐外還蕭颯,燈下攤書讀未殘。已分此身成鈍漢,任人他日誚儒冠。蛩聲漸近知秋老,酒味全消怯夜闌。太息無兒頭早白,那堪顧影瘦欒欒。[22]
這首詩摹寫的正是馬曰琯自個兒“獨坐”的畫面,正如杭世俊所描述的“退居一室,如枯僧靜衲”。檐外下著秋雨,蛩聲漸近,酒意已消。在這個秋夜里,馬曰琯像往常一樣在燈下攤開了書籍,但是,他的心情卻有些沉重。因為自己功業(yè)未建,更讓他嘆息的是自己沒有兒子。馬曰琯認(rèn)為自己是個“鈍漢”,而且也把自己當(dāng)成“儒冠”準(zhǔn)備將來被人譏嘲,今天看來似乎不好理解,因為他的生活過得很是優(yōu)裕,他有私家的園林,他還經(jīng)常接濟(jì)貧弱,他在揚州乃至天下文人中頗有聲名,還有什么遺憾呢?那么只有一個理解——他沒有科舉功名,因為沒有科舉功名,他未曾踏上仕途;沒有踏上仕途,他就未能實現(xiàn)儒家老祖宗們?yōu)樽x書人標(biāo)舉“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或許馬曰琯自許甚高,即便是有錢、有書、贏得了諸多文士們的尊敬,他還是覺得曾經(jīng)的理想沒有實現(xiàn)是永遠(yuǎn)的遺憾。另一方面,沒有兒子,意味著自己的生命得不到延續(xù),這在馬曰琯的時代,的確是一個莫大的遺憾和悲哀。這兩重心事,他在與文友們相聚唱和的時候,是不會輕易流露出來的,唯有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才涌上心頭、付諸筆端。
《乙卯午日》:小瓶艾葉剪香叢,墻角榴花委地紅。五日關(guān)心逢競渡,廿年積思等飄蓬。東西兄弟渾如醉(時弟半查暫寓西頭),酬唱賓朋孰最工。獨坐閑庭無一事,茶煙輕飏竹梢風(fēng)。[23]
這首詩雖然也寫自己“獨坐”,但從情緒上略為輕松一些。乙卯為雍正十三年(1735年),馬曰琯時年47歲,從“艾葉”、“逢競渡”等詞句看,這個“午日”當(dāng)為端午節(jié)。此時,他的手足兄弟馬曰璐和他住在一起,兩個人都有些醉態(tài),賓朋好友也多所酬唱。朋友們離開后,他“獨坐”庭院,享受著悠閑,眼里是“茶煙輕飏”的景色,連拂過竹梢的風(fēng)也是軟的。但在這舒緩優(yōu)雅的獨奏曲中,我們聽到了一組不和諧的音符——“廿年積思等飄蓬”。他的“積思”是什么,是壯志未酬?還是一直沒有兒子?乙卯年端午那一天,馬曰琯“獨坐”在小玲瓏山館內(nèi),他的思緒并沒有停止,內(nèi)心的那份遺憾并沒有丟卻。
【訴衷情】《寒蛩》:那堪秋去耳還聞,床下更相親。忘卻麤疎聲老,猶自怨黃昏。 無氣力,與誰論,雨紛紛。一燈如豆,兩鬢成絲,怎不銷魂。[24]
這首小詞重現(xiàn)了《秋夜獨坐》的畫面:依舊是秋雨,依舊是孤燈,依舊是蛩聲。只是在這個秋夜里,蛩的鳴叫聲被放大,而馬曰琯的心緒也伴著蛩聲變得更加低沉,“一燈如豆,兩鬢成絲,怎不銷魂”。秋夜的馬嶰谷是如此的孤獨,如此的黯然和頹喪。他的人生看似熱鬧非常,可他生命中的夜晚,又是如此悲涼和感傷。他擁有了很多:財富、園林、古玩、書籍,還有朋友。但他沒有得到的東西也很多,他最想得到的東西卻沒得到。于是,獨坐的他描摹了自己獨坐的模樣,也寫下了他獨坐的內(nèi)心世界。
馬曰琯有詞集《嶰谷詞》,其第一首《百字令·自述》就表達(dá)了一種人生感慨:
半生情味,嘆飛光激箭,流年隨手。踏遍槐花成底事,蠟燭三條孤負(fù)。洗墨池荒,畫眉人老,蕭索閑門舊。添丁詩句,玉川何日才就?贏得玉柱金庭,銀濤雪屋,湖海籠襟袖。回首東華塵土夢,布襪青鞋還又。桑柘騎牛,滄浪吹笛,沮溺真吾耦。從今以往,樂天惟是歌酒。[25]
寫這首詞的時候,馬曰琯應(yīng)該年過半百了,所謂“半生情味”說明了他的生命刻度。人在年過半百的時候想的是什么?一個文人想的是什么?像馬曰琯這樣的既是商人又是文人的人想的又是什么?他感慨的是“飛光激箭,流年隨手”,時光過得飛快,人生有許多變化,自己雖然“贏得玉柱金庭,銀濤雪屋”,過著富貴的生活,但再多的金銀和財富,仍然不過是一個豪華的夢而已,所以要像長沮和桀溺那樣作一個避世的隱士,不再有什么追求,“樂天惟是歌酒”。這種消極的人生態(tài)度,其他的文人也有,所不同的是馬曰琯不是感嘆功業(yè)難就,而是覺得整個人生都無趣。
“獨坐”,是杭世駿給馬曰琯繪寫的肖像,也是馬曰琯在詩詞中給自己繪寫的肖像。“獨坐”肖像的背景是財富堆積而成的小玲瓏山館。在這個諸景皆備的園林中,在這個熱鬧暫時消失的私人空間里,馬曰琯的“獨坐”是一個還原為本來的個體生命的存在,也是他以詩詞書寫的方式言說內(nèi)心世界的動作。
四、小玲瓏山館空間之生命體溫
沈德潛在《沙河逸老小稿序》中說:“(馬氏兄弟)以朋友為性命,四方人士,聞名造廬,適館授餐,經(jīng)年無倦色……有急難者,傾身赴之。”杭世駿的“墓志銘”也記載,馬曰琯“傾接文儒,善交久敬。意所未達(dá),則逆探以適其欲。錢塘范鎮(zhèn)、長洲樓锜,年長未婚,擇配以完家室;錢塘厲徵君六十無子,割宅以蓄華妍;勾甬全吉士被染惡疾,懸多金以勵醫(yī)師;天門唐太史客死維揚,厚賻以歸其喪”。馬氏兄弟的文友們大都沉抑于下層社會,貧困是大多數(shù)人的生活狀態(tài)。幫助文友擇婚配,幫助文友治病,乃至幫助去世的文友料理后事,馬氏兄弟的這些善舉自然令人敬佩。最重要的是,他們能夠做到“善交久敬”。中國古代的文人大多數(shù)又很清高,不受“嗟來之食”, 馬氏兄弟并非依仗自己的富有和他們交往,而是永遠(yuǎn)保持著對他們的敬重,以真誠之心和共同的文化志趣贏得了他們的友誼。由此,小玲瓏山館這個物質(zhì)空間中充盈著濃濃的生命體溫。
著名詞人厲鶚(號樊榭),浙江錢塘人,出身寒門,幼年喪父,家境清貧,但他刻苦用功,“讀書數(shù)年,即學(xué)為詩,有佳句”,“于書無所不窺,所得皆用之于詩”[26](P364)。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厲鶚參加鄉(xiāng)試中試,此后他雖曾入京參加會試和候選官員,但都因其個性原因而作罷。自雍正三年(1725年)起,他幾乎年年做客揚州,客居馬家20余年,也與馬氏兄弟結(jié)下了深情厚誼。
在馬氏兄弟現(xiàn)存的詩詞中,我們能夠感受到他們與厲鶚溫?zé)岬挠亚椤R淮钨p菊雅集時,厲鶚恰好自武林來到揚州,馬曰琯作《重九后二日,樊榭至自武林,同人適有看菊之集,分得佳韻》,高興地吟道:“菊蕊盈枝香霧排,陶家清興繞書齋。秋花愛寄蕭閑地,好友能開寂寞懷。三徑風(fēng)雨寧少負(fù),一年琴酒不教乖。峭帆才落吟情續(xù),又比皋亭句子佳。(樊榭來時有過皋亭臨平諸詠)”[27]曰璐則作《重九后二日,樊榭至自武林,同人適有看菊之集,分韻共賦,得侵韻》。
在厲鶚現(xiàn)存的作品中,我們同樣能夠捕捉到他對馬氏兄弟情誼的感念。在《樊榭山房續(xù)集》中,我們看到馬曰琯在炎熱的夏天送他漳蘭后彼此唱和的【清江引】詞作,馬曰琯詩曰:
清風(fēng)灑,涼露滋。瘦亭亭自憐幽致。伴同心玉琴調(diào)七絲。小窗中略添秋思。
厲鶚和作《嶰谷送漳蘭》:
心占易,佩擬騷。兩三莖送秋先到。吐幽香暗將炎晝消。雪窗僧寫來難肖。[28](P1677)
這樣的唱和詞,再現(xiàn)了馬氏對厲鶚的無微不至的關(guān)心。炎熱的夏天,送來幾莖幽蘭,令窗內(nèi)頓生涼意。而他們之間的表達(dá)方式又極其文雅,送的人以詞表情,收的人以詞寫意。沒有直露的“關(guān)心”,也沒有直露的“感謝”,一切的心情都在你來我答的默契之中。在《樊榭山房續(xù)集》中,我們還讀到一首【水仙子】《謝馬嶰谷半槎惠人葠(參)》:
靈苗合在阮生家。香蕊應(yīng)須溫尉夸。連根便是邊鸞畫。價兼金難賽他。起沉疴何必丹砂?秋寄逢江雨,晨煎汲井花。此意無涯。[29](P1679)
與前面的和詞不同,厲鶚這首詞的詞題就明確用了“謝”字。或許因為厲鶚身染“沉疴”,或許人參價格昂貴,所以馬氏兄弟在此時的關(guān)心已讓他越過了默契的境界,不僅言“謝”,而且深感“此意無涯”。厲鶚60歲還沒有兒子,愛妾又去世,馬氏兄弟甚至為厲鶚娶妾以續(xù)后嗣。因為山館之中有了這樣一份體溫,所以厲鶚才經(jīng)常入住其中。
厲鶚去世后,馬曰琯作《哭樊榭八截句》,其一道:“涼雨孤篷憶去時,無端老淚落深卮。年年送慣南湖客,腸斷秋衾抱月詩。”其六道:“曲曲長廊冷夕曛,更無人語共論文。宵分有夢頻逢我,海內(nèi)何人不哭君。”[30]厲鶚在世的時候,每年都要回浙江探親,馬氏兄弟總是渡頭相送,詩句吟別。而今,連這樣送別的機會都已經(jīng)沒有了。在小玲瓏山館里,馬氏兄弟建有覓句廊,他們和文朋詩友在此吟詩論文,厲鶚長居馬家,自然是這里常見的身影,而今,身影不再,只有廊冷夕曛,所能希冀的是在夢中能夠時常見到厲鶚這位朋友了。這些詩作寫得情真意切,令人回腸百結(jié),為馬曰琯對厲鶚的深厚情誼所感動。
如果說二馬兄弟和厲鶚的情誼以“深厚”形容,他們和姚世鈺的情誼可以說達(dá)到了“感人”的程度。姚世鈺字玉裁,號薏田,浙江歸安人。少嗜學(xué),負(fù)俊才,貫穿經(jīng)史,考訂必詳核精當(dāng),詩文清雋高潔。但他命運卻困頓坎坷,全祖望《姚薏田壙志銘》說他“重之以疾病,甚之以患難,終之以孤煢”。 1729年,清世宗借曾靜之案大興文字獄,他的姐夫王豫遭到株連,被逮入京師,姚世鈺則驚恐、無助,精神備受打擊。他來到揚州之后,成為小玲瓏山館的賓客,得到馬氏兄弟的真情幫助和關(guān)心。他曾撰《初夏薄游揚州,馬秋玉佩兮兄弟為余置榻叢書樓下,膏馥所霑丐,藥物所扶持,不知身之在客也。秋杪言歸,又以紅船相送渡江。所恨者京口勝游,尚負(fù)山靈諾責(zé)耳。途次有作,聊抒別懷》:
自嫌觸熱走殊鄉(xiāng),只為春明別有坊。做客渾如在家好,款門不厭借書忙。沈綿痼疾三年艾,安穩(wěn)歸人一葦航。回首離情滿江上,寒山千疊正蒼蒼。[31]
讀此詞,我們不難看出,真誠的謝意流溢于字里行間。“做客渾如在家好”,這是一種什么樣的感受!而在這感受的背后,馬氏兄弟又給了他多少的關(guān)心和愛撫!詩題就明白寫出,馬氏兄弟將他安置在叢書樓,供應(yīng)他的飲食,醫(yī)治他的疾病,珍本秘籍供他研讀,更在精神上給他以理解和撫慰。從而讓他這個身染痼疾之人,能夠成為“安穩(wěn)歸人”。
馬曰璐的【定風(fēng)波】《聽薏田談往事》[32]寫道:“往事驚心叫斷鴻,燭殘香灺小窗風(fēng)。噩夢醒來曾幾日,愁述山陽笛韻并成空。遺卷賴收零落后,牢愁不畔盛名中。聽到夜分惟掩泣,蕭寂,一天清露下梧桐。”就詞所寫,那當(dāng)是秋天的夜晚,馬曰璐聽著姚世鈺困頓悲涼的人生經(jīng)歷,那一樁樁不幸的遭遇,那一幕幕令人不堪回首的噩夢,讓他“驚心”,讓他“掩泣”,夜已很深,耳邊是南飛孤雁的悲傷的鳴叫聲,所感受到的是秋風(fēng)蕭瑟。這是沉重、冷寂的一幕,也是一幅心曲款通的畫面。姚世鈺終于早逝。馬氏兄弟和失去厲鶚一樣悲傷不已。馬曰琯的《題薏田書冊》寫道:“寒鑒涵秋冷,風(fēng)蘋引恨長。才名成底事,翰墨有余香。展冊對亡友,濡毫酸別腸。更搜零落稿,同置研函旁。”[33]又失去了一位和他品詩論文的朋友,何況是一位身世凋零的才人,翻展他的遺冊,不禁悲酸于心。據(jù)全祖望記載,姚世鈺去世后,“吾友馬曰琯、曰璐、張四科為之料理其身后,周恤其家,又為之收拾遺文,將開雕焉,可謂行古之道也。”[34](P360)
經(jīng)常參加小玲瓏山館雅集活動的另外一位文人樓锜《于湘遺稿》在馬曰琯去世后,也寫有《哭馬嶰谷》詩兩首,其二道:
廿載游從舊,當(dāng)筵擘短箋。謬推居客右,嘗許在廬前。含殮嗟何速,尪羸熟見憐。漫思隨令弟,早晚哭靈筵。[35]
在“尪羸熟見憐”一句后,他特意加注道:“予患羸疾,屢蒙贈問”。可見馬氏兄弟對他一樣關(guān)心和照顧,難怪樓锜傷心地表示要“早晚哭靈筵”。
馬曰琯的《沙河逸老小稿》中,有多首寫給全祖望的詩作,或送別,或思念,或重逢而喜,可以見出他對朋友的一片情誼。而全祖望本人眼疾嚴(yán)重,馬氏兄弟寄書請他到揚州,為之請醫(yī)療疾。正因為如此,全祖望去世的時候,特命弟子董秉純將其所抄文集五十卷交給馬氏藏書樓。*《全謝山年譜》載:“又十日,呼純之榻前,命盡檢所著述,總為一大簍,顧純曰:好藏之。而所抄文集五十卷,命移交維揚馬氏藏書樓。”參見全祖望:《鮚埼亭集內(nèi)編》,25頁,載《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作為商人的馬氏兄弟對文人們尊重有加,與文人們結(jié)下了深厚的情誼。他們以自己的經(jīng)濟(jì)實力,為一批潦倒的文人提供了從事文學(xué)創(chuàng)作、文史研討的物質(zhì)條件和溫馨的氛圍,撫慰了他們的心靈,讓他們保持了文化的自尊。難怪像厲鶚和全祖望那樣有骨氣有個性的文人,都能夠和馬曰琯保持極為密切的朋友關(guān)系。可見,小玲瓏山館中的生命體溫確實讓他們難以忘懷。
已故的蘇州大學(xué)嚴(yán)迪昌教授認(rèn)為,馬氏兄弟和文士們的文會和酬唱并不簡單。小玲瓏山館中所養(yǎng)護(hù)的多為浙江人,有厲鶚、姚世鈺、陳章等人。其時雍正帝大惡浙人,“圣諭”一而再、再而三讞定“浙江紳衿士庶刁頑澆漓”、“惡薄”,并空前勒令浙省暫停鄉(xiāng)會試科考資格。風(fēng)聲鶴唳,浙人自危之甚,紛紛遠(yuǎn)禍。金埴《不下帶編》記載:浙江余姚的舉人鄭世元(亦亭)為莊親王之長子“課文藝”, “雍正四年冬,亦亭以浙江舉人避嫌,力辭王門”[36](P89)。莊親王允祿是康熙第十六子,小于雍正帝十七歲,有“賢王”之稱,其王府亦有“避嫌”之舉,可知“浙人”一時幾與“麻煩”等同[37]。由此看來,在清代高壓的文化政策下,小玲瓏山館更是文士們避風(fēng)遮雨的一個溫馨的場所。
馬曰琯的【明月引】《行庵為同人吟會之地,年來故侶零落,愴然于懷,因賦此曲》[38]讓我們再次感受到他對朋友們的真情和他自己內(nèi)心的那片柔柔的情誼:
蕭蕭禪院冷秋鐘。約過從,怯過從,老樹疎枝,即輩倚吟筇。風(fēng)又易流云又散,徑苔里,一條條,認(rèn)舊蹤。舊蹤舊蹤總迷濛。叫斷蛩,記也記也記不起,魂夢相逢。才一追思,斜日下墻東。須鬢看看凋落盡,拌醉也,把衰顏,付酒紅。
人不能沒有朋友,但像馬氏兄弟視朋友為性命的情形并不普遍。如果說對厲鶚、姚世鈺去世后的情感如同長歌一哭,那么在這首詞里我們讀到的是失去朋友后自己生命的委頓。山館依舊,朋友已去,沒有了朋友,自己也是“須鬢看看凋落盡”,生命和精神都隨著朋友的離去而凋落了。
結(jié)語
正如本文開頭所說的,文學(xué)史其實是由無數(shù)個大大小小的“空間”構(gòu)成的。就作品的創(chuàng)作而言,任何一個作家的任何一篇作品,都是在特定的空間創(chuàng)作完成的。回歸作家創(chuàng)作的具體時間和空間,才能夠準(zhǔn)確理解作品的內(nèi)涵。就文學(xué)史發(fā)展而言,諸多對文學(xué)史演進(jìn)產(chǎn)生影響或者體現(xiàn)文學(xué)史發(fā)展趨勢的現(xiàn)象、事件,也需要將它們回歸到原有的時間和空間去考察。當(dāng)然,這樣的空間太多,我們需要選擇,更需要挖掘其中蘊含的“意味”。
作為文學(xué)空間的小玲瓏山館,曾經(jīng)是清代江南地區(qū)的一道引人注目的風(fēng)景,也是一個“有意味”的文學(xué)空間,它是一個私家園林,不僅折射著清代中期經(jīng)濟(jì)的繁榮和社會文化趣味,同時也是園林與文學(xué)的相互激發(fā)、相互浸潤的典型。從唐宋開始的園林文學(xué),到了清代已蔚為大觀。作為公共文學(xué)空間,小玲瓏山館中的文學(xué)活動有著集群性、高雅性、持續(xù)性,特別是平民性的特點,它們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xiàn)出清代文學(xué)發(fā)展的特點和趨勢,文學(xué)史中的重要作家在其中的活動和作用,也需要我們重新認(rèn)識。作為私人文學(xué)空間,小玲瓏山館的主人,既有商人的身份,又有詩人身份,這種身份的復(fù)雜性,以及對他們在文學(xué)史上作用的衡定,也是文學(xué)史研究的新命題,而他們在這一私人空間中的精神活動和文學(xué)書寫,也饒有生命趣味。馬氏兄弟和他們的集群所具有的生命體溫,更是讓我們回到當(dāng)年小玲瓏山館那個空間,體會到他們的喜怒哀樂,觸摸到他們生命的律動,感動于他們彼此間細(xì)膩的情感呵護(hù)。通過對于這樣的文學(xué)空間的挖掘,我們可以真正讓文學(xué)研究回歸到“心靈史”、“思想史”、“生活史”和“情感史”的層面,從而,文學(xué)史才擁有文學(xué)所應(yīng)該具備的生命之趣味。
[1] 李斗:《揚州畫舫錄》卷4,北京,中華書局,1969。
[2] 丘良任:《“揚州二馬”及〈小玲瓏山館圖記〉》,載《揚州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1983(3)。
[3] 馬曰璐:《南齋詞》卷一,《四部叢刊》本;馬曰琯:《街南書屋十二詠》,載《沙河逸老小稿》卷1,《四部叢刊》本。
[4] 厲鶚:《樊榭山房集》卷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5] 陳章:《孟晉齋詩集》卷3,乾隆四十四年勤有堂刻本。
[6] 程夢星:《今有堂詩后集》,乾隆十二年刻本。
[7]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17,載《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8] 杭世駿:《道古堂集》卷19,載《續(xù)修四庫全書》1426冊影印,清光緒十四年汪增唯增修本。
[9] 李斗:《揚州畫舫錄》卷8,北京,中華書局,1960。
[10] 厲鶚:《樊榭山房集》續(xù)集卷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1] 全祖望:《鮚埼亭詩集》卷3,載《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2] 厲鶚:《分賦鐘馗畫引》,載《樊榭山房集》續(xù)集集外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3][27][33] 馬曰琯:《沙河逸老小稿》卷3,《四部叢刊》本。
[14] 馬曰琯編:《韓江雅集》卷3,乾隆十二年刻本。
[15][16] 全祖望編:《韓江雅集》卷6,乾隆十二年刻本。
[17] 阮元:《廣陵詩事》,光緒十六年刻本。
[18] 全祖望編:《韓江雅集》卷7,乾隆十二年刻本。
[19] 全祖望編:《韓江雅集》卷首,乾隆十二年刻本。
[20] 杭世駿:《道古堂集》卷43,載《續(xù)修四庫全書》1426冊影印,清光緒十四年汪增唯增修本。
[21] 杭世駿:《朝議大夫候補主事加二級馬君墓志銘》,載《林屋唱酬集》附錄,《四部叢刊》本。
[22][23] 馬曰琯:《沙河逸老小稿》卷1,《四部叢刊》本。
[24][25][38] 馬曰琯:《嶰谷詞》,《四部叢刊》本。
[26] 全祖望:《厲樊榭墓碣銘》,載《全祖望集匯校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8][29] 厲鶚:《樊榭山房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0] 馬曰琯:《沙河逸老小稿》卷5,《四部叢刊》本。
[31] 姚世鈺:《孱守齋遺稿》卷2,《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32] 馬曰璐:《南齋詞》卷1,《四部叢刊》本。
[34] 全祖望:《鮚埼亭集》卷20《姚薏田壙志銘》,載《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5] 樓锜:《于湘遺稿》,乾隆二十年陳章刻本。
[36] 金埴:《不下帶編》卷5,北京,中華書局,1982。
[37] 嚴(yán)迪昌:《往事驚心叫斷鴻——揚州馬氏小玲瓏山館與雍、乾之際廣陵文學(xué)集群》,載《文學(xué)遺產(chǎn)》,2002(4)。
(責(zé)任編輯 張 靜)
Xiaolinglong Hilly House:A “Meaningful” Literary Space
ZHU Wan-shu
(School of Liberal Art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Xiaolinglong Hilly House, possessed by the famous brothers Ma Yueguan and Ma Yuelu in the Qing Dynasty in Yangzhou, is a typical literary space. Physically speaking, it is a private garden which include the Pavilion for the View of Mountain, and the Series Pavilion. As a public literary space, it is often used for social gatherings, which are characteristic of a cluster, elegance, civilians, etc,. As a private space, it is the place where the owner Ma Yueguan “sits alone amidst”, transforming his life experience into literary writing. The literature space clusters engage themselves in profound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reflecting the warmth in their lives. Through thorough excavation, connotations of various kinds of literary history can be perceived.
Xiaolinglong Hilly House;literature space; “meaningful”
朱萬曙:文學(xué)博士,中國人民大學(xué)文學(xué)院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