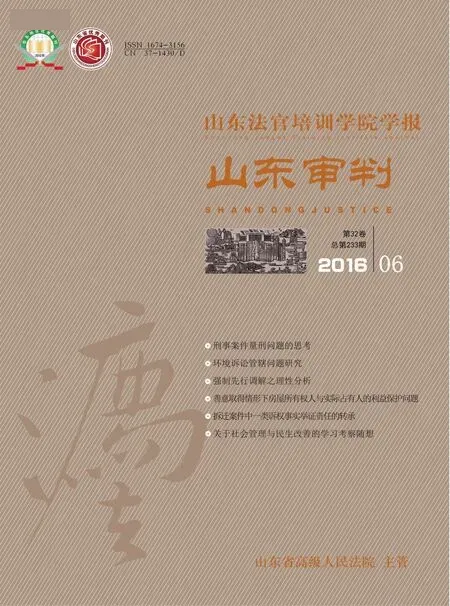犯罪化與非犯罪化:涉專利刑事政策的雙極取向
●胡安瑞
犯罪化與非犯罪化:涉專利刑事政策的雙極取向
●胡安瑞
現行《刑法》中假冒專利罪的主要客體是專利號的專有使用權或專利權人的身份權,次要客體是消費者(合同相對方)的知情權,其不處罰專利侵權行為和冒充專利等其他涉專利的違法行為,這似乎意味著冒充專利的行為得不到《刑法》的規制。筆者認為假冒專利的行為可以非犯罪化處理,專利侵權行為需要犯罪化處理。
犯罪化 非犯罪化 假冒專利罪 專利侵權行為
在刑事政策中,犯罪化和非犯罪化問題“涉及到公權力邊界問題,涉及到私權者的權利如何排除公權力的干擾和侵害而得以促全,涉及到私權者在其私人生活很大程度地依賴公權者的恩惠而不得自治時還能理直氣壯地向公權者主張自己的權利”。①夏勇:《法治與公法》,載http://www.iolaw.org.cn/showarticle.asp?id=228,2009年1月11日訪問。當我們用犯罪化和非犯罪化的理論去檢視我國現行《刑法》關于專利權保護的現狀時,我們難免會發出“該保護的得不到保護,不該保護的過分保護”的感嘆。
一、專利權刑事立法保護現狀——對專利違法行為涵蓋性梳理
《刑法》第216條規定的假冒專利罪是刑法典唯一一條專門針對專利權方面違法行為進行規制的刑法分則條款,我們并不能說刑法其它法則條規都沒有可能適用于涉及專利權的犯罪,更不可能說涉及專利方面的違法行為都能被《刑法》第216條所規制。在立法之初,假冒專利罪是否應包括專利法中的專利侵權行為或冒用專利的行為,學界存在著很大的爭議。2001年7月1日《專利法實施細則》的頒行,2004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頒布,標志著關于該罪客觀方面的爭議告一段落。該司法解釋第10條規定:“實施下列行為之一的,屬于刑法第216條規定的‘假冒他人專利’的行為:(一)未經許可,在其制造或者銷售的產品、產品的包裝上標注他人專利號的;(二)未經許可,在廣告或者其他宣傳材料中使用他人的專利號,使人將所涉及的技術誤認為是他人專利技術的;(三)未經許可,在合同中使用他人的專利號,使人將合同涉及的技術誤認為是他人專利技術的;(四)偽造或者變造他人的專利證書、專利文件或者專利申請文件的。”
從上述司法解釋來看,本罪的保護法益是復雜客體,主要客體是專利權人專利號的專有使用權和專利人的身份權,次要客體是消費者(或合同相對方)、公眾的知情權。前述司法解釋規定的前三種行為都是直接針對專利號的行為,這種專利號的專有使用權是依附于專利權的從權利,不能脫離主權利單獨轉讓;第四種行為中行為人偽造或者變造他人的專利證書、專利文件或者專利申請文件的目的是證明自己是一項專利的擁有者或者被許可使用者、發明人等,總之是想證明一個專利權人的身份。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刑法》中的假冒專利罪不包括專利侵權行為。結合其他刑法條文,筆者認為在刑法上真正得不到規制的行為只有專利侵權行為(狹義)。
二、實踐與理想分裂的應答——假冒專利罪的非犯罪化的提出
現代刑法學的啟蒙大師邊沁說“不應適用刑罰的案件可歸結為四類:當刑罰是:⑴濫用;⑵無效;⑶過分;⑷太昂貴之時”。②〔英〕吉米·邊沁:《立法理論》,李貴方等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73頁。由此分析,筆者認為將假冒專利的行為規定刑罰實屬不應當適用刑罰的情形。
(一)假冒專利罪的刑法規定背離了立法初衷,作用有限
1979年《刑法》并沒有假冒專利罪的規定,1984年《專利法》規定“假冒他人《專利》……情節嚴重的,對其直接責任人員比照刑法第127條規定追究刑事責任”,即比照假冒注冊商標罪的規定。時任專利局長的黃坤益在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上就專利法作立法說明時講到,“為了有效的專利權人的權利,草案對侵權行為除規定予以民事賠償外,還對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規定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由于我國的刑法對侵犯專利權尚無具體規定,在刑法補充相應條款前,可以比照《刑法》第127條假冒商標罪論處”。③周植赟、韓斌:《假冒專利罪辯析與質疑》,載《山東公安專科學校學報》2002年第4期。1997年《刑法》的假冒專利罪的規定即是沿用了《專利法》的上述規定。由此看來,立法者設立假冒專利罪的目的是為了保護狹義的專利權,即專利人的獨占實施權,制止專利侵權行為。但假冒專利罪所保護的只是專利權中的衍生權利,即專利標號的使用權等,對于專利侵權行為無能為力。罪刑法定的要求又使得類推為刑事法治所不許,立法的旨趣已喪失殆盡。而,實踐中專利侵權行為依然猖獗,統計數據表明:2003年—2007年專利案件呈明顯上升趨勢,其中絕大多數是侵權案件,年平均增長率17.64%,④邰中林:《2003-2007知識產權審判數據分析》,載《法制資訊》2008年第8期。再一次證明假冒專利罪的設立沒有起到立法者原本設想的效果。
(二)設置假冒專利罪的邏輯推理錯誤
學界有人為維護假冒專利罪之合理性談到“必須弄清楚商標和專利的不同作用。商標的基本作用是區分商品與服務的來源,而專利的基本作用是保護發明創造,這種不同的作用決定了假冒注冊商標以擅自使用他人的注冊商標為前提,而假冒專利的行為恰恰是指未使用他人專利的情形。”⑤周詳:《再論假冒專利罪》,載《電子知識產權》2003年第12期。筆者認為,專利和商標的作用不同只能推出侵犯商標權的行為主要應該是非法使用他人商標標識的行為,而侵犯專利權的行為主要應是非法使用他人發明創造的行為。我們很難從兩者的不同作用推出假冒專利的行為的行為性質,假冒專利的性質是由假冒專利這個術語的內涵本身決定的,而與專利的作用無關。相反,“從專利的基本作用是保護發明創造”,我們完全可以推出最應該得到刑罰處罰的應是專利侵權行為,而不是假冒他人專利的行為(其沒有實施他人專利)。
(三)假冒專利行為的危害性在常例上達不到應受刑罰處罰的程度
首先,假冒專利的行為主要是侵犯他人專利號的行為,而如前所述專利的基本作用是保護發明創造,對專利號專有權的保護遠達不到保護發明創造的作用。假冒專利的危害性不體現在對狹義的專利權的侵犯上。其次,專利號與商標不同,二者的影響力有著巨大的差距。“商標是消費者識別商品的首要外在標志,正因為如此,商標才有‘商標的臉’之稱。包括專利標記在內的商標上的其他標記作用則要小得多”,“專利號在市場上的識別作用極為有限”。⑥前引③。所以,專利號對普通消費者沒有很大作用的。而對于專業的合同相對方則更不應該因僅僅看到專利號而簽訂合同,這是因為專利權的取得是以專利技術的公開為代價,任何人均可以查到專利技術的具體內容和真正的專利人,從而核實行為人是否真正擁有專利權,所以專業的合同相對人一般也不會受欺詐。因而其對消費者的影響一般很小,危害性在常態上一般也不會影響社會秩序。另外,假定有影響的話,那么對于普通消費者來說,專利號的影響也不大于產品上標記的“專利”或“中國專利”字樣,在產品上標注他人專利號的影響也不大于在產品上標注一個完全不存在的專利號?在當下對后兩種行為沒有作出單獨的刑事立法時,對假冒專利的行為規定刑罰處置,也不盡合理。
(四)取消假冒專利罪的規定不會放縱應當進行刑事處罰的假冒專利行為
一種行為如果要作為一個單獨罪名在刑法中予以規定,必須在常態上具有相當的社會危險性。如果這種行為一般沒有達到應當受刑事處罰所需要的社會危害性,則沒有必要單獨規定一個罪名。而對于這種行為偶然需要刑事處罰則完全可以付諸其他罪名進行處理。如果取消了假冒專利罪,我們仍可以對此類中應當處罰的行為進行刑事處罰。假冒專利的行為是冒充專利的一種特殊形式,而冒充專利的行為,如果需要刑罰規制,可以詐騙類犯罪、虛假廣告罪、偽造、變造國家機關公文件、證件、印章罪處之。假冒專利罪當然也可以了。此外還有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可以對此規制,偽產品主要是指“以假充真”的產品,而假冒他人專利的行為,恰恰是以不是此專利產品冒充此專利產品的行為,也有假與真之分,是“以假充真”。
三、立足于國情的思考——專利侵權行為(狹義)犯罪化的論證
(一)關于專利侵權行為的社會危害性
專利侵權行為除侵犯了專利權人的權利外,還對社會還存在的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其一,此種侵權行為通過對專利權的侵害嚴重的破壞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專利權本身就是市場經濟體制本身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沒經過別人允許使用他人專利權本身就嚴重的破壞了市場秩序,專利侵權行為是一種不正當競爭的行為,也減損了市場經濟的誠信紐帶。其二,當今中國正在抓緊建設創新型社會,國家提倡以專利導航實現創新驅動,實現供給側改革;在知識經濟的時代,知識產權日益成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性資源和國家競爭力的核心要素。國家設立專利制度的目的是激勵人民發明創造和技術創新的積極性。因而如果對專利權保護不力,這種目的就將落空,勢必影響科技人員創新的積極性,影響國家的創新能力。其三,專利的保護程度直接影響著該國地國際經濟交往中的實際地位以及我國在經濟全球化中的獲益程度。如果我們對專利的保護不力,“國外將不愿意將核心技術輸入我國,最終導致我國只能成為一個從事低附加值、無技術涵產品生產的‘組裝工廠’”。⑦田文英、呂文舉、汪婷婷:《專利權的刑事保護研究》,載《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2003年第5期。其四,專利權的獲得是以公開其技術為前提的,專利技術的公開一方面是為了防止他人重復研究,做人力和財力的浪費;另一方面是為了方便他人獲得技術做后續研究,和教學之用。而我國現行刑法對商業秘密規定了刑罰保護,而對專利權沒有規定刑法保護。如此下去,發明創造人就會考慮公開技術獲得專利是否合算,法律對專利的保護遠不及商業秘密的保護強度。這必然導致技術公開率下降,重復研究浪費資源的現象普生,社會獲得新知識的路徑減少。其五,刑法中有侵犯商業秘密罪,而專利在申請之前本身就是一種商業秘密;申請之后與原本的商業秘密之間的區別也就是是否公開,及是否有專利權的形式,其它并無不同。而商業秘密既有民事法律的保護,又有刑法的保護,可是專利權只有民法的保護,這顯然難以成立。
(二)專利侵權行為與公眾法感情
對于犯罪化的基準中有學者提到對公眾的倫理價值的嚴重違反,一些學者則認為這種行為為絕大多數人不能容認。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爭議,筆者使用公眾法感情的概念,也就是公眾認為這種行為有必要作為犯罪處理,這是犯罪化的一個重要的條件。立法如果與公眾法感情相悖,則可能引起公眾的抵制,嚴重的將使這種立法在事實上失效。因而在今天信息極度暢通的年代,任何一個立法者或司法者都不能不注意公眾的意向,公眾法感情必然進入立法者的視野。對于專利侵權行為犯罪化,筆者認為也是符合公眾法感情的:一是新刑法出臺以后一段很長的時間,在刑法學界有絕大多學者(包括知名的學者、大家),或者講主流的觀點對假冒專利的理解上都認為包括專利侵權行為。如高銘暄教授認為“假冒專利是指非法實施他人專利的行為”;⑧參見高銘暄:《新編中國刑法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658頁。何秉松教授也在教科書中寫到假冒專利罪包括“未經專利權人許可,為生產經營目的而非法制造、使用、銷售其專利產品或者使用其專利方法的行為”。⑨何秉松:《刑法教科書》,中國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552頁。雖然作這種樣理解假冒專利罪是不正確的,但是他代表了學者的一種愿望和想法,認為專利侵權行為需要犯罪化處理。二是新刑法頒布后在司法實踐中對專利侵權行為作為假冒專利罪判決的不在少數,而且司法實踐中第一例假冒專利罪的判決就是專利侵權行為。案情大體是這樣:方舟集團董事長盧恩光獲得得“雙層藝術玻璃容器”專利。1999年3月,周小波注冊成立樂凱制品廠。周自滕州天元瓶蓋廠購進杯體,以每只65元的成本生產“雙層藝術玻璃容器”“樂凱”口杯,并于同年5月至9月以每只78元至182元的價格分別銷至河北開元實業有限公司等單位,直至被陽谷縣檢察院查獲。周共銷售樂凱口杯3168只,非法經營額282366.52元,非法獲利76446.52元。陽谷縣法院一審以假冒專利罪判處周某有期徒刑2年,并處罰金5萬元。2000年7月,山東省聊城市中級法院對周某假冒專利案作出終審裁定,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⑩參見程永順主編:《專利侵權判定實務》,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47-352頁。雖然這是不允許的類推,但這也反映了來自司法實踐的聲音。
(三)適用其他方法不足以抑制這種行為
學界有人認為對于專利侵權行為,“我們完全可以用民事責任代替刑事責任”,?劉憲權、吳允鋒:《假冒專利罪客觀行為的界定與刑法完善》,載《華東政法學院學報》2006年第1期。“用民事法律手段足以解決解決問題”,?劉平:《對假冒專利罪的澄清》,載《河北法學》2004年第11期。“受害人所受到的損害,完全可以通過民事賠償方式予以填平”。?楊春然、胡乾坤、陳一凡:《論假冒專利罪的客觀要件》,載《山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期。這種觀點完全是脫離現實的。實踐中專利侵權行為作為民事訴訟,權利人作為原告提起訴訟要承擔舉證的責任(方法專利除外,其對侵權證明實行舉證責任倒置),而作為私權利主體的專利權人在取侵權方面的證據上存在著非常大的困難,專利權人承擔著很大的敗訴風險。既使對侵權行為能夠證明,賠償數額的證明在實踐中也是幾乎不可能的。我國現行專利制度對侵權賠償實際三種方式:首先是權利人受到的損失;其次是侵權人獲得的收益;最后是酌定賠償。對于權利人受到的損失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新產品或新方法的預期市場份額,而此是不確定的,故難以證明。而對于侵權人因此的獲益由于最重要的證據財務憑證在侵權人手中,權利人很難獲得,既使獲得也很難保證真實性。而且無論所受損失和對方獲益都必須證明與專利之間的因果關系,這也是作為專利權人取證非常因困難的地方。最后只能由法庭進行酌定了,這個數額可能遠遠比不上侵權人的獲利或權利人的損失。如果侵權的成本遠遠小于侵權的獲利,這就不可能使人抵擋侵權的誘惑,不可能抑制侵權行為。因而有必有動用公權力來彌補這種不足(刑事偵查機關有證據獲得能力上明顯強勢),用刑罰來強化專利權的效力,增強侵權人的成本,讓刑法成為保護權專利權的最后一道防線。
(四)關于域外經立法經驗的影響
反對專利侵權行為犯罪化的學者多半會提到國外的立法經驗,如有的學者談到:世界上絕大多數(或許多)國家也沒有將專利侵權行為犯罪化,少數國家,如德國、法國等雖然將專侵權行為規定為犯罪,但實際上也是備而不用。國際上,對專利侵權行為是否犯罪化有兩種態度,這兩種態度又分屬于兩大法系,英美法系一般不將專利侵權行為作犯罪處理;大陸法系都將其作為犯罪處理。?參見于阜民:《專利權刑事保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3頁。有的學者可能指出德國對此規定基本“備而不用”,但是還是需要“備”的。而且我們還發現在二戰后發展的比較快的國家都規定了比較完善的專利權保護制度,對專利侵權行為都予以犯罪化處理。如在戰爭中受到極大破壞的日本、德國以及我國臺灣,這些經驗表明在經濟中處于落后地位的國家,為了實現國家主導的經濟發展對專利侵權行為作犯罪處理是有益的,而不是有害。雖然英美法系不作為犯罪化處理,但是中國的法律理論與大陸法系更相近,而且中國的現實情況更需要對此作犯罪處理。正如有的學者所說,“在英美法系國家中,知識產權所有人擁有較強的知識產權意識,人民普遍尊重知識產權。這個國家的各類行業協會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發揮著巨大的規范作用,人們一般不會輕易地去冒侵犯他人知識產權的風險”,“自然無需公權力的界入,以上這些因素恰恰是上前我國所缺乏的,這種國情的差缺,使我國暫時不適宜采取英美法系國家的做法”。?前引⑦。
(作者單位:山東舜天律師事務所)
責任編校:王文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