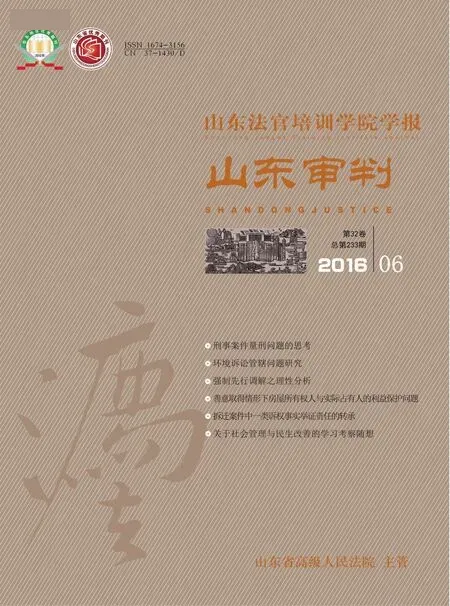侵權人是否應賠償受害人未繳納的社會保險損失
●于金強
侵權人是否應賠償受害人未繳納的社會保險損失
●于金強
企業職工因第三人侵權受到損害,因工受傷或非因工受傷,職工住院治療,并需要一定的休養期限,此即為侵權法中的誤工期限。此時,職工無法到單位上班,用人單位以職員未到單位上班為由拒絕為職工繳納社會保險,職工可否要求侵權人賠償該損失?實務中做法不一,本文擬從保險法和侵權責任法角度進行分析。
一、保險法之分析-繳納社會保險是義務也是法定權利,不能放棄
(一)繳納社會保險義務之定性—法定義務
1.繳納社會保險是行政法律關系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72條規定:“…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必須依法參加社會保險,繳納社會保險費。”《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第60條第1款規定:“用人單位應當自行申報、按時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非因不可抗力等法定事由不得緩繳、減免。職工應當繳納的社會保險費由用人單位代扣代繳,用人單位應當按月將繳納社會保險費的明細情況告知本人。”根據《社會保險法》第63條的規定,不繳納社會保險面臨著法律制裁,補交社會保險并繳納滯納金。用人單位向國家社會保障部門繳納社會保險費用,是一種公法上的行政法律關系,不是私法上的私主體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①王林清:《勞動爭議和裁訴標準與規范》,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707頁。因此,用人單位為職工繳納社會保險是法定義務。
2.自實際用工之日起產生繳納義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16條規定:“勞動合同是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確立勞動關系、明確雙方權利和義務的協議。建立勞動關系應當訂立勞動合同。”第19條規定:“勞動合同應該以書面形式訂立。”從勞動法的規定來看,勞動關系的建立僅要求訂立書面勞動合同。這在理論界和實務界均產生了爭議,這樣,就使得沒有訂立書面勞動合同而形成的事實勞動關系中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護②駱怡惠:《用工與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關系及其法律適用》,載《重慶科技學院學報》2012年第22期。。之后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厘清了建立勞動關系和訂立勞動合同的關系。建立勞動關系的標準是“用工”而非簽訂書面勞動合同。該法第七條規定,用人單位自用工之日起即與勞動者建立勞動關系。該法第十條規定,建立勞動關系,應當訂立書面勞動合同。已建立勞動關系,未同時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應當自用工之日起一個月內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在用工前訂立勞動合同的,勞動關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該法明確了建立勞動關系的標準即“用工”。關于“用工”理論上有控制說和使用說之爭。控制說認為,用工是指勞動者已將其勞動力使用權轉讓給用人單位或者說用人單位對勞動者的勞動力已取得使用權。③王全興:《勞動法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75頁。筆者贊同“使用說”,此處的“用工”應理解為“實際用工”,即實際使用勞動力,而不是其他。如果從“控制說”的角度理解“用工”則又重新回到《勞動法》規定的老路上,不利于勞動者利益的保護。
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系后,用人單位應當為勞動者繳納社會保險。《社會保險法》第58條規定“用人單位應當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內為其職工向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申請辦理社會保險登記。未辦理社會保險登記的,由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核定其應當繳納的社會保險費。”
3.繳納社會保險與實際用工的適度分離——非因法定事由不得停交社會保險
建立勞動關系后,從社會保險的實務操作來看,社會保險是按月繳納,該月勞動者即使是提供了一天的勞動,用人單位也應當為其繳納當月社會保險。
另外,用人單位在法律規定的醫療期內均應為其發放工資并繳納社會保險。《山東省工資支付規定》第26條規定,勞動者因工負傷或者患職業病的,企業應當按照《工傷保險條例》的規定,支付勞動者停工留薪期間的工資。勞動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負傷,在國家規定的醫療期內的,企業應當按照國家和省有關規定支付病假工資或者疾病救濟費,病假工資或者疾病救濟費不得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80%。《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列為甲類的傳染病,以及雖未列為甲類傳染病,但按照甲類傳染病進行防治的傳染病的疑似病人及密切接觸者,經隔離觀察或者留驗排除是病人的,企業應當按照勞動者提供正常勞動時的標準支付其被隔離觀察或者留驗期間的工資。
根據上述法律規定,法定醫療期間的工資不能停發。舉重以明輕,法定醫療期間工資尚不能停發,社會保險就更不能不繳納。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法定醫療期滿勞動者仍不到單位上班,用人單位應當采取相應的措施解除與勞動者的勞動關系。因為勞動關系已經自實際用工之日建立勞動關系,用人單位若不采取相應措施,仍然要承擔繳納社會保險的義務。
(二)繳納社會保險之再定性-法定權利
從權利角度而言,出現工傷事故時繳納社會保險的企業會降低經營風險。一個企業若發生一起工傷事故,但企業未為職工繳納社會保險,此時,對企業而言就可能是一個致命的打擊。繳納社會保險,對勞動者而言,會使自己的合法權益得到保障。
因此,社會保險的繳納關系到實質正義和形式正義的實現。法律的價值在于實現正義。烏爾比安認為,法律與完善的公道和正義是相似的,公道和正義是法律的目的,并且是它的準繩。法律的正義可分為形式正義和實質正義。形式正義又稱程序正義、訴訟正義,即嚴格按照法律程序辦案,它著眼于形式和手段的正義性;實質正義是指法律必須符合自然法和人的理性,它著眼于內容和目的的正義性。當職工發生因工受傷,則會出現作為個體的勞動者的實質正義能否實現,即其合法權利能否得到法律支持。法學界對形式正義和實質正義的地位爭論頗多,但對于社會個體而言,實質正義的意義顯然要大于形式正義。當勞動者發生工傷事故,因為繳納了社會保險,勞動者的權益更加有保障,用人單位的風險也會降到最低。因此,筆者將為勞動者繳納社會保險的義務定性為企業的法定權利或社會權利。此權利具有法定性,事關企業經營風險的降低和勞動者權益的保障,企業不能放棄該權利。
二、侵權法之分析-損失法定化,法律沒有規定者不能得到賠償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119條規定的侵權責任賠償范圍為醫療費、因誤工減少的收入、殘廢者生活補助費等費用;造成死亡的,應當支付喪葬費、死者生前扶養的人必要的生活費等費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17條規定的賠償范圍為醫療費、誤工費、護理費、交通費、住宿費、住院伙食補助費、必要的營養費,殘疾賠償金、殘疾輔助器具費、被扶養人生活費,以及因康復護理、繼續治療實際發生的必要的康復費、護理費、后續治療費、賠償喪葬費、被扶養人生活費、死亡補償費以及受害人親屬辦理喪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費、住宿費和誤工損失等其他合理費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16規定的賠償范圍為醫療費、護理費、交通費等為治療和康復支出的合理費用,以及因誤工減少的收入。造成殘疾的,還應當賠償殘疾生活輔助具費和殘疾賠償金。造成死亡的,還應當賠償喪葬費和死亡賠償金。上述法律規定均未規定未繳社會保險的損失。與此相近的概念是誤工費,《<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條文理解與適用》對誤工費進行了定義,是指受害人因遭受人身損害,不能正常工作而遭受的預期財產損失。④奚曉明:《<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條文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130頁。《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20條規定,誤工費根據受害人的誤工時間和收入確定,但并沒有涵蓋單位未繳社會保險的損失。
據此,有人認為,未繳納社會保險的損失應該得到賠償。因為在民法領域法無明文禁止則為權利,故受害人可要求侵權人承擔該損失。筆者認為,此種觀點是錯誤的。
1.權利與損失之間并非一一對應關系,在純粹經濟損失情形下的損失沒有權利相對應
純經濟損失又稱為間接損失,學理上也稱為對第三人的損害。由于純粹經濟損失常常表現為一種費用上損失,純粹經濟損失也被認為是因對原告的人身和有形財產造成的實際損害而產生的費用損失。⑤王利明:《侵權行為法研究》(上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69頁。我國的《侵權責任法》也認可純粹經濟損失的概念,該法第二條采用了民事權益的概念。民事權益包括人身法益和財產法益,如商業秘密、純粹經濟利益。⑥前引④,第20頁。特定條件下純粹經濟損失應該得到保護。因此,從純粹經濟損失的角度分析,權利與損失是分開的,權利與損失并不一一對應。對此,有學者認為,純粹經濟損失橫跨合同與侵權領域,對傳統的民事責任體系提出了重大挑戰。在純粹經濟損失賠償的問題上,首先應解決的是權利保護與純粹經濟損失之間的關系,以及權利損害與義務違反之間的關系。研究表明,權利的保護和損害賠償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裂隙,權利并不能決定財產損失是否屬于純經濟損失。因此,通過權利損害來界定可賠償的經濟損失的范圍,其作用相當有限,侵權法應更多地關注行為與損害之間的關系,從義務違反的角度整理侵權法。⑦梅夏英:《侵權法一般條款與純粹經濟損失的責任限制》,載《中州學刊》2009年第4期。因此,法無明文禁止則為權利的觀點僅僅是一種樸素的觀點,經不起推敲。
2.法律沒有規定該項損失可以得到賠償,則原告的訴求沒有請求權基礎
所謂請求權基礎,是指得一方當事人(原告),向他方當事人(被告),有所請求的法律依據。⑧王澤鑒:《請求權基礎、法學方法論與民法發展》,載百度文庫(http://wenku.baidu.com)。筆者認為,根據王澤鑒先生關于請求權基礎的理論,沒有法律規定該項損失可以得到賠償沒有法律依據,原告的訴求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因此,如果法律對該項損失沒有規定,原告的該訴求是不能得到法院支持的。
3.從司法“三段論”理論上講,沒有法律規定也就無法做出有利于原告的判決
“三段論”是邏輯學上的概念,后被引入司法領域,即“司法三段論”。所謂司法三段論,是指以法律規范為大前提,以具體的案件事實為小前提,將小前提與大前提結合起來,則得出結論,即判決。由此可見,如果法律沒有規定,則缺乏了大前提,也無法做出有利于主張人的判決。因此,一般情況下,法律沒有規定的損失是不能得到法院支持的,即損害法定化。從積極意義上來看,權利主張的增多有利于公民法律素質的提升、社會法律意識的增強,況且日新月異的科學技術和日漸稀缺的自然資源也在客觀上催生了新的法益,其中蘊含了法定權利的前身,使新型權利主張的出現成為必然。但從實證法角度看,并不是任何物質利益和人格利益都能被稱為權利,也不是任何主觀訴求都能借權利之名調動法律的強制力量,法律保護的權利是經過抽象處理的類型化利益,而不是主觀化的隨性要求。⑨刁芳遠:《新型權利主張及其法定化的條件—以我國社會轉型為背景》,載《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5年第三期。王利明先生也持此種觀點,他認為,“從原則上說,在法定損害賠償制度之下,只有符合法律規定的損害類型的損害,才得獲得補救…”。⑩前引⑤,第370頁。我國關于債權責任法的立法及司法解釋中沒有規定未繳納社會保險的損失可以得到賠償,根據損害法定化的理論,該損失是得不到法院支持的。
三、結論
綜合以上分析,對于未繳納社會保險的損失,在法定醫療期內用人單位不能拒繳,若拒繳應由用人單位承擔法律責任而不能要求侵權人賠償。同時,法律沒有明確規定未繳納社會保險的損失可以得到賠償,在采取損害法定化的立法例時該主張是不能得到法院支持的。
(作者單位:諸城市人民法院)
責任編校: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