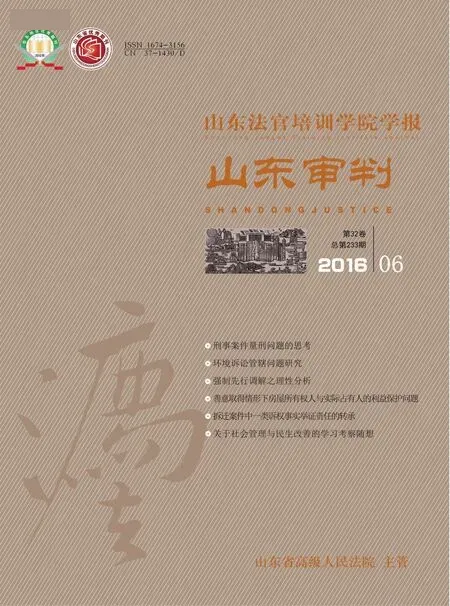從電影《定罪》說起
●胡科剛
從電影《定罪》說起
●胡科剛
影片《定罪》是一部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美國電影,講述了女主人公貝蒂以一己之力對抗強大的司法體系,克服重重困難最終為蒙冤入獄18年的哥哥洗脫罪名的感人故事。
案件發生于上世紀80年代初美國馬薩諸塞州的一個小鎮,一名女性被殘忍地殺害在家中,家里的財物被洗劫。她的鄰居,肯尼?沃特——從小就名聲不佳的小混混,被視為犯罪嫌疑人,在1983年被陪審團裁定罪名成立,判處終身監禁。肯尼的妹妹貝蒂堅信哥哥是無辜的,決心為他伸冤。作為一個高中輟學在酒吧打工的兩個孩子的母親,貝蒂不惜犧牲青春和家庭,捧起書本從頭開始學習法律,通過不懈努力終于拿到了法學學士學位并最終獲得律師資格。通過和一個致力于推翻冤假錯案的非盈利性組織“無辜者計劃”的合作,貝蒂與合作者運用DNA檢查這種新科學證據——案發時美國還沒有DNA檢測,只有血型檢查輔助定罪,以及對證人做偽證的調查,最終使肯尼的冤案昭雪了。肯尼入獄服刑18年后,終于在2001年被無罪釋放重獲自由。
在調查案件過程中貝蒂屢屢受挫:親人的不理解和絕望讓她忍不住痛哭,本應是正義化身的警察內心卻隱藏著陰暗,代表著公正的司法機關拒絕承認錯誤,當年幫助警察作偽證的證人怕受法律追究不肯站出來……但是不論過程有多艱難,她都毫無畏懼、毫不退縮地為哥哥的清白和自由,努力還原辦案過程的真相。貝蒂十幾年的努力沒有白費,她有幸得到大量的“天助”:幸好馬薩諸塞州沒有死刑,否則她哥哥不會活著等到被平反的那一天;DNA檢測技術誕生,“無辜者計劃”項目組織利用該技術為蒙冤者翻案提供援助;按規定本應過期銷毀的關鍵證物在貝蒂的堅持下僥幸重新找到……
貝蒂看起來是偏執的,同時也是偉大的,在這場別人都不看好的孤身奮戰中,她以頑強的意志和不屈不撓的精神戰勝了孤獨,戰勝了別人的質疑,甚至戰勝了鐵面無情的法律。現實中的“貝蒂”現居住于美國的新英格蘭,繼續幫助那些被錯判的犯人爭取公正的審判和自由,并為監獄的犯人爭取應有的人身權利。
從電影中,我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相對于一個龐大的國家法律運行體系,個人的力量是很渺小的。要不是新技術的誕生、別人的無私幫助和一些巧合事情的發生,此冤案是斷不可能翻轉的。也正因如此,貝蒂感同身受,所以她一直在幫助那些被錯判的犯人爭取自由。
一個妹妹為了證明坐冤獄的哥哥是清白的,不惜放棄自己的生活和家庭,頂著被別人嘲笑的壓力去上法學院,千辛萬苦考取律師資格證,親自調查當年的兇殺案,歷經18年,最終還哥哥以自由。正是為了親情,為了她心中的堅持,她一直走在討還公正的路上。她值得我們敬仰,我們可以說她是英雄。
在法律的實踐過程中,囿于辦案者的思想偏見,科學技術的限定,還有千變萬化的現實狀況等等,有些冤案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客觀上我們知道這種情形會一直存在,但在心理上承認這種現實的存在對我們是一種折磨。
法律作為一種強制性秩序,在規范社會行為方面是不可或缺的。但人們之所以推崇貝蒂的這種行為,正如思想家柏拉圖所說,“人類對于不公正的行為加以指責,并非因為他們愿意做出這種行為,而是惟恐自己會成為這種行為的犧牲者。”我們害怕有一天這種冤案會發生在自己身上,我們害怕自己成為“犧牲品”。人們都有趨利避害的自我預防心理,所以每每發生一起冤案,媒體在報道時,都能激起人們內心的憤慨,我們痛恨冤案這種心理也就不難理解了。
一部影片,如果僅僅從法律上來分析,來看待,未免無趣。人們熱愛生活,是因為對生活充滿期望,相信未來會有美好的事情發生。有人說,《定罪》可以當一部勵志片來看,這無可置疑。一個沒有文化、沒有地位的小人物,通過自己的不懈努力,最終實現了她的正義訴求。但我們也要反思,除了貝蒂的堅持不懈,我們更需要一個公正公信并能夠不斷矯正的司法體系。
今天,法律隨著社會生活的變化而適時地變動著,法律治理的相對穩定性使人們對生活有了預見性,這對于國家治理當然是好事。但現在我們也往往發現,在某些時候,有部分人喪失了對法律的心理認同,而采取對法律視而不見的態度,這對社會治理來說是一種挑戰。
一個荒謬的誤判,在圍墻中一呆就是18年,從絕望到有希望,希望破滅,再從絕望中走出來,當肯尼被打開手銬,說道“就這樣了”。簡簡單單的一句話,包含了多少意蘊在里面。在法律的框架內,貝蒂作為一名女性,通過個人的努力,通過個人的堅持,通過個人的不斷成長,她柔弱的社會性別角色與強制的國家秩序工具的一弱一強的對決,以弱勝強的強烈結局反差更讓人震撼。
天空中并不是每天都有太陽,有時候也有陰云。當生活中我們遇到了挫折與坎坷,透過貝蒂的故事,我們更應該堅守信念,通過堅強不屈的抗爭,去創造屬于我們的美好生活。
(作者單位:日照市中級人民法院)
責任編校:范岱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