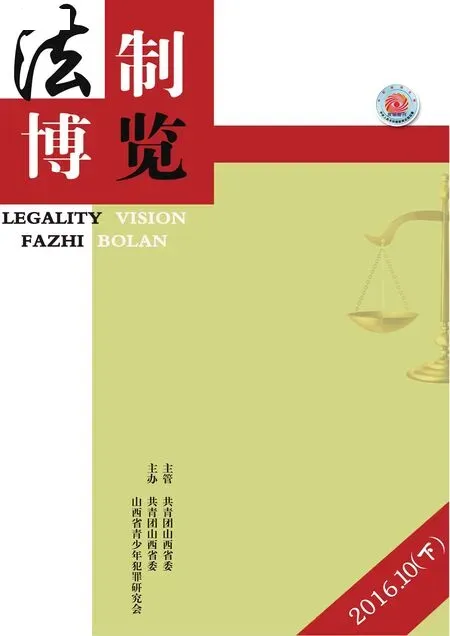為何要為民間投資松綁
王稚禎
中共重慶市沙坪壩區委黨校,重慶 400038
?
為何要為民間投資松綁
王稚禎
中共重慶市沙坪壩區委黨校,重慶400038
我國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時間還不長,出現的種種問題,必然伴隨著體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場經濟的完善,不斷得到解決。在這個過程中,最關鍵的是要堅定不移地走全面深化改革之路,加快清除市場準入的阻礙,打破競爭性行業的壟斷,建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完善民間資本的退出機制,依法平等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
民間投資;松綁;供給側
近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對各地促進民間投資政策落實情況開展專項督查,并委托相關單位組織開展第三方評估。
今年4月15日,國家統計局公布了我國第一季度國民經濟的運行情況。數據顯示,在第一季度中,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158526億元,同比增長了6.7%,整體運行平穩,結構優化。雖然還面臨不少不確定性,但中國經濟具有較長時間內保持中高速增長的潛力和條件。
十三五目標中,我國經濟年均增長率需保持在6.5%以上,2016年的年經濟增長目標在6.5%-7%的范圍內,即是說6.7%的增速雖然低于去年一季度的7%,也低于去年的年均增長6.9%,但依然在合理區間內。
我國的經濟發展形勢較好,但一些已經開始呈現的問題也不能忽視,比如在第一季度,我國的國定資產投資增長了10.7%,成為了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但是在增長的固定資產投資中,絕大部分是國有資本主導的投資,民間投資只增加了5.7%,而在去年,這一數據為10.1%.。特別是3月的固定資產投資中,民間固定資產投資比去年同期反而降低了3%。而事實上,在第一季度,民間投資整體都出現了十分明顯的下滑,這清晰的反映出民企生存環境并沒能獲得改善,甚至在向壞發展,已一定程度上拖累了我國經濟的反彈性增長。
單從大數據上就可以看出,民間資本的投資環境和形式并不樂觀,于是這樣的專項督查對此就顯得更加重要。當前一些地方確實還存在著民間資本“進不去”“動不了”等問題,甚至在極個別的地方問題還比較嚴重,這些困難都迫切地需要政府落實政策加以破解。
先說“進不去”。2010年,國務院出臺了《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即“新36條”,相關部委后來又相繼發布了實施細則。這些政策文件明確提出,支持民間資本進入基礎設施、社會事業、金融服務甚至國防科工等領域。但實際情況是,政府部門對一些領域的投資準入依然實行嚴格的前置審批和“牌照管制”,民間資本只能望洋興嘆,“玻璃門”并沒有真正打破。
事實上,一直以來,由政府把控的資源類和交通運輸類等行業中,民間資本一直難以進入。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但隱形的玻璃門、高門檻又確實存在著,盤根錯節的政商關系和屢見不鮮的利益交換導致民間資本與政府資本互不流通,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資源的優化配置,不利于經濟的健康發展。
退一步說,即便是民間資本真的成功地進入了某個行業,但在經營過程中要想立定站穩、發展壯大也很不容易。
以融資為例,任何一個企業在經營發展中往往需要通過資金的支持,而民間資本首先在“融資難”方面的處境就沒有得到有效的改善。國有商業銀行因風險控制和降低成本的需要,往往對民間資本“惜貸”,而上市融資之路對一般的民間資本而言又“高不可攀”。于是資金問題,就成了一個限制民營企業發展壯大的大問題。
就目前來說,我國的金融資源更多是向國有部門傾斜著,央企和國企的投資占據整個GDP一半以上的比重,這就導致中國經濟穩增長的重任,很大程度上落在了他們的身上。然而,當我國經濟發展再次露出疲態之時,僅靠央企和國企,特別是在其中有一部分企業生產經營效率不高的情況下,顯然是無法做到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借助民間資本的力量來刺激經濟持續增長已是勢在必行。
民間投資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力量,放寬行業的準入標準,打破玻璃門,讓民間資本能夠公平的參與到市場競爭中來,是目前刺激經濟增長所應該采取的重要手段。
長期以來,我國實行著寬松的貨幣政策來釋放經濟增長放緩的壓力,這種做法是合理的,新華社也表示我國會繼續使用這樣的方針直到經濟增長動力完全恢復。但政策寬松并不代表新一輪大規模刺激經濟的措施的到來,事實上,短期的刺激很有可能造成經濟發展的長期失衡。2008年全球經融危機爆發后,為阻止國內經濟放緩,在廉價貨幣政策的推動下,政府投資和房地產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大幅上升,使通脹水平迅速超過此前2003年和2007年時的最高水平。
類似的貨幣政策,美聯儲、歐央行、日本央行其實在遇到經濟危機時,大都會采用,造成的結果無一是一輪又一輪的資產泡沫,更將經濟復蘇的周期人為的拉長,讓經濟資源處于空前的整體錯配當中。特別是我國金融資源向國有部門傾斜之后,造成的影響就更大一些。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和國企部門加杠桿,更多的往往是加在了那些運轉效率不高的企業身上,直接的結果大多是在加劇國內產能過剩的同時,又增加了我國的債務風險。當經濟資源大部分被低能低效的企業所裹挾時,那些具有生產效率的企業往往還會被“擠出”,就如第一季度的民間資本投資減少一般。在供給側改革的大背景下,對運轉效率和經濟效益不高的企業本就提出了去產能的要求,再一味的對低效企業加大投資,就與初衷背道而馳,更不利于我國經濟的發展。
我國的金融市場目前尚未完全開放,針對地方和
企業的債務問題,政府的可操作空間很大,甚至在極端條件下,政府可將地方和重要央企、國企的債務轉移到自己的資產負債表上,以緩解企業的債務風險。但這樣的解決辦法無異于飲鴆止渴,不僅會讓原本失去競爭力,應該被市場淘汰掉的低效企業和對于它們的投資更加有恃無恐,也讓供給側改革成為空談。長此以往,也就讓貨幣政策失去了應該具有的調節作用,對人民幣的匯率造成不利影響。
要解決好上述問題,絕非一日之功。我國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時間還不長,出現的這些問題,必然伴隨著體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場經濟的完善,不斷得到解決。在這個過程中,最關鍵的是要堅定不移地走全面深化改革之路,通過加快清除市場準入的阻礙,打破競爭性行業的壟斷,建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完善民間資本的退出機制,依法平等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等途徑,不斷為民間資本“松綁”,激發其內在動力和創造力,真正讓民間資本成為推動中國經濟行穩致遠的強大引擎。
[1]佚名.進一步為民間投資“松綁”[N].經濟日報,2016-5-26.
[2]邱小敏.中央出臺政策為民間投資“松綁開路”[EB/OL].新華網,2013-9-6.
F832.4
A
2095-4379-(2016)30-0192-02
王稚禎(1991-),女,漢族,四川通江人,學士,中共重慶市沙坪壩區委黨校,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