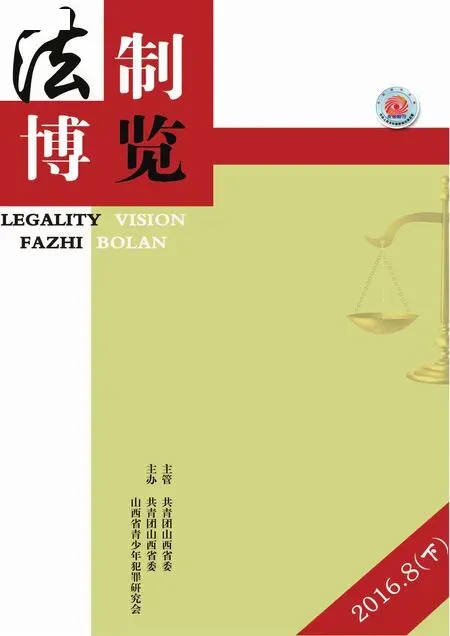淺談我國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及其完善
吳 碩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北京 100191
?
淺談我國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及其完善
吳碩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北京100191
摘要:我國的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自2012年《刑事訴訟法》確立以來,在實踐中取得良好效果,為未成年犯罪人提供重返社會的機會。但同時由于制度初步建立,其中還存在很多的漏洞,本文提出該制度適用的現實困境,并且針對案件范圍、啟動主體、查詢權等重點問題提出合理化建議。最終明確該制度在我國應當逐步完成由“封存”向“消滅”的過渡,使得立法目的得到充分實現。
關鍵詞: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消滅;完善
一、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概念及由來
“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是指對于判處輕罪的未成年人的犯罪記錄應當予以密封保存,除法律特別規定外,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查詢。”基于這一概念,犯罪記錄封存只是對于犯罪記錄的掩蓋,并沒有完全消失,這就是是在未成年犯罪人重返社會過程中的一顆定時炸彈,不知何時會成為阻礙其改過自新的障礙。因此,筆者認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只是一種特殊的檔案封存制度,排除法律規定情形外的查閱權,不可以稱為是有條件的犯罪記錄消除制度。
這一制度源于貫穿中國古今的“恤幼”思想。我國的《刑事訴訟法》在發展的過程中逐漸加入了這種思想,從而形成了如今法律中對未成年犯罪人的“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及“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事實上,在2012年的《刑事訴訟法》出臺之前,一些地方的司法機關已經開始嘗試在處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時采取前科消除制度,維護未成年犯罪人的合法權益。2003年,石家莊市的司法機關首次提出了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除制度,之后其他的省市如云南、山東、貴州等也在處理案件時紛紛效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因此,我國的《刑事訴訟法》明確的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是基于地方的立法和司法實踐的之上而形成的,是一個將地方性法規上升為國家統一的法律規則的過程。
二、我國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現實困境
(一)封存犯罪記錄的案件范圍具有局限性
針對犯罪記錄封存的案件范圍,《刑事訴訟法》規定“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中又明確將“免除刑事處罰”的未成年人納入其中;《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由在此基礎上增加了“做出不起訴決定”的情形。
筆者關注到的一個問題就是未成年人的違法記錄是否也應當封存。2013年“李某案”反映出違法記錄的存在對于一個未成年人發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使得建立未成年人違法記錄封存制度的呼聲越來越高。此外,我國實行的犯罪記錄封存是“輕罪”犯罪記錄封存,明確作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限定,筆者認為我國法律中之所以規定了這一刑期限定條件,是希望通過刑期的多少決定是否采取相應的措施,其目的是確定其社會危險性低,再犯罪的可能性較小,法律賦予他們一個悔過的機會。但是這可能會與制度設計的初衷存在一定的偏差,難以真正實現制度目的。單純以判處刑罰的多少來決定是否采取犯罪記錄封存的措施確實存在一定的問題。
(二)現實操作存在困難
提到犯罪記錄封存,筆者首先想到的是在實踐中如何操作的問題。在《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中簡單規定了建立專門的未成年人犯罪檔案庫,分冊裝訂,加密保存等方式。但是從這樣的規定中我們還是難以了解到現實中的操作是如何進行的。特別是隨著科技的發展,案件的信息并不僅僅存在于紙面的案卷材料之中,更多的情況下是以電子信息的方式存在于專門的辦案系統之中,這樣僅僅規定對于卷宗等書面材料的封存還是存在欠缺的。此外,對于一個刑事案件來說,從立案、偵查、起訴到審判的各個程序中涉及到的人員較多,如何保證公檢法機關工作人員對于案件信息予以保密也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
(三)具有查詢權的主體不明確
有權對被封存的犯罪記錄進行查詢的主體被明確為辦案需要的司法機關和國家規定的單位。這兩類查詢主體在法律并沒有更加詳細的規定,特別是對于單位來說,籠統地說是法律規定的單位還是不能確定具體是哪些。在實踐中很多用人單位在招聘的時候會關注應聘者是否有違法犯罪記錄,其實從立法目的上來看,用人單位應該是不被包含在具有查詢權的主體之中的,但是由于法律規定的不明確可能會使得檢察院在做出同意決定時無法可依。
三、我國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完善
基于上述的探討,在2012年《刑事訴訟法》頒布之后這一制度在立法和實踐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制度的剛剛建立,其中還存在很多的漏洞,還需要在不斷的探索中予以完善。
(一)進一步明確擴大犯罪記錄封存的案件范圍
我國犯罪記錄封存限定的范圍過于狹小,“被判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限定條件與制度目的之間相違背。由于犯罪記錄封存制度設置的目的是保護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幫助未成年人重新走上社會,實現人生目標,因而將罪行輕重、社會危險性等條件作為限定條件不符合立法目的,且《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這樣的國際準則中也沒有區分輕罪和重罪。因此,我國在設定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的案件范圍時應當逐步全面放開,一步步實現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全面封存的目標。
對于違法行為是否可以適用記錄封存制度,筆者尊重多數學者的觀點,即根據“舉重以明輕”的原則,既然犯罪記錄已經依法被封存,那么比犯罪更輕的違法行為理應依法被封存。
(二)建立切實可行的犯罪記錄封存實施機制
1.增加犯罪記錄封存程序的啟動方式
從目前我國的法律規定來看,犯罪記錄封存程序的啟動是由人民檢察院依職權決定的。筆者認為當前單純的依職權模式是基于我國目前犯罪記錄封存條件的確定性和對效率的追求。但是將啟動程序的主體完全限定在檢察院可能會出現疏漏,因此應當增加依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申請啟動程序的情形,使得未成年人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維護自身權利。
2.根據現實狀況采取封存措施
基于目前我國司法機關處理案件的實際狀況,在進行案件封存的過程中應當特別注意保密,防止案件信息的泄露。特別是在互聯網日益發達的今天,對于辦案系統中或者電腦中的案件記錄也同樣應當予以封存,而不能僅僅注重卷宗這樣的紙質材料的保密。因為電子信息的傳播速度更快、涉及的范圍更廣,一旦信息泄露可能會造成難以挽回的后果。
3.設立案件信息泄露的處罰機制
一起刑事案件涉及到的人員較多,盡管在法律中明確規定了相關人員的保密義務,但是如果沒有相對應的處罰措施也會使得保密義務的規定形同虛設。嚴格的處罰措施對于相關的辦案人員具有一定的威懾作用,從而促使相應人員更加重視案件信息的保密。
4.明確限制查詢主體的范圍
筆者對于司法機關基于辦案需要的查詢權沒有異議,但是對有關單位這一主體的定位存在質疑。《刑事訴訟法》中直接指向其他法律的規定,不具有完整性。因此,針對這一問題,立法者可以考慮制定專門的法條明確查詢主體,這樣不僅司法機關在適用時更加便利、明確,而且未成年人也可以更加了解自身具有的權利。
(三)逐步推行有條件的犯罪記錄消滅制度
“封存還是消滅”一直是學界在探討犯罪記錄封存制度時的爭議焦點,由于自2003年開始各地方法院嘗試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滅制度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而如今《刑事訴訟法》正式建立的卻是犯罪記錄封存制度,這與眾多學者起初的期待有所不同。從國外的相關制度來看,多數國家堅持的是一種犯罪記錄清除制度,充分給予未成年人忘記過去、重新開始的機會。但是筆者認為基于我國目前的司法現狀,規定全面的犯罪記錄消除制度可能還存在著一定的難度,“封存”向“消滅”轉變還是需要經歷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我國可以嘗試規定一個期限,在這一期限中對未成年人進行考察和教育,如果期限屆滿符合消除記錄的要求,沒有社會危險性、悔罪態度較好,則人民檢察院應當依法消除犯罪記錄。但應當明確的是,全面的犯罪記錄消滅制度是我國未成年人刑事程序最終追求的目標,從而實現這一制度的設立初衷。
四、結語
由于目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頻發,犯罪記錄封存制度應當進一步予以完善才能適應如今的現實情況。針對這一制度,筆者認為應當從案件范圍、程序啟動方式、處罰機制、查詢權等方面予以改進,從而逐漸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此外,我國立法者應當考慮逐漸從犯罪記錄“封存”向“消滅”轉變,為走上違法犯罪道路的未成年人提供改過自新、重新做人的機會。
[參考文獻]
[1]陳光中主編.刑事訴訟法(第五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431-432.
[2]王海東.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中國實踐:適用與走向[J].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19(5):125-132.
[3]民主與法制網.犯罪記錄:“封存”還是“消滅”[EB/OL].http://www.mzyfz.com/html/1855/2014-02-17/content-962087.html,2015-12-27.
[4]孟斌.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可操作性完善——基于實踐操作的體系性反思[J].法律適用.2015,5:106-110.
[5]丁俊濤.淺析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存在的問題[J].法制博覽,2015,09:196-198.
中圖分類號:D924.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4379-(2016)24-0099-02
作者簡介:吳碩(1992-),女,天津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