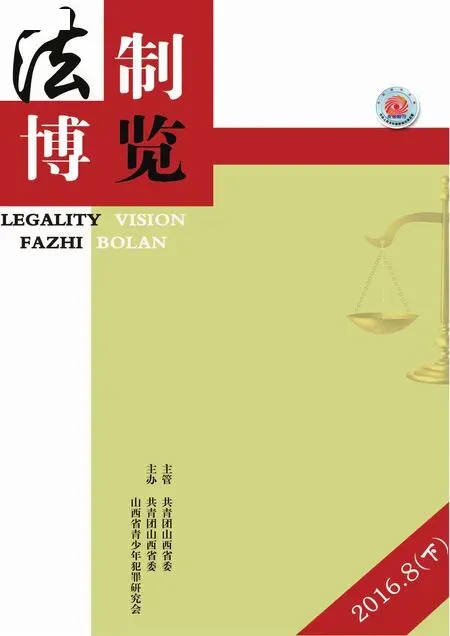論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罪
童 謠
廣西民族大學,廣西 南寧 530006
?
論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罪
童謠
廣西民族大學,廣西南寧530006
摘要:對于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原《刑法》第241條第6款存在著各種缺陷,并且隨著社會發展,弊端也越發的明顯。《刑法修正案(九)》對該條款作出了修正,使其與刑法基本原則、立法目的相符合,并且順應社會發展的需要。盡管該新修條款的諸多方面都值得肯定,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需要進一步區分婦女、兒童的收買來源;區分適用從輕或減輕處罰的條件,并且還需擴大上述兩種情節的適用范圍。
關鍵詞:《刑法修正案(九)》;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罪;完善
1997年《刑法》第241條的“但書”規定對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罪存在諸多不合理的地方,該條款規定了收買犯罪可不追究刑事責任的情形,與拐賣犯罪大都被判處較重刑罰形成強烈反差。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將人視為商品進行買賣,這種行為不僅嚴重踐踏了被害婦女、兒童的人權,還侵犯了他們的人身自由權,甚至是生命健康權。再者,對于受害家庭帶來的創傷是巨大的也是無法彌補的。
一、新修條款的合理依據
《刑法修正案(九)》對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罪作出修改,刪除了原條文的處罰阻卻事由,一律規定為犯罪,一定程度的彌補了原規定立法缺陷,同時也順應社會發展的趨勢,有效打擊犯罪。
(一)符合刑法基本原則
《刑法修正案(九)》將“一律不追究刑事責任”的規定刪去,取而代之的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那么可以看出,新修規定收買婦女、兒童犯罪一律要追究刑事責任。
此次修改首先符合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則。如所周知,罪刑法定原則依靠犯罪構成理論來支撐,行為人已經實施了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罪成立的所有構成要件行為,此時該行為人的犯罪已經成立,即使行為人之后不阻礙被拐賣婦女、兒童返回原居住地或對兒童沒有虐待行為等情形,也不能成為違法或責任阻卻事由,進而不追究刑事責任。所以嚴格按照法律的規定,其構成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的罪責已經明確存在,所以將此款規定為從輕、減輕情節才是合理的,彌補了原條款與罪刑法定原則相違背的情形。
再者,此次修改亦符合罪刑相適應原則。根據此原則,行為人只要實施了犯罪行為,就要承擔與其相適應責任與刑罰;對于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的行為人,相對于拐賣者來說,其對社會產生的客觀危害性可能較小,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也可能較小,但這完全不能夠成為其免于刑事責任的理由。反而,正因為收買者的存在,才滋生了“賣方市場”,其往往成為拐賣犯罪產生的源頭或者是助長因素。而無論行為人是出于什么樣的目的實施收買行為,將婦女、兒童當作商品進行購買,侵害其人身自由,就已經是對受害者人權尊嚴的一種踐踏,所以對于收買者的犯罪行為不可放縱。那么《刑法修正案(九)》所作的新修改就規定了對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行為要一律追究刑事責任,即加大了處罰力度,從而使符合了罪刑相適應原則。
(二)符合立法的目的
現實中,實施收買行為的人大多是家庭生活拮據甚至是一些殘疾人,希望組建一個完整家庭而收買婦女;還有些家庭可能無法生育但又渴望有個孩子而收買兒童,他們對待收買過來的婦女、兒童甚至都照顧得很好,所以基于這些情形,法官可能就會對買主產生同情,認為其行為并沒有產生很嚴重后果的情況下,會根據“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而選擇對行為人免責處理。最后導致的就是不僅沒有通過立法來威懾潛在的犯罪分子,還可能讓本沒有犯罪意圖的人在看到并沒有多重的刑事代價后而決意去犯罪,那么收買者作為鏈條反應的源頭,必定讓拐賣犯罪更加猖獗。
筆者認為某些法官處理案件時這種盲目而片面的同情買主是將道德與法律混淆了,并且犯罪的增多以及受害者遭受的傷害不利于社會的穩定。而新修條款的頒布,刪去“不追究刑事責任”,其處罰力度的增大,首先就是要告知公眾,這種收買行為就一定是犯罪行為,一旦實施就要承擔刑事責任,即使“不虐待”、“不阻礙”,刑法仍不會姑息這樣的收買犯罪行為。其次,新條款對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的行為人一律追究刑事責任,便是樹立了刑法的權威,從而彌補了本條罪名形同虛設的狀況。這樣的修改亦一定程度能夠避免收買者對逃脫處罰的僥幸心理,讓潛在的犯罪者對收買行為有個利弊衡量,當冒著會被追究刑事責任的風險時,行為人很有可能就會放棄犯罪的念頭。那么刑法對行為人的威懾力便起到了作用,從而預防更多的人犯罪。所以綜上,《刑法修正案(九)》對原《刑法》第241條第6款的修改是符合立法目的的。
(三)符合社會現狀要求
首先犯罪行為日益猖狂。歷年來,司法機關雖然對拐賣犯罪進行嚴厲打擊,其犯罪率的確有所下降。但是“治標不治本”,長期以來作為拐賣犯罪的源頭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的犯罪卻很少被追究刑事責任,往往收買行為在并不嚴厲的判決下,促使更多的潛在犯罪者懷著僥幸去犯罪;而在利益的驅使下,也使更多的拐賣犯罪行為人去鋌而走險;并且隨著拐賣犯罪的惡劣手段也使其他犯罪不斷激增。據媒體報道,有進醫院進行嬰兒盜竊的,當街搶奪的,利用網絡進行拐騙的;還有在對被拐賣兒童運輸過程中或是逼迫婦女就范的過程中,為達目的犯罪人可能會采取強暴手段從而傷害甚至殺害了被害人,這些犯罪都是令人觸目驚心。由此看來,新修條款將對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犯罪一律追究刑事責任是符合社會現狀的,改變一向對收買行為過于溫和的態度,加大對收買者的處罰力度,使其不愿買,不敢買,①這樣從根本上抑制拐賣犯罪。
此外,公眾觀念的改變。社會發展日新月異,普法力度的加強,公眾的態度、視角、價值觀也在隨之改變。近兩年,一些尋人的電視節目以及網絡平臺的推廣,社會公眾對拐賣犯罪越來越重視,隨著我國經濟、文明、法治的發展,更多的公眾有了權利和法制意識,在知曉受害者以及其家庭身心受到巨大創傷的沖擊下,通過各種形式參與到這種反對拐賣犯罪,普法活動,甚至“打拐”行動中。所以“對人販應該判處死刑”以及“對收買者重判”的呼聲也應運而來。所以新修條款對收買者處罰力度的加大,正符合公眾的期許。
二、進路探索
根據以上分析,新頒布的《刑法修正案(九)》彌補了《刑法》第241條第6款一些缺陷。但是,新修條款的頒布還是存在一定局限性的,所以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罪的新規定并非終點,我們可以進一步探索。
(一)區分兒童收買來源
兒童收買來源的差異反應映了行為人主觀惡性的大小,那么量刑也應該有所不同。目前收買來源大致兩種方式,一是從無監護權的主體處收買,二是從有監護權的主體處收買。同樣是收買行為,顯然前者的主觀惡性更大。從無監護權主體處收買兒童,收買者不問兒童出處,甚至可能明知對方是人販子,以“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心態購買兒童,非法占有目的之強,主觀惡意之大足以見得。對于后者,其主要是通過民間抱養的方式收買兒童,通常沒有通過政府許可或者收養程序,進而從有監護權的主體那里獲得兒童,并且以存在陳舊觀念的農村居民為主。那么新修訂的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罪在對這兩種主體均規定為不虐待被拐賣兒童,不阻礙對其解救即可從輕處罰,并沒有根據主觀惡性的程度區分刑罰力度。所以筆者建議,對于這種不問兒童出處,甚至明知出賣方是無監護權的拐賣者的收買者,應當予以考慮適當加重處罰。
(二)區分適用收買兒童行為處罰的兩個條件
根據新修條款,我們可以看出,只有同時符合不虐待兒童,不阻礙解救,才可以對收買被拐賣兒童行為“從輕處罰”。那么司法實踐中會出現兩種情形:其一,如果行為人這兩個條件都未滿足,既虐待了兒童,又阻礙了對其解救,那當然不可以從輕處罰;其二,如果兩個條件只滿足了其中一個,即行為人虐待了兒童,但不阻礙解救;或者行為人并未虐待兒童,但是阻礙解救。按照條款規定,也不可以從輕處罰。②所以在司法實踐中,如果行為人在沒有實施虐待兒童行為時知道只要自己不阻礙解救就“可以從輕處罰”,但是問題來了,如果行為之前已經實施了虐待兒童的行為了,那么不管他是否阻礙解救,都不可以從輕處罰了,此時收買者可能會“破罐子破摔”,反正結果已經是不可以從輕處罰了,那倒不如干脆阻礙解救,將孩子藏起來或者轉移,讓警方根本找不到,或許還可以逃避懲罰,這便大大加深了對被買兒童的解救難度,不利于保護兒童權益也會消耗執法資源。故筆者認為應適當區分適用收買兒童行為處罰的兩個條件,即可以將只滿足一個條件的情形和同時滿足了兩個條件的情形區分開來進行處罰,使行為人在未虐待行為時還知道不阻礙解救可以爭取從輕處罰,不致向犯罪的深淵越滑越遠。
(三)擴大從輕處罰的適用范圍
新修規定中對收買被買兒童提到“無虐待行為,并不阻礙解救,即可以從輕處罰”,那么從該條款字面上理解就是只有不虐待及不阻礙解救兒童,則可以從輕處罰。那么這樣理解,是否可以從輕處罰情形范圍太窄?由此可以看出,立法者只列舉這兩種情形,是因為現實案件中,收買被買兒童的犯罪者通常實行的行為是虐待行為和阻礙行為,但是這兩種行為更為常見,具有一定代表性,但其他的犯罪行為就可以不再考慮么?隨著社會復雜化,經濟利益的多元化,也使得犯罪手段變得更加多樣,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可能并不是出于組建家庭的目的,有的可能是利用收買來的兒童、婦女強迫進行勞役,或者乞討等行為。那么這些情形是否屬于不可以從輕處罰情形。所以筆者認為,僅僅對沒有虐待行為的從輕處罰還是遠遠不夠的,還應適當的擴大從輕處罰的適用范圍。換言之,可以納入非法剝奪兒童人身自由,強迫其進行苦役或乞討,或者侮辱、輕傷害被與虐待行為程度相似的行為。當被告人沒有實施這些實施傷害行為,也應給予從輕處罰。
[注釋]
①易雅男.淺議<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對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者重處罰的規定[J].法制博覽,2016(02):79.
②周燕燕.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罪探析——以<刑法修正案(九)>為視角[J],鐵道警察學院學報,2015(05):77.
中圖分類號:D924.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4379-(2016)24-0115-02
作者簡介:童謠(1991-),女,漢族,安徽巢湖人,廣西民族大學,法律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