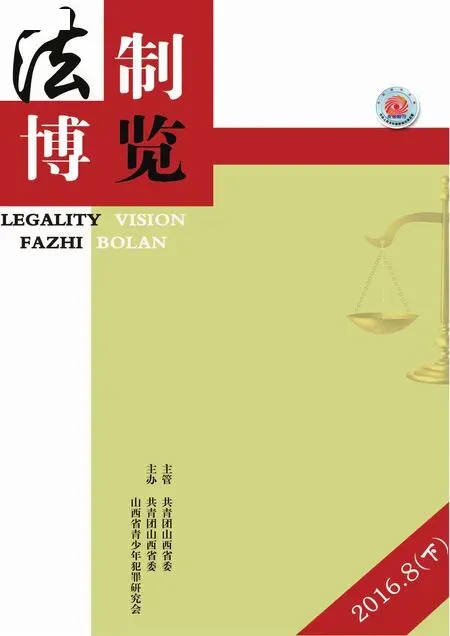“毒樹之果”原則對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借鑒
鄧亦凡
上海海事大學,上海 201306
?
“毒樹之果”原則對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借鑒
鄧亦凡
上海海事大學,上海201306
摘要:本文通過對美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之“毒樹之果”原則的介紹,分析當前我國刑事訴訟法中存在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適用少的現狀,探討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存在的問題以及今后的發展,以期取得有益的收獲。
關鍵詞: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毒樹之果”原則
一、“毒樹之果”原則
美國最高法院第一次使用“毒樹之果”的術語是在1939年的納多恩案中,該判例確立了以下規則:以違反制定法的方式獲得的證據,不僅該證據本身不能作為證據使用,而且借助該證據獲得的其他派生證據也應當予以排除。而該規則的思想最初起源于西爾弗索恩木材公司案。①
在西爾弗索恩木材公司案中,最高法院將第四修正案的排除規則②解釋為要求排除包括作為侵害被告第四修正案權利的間接后果而獲得的證據。該案表明,如果被告證明了一個違反第四修正案的行為——即“毒樹”,并且證明了證據是作為該違法的實際結果而獲得的——該證據是毒樹的一個“果實”,被告就有權使該證據被排除,除非控方證明了可以適用一般排除規則的某一個例外。根據這種方法,在非法行為和證據的發現之間的關聯只需要是,“要是沒有”被告所指稱的非法行為,該證據就不會在當時那樣被獲得。③
二、我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一)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發展
我國有關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研究始于20世紀90年代,從1998年最高院頒行的《刑訴法解釋》第61條規定看,我國早期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只將由刑訊逼供、暴力取證產生的言辭證據加以排除,并且,由于規定的過于籠統,使得其缺乏制度保障而成為擺設。
到了2010年為確保辦理的每一起案件都經得起法律和歷史的檢驗,最高人民法院等五部門出臺了《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采取務實的態度重建了我國的刑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④
2012年,我國修改《刑事訴訟法》時吸收了上述兩部證據規定中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合理內容,并提升為訴訟法層面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同時配套的司法解釋對于非法證據排除的舉證責任等問題也作了較為詳盡的規定。
(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我國的適用情況
根據我國最新的《刑事訴訟法》規定,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啟動可以通過以下兩種方式啟動:1)法官依職權啟動;2)當事人依申請啟動。但是,在實踐中應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情形卻和理想的情形相去甚遠。根據數據統計,法官依職權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情形缺乏,依被告方申請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情形也很稀少。
就目前而言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實踐極少,尤其是當排除非法證據將導致案件的處理陷入僵局或困境,可能不得不對被告人宣判無罪時,法官們選擇的不是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嚴格執行,而是另辟蹊徑,通過決定延期審理給檢察機關對相關非法證據進行補正、解釋,甚至補充新的指控證據機會,使非法證據在其他證據的印證補充下合法化,或者即使被排除,也不影響被告人的定罪量刑,這種“選擇性排除”情況的廣泛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中國的實踐走向。⑤
并且,由于我國的刑事證據立法及司法解釋欠缺指導理論,在立法和司法解釋制定過程中也未能清晰界定基本的證據法概念,因此,在我國刑事訴訟法以及配套的司法解釋中將各類證據都以“不得作為定案根據”條款的形式進行規范⑥,這和美國法中的“排除規則”似乎也是不同的。根據筆者上文的敘述,美國法中,對于證據的排除規則是否定了其證據資格,而我國的“不得作為定案根據”這一規范中排除的對象不僅包括非法證據,也包括了不能補正的瑕疵證據。也因此弱化了對于執法官員在取證過程中震懾作用,模糊了證據能力和證明力的界限。在證據采納中,我們應該堅守證據能力優先于證明力這一原則,而在證據能力的三性中不能忽視合法性的考量,應優先考慮該證據的合法性。
三、對我國司法制度的借鑒
通過上文的分析發現,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中對于非法證據的排除限于嚴重的違法行為所取得的證據,對于由此產生的間接證據并沒有規定可以排除,即“毒樹之果”的合法性并未進行考量。作為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延伸,筆者認為想要完善這一制度,應該將
由非法證據產生的間接其他證據的證明能力問題一同加以思考,否則,可能會導致執法人員利用這一漏洞逃避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使非法證據“合法化”。
而在學術界,對待毒樹之果問題也有兩種觀點:一種主張“砍樹棄果”,其價值取向是保護被告人的利益優于懲罰犯罪;另一種是“砍樹食果”,其價值取向是懲罰犯罪優先于保護被告人的利益。⑦但是筆者認為,非法證據排除原則以及“毒樹之果”原則的主旨應為,通過震懾執法人員的行為,從而達到保障人權的效果。因為通過合法途徑收集的證據更能經的起時間的檢驗,雖然在該規則應用的初始階段必然會增加司法成本,但是使執法人員在執法中養成更好的執法習慣更為重要。
無論是從美國的排除規則發展看,還是從我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看,這一項對于保護當事人權利的規則從出生之時就存在著諸多爭議,而如何適用以及適用的范圍、證明責任以及證明標準的認定,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規定。對于其他國家的立法以及判例的借鑒學習,有利于我國司法制度改革的。雖然表面上這一制度會產生保障當事人權利和打擊犯罪這一社會需求的矛盾,但是從規范執法人員的執法行為角度看,有利于保障司法純潔,從而保護整個社會群體的利益,從而達到程序價值與實體正義的有機統一,從而對減少冤假錯案以及執法人員自身的道德風險都是有利可循的。
[注釋]
①凱普羅.美國聯邦憲法第四修正案[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0:230.
②即“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③麥考密克.麥考密克論證據[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341.
④何家弘,劉品新.證據法學(第5版)(法學新階梯)[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358-359.
⑤左衛民.“熱”與“冷”: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適用的實證研究[J].中國檢察官,2015(13):151-160.
⑥縱博.“不得作為定案根據”條款的學理解析[J].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4,32(4).
⑦閆海.非法證據的衍生證據規則探討——美國毒樹之果理論述評[J].社科縱橫,2006,21(2):76-77.
[參考文獻]
[1]凱普羅.美國聯邦憲法第四修正案[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0.
[2]德雷斯勒.美國刑事訴訟法精解[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3]麥考密克.麥考密克論證據[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
[4]何家弘,劉品新.證據法學(第5版)(法學新階梯)[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5]閆海.非法證據的衍生證據規則探討——美國毒樹之果理論述評[J].社科縱橫,2006,21(2):76-77.
[6]左衛民.“熱”與“冷”: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適用的實證研究[J].中國檢察官,2015,(13):151-160.
[7]縱博.“不得作為定案根據”條款的學理解析[J].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4,32(4).
[8]華爾茲.刑事證據大全[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3.
中圖分類號:D92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4379-(2016)24-0183-02
作者簡介:鄧亦凡(1992-),女,漢族,江蘇徐州人,上海海事大學,法律碩士專業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民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