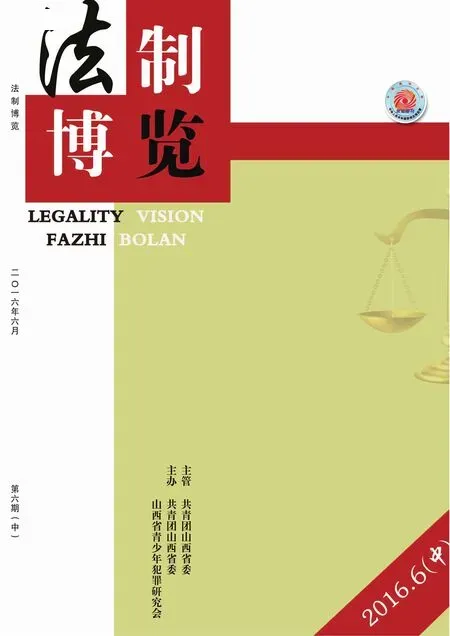大數(shù)據(jù)背景下壟斷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的量化問(wèn)題
——以法經(jīng)濟(jì)學(xué)分析為維度
沈熙菱
中南財(cái)經(jīng)政法大學(xué)法學(xué)院,湖北 武漢 430073
大數(shù)據(jù)背景下壟斷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的量化問(wèn)題
——以法經(jīng)濟(jì)學(xué)分析為維度
沈熙菱
中南財(cái)經(jīng)政法大學(xué)法學(xué)院,湖北武漢430073
摘要:壟斷會(huì)限制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增加交易成本,顯然威脅著法經(jīng)濟(jì)學(xué)家所追求的資源配置效率。世界大多國(guó)家已經(jīng)意識(shí)到壟斷的危害并制定一系列法律,但隨著理論界以哈佛學(xué)派和芝加哥學(xué)派為主的分野,立法模式也不盡相同。另外,壟斷規(guī)制客體的復(fù)雜性和主體的有限理性使得對(duì)相關(guān)市場(chǎng)、市場(chǎng)集中度和限制競(jìng)爭(zhēng)的行為等因素難以界定。然而大數(shù)據(jù)的出現(xiàn)為這一法經(jīng)濟(jì)學(xué)問(wèn)題的解決供了新轉(zhuǎn)機(jī),大范圍的數(shù)據(jù)共享與交換可以及時(shí)基于既建的數(shù)學(xué)模型做出標(biāo)準(zhǔn)量化的認(rèn)定,從數(shù)理分析擴(kuò)展到計(jì)量分析,使得司法判決更具可預(yù)見(jiàn)性。
關(guān)鍵詞:反壟斷;大數(shù)據(jù);法經(jīng)濟(jì)學(xué);量化
一、經(jīng)濟(jì)學(xué)中壟斷的認(rèn)定
(一)完全與不完全競(jìng)爭(zhēng)市場(chǎng)
完全競(jìng)爭(zhēng)市場(chǎng)中,出售相同產(chǎn)品的企業(yè)都是價(jià)格的接受者,單個(gè)企業(yè)相對(duì)于整個(gè)市場(chǎng)而言是如此之小以至于不能控制或影響價(jià)格。生產(chǎn)者面臨的是一條完全水平的需求曲線,當(dāng)企業(yè)在滿足邊際成本等于價(jià)格的條件時(shí)確定產(chǎn)量(MC=P),就可以實(shí)現(xiàn)利潤(rùn)的最大化。亞當(dāng)·斯密早就認(rèn)識(shí)到只有在完全競(jìng)爭(zhēng)成立時(shí),所有的商品銷(xiāo)售和勞務(wù)提供的交易渠道成本最低,同種產(chǎn)品的市場(chǎng)價(jià)格一樣,從而資源配置效果達(dá)到最優(yōu),企業(yè)能夠采用最有效的技術(shù)和最少量的投入換得最具效益的產(chǎn)出品。
而在現(xiàn)實(shí)經(jīng)濟(jì)生活中,不完全競(jìng)爭(zhēng)的市場(chǎng)是常態(tài),主要類(lèi)型是壟斷、寡頭和壟斷競(jìng)爭(zhēng)。不完全競(jìng)爭(zhēng)的本質(zhì)是某一企業(yè)對(duì)其產(chǎn)品的價(jià)格具有絕對(duì)的控制力。以可樂(lè)市場(chǎng)為例,可口可樂(lè)公司占有主要的市場(chǎng)份額,如果可樂(lè)的市場(chǎng)平均價(jià)為75美分,那么可口可樂(lè)公司完全可以售價(jià)70或80美分存活下去,當(dāng)然價(jià)格也不會(huì)低至30美分①。由此,一個(gè)不完全競(jìng)爭(zhēng)者對(duì)價(jià)格確實(shí)有某些拍板權(quán)。
(二)壟斷的釋義與危害
壟斷是指少數(shù)聯(lián)合的或獨(dú)家的大企業(yè)獨(dú)占市場(chǎng),控制著某一個(gè)甚至幾個(gè)部門(mén)的生產(chǎn)和流通,在該部門(mén)的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中占統(tǒng)治地位。多數(shù)壟斷例子可以歸于這樣兩條條主要的原因:第一,大規(guī)模生產(chǎn)出現(xiàn)規(guī)模效益并降低成本時(shí),一個(gè)產(chǎn)業(yè)的競(jìng)爭(zhēng)者就會(huì)越來(lái)越少。因?yàn)樵谶@樣的條件下,大企業(yè)就會(huì)比小企業(yè)以更低的成本進(jìn)行生產(chǎn),而稀奇企業(yè)只能以低于成本的價(jià)格銷(xiāo)售,因而無(wú)法生存;第二,“自然壟斷”領(lǐng)域,由于資源條件分布的集中不適宜競(jìng)爭(zhēng)或無(wú)法競(jìng)爭(zhēng),大多數(shù)國(guó)家采取公有企業(yè)的形式經(jīng)營(yíng),但放松這種規(guī)制已經(jīng)是國(guó)際趨勢(shì)。
這樣的市場(chǎng)結(jié)構(gòu)將會(huì)導(dǎo)致價(jià)格高于成本,消費(fèi)者購(gòu)買(mǎi)量低于效率水平,過(guò)高的價(jià)格和過(guò)低的產(chǎn)出都是非效率標(biāo)志。
(三)經(jīng)濟(jì)學(xué)中壟斷研究的局限性
綜上,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們會(huì)主動(dòng)探討市場(chǎng)的競(jìng)爭(zhēng)環(huán)境問(wèn)題,但是只是從市場(chǎng)內(nèi)部的資源配置機(jī)理出發(fā),局限于企業(yè)自身對(duì)內(nèi)的組織管理行為和對(duì)外的市場(chǎng)交易行為的研究,并未過(guò)多考慮公權(quán)力的強(qiáng)制性介入和政府的宏觀調(diào)控能力,對(duì)市場(chǎng)和政府、政府和市場(chǎng)、公法和私法、計(jì)劃和放任持一種孤立靜止的二分法思維,將任一組理解為非此即彼或替代關(guān)系,采用“市場(chǎng)本位”主義,認(rèn)為市場(chǎng)機(jī)制下的資源交易才是實(shí)現(xiàn)效率的最佳途徑,市場(chǎng)本身已然最接近完全競(jìng)爭(zhēng),國(guó)家和法律的功能僅局限于界定產(chǎn)權(quán)、履行合同和保持市場(chǎng)內(nèi)部秩序。②
這種態(tài)度既忽略二者之間的過(guò)渡形態(tài)和中間機(jī)制也會(huì)忽視調(diào)節(jié)社會(huì)中潛在利益沖突的公共政策決策。
二、法經(jīng)濟(jì)學(xué)中壟斷的認(rèn)定
基于經(jīng)濟(jì)學(xué)原理分析,壟斷狀態(tài)的市場(chǎng)是低效的,作為維護(hù)統(tǒng)治階級(jí)社會(huì)秩序和社會(huì)利益的行為規(guī)范,法律有建立制度約束壟斷行為的正當(dāng)性。也可以進(jìn)一步得出,經(jīng)濟(jì)學(xué)論述的壟斷僅在于市場(chǎng)狀態(tài)的判斷,而反壟斷法則側(cè)重于這種狀態(tài)下企業(yè)的市場(chǎng)交換行為及這種行為造成的消極后果。但是,在學(xué)術(shù)研究中,斷然分開(kāi)經(jīng)濟(jì)學(xué)中的壟斷理論與反壟斷法中的壟斷理論是不可能的③。壟斷一詞就來(lái)自經(jīng)濟(jì)學(xué),而經(jīng)濟(jì)學(xué)中的壟斷理論則是反壟斷法對(duì)壟斷予以規(guī)范的理論依憑。因此,研究法律意義上的壟斷就不能跨越經(jīng)濟(jì)學(xué)中的相關(guān)理論,這也正是反壟斷法的法經(jīng)濟(jì)學(xué)分析的題中應(yīng)有之義。
(一)結(jié)構(gòu)規(guī)制與行為規(guī)制
以哈佛學(xué)派為代表的結(jié)構(gòu)主義對(duì)集中市場(chǎng)的可競(jìng)爭(zhēng)性保持絕對(duì)的懷疑,認(rèn)為這樣的市場(chǎng)結(jié)構(gòu)必然會(huì)促生反市場(chǎng)的限制競(jìng)爭(zhēng)行為,使得資源配置效率低于平均的正常水平④。并且該主義的學(xué)者們質(zhì)疑抽象的“效率”判斷,認(rèn)為效率時(shí)難以證明、測(cè)算和比較的,相比而言市場(chǎng)結(jié)構(gòu)的評(píng)估和預(yù)測(cè)顯得更易量化和可靠,反壟斷法應(yīng)當(dāng)直接確認(rèn)具有市場(chǎng)支配地位的企業(yè)違法,政府需要采取措施遏制企業(yè)的市場(chǎng)壟斷地位,如強(qiáng)制性分拆企業(yè)等手段使市場(chǎng)恢復(fù)競(jìng)爭(zhēng)狀態(tài)。故而結(jié)構(gòu)主義反壟斷法注重市場(chǎng)結(jié)構(gòu)的整體狀況,忽略了國(guó)際市場(chǎng)上某些行業(yè)內(nèi)正當(dāng)?shù)南拗聘?jìng)爭(zhēng)行為的客觀需要。
與結(jié)構(gòu)主義相反,行為主義反壟斷注重經(jīng)濟(jì)效率的分析,以波斯納為代表的芝加哥學(xué)派將其效率的分析用到了極限,試圖最大化利用價(jià)格理論以構(gòu)建和完善反托拉斯法。“價(jià)格理論”由一整套關(guān)于廠家行為和競(jìng)爭(zhēng)性市場(chǎng)的假說(shuō)構(gòu)成:企業(yè)的總目標(biāo)是追求利潤(rùn)最大化;完全自由的市場(chǎng)有效率;二者的最大化滿足就會(huì)帶來(lái)最大化的“消費(fèi)者福利”,而這正是反托拉斯法所追求的目標(biāo)。他們認(rèn)為反壟斷法針對(duì)的對(duì)象是企業(yè)濫用市場(chǎng)支配地位的行為,而不是市場(chǎng)支配地位或是集中的市場(chǎng)結(jié)構(gòu)。該規(guī)制強(qiáng)調(diào)以效益理論解釋各種現(xiàn)象,包括產(chǎn)業(yè)集中、并購(gòu)、合同中的限制性規(guī)定,認(rèn)為結(jié)構(gòu)主義規(guī)制可能損害規(guī)模經(jīng)濟(jì)和規(guī)模效益。行為主義反壟斷極致追求效率的態(tài)度甚至到了忽略公平的地步⑤。
(二)壟斷認(rèn)定的主要因素
1.相關(guān)市場(chǎng)
相關(guān)市場(chǎng)是討論是否構(gòu)成壟斷的前提條件,消費(fèi)者和經(jīng)營(yíng)者行為都在其中發(fā)生,脫離了具體的相關(guān)市場(chǎng)范疇討論壟斷問(wèn)題是沒(méi)有意義的。大多國(guó)家的反壟斷法條文中只從特征層面定義了相關(guān)市場(chǎng)的概念,并沒(méi)有明確界定方法,并且隨著產(chǎn)業(yè)的多元化發(fā)展,尤其是互聯(lián)網(wǎng)項(xiàng)目的出現(xiàn)打破了地域、傳統(tǒng)產(chǎn)業(yè)的界限,相關(guān)市場(chǎng)的內(nèi)涵和外延變得模糊不明。
(1)相關(guān)產(chǎn)品市場(chǎng)。指能與某種產(chǎn)品發(fā)生競(jìng)爭(zhēng)關(guān)系的同類(lèi)產(chǎn)品或替代產(chǎn)品所在的市場(chǎng),其產(chǎn)生的本質(zhì)原因仍是經(jīng)營(yíng)者供給物的功能特性和物理特性有重疊部分。這種競(jìng)爭(zhēng)關(guān)系既可以從消費(fèi)者的需求層面表明,如需求交叉彈性系數(shù)大于零,也可以從生者的供給層面分析,如交叉價(jià)格彈性系數(shù)大于零。
(2)相關(guān)地域市場(chǎng)。是從地理位置的角度界定的相關(guān)市場(chǎng),也是從合理的替代性出發(fā),即一個(gè)企業(yè)生產(chǎn)的某種產(chǎn)品價(jià)格上漲時(shí)是否會(huì)直接導(dǎo)致另一地域產(chǎn)品的銷(xiāo)量上升⑥,如果這種直接相關(guān)性強(qiáng),如二者的價(jià)格、銷(xiāo)量數(shù)值有明顯的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就屬于同一地域市場(chǎng)。
2.市場(chǎng)支配地位
又稱市場(chǎng)控制地位,是德國(guó)和歐共體競(jìng)爭(zhēng)法中使用的概念,指企業(yè)在相關(guān)市場(chǎng)上具有某種程度的支配或控制力量,對(duì)產(chǎn)品價(jià)格、產(chǎn)量的決定有自由空間而無(wú)需過(guò)多考慮競(jìng)爭(zhēng)對(duì)手的行為。企業(yè)具有市場(chǎng)支配地位是反壟斷結(jié)構(gòu)主義規(guī)制中構(gòu)成“應(yīng)罰性”的充分條件,是行為主義規(guī)制中的必要條件。我國(guó)現(xiàn)行的《反壟斷法》第十八條中只抽象地規(guī)定了判斷是否具有市場(chǎng)支配地位時(shí)應(yīng)當(dāng)綜合考量的因素,對(duì)于怎樣的企業(yè)能夠控制商品價(jià)格、數(shù)量和達(dá)到什么情況的企業(yè)能夠阻礙、影響其他經(jīng)營(yíng)者進(jìn)入相關(guān)市場(chǎng)未作明確規(guī)定。
3.壟斷協(xié)議
是指一系列具有獨(dú)立決策機(jī)構(gòu)和法律地位的在相關(guān)市場(chǎng)的企業(yè),以簽訂協(xié)議的方式形成同盟,排除、妨礙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控制產(chǎn)品的數(shù)量、價(jià)格和銷(xiāo)售來(lái)獲取高額利潤(rùn)。以行為主體所處的經(jīng)營(yíng)層次為標(biāo)準(zhǔn),可以將壟斷協(xié)議劃分為橫向的與縱向的:
(1)橫向壟斷協(xié)議。又稱卡特爾,指處于同一經(jīng)營(yíng)層次的同行業(yè)經(jīng)營(yíng)者訂立排除競(jìng)爭(zhēng)協(xié)議或其他協(xié)同行為。在現(xiàn)實(shí)中是發(fā)生、查處數(shù)量最多的限制競(jìng)爭(zhēng)行為,對(duì)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機(jī)制的損害直接又明顯。德國(guó)人習(xí)慣上將反壟斷法稱為“卡特爾法”,可見(jiàn)其在反壟斷執(zhí)行中的普遍性和重要地位。主要形式有固定價(jià)格、限制產(chǎn)量、劃分市場(chǎng)不越界、聯(lián)合抵制第三方等。
但并非所有的橫向限制競(jìng)爭(zhēng)的聯(lián)合行為都是非法的,各國(guó)立法中都設(shè)有對(duì)其豁免的情形如為提高技術(shù)、改良品質(zhì)、增進(jìn)效率的卡特爾。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從德國(guó)、日本等國(guó)家近年來(lái)對(duì)反壟斷法修訂的內(nèi)容,可豁免的聯(lián)合限制競(jìng)爭(zhēng)行為的范圍有逐漸縮小的趨勢(shì),如德國(guó)1998年修訂了對(duì)反壟斷法,不再對(duì)交通、金融、保險(xiǎn)、能源供應(yīng)等行業(yè)適用禁止聯(lián)合限制競(jìng)爭(zhēng)行為的規(guī)定的豁免。
(2)縱向壟斷協(xié)議。兩個(gè)或多個(gè)處于不同經(jīng)營(yíng)層次的經(jīng)營(yíng)者之間訂立限制競(jìng)爭(zhēng)的協(xié)議或者其他協(xié)同行為。這種情況下的行為主體之間一般不存在競(jìng)爭(zhēng)關(guān)系,故而在簽訂壟斷協(xié)議后很難對(duì)某一方的既得利益造成損害,容易在客觀上造成鏈?zhǔn)降南拗聘?jìng)爭(zhēng)。比如縱向的價(jià)格限制,制造商固定再銷(xiāo)售價(jià)格時(shí),銷(xiāo)售商就喪失了價(jià)格自主權(quán)。美國(guó)最高院自1911年邁爾斯醫(yī)生案以來(lái),一直將其視為自身違法行為。
4.經(jīng)營(yíng)者集中
指一個(gè)企業(yè)通過(guò)購(gòu)得股份、訂立合同、取得財(cái)產(chǎn)等方式,對(duì)另一個(gè)企業(yè)施具有實(shí)質(zhì)性的控制能力,使得兩個(gè)原本相對(duì)獨(dú)立的競(jìng)爭(zhēng)主體混同,使得市場(chǎng)上的部分經(jīng)濟(jì)力量趨向集中。適度的規(guī)模經(jīng)濟(jì)無(wú)論是微觀抑或宏觀角度都是大有利好的,可以統(tǒng)一調(diào)控生產(chǎn)要素、增加資源配置效率和提高產(chǎn)出率。然而無(wú)限制地放任這種擴(kuò)張,競(jìng)爭(zhēng)者們的利益追求由相悖變?yōu)橥唬罱K必然會(huì)消除或窒息自由競(jìng)爭(zhēng)。
各國(guó)對(duì)于“適度”與“過(guò)度”的集中度的判斷大多采取程序性規(guī)范——合并申報(bào)制度,在現(xiàn)有的立法實(shí)踐大多列明了明晰的強(qiáng)制申報(bào)的量化標(biāo)準(zhǔn),如美國(guó)《克萊頓法》第7條以及1976年補(bǔ)充條款7A,歐盟《企業(yè)合并條例》中“具有共同體影響”的條件,德國(guó)《反限制競(jìng)爭(zhēng)法》中具體的市場(chǎng)銷(xiāo)售額條件,中國(guó)的《國(guó)務(wù)院關(guān)于經(jīng)營(yíng)者集中申報(bào)標(biāo)準(zhǔn)的規(guī)定》中滿足所列明的一項(xiàng)則需申報(bào),否則均不得集中。
但是,雖然各國(guó)在立法中對(duì)合并申報(bào)的數(shù)量上的要求已十分具體,但是執(zhí)法機(jī)構(gòu)對(duì)申報(bào)主體作出的是否限制競(jìng)爭(zhēng)的結(jié)論所依據(jù)的標(biāo)準(zhǔn)并未常態(tài)化、公開(kāi)化,仍停留在極具主觀色彩的定性的層面,未輔以必要的定量手段。
5.行政壟斷
一般指政府及其職能部門(mén)濫用行政權(quán)力損害市場(chǎng)自由競(jìng)爭(zhēng)秩序的行為,基本特點(diǎn)是將市場(chǎng)主體分為保護(hù)群體和被限制群體,前者在行政權(quán)的庇護(hù)下能輕易獲得交易機(jī)會(huì)和競(jìng)爭(zhēng)利益,后者不可能進(jìn)入相關(guān)市場(chǎng)公平競(jìng)爭(zhēng)。行政壟斷容易滋生貪污腐敗和權(quán)力尋租,最終消費(fèi)者的選擇權(quán)和公平交易權(quán)會(huì)受到損害,也不利于社會(huì)創(chuàng)新。
(三)傳統(tǒng)法經(jīng)濟(jì)學(xué)中壟斷標(biāo)準(zhǔn)量化的瓶頸
一方面?zhèn)鹘y(tǒng)經(jīng)濟(jì)學(xué)研究具有滯后性,對(duì)新生事物和事物最新的發(fā)展是不敏感的,必須待其成長(zhǎng)到一定規(guī)模后才能收集到足夠數(shù)據(jù)進(jìn)行研究;另一方面,正如波斯納所認(rèn)為法律訴訟的效率在于模擬再現(xiàn)市場(chǎng)機(jī)制下的自由交易以決定利益分配,這種模擬再現(xiàn)如今主要依賴于法官的理性思考和專(zhuān)業(yè)素養(yǎng),唯獨(dú)缺乏的便是大量、大范圍地?cái)?shù)據(jù)收集和分析,原因是這樣做會(huì)擴(kuò)大司法成本,降低效率,不利于整體社會(huì)福利的最大化。
因此,反壟斷規(guī)制中客體的復(fù)雜性和主體的有限性給法條留下了大量的解讀空間和自由裁量權(quán),使得法官面對(duì)反壟斷案件望而卻步,商家肆意行事、狡辯避法。
三、大數(shù)據(jù)背景下壟斷的認(rèn)定
(一)量化壟斷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的必要性
縱觀法經(jīng)濟(jì)學(xué)的既有文獻(xiàn),定量分析被視作是一個(gè)預(yù)設(shè)的無(wú)需考慮的前提,法經(jīng)濟(jì)學(xué)是否可以定量分析以及在哪些方面可以定量分析很少有人問(wèn)津。而如今國(guó)內(nèi)法經(jīng)濟(jì)學(xué)的定量分析也很少,既有的大多數(shù)也只是數(shù)理分析,而未給法律實(shí)施者提供一個(gè)具體的便于操作的計(jì)量標(biāo)準(zhǔn)。
可以看到“壟斷行為”是世界各國(guó)不同反壟斷法所要限制或禁止的對(duì)象,但經(jīng)濟(jì)學(xué)理論只是從市場(chǎng)結(jié)構(gòu)的靜態(tài)的角度揭示了壟斷的性質(zhì)和危害,傳統(tǒng)法經(jīng)濟(jì)學(xué)也只是對(duì)壟斷作出定性的分析。誠(chéng)然,壟斷一直具有綜合性和多變性,唯一肯定的便是其特征:違法性和應(yīng)受處罰性,它甚至是在不考慮法律干預(yù)時(shí)的一種利弊兼有的客觀經(jīng)濟(jì)現(xiàn)象。世界各國(guó)也因其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和價(jià)值保護(hù)的側(cè)重不同,分別對(duì)壟斷的認(rèn)定進(jìn)行了不同的制度設(shè)計(jì),而且構(gòu)成要件總會(huì)有模糊項(xiàng)而留給法官大量的自由裁量空間,裁決結(jié)果的可預(yù)見(jiàn)性及其低下,縱使有預(yù)見(jiàn)性也不是從條文、法理本身出發(fā)而大多基于以往的案例從經(jīng)驗(yàn)主義出發(fā)。
綜上,判斷壟斷適度與否也就是該行為是否構(gòu)成法律禁止之“壟斷”,關(guān)鍵在于衡量該行為所造成的社會(huì)利弊之大小,這也意味著壟斷認(rèn)定時(shí)不同方面既有的的量化標(biāo)準(zhǔn)是必要的。
(二)大數(shù)據(jù)的優(yōu)越性
大數(shù)據(jù)是指無(wú)法在可承受的時(shí)間范圍內(nèi)用常規(guī)軟件工具進(jìn)行捕捉、管理和處理的數(shù)據(jù)集合。大數(shù)據(jù)之父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早就在其著作⑦中前瞻性地指出大數(shù)據(jù)帶來(lái)的信息風(fēng)暴將會(huì)改變我們的生活、工作和思維,并提出了三大原則:不是隨機(jī)抽樣,而是全體數(shù)據(jù);不是精確性,而是綜合性;不是因果關(guān)系,而是相關(guān)關(guān)系。維克托還認(rèn)為大數(shù)據(jù)的核心運(yùn)用就是預(yù)測(cè)——,通過(guò)對(duì)數(shù)據(jù)的收集對(duì)未來(lái)的情況進(jìn)行模擬為人類(lèi)的生活創(chuàng)造前所未有的可量化的維度。
在大數(shù)據(jù)時(shí)代,可以即時(shí)依據(jù)海量數(shù)據(jù)對(duì)經(jīng)濟(jì)行為進(jìn)行分析,一旦有新動(dòng)態(tài)立即予以關(guān)注,從而實(shí)現(xiàn)對(duì)新生事物的早期分析和干預(yù),大數(shù)據(jù)以其本身具有的一定程度的“智能”輔助法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們發(fā)現(xiàn)問(wèn)題根源。
(三)壟斷認(rèn)定中主要因素的量化趨勢(shì)
1.市場(chǎng)相關(guān)性的量化
SSNIP是“數(shù)額不大但很重要且非臨時(shí)性漲價(jià)”(Small but Significant Not-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的縮寫(xiě),目前,美國(guó)、歐盟等國(guó)家主要運(yùn)用該方法對(duì)相關(guān)市場(chǎng)進(jìn)行界定,其主要內(nèi)容是對(duì)于假定的壟斷者要求其至少維持一年5%的漲幅,在能夠維持盈利的情況下找出最窄的相關(guān)產(chǎn)品市場(chǎng)⑧。可見(jiàn)這是一種通過(guò)相關(guān)數(shù)據(jù)來(lái)模擬完成的測(cè)試方法,它對(duì)涉案企業(yè)的相關(guān)數(shù)據(jù)尤其是衡量需求可替代性的數(shù)據(jù)有一定的要求。而大數(shù)據(jù)背景下,企業(yè)公開(kāi)的財(cái)務(wù)數(shù)據(jù)流通共享,使得相關(guān)市場(chǎng)界定更加明確而簡(jiǎn)易,這樣可以大大降低獲得相關(guān)數(shù)據(jù)的司法、執(zhí)法成本,這種方法最終也會(huì)得到普遍適用。
2.市場(chǎng)支配地位的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
就各國(guó)實(shí)踐情況看來(lái),市場(chǎng)支配地位的認(rèn)定以市場(chǎng)份額為首要考量因素,市場(chǎng)份額是特定企業(yè)的銷(xiāo)售額在相關(guān)市場(chǎng)的總銷(xiāo)售額中所占比例,如日本《禁止壟斷法》規(guī)定:一家企業(yè)市場(chǎng)份額達(dá)1/2以上,兩家企業(yè)市場(chǎng)份額達(dá)3/4以上,推定有市場(chǎng)支配地位。但很多國(guó)家并沒(méi)有規(guī)定市場(chǎng)份額所處的時(shí)間段,是一個(gè)月內(nèi)還是近年來(lái),單個(gè)企業(yè)乃至整個(gè)相關(guān)市場(chǎng)企業(yè)的銷(xiāo)售額的來(lái)源未作明確規(guī)定,很有可能出現(xiàn)即使在大眾都認(rèn)同的市場(chǎng)“霸主企業(yè)”面前,主張壟斷者也面臨著舉證難的尷尬情況。而大數(shù)據(jù)背景下,企業(yè)的銷(xiāo)售額將會(huì)按每個(gè)會(huì)計(jì)期間逐一錄入一個(gè)匯總的大數(shù)據(jù)庫(kù),數(shù)據(jù)會(huì)在已經(jīng)編輯好的運(yùn)算程序下自動(dòng)經(jīng)過(guò)數(shù)理模型,最終由計(jì)算機(jī)輸出分析結(jié)果。
3.限制競(jìng)爭(zhēng)程度的量化
大多國(guó)家仍采行為主義反壟斷規(guī)制,如中國(guó),一個(gè)企業(yè)即使占有市場(chǎng)支配地位但若無(wú)濫用該支配地位之行為仍不具有法律當(dāng)罰性。而這種濫用行為主要表現(xiàn)為掠奪性定價(jià)、強(qiáng)制交易、價(jià)格歧視、搭售等。舉幾個(gè)大數(shù)據(jù)運(yùn)用的例子,在認(rèn)定掠奪性定價(jià)時(shí),計(jì)算機(jī)每時(shí)每刻監(jiān)控某類(lèi)產(chǎn)品的價(jià)格變化,根據(jù)數(shù)據(jù)庫(kù)中存儲(chǔ)的該類(lèi)產(chǎn)品的市場(chǎng)平均價(jià)格(物價(jià)局及時(shí)整理報(bào)送)標(biāo)示出明顯過(guò)低的產(chǎn)品,在一段時(shí)間內(nèi)觀測(cè)該相關(guān)市場(chǎng)的企業(yè)虧損或盈利情況,以及價(jià)格回高時(shí)高于原市場(chǎng)平均價(jià)格的幅度,評(píng)析該幅度是否在合理范圍內(nèi)。同樣在認(rèn)定價(jià)格歧視時(shí),排列出同一企業(yè)的同一產(chǎn)品在不同地域、領(lǐng)域范圍內(nèi)的報(bào)價(jià)情況,再對(duì)比在同一范圍內(nèi)相同或相似產(chǎn)品的平均價(jià)格以得出報(bào)價(jià)是否合理的結(jié)論,這些數(shù)據(jù)分析結(jié)果都可以作為反壟斷執(zhí)行的依據(jù)。
4.經(jīng)營(yíng)者集中度的計(jì)算
傳統(tǒng)的反壟斷規(guī)制中對(duì)市場(chǎng)集中度的兩大計(jì)量標(biāo)準(zhǔn)有行業(yè)集中率(CRn)和赫爾芬達(dá)爾—赫希曼指數(shù)(HHI)。CRn指該行業(yè)的相關(guān)市場(chǎng)內(nèi)前N家最大的企業(yè)所占市場(chǎng)份額的總和,缺點(diǎn)是沒(méi)有指出這個(gè)行業(yè)相關(guān)市場(chǎng)中企業(yè)的總數(shù);HHI是計(jì)算一個(gè)行業(yè)中各競(jìng)爭(zhēng)主體所占行業(yè)總收入或總資產(chǎn)百分比的平方和,表明市場(chǎng)份額的變化和規(guī)模的離散度,缺陷是對(duì)數(shù)據(jù)的要求較高,而且含義不直觀。而大數(shù)據(jù)背景下,每個(gè)企業(yè)的月度、季度、年度的財(cái)務(wù)報(bào)表都會(huì)在公開(kāi)后第一時(shí)間自行匯入數(shù)據(jù)庫(kù),大容量的計(jì)算機(jī)對(duì)獲取的信息進(jìn)行高度精密的相關(guān)性分析,不遺漏任何一個(gè)相關(guān)企業(yè),再及時(shí)向反壟斷執(zhí)行部門(mén)提供市場(chǎng)集中度數(shù)值,作為查處壟斷行為的預(yù)警信號(hào)。
5.行政壟斷中的量化標(biāo)尺
明顯的行政壟斷的手段主要是規(guī)章、條例、通知等規(guī)范性文件的發(fā)布,我們可以運(yùn)用大數(shù)據(jù)分析市場(chǎng)因素的變化與文件發(fā)布的相關(guān)性。舉一個(gè)例子,在政府發(fā)布一個(gè)規(guī)范性文件后,計(jì)算機(jī)會(huì)自動(dòng)比對(duì)文件影響范圍內(nèi)的企業(yè)在該時(shí)間點(diǎn)前后一段時(shí)間的產(chǎn)品或者服務(wù)的供給量、銷(xiāo)售量的變化,所涉及到的企業(yè)則劃入相關(guān)市場(chǎng)界限內(nèi),再結(jié)合前述的CRN、HHI、SSNIP指數(shù)分析市場(chǎng)集中度的變化及處于市場(chǎng)支配地位企業(yè)的認(rèn)定。上級(jí)行政機(jī)關(guān)可以根據(jù)分析結(jié)果及時(shí)調(diào)查發(fā)布文件的行政機(jī)關(guān),消除限制競(jìng)爭(zhēng)的行為。
四、中國(guó)的大數(shù)據(jù)經(jīng)濟(jì)學(xué)的發(fā)展展望
我國(guó)以近幾十年來(lái)GDP的飛速增長(zhǎng)奇跡,在世界強(qiáng)國(guó)之林中傲為第二大經(jīng)濟(jì)體,但是在國(guó)際政治與經(jīng)濟(jì)形勢(shì)瞬息萬(wàn)變的環(huán)境下,國(guó)人們居安思危,不斷謀求發(fā)展。在21世紀(jì),各國(guó)競(jìng)爭(zhēng)的焦點(diǎn)已經(jīng)從傳統(tǒng)的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到高新技術(shù)密集型產(chǎn)業(yè)上來(lái),互聯(lián)網(wǎng)的出現(xiàn)及其擴(kuò)延項(xiàng)目為大數(shù)據(jù)登上世界經(jīng)濟(jì)的舞臺(tái)準(zhǔn)備了充足的條件,大數(shù)據(jù)作為一個(gè)“新生兒”,還處于發(fā)育階段,相關(guān)領(lǐng)域的市場(chǎng)主體的經(jīng)營(yíng)行為可能正好處于法律規(guī)制的“灰色地帶”,我們?nèi)孕枰獙?duì)這些行為持觀望態(tài)度,畢竟創(chuàng)新意味著打破傳統(tǒng)和冒犯既得利益集團(tuán),政府需要對(duì)此做出正確的政策引導(dǎo),切不可輕易向舊有的事物妥協(xié)。
[注釋]
①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微觀經(jīng)濟(jì)學(xué)(中譯本)[M].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03.
②凱斯·R.自由市場(chǎng)與社會(huì)正義[M].北京: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2.
③郭振杰,劉洪波.經(jīng)濟(jì)分析法學(xué)方法論的貢獻(xiàn)及局限[J].現(xiàn)代法學(xué),2005(3):98.
④魏建.法經(jīng)濟(jì)學(xué)基礎(chǔ)與比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2-85.
⑤馮玉軍.公平還是福利這是一個(gè)問(wèn)題[J].西部法學(xué)評(píng)論,2008(1):94-96.
⑥曹虹.論反壟斷法中相關(guān)市場(chǎng)的界定[J].現(xiàn)代管理科學(xué),2007(11):44-46.
⑦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大數(shù)據(jù)時(shí)代(中譯本)[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
⑧丁茂中.論SSNIP測(cè)試法與相關(guān)市場(chǎng)的界定[J].經(jīng)濟(jì)法論叢,2008(2):54-59.
中圖分類(lèi)號(hào):D971.2;D922.294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2095-4379-(2016)17-0017-04
作者簡(jiǎn)介:沈熙菱(1995-),女,湖南常德人,中南財(cái)經(jīng)政法大學(xué)法學(xué)院,2013級(jí)法學(xué)本科生,研究方向:法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