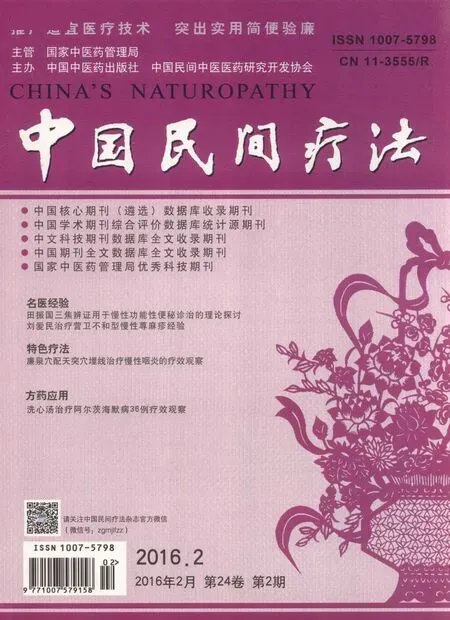腎氣丸在《金匱要略》中異病同治的思考
?
腎氣丸在《金匱要略》中異病同治的思考
申寶林
(山西省中醫(yī)院,太原 030012)
【關(guān)鍵詞】《金匱要略》;腎氣丸;異病同治;情志調(diào)適
腎氣丸一方源于《金匱要略》,該方配伍嚴(yán)謹(jǐn)、方證結(jié)合、構(gòu)思獨(dú)特。五種不同的疾病,仲景用同一方治療,是因?yàn)樗鼈冇泄餐牟C(jī)——腎氣虛衰,所謂“病異而證同,證同而治同”,即異病同治的原則。
張仲景對(duì)腎氣丸的妙用
1.腎氣丸的組成和方義。
組成:干地黃八兩、山藥四兩、山茱萸四兩、澤瀉三兩、茯苓三兩、牡丹皮三兩、桂枝一兩、炮附子一兩。
方義:腎為先天之本,元?dú)庵瑑?nèi)寄元陰元陽(yáng),凡腎虛則包括陰虛、陽(yáng)虛兩個(gè)方面,故在確立補(bǔ)腎治法時(shí),既要補(bǔ)腎陰,又要助腎陽(yáng);即使表現(xiàn)為單純的腎陰虛或腎陽(yáng)虛,在補(bǔ)腎時(shí)也不可單純滋補(bǔ)腎陰或溫補(bǔ)腎陽(yáng),否則易礙陽(yáng)或竭陰。腎氣丸方中重用干地黃養(yǎng)血滋陰,補(bǔ)精益髓為君藥;臣以山藥、山茱萸補(bǔ)肝脾而益精血;加附子、桂枝之辛熱,助命門以溫陽(yáng)化氣。君臣相伍,補(bǔ)腎填精,溫腎助陽(yáng)。又配澤瀉、茯苓利水滲濕、健脾泄熱;牡丹皮清熱涼血、活血散瘀。方中三補(bǔ)三瀉,少佐桂附,取“少火生氣”之功。方名為腎氣丸,意在補(bǔ)腎中之精氣,調(diào)腎中之陰陽(yáng)。正如《傷寒來蘇集》所言:“此腎氣丸納桂、附于滋陰劑中十倍之一,意不在補(bǔ)火,而在微生火,即生腎氣也。故不曰溫腎,而名曰腎氣。”腎氣丸方藥配伍補(bǔ)瀉兼施,陰陽(yáng)并調(diào),陰中求陽(yáng),且以丸藥緩圖,在虛損治療中獨(dú)樹一幟。
2.《金匱要略》中腎氣丸的應(yīng)用。
《金匱要略·血痹虛勞病脈證并治》曰:“虛勞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八味腎氣丸主之。”腎為先天之本,藏精氣而不泄;腰為腎之府,若腎精不足,濡養(yǎng)功能失常,則出現(xiàn)“不榮則痛”。腎氣不足,膀胱氣化不利,開合失司,故見少腹拘急、小便不利。治用八味腎氣丸益氣補(bǔ)腎。
《金匱要略·中風(fēng)歷節(jié)病脈證并治》曰:“崔氏八味丸:治腳氣上入,少腹不仁。”足少陰腎經(jīng)起于足小趾下,斜走足底涌泉穴,循行小腿內(nèi)側(cè),直行于腹腔內(nèi),止于舌根兩旁。肝腎氣血虧虛,正氣不足,寒氣夾濕,沿腎經(jīng)上行,致少腹痹著不仁。
《金匱要略·痰飲咳嗽病脈證并治》曰:“夫短氣有微飲,當(dāng)從小便去之,苓桂術(shù)甘湯主之;腎氣丸亦主之。”飲邪停滯,影響臟腑氣機(jī),導(dǎo)致短氣。腎主水,脾主運(yùn)化水液,飲邪為患,脾腎二臟功能失調(diào),故治療飲邪,當(dāng)從脾腎。苓桂術(shù)甘湯與腎氣丸都有溫而不燥、補(bǔ)而兼消的配伍特點(diǎn),同為“溫藥和之”的代表方,可以治療狹義痰飲輕證,其辨證要點(diǎn)都有短氣、小便不利,病機(jī)均為脾腎陽(yáng)氣不化,治療上均遵從“當(dāng)從小便去之”的治療原則。所不同者,苓桂術(shù)甘湯重在治脾,病機(jī)以脾陽(yáng)虛為主,其癥兼見胸脅支滿、目眩、心悸,治以溫脾陽(yáng)以化飲;腎氣丸重在治腎,病機(jī)以腎陽(yáng)虛為主,其癥兼見腰痛、少腹拘急不仁、畏寒足冷,治以溫腎陽(yáng)以化飲。有同病異治蘊(yùn)含其中。
《金匱要略·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脈證并治》曰:“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飲一斗,小便一斗,腎氣丸主之。”若津液內(nèi)傷,為口渴兼小便短少,今小便反多,為腎陽(yáng)虛衰,既不能蒸騰津液以上潤(rùn),又不能化氣以攝水,故出現(xiàn)消渴及小便多。腎氣丸主治下消,以渴喜熱飲、小便清長(zhǎng)而甜、消瘦、腰膝酸軟、腳腫或見手足心熱、唇淡舌淡、舌潤(rùn)無苔或少苔乏津、尺脈細(xì)弱等癥為辨證要點(diǎn)。因此,在辨證時(shí)以尿多清長(zhǎng)為要點(diǎn),伴有腎陰陽(yáng)兩虛之證。治宜滋養(yǎng)腎陰,壯水之主以制陽(yáng)光;溫復(fù)腎陽(yáng),益火之源以消陰翳。腎氣丸使腎能攝水而不直驅(qū)下源,腎氣上蒸則能化生津液,消渴自可緩解。
《金匱要略·婦人雜病脈證并治》曰:“問曰:婦人病,飲食如故,煩熱不得臥,而反倚息者,何也?師曰:此名轉(zhuǎn)胞,不得溺也,以胞系了戾,故致此病,但利小便則愈,宜腎氣丸主之。”“胞”即膀胱,“胞系了戾”指膀胱之系繚繞不順。婦人轉(zhuǎn)胞的主癥是小便不通,臍下急迫。病在下焦,中焦無病,飲食如故;由于小便不通,濁氣上逆,故煩熱不得臥,只能倚靠著呼吸。不過須知:轉(zhuǎn)胞除腎氣不舉,膀胱氣化不行而致外,中焦脾虛中氣下陷,上焦肺虛,氣化不及州都,通調(diào)失職;妊娠胎氣不舉,壓迫膀胱;忍尿入房等,都可導(dǎo)致胞系了戾而小便不通,朱丹溪用補(bǔ)中益氣湯,程鐘齡用茯苓升麻湯均為同病異治的具體應(yīng)用。
綜上所述,仲景在《金匱要略》中用腎氣丸治療以上五種疾病,其中虛勞、痰飲、婦人轉(zhuǎn)胞不得溺均有小便不利的癥狀,而消渴病則為小便反多。因腎主水,司開合,為胃之關(guān)。氣化正常,則開合有度,小便排泄正常。虛勞、痰飲、婦人轉(zhuǎn)胞中的小便不利,均為腎陽(yáng)、腎氣虛弱,膀胱氣化不利,失其“開”之職所致。而消渴病,因腎陰陽(yáng)兩虛,腎氣虛弱,不得化氣行水,失其“合”之職,故小便反多。小便不利與小便反多,癥狀雖不同,然兩者病機(jī)相同,為腎陰陽(yáng)兩虛,腎虛氣化失司,開合異常所致,故均可用具有補(bǔ)腎益陰助陽(yáng)的腎氣丸治療。寒濕腳氣亦為腎氣不足,寒濕之氣才得以循經(jīng)上入。根據(jù)“異病同治”的基本理論可知,無論任何雜病,凡符合腎氣不足的病機(jī),均可選腎氣丸加減應(yīng)用。
現(xiàn)代臨床在腎虛辨證的基礎(chǔ)上,應(yīng)用腎氣丸治療病種很多,如慢性支氣管炎、肺心病、慢性腎炎、慢性尿路感染、尿路結(jié)石、尿潴留、尿崩癥、糖尿病、泄瀉、便秘、前列腺肥大、更年期綜合征、性功能障礙、不育癥、甲低性神經(jīng)衰弱、老年性白內(nèi)障等均為依“異病同治”之法,活用腎氣丸之例。
本方對(duì)后世醫(yī)家影響很大,在其基礎(chǔ)上發(fā)展了兩類補(bǔ)腎方劑:一類溫補(bǔ)腎陽(yáng),從陰中求陽(yáng),如右歸丸、右歸飲等;一類則在原方中除去溫陽(yáng)暖腎藥物,以滋陰補(bǔ)腎為主,如六味地黃丸、左歸丸、左歸飲,以及在該方基礎(chǔ)上發(fā)展起來的杞菊地黃丸、知柏地黃丸、七味都?xì)馔琛Ⅺ溛兜攸S丸等。張景岳創(chuàng)立陰陽(yáng)并補(bǔ)的大補(bǔ)元煎,適用于元陰元陽(yáng)俱虛之證[1]。這些經(jīng)典的方劑均是師仲景法而成,已廣泛應(yīng)用于臨床。
同病異治和異病同治就是仲景診治雜病原則的具體體現(xiàn)。同病異治是指同一種疾病,由于病因、病機(jī)、體質(zhì)以及病位的不同,導(dǎo)致證候不同,故治亦不同。
典型案例
例1.患者,女,38歲。主訴:閉經(jīng)11個(gè)月伴腰困乏力。現(xiàn)病史:患者1年前因藥流不全大出血,之后閉經(jīng),曾服補(bǔ)血調(diào)經(jīng)藥效果不佳,漸感腰困、乏力,納食不香,面色萎黃,畏寒脫發(fā),性欲低下,小便清長(zhǎng)。舌體淡胖,苔白,脈沉細(xì)無力。彩超示:子宮內(nèi)膜3 mm。化驗(yàn)檢查E2、P均低于正常值。曾行宮腔鏡檢查:子宮腔形態(tài)大致正常。證屬虛勞;辨證為脾腎兩虛;治宜補(bǔ)腎健脾;方用腎氣丸加減。藥用熟地黃15 g,山茱萸12 g,山藥15 g,牡丹皮10 g,茯苓12 g,澤瀉10 g,附子6 g,肉桂6 g,黨參12 g,炒白術(shù)12 g,黃芪15 g,阿膠6 g(烊化),女貞子12 g,旱蓮草12 g,菟絲子15 g,炙甘草6 g。大棗5枚(擘),14劑,水煎2 h,早晚2次分服。
二診:患者精神好轉(zhuǎn),畏寒減輕,上方加雞血藤30 g,當(dāng)歸12 g,川牛膝15 g以活血調(diào)經(jīng),兩月后患者月經(jīng)來潮。
方中用肉桂代替桂枝,因桂枝善于通陽(yáng),其性走而不守,對(duì)于水飲停聚,用之較妥;肉桂善于納氣,引火歸原,其性守而不走,故對(duì)命門火衰、虛火上浮、腎不納氣、下焦虛寒、真陽(yáng)虧損,用之較宜。原方干地黃,今用熟地黃補(bǔ)血滋陰益精。
該患者因?yàn)槭а。瑸楹斡醚a(bǔ)血調(diào)經(jīng)藥效果不佳?是因?yàn)闆_任氣血不足,脾虛生化乏源;血虛日久,久病及腎。正如《景岳全書·婦人規(guī)》所云:“欲其不枯,無如養(yǎng)營(yíng),欲以通之,無如充之,但使雪消則春水自來。”
例2.患者,女,31歲。主訴:剖宮產(chǎn)術(shù)后1月小便不通。現(xiàn)病史:患者1月前行剖宮產(chǎn)術(shù),拔尿管后小便不暢,1月來逐漸加重,無尿痛。伴胸中煩悶,腰膝酸軟,小腹脹滿,惡露凈,乳汁較少,納食一般,睡眠差,大便如常,舌質(zhì)淡,苔白潤(rùn),脈沉細(xì)。化驗(yàn)?zāi)虺R?guī)未見異常。證屬轉(zhuǎn)胞;辨證為腎氣虛衰,氣化不行;治宜溫腎化氣行水。方用腎氣丸加減。藥用熟地黃24 g,山茱萸12 g,山藥15 g,牡丹皮9 g,茯苓9 g,澤瀉9 g,炮附子3 g,桂枝3 g,炒棗仁15 g,益母草12 g,通草12 g,菟絲子15 g,懷牛膝9 g,甘草6 g。5劑,水煎2 h,早晚2次分服。經(jīng)隨訪得知,患者服藥后小便通暢。
對(duì)婦科“異病同治”的思考
異病同治的基礎(chǔ)是證同治亦同。“同治”并非一成不變。從疾病本身來看,臨床上要考慮到病的差異性。既然為“異病”,必然有其疾病的特點(diǎn)與表現(xiàn),不同疾病有不同的發(fā)展轉(zhuǎn)歸。從發(fā)病的個(gè)體來看,每個(gè)人的體質(zhì)均有所差異。所謂體質(zhì)是指人體陰陽(yáng)氣血的強(qiáng)弱多寡和臟腑功能的盛衰。就女性個(gè)體而言,又有因特殊生理而形成的體質(zhì)差異。如正處經(jīng)、孕、產(chǎn)、乳的某個(gè)階段,其體質(zhì)可有某些暫時(shí)的變化。一年四季及南北地域的氣候不同對(duì)用藥均有影響。因此,在臨證中,必須根據(jù)每一位患者疾病的特點(diǎn)和規(guī)律,據(jù)其發(fā)病的病因、病位、體質(zhì)等具體情況,對(duì)處方的劑量和藥物進(jìn)行恰當(dāng)?shù)卦鰷p變化,方能保證臨床療效。如不孕癥腎陽(yáng)虛的患者,在選用右歸丸溫腎暖宮、益沖種子的同時(shí),如患者兼脾虛,則加黨參、白術(shù)、黃芪等健脾益氣;如兼痰濕則加膽南星、蒼術(shù)、陳皮等祛痰燥濕。
有同道認(rèn)為“同治”既可以是狹義的同一個(gè)方劑,也可以是廣義的治法[2]。對(duì)此筆者深表贊同。對(duì)于有相同證候的患者,臨床可以同治,卻不一定用同方。如對(duì)于腎陽(yáng)虧損證所致的不孕癥,羅元?jiǎng)P教授用右歸丸加淫羊藿、艾葉,《傅青主女科》用溫胞飲,《沈氏尊生書》則用艾附暖宮丸。在相同的治則下,靈活變更,療效卓著。
回顧古今驗(yàn)案可以看出,真正懂得“異病同治”的醫(yī)家,更深諳疾病本身的特點(diǎn)和治療方法。“異病同治”時(shí)絕不可忽略“病證結(jié)合”,應(yīng)該既重視證的同一性,又了解病的差異性,把握整體與局部的關(guān)系,才能取得良好的療效。如《素問·至真要大論》所言:“謹(jǐn)守病機(jī),各司其屬,有者求之,無者求之,盛者責(zé)之,虛者責(zé)之,必先五勝,疏其血?dú)猓钇錀l達(dá),而致和平。”
情志調(diào)攝法在婦科“異病同治”中的應(yīng)用
肝藏血,腎藏精;精血互生,乙癸同源。《張氏醫(yī)通》有言:“氣不耗,歸精于腎而為精;精不泄,歸精于肝而為血。”從五行來看,肝為腎之子,《傅青主女科》云:“夫經(jīng)水出諸腎,而肝為腎之子,肝郁則腎亦郁矣……治法宜舒肝之郁,即開腎之郁也”[3]。
從婦科病總的病機(jī)來看,由于婦女素稟不足,早婚多產(chǎn),房事不節(jié),常損傷腎氣;又由于婦女生理上數(shù)傷于血,以致氣分偏盛,性情易于波動(dòng),常影響到肝。從情志致病來分析,女性發(fā)生的怒、思、恐等強(qiáng)烈的情志變化,可以使人體氣機(jī)失調(diào),導(dǎo)致氣血病變,并且可以導(dǎo)致肝、脾、腎三臟的功能失調(diào)。如臨床診療中,常見到某些職業(yè)女性受到家庭婚姻與工作的雙重壓力致情志不暢,而全職太太們又常因?yàn)榉怕饲斑M(jìn)的步伐,面臨婚姻危機(jī)而心緒不寧、肝氣不疏。
筆者作為一名婦科醫(yī)生,在27年的臨床診療實(shí)踐中,對(duì)于因情志不暢、肝氣郁結(jié)所致的月經(jīng)后期、月經(jīng)先后無定期、痛經(jīng)、閉經(jīng)、不孕癥等婦科疾病,參照異病同治的原則,一方面開出方藥,另一方面筆者認(rèn)識(shí)到與患者有效溝通的重要性,正如華佗《青囊秘錄》所言:“善醫(yī)者先醫(yī)其心,而后醫(yī)其身。”在與患者的交談中,用心去傾聽她們的所思所苦,換位思考,用溫馨委婉之語(yǔ)去治療她們心靈的創(chuàng)傷。聞其言,觀其色,測(cè)其情,寬其心,順其志;“告之以其敗,語(yǔ)之以其善,道之以其所便,開之以其所苦”,打消患者的思想顧慮,消除患者的消極狀態(tài),取得患者的信任和配合。通過言語(yǔ)疏導(dǎo)和情志治療,患者親其醫(yī),信其藥,便可逐漸康復(fù)。
縱觀歷代醫(yī)家都十分重視心理治療在臨床上的運(yùn)用,有時(shí)了解患者的心比了解其病更重要。筆者在實(shí)踐中也深切感悟到“藥之所占只有一半,另一半則全不系藥方,而是心藥也”。針對(duì)患者個(gè)體采用不同方式的心理治療是筆者臨床工作中的一大亮點(diǎn)。比如,對(duì)于職業(yè)女性的肝郁,筆者認(rèn)為“凡病起于過用”。人體是個(gè)有機(jī)的整體,具有適應(yīng)或承受一定限度刺激的能力,但如果超出了人體自身的適應(yīng)程度或調(diào)控能力時(shí),就會(huì)發(fā)病。過勞則氣耗,過怒則傷肝,過思則傷脾,我們只要做到自己的最好就足矣。
隨著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人們對(duì)衛(wèi)生保健的需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鐘南山教授認(rèn)為:“健康的一半為心理健康,疾病的一半為心理疾病。”目前,新的醫(yī)學(xué)模式為生物—心理—社會(huì)醫(yī)學(xué)模式,每一個(gè)人都是自然社會(huì)環(huán)境中的一員,精神心理因素對(duì)患病和治療都有著很大的影響。由于相類似的精神心理因素可以導(dǎo)致不同的疾病,所以筆者為不同的患者進(jìn)行針對(duì)性的心理疏導(dǎo)和調(diào)適,亦可謂“異病同治”,其效甚佳。
結(jié)語(yǔ)
綜上所述,《金匱要略》腎氣丸是補(bǔ)腎氣的代表方劑,其證治體現(xiàn)了異病同治的原則,后世醫(yī)家在這一原則指導(dǎo)下,擴(kuò)大了腎氣丸的應(yīng)用范圍。“異病同治”要辨證使用。師古而不泥古,“同治”可以不同方,亦可為廣義的治法。心病還須心藥醫(yī),遵循“異病同治”之法,注重心理?yè)嵛亢驼{(diào)適,體現(xiàn)了醫(yī)療中的人文關(guān)懷和服務(wù)精神。“異病同治”、“同病異治”都是建立在辨證施治的基礎(chǔ)上,在今后臨床工作中,將繼續(xù)指導(dǎo)我們,并會(huì)得到更為廣闊的拓展和應(yīng)用。
參考文獻(xiàn)
[1]姜德友,黃仰模.金匱要略(案例版)[M].北京:科學(xué)出版社,2007:48.
[2]關(guān)靜,李峰,宋月晗.“異病同治”的理論探討[J].中國(guó)中醫(yī)基礎(chǔ)醫(yī)學(xué)雜志,2006,12(9):650-651.
[3]傅山.傅青主女科[M].北京:中國(guó)醫(yī)藥科技出版社,2011:16.
(收稿日期2015-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