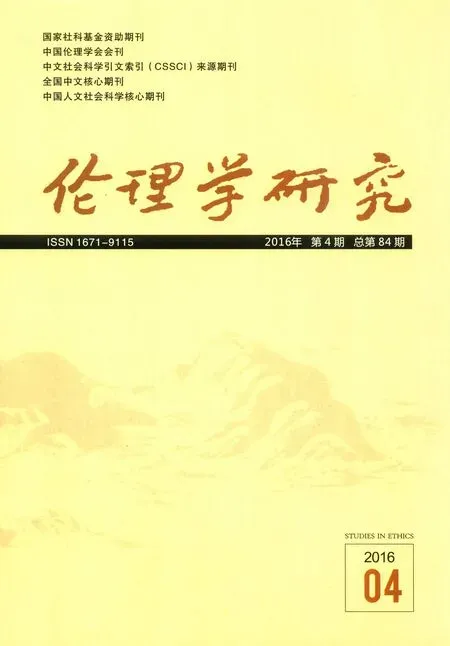論韓非的誠信觀
周四丁
論韓非的誠信觀
周四丁
韓非從富國強兵的目標出發闡述其誠信思想,形成了系統的誠信觀。他認為君主信任他人存在受制于人的道德風險,法律信用卻有利于贏得民心,有利于保護君主權力免受權臣侵蝕,有利于富國強兵;基于信任他人的道德風險和法律信用的價值,韓非提出了“循名責實”的誠信管理論,意在防范誠信風險、彰顯誠信價值。韓非的誠信觀可以為治理當代的誠信危機提供一些啟示。
韓非;誠信觀;誠信管理
誠信是韓非學說中的核心概念,韓非這些關于誠信的論述是比較完整的思想體系,實際上形成了其誠信觀。朱伯崑認為,“韓非同儒家爭論的焦點不是要不要道德的問題,而是如何理解人類的道德生活,怎樣確立和實行封建制所需的倫理規范”[1](P271)。將韓非的誠信觀置于其富國強兵的治理目標中考察,有助于梳理韓非是如何理解誠信以及如何發揮其對富國強兵的作用,也有利于發掘其對當今社會誠信管理的借鑒意義。
一、君主“信人則制于人”的道德風險論
《說文解字》關于“信”含義的解釋多達11種,從道德意義來看,包括言語真實、信任、信用等三層含義。韓非認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則制于人”[2](P159)。此處“信”是信任之義。韓非認為信任他人是將自己的利益寄托在他人道德水平的基礎上,自身利益受制于他人道德水平的高低,如果他人存在道德風險,則會給“主”帶來重大的成本與代價,這種觀點屬于道德風險論。誠信是以雙方信息不對稱為前提,由于君主通過大臣來治國理政,因此大臣比君主更具有信息優勢,“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誠信對行為人的約束主要是對信息優勢方的道德約束”[3](P41)。如果信息優勢方存在道德瑕疵,信息劣勢方就會面臨道德風險。
1.君主信任大臣會導致君權旁落
君主信任大臣,會使大臣因受信任而獲得更多的權力,進而擴大其謀取私利的空間。“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于法,而信下為之也”[3]。韓非的這種論斷遭到郭沫若等學者的批判,認為韓非非常邪惡地把人都當成壞人,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但是,韓非的論斷也很清晰地指出了一個客觀現實,即信任是以權力轉移為標志。挪威學者哈羅德·格里曼通過分析構成信任的五個要件得出與韓非相似的結論:“一個人的信任能夠成為另一個人權力的基礎”[4],哈羅德·格里曼認為,如果A信任B,那么在一段時間內應具備五個要件:A會將某物X置于B的監管之下,A將某物X的支配權賦予B,A看重某物X,B能合理處理X以符合A的利益,A很少防范B對X的支配權。因此,A信任B,B就獲得A讓渡的自由支配X物的權力。依此理論,出于信任,君主將賦予大臣官職,并讓其自由自配行政權力,卻往往疏于防范。但是,韓非認為君臣之間存在根本性的利益沖突,大臣不會從君主利益出發行使行政權,所以君主不能不防范大臣。“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韓非子·內儲說下》)如果君主對大臣缺少防范,君主不僅會損失利益而且會受制于群臣。“鬻寵擅權,矯外以勝內,險言禍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韓非子·三守》)君主的信任,導致大臣在行使行政權、處理行政事物時濫用因信息優勢而獲得的權力,使君主既無從防范大臣,也無法知悉其利益如何受損,因而受制于臣。
2.君主信任妻子也會導致君權旁落
由于同樣具備哈羅德·格里曼的信任五條件,君主信任妻與子也意味著將部分權力的轉讓。妻與子是骨肉之親,為何又不能信任呢?因為妻與子同樣不能基于君主的利益而行使他們基于君主信任而獲得的權力。
一方面,妻與子本來就與君主存在利益沖突,可能會為了謀取自己利益而傷害君主利益。“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為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死見疏賤,而子疑不為后,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韓非子·備內》)解釋了君主與其妻與子存在利益沖突的根本原因,一是夫妻之間色衰而愛馳,二是子憑母貴。由于君主與妻子之間存在利益沖突,所以,“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之死則勢不重”(《韓非子·備內》)。故而,為了防范權力旁落,妻子也不能信任。
另一方面,如果君主能信任妻與子,最終大臣還是會通過妻與子竊取君主的信任;君主信任妻子,就會使奸臣有可乘之機。“為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奸臣得乘于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傳趙王而餓主父。為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奸臣得乘于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傳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韓非子·備內》)最終,對妻子的信任反而使妻子成為大臣的進身之階,使君主而受制于大臣。“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余無可信者矣。”(《韓非子·備內》)如果對妻與子的信任都存在如此大的風險,都有被利用的可能,那么對他人的信任則風險更大。故而,無論多親近之人,亦不能給予足夠的信任。“立功者不足于力,親近者不足于信,成名者不足于勢。”(《韓非子·功名》)不能使人因獲信任而危害自身。
韓非指出信任的風險是為其法治主張服務的。他認為治國理政的合理方式是法治而不是信任他人。“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眾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群官無奸詐矣。”(《韓非子·五蠹》)依靠先天具有誠實守信良好品德的人為官,無法挑選出足夠理想的人才,所以,需要將治國理政納入法治的軌道。
二、“奉法者強則國強”的法律信用價值論
韓非認為“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韓非子·初見秦》)“奉法”的強弱包含恪守法律的嚴格程度,也包含法律信用的程度。“信用是遵守諾言,實踐成約,從而取得別人對他的信任。”[5](P223)如果說信任是授信者將某物的自主權賦予給他人,是權力的讓渡,那么信用則是主體為了贏得客體的信任而主動約束其對所許諾事物的自主權,是權力的自我約束;如果法律以信用為基礎,那么立法者(君主)必須約束乃至放棄其對法律隨意更改的自主權,使法律得到不折不扣地執行,才能取信于民。韓非認為,“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韓非子·主道》)。有學者對此的解釋是“韓非主張君主去除個人的情感因素對執法的影響,完全按照法的規定進行賞罰,做到信賞必罰”[6](P48)。這便是君主為了實現法律信用對權力的自我約束。韓非認為法律信用有利于維護君主統治和實現富國強兵。有學者指出“韓非的法律信用思想是建立在趨利避害的人性基礎上,運用信賞必罰的理念指導,在對法治歷史的深刻分析基礎上建立起來的”[7](P147)。韓非既重視對歷史經驗的總結,也重視理論論證,法律信用是其法治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1.法律信用有利于贏得民心而增強君勢
韓非通過正反兩方面的案例來說明法律信用對于贏得民心的作用。他通過秦民“聞戰則喜”的案例來闡述法律信用對于激發民眾從事耕戰事業的積極性,“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耳。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爐炭,斷死于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者不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死也。”(《韓非子·初見秦》)法律有信用,就能夠贏得民眾的信任,法律就能推行。他以趙國為反面例子,說明如果法律沒有信用,人們便不信任法律,法律便難以實行,“趙氏,中央之國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盡其民力。”(《韓非子·初見秦》他認為趙國之所以沒有實現富國強兵一統天下,主要是由于法律沒有信用,無法調動民眾積極性。“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韓非子·詭使》)法律需要讓民眾有可靠的獲得感,才能贏得民心。
2.法律信用有利于減少君臣權利斗爭而保護君權
韓非認為只有法律信用才能確保君主在權力斗爭中取得勝利,使君主權力免受侵蝕。他深刻地揭露出君臣之間的權力斗爭的一面。“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黨與之具,臣之寶也。”(《韓非子·楊權》)韓非列舉了殷周、齊、晉、燕、宋等國大臣奪取君權的例子來說明君臣之間的權力斗爭引發的政權更迭,“昔者紂之亡,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晉也分也,齊之奪也,皆以群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弒其君者,皆此類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韓非子·愛臣》)。君主雖然擁有天賦權力,但是權力的運行離不開臣民,需要向臣民授權,這就表現為權力的變化性、斗爭性。因此,需要一種新的手段來使君主向大臣授權時并不會產生尾大不掉的權臣,以減少權力斗爭、保持君權的穩定,韓非認為這種手段就是法律。“法律既是權力關系的表述,又是使這種關系正式化和合法化的重要機制。法律規定了權力的分配以及權力的具體內容,同時又規定了權力行使的程序條件,因而成為調整和擴張權力的主要依據。”[8](P33)所以,法律一定要有信用,“法不信,則君行危矣”(《韓非子·有度》),如果君主依法授權,那么臣民所獲的權力便會被法律所限制。“韓非之所謂法,即荀卿之禮加以偏重刑罰之義,其制定之權在人主。而法律既定,則雖人主亦不能以意出入。”[9](P53)法律一經制定就君臣共守,這是法律信用的基本要義。君主守法,就是依法刑賞,不赦宥。“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法制茍信,虎化為人,復反其真。”(《韓非子·楊權》)一旦君主恪守法律信用,大臣只能在法律限定的框架內運用權力,權臣現象將消失。
3.法律信用有利于富國強兵
韓非認為,法律信用是國家強弱的關鍵。“明于治之數,則國雖小,富;賞罰敬信,民雖寡,強。賞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韓非子·飾邪》)國家的強弱不在于人口的多寡、地域的大小,而在于法律信用。法律信用,國小民寡也能戰勝弱敵、廣地來民;失去法律信用,既有的國土與民眾要么失之于敵國,要么失之于權臣。“公孫鞅之治秦也,……,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卻,故其國富而兵強。”(《韓非子·定法》)他以商鞅治秦為例,認為秦國富強的根本原因在于公孫鞅信守法治,調動了民眾的積極性。他依據荊、齊、燕、魏等國的興衰軌跡判斷,這些國家的盛衰與君主的賢愚息息相關,當有為之主過世后,國家隨之弱亡;他認為人治不能長期維持一個國家的強盛,只有堅定不移地實行法治才能實現富國強兵之夢。
三、“循名責實”的誠信管理論
正是由于韓非充分地認識到信任他人的風險和法律信用的價值,所以他認為只有將循名責實之術與法律信用結合起來,才是構建誠信社會可行之道。雖然君主信任他人存在道德風險,但是韓非認為人與人之間需要信任,“恃勢而不恃信,故東郭牙議管仲”(《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他通過“東郭牙議管仲”的案例來說明信任缺失導致管仲見疑于東郭牙以反證信任的重要性。雖然法律信用價值是多維的,但是法律信用也還需要君主通過“術”來維護,“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君無術則弊于上,臣無法則亂于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韓非子·定法》)。所以,需要君主運用術和法律信用為個人的信用提供支撐。
1.誠信是指名實一致
從韓非對“誠信”一詞的使用來看,誠信的含義可概括為名實一致,“名”包括陳述、官職、主張等,與之相對對應的“實”包括事實、貢獻、效果等。《韓非子》一書提到“誠信”3次。“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名號誠信,所以通威也。”(《韓非子·詭使》)名號是指名位、稱號,有協調統一上下行動的作用,名號誠信是指名號與實際情況要相符,即官職爵祿與其實際貢獻相一致。韓非認為誠信還是包括“形名誠信”,“上以名舉之,不知其名,復修其形。用其所生。二者誠信,下乃貢情”(《韓非子·楊權》)。名是指臣民的主張,形是實際效果,形名誠信是指臣民主張與效果一致。韓非認為誠信還有誠實之意。“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韓非子·內儲說上》)子之通過驗證的方法知道左右對自己不誠實。所以,韓非的“誠信”包括誠實、名號一致、形名一致,意思是陳述與事實一致、官職爵祿與貢獻一致、主張與效果一致。
2.誠信管理是通過“循名責實”實現“名實一致”
如果說儒家的誠信是“誠中外形”,是“表現為這種個體德性人格與人文化成的外王事功的內在貫通”[10](P32),那么,韓非的誠信管理則是依靠非常嚴密、完整的“循名責實”的外塑機制來實現,該機制通過綜合運用法術勢編織士民相互監督的網絡來驗證信息真偽。“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韓非子·南面》)君主對于大臣所說之話,要通過查證其來龍去脈以知其真偽。
至于如何查證來龍去脈,韓非則提出參伍之道,賞告奸、連坐等方法。“參伍之道,行參以謀多,撰伍以責失。”(《韓非子·八經》)“參”是指要有多條相互驗證的信息來源渠道,“伍”是指運用一物與他事物之間的聯系來驗證事物的合理性;參伍之道就是驗證士民的陳述是否符合事實。如果僅憑一個人的內在的道德修養,則無法保證其所提供信息必然是真實的,但是通過參伍之道來驗證,則可以有效判斷信息的真實性;并且驗證程序的存在使得士民不敢提供虛假的信息。“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韓非子·定法》)士民不誠信的行為往往是隱蔽的,有些也無法通過君主一人的驗證而判斷真偽,于是,韓非極力提倡公孫鞅的賞告奸與連坐之法,這是要編制一張相互監督之網,使不真實的信息能立即得到驗證與揭露。參伍之道,賞告奸、連坐等方法都是君主控制臣民言行的方法,通過嚴密的控制,使臣民誠信。控制是管理的功能之一,韓非的誠信管理是通過信息監控來實現的,一切不誠信的行為都會被揭露且代價沉重,使人們不敢不誠信。
當然,“循名責實”的外塑機制還是以法律為中心,使臣民的行為都符合法律。“其信任的原則是從國家利益出發,一切以法律為準繩與教材。”[11](P123)法律也是檢驗誠信的標準與手段,在法律標準之下,君主知道是否名實一致,將“賞告奸”、“連坐”等制度化、法律化,法律也就是檢驗誠信的手段。
3.誠信管理以君主自律守法為前提
君主依法行賞罰是法律信用的前提。雖然君主是法律的制定者,但是法律一旦頒布,君主也要不折不扣地執行,不能因為自身的喜好而影響法律賞罰的實施。“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韓非子·飾邪》)只有君主守法,法律信用才能建立起來。“信賞,以賞者賞,以刑者刑,因其所為,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規矩既設,三隅乃列。”(《韓非子·楊權》)君主守法,臣民所做的好事與壞事都能得到相應的賞罰,這才是臣民誠信的原因所在。“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墯其業;赦罰,則奸臣易為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韓非子·主道》)如果君主違背法律有功不賞,功臣的積極性便會喪失,而其他人則會通過贏得君主的歡心而不是為君主建功立功來獲得賞賜;違法者也會因為免于懲罰而更加為所欲為,國家的誠信便會蕩然無存。所以,“飭令則法不遷,法平則吏無奸。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售法”(《韓非子·飭令》)。君主自我約束而遵守法律,則士民趨于誠信。
[1]朱伯崑.先秦倫理學概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
[2]韓非.韓非子[M].高華平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0.
[3]胡曉萍.信息不對稱條件下的誠信成本和價值選擇[J].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5).
[4][挪威]哈羅德·格里曼.權力、信任和風險:關于權力問題缺失的一些反思[J].哲學分析,2011(6):3-20.
[5]辭海[Z].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
[6]王威威.老子與韓非的無為政治之比較——從權力與法的角度看[J].哲學研究,2013(10):42-48.
[7]周慶峰.韓非法律信用思想基石及其建構[J].江西社會科學,2014(6).
[8]胡玉鴻.以法律制約權力辨[J].華東政法學院學報,2001(6).
[9]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7.
[10]李景林.誠信觀念與道義原則[J].天津社會科學,2012(2).
[11]王曉明.韓非的信任理論[J].石河子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3).
周四丁,湖南師范大學道德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湖南理工學院政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