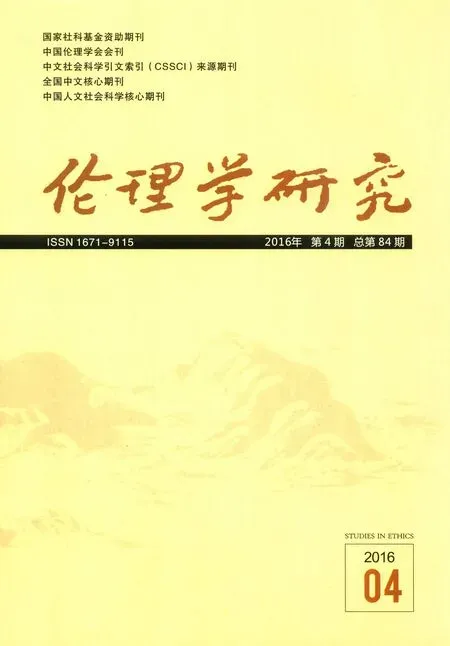人性之維:亞里士多德論邏各斯
謝芳
人性之維:亞里士多德論邏各斯
謝芳
人與其他物種有質的區別,人的存在有自身的尊嚴。亞里士多德認為邏各斯是人的靈魂之道,而中道是邏各斯的德性原則,也是人的尊嚴的體現,遵循邏各斯的道德實踐活動則是人的幸福與尊嚴的真正實現。
邏各斯;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幸福
《尼各馬可倫理學》一書的中心議題是沿襲蘇格拉底以來對人的存在本質的拷問。這同時也是自古希臘開始至今,哲學界不斷在推進思考的一個重要的哲學問題。亞里士多德給予了別致的答案,并引起了此后數千年哲學界的深刻思考。亞里士多德在第一卷第七章中將人的靈性分為三個部分:植物性部分、動物性部分和專屬人的部分,那么人整體的本質是個三連貫:獸性—人性—神性。人有靈性,亞氏又稱之為慧根,因而人有神性的部分,可人又有顯而易見的肉體需要,亞氏認為,這是動物性,是屬于獸性的部分。可見,人集三種品性于一身。可神、人、獸卻是三個根本不同的物類,亞氏認為人畢竟不是神,也不是獸,人是人,人不可能變成另一種東西,這就注定了人可能有三種存在形態:無限趨近于神(但永遠也不可能成為神,比如儒家訴求的圣人);既不趨近神性也不趨近獸性的人;無限趨近于獸。第一種狀態無疑是做人的極致狀態,第二種狀態是亞氏所謂的中庸狀態,是做到了人的本分,無可厚非,可是第三種狀態卻是萬眾譴責和詬病的,也被稱為獸類。理論上雖然潛在人的三種存在狀態,可實踐中,做到第二個狀態是非常困難的,因為“要在所有的事情中都找到中點是困難的。”[1](P55)人唯一能把握的,是盡量做到合適地處理三者的分量,這就注定了做人是個艱苦的嘗試過程。只有不斷嘗試從下往上攀,從人性趨近神性,才能避免自己墜入獸性,這是人的本質,也是人的尊嚴使然。那么,什么是人的尊嚴?康德認為“超越一切價值之上,沒有等價物可以替代,這就是人的尊嚴”[2](P87)。亞里士多德認為,從人性向神性攀越的這種普遍意義上的人的尊嚴純粹植根于人的理性即邏各斯。
一、邏各斯與人的靈魂結構
人與植物的區別顯而易見,人既具有植物所有的生長和營養的生命活動而且還具有植物所沒有的感覺生命活動,這一點似乎從來就沒有來自理論界甚至是百姓日常生活的質疑或困惑。但人作為一種高級的靈長類動物與一般動物的區別是什么,作為自然界中的具有特殊位置的一個元素,人的類本質何在?這個問題從古希臘開始,一直是包括哲學在內的各個社會科學爭論不休卻一直懸而不決的基礎問題,也是一個最具形而上學特色的問題。特別是人身上所具有的獸性、人性和神性之間是一種什么關系?只有首先解決了人的類本質問題,把人從動物界中區別出來、提升出來,使人遵循屬人的屬性,走屬人的發展道路,才能使人這個族類得到可持續性繁衍與發展。
17世紀法國布萊士.帕斯卡就人的本質問題曾提出過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他認為人在宇宙中相對于其他物種來說是更加脆弱的,但又是偉大,其全部的偉大就在于人有思想,思想是人的全部尊嚴所在。這個思想相對于先前對人諸多定義無疑是先進的,具有極其深刻的意義,他把人當作一個有特殊性質活動的生命而不是一個靜止的物體,接近了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對人的類本質的界定:“一個種的整體特性、種的類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動的性質,而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恰恰就是人的類特性”[3](P57)。植物自然地生長,動物靠本能追求感官的滿足與快樂,而唯獨人能夠有思想、有意識地自由選擇生命活動。無疑這個思想是符合人的本性的。但筆者認為,在人性界定這個問題上,無論是帕斯卡還是馬克思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這種對人的定義盡管觸及到了人的類本質但顯然還沒有深入,或者他們還沒有觸及到人的社會性。因為思想就其本性來說,是一種可驚嘆的、無與倫比的東西,自由的思想能夠創造、發現、選擇,但它的偉大可能也正是它的悲劇之處。因為人有自由的思想,表面上看起來,它不僅能夠主宰人自身,而且還能主宰其他物種甚至整個宇宙,它可以高尚地選擇過一種神圣的生活,也可以選擇過一種普通的屬于人的生活,最為要命的是,它也能選擇過一種屬于獸性的奴性生活,一切聽從感覺的召喚。因為就思想本性來說,它有兩個發展路徑,即向善和向惡。而現實生活證明,“一般人顯然是奴性的,他們寧愿過動物般的生活”[1](P11)。那么當人們運用自由的思想,選擇過一種奴性生活的時候,人便會降低為禽獸。由此可見真正的人與禽獸之間只是一步之遙,無怪乎尼采曾經說:“人便是一根索子,聯系于禽獸與超人間——架空于深淵之上。是一危險底過渡,一危險底征途,……”[4](P8)尼采所言的超人應該指的是真正意義上的人、高尚的人。所以人與禽獸的區別不應當只規定為自由的思想,作為自由的思想本身應該還要具有某種屬性或者德性,才能保障或者保證人之為人的類特征或者類本質,那么這個屬于思想本身的德性或者屬性是什么呢?
對于這個問題,筆者認為亞里士多德以一種實踐的態度給予了我們很好的答案——邏各斯或者有理性。亞里士多德在第一卷第七章中闡述“屬人的善的概念”時,提出了一個問題:什么是屬人的活動?“我們是否更應當認為,正如眼、手、足和身體的各個部分都有一種活動一樣,人也同樣有一種不同于這些特殊活動的活動?那么這種活動究竟是什么?”他運用了在《范疇篇》和《形而上學》中關于“實體”的界定方法,將屬人的生活與其他物種的生活進行了對比的區分,“生命活動也為植物所有,而我們探究的是人的特殊活動。所以我們必須把生命的營養和生長活動放在一邊。下一個是感覺的生命的活動。但這似乎也為馬、牛和一般動物所有。剩下的是那個有邏各斯的部分的實踐的生命(這個部分有兩重意義:一是在它服從邏各斯的意義上有,另一則是在擁有并運用努斯的意義上有)”[1](P19-20)。亞里士多德在第一卷第十三章考察人的靈魂本性時也進一步指出,“人的靈魂有一個無邏各斯的部分和一個有邏各斯的部分”[1](P33),亞里士多德把靈魂的無邏各斯部分又分為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指造成營養和生長的那個部分,亞里士多德稱之為普遍生物的能力德性,這個能力德性部分是普遍享有的、植物性的,是所有生物共有的,存在于從胚胎到發育充分的所有生命物中,因而也就不屬于人的德性或者人的本質。第二個部分是欲望部分,即無邏各斯的、卻在某種意義上分有邏各斯的部分,這個部分促使他們做正確的事和追求最好的東西。因而亞里士多德又認為欲望的部分更適合于說是有邏各斯的。第三個部分是與第二部分并列的,即抵抗、反對邏各斯的部分,當我們要它向右時,它偏偏向左,亞里士多德稱之為“沖動”的部分。亞里士多德認為,第三個無邏各斯部分盡管在實踐中往往表現為抵抗和反抗邏各斯,可是其本性確是“完全合于邏各斯的”[1](P34)。因而這個部分具有兩重性,在具有自制者、節制者、勇敢者的身上它是聽從邏各斯的。按照亞氏的理解,靈魂無邏各斯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其實同是指靈魂的欲望部分,欲望部分的靈魂既能在某種意義上服從邏各斯,但在一些不能自制者的身上它常常是抵抗、反抗邏各斯的。
通過對無邏各斯部分的分析,亞氏認為靈魂的邏各斯部分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在嚴格意義上具有邏各斯,這一部分是指本身就具有知識理性,但這個知識理性只是理論意義上的、嚴格意義上的具有,而不是實踐意義上、經驗意義上的具有,關于這一點非常明顯地看到,亞里士多德受到其老師柏拉圖的回憶說的影響;另一個部分則是在聽從邏各斯的意義上分有邏各斯。而聽從的這部分,它只是在本性上完全合于邏各斯,或者說具有服從邏各斯的潛能,但普遍情況下,特別是在不能自制者身上,它是反抗邏各斯的。根據亞氏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么一個理論假設:即邏各斯是特屬于人的潛能性本質,而且只不過是一種潛能性而不是現實性的東西,這是人與其他物種的本質區別,也是人的存在尊嚴所在。這個理論假設包含以下的意思:首先,人的靈魂潛在地具有邏各斯的功能和品質,但它畢竟還不是一個現實的存在,要把這種潛能變成現實需要人的實踐努力,因而人是否具有真正的邏各斯主要體現在其現實的活動上,這就指出了邏各斯的實踐性質,如果不實踐就如同沒有邏各斯的其他物種;其次,靈魂邏各斯的高貴之處就在于它能“辨別善惡”,因而邏各斯的德性就表現在對善的追求上,如果運用邏各斯去作惡,邏各斯就喪失了本來的德性,人就陷入與畜生同等的境地;最后,既然邏各斯具有一種實踐的性質,具有動態性質,因而個體靈魂邏各斯德性的成分或者程度就不會是確定的,會有差異性,我們評價它的正確與否就沒有一定精確的標準,“只能因時因地制宜,就如在醫療與航海上一樣”[1](P38)。這正是亞里士多德的深刻之處,因為他真正看到了人的本質的社會性。
綜上所述,亞里士多德認為“那個有邏各斯的部分的實踐的生命”是人特有的類本質活動,因而也是人的存在尊嚴,這種專屬人的尊嚴需要人通過現實活動來維護,因為“我們怎樣的就取決于我們的實現活動的性質”[1](P37)。因而人的活動就不僅僅表征為有思想,而更加應該是思想的遵循或者包含著邏各斯的實現活動,或者說人的活動應當是靈魂的一種合乎邏各斯的實現活動與實踐,一個高尚的人的活動就應該是良好地、高尚地完善這種活動。
二、邏各斯與道德選擇的中道原則
正如學者馮軍所言,“人的尊嚴不在于他有理智、知識,而在于他能不能受自然欲望的束縛去追求自己所設立的目標”[5](P226)。人的尊嚴不僅在于他有邏各斯、有理性,而且還要在于他的理性或邏各斯是否有一定原則約束。人的靈魂通常被分為兩部分,一部分屬于理智部分,這部分本身就擁有并運用邏各斯進行活動,它主要負責辨別是與非、真與假的事情,只有完全符合這部分靈魂本性的邏各斯才是正確的邏各斯,而人的行為也應該按照正確的邏各斯去做,而這個正確的邏各斯就是就是明智,它是這個部分靈魂的一種德性:理智德性。亞里士多德認為德性是事物或人固有能力的實現活動,人的德性就是“靈魂的遵循或包含著邏各斯的實現活動”,或稱之為“立己的實存(或實現)活動”。這里所說的邏各斯是一種正確的邏各斯,即合乎明智的品質。邏各斯幫助我們確定目的,也使我們選擇實現目的的正確的手段。而靈魂的另一部分屬于非理智部分,比如情感、欲望、意志等,這一部分本身并沒有邏各斯,但卻在某種意義上分有邏各斯,或者說這個無邏各斯的部分能夠選擇聽從或者服從邏各斯的指令,而能夠服從邏各斯的指令的品質我們稱之為道德德性。
無論是理智德性還是道德德性,它都是合乎邏各斯的。那么邏各斯自身有沒有一個要遵循的原則或尺寸呢?或者說邏各斯本身的德性是什么呢?亞里士多德說,盡管具體行為中的邏各斯標準是不確定的,我們對它的評價也只是“粗略的、不很精確的”。但是還是可以為邏各斯的德性制定一個基本的規范性的標準,這個標準就是適度,或者稱之為中道,他提出“善德就在于中庸——則適合于大多數人的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應該行于中庸,行于每個人都能達到的中庸”[6](P204)。中庸是什么?中庸就是適度,是既不太多也不太少的適度,它是兩種惡即過度與不及的中間。亞氏盡管認同適度具有一定的客觀邊界,但也具有主體性特征,它不是一,也不是對所有的人都是相同的。因為這個適度不是事物自身的而是對人而言的中間狀態。邏各斯的德性必定是以求取適度為目的。亞氏對于這種適度進一步界定為在適當的時間、適當的場合、對于適當的人、出于適當的原因、以適當的方式進行的行為。
三、實踐邏各斯與人的幸福和尊嚴實現
德性是一種品質,每種德性都既使得它是其德性的那事物的狀態好,又使得那事物的活動完成的好。那么“人的德性就是既使得一個人好又使得他出色地完成他的活動的品質”[1](P45)。這就需要實踐或者踐行,任何道德德性都需要實踐活動,才能實現從人性向神性的不斷攀越,才能實現人的最高善——“幸福”。可見,亞里士多德認為人之為人的重要本質在于尋求受實踐邏各斯制約的實踐。
首先,要維護作為人的尊嚴就必然要培養并養成屬人的德性,亞里士多德認為德性的養成與實踐有關。這里包含這樣的含義:人要實踐才能使邏各斯的德性由潛能變成現實,這種實踐在時間上是窮盡一生,在性質上必須是正確的或者合乎正確邏各斯的實踐。只是亞氏所指的實踐還不是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社會實踐,而可能更多的是指一種個體的心理體驗活動,例如,他把情感活動也作為一種實踐就是證明。因為它認為檢驗實踐正確與否有一個感情上的標準即快樂或者痛苦,“我們或多或少地都以快樂與痛苦為衡量我們行為的標準”[1](P41)。盡管亞里士多德也謹慎地指出,這種快樂與痛苦的情感必須是正確的,但何為正確的情感并沒有合理的說明。
首先,道德德性通過習慣養成。“我們所有的道德德性都不是自然在我們身上造成的。……由自然造就的東西不可能由習慣改變。”[1](P35),這里的“自然”指的應該是一種必然性,意思是說具有人的形體意義上的人并不必然具有道德德性,如果道德德性是一種必然性,那就很難被改變。我們從亞里士多德的以上論述中可以看到以下幾個論點:第一,人的靈魂具有德性的能力,即邏各斯,它是先以潛能的形式為我們所獲得;第二,這種潛能必須通過活動而成為現實,也就是說,德性功能不同于其他功能,我們必須先做它要求做的事,然后才可以獲得它,比如我們通過節制而成為節制的人,通過做公正的事成為公正的人。這是強調先有了活動才會有相應的適合的品質,因為適度本身是因時因地不同的,其中的把握必須在具體活動中;第三,德性產生、養成、實現于好的活動,同樣毀滅于壞的活動,“德性成于活動,要是做得相反,也毀于活動;同時,成就著德性也就是德性的實現活動”[1](P41)。具體情境中以不同的方式行動,有人變得節制,有人變得放縱,“一個人的實現活動怎樣,他的品質也就怎樣”[1](P37)。所以人們從小就應該注意實現活動的性質。
其次,亞里士多德認為實踐德性是人之為人的第一步,但做合乎德性的行為還不能證明就是一個有德性的人,或者說還不能說你就是一個高尚的、尊貴的人。因為一個人從事合乎德性的事情有可能是出于一些偶然性的因素,譬如別人的指點或者機緣巧合。只有當一個人明確地知道或者意識到自己所從事的行為的性質為善,并是在諸多可能性條件下經過靈魂邏各斯的自由選擇,而這種選擇是出于對行為本身的善的選擇,而不是基于其他功利性目的。亞里士多德特別強調的是這種自由選擇必須是出于一種穩定的品質,因而不是一次性的或者偶性的,而是一如既往的,貫穿一生的。
因此一個人要被稱為有德性的人首先他必須做德性的行為,因為只有先運用它們然后才能獲得它們。但做了德性的行為還不能是有德性人的充分條件,他還必須“像公正的人或節制的人那樣地做了這樣的行為”[1](P42)。這里的“像公正的人或節制的人那樣做”即是指有德性人的對行為的明確意識、對行為的自由選擇性及行為品質的穩定性等特征。只有這樣做,人才能保證了做人的尊嚴,也就實現了人的幸福。
四、亞里士多德關于邏各斯理論的現代啟示
邏各斯自身并不是一種現實的德性,是人專有的一種潛在的能力。按照亞氏的說法,這種能力是指“自然賦予我們接受德性的能力”,這種能力的特性就是“我們先運用它們而后才能獲得它們。”[1](P36)這是人與動物有根本區別的方面,是人完成其存在的類本質特性,并得以在這個世界上展開其獨特的存在活動的屬性。這些觀點有力地批判了當代社會中過渡強調人欲望的泛濫、追求感官生活、過渡張揚個性等感性主義思想。人,尤其是現代的人要成其為一個人,不至于降為動物,就必須遵循以下幾條原則。
首先,運用邏各斯的規范性克制肉體的感官欲望,獲取身體的善。亞里士多德認為對肉體的欲望控制需要兩種德性,即勇敢和節制。與勇敢相對立的兩種惡既是魯莽與懦弱,一個勇敢的人敢于面對高尚的死,盡管勇敢的人內心也會對超出人的承受能力的事物感到恐懼,但是他仍能夠以正確的方式,按照邏各斯的要求并為高尚之故,對待這些事物,比如面對暴恐事件的挺身而出。魯莽的人由于不清楚狀況也不度量后果因而可能在危險到來之前沖在前面,但當危險到來時卻退到后面。懦弱的人出于一種本能,在危險來臨時往往選擇逃之夭夭,這些都是奴隸性和畜性的行為。而勇敢的人在行動之前平靜,在行動時精神抖擻。因為勇敢的人有適當的原因、以適當的方式以及在適當的時間,經受住該經受的,也怕所該怕的事物。他這樣選擇和承受是因為這樣做事高尚的,不這樣做事卑賤的。所以一個人的勇敢不應當出于強迫,出于強迫是由于為了逃避可怕的事物,也不應當出于痛苦的驅動,出于痛苦的驅動的人并沒有預見到他們要遭遇的危險,所以勇敢僅僅應當出于高尚,出于邏各斯。勇敢的人敢于面對對于人來說是或者顯得是可怕的事物,他承受這些痛苦并非出于意愿,它肯承受它們是因為這樣做是高尚,不這樣做是恥辱。所以,面對突發的危險表現出無畏懼和不受紛擾的勇敢必然是出于品質。
而節制德性是指在快樂方面的適度,這種快樂不是指靈魂的快樂,而是指肉體方面的欲望得以節制的快樂。與節制相反的兩種惡是放縱與吝嗇,而其中尤以放縱為最惡,放縱的快樂不是屬于整個身體的,而只是身體的某個部分的。放縱會受到譴責,因為這種感覺不是我們作為人獨有的感覺,而是我們作為動物所具有的感覺,沉溺于這種放縱的快樂,是獸性的表現。放縱的人欲求所有快樂或那些最突出的快樂,他受欲望的宰制,只追求這些快樂,而不追求別的東西,所以他感覺到兩種痛苦:得不到的痛苦和渴望快樂的痛苦。而節制的人被稱為節制則是由于他在沒有得到快樂或回避快樂時不感覺痛苦。把人從獸性中解放出來的唯一辦法就是遵循邏各斯的指引。這些思想有力地抨擊了當今社會存在的享樂主義、奢靡主義思想,令人深思。
其次,運用邏各斯的規范性控制對財產、榮譽的過度追求,培養外在的善。亞里士多德把人們對于財富、金錢、榮譽等的追求,看作是對外在善的追求。 這種外在的善包括這樣一些品質:慷慨、大方、大度以及其他與榮譽相關的德性。慷慨與大方與財富相關,是財富方面的適度。慷慨是就一個人給予和接受財物的行為而言,揮霍和吝嗇是財物給予和索取方面的過度與不及。一個揮霍的人是一個在自我毀滅的人,而吝嗇則顯得比較與生俱來,因為多數人都喜歡得到錢財而不是給予,在給予上不及,在索取上過度。慷慨的人主要特征在于把財物給予適當的人,而不是從適當的人那里,或從不適當的人那里得到財物。所以慷慨的人總是給予而不是索取,總是把好處給別人而不大容易去接受好處,慷慨的人也不取不當之物,當然慷慨的人也會珍惜自己的財產,這種珍惜體現在以適當的數量、在適當的時間給予適當的人。大方不像慷慨那樣同所有處理財富的行為有關,而只是對于花錢的鋪張來說的。它指的是數量上超過慷慨的花費,意味著大數量的適度的花費,只有把大筆錢花在重要事物上人才是大方的。大方的人是慷慨的,但慷慨的人卻不一定是大方的。亞里士多德認為在對待財富問題上,盡管這是純屬人的活動,但要真正合乎人的屬性,就必須運用邏各斯來判斷、選擇適合于人的行為方式。因此那種無度的索取和不正當的給予的行為都不是合乎人的德性的行為,比如貪污、腐敗、賄賂等。
沒有德性的人很難處理這些外在的善,因而往往使人自己陷于非人的境地,從而喪失了一種屬人的目的性存在,成為純粹的工具性東西。因此運用邏各斯追求適度的德性是人之為人的本質所在,也是人之為人的尊嚴所在,是由人性攀越神性的一根繩索。現代社會的人們在五彩繽紛的物欲世界里似乎已經走得很遠,人們一邊是物質層面的富有,另一邊卻是精神層面的荒蕪。恣肆放縱于肉體的快樂,精神卻在無信仰的荒漠上失去自我。因此重新回到先哲尋找現代人失落的理性,重拾人之為人的邏各斯本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M].廖申白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2][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學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3][德]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德]尼采.蘇魯支語錄[M].徐梵澄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5]甘紹平、葉敬德主編.中國應用倫理學[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
[6][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M].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謝 芳,湖南師范大學道德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衡陽師范學院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
省情與決策咨詢研究課題“湖湘精神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研究”(2015BZZ001);湖南省教育廳科研項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視域下湖湘精神研究”(15C0223);湖南省社科基金項目(11B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