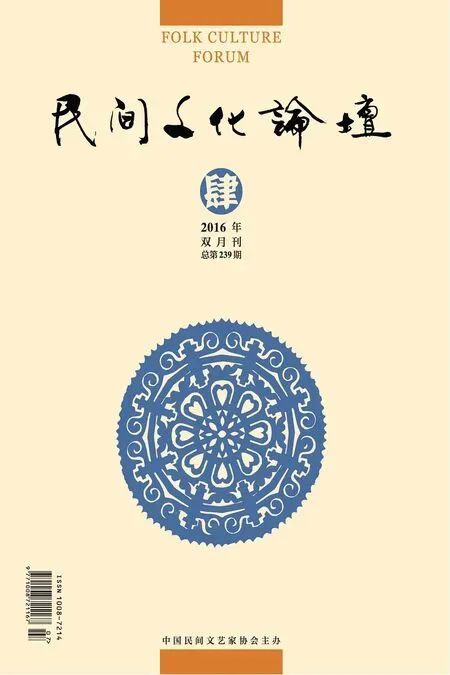四川博物院藏11幅格薩爾唐卡畫的初步研究—關于繪制時間問題
李連榮
四川博物院藏11幅格薩爾唐卡畫的初步研究—關于繪制時間問題
李連榮
關于《格薩爾》史詩的“連環畫”(或故事畫)由來已久。但是比較完整全面地用繪畫展示《格薩爾》史詩的“全部內容”,還是要數本文介紹的四川博物院所藏11幅格薩爾唐卡畫。在本文中,筆者主要通過分析此套故事畫的故事內容,探討了它的繪制時間、地點等問題。筆者認為,這套故事畫繪制的時間,最早應該不會超過16世紀,也即它是繪于清代的一套故事畫。更確切一點說,它最早繪制的時間應該是18世紀左右,最晚也不會晚于19世紀晚期。繪制地點應該位于昌都至康定的某個地區。明正土司有可能是此套繪畫的主持人或資助者。
《格薩爾》;唐卡畫;四川博物院;康定
一、引言
最近由四川博物院、四川大學博物館科研規劃與研發創新中心編著的《格薩爾唐卡研究》(中華書局,2012年3月)一書,比較細致地公布和介紹了四川博物院(以下簡稱“川博”)所藏11幅格薩爾唐卡畫的分解圖像及題錄(或題記)全文。其中,還附錄了一幅《格薩爾及三十大將》唐卡畫及石泰安等人的相關研究文章。筆者認為,這11幅唐卡畫的公布在《格薩爾》學界是一件重大事件。盡管這11幅唐卡畫于1958年①Rolf A.Stein, Peintures tibétaines de la vie de Gesar, Ars Asiatique, V, 4, 1958,pp.243—271.中英文譯稿可參見,石泰安:《格薩爾畫傳》,劉瑞云譯,Rolf A.Stein, Tibetan Paintings of the life of Gesar, Arthur Makeon Trans.,《格薩爾唐卡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199—227頁。、1988年②王平貞:《四川省博物館藏〈格薩爾王傳〉唐卡的初步研究》,《格薩爾研究集刊(3)》,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8年,第418—434頁。、2004年③陳志學、周愛明:《稀世珍寶〈格薩爾〉唐卡》,《中國西藏》,2004年1期,第36—39頁。公開發表并做了相關研究。但相對于此次公布來說,以往的公布情形就相形見絀了。以下筆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這11幅唐卡畫的繪制時間與地點稍作解讀,以求方家指正。
以《格薩爾》史詩為題材的“連環畫”(或故事畫)由來已久。據說8-9世紀在拉薩建立的舊木如寺(???????????????????),是為紀念格薩爾大王之驍將霍爾辛巴梅茹孜而建立的,晚近就有人拍攝到了其新寺院中題記為“辛巴梅茹孜”的壁畫④??????????????????????????????????????????????????????????????????????????????????????????????????????????????????????????????????????????????http://www. gesar8.com/article/word.aspx?id=728。遙想當年,若當時的寺院完整保存至今,我們就可以欣賞到其中所繪的精彩故事和栩栩如生的眾英雄們了。當然16-17世紀以后,西藏繪畫中選取《格薩爾》史詩作為題材,繪成故事畫,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了,比如我們知道17-18世紀羅布林卡中所繪的《賽馬篇》《北方降魔篇》等故事⑤?????????????????????????????????????????????????????????????????????????????????????????????????????。但是比較完整全面地用繪畫展示《格薩爾》史詩的“全部內容”,還是要數本文介紹的四川博物院所藏11幅格薩爾唐卡畫。此外,我們還曾看到過相關《格薩爾》史詩的不少故事畫,比如白瑪次仁等國外學者也曾公布和研究過幾組故事畫①Pema tsering. Historische, epische und ikonographische Aspekte des glin ge-sar nach Tibetischen Quellen, In Die mongolischen Epen: Bezüge, Sinndeutung und überlieferung (Ein Symposium), ed. by Walther Heissig.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1979,pp.158-189.(中文見《民族文學譯叢》第二集史燕生譯稿,中譯文缺圖片。)。
除去這類故事味道很濃的繪畫,在西藏歷史上還出現過許多以《格薩爾》史詩中的個別英雄為題材的單幅英雄畫,如上面提到的英雄辛巴梅茹孜的畫。其中,尤以格薩爾大王的形象為盛多。這類繪畫,我們一般稱為“格薩爾王騎征像”,它的特點是以格薩爾大王為核心人物創作的類似“佛、菩薩、護法神”等的唐卡畫。由于類似于佛畫,因此,現在所見此類繪畫多與英雄崇拜和信仰的關系比較密切。比如,比較典型的代表是德格印經院的大小雕版畫②小雕版畫可參見拙著《格薩爾學芻論》,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年,第52頁。大雕版畫可參見中共德格縣委?德格縣人民政府編:《香巴拉神殿——德格》,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57頁。等。事實上,此類繪畫從起源上看,起初有可能是用作講故事的道具③關于這個看法,已經有眾多學者指出過,比如石泰安:《西藏史詩與藝人研究》,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86頁。。也即它可能也是一幅故事畫,正像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四川博物院所藏的11幅中第6幅圖畫一樣。至今,這類繪畫還隨著時代發展,展現出了各種面貌④李連榮:《格薩爾學芻論》,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年,第40—57頁。。由于與本文關系不近,在此不贅。
正如上面提到,本文中關心的重點并不是繪畫,而是故事。因此以下根據這套系列連環畫所講述的《格薩爾》故事(史詩內容)特點,來考察其繪制時間與地點等問題。
二、“題記”的解讀與補充
首先我們來指出一些“題記”解讀方面的問題。當然,此次能夠全面詳細地公布每條題記和分解圖畫,是對學界的最大貢獻。但筆者認為也有一些瑕疵存在,這里根據筆者淺見,略做表述。
(一)據筆者統計,整套繪畫的全部題記約820條。其中有兩條遺漏:即第9幅20-2中的?????????????????????????(曲奔⑤現行本中稱為 ??????????即音為“曲珍”。背負鐵樣的情景)和第11幅16中的????????????????????????????????????????(世界大王去往天界的情景)。
(二)一些題記的解釋估計有誤,比如第11幅中的《地獄篇》,筆者認為應該是《地獄救母》而非解讀者所謂的《地獄救妻》。依照《格薩爾》史詩的傳承特點來看,第一,作為康區類型的《格薩爾》史詩,基本上不會講述《地獄救妻》的故事,很顯然這是“安多型”《格薩爾》的特征之一;第二,從所列“題記”可以推斷,講述的就是“救母”情節而非“救妻”情節(比如題記12中出現???????即果薩[格薩爾之母],其內容可與木刻版《地獄救母》故事對照,在此不贅)。另外如第9幅中的一條“題記”(23)???????????????????????????????????????????????????????????????????(嚓香、晁同二人在打獵的地方,得到金邊梵文經卷的情景),很顯然這里得到的是“漢文的金頭書信”而非“金邊梵文經卷”,這個情節見于《漢嶺傳奇篇》故事的開頭部分,漢公主通過射箭(或托飛鳥)帶信給格薩爾的情節,正是以上兩位得到了書信,而且晁同在向格薩爾匯報此事時還隱瞞了自己私藏書信上的憑證“金頭”之事。
(三)題記中“錯字”糾正。本書題記解讀者依據對《格薩爾》史詩的熟悉和良好的藏文功底,非常正確地解讀和糾正了題記中的許多錯別字,這是非常可貴的貢獻。這從石泰安對“題記”內容解讀的比較中,就可以看到本書著者的成績。很顯然石泰安及其給他提供幫助的藏族人,沒有做到這樣精細。但是,在這里本書著者也受到了時代和方言或多或少的影響,有些糾正字詞錯誤方面表現出了猶豫不決的情景,有時候本書著者也打上了問號,比如第4幅題記2-7中???????????????????????????????????????????????(覺如給藏地寺院?分配綿羊)。筆者認為,此處不應該把???????(思考)糾正為??????(寺院),而應該是?????(高原)。這從1661年完成于康區江達縣波羅寺的整理本《分大食財宗》和1723年完成于拉薩的整理本《霍嶺大戰》中就能見到?????????(高原西藏、高原吐蕃、高原藏人),這是《格薩爾》史詩抄本中一個非常頻繁的詞組。特別是前者,為我們解讀康區流傳的《格薩爾》抄本和康區方言讀音的正字,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參照(例如康方言讀音特點之一,ang音讀作ong音,如khang讀作khong)。這樣一來,第3幅題記2-7中的??????????????????????????????????(給高原藏地分配水晶的地方),第5幅題記1-2中的 ??????????????????????????????????????????????????????(覺吉為高原藏地分發金子的情景)等等都可以糾正為?????(高原)了。
總之,“題記”的解讀是以《格薩爾》史詩故事為基礎的,《格薩爾》史詩本身的傳承由于時代、方言區、記錄者的文字水平等的差異會呈現出各種各樣的差別。比如第10幅圖中的一條“題記”(12-2)?????????????????????????(嚓香發箭圈地的情景),解讀者將其放置在了故事結束部分,而筆者認為是否可以譯為“嚓香(丹瑪)表演射箭技藝”,將故事內容放置在比試階段更為合適呢?
三、關于繪畫時間與地點
關于這套唐卡畫是什么時候創作的,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如有說明代,有說清代等①李連榮:《格薩爾學芻論》,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年11月,第42頁。。筆者認為,它最早不會超過16世紀。除了從畫風上大家已經確認的那樣,作為噶瑪噶智畫風的這套系列繪畫,不可能超越它的畫風產生的歷史。正如一些學者指出的噶瑪噶智畫派成立的時間為16世紀②康?格桑益希:《噶瑪噶孜畫派唐卡藝術的與文化審美》,《青海民族學院學報》,2008年第1期,第59頁。,因此它也不會超越這個時間段存在。此外,筆者從這套繪畫的故事內容方面,也可以推導出上述時間,主要證據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一)證據之一:鳥銃(槍)
鳥銃或鳥槍傳入中國最早的時間是明朝。一般認為是1495年或1542年(即明朝弘治和嘉靖年間)兩種說法。來源地為嚕密(據說位于小亞細亞半島或土耳其,16-17世紀以其火繩槍(arquebus)出名,曾出口至阿拉伯、也門和印度,備受歡迎③Robert Elgood. Firearms of the Islamic World: in the Tareq Rajab Museum, Kuwait,London: I.B.Tauris,1995.pp.37—40.)和日本兩地④閻素娥:《關于明代鳥銃的來源問題》,《史學月刊》,1997年第2期,第104—105頁。。作為介于印度和中原內地之間的西藏,何時和何地傳入這種武器,雖暫無法考察,但最早也應該不會超過16世紀。從一些文獻記載來看,18世紀以后,這種武器已經在藏區比較普遍流行了,而且得到了上層人士與一般民眾的大力歡迎。
不管怎樣,可以確信的一點是,正如從這套《格薩爾》故事畫所繪一部《征服西寧鳥銃宗》中獲取這種武器寶庫的說法來看,這的確在現實生活中曾成為了藏區部落頭人們所倚重或炫耀的重要武器。而且,自明朝以來西寧在藏文獻中被稱作“嘉西寧”(即漢西寧),由此可見,“鳥銃”傳入西藏文化中,似乎更多來源于漢文化這條通道。若從清朝1648年設立鳥槍兵情況來看,從這條通道傳入西藏的時間大約也不會早于17世紀。事實上,清軍重視裝備這種武器始于18世紀①毛憲民:《清代火槍述略》,《滿族研究》,2005年第4期,第48、49頁。。在西藏大量使用這種武器,也可能始于清軍平定郭爾喀之后,也即18世紀晚期。從以上內容可以推斷,這套“連環畫”最早也不會早于16世紀。
(二)證據之二:???????(布杜)名稱及其他
這套連環畫中占很大篇幅的是《格薩爾》史詩中的一部《霍嶺大戰》,也可以說這也是這套連環畫的“核心部分”。事實上,在整部《格薩爾》史詩中,《霍嶺大戰》可以稱得上是名副其實的“故事核心”。由此,《霍嶺大戰》對于《格薩爾》藝人、畫師和民眾來說,在其心中所占的分量可見一斑。
我們知道,1723年經????????????????????????????????(多卡瓦)②關于1722-1723年《霍嶺大戰》的整理者問題,可參見拙文《試論〈格薩爾〉史詩的幾種發展形態》,曼秀?仁青道吉、王艷主編:《〈格薩爾〉學刊(2012年卷)》,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3年,第287—298頁。組織眾多藝人整理完成《霍嶺大戰》之后,這個“整理本”(以下稱“多卡瓦整理本”)迅速成為此部史詩的范本,而且傳遍了整個藏區,甚至成為學者們的學習典范③17、18世紀以來,拉薩貴族中閱讀《格薩爾》史詩成了一種學習傳統“詩學”的方法。可參見 ??????????????????????????????????????????????????????????[M]???????????????????????????????????????????????????丹津班珠爾著、湯池安譯:《多仁班智達傳》,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5年。和藝人創作《格薩爾》史詩的“底本”④可以說很多《格薩爾》史詩分部本是基于它的風格、特色乃至故事結構上創作出來的。。將這套系列繪畫中的《霍嶺大戰》與多卡瓦整理本的故事情節進行比對,可以發現,整個故事結構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也出現了一些不同的情節結構和人物。其中最具典型的問題,就在于稱作???????(音為“布杜”)一個人物。“布杜”一詞含義有二,意之一為“愛子”(從親友方),意之二為“可憐兒”(從仇視方)。這個人物是格薩爾單槍匹馬來到霍爾國之后的關鍵變化身形之一,正是通過此化身,格薩爾成了霍爾鐵匠部落的養子,融入了霍爾國的內部社會。但在多卡瓦整理本中他的名字不叫???????“布杜”,而叫???????(音為“唐聶”,意為“在草灘上找到的”)。不論他處,就這一點可以斷定,此部繪畫依據的“底本”是多卡瓦整理本之前或者同時并行于世的一個手抄本。
而且從《格薩爾》史詩的抄本與藝人說唱傳統來看,布杜一詞盡管在文字上有多種寫法,但確切的拼寫法更可能是扎巴藝人說唱本中的“布杜噶布”(??????????????)⑤????????????????????????????????[M]??????????????????????????????????????????????????????。這是格薩爾在天界時或幼年時使用的名字之一。其含義可能是“白色肉髻或肉坨”。其中???????“噶布”意為白色,乃“善、美好”的修飾詞,??????“布杜”意為肉髻或肉坨(圓髻),這是其真正含義。事實上此詞真正的源頭應該是???????????????????的縮寫,譯為“天神之子白髻圣人”,此為釋迦牟尼佛在兜率天界的名字。由此可見,此部史詩發展到佛教文化階段,格薩爾被稱為千佛化現等等,也就比較合理自然了。
但從格薩爾的誕生故事來看,特別是較早期英雄的神奇誕生故事,比如白馬藏族中傳承的《格薩爾》中可以看到,英雄最初誕生為一個“肉坨或肉蛋”(俗稱肚子,藏語????????,音為“卓布”①有些地區藏語方言中,使用了????????(音為卓布)一詞來指“肉坨”含義。????????特指牛羊的胃臟或反芻器官,牧民用來裝酥油。民和本《格薩爾》中就是將此“肉坨”(卓布)用箭劃開后,從中蹦出了天神之子(Prof.Ts.Damdinsuren ed.,Tibetan version of Gesar Saga Chapter I-III, Ulan Bator: Th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sciences and education of Mongolia,1961.p.22.)。格薩爾幼年時的另一名字??????(音為覺如)一詞,或許也可能與????????有關,在安多口語中????????可讀作????????(音為覺吾)這與??????(音為覺如)音近。關于??????的含義,有多種說法。但它也可能具有“肉蛋”的含義。比如甘南本中說,格薩爾初生如一歲孩童模樣,母親將其用哈達與綢衣卷裹起來,在母親懷中就如抱著一個??????一樣,因此母親取名為??????。可見這里的??????指的應該是“肉蛋”一類的東西( ????????????????????????????????????????????????????????????????????????????????????????????????????????????????????????????????????????????????????????????????????????????????????[M]??????????????????????????????????????????????????????????????????????????????????????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與甘南藏族自治州文聯編印:《誕生史》,1983年?,第15頁)。當然??????也與被稱作佛或尊者的??????(音為覺吾)音近。從語言近似上解釋、衍生故事新義,達到地方、文化認同的目的,也是建構故事、傳說的特點之一。),被拋棄在野外受到野獸的“守護”②這也可從中國古代傳說周朝祖先“棄”誕生后被棄之于野的故事中見到相同母題。參見司馬遷《史記?周本紀》(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11頁。,劃開肉坨后誕生了英雄及其天神兄妹等③邱雷生、蒲向明主編:《隴南白馬人民俗文化研究?故事卷》,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4—26頁。。因此,“肉坨”或者“帶包衣的孩子”(或者稱作“蛋卵”④有些《格薩爾》藝人自稱自己誕生時被包裹在卵殼中,如果洛藝人昂仁的自述。)更可能是此詞最初的含義。或許這也是早期社會中對于初生兒的稱呼。這種將初生兒稱作“肉坨”(或者“圓蛋”)概念及所采取的誕生儀式,其歷史可能非常悠久,而且傳承比較廣泛。格薩爾也成了其中一個鮮明例子。此外,此詞的另一種文字書寫方式,即現在通行的???????一詞,具有了特殊的含義,轉變成了“愛子”或“可憐兒”。尤其是“可憐兒”一意,比較符合格薩爾幼年的低賤身份。因此,也得到了廣泛應用,甚至成了其真正名字。其詞的另一種寫法,就是貴德分章本和民和本中提到的 ?????????(音為“杜楚”,意為可憐兒)⑤Prof.Ts.Damdinsuren ed.,Tibetan version of Gesar Saga Chapter I-III, Ulan Bator: Th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sciences and education of Mongolia,1961.p.23.(此書正文為藏文)一詞。這之后,理所當然地???????與??????也可以連接起來了,即???????成了??????的修飾詞,譯為“可愛的覺如或愛子覺如”。
此外,在這套繪畫的《霍嶺大戰》中,還講到了一個重要情節,即嶺國英雄??????????????(音為“森達阿董”)之死及其死后化為了狼的身形⑥四川博物院、四川大學博物館科研規劃與研發創新中心:《格薩爾唐卡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117頁。。這是比較罕見的一個情節。不論是多卡瓦整理本,還是其他通行抄本中,在此處擔當這個角色的應該是嶺國英雄???????????????(音為“阿奴斯潘”)。因此,也可確定此《霍嶺大戰》并非為多卡瓦整理本。
(三)關于“賽馬稱王圖”
作為一種旁證資料,我們來看此套繪畫所提供的第6幅《世界雄獅大王》的主尊像。它幾乎與17世紀的一幅“格薩爾騎征像(即戰神形象)”一模一樣,這就是爐霍畫家 ????????????(朗卡杰,1610-1690)所繪《賽馬稱王》畫①甘孜州文化體育和廣播影視局、甘孜州文化館編:《康巴唐卡畫名人作品選》,成都:四川美術出版社,2012年,第126頁。此外,2012年筆者參加四川省文化廳等機構主辦的“格薩爾故里行”調研活動,得贈此幅唐卡的模本小型畫一幅,上面記有“四川甘孜爐霍縣唐卡藝術協會贈《賽馬稱王》”等字樣。。這兩幅畫像中的格薩爾王的形象、姿態、手持物、坐騎和13威爾瑪戰神等,基本上是一致的。唯一較大的差別在于:馬首的朝向和相應造成的手的位置出現了差異。至于馬首朝向問題,筆者也曾做過揣測②李連榮:《格薩爾學芻論》,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年,第53—56頁。,這可能與藏族的民間信仰和佛教思想有關,藏族民間認為向上(向西)③向上即是向西的概念在苯教中有鮮明的反應,顯然后來佛教也采用了這種觀念。為善好,圍繞圣物向右旋轉為佛教信仰。鑒于這樣的想法,后來典型的“騎征像”中馬首定型為向左(即向西)得到了普遍認可,比如德格印經院的大小雕版為代表的一大批收藏于各大寺院中的格薩爾戰神形象既是如此。本書中所附川大博物館所藏“騎征像”(即《格薩爾及三十大將》)顯然也是這種想法的反映。但在此套繪畫的第6幅中馬首朝右,我們只能理解為“天神下凡”的含義了(即天神從上方天界下凡。在藏族民間文化傳統中,有時將表示天界的“上方”概念與表示西方的“上方”概念混用,如上部印度與下部中原之說。因此在此表示了天神從西方來的概念,這也可從格薩爾大王馬前“侍從”面向西方敬獻禮物中來理解此種含義)④在后期的畫家中一般固定為馬首向左。不過20世紀80年代初,四川幾位畫家所繪“騎征像”中馬首不但朝右而且雙前蹄騰空;另之后色達畫家拉孟所繪“騎征像”中馬首也是朝右。這也可以理解為是一種“傳統的回歸”吧。。關于馬首向左的畫法得到后來畫家的認可,這也可從11幅格薩爾唐卡畫中所繪各故事內容的分解畫面,基本圍繞主尊畫像向右旋轉的布局中得到了印證——即這顯然受到了藏傳佛教“右旋”概念的影響。
此外,還有兩點相似處在于這兩幅繪畫中均沒有出現13威爾瑪戰神中的“雙魚”形象⑤關于格薩爾王的13威爾瑪(藏文為??????)戰神形象(關于威爾瑪與戰神的關系,也有不同說法。早期兩者各司其職,比如此套系列繪畫第8幅主尊畫為九大戰神或者一些抄本中提到的“戰神念達瑪布(???????????????)”,而威爾瑪指人形身材動物頭顱的一組保護神。但到后來一般將二者連用在一起了),有多種說法,而且隨著時代變化不斷發生著變化。筆者簡略地將其分為兩組,一類是“雙魚組”,有“雙魚”、風馬中的四神獸、四種鳥類等為主的一組,約有15種動物;一類是“魯組”,有“魯”(蛇或龍)、兩種鳥類以及普通動物為主的一組,約有13種動物。很顯然,前者是居?彌旁等學者認定后出現的形制,后者則可能來自史詩本身或更早時期。雙魚原本是八祥瑞之一,進入格薩爾之威爾瑪系列可能用來代指龍族。另外也可能顯示了用佛教文化中的“龍”來取代苯教文化中“魯”(蛇或龍)的含義。和格薩爾胸前所系為金鎖而非護心鏡,這兩點也是后期此類繪畫中的重要標志。當然兩幅畫畢竟可能并非出自同一人之手,細處不同之處還有不少,比如格薩爾的鎧甲、幡矛旗的形制、“侍從”英雄的形象以及格薩爾之臉色(白色即天神臉色,而非史詩中所述的董氏族紫色或赭色)、戰馬的野驢色(而非棗騮色或赤兔色)等。另外,關于格薩爾將手置于耳旁的含義,一般有兩種解釋,即傾聽天神預言或者對臣屬唱歌宣教。前者可從眾多分解圖畫中找到類似例證,后者則可從米拉日巴等瑜伽修行者的圖畫中找到相似示意。
由此,筆者認為,“格薩爾騎征像”最早應該是從“賽馬稱王圖”發展而來的。它最初的功能逐漸發生了變化,尤其從“侍從”人員和30員大將的保留與否可見一斑。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種“稱王圖”已經完全變成了“騎征像(即戰神形象)”了。由以上情況推知,這套系列畫有可能吸收了17世紀的這幅畫的某些特點,也就是說它的繪畫時間有可能晚于17世紀。
(四)關于繪畫“底本”
我們已經知道,《格薩爾》藝人或繪畫者在進行創作一個大家熟悉的故事之前,必須具備一個故事草本。但是二者之間也有所不同,藝人根據自己掌握的眾多故事情節作為“草本”搭建完整的故事;而繪畫者的草本則需要更加周密詳細,這可稱之為“底本”。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我們可以從畫師創作的過程中必需要根據一個抄本或刻印本作為“底本”進行創作,可以斷定這一點。作為一個旁證,我們來看2007年完成的“《格薩爾》千幅唐卡畫”以及2013年完成的“《格薩爾》精選本”插畫的繪制過程,可窺見繪制《格薩爾》史詩故事的一斑。從畫師選定《格薩爾》底本,然后再選擇“經典的故事情節”進行構圖,到最后落筆成畫①甘孜州嶺?格薩爾王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格薩爾王傳?千幅唐卡》,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8年,第128頁。?????????????????????????????????????????????????????????????????????????????????????????????????????????《格薩爾研究集刊(6)》,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561—583頁。。這一系列過程,對畫師來說,盡管人物形象上有選擇的自由,但絕對不會憑空構想和創作“故事”。比如從此套故事畫中的《嶺國形成篇》至《賽馬篇》可見,更多采用了甘南地區發現的手抄本《誕生史》的內容②????????????????????????????????????????????????????????????????????????????????????????????????????????????????????????????????????????????????????????????????????????????????????[M]?????????????????????????????????????????????????????????????????????????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與甘南藏族自治州文聯編印:《誕生史》,1983年?。。《漢嶺傳奇》可能采用了昌都地區發現的抄本③??????????[M]?????????????????????????????????????????????????????,《地獄救母》則與江達縣瓦拉寺木刻本非常近似④?????????????????????????[M]??????????????????????????????????????????????????????????。
因此,通過這種觀點,我們來看這套系列故事畫時,除了能夠證明其畫師是根據某一個特定的“底本”進行創作的這件事之外,它還證明了這套系列繪畫依據的抄本肯定早于1723年的整理本或者或和它接近的一個時期。因為要繪制一套系列繪畫,必定要搜羅大量的、“信得過”的“抄本”作為“底本”。如果1723年本已經出現,畫師不會不采用這位經著名作家整理的權威本子。基于以上原因,筆者認為這套繪畫最晚也可能創作于1723年前后。當然,從這套繪畫保存得如此完好和色彩如此鮮亮方面來看,除了唐卡本身具有能夠長久保存的特色以外,單就從臨摹角度來說,如果這套繪畫是臨摹本的話,那么我們也可以確信這套臨摹畫的“唐卡畫底本”最早也肯定創作于18世紀左右。
(五)關于故事系統
從整套繪畫所描述的故事類型來看,無疑它屬于18大宗中的康區型。但從其所屬“故事系統”也即從整理者與藝人的“偏好”、《格薩爾》“知識”及整理、編校“完整故事”的觀念來看,這套繪畫所描繪的《格薩爾》故事系統更接近于居?米龐等整理的德格林蔥本(19-20世紀)與蒙文北京木刻本(1716年木刻⑤Prof.Ts.Damdinsuren ed.,Tibetan version of Gesar Saga Chapter I-III, Ulan Bator: Th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sciences and education of Mongolia, 1961.p.12.)。也就是說,這套繪畫也有可能依據這個時期的《格薩爾》手抄本繪制的,即繪制于18-20世紀之間。關于這套繪畫的故事系統方面的內容,我們將另著文作更進一步的闡述。
(六)關于繪制地點
關于此套繪畫繪制的地點,許多學者指出可能繪于康定(因為此套繪畫的擁有者明正土司就居于此處⑥參看本書中所附石泰安的論文,他指出本套繪畫的擁有者為明正土司甲聯升。石泰安:《格薩爾畫傳》,劉瑞云譯,Rolf A.Stein, Tibetan Paintings of the life of Gesar, Arthur Makeon Trans., 《格薩爾唐卡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199頁。)。但是筆者依據《格薩爾》史詩的傳承特點及噶瑪噶智畫派形成、發展的特點判斷,這套繪畫可能的繪畫地點或許是比康定更靠西部的地區①依據任新建考證,被稱為嘉拉甲波的明正土司管轄的范圍包括了康定以西的“魚通河、大渡河西部、瀘定縣”等處的廣闊木雅地區。由于與木坪土司的親屬關系,也曾管理過康定以東的寶興縣等地。由此可見,其管轄范圍位于康區的漢藏文化的連接地帶。參見任新建:《康巴歷史與文化》,成都:巴蜀書社,2014年,第119—133頁。,爐霍、德格甚至更靠西的昌都也許是這套繪畫創作的地點。從噶瑪噶智畫派興起的特點來看,昌都更可能是它的創作地點,因為它更靠近噶瑪噶智派興起的地區。
從《格薩爾》史詩的故事系統的發展來看,昌都地區(包括玉樹在內)在18世紀以前已經成了康區《格薩爾》史詩的傳承中心。但是18世紀以后,隨著德格土司的興起以及德格印經院的建成,康區文化中心開始轉移到了德格。受到當地文化人士與上層人士的關心,康區格薩爾的傳承中心也轉移到了德格甚至更遠的東部與北部地區。因此,在這一地區內產生這套繪畫可能比較合理。也即,此套繪畫創作的地點有可能在于昌都至康定的某個地區,比如爐霍也符合這些條件。
四、小結
從以上幾個方面的證據,筆者認為這套故事畫繪制的時間,應該不會超過16世紀,也即它是繪于清代的一套故事畫。如果我們確信此套繪畫并未選取多卡瓦整理本《霍嶺大戰》作為“底本”,而且也未囿于居?米龐等整理《天界》《誕生》與《賽馬》,那么可以更確切一點說,它最早繪制的時間應該是18世紀左右,最晚也不會晚于19世紀晚期。或者我們可以說,此套《格薩爾》史詩的故事畫,最早于18世紀左右在昌都至康定的某個地區,在一位有一定經濟實力和權力且愛好《格薩爾》史詩的土司或者活佛的主持、資助下完成的,明正土司也符合以上這些條件。因此,我們暫且將其確定為18世紀的《格薩爾》唐卡畫,也是可以說得通的。
[責任編輯:丁紅美]
J2“214”
A
1008-7214(2016)04-0081-08
李連榮,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