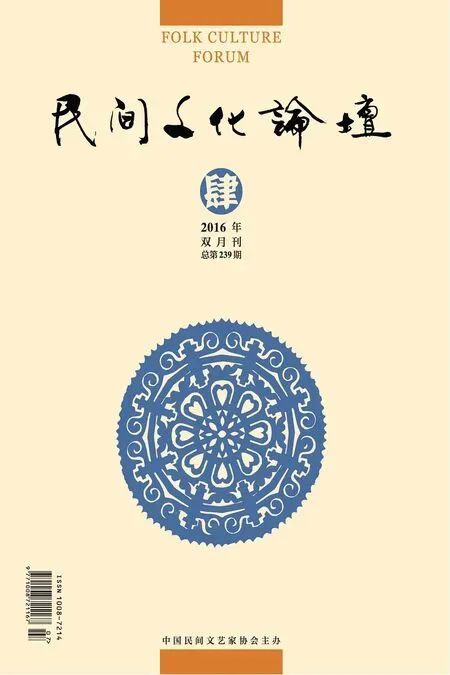臺灣賽夏族矮人傳說與祭儀流變
王人弘
臺灣賽夏族矮人傳說與祭儀流變
王人弘
賽夏族至今仍廣泛流傳祖先是如何與矮人相處的傳說,也有以祭祀矮人靈魂的祭典儀式“矮靈祭”。在賽夏族中傳說與祭儀有著相當緊密聯(lián)系,許多的儀式行為與過程能夠呼應(yīng)到傳說的內(nèi)容,當族人要解釋祭儀舉行原因時也會以傳說來進行說明。在時空的轉(zhuǎn)變中,傳說仍穩(wěn)定流傳于賽夏族的社會之中,而祭儀本身雖保持許多傳統(tǒng)精神與行為,但面臨現(xiàn)代化以及外族進入的影響,仍產(chǎn)生了部分的改變。對于賽夏族人來說,矮人傳說以及矮靈祭是族群重要的文化表現(xiàn),即便現(xiàn)代生活中族人大多離鄉(xiāng)背井,只要接近祭儀期間,族人大多會主動回鄉(xiāng)幫忙以及參與為期將近一個禮拜的矮靈祭。正因為賽夏族人面對自身文化的態(tài)度,也讓矮人傳說與矮靈祭能夠生生不息。
賽夏族;矮靈祭;芒草;矮人傳說
前 言
臺灣原住民賽夏族傳統(tǒng)儀式“矮靈祭”(paSta’ay),為兩年一度全族參與的盛大祭儀。2013年其被列入臺灣無形文化資產(chǎn)潛力點①臺灣稱“無形文化資產(chǎn)”即為聯(lián)合國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為與國際接軌,“文建會文化資產(chǎn)總管理處籌備處”仍然關(guān)注“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申請。目前“文化部文化資產(chǎn)局”共推出十二個無形文化資產(chǎn)潛力點:1.泰雅口述傳統(tǒng)與口唱史詩,2.布農(nóng)族歌謠,3.北管音樂戲曲,4.布袋戲,5.歌仔戲,6.糊紙(紙扎),7.阿美族豐年祭,8.賽夏族矮靈祭,9.王爺信仰,10.媽祖信仰,11.上元節(jié),12.中元普渡。見《臺灣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潛力點簡介》,臺中:“文化部文化資產(chǎn)局”。十二個潛力點中第八項為賽夏族矮靈祭,可知其重要性。。此祭儀從1915年左右就被日本學者認為是相當特殊的族群祭儀并觀察記錄,至今祭儀仍定期舉行,矮靈祭已成為賽夏族代表性的祭典儀式。族內(nèi)也流傳著矮人與矮靈祭關(guān)系的傳說,傳說不僅涉及賽夏人與矮人之間的糾葛,也解釋矮靈祭中許多祭儀行為及權(quán)力關(guān)系,諸如:將芒草作為避免矮靈作祟之物、族內(nèi)朱姓掌握主祭權(quán)之緣由或是面向東方請神靈等。矮人傳說與矮靈祭在不斷重述與舉行的祭儀兩者相互影響下,對于賽夏族穩(wěn)定傳統(tǒng)與社會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有著相當大的作用。但賽夏族群面對臺灣社會、物質(zhì)以及價值觀的轉(zhuǎn)變,矮人傳說及矮靈祭皆產(chǎn)生些許變化。賽夏族在傳說與祭儀的傳承上,選擇保留什么,又改變了什么?其原因為何?這些是本論文試圖探討的問題。
矮人傳說與祭儀流變
臺灣原住民文化的科學性記錄大約是在1909年之后才陸續(xù)展開,日本學者基于各種目的進行調(diào)查,此時期多以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甚至是語言學的角度進行研究,因此故事僅被視為輔助材料,并未以民間文學為主體進行調(diào)查研究。目前文獻所見較早載錄賽夏族矮靈傳說資料的為1915年“臨時臺灣舊慣調(diào)查會”出版的《番族慣習調(diào)查報告書〈第三卷〉》,書中記錄兩則矮人傳說①“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diào)查會”原著,中研院民族所編譯:《番族慣習調(diào)查報告書(第三卷)賽夏族》,臺北:中研院民族所,1998年6月初版,第11—12、12—13頁。,其中一則內(nèi)容相當完整,傳說梗概如下:
矮人居住于賽夏族部落附近,擁有特殊能力同時能歌善舞,賽夏族雖畏懼但仍定期邀請參加收獲祭祀。每每前往邀請矮人參加祭祀,通知者會被捉弄致昏死,需依靠老矮人以芒草施法才能蘇醒。矮人也性好女色,時常于祭祀中騷擾賽夏族婦女。某次祭祀中一賽夏族男子見妻子受辱,伙同部分族人對矮人回程河邊休憩的樹木動手腳,矮人們不察幾乎連同樹木摔入河中淹死,僅存兩名矮人回賽夏族問罪,知曉因緣后兩名矮人決意離開不再回來,并教導賽夏族人祭祀的歌謠,但歌謠太難僅朱姓族人學會,之后矮人便向東方離去。②“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diào)查會”原著,中研院民族所編譯:《番族慣習調(diào)查報告書(第三卷)賽夏族》,臺北:中研院民族所,1998年6月初版,第11—12頁。
此則記錄是1945年之前日本文獻中情節(jié)較豐富的記錄,同書中亦記錄另一則矮人傳說,并特別說明為大隘社朱姓族長所述,內(nèi)容差異主要有二:首先,傳說開頭講述是朱姓祖先與矮人接觸互動,開啟兩族交流;次者,矮人在被害后,殘存矮人對賽夏族下咒,詛咒內(nèi)容為農(nóng)害與被平地人欺壓。③“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diào)查會”原著,中研院民族所編譯:《番族慣習調(diào)查報告書(第三卷)賽夏族》,臺北:中研院民族所,1998年6月初版,第12—13頁。同書中存有兩則內(nèi)容些許差異的矮人傳說,顯示當時傳說內(nèi)容已存在異文,類似的矮人傳說也見于1919至1945年期間《臺灣原住民族系統(tǒng)所屬之研究》④“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調(diào)查,楊南郡譯注:《臺灣原住民族系統(tǒng)所屬之研究》,臺北:原住民族委員會、南天書局,2011年,第120頁。《原語臺灣高砂族傳說集(一)》⑤“臺北帝國大學言語學研究室”:《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臺北:南天書局,1996年,第125—128頁。《高砂族調(diào)查書?第五編,賽夏族》⑥“臺灣總督府警務(wù)局理蕃課”編,余萬居譯:《高砂族調(diào)查書?第五編,賽夏族》,臺北:中研院民族所館藏,未發(fā)行,第27—28頁。《賽夏族之音樂》⑦黑澤隆朝著,余萬居譯:《賽夏族之音樂》,臺北:中研院民族所館藏,未發(fā)行,第27—28頁。《高山族的祭典生活》⑧古野清人著,黃耀榮譯:《高山族的祭典生活》,臺北:中研院民族所館藏,未發(fā)行,第399—401頁。《賽夏(特)族的矮人祭》⑨山路勝彥、松澤員子著,黃政雄譯:《賽夏(特)族的矮人祭》,臺北:中研院民族所館藏,未發(fā)行,第1—3頁。等書,共通的主要情節(jié)有“矮人擁有特殊能力”“矮人戲弄族人、玷污賽夏族婦女”“賽夏族人不堪受辱計殺矮人”“矮人教導祭儀過程或祭歌由朱姓傳承”,這些情節(jié)也常見于目前賽夏族流傳的矮人傳說。于各異文中較多的差異在解釋朱姓擔任矮靈祭主祭之緣由,有說是朱姓為設(shè)計誅殺矮人之主謀,才成為司祭者:
往昔這個祭司是由豆姓(tautausai)主持,為小人而受虐待,其職同移到朱姓之手。矮人之誅殺,多出于朱姓之謀,祭祀職司遂移朱姓。⑩“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調(diào)查,楊南郡譯:《臺灣原住民族系統(tǒng)所屬之研究》,臺北:南天書局,2011年,第120頁。
或稱僅朱姓能將矮人傳授的祭祀之法全部學會:
豆姓和朱姓承taai教授有關(guān)祭典的事,但豆姓無法學會,朱姓學會了,因此pastaai祭典由朱姓執(zhí)行。?小川尚義、淺井惠倫著,余萬居譯:《原語臺灣高砂族傳說集(一)》,臺北:中研院民族所館藏,未發(fā)行,第234頁。
雖然朱姓成為賽夏族矮靈祭司祭者的原因各異,但傳說中凡提及矮靈祭主祭擔任之姓氏,皆無一例外稱朱姓為主祭。現(xiàn)實中矮靈祭之主祭者確實與傳說所述相契合①賽夏族的許多儀式由各姓氏分別擔任主祭的職務(wù),現(xiàn)實中從有記載賽夏族矮靈祭以來擔任賽夏族主祭角色一直都是由朱姓家族的代表擔任,1945年之前也皆是由朱姓族人于祭儀期間擔任領(lǐng)唱。,傳說解釋了矮靈祭朱姓擔任主祭之緣由。
1945年后,矮人傳說仍流傳于賽夏族部落中。1968年,陳春欽《賽夏族的宗教及其社會功能》②陳春欽:《賽夏族的宗教及其社會功能》,《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26期,臺北:中研院民族所,1968年,第83—119頁。以及1986至1989年間臺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撰的《臺灣土著祭儀及歌舞民俗活動之研究》③《賽夏族矮靈祭與歌舞》為此計劃的其中一本文獻匯編《賽夏族矮靈祭與歌舞》,臺北:中研院民族所館藏,未發(fā)行。,皆為實地調(diào)查記錄。矮人傳說也散見于部分著述如《臺灣風物》④陳正希:《臺灣矮人的故事》,《臺灣風物》第2期第1期,臺北:臺灣風物雜志社,1952年,第29-30頁。陳正希:《臺灣矮人的故事(完)》,《臺灣風物》第2期第2期,臺北:臺灣風物雜志社,1952年,第25—28頁。《中國民間故事全集》⑤陳慶浩、王秋桂主編:《中國民間故事全集?臺灣民間故事集》,臺北:遠流出版事業(yè)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第513—516頁。,但兩書內(nèi)容已重新編撰改寫。較符合科學性調(diào)查的采錄則為2001年吳姝嬙碩士學位論文《賽夏族民間故事研究》⑥吳姝嬙:《賽夏族民間故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7月。,及2004年金榮華《臺灣賽夏族民間故事》⑦金榮華:《臺灣賽夏族民間故事》,臺北:口傳文學會,2004年3月。二書。1945年后采錄的矮人傳說,主要情節(jié)并無太大變化,仍以“矮人擁有特殊能力”“矮人戲弄族人、玷污賽夏族婦女”“賽夏族人計殺矮人”以及“矮人教導祭儀過程或祭歌朱姓由傳承”為傳說內(nèi)容。于賽夏族大隘部落所流傳的內(nèi)容,多會敘述兩族接觸始末⑧(1)傳說在四百年前,矮人就住在現(xiàn)在大隘村的對面山上,矮人很喜歡唱歌,而且唱得很好聽,有一次賽夏族趙家的人發(fā)現(xiàn)矮人在唱歌,于是就回來通報族人,后來朱家的人就跑去聽,果真有矮人在唱歌而且真的很好聽,于是朱家的人就想學矮人所唱的歌,去學幾次之后,終于把矮人的歌學會了。講述者:朱逢祿,采錄者:王俊勝,時間:2000年8月26日,地點:新竹縣五峰鄉(xiāng)大隘村。(2)發(fā)現(xiàn)矮人是在有一次賽夏族除了朱姓以外的各姓氏長老到山上找蓋房子用的藤樹時,聽到有人在唱歌,于是就發(fā)現(xiàn)是個子小小的矮人在山枇杷樹上唱歌,而且它們的語言跟賽夏族一樣,在場賽夏族人覺得矮人唱的歌很好聽,所以就想學它們唱的歌,可是怎么學都學不會。講述者:朱秀春,采錄者:王俊勝、郭爵源,時間:2000年10月30日,地點:新竹縣五峰鄉(xiāng)大隘村。,很可能承襲自《番族慣習調(diào)查報告書(第三卷)》中所載大隘社朱姓族長的說法,未交代與矮人相遇的傳說,情節(jié)多著重于矮人與賽夏族人相處、欺辱、計殺、最后祭祀矮人之靈的說法,講述傳說者也不局限于朱姓族人⑨1945年之后采錄集中講述過矮人傳說的賽夏族人有風家、朱家、豆家、日家、高家以及絲家等氏族族人。金榮華:《臺灣賽夏族民間故事》,臺北:口傳文學會,2004年3月,第71—81頁、第155—159頁。。
比較各時期矮人傳說,主要情節(jié)并未有明顯改變,但1945年之后的傳說增添些許敘述的枝節(jié)。部分文本對矮人的外表或能力描述的更為詳細,不再只用外表矮黑或是具有法力帶過。“達愛”(矮人)身高不會超過70公分,男女都穿白衣服,還會在腰間綁上一條帶子。⑩金榮華:《臺灣賽夏族民間故事》,臺北:口傳文學會,2004年3月,第75頁。矮人有棕黑色的膚色,不到三尺高。
他們有一些特殊的能力,例如:可以如蜻蜓點水般過河、具有隱身術(shù)等。?金榮華:《臺灣賽夏族民間故事》,臺北:口傳文學會,2004年3月,第79頁。這些敘述并沒有一致性,大約依據(jù)講述者的不同有所變化。
矮靈祭起源時間難以從現(xiàn)階段資料考證確切時間帶,從文獻或耆老口述可知矮靈祭在賽夏族社會中存在已久,1945年之前有關(guān)矮靈祭的起源敘述皆以古代、古時候、很久以前來概論之。近代的采錄則是講述賽夏族還居住于大霸尖山時就已與矮人來往①在大霸尖山上生命初長的時候,矮人來照顧我們,我們問他們從哪里來?他們說:“我們是從太陽升起的那個方向來的。”金榮華:《臺灣賽夏族民間故事》,臺北:口傳文學會,2004年3月,第77頁。,或是與耆老問答中推估時間②按:據(jù)講述者說,傳說在荷蘭人統(tǒng)治臺灣的那一年,當時賽夏族有舉辦矮靈祭,聽老人說,那時在舉行矮靈祭時,有長得像美國人的外國人曾統(tǒng)治臺灣,那應(yīng)該就是荷蘭人,表示在荷蘭統(tǒng)治臺灣時,賽夏族就已有矮靈祭,距今大概至少有四百年了。朱逢祿講述,王俊勝采錄(2000年8月26日,于新竹縣五峰鄉(xiāng)大隘村)。。《番族慣習調(diào)查報告書(第三卷)》較早以文字記錄矮靈祭過程,詳細記錄長達五天的祭儀過程。祭祀每兩年舉行一次,并分成南、北兩團,南部是大東河、紅毛館以及紙湖地方各社;北部由大隘、pi:lay(比來)、Sipazi:(十八兒)等三社共同舉行,南北皆由朱姓家擔任主祭,各姓氏共同參與協(xié)助,于稻子快成熟時舉行。南北主祭相約協(xié)定祭儀之日,祭儀約五天,主要分為迎靈、娛靈以及送靈三階段,各階段進行吟唱的祭歌內(nèi)容多有差異且不能混淆③“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diào)查會”原著;中研院民族所編譯:《番族慣習調(diào)查報告書(第三卷)賽夏族》,臺北:中研院民族所,1998年,第30—34頁。。1945年后記錄矮靈祭過程的文獻主要有鄭金德《賽夏族的矮靈祭》(1967)④鄭金德:《賽夏族的矮靈祭》,《邊政學報》第6期,臺北:中研院民族所,1967年,第41—45頁。、趙福民《賽夏族矮靈祭之研究》(1987)⑤趙福民:《賽夏族矮靈祭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民族與華僑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年。、趙福民《賽夏族十年大祭 : 民國七十五年矮靈祭南北兩祭團采訪錄》(1987)⑥趙福民《賽夏族十年大祭 : 民國七十五年矮靈祭南北兩祭團采訪錄》,南莊:中國民俗學會:復(fù)印本,1987年。、陳運棟、張瑞恭著《賽夏史話 : 矮靈祭》(1994)⑦陳運棟、張瑞恭著:《賽夏史話 : 矮靈祭》,桃園:華夏書坊,1994年。、《賽夏族文化特展 : 以“巴斯達隘(矮靈祭)”祭典活動探索賽夏族文化精髓》(2001)⑧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賽夏族文化特展 : 以“巴斯達隘(矮靈祭)”祭典活動探索賽夏族文化精髓》,臺北: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2001年。、簡鴻模《矮靈?龍神與基督》(2007)⑨簡鴻模著:《矮靈?龍神與基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北:“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2007年。等書。隨著時代與科技的進步,矮靈祭除了以文字敘述之外也以影音進行記錄,更能夠了解祭儀現(xiàn)場狀況。
將各時期記錄與2010年及2012年現(xiàn)場實際觀察記錄進行比對,矮靈祭絕大部分過程、行為與禁忌仍與文獻記錄相同,諸如:矮靈祭過程中各項人事物皆須綁芒草預(yù)防矮靈作祟、祭拜矮靈以及祖靈時的祭品與行為、歌舞漩渦陣型以及氏族舞帽等,這些皆與文獻敘述接近,但仍有差異存在。首先是領(lǐng)唱者不再局限于朱姓族人,1945年前的文獻敘述三晚娛靈過程的歌舞皆由朱姓族人負責領(lǐng)唱,但從朱鳳生記錄2000年度新竹五峰鄉(xiāng)的矮靈祭活動期間祭歌輪唱表⑩朱鳳生著:《導論賽夏族》,新竹:新竹縣文化局,2011年,第121頁。,以及2012年于南莊向天湖祭場現(xiàn)場實際訪談其中幾位擔任領(lǐng)唱的年輕族人,卻發(fā)現(xiàn)亦有其他姓氏青年領(lǐng)唱,且青年表示祭歌的教導與學習屬于自發(fā)性并未特別挑選傳承。第二項差異為儀式舉行過程因大量游客參與而對共舞者有所規(guī)范。依現(xiàn)場耆老敘述,過往矮靈祭進行娛靈歌舞時,非賽夏族人必須經(jīng)過午夜十二點且身穿賽夏族傳統(tǒng)服飾才可入內(nèi)共舞,但2010年與2012年兩屆矮靈祭未到午夜十二點即開放外來客參與歌舞。第三項差異為向天湖旁的祭儀會場與祭屋并非該年度矮靈祭時才整理搭建,而是以現(xiàn)代建筑材料建成并定期維護保養(yǎng)。文獻記載過往舉行矮靈祭之空間,是該年度于朱姓主祭家前整理出一塊空地,并搭建祭儀用小屋。但現(xiàn)今向天湖祭場舉行矮靈祭已經(jīng)使用現(xiàn)代建材的祭屋,空間與交通皆有設(shè)計規(guī)劃。還有部分差異在于周邊環(huán)境氛圍改變,隨著信息傳播發(fā)達,參與祭儀游客涌入,吸引流動攤販設(shè)攤,因此每當矮靈祭舉行時,祭場周邊聚集許多攤販,雖然攤販未以擴音喊叫,也提供族人和游客休憩之處,但夜晚從攤販聚集處投射出來的強光確實影響到祭場上肅穆的氛圍。
矮靈祭與矮人傳說歷經(jīng)時空,存在部分不變內(nèi)容、行為以及象征,傳說中朱姓學會所有祭歌以及祭祀方法、賽夏族人于樹木上動手腳使矮人中計落入水中,以及最后殘存老矮人向東方離去這些情節(jié)內(nèi)容皆在不同時空講述過程中出現(xiàn);儀式中芒草作為預(yù)防作祟的重要物品、漩渦圓陣舞蹈方式、送靈儀式的毀壞榛木架以及諸多儀式行為必須面向東方等,這些行為自日本學者記錄以來幾乎沒有改變過。對賽夏族群來說或許這些存在是理所當然,不過正是這些不變的存在,使得賽夏族的矮人傳說與矮靈祭具有獨特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傳說與祭儀中存在哪些象征及隱喻不僅互相交融影響,也形塑出賽夏族群的民族性。
祭儀與傳說互涉
矮靈祭儀式作為傳說與現(xiàn)實的聯(lián)結(jié),經(jīng)由舉行過程將矮人傳說具體化,儀式本身也從傳說獲得實踐的解釋性。兩者互相交融過程有許多不斷重復(fù)強調(diào)的事物,祭儀行為、物品的解釋及象征往往與傳說相涉。首先,賽夏族矮靈祭自結(jié)芒草約期后①結(jié)芒草約期是矮靈祭中傳統(tǒng)的儀式過程,古早矮靈祭會考量稻子成熟時間,南北兩祭團代表集合討論并確定該年度矮靈祭的日期,由雙方主祭用芒草打結(jié)做計算日期之用,每過一天解開一個結(jié)。即正式進入矮靈祭準備期,此刻開始賽夏族人會在各項用具綁上芒草,并且開始嚴格遵守各項禁忌。芒草為矮靈祭期間的重要存在,祭儀過程中無論族人或外來者,所有的物品都必須系上芒草,直到祭儀結(jié)束。芒草是為避免矮靈作祟,日本學者調(diào)查資料即已留下記錄:
我們也為了能逃避矮靈的咒術(shù)而讓村人為我們在手腕上扎上葉子。還說照相機和錄音機不綁上草的話,神一發(fā)怒就不能使用云云。并且舉了幾個曾經(jīng)有過的實例給我們聽。②山路勝彥、松澤員子著,黃政雄譯:《賽夏(特)族的矮人祭》,臺北:中研院民族所館藏,未發(fā)行,第5—6頁。
此段敘述可知,日據(jù)時期賽夏族人已有系芒草避免矮靈作祟的習俗。祭儀現(xiàn)場若有人觸犯禁忌,必須由朱姓耆老向矮靈道歉并祈求解除捉弄或懲罰,過程中也必手持芒草。矮靈祭中祈求天氣晴朗的祭儀中的蛇鞭③蛇鞭(賽夏族語為babte)也有人稱之法鞭,它不但具有驅(qū)雨以及除病的法力,也象征著主祭權(quán)力所在。蛇鞭儀式只由南群主祭家族的男性負責。北群祭團所沒有的。外族、他姓、女孩及孕婦均不許觸摸,以免造成意外及不利。朱鳳生:《導論賽夏族》,新竹:“新竹縣文化局”,2011年,第105頁。也是由芒草編制而成的。矮靈祭尾聲伐榛木的儀式中也有芒草,族內(nèi)青年輪流跳抓榛木架上的芒草結(jié),若能將芒草結(jié)扯下則會帶來好運。朱姓族人解釋習俗源自過往賽夏族人欲邀請矮人參加祭儀,前往的通知者卻因矮人捉弄而昏死,后由老矮人以芒草念咒祈禱才甦醒。此說法與文獻中矮人傳說內(nèi)容雷同:
本族人邀請他們時,照例射箭做信號,但是ta’ay的壯丁涉溪而來,立刻逮住本族的使者,緊勒他的睪丸使其氣絕,幸而其后ta’ay的老人趕來,憐憫他而用芒草綁住他的全身,一面誦咒,一面祈禱,該族人才因而獲得蘇生。④“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diào)查會”原著,中研院民族所編譯:《番族慣習調(diào)查報告書(第三卷)賽夏族》,臺北:中研院民族所,1998年,第11頁。
從族人的解釋以及文獻內(nèi)容可以清楚呈現(xiàn),對賽夏族群來說,芒草在矮靈祭期間作為重要物件,源于相信芒草與矮人之間有著強力的連結(jié)性(作為矮人施法蘇生之用)。傳說中矮人形象為正邪參半,但以矮人之靈為祭祀主體的矮靈祭勢必得引導矮靈進入會場以及部落,為了避免災(zāi)禍,賽夏族人必須轉(zhuǎn)化或抑制矮靈負面的形象,使用芒草作為保護、避邪、祈福,芒草之所以能起作用,關(guān)鍵原因就是傳說中老矮人用此來甦生被捉弄的族人,以此詮釋、建構(gòu)出矮靈與芒草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性。芒草不僅淡化矮靈祭期間矮靈負面的性質(zhì),同時也對族人達到警醒的作用,當部落空間處處皆可見到芒草結(jié)時,就是宣告部落空間已從日常生活進入到祭儀的特殊空間中,期間族人須遵守各項禁忌。
矮靈祭最吸引外來參與者的就是娛靈歌舞,連續(xù)三晚隨進行儀式進入不同階段,此歌舞只能于矮靈祭期間進行,歌舞行為與規(guī)范從日本學者記錄以來至今無太大改變。賽夏族歌舞娛樂神靈的特殊旋渦圓陣韻律的方式,從未因時空而改變。旋渦圓陣則起因于矮人們落水淹死的傳說①賽夏族矮人傳說從被記錄至今依賽夏族人所述,關(guān)于矮人被賽夏族人害死的過程無一例外全是對樹木設(shè)下陷阱讓矮人們最后跌入水中淹死。,舞蹈方式模擬矮人落水后的模樣,以此慰藉矮人之靈。漩渦圓陣的舞蹈方式不僅是“娛樂神靈”,更是賽夏族人藉重現(xiàn)矮人落水之痛苦,反省自身過往所犯的過錯。金榮華在《臺灣賽夏族三大傳說試探》一文中提出,矮人傳說對賽夏族具有族群自省的作用②金榮華:《臺灣賽夏族三大傳說試探》,《2006年民俗暨民間文學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津出版社,2006年7月,第25—47頁。,此種自省的態(tài)度不僅反映在傳說中,更體現(xiàn)于矮靈祭儀式與歌舞之中,透過傳說與儀式在族內(nèi)傳承。
矮靈祭過程中東方是特殊的方位,從祭儀初期邀請矮靈與祖靈或是進行祭拜時皆朝向東方,至祭儀尾聲送靈儀式過程所有廢棄的祭儀用具皆向東方丟棄,顯示東方在矮靈祭期間具有特殊意義。部分矮人傳說于結(jié)尾處提及沒有被害死的矮人最后朝東方離去:
那時只有二個人幸免于難,他們離去時對我們說,以后你們的耕地將會永遠有麻雀和老鼠來為害谷類,并且又說,你們到平地人莊落出草時,一定會被平地人殺死等等。他們說完就朝東方離去。③“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diào)查會”原著;中研院民族所編譯,《番族慣習調(diào)查報告書(第三卷)賽夏族》,臺北:中研院民族所,1998年6月初版,第13頁。
你們學會以后,我們便要走去太陽出來的地方,再也不回來了。④金榮華:《臺灣賽夏族民間故事》,臺北:口傳文學會,2004年,第74頁。
那兩個矮人說完話就往東方走了。……又因為最后那兩位矮人是走往太陽出來的東方,所以我們朝東方祭拜。⑤同上注,第159頁。
矮人離去之前大多要求賽夏族人祭拜死去的矮人或是說出詛咒,之后向太陽出來的方向或東方離開。矮靈祭中的東方體現(xiàn)了傳說中東方的位置意義。另外,送靈過程中的伐榛木儀式也體現(xiàn)了傳說中的隱喻性。男性族人上山砍伐榛木返回祭場,于祭屋前搭起榛木架并系數(shù)十個芒草⑥前面曾提及這芒草對于祭祀對象矮靈以及賽夏族人之意義,此處也有可能以芒草來作為矮人的想象。,由在場青年輪流跳起扯下芒草,榛木架高度遂逐漸降低,待有青年可以握到榛木架時用力扯下,周圍的青年也一擁而上,將榛木毀損折斷并將之向東方丟棄。這一連串的儀式,如同漩渦圓陣舞一般,再現(xiàn)矮人被害的過程,也提醒儀式結(jié)束,矮靈終將離開,人鬼殊途,回歸各自所處的境界。傳說內(nèi)容不斷地以隱喻或轉(zhuǎn)化的方式出現(xiàn)于祭儀過程中,使得賽夏族人即便歷經(jīng)時空轉(zhuǎn)變?nèi)阅芰私獍`祭所應(yīng)具有的核心與內(nèi)涵。
矮靈祭過程中許多祭儀行為與矮人傳說有著隱喻和詮釋關(guān)系,族內(nèi)解釋這些祭儀過程或是傳說內(nèi)容的權(quán)力,往往導向擔任主祭的朱姓氏族或族內(nèi)具有一定社經(jīng)地位的耆老,這些在祭儀與傳說方面具有發(fā)言權(quán)的族人,對于兩者的互涉及發(fā)展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
朱姓長期作為矮靈祭與傳說之主祭及詮釋者,在兩者發(fā)展過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從文獻記錄直到現(xiàn)在,可以發(fā)現(xiàn)矮靈祭的過程,朱姓族人負擔重要責任與權(quán)利,各氏族雖然也參與協(xié)助矮靈祭的準備①矮靈祭其間各姓氏家族也會有一名姓氏代表的主祭,矮靈祭期間各姓氏祭請矮人吃飯也多聚集于姓氏代表的主祭家中。除此之外每一次矮靈祭各姓氏族也要準備肩旗(亦稱舞帽)、臀鈴等重要物品。,但整個祭儀過程中重要的關(guān)鍵還是由朱姓族人所傳承與執(zhí)行②祭儀過程中許多物品與工作是除了朱姓相關(guān)族人之外其他姓氏族人不能碰觸或擔任的,諸如:為參加者綁芒草結(jié)、祭儀過程中站在臼上訓誡族人、當有人被矮靈捉弄也只能請求朱姓耆老為其解除等。,朱姓族人的地位在每一次矮靈祭及傳說的講述過程中不斷被突顯與強調(diào)。矮人傳說今日仍然為絕大多數(shù)賽夏族人所知,但年輕一輩或是非朱姓的族人經(jīng)常拒絕擔任講述者,指出耆老或朱姓族人才是適合的講述者,此種將族群文化的解釋權(quán)力集中于較核心成員的現(xiàn)象并不罕見。矮靈祭中朱姓一直以來擔任主祭的角色,領(lǐng)導其他姓氏家族進行祭儀,甚至過往祭儀中進行的歌舞領(lǐng)唱者也由朱姓族人負責③總主祭以朱姓的族長擔任為慣例。……首先在廣庭做圓陣,數(shù)人一起唱paSta’ay之歌,由一位朱姓的人領(lǐng)唱。……“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diào)查會”原著,中研院民族所編譯:《番族慣習調(diào)查報告書(第三卷)賽夏族》,臺北:中研院民族所,1998年,第30—33頁。,甚至部分祭歌僅能于送靈儀式期間誦唱,即便是祭儀準備期間族人也不能練習歌唱,因此只能由朱姓主祭念一遍歌詞,再帶領(lǐng)族人大聲歌唱。雖然朱姓長期擔任矮靈祭的主祭,但矮靈祭舉行前必須進行一次以上族內(nèi)各姓氏耆老或代表聚會討論,檢討前次矮靈祭的缺失并尋求改進與共識。朱姓氏族雖然較一般族人在理解傳說與祭儀的隱喻以及詮釋與發(fā)言權(quán)上高出許多,但舉行矮靈祭的過程是經(jīng)由族內(nèi)耆老所共同討論的“共識”,也因此提升賽夏族族人的參與感。全族參與度高,愿意認同此傳統(tǒng)文化,因此祭儀重復(fù)一次就強化族人對于傳說的記憶以及對自身族群的再認識。
矮人傳說賦予矮靈祭舉行的特殊意義,對于賽夏族人,它具有祭儀過程中行為的解釋與依據(jù)。對于外來客,傳說增加祭儀的故事性與趣味性。定期舉行也為傳說塑造出良好的傳承時空,矮人傳說能夠發(fā)展至今仍為賽夏族老幼皆曉,甚至鄰近族群也略知一二,矮靈祭的定期舉行具有很重大的助益。因此賽夏族矮靈祭與傳說,除了互相詮釋與隱喻外,對于兩者的傳承與發(fā)展也呈現(xiàn)出發(fā)展性的作用。
傳統(tǒng)續(xù)存與變因
矮靈祭從來都是賽夏族群的族內(nèi)祭儀,隨著與異族的交流,參與儀式的群體不再局限族人,至今已成為允許他族參與的族群祭儀。在社會環(huán)境轉(zhuǎn)變的影響下,矮人傳說和祭儀皆呈現(xiàn)出些微差異。
根據(jù)文獻,1945年之前賽夏族物質(zhì)生活即已受到外族影響④(1)大體上,他們的服裝類似' tayal族,不過與漢人接觸久了,也就逐漸有人模仿,例如褲子,現(xiàn)在男女已和漢人使用的相同了。(2)近來由于政府的獎勵,他們才懂得水田之利,而頻頻雇用漢人來開辟。并且也學習驅(qū)使水年、施肥料、除草及割稻、貯藏之方法。“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diào)查會”原著,中研院民族所編譯:《番族慣習調(diào)查報告書(第三卷)賽夏族》,臺北:中研院民族所,1998年,第49、59頁。,連帶也影響祭儀中所使用的物品,賽夏族至今舉行矮靈祭仍遵守該年度祭儀物品需當年才制作的傳統(tǒng),但許多祭儀物品已由方便取用的現(xiàn)代材料制作,如肩旗、臀鈴以及族服等傳統(tǒng)祭儀用具。連原本每年度重新整理出的祭場、祭屋以及族人休息區(qū)都改用現(xiàn)代建筑材料并固定存在,并非每次重新搭建。娛靈歌舞進行時,領(lǐng)唱祭歌者配戴麥克風藉由喇叭傳至祭場各處,處處有著現(xiàn)代化介入的痕跡。但較具核心或象征意義的部分,仍然部分存在依循傳統(tǒng)做法①2010年以及2012年矮靈祭中所見之各姓氏肩旗以及臀鈴皆用紅布、彩帶、亮片等現(xiàn)代材料制成,但外形仍與日本人所記錄相當雷同。除了上述之外,祭儀過程中使用到的蛇鞭,仍維持傳統(tǒng)做法以芒草制成,或是作為祭品之一的麻糬仍由朱姓氏族中的男性擔任且祭儀當天制作。。
雖然賽夏尊重族群文化②2010年參與矮靈祭期間就目睹某電視臺進入拍攝,卻沒有于攝影機上綁芒草,第二晚祭儀拍攝到一半攝影機就從架高臺上掉落,幸好攝影機被各式連接線卡住并未直接掉到下方人群中。事情發(fā)生后就于現(xiàn)場附近聽到賽夏族青年隊在抱怨該電視臺無視警告未綁上芒草,祭場旁族人休息區(qū)走出來探究竟的耆老聽聞賽夏族青年隊的敘述紛紛表示出該電視臺活該的態(tài)度。2010年及2012年于矮靈祭現(xiàn)場也都目睹有人于歌舞進行時手持攝影或照相器材跑至場中央正對著舞者進行攝影工作。等,還有隨著人潮的集中逐漸出現(xiàn)在祭場四族能夠掌握傳統(tǒng)矮靈祭儀的核心,但在媒體宣傳及地方政府觀光政策下,矮靈祭已從默默進行的族內(nèi)儀式到成為南莊、向天湖一帶兩年一度的觀光盛事。隨著越來越多觀光客進入祭儀現(xiàn)場“參與”,矮靈祭諸多問題漸漸產(chǎn)生,無論是祭儀過程中大量素養(yǎng)參差不一的觀光客,對賽夏族矮靈祭的文化內(nèi)涵不了解而產(chǎn)生不恰當?shù)男袨棰勖缋跄锨f鄉(xiāng)賽夏族矮靈祭結(jié)束前,祭典場地涌進許多趕搭“末班車”的游客,在不知其所以然的心境下,竟然在祭場中跳起土風舞,還有些年輕人大跳迪斯科。李德仁(1988年11月30日)原住民文化應(yīng)獲尊重矮靈祭涌進土風舞及迪斯科,是“文化沖突”也是“文化危機”,《聯(lián)合報》,第四版。,或是為了拍攝記錄而忘記最基礎(chǔ)的禮儀,或是不周的攤販不僅破壞祭儀現(xiàn)場的氛圍也影響族人的權(quán)益④一位參與籌劃的族人說,原本他們只想在會場設(shè)置山地傳統(tǒng)風味的攤位,收入用來改善鄉(xiāng)內(nèi)道路。可是部分長老卻私下與平地人妥協(xié),結(jié)果平地人攤位反比族人多,搶走了大部分生意,使祭典流于商業(yè)化。黃安勝(1984年11月10日)商業(yè)污染了矮靈祭!游客嬉笑娛弄族老戒慎恐懼“卡拉OK”介入抹殺會場莊嚴,《民生報?戶外活動新聞版》,第四版。。賽夏族歷經(jīng)不同政經(jīng)體系,過往無論是何政權(quán)都很難阻止矮靈祭的舉行,現(xiàn)今政府相關(guān)單位對于矮靈祭具有良性影響之時⑤矮靈祭期間在東河部落往向天湖會場的道路就會進行人車管制,游客只能搭乘鄉(xiāng)公所招攬的苗栗客運上下祭場。祭儀現(xiàn)場周圍也隨時都有警察與醫(yī)護人員待命。,矮靈祭觀光化現(xiàn)象著實讓部分族人與文化工作者感到憂心⑥對于矮靈祭觀光化的現(xiàn)象也已經(jīng)有學者關(guān)注論述,詳參簡鴻模著:《矮靈?龍神與基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北:“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2007年,第85—87頁。。
從文獻記錄及今日舉辦祭儀的觀察,矮靈祭周期皆為兩年一度,但族群耆老述及,更久遠之前的矮靈祭是每年舉行,日本人統(tǒng)治后才更改為兩年一次,延續(xù)至今。雖然舉行的周期因外來政權(quán)影響而有所變化,但賽夏族人仍定期舉行祭儀。臺灣許多原住民族群因時空環(huán)境轉(zhuǎn)換,傳統(tǒng)生活場域不復(fù)存在,傳統(tǒng)祭儀受到相當大沖擊,部分儀式已難窺全貌,甚至不再舉行。除了祭儀之外,目前臺灣原住民各族群社會中普遍存在因傳統(tǒng)講述故事的場域逐漸消失殆盡,導致故事傳承的斷裂現(xiàn)象,加上娛樂環(huán)境刺激,影響族內(nèi)下一代聽耆老講述自身族群故事意愿低落。在此種情形下,矮人傳說至今仍在賽夏族人口耳間流傳,是值得關(guān)注的現(xiàn)象。
矮靈祭雖然由朱姓擔任主祭,但祭儀過程全族皆會參與并協(xié)助祭儀的進行,即便與外地工作之家庭也會舉家回向天湖參與矮靈祭。絕大多數(shù)族人屬于自發(fā)性的參與矮靈祭,而且在其人生經(jīng)驗中凡舉行矮靈祭必會到場參加,甚至現(xiàn)場可見旅居在外地的賽夏族家庭。這些現(xiàn)象呈現(xiàn)出對于賽夏族群來說,在長時間不斷重復(fù)舉行祭儀的過程中,此項傳統(tǒng)漸漸成為支持族人凝聚力的動力。賽夏族長期處于人口以及活動范圍遠比鄰近其他族群稀少的狀態(tài)①截至2013年9月最新官方統(tǒng)計,賽夏族群總?cè)藬?shù)也才6304人,居住于新竹、苗栗一帶的族人僅2090人。鄰近的泰雅族群總數(shù)為84501人,居住于新竹、苗栗一帶的族人為11010人。客家族群至2011年的調(diào)查,總?cè)藬?shù)為3147100人,居住于新竹、苗栗一帶的客家人為661500人。由此可知居于賽夏族不論是人口總數(shù)或是居住于傳統(tǒng)領(lǐng)域的族人數(shù)都遠低于鄰近的泰雅族與客家族群。數(shù)據(jù)引自“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原住民人口數(shù)統(tǒng)計資料:http://www.apc.gov.tw/portal/ docDetail.html?CID=940F9579765AC6A0&DID=0C3331F0EBD318C21985875FCD290BDE“客家委員會”客家人口調(diào)查,99年至100年客家人口基礎(chǔ)資料調(diào)查研究:http://www.hakka.gov.tw/ct.asp?xItem=43944&ctNode=1894&mp=1&ps= 2013年10月13日瀏覽。,因此自身族群消亡的恐懼一直存在②賽夏族部分老壯年紀的族人會開玩笑講,說賽夏族睡了50年才增加2000人,雖然是當笑話在講述,但從其講完后神情略顯憂愁的轉(zhuǎn)變,凸顯自身族群與文化不復(fù)存確實是賽夏族部分族人的憂慮與恐懼。,加上部落就業(yè)機會低于都市,青壯年人口普遍外移,在接受外界刺激下,部分族人恐怕對于自身文化漸漸遺忘或舍棄。矮靈祭的舉行提供族人再認識自身族群文化的場域,也正因為矮靈祭是全族參與的盛大祭儀并非部落或家姓自行舉行的小型祭儀,所以儀式過程中充滿賽夏族特殊的象征與隱喻,在長達五天左右的祭儀過程中,族內(nèi)的男女老幼回到部落沉浸在傳統(tǒng)文化的氛圍之中,具有提升賽夏族社會的凝聚力以及族群意識的正面效果。
部分族人因職場或生活要事而無法參與矮靈祭時,總會因為錯過參加某年度矮靈祭而心存罣礙,直到再次參與矮靈祭時才稍微舒緩。這樣的現(xiàn)象可說明,部分賽夏族人對矮靈祭已產(chǎn)生某種責任與義務(wù)的心理,也顯示賽夏族人參加矮靈祭不僅有積極的族群認同也有消極被動的一面,因為未參與身為賽夏族人“應(yīng)該”參加的矮靈祭,使得未參加者出現(xiàn)愧疚或自我譴責的心理狀態(tài),且此心理狀態(tài)又必須透過參與矮靈祭才得以解除,賽夏族群的這種現(xiàn)象部分詮釋了儀式于社會中的作用③現(xiàn)在學者們正逐漸看到,儀式正是這么一個機制,它將這種應(yīng)盡的規(guī)范和責任周期性地轉(zhuǎn)換成想要做的規(guī)范和責任。儀式的基本單位,即支配性象征符號,壓縮了帶來這種變化的整個儀式過程的主要特點。在其意義框架內(nèi),支配性相爭符號將社會的道德和法律規(guī)范與強烈的情感刺激緊密相連。維克多?特納著,趙玉燕、歐陽敏、徐洪峰譯:《象征之林:恩登布人儀式散論》,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6年,第29頁。,因此矮人傳說以及矮靈祭中的隱喻與象征將賽夏族群的情感緊密連結(jié),經(jīng)由對于傳說與祭儀的共同認識和參與感,強化對于我群的認識與肯定。
結(jié) 語
在臺灣原住民中并非只有賽夏族流傳矮人相關(guān)傳說,但僅有賽夏族舉行祭祀矮人的儀式,因此環(huán)繞矮人族群與自身族群的敘事以傳說和祭儀兩種方式詮釋。這兩種詮釋方式與賽夏族的族內(nèi)關(guān)系緊密結(jié)合,傳說與祭儀兩者形成互為作用關(guān)系,傳說內(nèi)容作為祭儀實踐過程中象征的由來與解釋,祭儀行為再現(xiàn)與強化族人對于傳說的形塑與記憶,經(jīng)長時間一次次的重復(fù)行為與講述,兩種文本交互影響,成為賽夏族社會重要的族群記憶,也強化了族人對于傳說和祭儀傳承的族群意識與社會義務(wù)。
歷經(jīng)時空的交融,外族與現(xiàn)代化文明的介入,傳說與祭儀產(chǎn)生些微變化。不論是物質(zhì)環(huán)境改變、族內(nèi)解釋權(quán)力的集中或外來者行為的刺激等,都讓矮人傳說以及矮靈祭在賽夏族社會中產(chǎn)生轉(zhuǎn)變,面對部分轉(zhuǎn)變,族人正反見解皆有④2012年在矮靈祭現(xiàn)場非朱姓青年表示,能夠于矮靈祭中擔任領(lǐng)唱工作讓他更有參與感,也因此加強他在祭儀準備期間的熱情與責任感。另外祭儀期間于祭屋前擔任綁芒草工作的朱姓少年對于自己在祭儀中的職位表示,此為長輩交代之工作并無特別情感于其中,但對于許多外地人來到向天湖參與矮靈祭是感到高興的。同樣年度也于祭場遇到一位豆姓耆老反對外人參與祭儀歌舞的時間從午夜12點提前至晚間10點,認為此做法違反過往慣例。,這也是族群在時空轉(zhuǎn)換下,傳統(tǒng)接受挑戰(zhàn)下族人的各自選擇。
[責任編輯:王素珍]
K890
A
1008-7214(2016)04-0096-09
王人弘,東華大學民間文學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