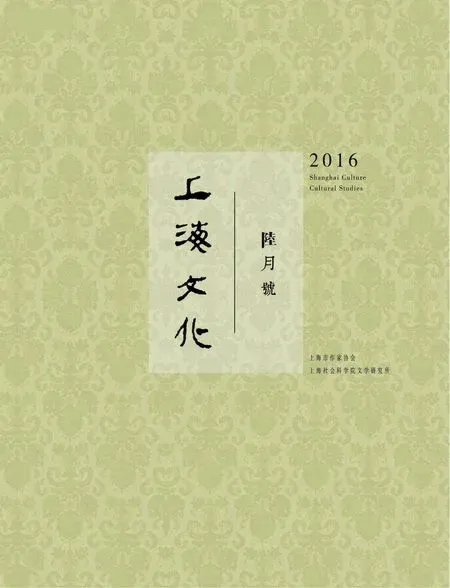重視開展對當代信仰問題的研究
——“中國當代文化發展中的信仰”討論會綜述
沈 潔
?
重視開展對當代信仰問題的研究
——“中國當代文化發展中的信仰”討論會綜述
沈潔*
內容摘要為進一步推動有關信仰問題的討論,北京大學文化研究與發展中心、四觀書院,以及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上海文化》和社聯《學術月刊》分別在北京與上海兩地舉辦有關中國當代文化發展中的信仰問題學術討論會,幾十位知名專家學者紛紛發表高見卓論。從信仰的本體理論、信仰與當代社會的關系、中國文化的信仰傳統三個方面作了深入的闡述和探討。本文即是南北兩次會議的綜述。
關鍵詞信仰當代社會中國文化
在振興中華文化宏偉愿景的鼓舞下,中國文化建設不斷推進,同時信仰問題亦日益受到人們的關注。《上海文化》自2015年第8期起連續3期發表了南京大學潘知常教授的《讓一部分人先信仰起來——關于中國文化的信仰困局》長文,對中國文化在現代化轉型中如何走出信仰困局、重建信仰的問題作了專門的論述。為進一步推動這一討論,由北京大學文化研究與發展中心、四觀書院主辦,《上海文化》協辦的“中國當代文化發展中的信仰建構”學術討論會,于2016年3月26日在北京四觀書院召開。中央黨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國藝術研究院、南京大學等20多位專家、學者出席會議;由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上海文化》和社聯《學術月刊》聯合主辦的“中國當代文化發展中的信仰問題”學術討論會于4月16日在滬舉行。來自南京大學、浙江大學、蘇州大學和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華東師范大學、上海大學、上海師范大學的20多位教授、學者參加了討論會。
在南北兩地會議中,與會者聯系當代社會實際和百年來中國社會的轉型,對當代中國的信仰問題展開熱烈討論。歸結起來,作了三方面的探索:一是對信仰本體理論的探索,二是對信仰與當代社會關系的經驗描述與理論反思,三是對中國文化的信仰傳統的思考。
一、對信仰本體理論的探索
與會者對信仰的概念進行定義,對信仰的歷史進行了梳理。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牛宏寶指出,第一,我們是在現代意義上談信仰,還是在傳統意義上談信仰?是在共同體意義上談信仰,還是在個體意義上談信仰?是在有神論的宗教意義上談信仰,還是在無神論的意義上談信仰?不同的立足點會有不同的關于信仰的闡釋。第二,我們如何來診斷當代的信仰危機?這個信仰危機是怎么形成的?是我們曾經有信仰,而今天丟失了那個信仰,還是原來那個信仰已經失去其召喚力?目前的信仰危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信仰方式的更替造成的?如果把當代信仰危機問題,診斷為一個傳統體系的崩潰,或者傳統文化被割斷呢,還是新的現代的信仰方式沒有有效建立的問題?第三,就是信仰與知識之間的關系。西學的進入,既有知識體系的層面,也有信仰的層面。西學的知識體系層面,對中國現代知識體系的形成是一個推動力。要注意既不能以這套知識體系替代信仰,也不能用信仰的體系來批判這套知識體系。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郭英劍認為,信仰的定義必須明確。信仰有兩種。英文的信仰有兩個最基本的詞匯,“belief”和“faith”。如果仔細觀察,會發現這兩個英文的闡釋當中有一個中心詞,叫“truth”。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真理”、“真相”,也是“事實”、“實質”的意思,說明在談信仰的時候,都要以“真理”或者“事實”為前提。信仰一般可以分為兩種,第一種是跟宗教有關的思想理念,也就是宗教理念。第二種跟宗教無關,就是非宗教人士如何看待生命和萬事萬物的人生態度及其體現的價值觀。在當下中國,我們更關心第二種信仰,就是對于那種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如何看待生命和萬事萬物的人生態度及其體現出的價值。在中國如何建立信仰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同時如何超越世俗化去思考現實,也是經濟高速發達的中國所必須要回答的問題。
復旦大學教授王振復認為,信仰問題有三個層次,第一個是宗教信仰;第二個是與宗教信仰相對應的世俗信仰;第三個是指宗教信仰和世俗信仰之間的一個文化信仰。中國早期的信仰文化,主要是巫性文化。巫性包含兩重性,既“信”天人、物我、主客和物物之間的感應,又“信”人能使感應變成現實,包含講求“實用”的原始理性意識。早期文化信仰主要是巫的信仰,這是中國獨特的文化特點。如果我們不去研究巫,便不能從“根”上說清文化信仰問題,要進一步講當前的信仰問題就比較難。其實我們不是沒有信仰,凡是一個思想成熟、有追求的人,大凡都是有信仰的。比如說我們都喜歡學術,一輩子就想做學術,出于極度的喜歡,就是一種世俗信仰。而中國夢是一種崇高的信仰。問題不在于有沒有信仰,信仰是有的,問題在于信仰什么、怎么信仰。我們提倡社會進步、追求完美人格的“信仰”。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郭家宏援引英國歷史,說明他國是如何運用宗教信仰來重塑民族精神的。除了先進的生產方式和先進的制度文明,英吉利民族本身所具有的宗教信仰、民族特性,以及英國社會各個階層與英帝國發展的互動關系等因素十分重要。如果說,宗教信仰在英國民族國家形成、在工業革命中發揮重要作用的話,那么在19世紀,宗教信仰對維護社會穩定起了重要作用。如經過長期的沖突與對立,針對中產階級的慈善活動及普通群眾的自尊運動影響巨大。由此各階層不同的價值取向融合成一種獨特的標準,即紳士風度。其特點包括公平合理的競爭原則,言行處事應盡量抑制感情的色彩,而讓理性來主宰一切。堅韌不拔、勇往直前的氣概,為維護個人與國家的榮譽在所不惜。正是這種宗教信仰和民族傳統結合形成的新的民族精神,使英國保持了長達200多年的世界超級大國的地位,且國內長達300多年時間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戰爭與動亂。這在世界各大國是絕無僅有的。由此可見,宗教信仰必須根植于民族傳統的土壤里才會生根發芽、茁壯成長。
《學術月刊》編輯張曦博士認為,如果通過論述基督教信仰為西方帶來的一系列革命性變革,來證明中國人應該信仰起來,其目的并不最終落在信仰本身,而在中國一系列現實問題的解決,即所謂社會福音的思路是不恰當的。一旦把基督教視為解救社會的良藥,其實就偏離了真正的基督信仰本身。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基督信仰的重點不是指向人,而是指向神,上帝的計劃才是整本《圣經》的重點;它關心的也不是這個世界所關心的,神要在這個世界里建立他的國度,實行他的憐憫與救贖。這個世界遲早要廢去,神的國度——天國才是永恒的存在。當然,人和人類社會自然也是神創造的一部分,但是其目的并不在于人類自己的理想。而由信仰派生出來的諸多現實福利,如自由、平等、愛、美、人權,看起來是可行的,但與終極信仰無關。基督信仰乃是要人悔改、離棄自己的罪,彰顯神智慧和真理的美。關于人權,基督教從來沒有過借助“神權”以高揚“人權”,相反,它是對人犯罪墮落、走向滅亡的徹底肯定。所以說這一切,包括自由、平等這些,離開了神,離開了耶穌釘的十字架,都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都是無法想象的。
復旦大學教授李天綱認為,今天談宗教的問題,應該在一百年的歷史脈絡和世界的脈絡當中做一個徹底的反省,中國到底有沒有宗教?傳統的儒、道、佛是不是宗教?我們一百年當中已經把儒、道、佛變成了一個現代宗教,今天的佛教、道教,包括儒教到底是什么?現在的某些知識分子,包括提倡宗教的知識分子,他們想把儒教政教合一,想做官方的儒教,也想參與官方的佛教,這是政教不分。而政教分離是要堅持的,過去一百年當中,我們好不容易把政教分離了,使得社會的危機降低了,而現在搞政教合一,會加強社會危機,會強化整個社會的沖突,這是違背中國人信仰的傳統。因為中國人的信仰基本上是多神教的,宗教之間是有寬容的,只要不搞政教合一,不要官方宗教,大一統是在宗教和諧的關系下處理的。雖然有儒家,但儒家很少涉及佛教、道教最高的信仰。這些東西如果用現代社會的治理原則,搞政教合一,宗教的問題會引起很大的沖突。
上海大學教授陶飛亞從國家治理和宗教結構的角度,論述宗教與社會的關系。他認為各個宗教在其宗教儀式后面的修身養性、無我、愛人如己、積德行善以求來世的道德說教,會影響到民眾在王法不及的思想深處有敬畏之心和道德上的追求。一方面,宗教對于人的處境給予一種解釋,滿足了一些人的心理需要,使人安于和接受現狀;另一方面,宗教也給人一種希望,即通過自身的努力,在宗教崇拜中提升道德和在社會生活實踐善行以求將來或來世命運的改善。所以中國歷史上除了三武一宗的滅佛和清前中期的查禁西方來華天主教等特殊時期之外,歷代統治者都寬容宗教甚至民間信仰,希望宗教能在社會治理中,不僅對信仰者群體,而且在教化社會人心向善方面起到或多或少的輔助作用。從宗教自身來講,它總是希望能影響其他人群。從社會來講,則是希望宗教能在實踐層面彰顯宗教的善。因此,從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來說,世俗社會的力量和宗教界力量,各自有分工有合作地為社會服務,并互相促進,這對宗教與社會都有更積極的意義。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陳衛平引述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說到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國家有力量。但這里說的信仰,肯定不是指宗教信仰,無疑是指社會民眾的公共精神信仰。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們所講的信仰危機、信仰缺失,都不是講宗教信仰的問題,而是講社會公共的精神信仰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宗教發展是很快的,信教的信徒占了人口總數很大的比重。這似乎已經引發了某些擔憂。從這個意義上講,在當代中國文化發展中,宗教信仰并不缺失。當然,宗教信仰在構建當代中國社會公共精神信仰中的地位、功能、作用等問題,也迫切需要認真地研究。
北京大學教授閻國忠認為,真、善、美作為人類最高的旨趣,是超越一切時代和民族的,但是每一個時代和民族,甚至同一時代和同一民族中可以有不同的載體。美學是討論信仰問題的最佳切入點,真正的信仰應以真、善、美為指向。回溯老子與孔子及柏拉圖與奧古斯丁的信仰經驗,梳理信仰與宗教、哲學、藝術的關系,以及有關信仰危機引發的一系列思考,可以看出信仰是人類精神生活的最高形式,是宇宙觀、人生觀、價值觀的最高體現,因此克服信仰危機,重新確立真、善、美的崇高地位,是關涉整個社會的浩大的系統工程。
二、對信仰與當代社會關系的經驗描述和理論反思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李向平認為,中國人現在不缺信仰。我們現在講信仰的話,按照中國的定義一個是政治信仰,一個是宗教信仰,還有一個就是文化信仰。中國歷史傳統中的信仰危機(并非信仰缺失)往往是在朝代權力更替之后,這也是辛亥革命以后為什么有四大宗教替代思潮,而非信仰危機的直接出現。至于在宗教替代思潮之后,各種思潮又被總體整合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乃至于后來提的共產主義,建構成為一個政治信仰體系或者人文信仰體系,如此看來“信仰缺失”這個概念應該是不能成立的,應該說“信仰危機”應該更加切題,但這是哪種信仰危機?是政治層面的信仰危機?還是宗教層面的信仰危機?或者這種危機是因為缺乏信仰之間的價值共識?因為,無論從哪種信仰視角出發,中國社會的信仰并非缺失。另外當代中國社會還有一個普遍的感覺,那就是“信仰無用”或信仰的功利化。我們不是缺信仰,而是各種信仰類型之間沒有達成一個價值共識,沒有一個共同表達的公共領域,沒有一個普遍認同的公共關懷,進而才會使這些有信仰的人難以基于自己的信仰表達出自己的公共關懷。信仰很重要,誰也缺不了信仰,但信仰關系的私人化如何構成個體化,以后再有公私領域的相互配合,能夠提供信仰關系進入公共領域,這可能還需要有一個長期的努力過程。
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包亞明認為,因為我們二三十年來已經進入了資本主義大循環,面臨很多的社會背景、思想背景,和當代西方社會其實有非常大的相似性。而且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社會其實已經在不知不覺中建立了世俗的共同信仰,這種共同信仰已經非常根深蒂固,這就是對于資本主義的信仰,對于商品拜物主義的信仰。正像本雅明認為的那樣,資本主義這一世俗的公共信仰,恰恰具有非常大的宗教性。據托尼·朱特的觀點,這種公共信仰形成了追求物質上的自我利益的目的集體意識,導致我們會迷戀創造財富,貧富更加分化,對不受約束的混亂市場毫無批判的崇拜,對無限增長的幻想,因此當代中國社會不是沒有世俗的信仰,而是已經形成了非常根深蒂固的對于資本和商品拜物教的公共信仰,而且這種世俗的信仰恰恰具有相當程度的宗教性。
與會專家、學者對如何建立小康社會的信仰,紛紛從多個層面提出了建設性的對策與建議。
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原所長、上海師范大學教授陳伯海認為,“信仰”體現人的終極關懷,而其根子仍深植于現實世界。面對當前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必然呈現的多元分化與矛盾錯雜的態勢,中國社會當奉行具有較大包容性的生活理念,或可嘗試以法制公正與人際互利前提下的“和協共生”原則為出發點,進而溝通“天人關系”,為打造自然與人文為本的新信仰提供借鑒。他主張宗教僅作為個人信仰,社會共同信仰以非宗教的信仰為宜。非宗教的信仰如何來建立呢?要從現實出發,正在建設中的小康社會,是我們的立足點。可以用“敬天立人,和協共生”八個大字來加以概括,就是“在法制公正與人際互利條件下的和協共生”。因為信仰作為終極關懷,不能停留于一般生活準則的層面,它要含藏一個終極的指向,也就是形而上的維度。這個維度可以從“和協共生”自身開發出來,途徑是將這一理念指向天人關系,即傳統哲學思想中的最高命題。如果嘗試將“和協共生”的理念應用于人所面對的天人關系、人際關系以及自我身心關系三個方面,以“天人和協”、“人際和協”、“身心和協”為貫徹這一理念的三個向度,那么,真能做到這方方面面的和協共生,才有可能實現人類及其社會的發展,推動歷史與文明的進步,進而爭得自由、民主、和平與愛。
浙江大學教授王杰認為,信仰問題最根本的是人生意義的問題,所有的宗教最關鍵的就是人生意義的問題。科學已經非常強大了,但人生的意義在今天仍然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并沒有解決。有很多人賺了很多錢,人生意義卻是落空的。如果從這個意義來講,我們當代中國文化的發展,就應該和當代中國人的人生意義結合在一起。如果我們去找孔夫子,找釋迦牟尼,找耶穌,可能都不能最終解決今天的現實問題。今天的現實問題就是重新激活文化的烏托邦沖動,重新思考一種超越資本主義文明的更合理的文明。
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許明從信仰的多樣化與主流價值的歷史定位入手,指出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知識精英的價值問題,總會面臨一次次的選擇。20世紀初西方現代性的思想,西方啟蒙進來以后,對知識精英形成了沖擊,中國知識分子在價值重建和價值選擇的層面上苦苦掙扎。目前問題在于:第一個層面是社會世俗階層支撐這個社會結構穩定的倫理危機,第二個層面是知識精英的理性價值選擇危機,第三個是執政黨的理想危機。所有的危機綜合起來,是一個社會轉型、文化轉型的危機,這個危機是一個必然的過程。我們要把問題提得很明晰,建議要非常具體,信任問題、信用問題,通過政策、制度設計一步一步往前推進,可能這個社會性危機會得到合理的解決。
上海交通大學教授胡惠林認為:信仰是一種社會的精神秩序。信仰是由不同的土壤決定的,不同的土壤產生不同的信仰。對當代中國來說,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兩種不同的土壤,不能指望兩個不同的土壤產生同一種信仰,因此在計劃經濟的土壤之下形成和建構起來的這樣一種信仰或者精神秩序,到了市場經濟條件下,土壤發生變化了,那么它也要發生變化。現在文化產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生產著一種精神秩序,某種信仰的形式。從我們電視中各種各樣的娛樂節目就看到,現在的媒體,在生產供給一種怎么樣的文化產品給我們?有些東西是深刻地影響和建構著我們的信仰體系的。特別是這10多年來,文化產業在中國的發展,一方面從制度和體制上是非常開放的,具有許多重大改革的舉措。但在這個過程中,忽視了文化產業發展過程中對人們精神秩序和社會精神結構進步的影響,尤其是對年輕人的影響。只要打開我們現在的電視機,尤其是那些真人秀節目,有些語言和觀點實在不應該出現在電視屏幕上,非常的少兒不宜。這種價值導向深刻地影響著我們年輕人。另外就是網絡,現在很多網絡語言非常不健康。所以娛樂至死這樣一種文化產業發展的導向,對于我們當下的年輕人的信仰、精神秩序的建構是不利的,可能導致我們當下最嚴重的一個信仰危機。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高瑞泉不贊成把道德危機完全歸結為僅僅是信仰的問題,道德危機造成的原因非常復雜。圍繞“信”,應該有四個關鍵詞,第一個是信用,第二個是信任,第三個是信念,第四個是信仰。信用是第一位的,信用社會是依靠法治建立的。如果一個人進入誠信黑名單,以后就會遇到很多問題,這是一個合理的、健康的社會建設。第二步是信任,一個穩定健康的社會,應該是實現高度團結的社會,而高度的團結需要建立在社會信任的基礎上。沒有基本的社會信任,就沒有社會團結,如果沒有社會團結,宗教越多,越困難。第三個是信念,人與人之所以有高度的信任,是在平等主義的政治、文化中間有一些共同的信念。實際上中國是有的,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第四個是信仰,信仰是精神生活中追求超越的一面。應該承認信仰是個人選擇,可以是多元的,而國家應該尊重和保護個人的選擇。
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社會科學報》總編段鋼認為,就當下的現實來說,由道德而致道德信仰或許是一條中國的發展路徑。一直以來,中國社會都是由倫理道德代替宗教的社會功能,也能維系社會的發展。道德雖然缺乏宗教的儀式、功能等,卻未必不能代替宗教的社會功用。當下中國社會,隨著經濟高速發展,倫理道德顯得有些弱化,同時缺乏強大的如西方的傳統宗教基礎,社會的凝聚力顯得薄弱,社會分層、社會部落化等現象明顯,這樣的情況下,只有靠社會倫理道德的再造,為社會提供更為強大的黏合劑,可以起到替代宗教缺位的社會倫理作用。對于一個缺乏宗教傳統的社會,社會的倫理道德結構顯得更為重要。社會倫理道德是一種群體與個體遵守的社會秩序底線,突破這一底線就屬于法律的管轄領域。良好的社會倫理道德對社會的進步具有能動作用。其實在這方面我們也是有傳統的,只是近代以來被摧毀得比較厲害。比如,傳統中國鄉村社會的士紳階層,是凝聚傳統社會的強大黏合力,現在的鄉村宗廟祠堂消失殆盡,地方士紳權威缺少,這一階層的力量逐漸分崩離析,社會倫理道德作用在弱化,這也是為什么現在的農村很凋敝的原因。靠什么重新聚合散亂的鄉村社會?靠社會倫理方面的建設更為重要,而不是簡單拿西方信仰說事。因此,中國需要的不僅僅是在生存層面,而是聚合在更高層面的信念共識,更多落腳于社會建設和社會秩序上,這就需要更多現代社會的基本信念共識,這個信念共識就是維系社會存在所必需的價值基礎、倫理規范等。
上海文化局巡視員毛時安認為,信仰實際上是有好壞、有有用和沒用的。今天中國的第二次信仰危機,就把我們原來建立的這種溫情、倫理、道德沖垮了。現在許多人相信壞人,信任壞人,教自己的孩子也是投機取巧做壞人。所以現在首先要建立一個基本的信仰,即是要做好人的信仰。“信”和“仰”,“信”就是你內心真正要去相信,“仰”就是頭頂上的星空,你要仰望,這是道德的東西。有信仰的文化才是有感召力的文化。
上海師范大學教授楊劍龍從三個方面指出:第一,大眾文化流行背景中的道德危機。我們的道德確實存在某種危機,大眾文化流行以后物欲主義盛行,市場經濟加速了生活世俗化,文學也世俗化。從文學來說,從宏大敘事到日常生活,都是一些瑣碎的東西,在這樣的背景中確實存在一種道德危機。第二,當代文化發展中的宗教。有人類一定有宗教。在當代的文化背景中,宗教也在發展,宗教是和諧社會的助動器,宗教可以促進和諧社會。第三,信仰問題與宗教出路。不太贊成“替代”這個詞。五四時期的非宗教、非基督教思潮想替代宗教,但在替代背后有一種潛在的隱憂和潛在的自卑,宗教力量強大。另外從信仰跟宗教的關系看,信仰是一個大概念,宗教是一個小概念,信仰不能代替宗教,宗教可以是信仰。
三、對中國文化信仰傳統的思考
中國傳統文化具有悠久的信仰傳統,尤其是儒家文化。不少與會專家、學者認為應對當代社會的信仰危機,不僅不能削弱儒家文化的影響,而且應該加強儒家文化的力量。發掘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精髓,并創新與堅守當代中華民族的信仰精神。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李景林指出:周代的禮樂和宗教信仰系統,經過儒家形上學的意義轉化,成為一種真正意義上的“道德的宗教”,構成了幾千年中國社會超越性價值與信仰的基礎。這套禮儀的系統,因社會的歷史發展不斷因革損益,以適應時代的變化。這使得儒家的這一套教化能夠與社會生活密合無間,保持有一種生生不息的、活的生命精神。因此,儒家的教化,既有全社會意義的普遍性,又具有極大的包容性。中國當代信仰的重建,一方面是社會生活這一套信仰禮儀系統的重建,另一方面是接續傳統的與之相切合的思想理論的重建。把這兩個方面統合起來,中國當代信仰的重建才能獲得一個光明的前景。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任登第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由儒、釋、道三家組成,以儒家為代表。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大公無私、天下為公。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是孝,其本是敬,落實在生活,就是孝親尊師。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大根大本。因此,一要相信中國傳統文化能夠救中國,救世界,救人類,救地球;二要相信中國共產黨能夠領導我們實現中國夢。這是我們中國人當前急需建立的最高信念和最高信仰。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毛佩琦認為,強勢輸入的外國的思想理論和根深蒂固的中國傳統的文化沖突,是當今信仰缺失的基本原因。西方文化的核心是分,從科學到社會都是分,是斗爭,是奪取,是利己。中華傳統講究義利之辨,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舍生取義是中華傳統文化恒久的價值觀。一方面,我們對所謂西方文明做了實用主義的選擇性引進;另一方面,則是無情地、不加區分地拋棄了我們的固有文化,因而造成了信仰的混亂,甚或蕩然無存。信仰分政治信仰和非政治信仰。應把政治態度、政治主張與信仰剝離開來,允許信仰的不同選擇,這樣更實事求是,也避免了信仰者的內心糾結,使信仰更為坦然。讓人們更為寬松地選擇不一樣的信仰,這是當今建立信仰的一個關鍵所在。在允許多種信仰的大前提下,重建中華文化的主體性。當代信仰的構建一定也是多元的。需要有適應新時期,引領新時期的理論研究和理論建設,沒有切實可行的理論是不行的。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劉成紀認為,人在社會中生存,終歸是需要信仰的。與西方相比,中國人宗教信仰的薄弱是不爭的事實。基于西方一神教信仰的專制性,中國人信仰的薄弱和多元性可能正是中國文化的優勢所在。首先,中國由于沒有西方式的嚴格的知識分類標準,一切人文性的東西均無法做出截然的分割,知識與信仰的關系也是如此。中國人可以從知識直達信仰,或者反過來從信仰貫通知識,兩者具有一體性。它是一個從知識到信仰、從經驗到超驗的連續的系統。同時,單就信仰而論,傳統中國人的信仰,也表現為一種內在的過程或連續性的狀態。比如中唐之后中國的文人,往往有一個典型的特點,即青年時基本上都是儒家,中年之后開始轉入道家,老年時開始轉入佛教。儒、釋、道三教,分別在人生的不同階段,給中國人提供了精神的安頓。另外就是中國人宗教信仰的復合性,它表現于個體、家族、國家、文化諸層面。對于個體來講,有一個從儒向道、再向釋的連續演進。對于家族來講,現世有父慈子孝,來世則有祖宗神信仰,即以家祠宗廟供奉列祖列宗;最后則直達漢民族的共同祖先,即炎黃子孫。對于國家來講,家族內部的父子關系被延伸到國家層面的君臣關系,即按照家國同構的原則從孝走向忠。忠上面還有神,還有一個超越性的自然神靈,即天。從文化藝術層面講,中國傳統哲學歷來強調教化,即詩教、禮教、樂教。詩教主要面對幼童,禮教主要面對青年,樂教主要面對成年,最終達至“大樂與天地同和”。因此中國人不是缺乏信仰,而是缺乏西方獨斷性的一神教信仰。或者說它的信仰不是一個絕對實體,而是一個過程性的東西。這種復合式、連續性的信仰在人生的每一個環節給人提供具有針對性的精神指引。它為人提供的精神撫慰和安頓,比西方的基督教要更到位。
北京大學文化研究與發展中心副主任、四觀書院院長周易玄認為,中國文化儒、釋、道三大家,就是合在一起為我們中華民族構架了一個完善的、完整的信仰系統。用12個字來概括,就是“誠虛靜,正清和,真善美,精氣神”。以誠心、虛心、靜心養正氣、清氣、和氣,成真人、善人、美人,最后精氣神貫通天地,充塞寰宇。所以是以心使氣,以氣養人,最后天人合一。這就是中華文化儒、釋、道的信仰建構。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摩羅認為:第一,地緣政治學、戰爭學能解釋的問題,未必需要用文化和信仰來解釋。中國近代以來遭遇的失敗,都是在西方殖民全世界的背景下發生的,那是赤裸裸的搶劫和戰爭,后來演變為赤裸裸的地緣政治博弈。如果僅僅從文化和信仰角度解讀這段歷史,適用性很小。第二,我們進行文化的、信仰的建構時,所能仰仗的資源,恐怕還是得以本土文化為主。第三,我們不能陷入信仰依賴癥之中,而應該把信仰看作諸多文化現象的一種。信仰究竟能解決什么層面的問題,最好持謹慎態度。我們如果把西方文明的正面成果都歸功于基督教,歸功于信仰,那么,西方文明的負面現象,足以對這樣的結論否定一千遍、一萬遍。如果期待輸入這樣的基督教來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恐怕很難如愿以償。中國社會確實面臨著許多問題,但是不可期待各種社會問題都靠信仰來解決。對待歷史問題也一樣。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一代賢才對中國社會的現實問題和歷史問題,做了“唯文化論”的解釋,今天看來這種解釋較為偏頗。今天我們如果企圖以“唯宗教論”、“唯信仰論”的方法來解釋中國的歷史問題和現實問題,必須十分謹慎。
蘇州大學教授方漢文認為,儒學批判,是現在必須要做的,要用馬克思主義來闡釋儒學。儒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觀念,一方面要繼承,因為我們現在討論的確實不是個人的,不是每個人信什么的問題,現在需要討論的是國家需要的中國傳統文化核心價值的評定。因此應從馬克思主義本體論、認識論、實踐論三個角度對儒學進行評價,要好好審視儒學里面有哪些不適用現代社會的,比方說儒學中否定宗教的內容,針對法治的言論,或者說儒學和現代科技的關系,這個確實應該是我們很好研究的。只有認真地對儒學進行新批判,這樣才能真正有新儒學。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陳衛平認為,現在不少提倡儒學的人認為民眾信仰或被“洋教”所滲透,或被鬼神迷信所蠱惑,必須以弘揚儒學予以抵制。一些人大力推進儒學,以為應當接續近代康有為的“孔教會”,把儒學建構為當代中國社會的公共精神信仰,成為中國的國教。但真若以為把儒家的思想變成“國教”,就能解決中國人的公共信仰問題顯然是不可能的。為什么呢?要使得這樣一種行為的規則絕對能夠發生效用,絕對去遵守,要有兩個東西,一個是理性,一個是宗教情緒。儒家所訂的行為規則是學說的結論,是理性的產品,本來是可以為人們的行為絕對遵守。但后來把儒家的思想變成了宗教教條,看作神的誡命,要求人們無條件地服從。于是理性便無可應用;而學說對人們的行為發生效力只有通過理性一條路,因而把儒學宗教化是割斷了學說在人們內心唯一可靠的理性基礎,失去了為人們絕對遵守的機會,雖然人們在口中人云亦云地背誦它。中國有句話流行的話,叫作“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宗教講的死后的懲罰不在儒家的賞罰范圍之內,儒家的賞罰是人死后的褒貶,這對中國人的作用是很微弱的。
除了以上學者的發言外,國家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宋澎、中國人民大學孟憲實、上海交通大學范慕尤等專家、學者也都到會參與了討論。
責任編輯:任天
*沈潔,女,1963年生,上海市人。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