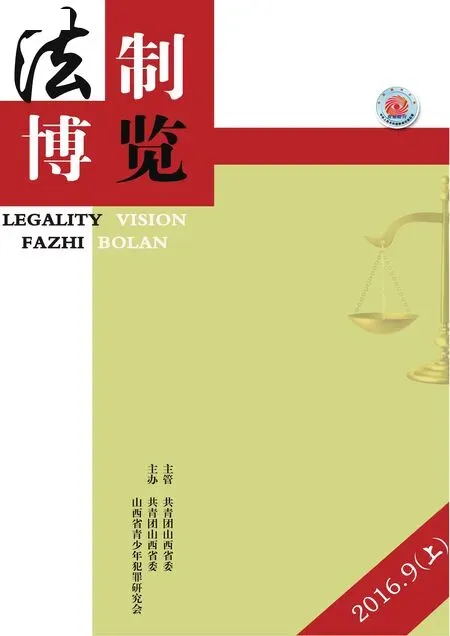警察訊問語料在刑事司法過程的格式轉換研究*
楊淑芳
湖北警官學院,湖北 武漢 430034
?
警察訊問語料在刑事司法過程的格式轉換研究*
楊淑芳
湖北警官學院,湖北武漢430034
本研究以英國刑事司法體系為例,分析了警察訊問語料在整個司法過程中的格式變化,提出警察與嫌疑人的對話不應該被看成是孤立的、自成一體的單個事件,而是整個刑事司法過程的一個環節。研究認為,在刑事司法過程中,訊問語料格式的變化可能會給司法的公正性帶來一定影響,因此所有證據都必須盡量保持其原始性。
警察訊問;語料轉寫;格式轉換
偵查訊問是公安等偵查機關為了查明刑事案件的事實真相,收集案件證據,揭露和證實犯罪,依照法律程序,面對面地以言語方式對犯罪嫌疑人進行審問的一種偵查手段。但是,在審訊室中,警察與嫌疑人的對話不應該被看成是孤立的、自成一體的單個事件,而是整個刑事司法過程的一個環節。作為收集犯罪事實信息的第一步,審訊室的訊問對話將成為刑事證據。在刑事司法過程中,根據信息使用者(如審訊員、檢察官、律師、法官等)的不同,訊問語料被轉寫為多種形式,具備多種功能,因此訊問語料在司法過程中至關重要。
一、訊問語料轉寫的過程
由于人們對口頭語篇產生的基本原則、口語和書面語的區別、以及語境和受眾對互動的影響等缺乏理解,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在整個刑事司法過程中,審訊室中的互動和審訊材料的最終處理都會被(無意地)“歪曲”和“誤讀”。
與物證保存的嚴格規范截然不同的是,從審訊室到法庭的過程中,訊問語料的形式發生了顯著變化,具體體現在:原始的口語互動被錄制成音頻,音頻內容隨后被轉寫成筆錄,法庭審判是筆錄被口頭宣讀出來。審訊室中的談話是原始語料,這些語料以音頻形式保存在錄音帶上。即使是在這個初始階段,審訊語料已經發生了改變,因為聽錄音與在現場親歷審訊是不一樣的,我們會缺失所有的語境信息和提示。另外,錄音的質量往往也是不盡如人意。
然后,錄音被轉寫為詢問筆錄,也就是說,錄音被轉寫成了書面語。這是訊問語料發生最重大變化的階段。但是目前在司法系統中尚且沒有承認該過程會造成訊問語料的形式轉換。相反,從這階段開始,錄音直接被筆錄內容所取代。這些語料被當作控告證據呈上法庭。通常情況下,在法庭上警方目擊證人和公訴人往往是朗讀筆錄內容而不是播放原始的審訊錄音帶。更重要的是法庭審理程序中審理筆記的制作。在本案例的法庭審理過程中,警察筆錄被當堂宣讀出來,之后又被法庭書記員轉寫成另一種版本。書記員的記錄依賴于自己當庭聽到的內容,而不是警方的筆錄,由此,訊問內容又產生了進一步變化。
二、訊問語料轉寫中存在的問題
訊問語料的轉寫整個過程本身就是有問題的。首先,人們很難判定錄音的質量和精確性;其次,怎樣用書面語來轉述口頭用語,本身就是個問題;再者,由于很少有錄音帶的內容被全部轉寫為書面語,那么就存在著筆錄文字的編輯取舍問題;最后,法庭上,筆錄又被轉換為口頭用語,而這時的口頭語言與審訊室的原始對話又有了出入。另外,在錄音形式下,訊問會話的內容和意義(尤其是一些問題特征,如指示詞)會有一定程度的流失。
錄音謄寫員本身也是一個重要因素。英國警方在這方面沒有一個標準性的全國通用模式,語料的轉寫完全是掌握在謄寫員個人手里。一般而言,錄音的轉寫往往就是由審訊警員來完成,他們對筆錄內容的影響之大本身就值得考慮,警局很少會聘用平民謄寫員來完成這項工作。
(一)錄音的清晰度問題
訊問經過的錄音必須是公開的(而不是暗中監視錄像),這意味著錄音質量應該不存在質量問題。訊問環境一般是安靜的受控環境,錄音設備顯眼地擺放在對話雙方之間,雙方都清楚對話會被錄音,他們的表達必須清楚、大聲。但是這些問題還是會出現,有時錄音的一些部分完全聽不到,或者不清晰。然而,即使是質量再好的錄音,也無法被“完美”的轉寫。Frazer(2003)羅列了幾個人類言語和言語感知影響我們轉寫語料的方面。她認為轉寫語料的固有難點在與“怎樣判斷感知的準確性,怎樣質疑,以及在感知不準確時注意糾正……這些都是準確轉寫的必要步驟。可是問題是,錄音轉寫不同于我們平常的交流場景,這里沒有有意義的場景,說話人也不在現場,不能糾正語誤。我們從真實語境中被抽離了出來。”(2003:216)她還警示說即使是較高質量的錄音,“也只是‘足夠’準確,而不是百分之百的準確”。
錄音中會有數不清的值得質疑的地方,但是只有極少數警員在謄寫筆錄時會表明“聽不清”或“不清晰”。謄寫員面對這些不確定因素時往往會憑直覺猜測。正如Frazer(2003)所言,我們可能不會認識到,我們的聽力感知不是那么準確,尤其是當我們期望聽到某種信息時。Frazer將這種現象叫做“感知者未被承認的角色”,這種角色就是“我們將語言信號與我們頭腦中的已有知識相結合,對聽到的信息進行構建時扮演的角色”。
Coulthard和Johnson(2007)曾描述了這樣一個例子。一個謀殺案的嫌疑人帶有濃重的西印度口音,在他的審訊錄音文字稿中,謄寫員記下了這樣的字眼“got on a train”,然后“shot a man to kill”;而事實上他說的是“showed a man ticket”(145)。
因此即使在一些沒有爭議的錄音中,謄寫員將他們自己的理解加入到了對原始材料的解讀。隨著錄音質量的下降,這種主觀解讀的份量就越大。問題是,那些最終閱讀轉寫筆錄的人對這種“篡改證據”毫無所知,除非他們親自聽取錄音原件,但事實上筆錄一旦制作完成,很少有人再去聽取錄音。這時候,“口供污染”就發生了。
(二)轉寫:從口頭語到書面語
除了錄音的清晰度等原因,口頭語轉寫為書面語的過程本身問題重重。Gibbons認為,“根本的問題是言語和書寫是兩種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特性”(2003,28)。Walker本身就是一名法庭書記員,她基于自身經驗,認為轉寫過程中“書面語區別于言語之處,最重要的就在于書面語無法體現出說話人表達自己意思的那些副語言和非語言信號”。她提出,副語言因素包括“語調、氣息、強調處、音高、拉長的語調等”,非語言因素包括“眉頭高聳、雙臂張開、點頭,冷笑和微笑等”,這些因素本身可以傳達他們的意思,或者改變隨之說出的話的意思。她還指出,“書面語是單維度的,話語里富含意義的這些語境要素無法通過拼寫表達出來……因此有時某個至關重要的交流要素在書面語中無法體現出來。”
警察訊問語境下的謄寫員與法庭書記員不同,他們在審訊時并不在場,因此非語言因素表達的意思在轉寫時已經丟失。而副語言因素完全取決于謄寫員的描述,這種情況也是極少。正如Gibbons所言,在書面語中將這些特征進行視覺重現會令會使人很難讀懂筆錄內容。他認為這是“轉寫中無法調和的相互矛盾的兩個標準,”即“可讀性”和“準確性”標準。他肯定了“在同一個版本中同時滿足這兩大標準是不可能的。
Gibbons和Walker還發現了另一個問題,即人們傾向于在書面語中“修正”口語的一些特征。這些特征包括“錯誤的話語開頭”、“修正”、“反復”、“重疊”、“打斷”等,盡管這些特征在口語中非常普遍牡丹石在書面轉寫中往往都會被忽略。類似的還有,口語中“不完整”的句子結構往往在轉寫時被補充“完整”了。這種行動雖然在增加筆錄的可讀性上起到了作用,但是事實上從語言學家的角度來說,這些特征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它們口語揭示出很多與說話人有關的重要信息。即使是從非專業的角度來看,折疊特征揭示了說話人的某些性格特征。比如,一個總是插話想要說服別人的人,和一個說話很平靜很猶豫的人,給我們的印象是完全不同的。當然我們的印象也可能是完全錯誤的。但是,旁觀者至少應該能夠基于會話雙方的實際行為來做出自己的判斷。經過書記員的編輯藝術修改后——語法錯誤得以改正,錯誤的話語開頭被去除,句法被重新整理,這樣的筆錄毫無疑問比逐字逐句的記錄更具有可讀性。當然在大部分情況下,以上描述的這種修改對審訊結果不會產生太大影響。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就應該輕易地認同這種對原始材料的修改,使之成為在法庭上對被告不利的證據。
(三)文字編輯:錄音帶的記錄
絕大部分訊問都會經歷大規模的編輯加工過程。一般來說,訊問筆錄跟訊問總結差不多,只是全面轉寫了訊問的一部分內容。只有一些非常重大的案件才會對整個訊問過程的錄音進行轉寫。這對原始的訊問語料又是一次及其重大的改變,尤其是整個被重新編輯后的版本會成為呈堂證供。但是這個編輯過程完全被委托給了謄寫員,謄寫員必須利用自己的判斷力來決定哪些內容是相關或重要的內容。事實上在英國,這么重要的任務完全托付給了未受過培訓的業余警局雇員,這是錄音語料轉換成文字語料時人員產生偏差的原因之一。
(四)呈上法庭:書面語——口頭語
嚴格來說,呈上法庭的訊問語料是真正的證據,這個證據應該是訊問錄音帶,而不是訊問筆錄。但是,筆錄往往被當成了原始證據的“副本”。事實上在具體操作時在法庭上很少會播放原始審訊的錄音帶,而人們往往選擇通過筆錄來了解審訊室的情況。而且,在法庭上我們不是呈上筆錄文本,而是當堂口頭宣讀其內容。換而言之,警方證人扮演訊問警員,當堂大聲念出筆錄內容,更有甚者,檢察官往往扮演的是被告的角色,宣讀被告人的供詞。這樣一來,法庭審訊的各方可以根據自己的期望去解讀訊問材料,比如著重強調、放緩語速、改變語調等等。毫無疑問,這會極大地改變說話人原有的意思和目的。副語言和語言外的這些特征在轉寫階段已經被去除,而現在又重新回歸到訊問材料中,只是此時已經不再是當初說話人要表現的那些特征了,而是檢察官和警方證人(也許還不是訊問時的警察)要表達的特征。即使說話人是懷有善意的,以起訴人的身份發言,對這些語料的操作利用(如確定某項罪名)仍然不可避免。
但是,在法庭看來,不同媒介使用的是同樣的字眼,因此其代表的信息也應該是相同的。在接下來的陳詞中,法官和陪審團都會看到這些問話的文稿。這一點被看作是確保訊問證據的一種形式,因為他們能看到“訊問話語的實際字眼”,并且對這些字詞的正確音調和寓意做出自己的理解。但是,我認為,任何對文本的后續閱讀都深受其親耳聽過的版本的影響(將正式的筆錄當成是訊問原話,這本身就是問題重重的。)
三、總結
從以上分析我們發現,訊問語料從最初的口頭語言被逐步轉化成呈堂證據,期間經歷了一系列格式的轉換。訊問階段,語料以口頭對話形式出現,在個案評估階段,主要以警方的筆錄為依據,偶爾會參考訊問錄音;在庭審、判決和宣判階段,主要依據的都是法庭上宣讀的詢問筆錄,偶爾會參考警方的筆錄文件。在日常的實踐中,人們很容易地認為這種轉變不會造成司法公正的干擾。但是研究者認為,所有證據都必須盡量保持其原始性,至少,目前這一原則在哈羅德·希普曼案件的審判中沒有得到實現。
[1]Coulthard,M.and Johnson,A.(2007).An Introduction to Forensic Linguistics:Language in Evidence.Abingdon:Routledge.
[2]Fraser,H.(2003).Issues in transcription:factors affecting the reliability of transcripts as evidence in legal cases‘.Forensic Linguistics 10(2):203-26.
[3]Gibbons,J.(2003).Forensic Linguistics: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in the justice system.Oxford:Blackwell.
2016年湖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語用學視角的警察訊問話語分析研究”的中期成果(項目號:16Y145)。
D926
A
2095-4379-(2016)25-0032-03
楊淑芳(1981-),女,漢族,湖南益陽人,碩士,研究生,湖北警官學院,講師,研究方向:英語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