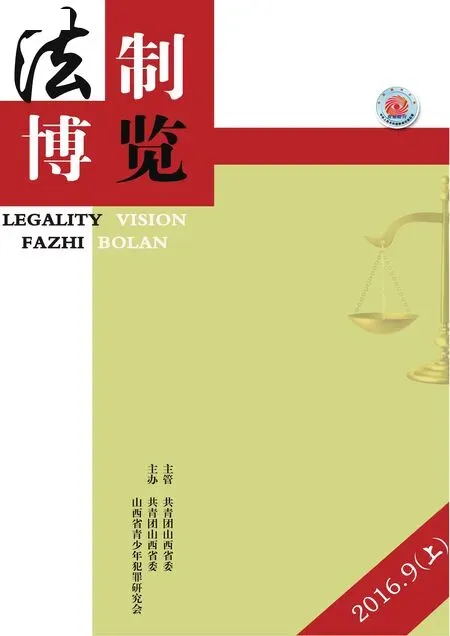立法語言規范化運用的再探討
——以《刑法》為例
楊曉紅
棗莊學院文學院,山東 棗莊 277160
?
立法語言規范化運用的再探討
——以《刑法》為例
楊曉紅
棗莊學院文學院,山東棗莊277160
在現行的法律法規中,存在著立法語言運用不規范的現象。本文以《刑法》為例,分析了其中存在的幾種語言運用不規范的現象,并由此指出了立法語言規范化的重要性及其實現的途徑,特別強調了各方參與和支持的必要性。
立法;語言;規范化;《刑法》
對于法律語言這個概念,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完全被公眾所接受的定義。宋北平在《中國法律語言規范化研究》一文中認為,法律語言是表述法律意義的語言,它由書面的“語言”和口頭的“言語”組成,包括立法、司法、執法等法律行業或職業中所使用的語言。①
人們經常談到法律語言的特點是什么,是模糊性、準確性抑或嚴謹性?②法律語言研究者為此而爭論不休。其實,不論是模糊性、準確性還是嚴謹性,它們都要建立在法律語言規范化的基礎之上。舍棄法律語言的規范化,其他的一切則無從談起。
郭龍生在《淺談法律語言的規范化》一文中認為,所謂法律語言規范化,就是使法律語言應用的行為、過程與結果等都符合其應有的規范標準要求的過程。③也就是說,立法者、法官、檢察官及律師、法學研究者等法律工作者,在法律運用和法律闡述領域中,為了使法律得到更充分的運用,對法律語言,包括語音、詞匯、語法、語用等各方面進行加工,使之更加規范化,表達更加完善、準確,從而有效地發揮法律的效力。
下面本文就以《刑法》④為主要討論對象,結合其他法律及語言理論知識,選取幾個角度,來探討一下立法語言規范化運用的問題。
一、關于詞語的理解與運用
法律語言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它的準確性。在一部法律里,處在那個特定的語言環境下,其詞語的含義必須確定,不允許詞義含糊不清或模棱兩可,更不允許自相矛盾。對某些詞語的含義,不能使人產生似是而非的感覺,而應該給人一個清晰的概念。例如:
《刑法》第十七條:“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④
這里出現了“投毒罪”這一概念。
《刑法》第二編分則的“危害公共安全罪”第一百一十四條:【放火罪、決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險物質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一】放火、決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或者以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④
第一百一十五條:【放火罪、決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險物質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二】放火、決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或者以其他危險方法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④
這兩條中都出現了“投放危險物質罪”這一罪名。
從以上的法律條文中可以看出,投毒應是投放毒害性物質,而投放危險物質應該是投放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這看起來好像很清楚了,但實際上其中是存在疑問的。前面提到的“投毒罪”中的“投毒”是否就是后面所說的“投放毒害性物質”?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畢竟對人體也是有毒害性的,如果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投放的是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對他人造成了傷害,算不算投毒罪?是否應承擔法律責任?
哪些物質是毒害性物質?那些物質是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兩者之間是否有交叉的情況存在?法律中并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由此可以看出,“投毒罪”中的“投毒”與“投放危險物質罪”中“投放危險物質”還存在著界限模糊不清的問題,所包含的范圍似乎明確而又糾纏不清。兩者之間關系如何確定,對定罪量刑至關重要,立法者在這里似乎應給予一個明確的說明和界定。
二、關于語序問題
語序是現代漢語中重要的語法手段之一。不同的語序可以形成不同的結構關系和語法意義,句子的含義也會因語序的不同而產生一定程度的改變。同時,不同的語序中也存在著語言運用不規范的問題。例如:
《刑法》第八十五條:【緩刑的考驗及其積極后果】對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依法實行社區矯正,如果沒有本法第七十七條規定的情形,緩刑考驗期滿,原判的刑罰就不再執行,并公開予以宣告。④
《現代漢語詞典》(2002年增補本):“【公開】①不加隱蔽;面對大家(跟‘秘密’相對):-活動。②使為秘密的公開的:這件事暫時不能成為-。”從語法角度講,當“公開”一詞作形容詞時,它是直接跟在動詞的前面,作狀語,修飾限制動詞的。例如:
(一)趙樹理《小二黑結婚》:“小二黑也知道這事是合理合法的了,索性就跟小芹公開商量起來。”⑤
(二)沙汀《闖關》:“‘你要知道,我們是公開住的呢。’來客提醒著他。”⑥
當“公開”與“予以”結合使用時,一般用法為“予以公開××”。所以本句的說法應為“予以公開宣布”,很少有“公開予以宣告”的說法。
從語法角度看,本句存在著語序不當的問題,應予以糾正。
另外,從含義上講,“公開予以宣告”強調的是“公開”,重點在于強調宣布的形式,是采取面向大眾、大眾參與并使大眾知曉的形式。而“予以公開宣布”則側重于強調宣布的內容,指內容被公眾所知曉,與“秘密”相對。在這里,《刑法》第七十六條所表現出來的意思是強調宣布的內容被大眾所知曉,而不在于要采取何種形式,因此《刑法》第八十五條還是應以采用“予以公開宣布”的表述為佳。
三、關于標點符號
標點符號是書面語言的有機組成部分,是書面語言不可缺少的輔助工具。它幫助人們確切地表達思想感情和理解書面語言。每個標點符號都有一定的使用范圍,有其自身的規范性。標點符號是書面上的,它的使用同語句的結構和意思有密切的關系。
在《刑法》條文中,有標點符號使用不規范的現象。例如:
(一)第八十五條【假釋考驗及其積極后果】對假釋的犯罪分子,在假釋考驗期限內,對假釋的犯罪分子,如果沒有本法第八十六條規定的情形,假釋考驗期滿,就認為原判刑罰已經執行完畢,并公開予以宣告。④
本句應改為兩個句子,在“依法實行社區矯正”后應改為句號。因為開頭的三個分句表達的是一個意思:對假釋的犯罪分子對假釋的犯罪分子。而后三個分句是另一個意思:假設了一種情況及結果。
對比《刑法》第八十七條第四款,可知第八十五條是應該用句號的:
《刑法》第八十七條:(四)法定最高刑為無期徒刑、死刑的,經過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認為必須追訴的,須報請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④
句號表示陳述句末尾的停頓,文章中該用句號而不用,會使句子結構層次不清,表述不明。因此第八十五條的這個位置上應修改成句號。
(二)《刑法》第一百條【前科報告制度】第二款:犯罪的時候不滿十八周歲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人,免除前款規定的報告義務。④
《刑法》第一百條第二款中,應在“犯罪的時候不滿十八周歲”與“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人”之間加一個頓號。因為頓號主要用來表示句中較短的并列詞語之間的停頓。“犯罪的時候不滿十八周歲”與“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兩個短語是并列的兩個條件,共同修飾限制“人”這一中心語。且加上頓號后,使整個句子層次清晰,讀起來語氣也比較地舒緩。
四、關于行文體例
體例指著作的編寫格式或文章的組織形式。一篇文章,一部著作,甚或一份公文,都有一定的行文規范,有一定的編排體例。從廣義角度講,行文體例也應該是一種修辭方式。確定了一個明晰合理的行文體例,才能從宏觀上勾畫該文的結構,才能知道采用何種的語言表達形式。行文體例對于立法規范來說,就像鳥之雙翼、車之兩輪一樣不可或缺。
作為具有莊嚴性、權威性的法律,更應該是莊重、嚴謹的典范,更應當注意行文體例方面的規范性。但相比之下,中國的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時似乎對行文體例重視不夠,存在著行文體例不協調的現象,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刑法》也不例外。例如:
第二十條【正當防衛】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的,屬于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④
……
第二十一條【緊急避險】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發生的危險,不得已采取的緊急避險行為,造成損害的,不負刑事責任。④
……
正當防衛和緊急避險是刑法明文規定的兩種排除犯罪的事由,在行文上是一種并列的關系。第二十條在規定“正當防衛”時,實際上采取的是一種下定義的形式,就是“什么是正當防衛”。通過這種形式的規定,讓人們對采取的何種行為是正當防衛有了一個比較清晰的認識。而第二十一條在規定“緊急避險”時,卻沒有采取這種形式,而是直接提出了“緊急避險”這一概念,給人一種突兀的感覺,形成了一種行文體例上的不協調。
實際上,從一般人們的生活常識來說,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對正當防衛大多有所耳聞,多少有所了解,有一個基本的印象和認識。而相對于正當防衛,一般的人們對緊急避險則知之甚少,沒有多少的印象和了解。從這個角度講,第二十一條更應該同第二十條一樣,采用下定義的形式加以規定,使人們對緊急避險有一個相對明確的認識。
因此,對“緊急避險”這一排除犯罪的事由,采取與規定“正當防衛”一樣的形式,不僅是行文體例上的要求,也是增強人們對“緊急避險”這一概念認識和理解的要求。
以上選取了幾個方面,對《刑法》中存在的語言運用不規范現象進行了分析。這種語言運用的不規范現象,并不僅僅存在于《刑法》之中,在其他的的法律法規中也經常出現,特別是在一些地方立法的法律文件中表現尤為突出。
法律是用來規范人的行為的,它是通過語言來表述的,其本身首先要受到語言規范的制約,然后才能有效地規范他人的行為。法律語言的運用具有法律的后果,它牽涉到權利、義務、公平、正義等重大的社會問題。不能將法律語言的規范問題僅僅看做是一個簡單的技術性問題,更不能看做是一個單純的文字問題,它是一個重大而又嚴肅的理論問題。因為語言不規范的法律無法實現立法的宗旨。⑦
中國的法律語言同時也是社會方言的一種,是現代漢語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它首先應該是規范的現代漢語。立法語言的規范主要指書面的法律法規語言規范。立法語言莊重嚴肅,完善精確,在詞匯、語法及修辭的運用上有顯著的自身特點。立法語言的莊嚴權威性體現于內容和形式兩個方面,立法時應從這兩個方面加以嚴格規范。⑧
若要在中國真正實現法律語言運用的規范化,必須強化意識,認識到法律語言規范化的重要性,從源頭與本質上抓起。
從某種意義上說,法律就是語言,法學就是語言學。立法語言的規范化離不開法學與法律工作者、語言學者及立法、司法部門的大力合作與積極參與。
首先是專門從事法學研究的法學家。這些人具有相關的法學和法律知識,能夠使立法語言忠于立法原意,保證立法語言不會因規范化活動而脫離法律的軌道,從而實現立法的宗旨。
其次是法官、檢察官、律師等法律工作者。他們是法律的實踐者,能夠從實踐中積累法律語言運用的經驗。他們能以自己的切身感受和時間經驗,彌補法學家們實踐不足的缺陷,使立法語言更貼近于現實生活。
再次是語言學者。在立法語言規范化問題上,需要從事語言教學與研究的學者們的參與。他們在語言學方面的專業知識,可以彌補法學家和法律工作者語言知識方面的不足。通過他們的把關,能使立法語言更加規范化,符合語言運用的各種規則。
當然還需要立法、司法相關部門的組織、參與和支持,如人大、檢察院、法院和司法部門等。沒有他們的參與和實踐,立法語言的規范化只不過是一句空談,只是一種紙面上的語言游戲。
立法工作者、法律研究者與法官、律師等法律運用者,除應具備所必需的法律知識之外,還應主動學習一些語言規范的理論知識,這樣才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因立法語言的不規范而引起的對法律的誤解。加上邀請語言工作者的參與,法律的制定才會更加的規范與完善。
法律語言的規范化問題,從表面看,好像僅僅是一個簡單的糾正法律語言的語法毛病或者措辭不妥的問題,是個別的、局部的問題。但從法律實施與運用的本質上來說,絕不能將法律語言的規范化問題看成是一個可有可無的東西。法律語言的規范化體現了法治文明的發展歷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法律語言規范甚至比法律本身還要重要,因為語言不規范的法律法規無法實現立法的宗旨。
[注釋]
①宋北平.中國法律語言規范化研究[J].北京政法職業學院學報,2006(03).
②羅士俐.法律語言本質特征的批判性分析[J].北方法學,2011(04).
③郭龍生.淺談法律語言的規范化[J].法律語言學說,2009(02).
④本文中所引用的<刑法>條文均出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2015年修正).
⑤趙樹理.小二黑結婚[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09):232.
⑥沙汀.闖關[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8(10):63.
⑦廖美珍.中國法律語言規范化若干問題之我見[J].修辭學習,2008(05).
⑧趙艷平.關于法律語言規范化標準的思考[J].北京政法職業學院學報,2008(02).
[1]杜金榜.從目前的研究看法律語言學學科體系的構建[J].現代外語,2000(01).
[2]劉紅嬰著.法律語言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3]王業坤.淺談中國法律語言學研究的方法問題——以“法學和語用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為參照[J].研究生法學,2013(05).
[4]童珊.我國法律語言學研究現狀及發展趨勢[J].山東社會科學,2009(05).
[5]陳炯.論立法語言的風格特征[J].畢節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綜合版),2005(01).
[6]邢欣.國內法律語言學研究述評[J].語言文字應用,2004(04).
Legislative language use standardized Further Discussion
Yang Xiao-hong
The art college of zao zhuang university in shan dong;shan dong zao zhuang 277116
Under the existing laws and regulations,The existence of legislation does not regulate the use of language phenomena.In this paper,“Criminal Law”as an example,Analysis of the use of several languages in which the presence of non-standard phenomena,And thus points out the importance of legislative language standardized way of its realization,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need for all parties to participate in and support.
legislation;Language;Normalization;《Criminal law》
D90-055;D924
A
2095-4379-(2016)25-0055-03
楊曉紅(1970-),男,山東德州人,碩士,棗莊學院文學院,副教授,山東法揚律師事務所,實習律師,主要從事古代漢語及法律研究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