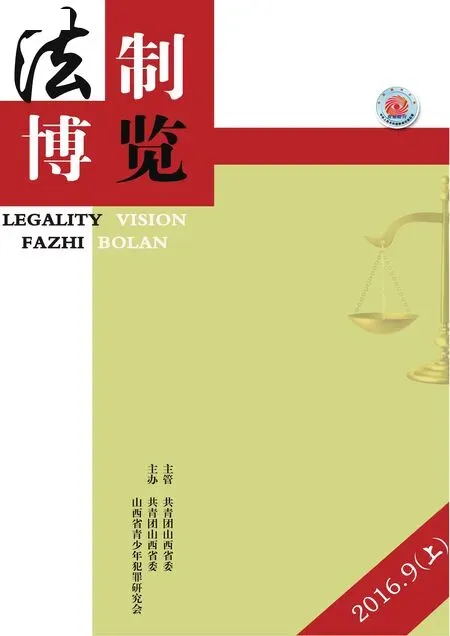刑事訴訟中程序性事實的證明責任與證明標準
龐愷曄
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上海 200042
?
刑事訴訟中程序性事實的證明責任與證明標準
龐愷曄
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上海200042
我國刑事訴訟法已確立起基本的司法證明機制,較為清楚的明確了訴訟參與各方的證明責任,同時司法裁判制度中對于程序性事實的裁判有其特殊的證明要求。證明責任與證明標準對于刑事訴訟的意義毋庸置疑,但在法律中仍有尚待規范與厘清的空間,鑒于我國并未確立專門的證明標準來解決程序性事實的證明問題,因此以現有的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為切入點來研究這一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刑事訴訟;程序性事實;非法證據排除;證明責任;證明標準
修改后的刑訴法及其司法解釋極為突出的一大亮點就是在證據及證明規則方面的修正與進步。新刑訴法解釋在應當運用證據證明的案件事實中加上了“有關管轄、回避、延期審理等的程序事實”,說明法律引入了程序性事實作為證明對象。
一、程序性事實的定位
在刑事法律事實中,依據調整和規范的來源,可將其分為程序性事實與實體性事實。對于程序性事實,我國法學界的通說為“法律效果說”,即凡是能推動、促進訴訟程序的進程,對偵查、起訴、審判、執行等訴訟程序的啟動、中止具有影響、具有法律意義的事實均為程序性事實。如有學者認為發動、終止、變更或者消滅一定訴訟程序的客觀事實稱為程序事實,程序事實并不與實體法利益直接關聯,但對訴訟的方向以及當事人訴訟權利的保障或消除具有引導和推定作用。[1]也有學者認為程序事實是指對訴訟程序解決有法律意義的事實,它是由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能夠引起訴訟程序相應法律后果的事實。[2]有的學者則以列舉的方式說明需要運用證據進行證明的案件程序事實:(一)關于管轄的事實;(二)關于回避的事實;(三)耽誤訴訟期限是否有不能抗拒的原因或者其他正當理由的事實;(四)影響采取強制措施的程序事實;(五)違反法定程序的事實;(六)影響執行的程序事實;(七)其他應當證明的程序事實。[3]
根據上述內容,可歸納出程序性事實的一些特性:
(一)程序性事實會對訴訟進程產生重要影響
與實體事實相對,程序性事實是由規范程序運行的法律、法規調整所形成的事實。它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對訴訟進程的影響上,有時是局部性的,如申請回避、延期審理、重新鑒定等;有時則是終局性的,如刑訴法第十五條中規定不予追究的六種情形,或由于出現法定的程序違法事實導致訴訟行為無效,由此可見程序性事實會對訴訟進程產生重要影響。
(二)程序性事實帶有權利和權力的性質
一方面,程序性事實體現當事人的訴求,保障其合法權利。針對社會上頻頻曝光的冤假錯案,為維護國家的司法公信力,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成為了此次修改的重頭戲。另外諸如回避、管轄、重新鑒定等由法律授權當事人提出的程序性事實都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當事人訴求的實現途徑,在程序上實現當事人與國家公權力的“同等力量武裝”。
另外一方面,以法院為代表的公權力對當事人提出的程序性爭議進行裁定,完成程序性裁判,引導訴訟程序的順利行進。由于國家公權力天生的強制性和暴力性,為實現公平正義,司法機關必須依法保障當事人的平等對抗權。刑事訴訟法保障憲法和法律賦予個人最基本的權利和自由,包括實體性權利,如生命權、健康權、人身自由權,以及程序性權利,即憲法和法律賦予個人用以保護實體性權利、對抗政府非法或無理侵權的基本訴訟手段[4]
(三)程序性事實與程序性裁判密切相關
程序性裁判程序主要解決程序上的爭議問題,這一裁判的結果雖然不涉及被告的刑事責任問題,但對刑事訴訟的進程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程序性裁判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程序性裁判,泛指一切旨在解決程序性爭議的司法裁判活動[5],主要包括圍繞回避、管轄、重新鑒定、補充鑒定或延期審理等問題所發生的程序性爭議。而狹義的程序性裁判,專指法院針對偵查機關、公訴機關或者下級法院的程序性違法行為,為確定是否實施程序性制裁所進行的司法裁判活動。[6]我國迄今為止一共確立了兩種典型的程序性制裁制度:一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二是針對原審程序違法的撤銷原判、發回重審制度。在非法證據排除制度當中,核心是解決證據是否為違法取得的問題,這就要求對所謂“非法證據”確立一定的證明責任和證明標準。
二、非法證據排除中的證明責任
證明責任是證明制度的核心,證明責任是指當事人為了避免不利于己的裁判而提供證據證明自己的訴訟主張,并且說服事實裁判者確信其主張為真實的一種責任。[7]在同一件案件中,訴訟當事人可能存在不同的爭議事實,證明責任分配由此應運而生,決定案件中某一具體待證事實證明責任的承擔主體問題。正如前文所述,我國公訴案件是國家公權力對個人的追訴,雙方的力量帶有先天的不平等性,因此根據“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公訴案件中由人民檢察院承擔證明被告有罪的舉證責任,但被告也要為自己的一些主張提供證據。
迄今為止,我國刑訴法中唯一的證明責任倒置情形就是非法證據排除程序。在這一程序中,被告在提供自己被以非法方式獲取證據的依據之后,檢察機關必須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承擔證明責任和不利后果。也即提出積極訴訟的一方反而不需要承擔證明責任,這也是探討非法證據排除的證明責任的意義所在。
新刑訴法對非法證據排除設置了三種不同的規則,即分別針對非法言詞證據的強制性排除規則、針對非法實物證據的裁量性排除規則和針對瑕疵證據的補正規則。在這一背景下,公訴方針對這三種情形來證明證據取得合法性的證明責任是有所區別的,因此必須分情況討論。
(一)強制性排除規則的證明責任
在調查程序正式啟動以后,公訴方需要從兩個方面對言詞證據承擔證明責任:一是要證明偵查人員不存在被告方所說的“刑訊逼供”、“暴力”、“威脅”等非法取證的情形;二是要證明偵查人員所獲得的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都是通過合法的方式取得的。這一證明責任較為單一,也不會轉移到被告人身上。被告人雖然可以提供證據來證明偵查人員確實存在非法取得證據的行為,但并不意味著被告人需承擔證明責任。同時,只要公訴方無法從根本上排除非法取得證據的可能性,法院都必須作出排除非法證據的決定,由公訴方來承擔“舉證不能”的敗訴風險。
(二)裁量性排除規則中的證明責任
這一排除規則針對的主要是偵查人員非法獲取的書、物證等實物證據,法院對此享有自由裁量權。針對這一規則,公訴方在證明證據取得合法性上,首先要對偵查人員收集實物證據的合法性進行調查,如果法院認為公訴方無法證明實物證據取證合法,就進入下一個環節,反之,如果法院認為公訴方對實物證據取得的合法性的證明已經到了法定的最高標準就不會做出排除實物證據的決定。
在程序的第二步,被告人需要證明偵查人員的非法取證行為已達到足以“可能影響司法公正”的程度,如獲取的實物證據是不真實、不可信的甚至可能造成冤假錯案等等。
最后,如果被告方能夠證明取證的非法行為確實可能造成影響司法公正的后果,證明責任再次回到公訴方身上。公訴方則需要對取證行為進行必要的程序性補正:一是進行單純的程序性補正,如要求偵查人員重新或補充制作證據筆錄;二是進行合理的解釋或說明。因此如果偵查人員的非法取證行為所造成的危害后果是“可以治愈”的,并不存在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風險時,法院不會作出排除證據的決定。反之,如果公訴方沒有進行必要的補救措施,法院就不會將該證據作為確定案件事實的依據。
(三)瑕疵證據補正規則中的證明責任
對于偵查人員通過帶有程序瑕疵的方式獲得的證據,法律確立了可補正的排除規則。這種有瑕疵的程序并沒有侵害重大利益,也沒有造成嚴重后果。與前兩種規則相類似,此時仍然由公訴方來證明偵查行為的合法性,同時公訴方還是需要對該瑕疵證據進行補正,以證明偵查人員的程序性瑕疵并沒有造成嚴重后果,或者已消除了消極后果,否則法院依然可以將該證據排除。
三、非法證據排除中的證明標準
證明標準與證明責任密切相關,證明標準是指承擔證明責任的訴訟一方對待證事實的論證所達到的真實程度。[8]新刑事訴訟法確定了“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并且引入了“排除合理懷疑”的概念。雖然法律并未明確規定在非法證據排除程序中公訴方與被告人各自的證明標準,但也可根據程序性裁判的性質以及程序性證明的要求作出推斷。
(一)公訴方的證明標準
按照新刑訴法的內容,法院確認或不能排除偵查人員存在以非法方式獲取證據的情況的,應該對相關證據予以排除,所謂的“不能排除”是指公訴方對于取證行為合法性的證明沒有得到法官的內心確認,由此可見此時的證明標準應該要達到與定罪標準相同的最高證明標準。同樣的,在裁量性排除與瑕疵證據的補正程序中也需要將證據的補正證明到排除合理懷疑的地步。
一方面,將公訴方的證明標準定為最高證明標準有其現實意義。公訴方進行取證行為合法性證明的證據屬于指控被告人犯罪事實的所有證據的一部分,同時由于無罪推定的存在,公訴方有義務來證明這些證據全部屬實,因此只有包含需證明取證合法性的證據在內的所有證據都達到了最高的證明標準,公訴方才能夠推翻無罪推定,說服法院作出被告人有罪的判定,從而提高司法的公信力。
另一方面,將公訴方的證明標準定為最高證明標準具有現實的可行性。公訴方手中的力量和資源豐富,可以獲得偵查人員的幫助,獲取其在偵查行為中制作的各自筆錄證據。對于一些自偵案件,公訴方還掌握著全程同步錄音錄像的資料,也可以去監獄向看守人員調查情況等等。即使窮盡了上述的調查手段,公訴方還可以傳召偵查人員出庭提供證言,這一切都為
公訴方證明取證行為合法性提供了便利。
(二)被告人的證明標準
在非法證據排除程序中,由于自身條件的限制以及無罪推定的存在,被告人承擔的是次要的證明責任,主要體現在初步審查與裁量性排除程序之中。
在初步審查程序中,被告人提出的對取證行為合法性的質疑只要達到令裁判者產生疑問的程度就可以了,這一標準大體相當于說服裁判者產生合理懷疑的程度[9]。在這種情況下,假如只是通過閱卷與庭前會議中的聽取意見仍不足以排除這些合理疑問,被告人的初步證明就已完成。
在裁量性排除程序中,如果法院認為偵查人員收集實物證據的行為違法,則要求被告人承擔這一行為達到了“可能影響司法公正”的地步的證明責任。對這一證明內容,被告只要到優勢證據的程度就可以了,沒有必要達到最高的證明標準。優勢證據是指承擔證明責任的一方對于某一事實成立的可能性,證明到超過該事實不成立的可能性的程度。[10]也即被告方只要證明該取證行為影響司法公正的可能性高于不影響的可能性即可。
以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完善為借鑒和契機,明確其中當事人(包括司法機關)的各種證明責任,推斷其證明標準,在司法實踐中加以合理運用,同時為其他程序性事實及程序性裁判的合理規制提供經驗,使得刑事訴訟程序更為流暢,從而節約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
[1]陳浩然.證據學原理[M].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2002:385.
[2]黃河,付延威等.刑事抗訴的理論與實務[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0:169-170.
[3]陳光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證據法專家擬制稿:條文、釋義與論證[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
[4]徐靜村.刑事訴訟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58.
[5]陳瑞華.刑事證據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360.
[6]陳瑞華.刑事證據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360.
[7]樊崇義,蘭躍軍,潘少華.刑事證據制度的發展與適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70.
[8]陳瑞華.刑事證據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295.
[9]陳瑞華.刑事證據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375.
[10]陳瑞華.刑事證據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376.
D925.2
A
2095-4379-(2016)25-0065-03
龐愷曄(1992-),女,浙江臺州人,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2014級訴訟法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事訴訟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