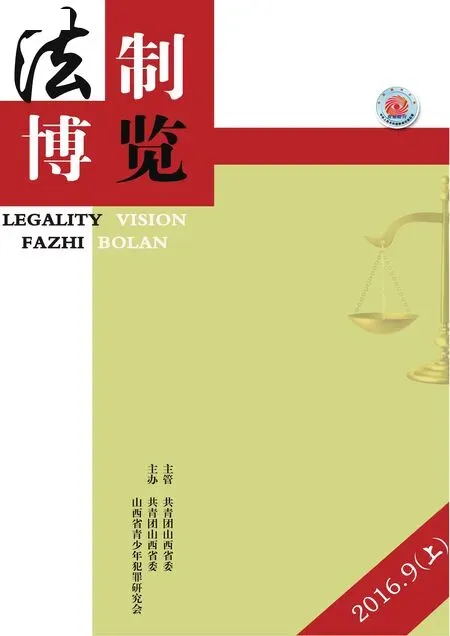道德與法律
何曉雯
北京理工大學,北京 100081
?
道德與法律
何曉雯
北京理工大學,北京100081
道德與法律作為兩種評價標準,既對立又統一。在通常情況下,法律作為道德的底線,將一些道德標準制度化,通過國家強制力保證實現。在實踐中,道德不僅在立法活動中對法律的形成產生作用,近年來還尤其顯著的對司法審判活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在司法審判活動中,道德評價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卻應該以更加審慎的態度進行考量。
道德;法律;社會危害性;罪刑法定;審判活動
在司法審判活動中,我們趨向于強調絕對的程序正義,以求在這一正義的程序之下獲得一個能夠被普遍接受的結果。但由于法律本身的特征,規則的使用在某些場合仍然是無能為力的,故而司法自由裁量的存在也是必然的。道德作為一種社會普遍通行的價值評判標準,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司法自由裁量的結果。尤其在對一個行為的社會危害性進行判斷時,無論是審判者、原告、被告或者普通大眾,都不可避免的會帶有道德評判的色彩。
以刑法為視角來看。刑罰具有嚴厲性的特征,刑罰可以剝奪犯罪分子的財產,剝奪犯罪分子的政治權利,限制或剝奪犯罪分子的人身自由,甚至可以剝奪犯罪分子的生命。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刑罰是通過一種“以暴制暴”的手段對犯罪行為進行懲罰。所以在實踐中,我們必須對刑罰進行嚴格控制,以免這一嚴厲制裁手段的濫用。
于是,刑法設置了罪刑法定這一基本原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條,要求“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這一原則,簡而言之就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即在司法審判活動中,必須嚴格依法行事。甚至在某一社會階段,一些政治家曾較為理想化地主張:通過演繹的方法準確地規定所有事物,讓法官和律師除了查明事實,并將事實邏輯地套進預先制定的法條構造外,再也無事可做。
但實際上,在司法審判活動中,尤其在量刑階段,由于法律自身的缺陷和客觀情況的復雜性等原因,我們又不得不賦予審判者以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參照刑法第四章第一節量刑部分的內容進行分析,如第二十六條規定“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規定的從重處罰、從輕處罰情節的,應當在法定刑的限度以內判處刑罰”。對于此處提及的“從重處罰、從輕處罰的情節”,就可見立法留給審判者的自由裁量空間。但怎樣的情節需要從重或從輕處罰?從重和從輕的程度如何把握?等,都是需要進行仔細分析的問題。
如刑法明文規定,“對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這是法定的從輕情節,相對易于認定。但某些案件中的情節,卻沒有明文的規定,需要審判者憑借自身的專業水準和職業要求進行判斷。
如昔日戀人中的男方甲不愿意維系戀愛關系,女方乙為此攜帶毒藥去男方住處,聲稱如果甲與其斷交,就在甲處自殺。甲不為其所動,乙見恢復無望于是自殺并身亡。甲是否構成不作為犯罪?在此先排除其他的構成要件不考慮,光就甲是否應對乙的死亡負刑法上的責任進行分析。根據刑法,甲并不需要對乙的自殺行為負責,因為甲并沒有刑法上的相應義務。但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往往會覺得,他們是戀人,而且乙已經以性命相逼,甲為何如此絕情!如若分手是因為甲的過錯,那更是必定會受到來自社會的輿論壓力和道德譴責。在這一情形下,審判者應該如何決斷呢?是遵從法律的規定,依法判決,還是聽從社會的呼聲,法中容情?
對此,筆者認為,由于法律調整對象自身的特性,在法律適用過程中的確給道德判斷留下了一定的空間。法律具有抽象性,而實踐中的個案卻具有多樣性和復雜性,法律的適用并不是機械的針對一系列抽象的事實,而需要根據每個案子的具體情勢進行有針對性的適用。這里,就不得不調到法律適用過程中的自由裁量權。而道德的標準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審判者的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因為道德標準是與一個人的生活和思想密切相關的評價準則,它植根于人的腦海深處,人會不自覺受其影響從而形成自己的判斷和價值取向。但是作為一個審判者,是否能用通常我們所說的道德標準來評判一個行為的罪與非罪、重罪與輕罪呢?可見,雖然法律適用過程的確給個人的道德判斷留出了許多空間,但在適用司法自由裁量領域,其需要受到嚴格限制。
為避免這一權利的濫用,其設置必須有一定的前提,其中之一就是要求審判者必須具備相應的專業素養,并擁有正確感和公正感。對于一個判決的作出,審判者首先要做到的是嚴格依照相關的法律規定,其次,在自由裁量的領域,審判者必須做到嚴格遵從自己專業的判斷和職業的要求。這就一方面要求審判者提高自己的專業素養,形成自身完善的專業體系,以支撐實踐分析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要求審判者具有很高職業道德,形成嚴格的職業標準,以確保實踐公正的需要。當一個判決是審判者基于完善的專業知識和嚴格的職業的標準作出時,它才具備公平正義的出身,才能說服判決的做出者和結論的承受者。
此外,在道德和刑法重復的部分,刑法只確認道德的底線。因為從主旨上考量,道德涉及人的思想和情感,而法律只涉及人的行為;道德的目標是完善人的個體品德,而法律知識嘗試去調整個人和個人之間、個人和國家之間的關系。如果在審判活動中,我們盲目的以嚴格的道德標準來評價人的思想和行為,是不必要更是過于嚴苛的。近年來,很多案件的判決中,審判者似乎太容易受到社會輿論的影響,更注重考量違法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有時甚至超出了罪刑法定的許可的范圍。
舉個例子,辯護律師在辯護中提出:強奸陪酒女比強奸良家婦女危害性要小。在此,我們單純關注這句話含有的對于強奸陪酒女與強奸良家婦女的社會危害性的大小的評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個原則性的規定,筆者認為辯護律師這種觀點的錯誤在于他把受害人的身份作為衡量危害性大小的依據,而刑法當中的社會危害性主要決定的是定罪而非量刑。試問,同樣是作為受害者,同樣受到了犯罪分子的暴力或脅迫,同樣是違背自身的意愿被強行與他人發生性關系,人身權利同樣受到了損害……為何強奸良家婦女和強奸陪酒女等的社會危害性的輕重需要進行比較呢?如果僅僅以為受害人的身份、地位因素,就判定她們遭受傷害的程度不同、對社會的危害性程度不同,就會產生非常荒謬的邏輯,以致誤導人們,違反司法公正。這種辯護觀點雖然只代表個人立場,但其實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會上的某些群體的觀點,即用道德去評價行為來進行定罪量刑。
在定罪量刑中并非不能加入道德因素的考量,但卻應該嚴格控制道德標準的作用范圍和影響程度。通過研究立法活動我們可以看出,道德的標準往往是高于法律的,而刑法則是作為最后的、最嚴厲的手段彌補其他機制無法調整的社會關系,從而保證社會最基本的運行活動。正如15世紀的法律人在《年鑒》(Year Books)中所說的那樣,有些事物適合國家法律管轄,有些事物適合大法官管轄,有些事物則宜交予個人和聽他懺悔的牧師。
故,道德和法律不能完全分離,在法制的進程中他們彼此也會不斷的進行相互作用,互相彌補、互相制約。但道德在某些層面上對法律施加的影響卻是需要謹慎吸收,甚至嚴格排斥的。道德可以規范人的思想和日常生活,使個人和社會更加善意,從而有助于法律的實施,但道德卻不能凌駕于法律之上,指揮法律的判斷。
[1][美]羅斯科·龐德.法律與道德[M].陳林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2]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B82-05
A
2095-4379-(2016)25-0171-02
何曉雯(1990-),女,哈尼族,云南人,北京理工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環境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