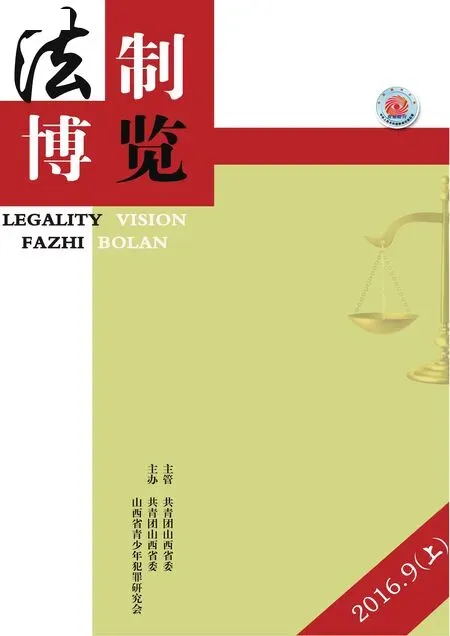我國刑訊逼供現狀及問題研究
楊尚林 林 翠
西北政法大學公安學院,陜西 西安 710122
?
我國刑訊逼供現狀及問題研究
楊尚林林翠
西北政法大學公安學院,陜西西安710122
刑事冤假錯案頻發不僅違背了刑事訴訟打擊犯罪和保障人權、實現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基本價值理念,而且也給案件當事人帶來了無法彌補的傷害。同時也引發了社會各界對司法公正的的質疑和擔憂,極大地動搖了社會公眾對法律的信仰和法治信念,也與全面依法治國方針相抵觸,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在司法實踐中,刑訊界定都尚不明確,相關法律規定并不完善。基于此,本文以刑訊逼供歷史遺留問題為對象,結合當前依法治國的新形勢對該問題進行研究。
人權保障;刑訊逼供;口供
隨著近年呼格吉勒圖案的甚囂塵上,案件本身的細節也引起了越多人的關注,然而近年來聶斌案、杜培武案、佘祥林案等刑事冤案陸續浮出水面,人們注意到案件的背后往往都涉及到刑訊逼供行為,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講,刑訊逼供既已存在且屢禁不止,那么它背后就必然有其生存的土壤和發展的條件來支撐其發展蔓延;那么在當前依法治國大背景下,這些案件的案情看起來都與法治大環境不契合,有損國家司法公信和權威,顯得格格不入,鑒于中西方社會情況不一,還是要走中國特色的法治道路來預防刑訊逼供。
一、我國刑訊逼供研究現狀
縱觀當前理論研究,仍然以“現象、成因、對策研究”的傳統邏輯思維來看待刑訊逼供,以尋求解決方案顯然已無法滿足現實需要,從深層需求來看,刑訊逼供的產生是以口供的獲取為終極目的,因此,在一些疑難案件中,口供是取得案件突破的唯一途徑,也是深挖犯罪、破獲積案的有力輔助。在實踐當中,多次作案的慣犯,既是犯罪案件當事人,又是違法犯罪情報的知情人,所以對于這一部分人,既是一個單獨的案件犯罪嫌疑人,又是一個數據龐大的信息庫;對于偵查人員而言,就是如何快速高效的獲取足夠多的信息,取得意外的“收獲”;此外,口供還能對于案件的其他性質予以輔助,如警方在掌握一定量的證據情況下,尚不足以摸清整個事情的脈絡,口供也就自然而然成為了串聯案情,證明執法者自身判斷的工具;而且,在一些特定案件當中,口供本身也是唯一證據,若沒有其他證據支撐,口供就顯得格外重要。
基于口供的特殊地位,也就造成了世界范圍內對口供狂熱追求的通病,一般案件偵破需要的證據雖然主要有人證、物證、證人證言、當事人陳述等,那么這個時候口供的重要性就主要從其他證據的質量上體現。
二、西方國家刑訊逼供問題探索
在西方發達國家,國家配置大量資源給警務工作,另外在社會有效控制層面,通過閉路電視、豐富完善的人口基本信息數據庫、以及金融管控等現代科技建立起的電子防控體系,可以輕易掌握犯罪嫌疑人動向,精確打擊。而反觀我國,由于歷史現實原因,人口基數龐大,改革開放以來人口流動性增加,警務人員業務素質低下、資源匱乏等導致我國在人口控制方面很多工作并不完善。另外,從立法角度對證人保護力度的不夠導致證人對于案件偵破所作貢獻也日益減小,證人補償機制的缺失,證人的數量和質量也大大受到影響。
我國的現實原因導致在刑事訴訟當中,警方不能夠作出取保候審的決定,所以,對于犯罪嫌疑人互換利益通道的不暢通,導致警方口供獲取便是難上加難,反而還會造成警察失信的負面影響,導致犯罪嫌疑人不愿與警方合作。
三、我國刑訊逼供立法現狀
從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原則角度來講,我國在2012年3月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新《刑訴修訂案》中50條明確指出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該原則就是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原則在立法方面的體現,但是,并不是不允許犯罪嫌疑人陳述自己有罪,而是不得強迫,反之,強迫錄取口供的行為應當認定為非法證據,通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來認定。那么,在這個過程當中次就涉及到強迫自證其罪獲取口供的認定,即刑訊逼供。依據“兩高”對刑訊逼供的解釋,刑訊逼供的定義是:通過暴力行為逼迫當事人承認非意愿的陳述,而且造成當事人精神或者肉體上的痛苦的審訊方式。我認為,在“兩高”解釋中其中部分事實認定在實際操作當中有困難,其一是對定義當中暴力行為逼迫當事人承認非意愿陳述的辯護,刑訊逼供的實施主體可以通過實施暴力行為但未達到迫使當事人陳述非意愿供詞程度而進行辯解,無法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導致被告人的人權受到侵害,合法權益受到侵害;
二是在定義當中造成精神或肉體上的痛苦,意義不明,采用一個什么樣的標準來衡量這種痛苦,不同人群的耐受程度不一樣,不能采用特殊情況和一般情況來判別,而在現實刑事偵查案件偵破中,這一點在實際操作時還有很大的疑問,關于痛苦的劇烈程度的判別,在犯罪嫌疑人的耐受程度低于常人時,人權保障功能才能完全凸顯出來。
四、改善我國刑訊逼供難題方法探索
綜上所述我認為有以下幾個途徑來改善當前法制環境下刑訊逼供的生存土壤,探索解決中國式刑訊逼供難題意見如下:
(一)增加其他證據形式的認可與獲取,對口供的畸形依賴,不僅不利于案件偵破,也不利于人權保障,還對法制大環境增加負面輿論,所以,首先要做的就是降低口供的依賴程度,引導其他證據充分參與訴訟。
(二)更新新的訊問手段和方法,加大理論研究,方法創新,培養人才,在平衡保障人權與獲取口供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提升偵查人員素質和業務能力,強化對人權問題的重視。
(三)加大對辦案資源的投入,基層是辦理案件的一線陣地,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來提高效率,減少發揮主觀能動性在破案當中的作用,提高科技手段在偵破案件當中的比重,用科學的方法辦理案件增強說服力。
(四)健全被告人的法律制度保護,積極探索舉證責任倒置、偵押分離等,并且把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律師在場制度落到實處。
(五)加大違法違規懲治力度,對刑訊逼供行為啟動問責程序,完善監察機制,把“誰辦案誰負責”落到實處,切實做到錯案追究,有案可查。對于上級授意 包庇刑訊逼供陽奉陰違的,嚴格查處,須承擔連帶責任。
五、結語
刑訊逼供是中國封建社會千年來的頑疾,有其形成發展的歷史慣性和人文環境,先入為主的思想占據了大多數中國人的思想,尤其在當前警察文化層次并不高的國情下,短期內解決問題已然不現實,但是通過對一些具體問題的分析來糾正當前警務工作的一些不足之處,修正錯誤的方法和概念,既有利于貫徹落實全面依法治國大方針,也對充分保障人權有現實意義。
[1]吳紀奎.口供供需失衡與刑訊逼供[J].政法論壇,2010.
[2]肖治.論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原則在我國立法中的不足[J].法制博覽,2016.5.
[3]楊希奇.論“兩高”司法解釋下“刑訊逼供”的釋義與認定[J].法治與社會,2016.4.
[4]趙秉志,彭新林.遏制刑訊逼供的域外法治經驗及其啟示[J].江海學刊,2015.1.
D925.2
A
2095-4379-(2016)25-0201-02
楊尚林(1994-),男,漢族,內蒙古巴彥淖爾人,西北政法大學公安學院,2014級偵查學專業本科生,研究方向:刑事偵查;林翠(1995-),女,漢族,河南信陽人,西北政法大學公安學院,2014級刑事科學技術專業本科生,研究方向:刑事科學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