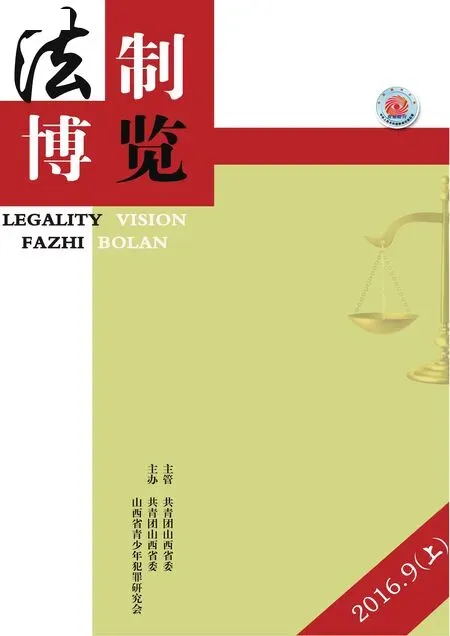法律判斷形成模式
張婧婷
青島大學,山東 青島 266071
?
法律判斷形成模式
張婧婷
青島大學,山東青島266071
法律判斷是法律人在解決糾紛過程中,對客觀事實上升為法律事實再與法律規范對比后運用法律發現、法律推理、法律論證作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結論性判斷。根據法律應用是取決于法律發現還是法律適用,我們可總結出兩種判斷形成模式,即通過司法三段論進行法律推理的推論模式和通過類比在事實與規范之間進行等置的等置模式。但二者在處理一些案件時均會有些弊端,如事實與規范不適應時,應進行漏洞補充和法律解釋來形成最終的法律判斷。
法律判斷;結論性判斷;等置模式;漏洞補充;法律解釋;司法三段論
法律人在應用法律過程中如何形成法律判斷,影響著法律判斷的形成事實與規范是否統一、相符,這均是值得探討的問題。目前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均對法律判斷形成的方法研究日盛,但是選擇何種的法律方法,各種法律方法之間的關系,以及怎樣搭配使用這些法律方法,均在較大程度上依賴于法律判斷形成的模式。
一、法律判斷的概念
法律判斷是法律人在解決糾紛過程中,對客觀事實上升為法律事實后,再與法律規范對比后運用法律發現、法律推理、法律論證作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結論性判斷。
這種結論性判斷在不同的法律部門它體現的形式不盡相同。比如在法院表現為判決書或裁定書;在檢察院表現為起訴書或決定書等等。
在法律判斷形成過程中對客觀事實、法律事實的判斷;選擇何種法律規范的判斷交織在一起,法律發現、法律推理為簡單法律判斷的形成起著關鍵作用,而對復雜的法律判斷還需要法律解釋、法律論證等不同的法律方法來實現。
二、法律判斷如何形成
法律人在應用法律過程中如何形成法律判斷,實際上有復雜的法律思維過程,比如法官如何裁判案件,如何選擇適用法律,在選擇適用法律過程中適用何種法律方法。根據適用法律方法的不同,針對法律判斷的形成,可總結出不同的判斷形成模式。
(一)通過司法三段論進行法律推理的推論模式
法律推理是司法過程中必須應用的一種方法。王晨光教授曾說:法律推理是人們解決具體問題和糾紛的過程中,適用法律規范,查證事實情況和為做出具有說服力的法律結論所進行的合乎邏輯和情理的思維活動。真正的法律推理就是以法律作為大前提,以事實作為小前提的司法三段論推理的過程,即為推論模式。
美國的一些法官說:“我們總能看到法官推理。法官推理首先要決定法律規則是什么,其次決定與規則有關的事實,第三將法律適用于事實。做出這樣的決定是法官每天工作的一部分。”
但是判決僅僅是把事實和規范分別作為大前提和小前提,通過三段論合乎邏輯地導出必然結論的審判制度——這一理念,在今天的社會常識里已經不過是一種神話而已。因為作為小前提的事實或案件,絕大部分不可能是精確依法律地發生,尤其是違法者不可能按照法律從事違法行為。面對這些情況,推論模式則變得無能為力,因為演繹的三段論不能帶來什么新的認識,也就不能解決大前提未明確指向或未涵蓋的新問題。
既然通過司法三段論進行法律推理的推論模式已經無法滿足法律人判案的需求,那何種方式能夠帶來改進呢?
(二)通過類比在事實與規范之間進行等置的等置模式
法官在做出判決的過程中,并不只是邏輯推理的機器,而是需要運用一定的法律思維。在法律思維的幾種模式中,以演繹方式進行的三段論方法缺少對事實與規范之間聯系的必要重視,排斥了規范與事實之間的辯證聯系;而循環理解的等置模式雖然克服了三段論模式的單向度弊端,但依然可能受判斷者對結果選擇的影響,為“假推論”提供合法的外衣。唯有結合探求行為者意圖的等置模式,才不會使法官停留在其屬意的規范與事實當中,才是有效的和法官應有的法律思維方式。
因而我們需要選擇通過類比在事實與規范之間進行等置的等置模式。
但是我們并不是像從樹上摘取成熟的果子那樣“摘取”成熟的法律規則,假設所有的法律判斷都可用等置來解決,那我們就不需要培養法官、律師等專門的法律人。比如當規范與事實之間不適應時我們應該如何做出正確的法律判斷呢?
三、規范與事實不適應如何做出正確的法律判斷
在法律發現中,我們要想形成法律判斷,首先應有一個等置過程,用它來解決法律判斷的大前提與小前提之間相適應的問題。它也需要確定事實行為,事實查清后,就要進入尋找法律規范。尋找的結果有三種可能性:有相適應的規范;無相適應的規范,出現了法律漏洞;再者規范不明確,如何做出正確的法律判斷。
(一)漏洞補充
現實生活極為紛繁復雜,新問題、新矛盾成出不窮,由于法律還不完善,勢必產生許多法律上沒有規定的案件。事實查清了、認定了,而規范、準繩卻找不到;邏輯推論的小前提有了,卻沒有了大前提,這樣難道就不做出法律判斷了,法官就不判案件了?這個問題世界各國法律中都有明確規定,法官不得以沒有法律規定為由拒絕裁判案件。面對法律的空缺和漏洞,法官的任務就是就是設法補上漏洞。按照梁慧星教授的說法,包括習慣補充、類推適用、目的性擴張、目的性限縮、反對解釋、比較法的補充、直接適用誠信原則、和直接創設法律規范等。但進行漏洞補充時,仍需尊重立法者的權威,進行法律內的漏洞補充,而不是進行真正的立法。
(二)法律解釋
法律都要進行解釋,法律不經解釋不能適用。法律解釋直接關系到法律適用的正確性。形成法律判斷的過程中,事實可能影響主體對法律的認識,而法律也會影響主體對事實的認識,這一過程牽涉解釋主體與事實、解釋主體與法律、法律與事實的互動過程。在解釋者的解釋活動中,法律判斷最終形成。
四、結語
法律判斷在法律人解決糾紛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而如何形成法律判斷,面對眾多或簡單或復雜的案件如何選擇最適用的法律判斷起著核心的作用。推論模式即是以法律作為大前提,以事實作為小前提的司法三段論推理的過程。等置模式則是結合探求行為者的意圖,通過類比在事實與規范之間進行等置的模式。這樣有利于避免法官停留在其屬意的規范與事實當中,是有效的和法官應有的法律思維方式。在事實與規范不適應時,若出現了法律漏洞情況,則進行漏洞補充;對規范不明確,則進行法律解釋,法律判斷最終形成。
[1]陳金釗.法治與法律方法[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3.
[2][美]波斯納.法理學問題[M].蘇力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576.
[3]梁慧星.民法解釋學[J].黃河口司法,2001.
[4]陳金釗.法治與法律方法[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3.
D90
A
2095-4379-(2016)25-0210-02
張婧婷(1994-),女,山東濟寧人,青島大學,會計專業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