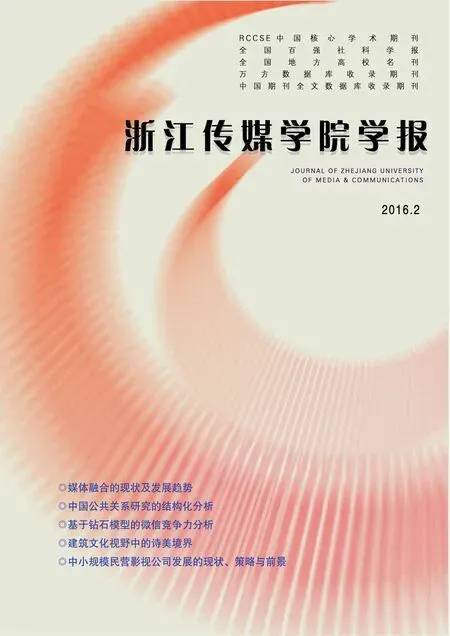《科學》雜志與近代中國科學觀念的建構及傳播
郭 靜
?
《科學》雜志與近代中國科學觀念的建構及傳播
郭靜
摘要:《科學》雜志是近代中國影響最大的科技期刊,它以“提倡科學,鼓吹實業,審定名詞,傳播知識”為宗旨,大量傳播科學知識、科學方法、科學精神等內容,致力于近代科學觀念的建構,并采用白話文、新式標點等新的傳播方式,在國內外積極推介科學觀念,對國民進行了全面的科學啟蒙。但是,《科學》雜志及其中國科學社在極力宣揚科學觀念的同時,帶有明顯的唯科學主義傾向,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當時人們思想的自由發展。
關鍵詞:《科學》;科學觀念;建構;傳播
期刊作為公開出版的大眾傳播媒介,成為人們思想傳播與交流的公共平臺,也為近代西方科學知識、科學觀念的傳入提供了最基本、最重要的傳播載體。從科學期刊的演變可以考察科學觀念在近代中國的傳播路徑。中國早期傳播西方科技知識的刊物,如《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中西聞見錄》等都是外國人創辦的以傳播宗教知識為主,同時涉及到近代科技知識的綜合性期刊。1876年出版的《格致匯編》是近代中國最早傳播科技知識的專業性期刊之一,此后相繼出現的《農學報》《算學報》《湘學新報》等,雖同為專業科學期刊,但都存在時間很短。一戰期間,任鴻雋、楊銓、趙元任等留美學生在看到科學技術對于戰爭和國家富強的重要性之后,產生了創辦科學期刊進而實現“科學救國”的理想。隨后他們通過組織人員、籌集資金,成立科學社,于1915年1月創辦《科學》雜志,從此引領中國科技期刊進入一個相對繁榮、穩定的發展時期。
《科學》以“提倡科學,鼓吹實業,審定名詞,傳播知識”為宗旨,致力于從多層次、多視角、多維度對科學知識、科學方法、科學精神等進行展示和推介,是近代中國刊行時間最長、影響力最廣、涉及科技人才最多的科學期刊。“科學至1950年為止,出了32卷,以每卷12期,每期6萬字計算,應該有3000余萬字,每期除了科學消息、科學通訊等不計算在內外,以長短論文8篇計算,應有論文3000余篇,假定平均每人作論文3篇,則有作者1000余人。”[1]“有學者從1至32卷所作的統計,則有8964篇(不含雜俎、文獻集萃、消息等短文)。”[2]為了更好地發行《科學》雜志而成立的中國科學社也是當時中國影響最大的民間學術團體,主要成員翁文灝、秉志、竺可楨、過探先、周仁、胡先骕、李四光、王琎、劉咸、侯德榜等都是近代科學的開拓者。在《科學》刊行的35年中,中國科學社與《科學》雜志一直相依相伴,中國科學社是《科學》雜志的強大后盾,不斷為《科學》提供人員支持、經濟援助和稿件支撐;《科學》為中國科學社社員提供學術展示和交流的平臺,使越來越多的學者為世人所知;《科學》及中國科學社試圖輸入西方科學知識和觀念來改變中國落后的局面,使科學融入到社會的方方面面,為人們提供了新的認識社會、參與社會的生活方式。
一、《科學》雜志與近代科學觀念的建構
《科學》創刊的1915年是中國新舊社會交替之際,國內的政治形勢和社會氛圍使得國人處于迷離惝恍、無所適從的狀態之中,甚少有學者專注學術。任鴻雋等留美學生“親睹異邦文物之盛,日知所亡,坎然其不足也。引領東顧,眷然若有懷也。”[3]此時的他們看到先進的科學技術使西方國家強盛,而自己國家卻因科技落后屢遭欺凌。認識到“世界各國生存競爭的劇烈,無論是戰爭或和平,設如沒有科學,便休想在世界上立住腳。而環顧我們國內,則科學十分幼稚,不但多數人不知道科學是什么,就連一個專講科學的雜志也沒有。”[4]于是,他們創辦了《科學》雜志,將西方先進的科技引入中國,并為國內的科學研究者提供一個交流學術成果的公共平臺,以此來推動科學觀念的傳播,進而實現“科學救國”的理想。
(一)以自然科學、應用科學為主的科學知識
晚清時期的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雖然最終以失敗告終,但是其辦西學、學習西方技術的思想為科學的傳播埋下了種子。隨著大批留學生不斷外派出國學習,這批留學回國的人成為近代中國第一批科學家的主力。近代科學家早年大多受到經世致用思想的影響,因此,在救亡圖存的關頭,紛紛選擇自然科學作為學習研究的對象,希望通過科學實現國家富強。《科學》是留美學生創辦,是其宣揚與踐行“科學救國”的主戰場,因此其主要的目光集中在自然科學、應用科學領域。
《科學》從創刊始多著力于“器物利用”方面的內容,據前人統計,《科學》的“近萬篇文章中,數量居前10位的科學領域分別是生物、化學、物理、地學、醫藥衛生、農林、科學插圖、氣象、科學通論和天文學。”[2](12-32)正好引證了《科學》在創刊號“例言”中所言“專述科學,歸以實效。玄談雖佳不錄,而科學原理之作必取。工械之小亦載,而社會政治之大不書。斷及科學不及其他。”[5]盡管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占據了《科學》的主流地位,但是其在不同時期隨著社會的發展變遷又有不同偏重。創刊之初,由于中國近代科學不發達,民眾的科學素養有限,《科學》的主要目的是普及科學常識、衛生常識,宣傳科學理論等。隨著科學的發展和國家建設的需要,《科學》逐漸向科學研究轉變。最明顯的標志是中國科學社在1922年南通年會之際把宗旨由“提倡科學,鼓吹實業,審定名詞,傳播知識”改為“聯絡同志,研究學術,共圖中國科學之發達”,學術研究成為明確關注的重點。其實,《科學》的創辦群體從創刊之始就對學術研究寄予很高期望,只是創刊之初,由于科學社成員剛剛畢業,科研能力以及國人的接受能力有限,他們大多是對西方科學的基礎常識和理論知識進行轉述和傳播,但隨著后期的積累,中國科學社逐漸開始通過自己的實踐進行自主的科學研究。中國科學社創辦的生物研究所就是符合本國國情發展的中國本土化的生物科學研究機構,這也為其他學科的發展提供了一個藍本。不管是早期對科學知識的普及,科學生活方式的推廣,還是后期對科學研究的重視,都使得科學觀念被越來越多的人們所理解和接受,推動了近代中國科學的傳播和發展。
(二)撐起科學大廈的科學方法
科學的發展關乎著國家未來的發展走向。要發展科學實現科學救國理想,首先要掌握科學的研究方法。近代以來最早介紹科學方法的是嚴復,他在《天演論》中提出了歸納和演繹的研究方法。“及觀西人名學,則見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內籀之術焉,有外籀之術焉。內籀云者,查其曲而知其全者,執其微以會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據公理以斷眾事者也,設定數以逆未然者也。”[6]“內籀之術”即歸納法,“外籀之術”即演繹法。同時提倡實驗的方法,主張“始于實測,繼以會通,而終于試驗,三者闕一,不名學也。而三者之中,則試驗為尤重”。[7]由此可見,早在晚清時期就已經有學者注意到研究方法對于科學發展的重要性。
任鴻雋把近代中國沒有產生科學的原因歸結為沒有掌握科學的研究方法:“是故吾國之無科學,第一非天之降才爾殊,第二非社會限制獨酷,一言以蔽之曰,未得研究科學之方法而已。”[8]因此,對于科學方法的普遍掌握,并廣泛而有效地利用到科學研究之中,《科學》雜志在科學方法的推介方面作出了很多努力。《科學》倡導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歸納法,并多次對歸納法進行闡釋。《科學》開篇就闡釋道:“欲救東方人馳騖空虛之病,而使其有獨立不倚、格致事物、發明真理之精神,亦唯有教以自然科學,以歸納的論理、實驗的方法,簡煉其官能,使其能得正確之智識于平昔所觀察者而已。”[8](8-13)這是針對千百年來,受儒家文化所推崇的古文經學等虛空之文的正面批駁,他們認為應該首先對一事物進行假設,再通過實驗、歸納的方法來得出正確結論。對于如何歸納,《科學》也作出了詳細的解說,首先由事實的觀察而定一假說,其次由假說演繹出結果,再以實驗考察結果的現象是否符合預期者,如果實驗符合事實,那么則代表天然事實的科學規律。這種新的研究方法對于當時的人們來說可謂是茅塞頓開,相對于古人的苦思冥想,更有說服力和操作性,也更有利于科學觀念的傳播以及“國家獨立進步”的早日實現。
除了對于科學研究自身提出的觀察、歸納法之外,任鴻雋還提出另外三點科學研究需要注意的問題,“第一欲圖科學之發達者,當以設立研究所為第一義;第二,欲一般人知科學之可貴,必使科學于人類幸福確有貢獻;第三,為科學而研究科學。”[9]任鴻雋首先認識到聚集人才,提供研究場地及設施的研究所對于科學研究最基礎最重要的作用,然后使科學回歸生活與自身,提出科學為人們服務的最終目的以及科學研究應該回歸到純粹的自身規律上,努力做到為科學而科學研究,這對于當下中國的科學研究有著很好的啟發借鑒作用。
科學的研究方法是科學取得進步的必要條件,西方由鋼鐵、汽車、電力等形成的科學世界推動了西方文明的巨大進步。就連胡適也認為,“我們也許不輕易信仰上帝的萬能了,我們卻信仰科學的方法是萬能的。”[10]科學的方法在當時特殊的背景下被認為是萬能的、不可限量的。
(三)作為科學發生泉源的科學精神
不管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還是“經世致用”,始終強調的都是“制器利用”,強調通過技術來改變世界。但是,實事求效的心態忽視了為實用技術提供泉源的科學精神,即求真、實證、實事求是地解釋世界的精神,因此,僅僅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追根溯源從根本上學習西方的科學精神,這樣才能真正掌握科學的內涵并長久發展下去。1914年發表于《留美學生季刊》上的《建立學界再論》一文就指出,“蓋學者,一以求真,一以致用。吾國隆古之學,致用既有所不周,求真復茫昧而未有見。以人類為具理性之動物,固當旁搜遠討,發未見之真理,致斯世于光明,而不當以古人所至,為之作注釋自足。故近日為學,當取科學的態度,實吾人理性中所有事,非震驚于他人成效,昧然學步已也。”[4](10)由此可見,西方的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同樣重要,不能再像以前那樣茫昧地學習知識,而是要學以致用,同時還需要學習國外的科學態度也即科學精神,從深層次傳播科學觀念。
科學精神作為科學發生的重要泉源,是科學不斷發展的不竭動力。而科學精神為何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任鴻雋于1916年對此作出過解釋,“以自然現象為研究之材料,以增進智識為指歸,故其學為理性所要求,而為向學者所當有事,初非豫知其應用之宏與收斂之巨而后為之也。夫非豫去其應用之宏與收斂之巨,而終能發揮光大以成經緯世界之大學術,其必有物焉為之亭毒而蘊釀,使之一發而不可遏,蓋可斷言。其物為何,則科學精神是。”[11]他認為科學精神是理性的,是一發不可遏的,是至死不悔地對于真理的追求。他提出科學精神最顯著的特征是崇實、貴確、察微、慎斷、存疑,進一步對科學精神進行了細致的闡釋。中國科學社成員竺可楨同樣非常注重科學精神,他把科學精神比喻成培植花種的土壤,是培養科學的空氣,“科學精神是‘只問是非不計利害’”,[12]學者們應該不計較利害得失,只追尋真理。同時他認為,“科學方法是可以隨時隨地而改換,這科學目標,蔪求真理,也就是科學的精神,是永遠不改變的。”[13]此外,梁啟超和胡適雖不是科學研究者,但同樣認為科學精神對科學發展是至關重要的,梁啟超認為,“有系統之真智識,叫做科學,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統之真智識的方法,叫做科學精神。”[14]胡適更是提出“科學精神便是尊重事實,尋找證據,證據走到那兒,我們就跟到那兒去。”[15]由此可以窺見當時人們已經意識到科學精神在科學發展中的重要地位。但是,不管何種闡釋,求真、求實、實證始終是科學精神的核心內容,是科學發展和國家富強的內在要求。
二、《科學》雜志與近代科學觀念的傳播
科學觀念的形成建立在科學技術的發展基礎上,需要一個開明、開放、平和的社會環境,一個統一、完善、功能齊全的傳播體系。《科學》在其刊行的35年間,一直努力通過新的傳播形式和廣闊的傳播路徑來對國人進行科學啟蒙,進而實現“科學救國”的理想。
(一)《科學》采用新的傳播形式
科學的傳播形式,既影響著雜志的傳播內容,又是一種科學態度的反應。中國古代和近代的自然科學落后,很大程度上是缺少一個簡單、有效的傳播系統。《科學》雜志之所以能夠成為20世紀上半葉影響最大、涉及面最廣、凝聚人才最多的綜合性科學期刊,也與其傳播形式有著密切關系。
首先,《科學》使用白話文進行書寫。《科學》創刊的1915年,正是幾千年來的封建體制剛剛覆滅,新的民主共和體制正在構建的社會轉型時期。此時,西方科學、民主觀念開始影響中國的有識之士,國家體制和國民精神的變遷歷程反映到期刊層面就是白話文的使用。民國初年的白話文,是在西學東漸的背景下,承接晚清白話余脈的同時,融入西方外來詞匯和語法,形成的新的語言書寫體系。《科學》雜志致力于向國民傳播科學知識,啟蒙大眾,開啟民智,以實現科學救國。白話文具有清晰、準確、簡明的描述和傳達信息的功能,便于普通大眾閱讀和書寫,更有利于科學觀念的接受和表達,這一特征正好契合了《科學》雜志的辦刊初衷。此外,立足當時的歷史背景,統一的現代民族國家正在努力建構之中,很多有識之士呼吁使用統一的白話文來強化認同、凝聚共識。而新文化運動風起云涌之時,《科學》使用白話文也是用行動對新文化運動給予支持與響應。因此,《科學》使用白話文進行書寫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白話文作為一種文體,它的形成和應用過程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近代中國從傳統封建社會到現代新型國家的變遷過程。
其次,《科學》采用漢字橫排排版,西式標點。報刊的版面語言具有引導和輔助讀者進行閱讀的功能。按照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在內容與形式這一對矛盾中,內容決定形式,形式必須適應于內容。形式對內容的適應不是消極的、被動的,而是在適應中對內容有巨大的反作用。這個原理同樣適用于版面語言與版面內容之間的關系。[16]《科學》作為傳播西方科學知識的刊物,在選擇橫排編排時,首先受到了西方橫排編排刊物的影響,其次也與《科學》傳播的內容有關。《科學》雜志刊行的35卷之中,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占絕大部分,為了更好地向人們傳播科學理論知識,運用橫排排版的方式更有利于人們閱讀、理解刊物中登載的大量的數字、公式、符號、圖形、插圖等。而西式標點的采用,使漢語的意思更加簡明、準確,大大提高了人們閱讀的效率,有利于提高文字的普及率和整個民族的文化水平。從傳播學視角來看,簡明、科學的傳播符號不僅有利于人們對大量知識的吸收和把握,也有利于科學的有效傳播與發展。《科學》雜志的傳播形式為近代科學期刊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樣板,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我國科學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
(二)《科學》在國內外的傳播與推介
旨在傳播近代西方先進科技的《科學》雜志的傳播范圍決定著其傳播效果是否顯著。然而,《科學》銷路的通暢與否,不僅由其內容決定,也受其銷售模式的影響。事實上,中國科學社成立之時學習西方的經營管理制度,設有經理部,專門負責刊行發售各種期刊圖書。同時,《科學》的發行機關中國科學社每年都組織科學年會以便凝聚科學人才,《科學》也隨年會的召開而逐步擴大影響。此外,中國科學社成員代表國家參與各種國際會議等學術活動也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科學》在國際上的傳播范圍。
1.《科學》的銷售
雜志的傳播范圍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刊物的影響力。《科學》創刊之后不久,其銷售范圍雖以上海為中心,但不拘泥于上海地區,內陸、香港等地也可以看到《科學》的身影,以《科學》1916年科學代售處一覽表為例,除各省的商務印書館和上海市內的各書局、圖書館、商店等代售處外,蘇州、重慶、成都、瀘州、香港等地也是《科學》覆蓋的范圍,但是此時《科學》的分售處和影響力尚有發展空間。這一時期可能因蜀地為中國科學社創辦人及社長任鴻雋的故鄉,所以《科學》能夠首先進入中國的內陸腹地,這里也許有地緣、學緣的關系存在。至1920年,《科學》的分售處擴展到奉天、武昌、濟南、北京等地;到1949年,分售處擴展到上海、南京、青島、漢口、天津、廣州、臺北、高雄、潘陽、重慶、蘭州、西安、酒泉等地,由于《科學》涉及的內容層次比較高、影響力比較大,且多刊載科學前沿內容,所以國內中等以上的學校、圖書館、學術機關、職業團體訂閱《科學》的相當普遍,《科學》在國內得到廣泛的傳播。
2.中國科學社年會的舉辦
《科學》是中國科學社的機關刊物,《科學》雜志上登載的中國科學社記事一直記錄著中國科學社的發展歷程。其中中國科學社年會便是該社每年的重要議程。中國科學社年會的創辦目的,主要是為使不同學科之間加強學術交流與信息溝通,交換研究成果,彼此啟發,促成學術進步,進而傳播科學知識,聯絡社員之間感情,凝聚科學社團力量,擴大社會影響。中國科學社自成立起一共召開過26次年會,除戰爭影響以外,基本上每年召開一次,召開的地點包括美國的恩多佛高等學校、布朗大學、康奈爾大學以及國內的杭州、南京、北京、南通、上海、青島、西安、成都、昆明等地,時間跨度大,涉及地域廣泛。
中國科學社成立后的前三年由于主創人員大多在美國,因此年會分別設在美國麻省、羅島州和紐約州。主創人員大多回到國內之后,中國科學社的選址在地理空間上從北方到南方,從沿海到內陸,遍布祖國的大江南北,中國科學社年會舉辦地的覆蓋范圍,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科學觀念傳播范圍之廣闊。1919—1933年這段時期為中國科學社單獨召開年會,年會參與人員主要是科學社社員。從1934—1948年開始舉辦科學聯合年會,因為隨著中國科學社社員的增多,部分社員紛紛創辦了獨立的專門學科學會。科學社團于20世紀30年代前后日漸形成一定規模,同時,不管是戰爭年代還是社會重建時期,都需要科學的支撐和推進;加之中國科學社作為后來很多新建科學團體的“母體”,負有與各團體合作聯絡之責。鑒于以上種種原因,中國科學社與各科學團體共同舉辦聯合年會。
中國科學社作為《科學》雜志的重要依托,其最新的研究成果、發展方向和進展基本上都刊載于《科學》雜志上,這些都為近代中國科學的學術研究提供了基本保障和運行基礎,極大地推進了中國科學的體制化建設。
3.中國科學社的“引進來”與“走出去”
20世紀上半葉,中國思想界極其活躍,中西文化交流頻繁,思想觀念變化迅速,政治跌宕起伏反而為科學提供了一個相對自由的發展環境。在這樣的歷史文化背景下,中國科學社除了對內組織召開科學年會之外,對外也引進國外著名科學家進來講學,代表國家走出去參與國際學術會議。1920年9月法國前國務總理班樂衛訪華*《科學》于第5卷第12期的第1頁上就刊登上了班樂衛的照片,并發表了《班樂衛氏關于中國教育問題之言論》的文章。,同年英國著名學者羅素來中國講學*中國科學社成員趙元任為其翻譯,羅素專門為中國科學社作了一場題為《愛因斯坦引力新說》的演講,《科學》雜志第6卷第2期還刊載了羅素的演講《物之分析》。以及1922年德國哲學家杜里舒在中國的巡回演講*1922年德國哲學家杜里舒偕同夫人乘船抵達上海,其后在上海、南京、武漢、北京、天津等地進行巡回演講,《科學》第7卷第12期,刊載了德國哲學家杜里舒于12月20日在科學社友會的演講《科學與哲學之關系》。都與《科學》雜志社密切相關。此外,《科學》雜志于1925年先后刊登刊載了《無線電學專號》《赫胥黎紀念號》等來紀念偉大的發明家。以上種種,可以看出中國科學社在“引進來”西方先進科技方面做出的努力,這些行為都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中國與國際學術界的距離,使中國的科學能夠進一步與國際接軌,也有利于西方科學知識、科學觀念的直接傳播。
中國科學社在把國外的著名科學家、先進技術“引進來”的同時,也積極地“走出去”與國際科學團體交流經驗和研究成果,開拓眼界。中國科學社代表國家在國際上參加的會議有1926年8月美國的國際植物學會,1930年9月葡萄牙的國際人類學考古學會,以及中國科學社成員任鴻雋、翁文灝、竺可楨、胡先骕、陳煥鏞等代表中國參加的1926年在日本東京召開的第三次泛太平洋科學會議。《科學》還曾于第12卷第4期專門出版“泛太平洋學術會議專號”。盡管當時中國的科技水平遠落后于世界發達國家,但是中國科學社對于發展中國科學事業的種種努力還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48年李約瑟在倫敦出版的《自然》(Nature)周刊上,“稱許《科學》可與倫敦《自然》周刊,美國《科學》周刊媲美,正如美英之科學促進協會,合中國科學社編為ABC科學促進協會,刊物亦同此相并,為科學期刊之ABC。”[17]中國科學社能夠屢次代表國家“走出去”參與國際性的學術會議,說明其在當時中國和國際科學界的地位和影響日顯,中國科學社在與國際科學界的直接互動中把科學知識、科學觀念引進來的同時,也把自己推向世界,可以看出當時科學社對于融入國際科學界所做的努力。
(三)《科學》雜志的傳播效果考察
傳播效果是考察刊物傳播有效性及影響力的重要因素,一百年前的《科學》由于年代久遠,史料和數據不足,加上筆者能力有限,因此本文所述的該雜志傳播效果,主要是考察其對當時社會所產生的作用和意義。
首先,《科學》是近代中國刊行時間最長、涉及學科最廣、影響最大的科技刊物。《科學》的內容涉及算學、生物、天文、物理、化學、工業、飛行、工程、農業、地學、衛生、經濟、礦業、科學名詞、科學教育、科學史料等多個學科與分類,同時兼有通論、插圖、記事、來件、書評、附錄等欄目,全方位地傳播科學知識,為近代中國學者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展示的平臺,對社會的影響不言而喻。此外,從《科學》雜志的發行機關中國科學社領導層組成來看,有政府官員蔡元培、熊希齡、汪兆銘、孫科等,實業家張騫、銀行家宋漢章等,著名學者梁啟超、胡適等,教育家范源濂、馬相伯等,還有大批科學研究者翁文灝、丁文江、竺可楨、侯德榜等,可見覆蓋面非常之廣,涉及人才之多,而且基本上都是當時社會頂尖的人才,所以有力地推動了近代中國科學的傳播和發展,其影響和傳播效果不容忽視。
其次,科學的影響力主要在精英知識分子,對普通民眾影響不夠。盡管《科學》的發行范圍覆蓋全國各地,但是“《科學》的銷路,自來就很有限,大概始終不超過3000份,但國內所有中等以上的學校,圖書館、學術機關、職業團體,訂閱《科學》相當普遍,而且《科學》也曾被用來與外國的學術機關交換刊物。”[1](3)《科學》的發行量雖然不算太高,但是讀者群主要是精英知識分子群體,正如熊月之所言:“學者論及西學傳播的社會影響,往往就是在知識分子精英階層中的影響,對于在一般民眾中的影響注意不夠。”[18]這與當時的社會發展水平和民眾的受教育水平有很大關系。
《科學》創刊之前,國人對科學的認識大多停留在“致用”層面,把科學當成是救國的“工具”。盡管《科學》雜志確實想通過科學知識實現“科學救國”的理想,但是卻遠不止于此。《科學》對于自然科學的普及和推廣使人們擺脫愚昧,使近代工業有了長足發展;《科學》對于科學精神、科學方法的倡導,使國人從故紙堆里解脫出來,不再僅僅專注于虛空之文,看到更加真實的世界。而觀察、歸納的科學方法培養了人們追求真理的信念,推進了近代中國學術的發展。科學不僅僅是科學救國的工具,更是一種生活態度,甚至是一種信仰。
三、《科學》雜志在近代中國的影響
《科學》雜志刊行的35年間,盡管中國科學還沒有達到西方先進國家的水平,但是《科學》通過不間斷地向國人傳播科學知識、科學精神、科學方法、科學態度等內容,對中國的科學進步和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和意義,其主張的科學觀念也在此過程中被很多人所接受。正如胡適于20世紀20年代“科玄之爭”時所說:“這三十年來,有一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有不敢公然地對他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態度。那個名詞就是‘科學’”。[19]
《科學》最大的影響是對國人進行了全面的科學啟蒙。近代以來迫于民族生存的壓力,中國逐漸開始主動學習西方,維新變法、洋務運動以及新文化運動等,經歷了一個從器物層面到制度層面轉變的過程。與之前學習西方科技的不同之處在于:《科學》向國民呈現了一個完整的科學樣本。《科學》的欄目設置包括插圖、通論、科學論壇、科學思潮、專著、科學通訊、科學咨詢、名詞審查、書報介紹、研究簡報、雜俎、調查、新聞、紀事、附錄、索引等等,不管是理論層面的科學理論知識(科學原理、科學理論、科學公式)、科學研究方法,(歸納、演繹、實驗方法)、還是器物層面的科學應用(發展國家工業與武器),抑或是制度及觀念層面的科學精神、科學建制、科學價值觀(科學的思想觀念、精神面貌、科學的運營與管理、科學的求真精神、科學的原則)等,都使中國科學的學科體系和知識體系逐漸成形,并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科學系統。《科學》內容非常廣泛,從理論到實踐、從自然到社會、從宣傳到研究,涉及領域廣、涉及人員眾多,凝聚了當時中國最具有科學素養的一批人,對幾千年來中國的科學狀況進行了總結,對國民進行了全面的科學啟蒙,也為中國未來科學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盡管《科學》雜志在20世紀上半葉的35年中取得了無可取代的輝煌成績,但《科學》雜志和中國科學社發展過程中還是暴露了很多問題。例如對科學的物用價值過多關注,對科學思想、科學精神、科學價值等內涵的傳播有所忽略,這種觀念還是經世致用思想的延續,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科學的全面發展;再如《科學》的主編人員大多身兼數職,很多人都有政府、高校,甚至企業等職務在身,對《科學》投入的精力嚴重不足;又如中國科學社年會后期慢慢變得不那么純粹了,更多地趨于形式化,年會真正的目的基本上無法實現;此外,中國科學社部分社員后期隨著其他社會事務的增多,慢慢地對科研失去了興趣,偏離了科學研究的軌道等。就《科學》自身而言,也曾出現了明顯的唯科學主義的傾向,二三十年代的科學與人生觀的論爭就是集中的反映,迷茫之中的中國人把科學當作一種信仰,認為科學萬能,科學可以救國,“毫不質疑地把科學作為一種最好的東西,并把科學方法作為尋求真理和知識的唯一方法來接受。”[20]然而,《科學》并沒有使近代中國真正實現“科學救國”的理想,一元論的科學觀念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人們思想的自由發展。
參考文獻:
[1]任鴻雋.《科學》三十五年回顧[J].科學,1951(增刊號):1-3.
[2]陳首,任元彪.《科學》的科學——對《科學》的科學啟蒙含義的考察[J].自然科學史研究,2003(22增刊):12-32.
[3]社員.發刊詞[J].科學,1915(1):3-7.
[4]樊洪業,張久春.任鴻雋文存——科學救國之夢[M].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2002:716-720.
[5]社員.例言[J].科學,1915(1):1-2.
[6]汪奠基.中國邏輯思想史(第1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09.
[7]嚴復.嚴復集(第5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6:1358.
[8]任鴻雋.說中國無科學之原因[J].科學,1915(1):8-13.
[9]任鴻雋.發展科學之又一法[J].科學,1922(6):521-524.
[10]胡適.我們對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J].現代評論,1926(4):3-11.
[11]任鴻雋.科學精神論[J].科學,1916(1):1-8.
[12]唐建光.百年清華的中國年輪[M].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11:240.
[13]竺可楨.竺可楨全集(第2卷)[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541.
[14]梁啟超.少年中國說[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89.
[15]唐德剛.胡適口述自傳[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218.
[16]繆克構.報紙版面語言探析[D].上海:復旦大學,2008.
[17]張孟聞.《科學》的前三十年[J].編輯學刊,1986(4):43-45.
[18]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6.
[19]張君勱等.科學與人生觀(一)[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9.
[20][美]郭穎頤.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1900—1950)[M].雷頤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17-18.
〔責任編輯:詹小路〕
中圖分類號:G237.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6552(2016)02-0029-08
作者簡介:郭靜,女,新聞學博士生。(安徽大學文學院,安徽合肥,230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