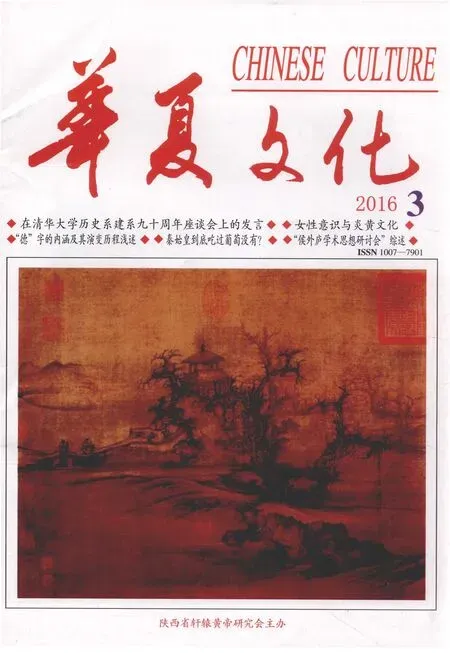“德”字的內涵及其演變歷程淺述
□ 姜海軍
·語言文化·
“德”字的內涵及其演變歷程淺述
□姜海軍
“德”字的產生,從目前的出土文獻、傳世文獻來看,最早可以追溯到商代甲骨文。由于“德”字本身是一個會意字,表示作為個體行動的目標(“道”),對個體“德”的方式、內涵有直接的規范性。可以說,“道”不同,“德”的意義也隨之不同。所以,從商周之后,歷代學者、學派對“道”的理解不同,“德”的內涵也隨之改變。
一、先秦時期“德”字的產生
在周代金文中,“德”字的構造中,又在直視前方的眼睛下面加了一個“心”字旁,變成了“”字,這樣意在強調人在實現目標(“道”)的時候,除了眼睛要直視前方之外,內心也要有這個意念在內,身心要一致。周代以后,“德”盡管多次演化,都離不開這個基本構造。如小篆為“”。由于這個“德”字有時候也寫作“惪”字,即“直心”為“德”。所以,結合周代“德”字的構型來分析,就表示個體在實現目標時,應當做到內心意念與外在行為的表里如一,進而最終實現目標(道、路)。這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周代比商代更加突出人的內心感覺、思想觀念。
周代與商代的“德”字一樣,“德”的內涵由外在的“道”所規范。這正如《禮記·樂記》云:“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又《禮記·鄉飲酒義》云:“德也者,得于身也。”周代所說的“道”,不再像商人那樣強調絕對的天命觀,而是天道、人道的合一,也就是說周人在目標的實現上,更加注重人的客觀存在性與主觀能動性,強調了對人本身的重視,對內心情感的重視。所以,周人強調在目標的實現上(或者說對“道”的遵循上),希望人們做到內心情感與外在行為的一致。換句話說,周人希望人們要敬畏上天,遵守禮制,同時將敬畏上天的觀念轉化為對人的重視(以民為本),同時要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發自真心的關愛百姓,做到“以德配天”。所以,我們看到在《尚書·周書》中,周朝統治者反復強調作為統治者要“以民為本”“以德治國”,就是強調統治者無論是外在行為,還是內心情感都要敬畏天命,遵守外在禮儀規范,以民為本,自覺維護社會政治秩序。
商周時期所形成的這種“道”決定“德”的觀念,或者“道”為“德”之體(內在根據),“德”為“道”之用(外在體現)的思想模式,對先秦各家各派的影響都非常大,比如《老子》一書共41處提到了“德”字:“上德” “玄德”“孔德”“積德”等等,這些“德”目都是對“道”的體認。如《老子》第51章就說:“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 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其中“道”和“德”的關系,就是道乃“生長萬物”,而德乃“畜養萬物”。后來《莊子》的《天地篇》也繼承了這樣的思維模式,他說:“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萬物者,道也。”并稱:“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這里的“道”與“德”基本上就是體用的關系。對此,后代很多學者也都如此認識,如韓非子云“德者,道之功也”,唐人陸德明云“德者,道之用也”,宋人蘇轍云“德者,道之見也”。當代學者陳鼓應在分析“德”的概念時也認為,它有三個意義:一是“道所顯現于物的功能”;二是“內在于萬物的道,在一切事物中表現它的屬性,亦即表現它的德”;三是“道落實到人生層面時,稱之為德”,即通常說的人的“德行”。盡管陳先生的理解沿襲了先秦道家的思維模式,但其實也是對商周對“道”、“德”關系的基本認知。由于老、莊所代表的道家,所言的“道”,具有虛無性、自然性,所以“德”的內涵便是清靜無為、返璞歸真。
不僅是道家,先秦時期影響甚大的儒家也是如此。比如《論語·述而》記載孔子的話:“子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后來朱熹在《論語集注》中對此作了解釋,他說,“據”為“執守之意”;“德”為“得”,“據于德”就是“得其道于心而不失”的意思。這里的“德”也是對“道”的一種體認、踐履。這種思維方式,其實也是周代對“德”的基本認知。只不過,與周人、道家相比,孔子儒家在繼承“道”要遵循天命、注重儀禮之外,更強調“仁”在“道”中的分量,或者說“道”即“仁”,所以孔子對“德”的理解,就不僅僅是表現為個體對禮儀的自覺遵循,還表現為個體當以愛人之心來自覺維護禮儀秩序,而非形式上的遵循,這里極大地突出了人的主觀能動性與自覺性。
總之,商代建構了“德”字的基本形態,強調了“德”乃“道”的具體展現,正如《管子》所說“德者,得也”,但這個字形強調行為結果,而沒有凸顯人們對“道”的內心感受。周代在商代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德”字,突出“德”的內心自覺、主體自覺,希望外在言行與內心情感要保持高度一致,進而實現對“道”的體認。不僅如此,周代對“道”本身的理解也異于商代,所以周代所說的“德”,并不是商代那種無條件的絕對服從,而是一種發自內心的行為自覺,這種行為主要體現為:敬畏天命、遵守禮儀、以民為本等思想。周代對“德”的進一步規范,這種思維模式不僅對先秦道家、儒家有直接的影響,就是對其他各家各派也都有直接影響。只不過,各家各派對“道”的理解不同,他們的“德”字內涵的體現也各有不同。由于“道”、“德”關系緊密,所以在戰國后期“道”、“德”這兩字連結為一個詞,不過重心則在“德”字,它是“道”的體現或踐履。
二、漢唐時期“德”的意涵
漢唐時期在社會思想方面影響最大、最深的莫過于儒學。所以,儒家學者對“道”的理解成為這一時期的主流思想,受其影響的“德”的內涵體現也成為這一時期的基本觀念。
董仲舒是漢代儒學體系的主要建立者,他作為兩漢最有影響力的儒家學者,他的觀念學說為漢朝廷所認可,并進而成為漢唐之際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董仲舒的思想,主要是繼承了孔孟儒家的思想,同時借助陰陽刑名的學說,建構了以天人感應為核心內容的思想體系——“道”。由于董仲舒的“道”有別于商周之“道”,此“道”為陰陽變化之道,陰陽天道被賦予主觀精神的品格,而與天道相應的人道,是效法天道而建立;陰陽之義下的三綱五常的中和乃是天道的自然體現。所以,董仲舒所強調的“德”的內涵便是:人們包括統治階層對三綱五常的自覺遵守,促使社會進入陰陽調和的中和狀態,這也是最大的“德”,如其所謂:“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達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興盛,以何晏、王弼所代表的玄學派學者,以老莊道家學說解讀儒家經典,認為“道”為“無所有”,“夫道者,惟無所有者也”,也就是說世界的本體“道”就是“無”,“無”就是“道”:“夫道之而無語,名之而無名,視之而無形,聽之而無聲,則道之全焉。”(《列子·天瑞》張湛注引何晏《道論》)他們甚至認為“道同自然”。如王弼解釋孔子“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時云:“故則天成化,道同自然,不私其子而君其臣。”(《論語釋疑》)道同自然,實則是將天道貫徹于人道,強調自然無為的治國理念、無為而為的做人態度。所以,作為“德”的內涵深受“道同自然”觀念的影響,如王弼所說:“何以得德?由乎道也。何以盡德?以無為用。”(《老子道德經注》)意思是說,人之“德”當以“道”為體,以“無”為用,摒棄儒家的綱常名教、仁義道德,無所作為即可。王弼之后的著名玄學家郭象也有這樣的觀念,他對“德”的內涵做了進一步的發展:“不為此為,而此為自為,乃天道;不為此言,而此言自言,乃真德。”(《莊子·天地》注)“絕操行,忘名利,從容吹累,遺我忘彼,若斯而已矣”(《莊子·駢拇》注)簡單一點講,郭象更加強調說“道”就是自然無為,客觀存在;“真德”也就是不用言語表達而自明的,道、德皆屬自然。他的“德”講具體一點就是:要忘卻名利,沒有要求,達到物我合一、自然而然的境界。
隋唐時期,盡管儒學依舊是官方意識形態,但佛學的發展此時達到了頂峰,其影響也甚大。當時儒家的“道”強調天人感應與三綱五常,人的“德”則注重秉承三綱五常,順應社會秩序。而此時的佛教也講“道”,他們的“道”與玄學所說的“無”頗為近似,即強調“空”,而事物與事物之間的關聯或者說因果報應造就“道”的客觀存在。所謂:“道者通也,以如此因,得如此果,以如是果,酬如是因。通因至果,通果酬因,故名為道。”由于事物之間的作用缺乏恒定性,所以在他們看來萬物皆空、萬法皆空,所以佛教認為人所秉承的“德”的內涵便是:“無所住而生其心”“心不住即通流,住即被縛”,即要求人們心不要固執于偏見,不要有空與有、色與無色、生與滅等的分別,不要執著于名利欲念,甚至不拘泥于佛所說的一切法,總之一切都不要執著,不拘泥,這樣才能實現對“道”的體認,或曰成佛,這樣才可謂是“至德”。佛教對“德”的規定,較玄學走得更遠,極力淡化人與社會的關聯性或曰“德”的社會性。
總之,漢唐時期,一方面是占主導地位的、董仲舒所倡導的天人感應學說,而“德”則是天道貫徹下的人道,可以說他對“德”的界定,就是要求人們對天意展現的三綱五常進行無條件遵守,正如賈誼所說“德之有也,以道為本,故曰‘道者,德之本也’”(《新書·道德說》)。由于董仲舒對“道”、“德”的規范需要強大的中央集權的支持,所以漢代滅亡之后,儒家帶有強制性的道德約束,為自然無為的玄學替代。以至于玄學盛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德”的內涵多具有自然無為、物我合一的宗教意味。由于玄學的盛行,促使了佛教在中古時期的興盛,佛教比玄學走的更遠,他們干脆摒棄人們對一切綱常名教、人倫道德的遵守,希望禪定修心,從而實現對“道”的體認,或曰成佛。當然,玄學、佛學這種極端“德”性,最終隨著安史之亂的爆發、社會危機的出現,促使人們尤其是韓愈、柳宗元等有志之士開始反思以往玄學、佛學之“德”的弊端,開始強調儒家“德”的重要性,這為宋代理學的建構奠定了思想基礎。
三、宋代以后“德”之內涵
按照日本學者內藤湖南的觀點,宋清之際屬于中國的近世,在學術思想上基本上屬于理學的世界。所以,在“道”的理解與詮釋上,學者們所言多屬于理學化范疇。其中,最有名的當屬二程、朱熹。
在二程看來,“道”乃是萬物的根本所在,它的特征在于客觀性、永久性。二程對“道”的理解汲取了很多佛教、道教的思想,為了有別于佛老之學的“道”,他們以“理”或“天理”來替代前人盛言的“道”。“道”即“理”,它是人倫道德、綱常名教的根源所在,正如程頤所說:“道之大本如何求?某告之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于此五者上行樂處便是”(《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這樣可以看出,二程所言的“道”與玄學、佛學的“道”截然不同,盡管他們汲取了佛老之學對“道”的詮釋思維方式,強調“道”的神圣性、永恒性、普遍性,但卻認為“道”的內涵乃是集宇宙本體、自然規律、人倫道德、綱常名教為一體的核心范疇。后來,朱熹在二程的基礎上,又吸收了張載、邵雍等人的思想,進一步豐富、完善了“道”的論證,認為“道”是至上的存在、自然而然,但是它是宇宙人生、綱常名教、人倫道德等一起存在的內在依據,這樣一來“道”的內涵具備了綱常名教、人倫道德的基本特征,所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也”(《論語集注·述而》)。
正是由于“道”乃綱常名教、人倫道德根本所在,這就突出了“德”存在的客觀性、必然性。所以,二程、朱熹等人都認為人的“德”應當無條件而且應當自覺遵守“道”的規定性,其內涵的便是:一方面要從《四書》入手,學習并掌握《五經》及有關綱常名教、人倫道德方面的基本知識;另一方面還要不斷地反省自我,提升自己在自覺踐履儒家綱常名教、人倫道德方面的境界。如其所謂學者當“道問學”、“尊德性”,進而成就圣人德行。
隨后的理學各派發表了不同的觀點,像浙東學派強調經世致用,強調“道”非“天理”,而是五經所蘊含的綱常名教、禮儀規范、治國方法等等,而“德”的內涵自然不是道德修行、內心反省,而是強調對禮儀、農田、水利、軍事等具體治國能力的掌握。像陸九淵、楊簡、王陽明等人則強調“道”乃“心”,心中有道、心外無道的觀念。“德”的內涵就是:不是看一個人的行為好壞,而是在于一個人的內心是否合乎“道”,突出強調“德”的內省、體悟特征,而非外在學習禮儀、社會實踐。盡管從宋代之后有很多的學者、學派闡釋自己的“道”與“德”,但影響最大的莫過于程朱理學,而且程朱理學被視為官方學說一直到清末,其對“道”“德”的規定影響了中國后期長達700多年的歷史。
進入近代之后,隨著西方思想的日漸滲透,中國古代一直占主導地位的儒家道德觀念開始受到西學的沖擊,“道德”作為一個詞,也漸漸失去了“道”的規定性,而側重強調“德”的意味,而“德”的內涵也較以往有了本質的區別。這一時期,中國的社會精英如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人開始提出一些帶有西方色彩的道德觀念,比如人權、人格、尊重他人、正義、自由、平等、博愛等。五四以后,傳統儒家“德”所包含的自覺踐行三綱五常、三從四德、忠孝等漸漸被人所拋棄。建國以后,“德”的內涵受到時代的影響,突出強調愛國主義、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愛公共財產等新的道德內涵。
結語
“德”在中國古代五千年的歷史中,盡管它是不同“道”的展現,但由于中國古代的“道”本身兼具天、地、人三者的內容,既對形而上的存在有系統的解說,也對形而下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有具體的論述。所以,無論“德”有何種不同,但它們都是基于個體完善,以迎合天道昭昭、人倫道德敦化、社會秩序重建的需要,以期實現天道、地道、人道的三者合一。這種具有天人合一特色的“德”,充滿了鮮明的精神性、文化性、社會性,而非單純的政治性。所以,在中國古代“德”的實現,或者說“德”對于“道”的體認,極力淡化宗教的色彩,而突出人的主體性、自覺性、生命性。從商代“德”字的產生開始,一直到宋明理學對佛老之學所言“道”與“德”的改造完成,就充分體現了這一點。正是這種傳統特征,在中國古代,形成了道德倫理至上的局面,使道德轉變為一種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前提,人對“德”的完善主要是出于自身完善、人格完善、人性完善乃至生命完善,而并非基于功利、政治之需要,這樣自然促成了社會秩序的倫理化、道德化,一切都顯得“潤物細無聲”。近代以后,隨著“道”的瓦解,“德”也隨之崩潰。盡管新的“道”始終在建設之中,但并未能形成系統,而受制于“道”的“德”自然也始終處于變動不居之中,這種變動不居反過來又進一步消解著“道”的存在。這不能不令人反思。
(作者:北京市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郵編100875)